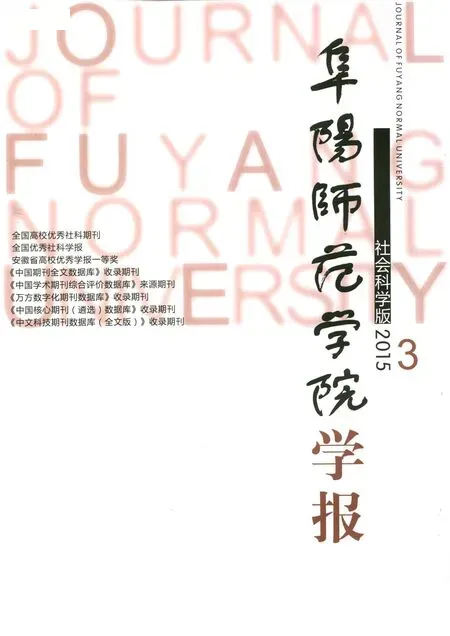“浑沌”视域中的“是非”与“秩序”
2015-04-18张新
张 新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浑沌”视域中的“是非”与“秩序”
张 新*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倏忽一章的真实意涵即暗指“浑沌之死”实乃“人之死”,浑沌与人的双重死亡才是此则寓言的深刻悲剧性所在。“浑沌之死”的内在原因及其深刻的哲学意涵,需从互摄互涵、深度关涉的两个向度进行解读,即认知意义上是非观的解构与政治维度上秩序观的溯源。庄子所刻画出的层层下坠的是非价值链与层层堕落的历史秩序观实乃揭示由于天人本真关系的疏离而造成的严重后果。是非观的解构与秩序观的溯源乃是为了解蔽天人之间的原始本真关系,奠基于此基础之上健康的主体性的生成与健全的天下秩序的建构,才是致思的必然选择。
庄子;浑沌;是非;秩序;天;人
《庄子》内七篇的第七篇《应帝王》,以南、北二帝倏与忽因谋报浑沌之德而为其“七日凿七窍”从而导致浑沌死亡终结全篇。憨山大师认为:“此倏忽一章,不独结《应帝王》一篇,其实总结内七篇之大意。”[1]149即“倏忽一章”融贯并完结内七篇之意旨,其重要性可见一斑。然而,历来解庄诸家于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以认知意义上是非观的解构与政治维度上秩序观的溯源作为基本切入点,以期揭橥“浑沌之死”的内在原因及其深刻的哲学意涵。
一、致思“浑沌之死”的双重向度
关于浑沌之死的完整表述如下:
南海之帝为 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 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 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应帝王》)
庄子采取其最擅长的寓言而非论证性的逻辑推理言说“浑沌之死”,其表达效果远非后者所能及。而庄子之所以采用寓言这种言说方式,实乃有着深刻的考量。作为“内外杂篇之序例”[2]246的《寓言》篇指出,《庄子》一书“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在寓言、重言、卮言三种言说方式中,庄子最重寓言,原因在于采取寓言的形式可以避免“言出于己,俗多不受”[3]494的弊病,从而过滤掉读庄者主观意义上的解释学偏见。在这则寓言中,共关涉四个表达意象:儵、忽、浑沌以及“人”,其中,浑沌与人则是此寓言的核心意象。就上述四意象的关联而言,涉及前后相递的三个不同层面:儵、忽因感恩浑沌“待之甚善”而“谋报浑沌之德”,其谋报方式乃是为“无面目”的浑沌开凿七窍,结果便是浑沌因生成了人所具有的七窍而死。其悲剧性结局暗示了寓言本身所要传达的儵、忽与浑沌之间的内在张力乃至矛盾,而对其原因的追问必然指向倏、忽对浑沌的谋报方式——为浑沌开凿七窍从而让浑沌成为人。因此,儵、忽与浑沌之间的紧张究其实质而言就是“浑沌”与“人”的冲突。
那么,该如何理解这种冲突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评判人之七窍的功能。所谓七窍,即双目、两耳、一口、两鼻孔;其功能分别对应庄子所谓“视听食息”,其深刻含义乃是隐喻人的感官欲望与认知功能,后者尤为庄子所强调。钟泰对该章评论道:“此承接上‘无为知主’而言,并与篇首‘不知’语意相应,欲人知而复于不知,老子所谓‘歙歙为天下浑其心’者,故设为浑沌之凿,以示其鉴戒焉。‘儵’与‘忽’皆喻知。”[4]180钟氏此段评论明言人之“知”乃是理解浑沌之死的“达芬奇密码”(1),并认为此章与篇首“不知”在语意上首尾呼应,其目的便是“欲人知而复于不知”。因此,“浑沌”与“人”的冲突便转换成“不知”与“知”的对立,“浑沌”的意义即是象征“不知”,而“人”的诞生便是“知”的彰显。最为关键的是:“夫浑沌死,而知亦凌乱破碎,无复统纪。则贼浑沌者,亦即所以自贼其知。”[4]180所以,主体之“知”的彰显导致了浑沌的死亡,而浑沌的死亡进而导致人之“知”的凌乱无序。儵忽一章的真实意涵即暗指“浑沌之死”实乃“人之死”,浑沌与人的双重死亡才是此则寓言的深刻悲剧性所在。
如钟泰所言,将《应帝王》的首尾两章作一意义上的关联,实能有效切中庄子的本真意图。《应帝王》篇首云:
啮缺问于王倪,四问而四不知。啮缺因跃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
啮缺四问王倪最先出现在《齐物论》,与《齐物论》偏重于解构认知意义上的是非观念不同,庄子在这里将“不知”和“知”与政治维度上的秩序观念相联结。析言之,即将前者与作为儒家理想天下秩序的有虞氏时代及其超越者泰氏时代作出了具有意义关联的对应性比照,从而彰显出庄子思想“内圣外王”的双重诉求。通常的观点往往认为庄学乃是出世之学,强调个体的“心斋”“坐忘”等心性修为而忽视外在的天下秩序问题。而这种观点已经遮蔽了庄子思想的本来面目。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指出:“《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5]3993先秦诸子虽然思想各异、主张不同,然就其思想指归而言则是“务为治”,即治理天下。可见,天下秩序问题乃先秦诸子思想诉求的普遍关切所在。事实上,首次出现“内圣外王”的《天下篇》(2)已经阐明庄子思想的核心关切。《天下》篇指出:“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内圣外王之道的遮蔽会导致“道术将为天下裂”的严重后果。这不仅是庄子所处“轴心时代”的事实描述,其中更是暗藏着叙说者的价值判断。而单就《应帝王》之题目而言,即流露出庄子思想的基本主旨。“《应帝王》,明外王也……‘应’读去声……后之解者不察,或读‘应’为平声,以为惟圣人当居帝王之位。不独失本书之旨,亦违子玄注《庄》之意矣……游与应,名异而理则一。盖游就心言,应就事言。游者理无碍,应者事无碍。合而言之,则理事无碍,时时无碍也。七篇以一‘游’字始,以一‘应’字终,前后照摄,理至玄微,不观其通,何由穷‘内圣外王’之蕴奥哉!”[4]167事实上,在《庄子》一书的叙事模式中始终存在着两种互摄互涵、深度关涉的致思向度:认知意义上是非观的解构与政治维度上秩序观的溯源。只有将两者统一起来考察,才能一窥庄子之本意,并且,就先秦诸子的终极目的而言,对后者的阐明远比前者更为关键。
二、是非观的解构与秩序观的溯源
就是非观的解构而言,涉及庄子话语世界里三个具有维特根斯坦所谓“家族相似”意义上的概念——知、是非与成心。人的七窍隐喻着主体的认知功能,不同的主体基于自身的立场必然产生多样的是非观念,而是非观念的诞生究其实质而言则是人之“成心”的凸显。“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齐物论》)然而,庄子认为这种基于自身的“成心”而产生的是非观念最终导致的后果只能是像儒墨相互诘难一样落入“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的争论怪圈。原因在于,基于“成心”而产生的是非观念缺乏客观的判断标准。庄子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质疑客观判断标准的存在从而解构是非观。(一)在人类世界中,A与B的争论就其客观标准而言始终存在着“第三者悖论”,即:假如A与B的观点不同,必然要引入C来裁断A与B之间的是非,而如果C同意A与B之间任何一方的观点,又需要引入D来评判C与A或C与B之间的是非,所以,结果只能是无限地引入“第三者”来裁断,但终究无法解决A与B之间的是非问题(3)。(二)超出人类世界而把天地万物都放在讨论的范围内,则基于人、鰌、猨猴、麋鹿等不同角度上,那么是非观念的客观标准完全陷入相对主义之中,不但“第三者悖论”的问题会更加复杂,而且会导致无法交流的沉默状态(4)。进一步追问客观标准缺乏的实质原因,在于言说者主体身份的存在,主体一旦凸显,是非必然无穷。
因此,“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秋水》)。但庄子对是非观的解构虽颇具后现代意味,但与后现代解构主义的“去本质化”立场有着实质性不同。虽然基于不同言说主体会导致是非观的相对主义立场,但庄子认为应该超越主体身份从而切实做到“以道观之”(《秋水》)。这里需要作出一个重要的分疏,是非观念存在的前提是“主-客”二分或“心-物”对待这一基本预设。“以道观之”实质上是对“主-客”二分或“心-物”对待的超越。庄子认为,“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齐物论》)。“道”与“是非”在庄子看来是严重对立的,“是非”的彰显遮蔽了“大道”本身。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庄子主张“无以人灭天”(《秋水》)。《庄子》中“道”与“天”乃是相应同的,庄子“常常好以‘天’字代替‘道’字,荀子在《解蔽篇》里便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杨倞《注》:‘天谓无为自然之道’”[6]327。而浑沌作为寓言中的意象所隐喻的乃是“天”或“道”,这三者名异而实同。浑沌与人的紧张、不知与知的对立,最终归结为“天人之辨”,而“天人之辨”在前文所述“浑沌之死”即是“人之死”的悲剧性事实下,更是凸显了天人相分背后所暗藏的天人合一、天人不二致思模式。
然而,当庄子的视域从对是非观的解构转换到对秩序观的历时性溯源时,乃是将对“天人之际”的剖析转换成“古今之变”的思索。为此,需要将作为是非观解构的经典代表《齐物论》中的一段文本与上述所引《应帝王》首章作一总体意义上的关联(5)。《齐物论》云: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
这里,庄子将人之“知”按照从古至今的时间顺序排成一个价值下坠的链条,古人的“未始有物”与今人的“是非之彰”形成鲜明对比。其中,“物”的出现是价值堕落的开端;因为,“物”的出现必然导致对物界的划分即“封”,“封”的划界必然导致“是非”的彰显。而庄子在《应帝王》中所尊崇的“泰氏”实应对应于古之人的“未始有物”,因为在泰氏那里“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从而“未始入于非人”。泰氏所代表的时代乃是不辨物我时代,因此才能“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绝于有虞之世”[3]159。与此相应,有虞氏即舜所代表的时代则已经进入“是非之域”。一个“藏”字“是非”尽显,成玄英认为:“夫舜包藏仁义要求士庶,以得百姓,未是忘怀,自合天下,故未出于是非之域。”[3]158-159用今天的术语表达即是:泰氏所代表的时代处于前主体性状态,而有虞氏所代表的时代则已经是主-客对峙、心-物二分的状态。基于庄子的视角,就价值排序而言,泰氏优于有虞氏;就时间顺序而言,泰氏先于有虞氏。故而,在价值排序上居于高位的泰氏同样在时间链条上处于前段,实际上已经暗藏着一种巧妙的转换,即前文所说:将对“天人之际”的是非观的解构悄然转换为“古今之变”的秩序观的溯源。《列御寇》中的“古之人,天而不人”这一精辟论断就是其明证(6)。而如果我们将《天运》篇与《知北游》中的两段文本放在一起进行对照,则会发现上述两种叙事模式互摄互涵、深度关涉。
老聃曰:“小子少进,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尧之治天下,使民心亲,民有为其亲杀其杀,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竞,民孕妇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谁。则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人有心而兵有顺,杀盗非杀;人自为种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骇,儒墨皆起。其作始有伦,而今乎妇女。何言哉!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其知 憯于蛎虿之尾,鲜规之兽,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犹自以为圣人,不可耻乎?其无耻也!”子贡蹴蹴然立不安。(《天运》)
知问黄帝曰:“我与若知之,彼与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黄帝曰:“彼无为谓真是也,狂屈似之,我与汝终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为也,义可亏也,礼相伪也。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故曰:‘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今已为物也,欲复归根,不亦难乎!”(《知北游》)
结合《盗跖》篇的相关论述(7),前者刻画出层层堕落的历史秩序观:古人(泰氏)—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后者则可以粗略地视为与前者相对应的时代之是非观,同样,作为治世方式的是非观同样处于层层下坠的价值链条之中:道—德—仁—义—礼。需要指出,上述历史秩序仅仅是一种观念上的真实,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事实。很明显,上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乃是儒家所标榜的道统,而“仁(德)—义—礼”则是儒家所主张的治世方法。庄子这种秩序上的溯源与是非观的解构虽然在流俗的意义上有明显的“剽剥儒墨”的意图,但笔者真正关心的是庄子所要传达出的深刻的思想观念。儒家的理想诉求就其内圣层面而言,则是通过个体的心性修为而成圣成贤,而外王方面则体现为社会秩序的礼制化建构。但是儒家内圣外王层面的双重诉求乃是建立在“是非之彰”的基础之上,庄子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因“是非之彰”而带来的“藏仁以要仁”。“藏仁以要仁”内蕴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内在紧张,尤其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造成的异化现象。“仁”作为成圣成贤的标准有其内在于主体自身的价值尺度,即“仁”构成其自身的目的。但儒家的外王诉求却内孕着将“仁”异化为工具或手段的必然性。“仁”作为目的与手段的双重特质决定了其所隐藏的内在分裂。“藏”与“要”将上述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异化展现得淋漓尽致。有虞氏的忧心忡忡为天下计,实内蕴着“包藏仁义要求士庶,以得百姓”,这与儵、忽对浑沌的“谋”与“报”前后对文、相互对照。庄子这里所指向的并非是假仁义之名而博取功名利禄的“伪君子”,这样的理解是肤浅的。庄子的深刻在于,他看到有虞氏的“藏仁以要人”与儵、忽的“谋报”就其主体自身的真实意图而言,乃是善良的、善意的,但是,正是这善良的或善意的“藏要”与“谋报”,导致了悲剧性的后果。
因此,在庄子看来,道、德、仁、义、礼之间的价值下坠链条乃是后者对前者的一步步异化,正所谓“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发人深省的是,庄子已经指明了因“是非之彰”所带来的对“道”的异化的必然性。“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请言其畛:有左,有右,有伦,有义,有分,有辩,有竞,有争,此之谓八德。”(《齐物论》)“畛”即上文所言“封”,即畛域、物界的意思。基于是非观基础之上,会对万物进行畛域的归类,从而会产生儒家所说的秩序化建构,即天、地、人、神各安其位、各守其分、和谐有序。但庄子恰恰认为以“礼”为代表的秩序化社会乃是“乱之首”。事实上,就上述价值链条而言,儒家绝不会反对道、德、仁、义、礼之间价值上的优先次序,但儒家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老庄所主张那样是后者对前者的异化,而是道德仁义礼层层下贯、互相通达。孔子一方面主张“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认为“仁”是“礼”的基础,另一方面也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认为“礼”是“仁”的保障。孟子和荀子都继承了这一致思理路,荀子更是言明:“仁、义、礼、乐,其致一也。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三者皆通,然后道也。”(《荀子·大略》)然而,庄子却并不如儒家那么乐观,他指出建立在是非观基础上的仁、义、礼一旦开启,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正所谓“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庚桑楚》)。对此,王船山指出:“故有虞氏之治,则必有武王之师;有武王之师,则必有五伯七雄之祸矣。”[2]110尧舜所代表的秩序化时代在其深处的“幽暗意识”中隐藏“大乱”的威胁,尧舜时代“利天下”内蕴着“贼天下”(8)。如此一来,也就不难理解:出于善良之意图去“谋报”的儵、忽为何凿死了浑沌?
三、天人原初本真关系的解蔽
基于上述观念,庄子主张“无以人灭天”(《秋水》)。就是非观的解构而言,庄子认为应该“吾丧我”。所谓“吾丧我”,即“丧其耦”。“偶,匹也,为身与神为匹,物与我为耦也。”[3]23“我”的诞生由于“物”的出现,心-物对待或主客二分作为是非观的观念预设是需要超越的。“丧我”即是对心-物对待进行超越,“复归于无物”,从而达到“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的“物化”状态。从秩序观的溯源来讲,即是返回到庄子笔下泰氏“一以己为牛,一以己为马”的不辨物我、心物未分的原初状态,正所谓“古之人,天而不人”。然而,庄子对天下秩序的要求无疑与老子的“小国寡民”一样充满浓重的社会乌托邦情结,泰氏时代仅仅是庄子理想社会的观念建构而已。与此相应,“吾丧我”的心性修养要求对于社会普罗大众来说亦是可望而不可即。“浑沌之死”即是“人之死”的事实已将我们逼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困境:是非的彰显所造成的对“道”的亏损、秩序的建构所蕴含的社会之悖乱,无疑要求我们超越是非、齐同物我,切实做到“无为而天下治”;然而,主体的诞生乃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事实,秩序的建构实根植于普遍的人性诉求,而伟大的轴心时代所宣示的难道不正是“人的发现”么?对物我的混同与对是非的超越是不是已经滑入荀子所批评的“蔽于天而不知人”?问题关键既不是“以人灭天”亦不是“蔽于天而不知人”,恰恰是在天人原初本真关系的基础上重建天与人的本真存在状态。
事实上,对天人关系的追问乃是先秦诸子共同的问题意识,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追问天人关系的前提乃是天与人的分离。这涉及到“轴心时代”中国观念史上最重大的事件——绝地天通。孔安国在注释《尚书·周书·吕刑》篇中的“绝地天通”时指出:“尧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言天神无有降地,地民不至于天,明不相干。”[7]539“绝地天通”的结果是天与地的隔绝、人与神的分离,其实质是天下秩序的礼制化建构与安排。然而,“绝地天通”就如同庄子笔下的泰氏时代一样并不是真实的历史存在,毋宁反映了言说者所处时代的观念事实。“这次观念事件所标志的,却是中国的形而上学在轴心时期的初步建构。中国的形而上学是在轴心时期(西周、春秋、战国)中逐步建构起来的;而这种形而上学在制度建构上的落实,便是专制秩序的建立,亦即礼制的确立。”[8]事实上,以庄子的视域观之,“绝地天通”所导致的“民神不杂”“人神异业”的天下秩序的礼制化建构恰恰是对“民神杂糅”“人神共在”的原初本真关系的异化。异化的结局便是不健康的天人关系的出现,即浑沌与人的双重死亡。“浑沌”的“不知”、“泰氏”的“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即是庄子所向往的天人之间的原初本真关系,而“人”之“七窍”、“有虞氏”的“藏仁以要人”即是对天人之间的原初本真关系的沉沦。而在天人原初本真关系的基础上重建天与人的本真生存状态就是避免上述异化与沉沦,从而真正避免天人双重死亡的悲剧。
然而,重建天人之本真生存状态绝不是简单地回复到“民神不杂”的前主体性状态,而是要真正保持主体是非观的彰显、天下秩序的建构与发挥着奠基性作用的天人原初本真状态之间的良性互动的健康关系。是非观的彰显、天下秩序的建构必须奠基于天人原初本真关系的基础之上,而在是非观彰显、天下秩序建构过程中存在着疏离天人原初本真关系的潜在风险。原因在于:是非观的彰显乃是主体性成型、固化的必然要求,天下秩序的建构更是需要一套硬性的制度规定,究其实质,即是“道”本身“道者化”或“存在”本身的“存在者化”。庄子所刻画出的层层下坠的是非价值链与层层堕落的历史秩序观就是揭示对天人本真关系的疏离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前文提及,有虞氏的“藏仁”实乃出于自己的善意,然而,其问题所在即是对“仁”的固滞化。钟泰指出:“‘藏仁’,则所谓久处者也。久处则滞矣。”[4]168而中国历史“一治一乱”的循环模式更是证明了庄子思想的深刻前瞻性。所以,庄子给我们的启示是:在“道—德—仁—义—礼”这一价值链条中,如何防止后者对前者的疏离,从而真正实现道德仁义礼之间的层层贯通、互相通达,从而有效地治愈因主体的固滞化而带来的对天人本真关系的疏离所造成的“以理杀人”之类的毒素累积。秩序的建构更是如此,其固滞化所造成的后果远比主体之是非观的固滞化危害更大。
因此,如果说,儵与忽相遇于浑沌之地乃是无可避免的、七窍的生成是必然的,那么,浑沌与人的双重死亡绝不是我们想要的结局。是非观的解构与秩序观的溯源是为了解蔽天人之间的原始本真关系,立足于此基础之上健康的主体性的生成与健全的天下秩序的建构才是致思的必然选择。
注释:
(1 )钟氏认为 儵、忽比喻“知”似乎并无严格的文本依据,但将人的“七窍”之“视听食息”理解为隐喻“知”则毫无疑议。
(2)关于《庄子》一书内、外、杂三篇之关系,历来说法各异。笔者赞同钟泰的看法,他认为:“是故欲通《庄子》,当以内七篇为本经,而以外篇、杂篇为佐训。外篇十五,杂篇十一,纵说横说,莫有能出七篇外者。而其瑕瑜纯驳,以七篇印之,则判如黑白,无所隐遁。”见钟泰《庄子发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至于《天下》篇,钟泰指出:“此篇历叙道术由全而裂之故,以及《诗》《书》、六艺之用,墨翟、禽滑 釐以至关尹、老聃之优劣,而后述己所以著书之意,与夫察士辩者之异同,盖与《论语·尧曰》之篇、《孟子·尽心篇》之末章,上追尧、舜授受之渊源,下陈孔子与孟子自己设施志趣之所在,大略相似。故自明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及王夫之《庄子解》皆以此为庄子之后序,其为庄子自作,无可疑者。”见上书,第754页。
(3)《齐物论》载: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暗,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4)《齐物论》载:啮缺问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恶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恶乎知之!”“然则物无知邪?”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尝试问乎汝:民湿寝则腰疾偏死,䲡 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 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 蝍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 猨猨狙以为雌,麋与鹿交,䲡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
(5)钟泰认为:“《天下篇》深致叹于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而此内七篇则所以反复发明内圣外王之学者也。是故《逍遥游》之辨小大,为内圣外王之学标其趣也。《齐物论》之泯是非,为内圣外王之学会其通也。《养生主》,内圣外王之学之基也。《人间世》,内圣外王之学之验也。《德充符》,则其学之成,充实而形著于外也。若是,则斯内可以圣,而外可以王矣。故以《大宗师》《应帝王》二篇终之……是故内七篇分之则七,合之则只是一篇。”见钟泰《庄子发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6)钟泰认为:“此篇多记庄子之言,且及庄子之死,自是庄子门下所作,然大义则与庄子无悖也。”见钟泰《庄子发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32页。
(7)《盗跖》篇载: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之后,以强陵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
(8)《徐无鬼》载:啮缺遇许由曰:“子将奚之?”曰:“将逃尧。”曰:“奚谓邪?”曰:“夫尧畜畜然仁,吾恐其为天下笑。后世其人与人相食与!夫民不难聚也,爱之则亲,利之则至,誉之则劝,致其所恶则散。爱利出乎仁义,捐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夫仁义之行,唯且无诚,且假乎禽贪者器。是以一人之断制利天下,譬之犹一 覕也。夫尧知贤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贼天下也。夫唯外乎贤者知之矣。”
[1]释德清.庄子内篇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王夫之.庄子解[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4.
[3]庄子注疏[M].郭象,注.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
[4]钟泰.庄子发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司马迁.史记 [M].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4.
[6]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上海:三联书店,2001.
[7]孔颖达.尚书正义[M]//十三经注疏:点校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8]黄玉顺.绝地天通——天地人神的原始本真关系的蜕变[J].哲学动态,2005,(5).
On the Truth and Order in the Vision of Hundun
ZHANG Xin
(Advanced Institute of Confucian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China)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chapter “Shu-Hu(倏忽)”is that the death of Hundun is just the death of the human. The double deaths of Hundun and the human are profound tragedy which the fable expresses. The intrinsic reason of the death of Hundun can be analyzed from two related dimensions: the deconstruction of cognitive truth and the source of social order. The falling value chains and the degenerating history orders reveal the severe result caused by the alienation between Heaven and the human. The deconstruction of truth and the source of social order are to find the original and authentic relation between the human and Heaven. Based on this, the generation of healthy subjectivit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normal international order are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thinking.
Zhuang Zi; Hundun; truth; order; Heaven; the huamn
B223.5
A
1004-4310(2015)03-0017-06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5.03.005
2015-02-22
张新(1991- ),男,山东临沂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中西哲学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