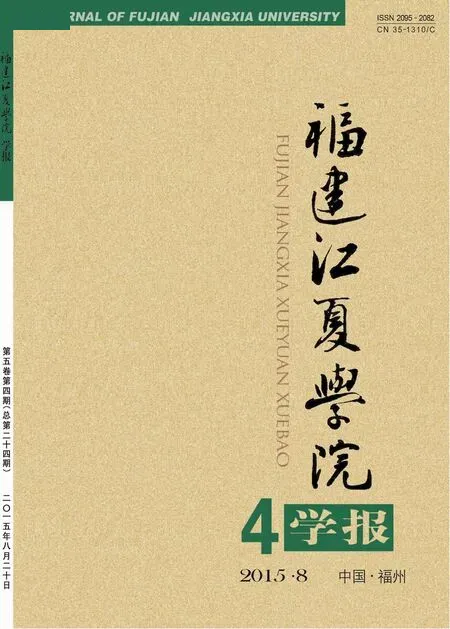朱熹孝伦理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2015-04-17蒋颖荣叶文振
蒋颖荣,叶文振
(1.云南大学哲学系,云南昆明,650091;2.福建江夏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朱熹“仁是孝之本、行孝以为仁”的伦理主张是其哲学伦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孝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对朱熹孝道思想的伦理学研究,及其对当代的启示与现实意义的研究,都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本文从朱熹孝思想的理论来源入手,着重探讨朱熹关于孝与仁之间关系的论述,以及朱熹把孝伦理转化为知行修养与道德实践的路径,最后再从个人和家庭、社会、国家的层面揭示朱熹孝伦理思想给当代社会所带来的理论启示与实践引导。
一、孝与理:孝是对理的分殊
在朱熹看来,宇宙万物都是由理与气构成的,气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材料,理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则。他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1]朱熹认为理在气之先,在世间万事万物之先。“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2]114“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先有父子之理。不成元无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将道理入在里面!”[3]这就是说,不是先有了君臣、父子之间关系,才有反映这些关系的道德观念,恰恰相反的是,先有了“君臣之理”“父子之理”,然后才有君臣、父子等人伦关系。也即君臣、父子等伦理关系就是理的体现,“如事亲当孝,事兄当弟之类,便当然之则。”[2]625在《四书或问·大学或问》中朱熹便明确指出,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常是当然之则,他说,“及于身之所接,则有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常,是皆必有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己,所谓理也。外而至于人,则人之理不异于己也;远而至于物,则物之理不异于人也;极其大,则天地之运,古今之变,不能外也;尽于小,则一尘之微,一息之顷,不能遗也。”[4]527
那么,“理”如何与万事万物发生关系呢?朱子发挥了二程“理一分殊”的理论,“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2]606他认为世间万物都各有其特殊的理,而整个宇宙则有一个总的理,这个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理先于世间万物而存在,万物不过是分有了这个理,比如,父子之理就是对“理”的“分殊”,这父子之理强调的便是父慈子孝。
朱熹以天理为本原,指出“仁包五常”“统兼四者(义、礼、智、信)”仁是天理,是本体,规约着礼义智信敬孝等道德范畴,共同调节着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人伦关系。“行仁自孝弟始。盖仁自事亲、从兄,以至亲亲、仁民,仁民、爱物,无非仁。”[2]702在《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中,朱熹明确指出,分有了“仁”这一天理的“孝”就是“善事父母为孝。”[5]48
二、孝与仁:仁是孝之本、行孝以为仁
在朱熹最为重视、也是他手定的《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论语集注·卷第一·学而第一》中,有子的原话是:“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5]47-48朱熹在注解“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两句话时说道,“务,专力也。本,犹根也。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为仁,犹曰行仁。与者,疑词,谦退不敢质言也。言君子凡事专用力于根本,根本既立,则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谓孝弟,乃是为仁之本,学者务此,则仁道自此而生也。”[5]48在朱熹把“为仁”解释为“行仁”之后,又加入了引申的解释。他引用了程子的话:“程子曰:‘孝弟,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或问:‘孝弟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何尝有孝弟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5]48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首先,有子的话中“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本来可以在“孝弟”和“仁”之间有直接的关联:“孝弟……为仁之本”。这一点从孔子本人的话,以及其学生的话语中都能找到相关的证据,比如《论语·学而第一》第六章就记载了孔子本人的原话:“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从《论语·学而第一》的第一章,开篇就讲“学”: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到第六章谈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①后来的《弟子规》就是按照这句话展开的。,这实际上是把在第一章还没有明确说出的“学”的内容和盘托出,指明“学”的基本内容和根本要求。孟子也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5]339因为“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5]339孟子直言:“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5]287朱熹的解释是,“仁主于爱,而爱莫切于事亲;义主于敬,而敬莫先于从兄。
故仁义之道,其用至广,而其不实不越于事亲从兄之间”[5]287“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无可已也,无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5]287由此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有子的话可以在“孝弟”和“仁”中间做出直接的关联,但是朱熹显然不愿意这样来理解和处理。他试图做出一种新的解释,因此他要把“为仁”解释为“行仁”,他只能承认“孝弟为为仁之本”(《四书或问·论语或问》),[4]613一定要在“为”前面再加一个“为”字或“是”字。这样一来,“孝弟”就不能直接是“仁”了,而是实践仁的根本。而“仁”此时成了“爱之理,心之德”,似乎比直接能实现的“孝弟”更为高远。这是朱熹把“仁”当作“理”“性”的思路的必然要求和自然结果。
其次,朱熹为了让自己这样的解释更加有说服力,在附加的、引申的解释中直接引用了程颐(程伊川)看起来显得有些极端的说法:“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以及“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何尝有孝弟来?”,而在这些说法的背后隐藏的是程颐、朱熹这一系特殊的想法。为了把“仁”推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他们强调“仁”以及其包含的“义、礼、智”都是“性”,而这个“性”是“理”,也即“天理”。“天理”是纯粹至善的,是没有任何不好的东西在里面的。而与此相对的则是有可能出现不好的东西的“气”或“情”,恶就是出现在“气”或者“情”这个环节里面的。如果说“仁”这个性是纯粹至善的形而上的“道”或者“体”的话,那么“孝弟”就是只能在形而下的领域内活动的“用”或者“情”。在这里,形而上和形而下的领域得到了严格的区分,而且似乎有割裂开来的倾向。他们针对这个倾向也在考虑如何在严格分开的这两个领域之间做出一个勾连,使得割裂开来的东西能够再度重新恢复起来。朱熹在《论语或问》里面也用了比较大的篇幅试图做出比较合理的解释。
三、孝与《大学》《小学》:《大学》之格物致知与《小学》孝之道德实践
在形成了“性”“理”为形而上而“情”“气”为形而下的分类框架之后,朱熹面临的首要的任务就是如何保证“存天理、灭人欲”。而他发展出来的基本方法就是“喜怒哀乐未发”时的“涵养”和“喜怒哀乐已发”时的“省察”,这也辗转成为“知”和“行”两条腿并行的修养途径。因此后来的任务就不再是先“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然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而是先要把握“理”“性”,然后再加以“行”的功夫。这样一种图景的改变,就必然使得朱熹把《大学》的重要性提得很高,放在了首要的地位。“古之圣人,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6]“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学章句序》)[7]3672在朱熹看来,复其天命之性,尽其人伦,自然就成为忠孝两全的道德高尚之人了。而为了弥补他认为当时缺乏的“小学”一段的学习,②朱熹认为,在八岁以前是学龄前教育阶段。这一阶段的教育应该从胎教开始,朱熹就胎教一事对妊娠女性的坐、立、卧的姿势以及耳目视听提出了极其严格的要求,同时也强调孩子出生后蒙学期间的施教者应符合“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的道德要求。朱熹同时也强调,女孩子学习的内容就是《女诫》这一类的女教书。他认真编写了《小学》,“后生初学,且看小学之书,那是做人底样子。”[2]272并把“孝”放在了比较重要的位置上,强调孝的道德实践。“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杆格不胜之患也。今其全书虽不可见而杂出于传记者亦多。读者往往直以古今异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无古今之异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颇搜辑以为此书,授之童蒙资其讲习,庶几有补于风化之万一云尔。”(《小学原序》)[8]393“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学章句序》)[7]3672朱熹在《小学·内篇》中讲述的内容就是“父子之亲”,他广泛引用《礼记》中《内则》《曲礼》《礼记》《士相见礼》《祭统》《祭义》《王制》中的相关内容,以及孔子、曾子和孟子的话,对于子女如何事父作了详细而又严格的规定。
敬事父母。朱熹在《小学》里强调指出敬事父母必源于内在于心的爱,必在于日常的生活起居、冬温夏清、昏定晨省,必在于忧父母之有疾、哀父母之丧。“礼记曰,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执玉,如奉盈,洞洞属属然,如弗胜,如将失之。严威俨恪,非所以事亲也。” (卷之二·内篇)[8]399所以朱熹进一步强调,敬事父母即在于爱父母之所爱、敬父母之所敬。朱熹说,“曾子曰: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是故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马尽然,而况于人乎?”[8]401“孝子之事亲,居则致其敬,夔夔齐栗。养则致其乐,乐亲之志。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严犹恭也。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8]403
以父母之心为心。在朱熹看来,孝应当是体会父母挂念自己的心情而不让父母对自己忧心忡忡,并进而指出此即“父母在,不远游”的内在本质。朱熹在《四书集注·论语集注》对孔子所说的“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注释是“远游则,去亲远而为日久,定省旷而音问疎;不惟己之思亲不置,亦恐亲之念我不忘也。游必有方,如已告云之东,则不敢更适西,欲亲必知己之所在而无忧,召己则必至而无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为心则孝矣。’” (《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5]73朱熹进一步明确“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道德依据即是以父母之心为心,在于“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朱熹说,“孔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父在,子不得自专,而志则可知。父没,然后其行可见。故观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恶,然又必能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乃见其孝,不然,则所行虽善,亦不得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虽终身无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则三年无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无改,亦谓在所当改而可以未改者耳。”(《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5]51
几谏父母,养父母之志。在朱熹看来,对父母的孝是出自本心的,应该符合于义的要求,要和颜悦色、柔声细语、不厌其烦地劝谏父母、复谏和熟谏父母,要避免父母陷于不仁不义之中。当然,在这当中,我们要注意的是,如果父母置劝谏于不顾的情况下,子女一方面要听从父母的安排,一方面还要不停地和父母讲说道理,感动父母,让父母自觉自为地改变。朱熹说,“内则曰: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熟谏。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8]401“曲礼曰,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至亲无去。志在感动之。”[8]401
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在朱熹这样编撰的《小学》中,对于“子”基本上是一种单向度的,近乎绝对的、自上而下的要求,在篇末最后一则是“孔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异罪同罚合三千条。”[8]404至于为什么要孝,以及怎样真切的唤醒在孟子那里称之为“良能”“良知”的东西,朱熹显然没有更多的涉及到,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5]353朱熹解释道,“良者,本然之善也。”[5]353就“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5]353朱熹认为,“言亲亲之敬长,虽一人之私,然达之天下无不同者,所以为仁义也。”[5]353相比于孟子的说法,朱熹那里并没有体现出“孝”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自发的情感,而是显现出一种更高的、甚至是外在的要求。这种要求由于在我们自身上没有回溯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同身受的基础上,因而显得有点像是强制性的。因此他最后才会引用那种要惩罚的刑罚来。本来“孝弟”就是活生生的在我们身上发挥作用的“天理”,实现“孝弟”的过程本身就是“天理”得以实现的过程。但是由于朱熹过于推高“天理”的地位,把“天理”在我们自身中显现和实现出来的基础和“天理”本身割裂了。他不希望那个纯粹至善的“天理”沾染我们一生下来就有的“气质”,不太放心那种本来就有的、也是应该具有的“情”,因此“天理”似乎逐渐变成了一种空洞的东西,硬生生的对我们做出各种要求。我们在这种状况下更多的是处于一种被动的、受到束缚和约束的状态,在其中,我们并没有时时地感受到实现“孝弟”本身所带来的欢乐。而且“知”和“行”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分裂。
正是针对朱熹的思路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同时代的陆九渊指责他“支离”,不像孟子那样“简易”。而到了明代,王守仁才会提出“致良知”,把实现“天理”的基础拉回到我们的“良知”或“本心”上。这才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朱熹形而上形而下分离带来的“孝”的领域出现的问题。
四、朱熹孝伦理思想的当代启示
朱熹的孝伦理思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当下,对个人的道德修为的提升与家风家教的建设、对整个社会养老模式的确立、对把“孝”父母的齐家之道延伸为“忠”国家的治国平天下之道德责任提供有力的伦理支持和重要的精神保障。
(一)有助于个人道德修为的提升与家庭中家风家教的建设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朱熹著《小学》以弥补《大学》之不足,“小学之方,洒扫应对;入孝出弟,动罔或悖。行有余力,诵诗读书;咏歌舞蹈,思罔或逾。穷理修身,斯学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内外。德崇业广,乃复其初;昔非不足,今岂有余。世远人亡,经残教弛;蒙养弗端,长益浮靡。乡无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纷拏,异言喧豗。幸兹秉彝,极天罔坠。爰辑旧闻,庶觉来裔。嗟嗟小子,敬受此书;匪我言耄,惟圣之谟。”(《小学题辞》),[8]394朱熹通过日常生活中洒扫应对的道德实践进行具体而严格的规范,从而在生活世界中的每一个枝节培养对父母的孝心孝行,这是一个教导人们如何做人、如何实践孝道的知其然之过程,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其所以然则放到《大学》追问。朱熹以《小学》作为以家庭孝道建设乃至于个人涵养、家庭和睦建设的教科书,“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讲明义礼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7]3587如何敬事父母、以父母之心为心、几谏父母的这些告诫式的外在道德约束,在人们不断重复的道德实践中逐步转化为内心的道德自觉,“习与智长,化与心成”从而成为人们行动的道德指南。人们在实践孝道的过程中,以行孝的内心自觉感动感染父母以及家人,既提升了自己的内在道德涵养,也带动了家庭整体道德水准的提升。“身修,则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于家者也;然而国之所以事君事长使众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齐于上,而教成于下也。” (《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5]9
(二)有助于全社会养老模式的确立
朱熹不断以发布榜文、创办书院的形式,在全社会提倡和推行“孝道”。在朱熹看来,敬事父母应该在对父母提供物质方面赡养的同时,孝敬父母、顺从父母、养父母之志。他强调孝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自为,强调敬事父母是每个人生命历程中的“自然之则”,是必然的道德本分和道德义务,“生则敬养之,没则哀送之,所以致其孝之诚者,无所不用其极而非虚加之也以为不。如是则无以尽乎吾心云尔。”[7]3618朱熹认为,行孝以为仁,而仁是“爱之理、心之德”(《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5]48“如爱,便是仁之发,才发出这爱来时,便事事有:第一是爱亲,其次爱兄弟,其次爱亲戚,爱故旧,推而至于仁民,皆是从这物事发出来。”[9]儒家历来提倡忠恕之道,强调爱由亲始,推己及人,泛爱众而亲仁,进而达成“此老老、长长、恤孤方是就自家身上切近处说,所谓国齐也。民兴孝、兴悌、不倍此方是就民之感发兴起处,说治国而国治之事也。缘为上行下效,捷于影响,可以见人心之所同者如此。”[2]554目前我们国家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4+2+1”的家庭结构模式已然成为国家和全社会主要的模式,局限于家庭的“养儿防老”“养老送终”的家庭养老模式已然不能满足需求,建立全社会参与的社会养老模式势在必行。作为人类内发而自然的至诚挚爱,孝是中国传统社会人伦关系得以展开的精神基础,是关于人的生命关怀,是社会共融的内在思想基础,具有超越时空的恒长性,能够为社会养劳模式的确立提供有力的伦理支持和精神保障。
(三)有助于治国平天下之道德责任的培育
如前所述,朱熹一方面指出修身的前提是格物穷理,另一方面也强调躬身践行的必要性。如此,朱熹的孝伦理思想一方面有助于提升个人的道德修养,另一方面也敦促个人以齐家治国为己任,从而能够使涵养自我以圆个人价值之梦与忠诚奉献以成就中国梦通融一体。
朱熹把《大学》的重要性提得很高,放在了首要的地位。《大学》是讲述成人的道德修养方法以及道德修养目的的。《大学》开篇即提出了三纲领,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朱熹订为“新民”),在止于至善。为实现三纲领,《大学》提出八条具体的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十分重要的环节了,所以格物、所以致知就是为了修身,“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而修身的旨趣又在于以诚意、以正心实践治国平天下的道德责任。这当中,重要的是在家庭中对父母的孝移至国家、天下从而演变为对君主和国家的忠诚奉献。这样,“孝”便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道德范畴较好地连接了个人的道德涵养与家国天下的治理,实现了体与用的统一,这一个统一,也就是个人价值之实现与国家繁荣昌盛之达成的统一。
[1] [宋]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M]//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 朱子全书(第23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2755.
[2] [宋]朱熹. 朱子语类[M]//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 朱子全书(第14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3] [宋]朱熹. 朱子语类 [M]//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 朱子全书(第17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3204.
[4] [宋]朱熹. 四书或问 [M]//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 朱子全书(第6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5] [宋]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8.
[6] [宋]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 朱子全书(第20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692.
[7] [宋]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M]//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 朱子全书(第24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8] [宋]朱熹. 小学[M]//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 朱子全书(第13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9] [宋]朱熹. 朱子语类[M]//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 朱子全书(第18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3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