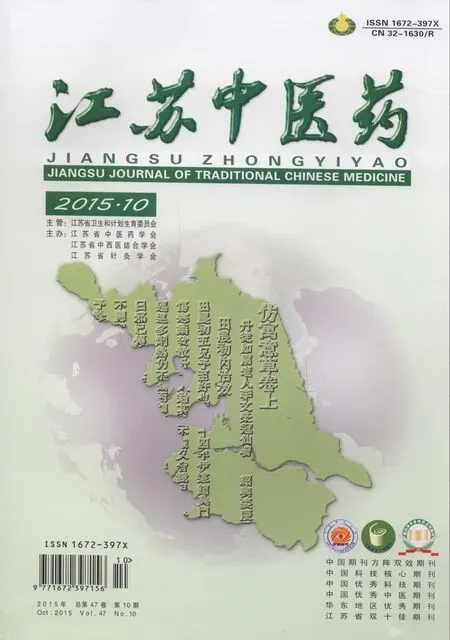浅析独重阳明思想在疫病治疗中的临床运用
2015-04-16胡慧良
胡慧良
(绍兴市柯桥区中医医院,浙江绍兴 312030)
浅析独重阳明思想在疫病治疗中的临床运用
胡慧良
(绍兴市柯桥区中医医院,浙江绍兴 312030)
几千年来中医药在各类疫病防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古籍文献中有着大量的记载和可资借鉴的技术方法。而“四时百病,胃气为本”,疫病亦然,独重阳明思想在疫病治疗中亦得到了一定应用,主要是从四个方面:顾护中州,扶正祛邪;急下存津,其治在胃;重剂石膏,清热泻火;寒温汇通,截断扭转。
独重阳明 疫病 治疗应用
从中医学的理论渊薮《黄帝内经》关于疫病的描述“疠大至,民善暴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到第一部温疫学专著《温疫论》提及“是气也,其来无时,其着无方,众人有触之者,各随其气而为诸病焉”,“疫气盛行,所患者重,最能传染”,疫病因其传染性、流行性、起病急、发展快、症状相似、治疗困难等特点备受历代医家关注,中医药在预防季节性、地方性传染性疾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古籍文献中有着大量的记载和可资借鉴的技术方法,而“四时百病,胃气为本”,疫病亦然,故笔者试从以下四个角度浅析独重阳明思想在疫病治疗中的临床运用。
1 顾护中州,扶正祛邪
《素问·五脏别论》“胃者,水谷之海,六府之大源也”、《素问·玉机真脏论》“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也”,都意在强调胃在五脏六腑中的重要性。方春平等[1]对《黄帝内经》按脏腑之气进行数据挖掘,结果显示,“胃气”出现23次,只比“肾气”少1次,在五脏六腑中排名第二。张仲景秉承《黄帝内经》“以胃气为本”之要旨,始终把顾护脾胃元气作为扶正的重要手段,把“无犯胃气”作为祛邪的前提条件,提出了“令胃气和则愈”的治则,在治法方药上善用甘草、大枣、人参、粳米等,建中州,保胃气,如《伤寒论》112方用甘草71方,用大枣39方,用人参20方,用粳米5方[2]。宋金元时期,王朝更替频繁,民族矛盾激化,战事连年,民不聊生,疫病流行,客观上促进了中医疫病学的发展。公元1232年,元兵围汴梁,城中大疫暴发,李杲亲历了这场大疫,在《内外伤辨惑论》中有详细记载,认为这是一种在脾胃虚损(饮食不节、劳役所伤、起居不时、寒温失所致胃气久亏)基础上的外感病(感而伤人)。以“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立论,用甘温除热之名方补中益气汤治疗烈性传染病,从临床实践上验证了顾护中州、扶正祛邪的确切疗效,堪称经典。
2 急下存津,其治在胃
《伤寒论》虽为东汉时期的寒疫背景而设,然观张仲景投白虎汤清桂枝汤之热化、选麻杏石甘汤开麻黄汤之热化、取葛根芩连汤折葛根汤之热化,分阶段用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大承气汤治疗腑实肠结之轻中重症,处处体现出存津液、保胃气的学术思想。至于阳明三急下、少阴三急下更体现出急下存津在疫病急危重期力挽狂澜的作用,故叶桂在总结张仲景的学术思想后提出“仲景急下存津,其治在胃”的观点。明末清初,疫病肆虐,感邪甚众,以至延门阖户,死者枕藉,吴有性认定异气是引起疫病的根源,故“邪自窍而入,未有不由窍而出”,“大凡客邪贵乎早逐”,治疗疫病以祛邪为首要目的。治法上“汗、吐、下三法,总是导引其邪……可为治法之大纲”。对于下法的阐述尤为精辟,认为“温疫可下者,约三十余证,不必悉具”,“温病下不嫌早”,明言“承气本逐邪而设,非专为结粪而设”,将大黄作为祛邪攻下的要药,取其祛邪拔毒、走而不守、润而最降、破结导滞之性祛邪务尽,“急下存津,其治在胃”之法通过以大黄为主的专药,以承气为主的专方表露无疑。
3 重剂石膏,清热泻火
回首中医疫病史,纵使时光荏苒,理法方药层出不穷,而石膏却为历代医家所倚重。《伤寒论》中含石膏的方剂只有7首,但张仲景用大剂石膏(1斤)清解阳明气分实热的白虎汤却为后世医家效法并多有发挥。隋唐时期的孙思邈在实践中意识到疫病的临床表现以热证为多,在病变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证候,也多因热毒所致,故善用石膏清热解毒,截断病势。《备急千金要方》中治疗温病阴阳毒的6个处方中,有5个使用石膏,并配栀子、大青、芒硝、玄参等解毒逐疫,并有用石膏至八两的记载。北宋庞安时,结合疫病起病急、传变快、易化热的特性,重用辛寒的石膏直折热势,苦寒、咸寒、甘寒的大青、栀子、芒硝、知母、玄参等随症辅之。其治疗温毒之五大证(青筋牵、赤脉攒、白气狸、黑骨温、黄肉随),除黄肉随证以寒水石代替石膏,其余四大证均用石膏达四两。明代缪希雍针对疫病易损伤阳明脾胃津液的特性,治疗上独重阳明,清热护津。邪在太阳,顾护阳明,先证而治;邪在阳明,重剂石膏,寒凉直折;邪在三阴,详辨寒热,不忘阳明。处方大半出入于白虎汤、竹叶石膏汤之间,其中生石膏的用量常在30g左右,重者1次量达100g,甚至有一昼夜连服近500g。[3]清代余霖在《疫疹一得》感言:“因运气而悟疫症,乃胃受外来之淫热,非石膏不足以取效耳!且医者意也。石膏乃寒水也,以寒胜热,以水克火,每每投之,百发百中”,说明重剂石膏、清热泻火的意义,创清瘟败毒饮,以石膏为君,集黄连解毒汤、白虎汤、犀角地黄汤之精华,对于火热类疫病,疗效确切,沿用至今。民国时期张锡纯亦赞石膏为“清阳明胃腑实热之圣药”,其治瘟疫之青盂汤对石膏颇为倚重。
4 寒温汇通,截断扭转
细考寒温诸家之言,缪希雍在《先醒斋医学广笔记》中认为“伤寒、瘟疫三阳证中,往往多带阳明者……凡邪气之入,必从口鼻,故兼阳明证者独多”,故常用白虎汤、竹叶石膏汤清热护津,截断病势。叶桂将胃气的盛衰作为疾病转归的重要依据,阳伤者,其重在脾,甘温建中,方如建中汤、补中益气汤等;阴伤者,其重在胃,创胃阴学说,甘平与甘凉并举,通降阳明,润养胃阴。杨璿在《伤寒瘟疫条辨》中说:“其所同者,伤寒温病皆致胃实”,善用白虎、承气类方剂清热导滞。俞肇源在《通俗伤寒论》中明确提出“伤寒证治,全藉阳明”的观点,认为“邪在太阳,须藉胃汁以汗之;邪结阳明,须藉胃汁以下之;邪郁少阳,须藉胃汁以和之。太阴以温为主,救胃阳也;厥阴以清为主,救胃阴也。由太阴湿胜而伤及肾阳者,救胃阳以护肾阳;由厥阴因风胜而伤及肾阴者,救胃阴以滋肾阴,皆不离阳明治也”,“伤寒多伤阳……温热多伤阴……扶阳滋阴,均宜侧重阳明”,把阳明胃经作为扶正祛邪的根基,将胃阴胃阳视为疾病转归的关键,治疗疫病独重阳明的思想由此而彰显。吴瑭云:“阳明如市,胃为十二经之海,诸病未有不过此者”,判定阳明经是疾病传变的必经之路。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体会到“伤寒与温病,始异而终同”,且传入阳明均属于热,治宜独重阳明。据此可见,之于疫病,各家流派泾渭分明、寒温争鸣不息、所用方药相距甚远,但抛开伤寒与温病的门户之见,阳明经恰是伤寒六经传变与温病卫气营血、三焦传变的汇通点[4],故阳明经成为截断扭转的关键。
近几年禽流感、埃博拉出血热等疫病在全球引起恐慌,对地区经济、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影响。中医因为能在西医尚无有效疫苗和药物的情况下仍可确立治则治法,并予以有效治疗,故其优势与前景引起广泛关注。而“阳明居中,主土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故在顾护中州、扶正祛邪原则的指导下,针对阳明经这个特殊靶点,急下存津、其治在胃,采用以大黄为主的下法,让承气剂直捣阳明、截断扭转,重剂石膏、清热泻火,采用以石膏为主的清法,让白虎剂成为疫病入里化热的拦路虎,从《黄帝内经》“以胃气为本”的学术思想,到张仲景“保胃气,存津液”的理论精髓,从吴有性善用大黄,孙思邈、庞安时、缪希雍、余霖、张锡纯等重用石膏的临床实践,到卫计委SARS、甲型H1N1流感、人感染H7N9禽流感的诊疗方案来看[5-7],在疫病的治疗中独重阳明是可行可法的。
[1]方春平,刘步平,朱章志.《内经》“胃气”思想概探.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4,16(5):155
[2]徐国龙.试析《伤寒论》治学思想.安徽中医学院学报,1992,11(2):2
[3]吴施国,秦竹.生石膏功效历史沿革探析.江苏中医药,2010,42(6):59
[4]胡慧良.刍议外感疫病的中医药治疗.中华中医药杂志,2015,30(3):673
[5]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诊疗方案(2004版)[EB/OL].[2005-05-25].http://www. nhfpc.gov.cn/yzygj/s3573/200804/8538589dd6e9475dab3f 77fa0f69edf0.shtml
[6]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甲型H1N1流感诊疗方案(2009年第三版)[EB/OL].[2009-10-12].http://www.nhfpc. gov.cn/yzygj/s3593g/201306/5fc4b2d158d7475fa0da32e959f 9a7ac.shtml
[7]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人感染H7N9禽流感诊疗方案(2013年第2版)[EB/OL].[2013-04-10].http://www. nhfpc.gov.cn/yzygj/s3585u/201304/7e2ad4cdf98b4e2285eab 1c15ded8370.shtml
编辑:傅如海
R254
A
1672-397X(2015)10-0009-02
胡慧良(1984—),男,医学硕士,主治中医师,从事绍派伤寒及中医临床基础的研究。707634264@qq.com
2015-0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