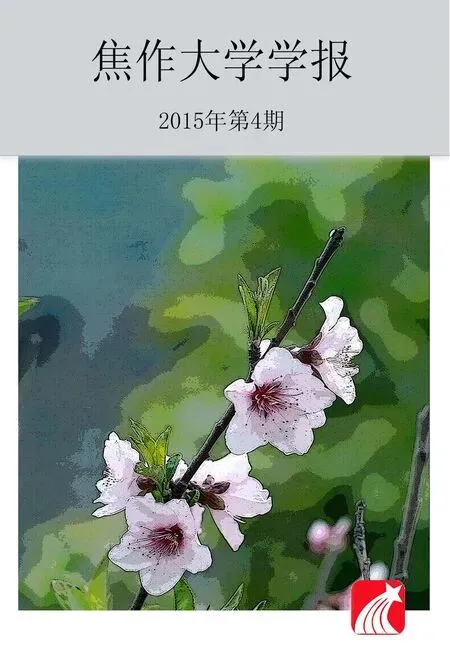浅谈劳伦斯作品中的生态思想
——以《儿子与情人》为例
2015-04-15黄丽兰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黄丽兰(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浅谈劳伦斯作品中的生态思想
——以《儿子与情人》为例
黄丽兰
(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戴维·赫伯特·劳伦斯十分关注工业文明所引发的一系列生态危机,并在其众多作品中对此进行了披露。文章试图从生态批评视角解读《儿子与情人》,通过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三个角度分别窥探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精神世界中所存在的生态失衡现象,以期进一步解读劳伦斯作品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
生态主义;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儿子与情人
工业化的进程不仅对自然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还引发了一系列存在于人际关系与个人精神世界中的生态失衡问题,因此劳伦斯毫不避讳地将工业化称为导致“现代社会退化”的罪魁祸首,同时还盛赞原始自然生态的迷人之处及其永恒的魅力所在。劳伦斯被誉为一位杰出的、富有预见性的生态主义作家。以《儿子与情人》为代表,劳伦斯生动地描绘了一系列生态失衡现象,并进一步揭露了其中的内在原因。
1.《儿子与情人》中的自然生态
自然生态是生态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本章从经过人类改造的工业化环境,未受打扰的自然生态环境以及“自然人”三个方面解读作品所呈现的自然生态。
1.1 扭曲变质的工业化环境
翻开小说,展现在读者眼前的便是一幅阴暗的画面——矿工破旧不堪的住所。作为奋战于工业化进程第一线的矿井工人们,工业化的飞速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并不是财富与幸福,而是阴郁的面庞、时刻笼罩在空气中的恶臭与随处可见的废弃煤堆。阴沉的工业化环境令往日的生机与希望消失匿迹,人们的情绪与健康都受到了极大的挫败与伤害。
不幸的是,不仅他们的居住环境破败不堪,工作环境同样不尽如人意。作为一家之主的莫瑞尔,即使已经工作多年,却依然只能终日在暗无天日、危机四伏的矿井中谋求生计;当保罗踏入社会,迎接他的也不过是狭窄陈旧的工厂,封闭的环境给保罗的健康带来了极大的隐患,迫使他成为一名“工业的囚徒”。
人类居住与工作环境是经过人为干涉与工业文明改造的自然环境,它们往往丢失了原始生态的特性而逐渐变得扭曲、变质。然而人们也因此付出了代价——工业污染使人体健康受到了严重的侵害,人类似乎也面临沦为工业文明奴隶的威胁。
1.2 治愈性的自然生态环境
除却对变质的工业化环境的不满,作品也传递着对充满魅力的原始生态环境的向往与赞美之意。不曾遭受工业文明侵蚀的自然生态似乎存在着一种魔力,将人们的身体与心灵从现代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和自然处于平衡和谐的关系之中。
小说中,置身原野、远离工业化的威利农场便是原始生态环境的杰出代表。当主人公保罗与母亲造访农场时,长期遭受工业化污染的他们深深折服于清新的自然景色,并在不知不觉间投入自然的怀抱。与威利农场首次会面,他们的赞美之情就溢于言表:
“他们找到一扇小门,很快就隐没在树林里,踏上一条宽宽的绿色通道,一边是新栽的杉树和松树。另一边是沼泽低地,那儿耸立着一株株古老的橡树。橡树间以及那一棵棵新栽的碧绿的榛树下撒满了淡黄褐色的橡树枯叶,也就在那儿长着铺天盖地的风铃草,宛若一池蓝蓝的水。 ”[1](P139)
与工业化的环境不同,这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一切都代表着新生,宁静和谐的景色在不经意间坦露着人物轻松愉悦的心境。因此,即使是保罗为母亲采来几枝花朵这样的小事,也能让他心里充满了怜爱,而她也欣喜得不能自已。
远离了现代文明的喧嚣,农场笼罩在一片和谐与宁静之中,各种动物——狗、马、鸡都有属于自己的领地,各自过着悠闲的生活,互不打扰;各种各样的植物都自由地生长,不受外界的干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互不侵犯。
接受大自然的洗礼,人们似乎摆脱了工业文明永无止境的利益纠葛,逃离了饱受工业污染的生活、工作环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所以,当保罗与母亲启程回家时,他们依然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之中,正如书中所述,“一弯细细的月牙钻了出来。他的心沉浸在幸福之中,甚至都有些隐隐作痛了。莫瑞尔太太一路上把话儿说个不停,因为她也高兴得直想哭。 ”[1](P144)
在大自然和谐的景色中,人性也得以返璞归真。在威利农场上,男孩们总带着几股野性与傲气,“他们不屑于同外人建立一般的感情及普通的友谊,而是不懈地追求一种更深一层的东西”[1](P169)。不同于工业文明熏陶下的人们固有的勾心斗角,他们生性耿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本性——“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吃什么就必须要吃到”,但是“……他们的蛮横只是表面现象。他们一旦遇到可以信赖的人,就会变得出奇的温柔和可爱”,“一旦跟他们在感情上接近,他们就会成为你亲切和贴心的朋友”[1](P170)。
此外,大自然还富有神奇的治愈能力。在小说第一章中,莫瑞尔太太与丈夫争吵过后,在院中柔和的月光中,她的心智得以舒展,与自然融为一体,“她就像花的香气一样融入了晴朗、苍白的夜色里……她与群山、百合花以及屋舍栖息在一处,所有的一切都宛若在朦胧的梦境里”[1](P28)。 在洗礼过后,莫瑞尔太太的心灵得到了宽慰,重拾了勇气,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同样,对于保罗而言,当他被世俗烦扰时,就会选择到郊外散步,借助大自然的力量寻找心灵的抚慰。
显而易见,与经过人类改造与工业文明侵蚀的环境相比,原始的自然生态环境似乎具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使人们浮躁的心灵重归平静。
1.3 “自然人”
在劳伦斯的作品中存在一类人,拥有着相似的特征——他们总是保存着童真,有意识地与工业文明保持一定的距离,永远充满单纯的活力与热情。这就是“自然人”。
在《儿子与情人》中,米莉安就是“自然人”的代表。作为一个在农场长大的女孩,虽然她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但却拥有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自觉地与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对于自然,米莉安有着自己独特的情感,与自然始终保持着微妙的联系,即使在再普通不过的植物身上,她也能捕捉到与众不同。对于自然界的东西,“她能确切地感受到它们的存在”——“鸟窝似乎一下子有了生命……觉得那鸟窝和她无比亲近”;“白屈菜就对米莉安产生了魅力”,“松树在她看来的确妙不可言,而且风格独特”[1](P170)。同样,她也能在大自然中找到情感的寄托:“她生性不合群,极少能和别人正常交往,所以只有大自然才是她的朋友、伴侣和恋人。她看到太阳在有气无力地向下沉。在昏暗、阴冷的树篱丛中有几片红叶。她放慢脚步,以一颗温柔、倾慕之心去收集那些叶子。她爱意绵绵地摩挲着红叶,内心的激情喷泄而出。 ”[1](P189)
虽然生活在工业化环境中,但保罗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视为一个“自然人”。他踏入社会后并没有放任工业文明完全占领自己的心灵,而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也即将成为一名“工业的囚徒”,下意识地与工业文明保持一定的距离。和米莉安一样,保罗与大自然也存在着情感的契合,在受世俗干扰时,他总能在大自然中找到慰藉。最后,保罗下定决心抛开支离破碎的生活、探索单纯。
对饱受人类干涉而扭曲变质的工业化环境的鞭挞,对迷人的自然生态环境的推崇,以及对单纯可爱的“自然人”的赞美,使得工业文明对自然环境的侵害与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的陶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充分传达了劳伦斯在作品中的自然生态思想。
2.《儿子与情人》中的社会生态
社会生态重点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原始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人与人之间单纯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质。受物质利益的驱使,最大限度地追求金钱与功利成为人们深信不疑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的主导因素。下面将围绕社会生态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逐渐疏远与扭曲的关系展开论述。
2.1 支离破碎的婚姻
在《儿子与情人》中,保罗父母不幸的婚姻是悲剧的导火索。莫瑞尔太太原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小姐,良好的生活环境使她理所当然地认为有了爱情的婚姻必定是幸福美满的,而忽视了经济条件——一个巨大的现实问题。但同样生于工业文明中的莫瑞尔却只是工人阶级中一名普通的矿工,必须面对资产阶级的剥削,逃离不了经济拮据的命运。工业文明中分明的阶级制度与工人阶级所遭受的无情剥削早已在他们的婚姻中种下了不幸的种子。
在短暂的幸福过后,不同的价值观念与拮据的生活条件使夫妻间的矛盾全面爆发。在爱情消失殆尽之后,莫瑞尔太太仅仅把丈夫当成赚钱的工具,即使是照顾受伤的莫瑞尔,她也仅仅把这当成一项任务,目的是维持自己的经济来源。莫瑞尔则把妻子当成自己的附属品,视为一个为自己操持家务与抚养孩子的角色。甚至在妻子弥留之际,莫瑞尔仍拒绝与妻子道别。
同住一个屋檐,夫妻却始终形同陌路,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变质,从对方身上寻求因素以满足自己的需求成为了维持关系的惟一目的与动力。
同样破碎的婚姻关系也发生在克莱拉与丈夫巴克斯特身上。因为财富,克莱拉选择与巴克斯特结婚,但他们却长期分居,各自在外面寻找情人与激情。婚姻于他们而言早已形同虚设,但为了经济关系与面子,仍然维持着变形扭曲的夫妻形式。
2.2 疏离的人际关系
除了破碎的夫妻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在小说中随处可见。以威廉与其未婚妻莉莉为例,为了满足未婚妻挥霍无度的生活,威廉以付出健康的代价超负荷地工作。终于有一天他透支了身体,被病痛折磨时,莉莉却毫不犹豫地抛弃他,留他独自一人在小房间里自生自灭。当莫瑞尔太太赶到时,房间里一片惨淡:
“威廉躺在床上,眼里布满血丝,面无血色,衣服扔得满地都是,屋里也没生火。一杯牛奶放在床边,没有一个人陪他。 ”[1](P152)
“没有一个人陪他”,这一句看似普通的话语却将人与人之间毫无人情味的疏远关系表达得淋漓尽致。没有了金钱的支撑,威廉对于莉莉来说已经毫无价值,在威廉的葬礼尚未举办的时候,莉莉已经展开她对自己下一个经济来源目标的搜索。
莫瑞尔与儿女之间同样也变得疏离。不幸福的婚姻、粗鲁的行为方式以及拮据的经济条件,使莫瑞尔与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渐行渐远,他对孩子的教育与前途漠不关心,惟一的念想竟是让孩子们成为像他一样的矿工。而对于孩子们而言,他并没有履行当父亲的责任与义务,似乎仅仅是为他们提供基本生活支柱的工具。
婚姻关系的破裂,家人关系的疏远,以及各种各样人际关系的陌生化都在阐述着同一个事实——在工业化社会中,社会生态严重失衡,人性逐渐异化,人际关系面临严峻的危机。
3.《儿子与情人》中的精神生态
作为完整生态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精神生态是存在于人类个体上的生态系统,反映出个人的精神世界。在工业化社会,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危机往往引发精神生态的失衡。
小说中保罗便承受着精神生态的失衡。莫瑞尔太太婚姻的失败和威廉的早逝,使她将所有的感情都寄托到保罗身上。终日面对母亲的束缚和近乎极端的母爱,他的精神世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虽然有时他试图通过争吵或者与其他女孩坠入爱河以逃离这种困境,但同时他必然会陷入对母亲更深的愧疚感之中,因此,保罗没有办法和其他的女孩同时建立身体与情感的联系,继而又被自责情绪左右。如此周而复始导致保罗的精神生态严重失衡。
与保罗不同,作为大自然的孩子,受自然生态滋润的米莉安拥有一个完整、独立的精神世界。她虔诚且对生活充满热情,还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保持自己的个性,拒绝迎合兄长和外界的要求。同时米莉安还具有坚定的意志,始终以忠诚之心对待爱情。在物欲横流的工业社会,她时刻保持理性,不同流合污,立志成为一名无私奉献的教师。毫无疑问,米莉安的精神世界中存在着道德、情感与理智的平衡,维持着良好的精神生态。
4.结论
工业文明下变质的工业化环境、不合理制度以及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引发了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以及精神生态中一系列的失衡问题。劳伦斯在其作品中对此进行了客观细致的披露,隐含的对比也在提醒人们:面对这样的困境,人们必须建立起生态意识,积极解决生态失衡问题,只有这样才能重建一个和谐、平衡的生态体系。因此,从生态批评视角解读劳伦斯的作品,有利于读者更深层次地解读与挖掘其生态主义思想。
[1]D.H.劳伦斯.儿子与情人[M].陈红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2]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3]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苗福光.生态批评视角下的劳伦斯[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
[5]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孔占奎)
I106.4
A
1008-7257(2015)04-0040-03
2015-03-09
黄丽兰(1990-),女,福建宁德人,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