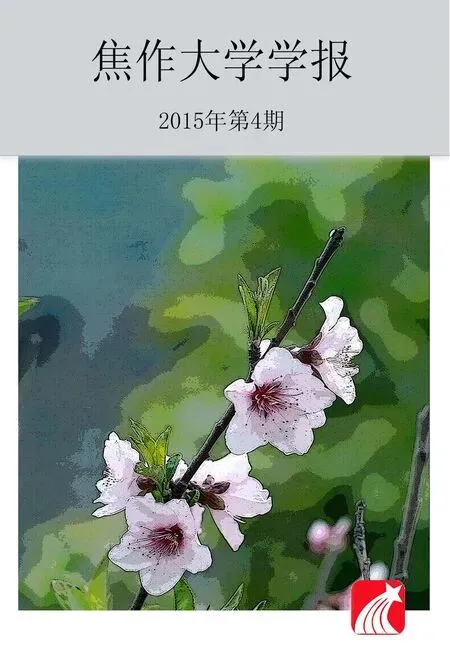园林·旅林·山林
——从《文选》诗看魏晋时期的山水书写
2015-04-15旷丹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00
旷丹(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园林·旅林·山林
——从《文选》诗看魏晋时期的山水书写
旷丹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文章拟从文本分析的角度对《文选》诗的山水书写作一番考察,主要观点有:一、古代并无山水诗的分类传统,所谓山水诗、田园诗是今人强行分派;二、《文选》中的山水书写主要集中于游宴、游览、游仙、招隐、行旅这几个诗类中,根据各个诗类中山水书写的不同手法、山水呈现的不同面貌将之分为以下三个模式:(1)游宴式的山水书写——以园林山水为书写对象,充满优游行乐的趣味,山水清丽有致,其特点是巧言切状、酷不入情;(2)行旅式的山水书写——以旅途中所见野外山水为书写对象,充溢着行路难的忧愁和羁宦之情,山水荒凉沉郁,其特点是居高临下、极目远眺式的全览概述;(3)仙隐式的山水书写——以深山幽谷的山水为书写对象,大体凭印象或想象来写。根据书写对象的差异分别概括为园林、旅林、山林。
文选;山水;宴游;行旅;仙隐
自刘勰《文心雕龙》言“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山水方滋”①,山水诗这一名目就开始被肯定、被沿用不废,后人论及山水诗产生于魏晋六朝时期多援引此语。事实上,古代诗歌并无山水诗这一分类传统。《墨子·公孟》曾有过“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②之说,这是从诗歌的实际功用方面说的。《诗经》将诗歌分为风、雅、颂,这是从音乐的角度区分的。诗歌发展到了齐梁时代,作品数量极大的丰富了,样式也繁复得多,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逐渐明晰起来,萧统《文选》立 23个诗类,这其中也没有山水一类。而且,自晋宋至隋唐以迄于清代,从未有谁给所谓的山水诗下定义,明确其含义。可见,所谓的魏晋六朝山水诗、田园诗是今人分派,古代并无此分类传统。
细细玩味 《文选》所立的23个诗类:“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燕”、“祖饯”、“咏史”、“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咏怀”、“哀伤”、“赠答”、“行旅”、“军戎”、“郊庙”、“乐府”、“挽歌”、“杂歌”、“杂诗”、“杂拟”、“骚”,我们发现基本上每一个类目都有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为依托,都有切实的依据,并不是凭空虚立的。这说明魏晋时期的诗歌写作还没能跳出具体的事件,没有从特別上升到一般的普适高度。山水,作为自然美的代表,在魏晋时期与其说是诗歌的一种类型,毋宁说是诗歌创作的原材料,越往后发展,山水的普适价值越明确。
从 《文选》诗来看,山水书写主要集中在游览、行旅、公燕、游仙、招隐、反招隐中,赠答、杂诗、杂拟中也有一些。细读文本,笔者发现各个诗类中山水书写的对象手法以及所呈现的面貌都有显著的差异,故将之分为以下三种。
1.园林
魏晋南北朝时期,造园之风盛行,不但主政者好营宫室苑囿,贵族名士亦广建庄园別业。他们建山筑楼,引水营园,或登或眺,或宴或息,不必长途远涉,即可享受山水之妙。建安以来,曹氏父子齐聚英才,他们雅集西园,“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③。曹丕《与吴质书》叙及当时游宴之乐:“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④园林宴游渐成风尚。西晋时,武帝附庸风雅,踵武西园之会,广召群臣共聚华林园,游园赋诗;石崇亦会集名流于金谷园,昼夜游宴,流连风景,吟咏赋诗。读《文选》公燕、游览两类诗可以使人充分感受到当时园林宴游之快意驰骋、优游畅适。曹丕的《芙蓉池作诗》,曹植、刘桢所作的《公燕诗》,表现重点都以“园林美景”与“优游行乐”为主,他们流连风景,享受“怜风月,狎池苑”之乐,氛围愉悦,身心畅适。请看
曹丕的《芙蓉池作诗》:
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双渠相溉灌,嘉木绕通川。卑枝拂羽盖,修条摩苍天。惊风扶轮毂,飞鸟翔我前。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鲜。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⑤
全诗大部分內容都是在描写西园的美景,清新雅致,描写细致,虽然诗人有“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之叹,却在行游西园、观览园林的经验里体会到“遨游快心意”。
曹植《公燕诗》:
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神飙接丹毂,轻辇随风移。飘摇放志意,千秋长若斯。⑥
在公宴之后,主客兴致未尽,于是飞盖相随,夜游西园,在西园丽景的游览中感受到“飘摇放志意,千秋长若斯”。
刘桢的《公燕诗》:
永日行游戏,欢乐犹未央。遗思在玄夜,相与复遨翔。辇车飞素盖,从者盈路傍。月出照园中,珍木郁苍苍。清川过石渠,流波为鱼防。芙蓉散其华,菡萏溢金塘。灵鸟宿水裔,仁兽游飞梁。华馆寄流波,豁达来风凉。生平未始闻,歌之安能详。投翰长叹息,绮丽不可忘。⑦
诗人敷容写态、捕光捉影,飞鸟游鱼自在嬉戏,芙蓉菡萏争开互映,园林山水在其笔下显得摇曳多姿、清丽雅致,历历如在目前。
从公燕和游览这两类诗作来看,诗人游览的范围仅限于贵族林苑或京城近郊,多是私家园林,并不是野外的自然山林。这种园林山水的游览与书写并不一定是避世离俗的象征,或愤世嫉俗的姿态,而是一种生活的调剂,其中充满了优游行乐的意味。由于多是侍从出游,吟诗纯属游戏性质,诗歌创作只是竞技呈才的即兴娱乐。这种模式的山水书写,刻画细膩,所占分量大,其特点在于:一是巧言切状,即用精研的语言细微地刻画,园林山水清丽有致;二是酷不入情,即纯客观的态度,诗中较少注入自己的主观感情,多着笔呈现园林山水本身的美。但这些诗作中也有些微区別,一些公燕诗作,常为应诏而作,多有颂德之词,叙写游乐时雍容有节、不渝分毫,如陆机的《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赋诗》,陆云的《大将军宴会被命作诗》,范晔的《乐游应诏诗》等,不似园林雅集时自发而作的诗作洋溢着一股纵放豪情的风流。
2.旅林
学优则仕、显耀门楣、兼善天下是士人之自我期许,然而一旦进入仕宦生涯,经常会因赴新任、去旧职、祖道、迎驾、从幸、省亲等诸多原因,跋涉于山水旷野,行旅诗由此产生。诗人面临跋涉艰辛与旅途孤寂,往往感山水而吐胸中块垒。对于在政治漩涡中寄讨生活的文士来说,行旅途中的自然山水能够豁畅胸怀,澄净心灵。例如:
潘岳的《河阳县作二首》之二:
日夕阴云起,登城望洪河。川气冒山岭,惊湍激岩阿。归雁暎兰畤,游鱼动圆波。鸣蝉厉寒音,十菊耀秋华。引领望京室,南路在伐柯。大厦缅无觌,崇芒郁嵯峨。总总都邑人,扰扰俗化讹。依水类浮萍,寄松似悬萝。朱博纠舒慢,楚风被瑯邪。曲蓬何以直?托身依丛麻。黔黎竟何尝,政成在民和。位同单父邑,愧无子贱歌。岂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⑧
潘安仁日夕登临,但见“惊湍激岩阿”、“鸣蝉厉寒音”等一派沉郁之色,引领而望,回京之路似近实遥,嵯峨芒山艰险多阻,颇有行路难的忧愁。
鲍照的《还都道中三首》之一:
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芦洲。客行惜日月,奔波不可留。侵星赴早路,毕景逐前俦。鳞鳞夕云起,猎猎晩风遒。腾沙郁黄雾,翻浪扬白鸥。登舻眺淮甸,掩泣望荆流。绝目尽平原,时见远烟浮。倏悲坐还合,俄思甚兼秋。未尝违户庭,安能千里游。谁令乏古词,贻此越乡忧。⑨
鲍明远极目远眺,行旅之辛酸、乡忧之情一齐涌上心头,笔下山水呈冷色调,“黄雾”、“白鸥”,全诗笼罩着一股凄寒之气。
陆机的《东宫作诗》:
羇旅远游宦,托身承华侧。抚剑遵铜辇,振缨尽祗肃。岁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载离多悲心,感物情凄恻。慷慨遗安愈,永叹废寝食。思乐乐难诱,曰归归未克。忧苦欲何为,缠绵胸与臆。仰瞻陵霄鸟,羡尔归飞翼。⑩
“羁旅”、“游宦”二词就出自此,诗中充盈着 “悲心”、“凄恻”、“忧苦”等悲苦之声,人在旅途,险象环生,“托身承华侧”的人生如同旅途般艰辛。
和流连光景、优游行乐式的游宴诗比起来,行旅诗中并无观览行游之乐,而是充溢着行路难的忧愁,羁旅深愁溢于言表。诗中的山水书写无模山范水的精细之功,而是居高临下、极目远眺式的全览概述,且多显荒凉、沉郁之色,不似游宴诗中清新雅致。诗中表现的由山水而引情、感物而吟志的程序是行旅诗中山水书写的普遍模式,这也恰符合萧统诗言志的选诗标准。
3.山林
由于隐士所处总离不开山林川渚,故招隐诗的內容自然有山水书写。这类诗通过自然山水的书写,极力揭示高岩幽谷环境之美,以反衬世俗官场的污浊,应该说都是山林的赞美诗了。请看
陆机的《招隐诗》:
明发心不夷,振衣聊踯躅。踯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朝采南涧藻,夕息西山足。轻条象云構,密叶成翠幄。激楚伫兰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飞泉潄鸣玉。哀音附灵波,颓响赴曾曲。至乐非有假,安事浇淳朴。富贵久难图,税驾从所欲。(11)
诗人直言与世不谐,心情郁闷,欲深入幽谷,寻访高洁隐士,藉以淡却俗情,排遣世虑。一个“欲”字表明,山林之景多半出自诗人想象。山中旷寂,不闻鼎沸人声,亦无高楼广厦,但见林木耸立,绿条垂掛,宛如隐者的华屋翠幄,清风微拂,余香袅袅,清音泠泠。仕途多舛,不如闲处林野,丘山隐逸。
左思的《招隐二首》其一:
杖策招隐士,荒途横古今。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白云停阴冈,丹葩曜阳林。石泉漱琼瑶,纤鳞或浮沈。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糇糧,幽兰间重襟。踌躇足力烦,聊欲投吾簮。(12)
左思明确表达了对隐居生活的向往。诗人是否真的入山访隐,笔者此处存疑。或为诗人想象自己入山访隐,一路行来,则见白云似雪,丹花耀采,树焕清光,流泉漱石,鸣声如玉,游鱼戏水,畅适逍遥,尘虑尽除,心神宁定。山林一派祥和,万物自在,反衬出红尘喧嚣,世俗多诈。与其追攀富贵,流连丝竹,莫如投簪弃世、聆听山水清音。
但是,事实上西晋时人们向往隐逸,大多只是一种精神寄托,并不是真的实际行动。如陆机感慨良深,常有忧生之叹,然而自负才望,志匡世难,又盼重振家风,显耀祖德,所以虽怀“丘山隐逸“之想,终究难以投簪弃世。左思之向往隐逸,也有失真之嫌,事实上,他从未自甘寂寞,依附权贵贾谧,贾谧被诛后,他一度消沉,他的《招隐诗》不是真要学许由去归隐,而是借以抒发仕途失意的苦闷。因此,笔者认为,隐逸诗中的山水书写,大体是凭印象或想象来写的,或是按照自己对山水的审美经验来虚拟创造,山水多深幽清美。
同样地,追求仙道的人,要到深山炼丹采药,他们的生活也像隐者一样离不开深山密林、高岩幽谷,因此游仙诗中自然也有山水的书写。在求仙、采药的过程中,顺便游览山水是及其自然的。诗人若以求仙、采药的经验入诗,其所见的名山大川就会成为书写的对象。可是,诗人如果执着于山水为求仙之所、神仙之居的概念,诗中的山水往往就成了求仙主题的陪衬,且多属神仙世界的幻想景物,所谓蓬莱、昆仑、瑤池之类。所以,游仙诗中的山水书写还有虚幻想象的成分在,真实山水的书写只是一部分。请看
何劭的《游仙诗》: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柏。光色冬夏茂,根柢无凋落。吉士怀贞心,悟物思远托。扬志玄云际,流目瞩岩石。羡昔王子乔,友道发伊洛。迢递陵峻岳,连翩御飞鹤。抗迹遗万里,岂恋生民乐。长怀慕仙类,眇然心绵邈。(13)
何劭观凌峰松柏四季苍郁,自觉胸中畅朗,遂“悟物思远托”,之后全是想象之辞,表达不恋世间名利,但愿如王子乔之修身养性而得道成仙,乘云随风,遨翔峻岳之间的仙游意绪。
郭璞的《游仙诗》十九首其三:
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绿萝结高林,蒙笼盖一山。中有冥寂士,静啸抚清弦。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飞泉。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崕肩。借问蜉蝣辈,宁知龟鹤年。(14)
诗中前四句写景,鸟戏花间,萝攀高木,山中之景明丽可爱、清幽原始,由此带出冥寂士择此闲隐,自能优游畅适,淡泊名利。诗人将山林想象成人间仙境,自己如愿为冥寂士,驾鸿乘紫烟,遨翔名山大川之间,以舒忧解郁,安顿身心,寄托蔑视荣华、超然物外之思。
其实,剥开“游仙”的表皮,会发现许多诗人并非真正相信神仙,他们不过托“游仙”以抒怀,即表现不满现实的情绪,力图摆脱人世的种种苦闷,故钟嵘说:“游仙之作,辞多慷慨……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去也。”
所以,从招隐诗和游仙诗的山水书写来看,其对象以深山幽谷的山水为主,故多呈深幽清美之貌。这种模式的创作多是“悟物思托远”,作诗以寄遐想,故山水书写总有想象虚拟之辞。由于诗人“坎壈咏怀”,诗中又多有遗世独立、超然物外之思。
4.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些结论:
第一,古代并无山水诗的分类传统,所谓山水诗、田园诗是今人强行分派。
第二,魏晋时期的山水书写呈现出多样的面貌,大致可以归为以下三个模式:(1)游宴式的山水书写——以园林山水为书写对象,充满优游行乐的趣味,山水清丽有致,其特点是巧言切状、酷不入情;(2)行旅式的山水书写——以旅途中所见野外山水为书写对象,充溢着行路难的忧愁和羁宦之情,山水荒凉沉郁,其特点是居高临下、极目远眺式的全览概述;(3)仙隐式的山水书写——以深山幽谷的山水为书写对象,多凭印象和想象来写。可见,魏晋时期的山水书写还没能跳出具体的事件,没有从特別上升到一般的普适高度。
注释:
①(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 67页。
②墨子著.吴毓江校注 《墨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 705页。
③(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 66页。
④(梁)萧统编.(唐)李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86页。
⑤(梁)萧统编.(唐)李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05页。
⑥(梁)萧统编.(唐)李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69页。
⑦(梁)萧统编.(唐)李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70页。
⑧(梁)萧统编.(唐)李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90页。
⑨(梁)萧统编.(唐)李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03~504页。
⑩(梁)萧统编.(唐)李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93页。
⑪(梁)萧统编.(唐)李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04页。
⑫(梁)萧统编.(唐)李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03页。
⑬(梁)萧统编.(唐)李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99页。
⑭(梁)萧统编.(唐)李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00—401页。
[1](唐)李善,呂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六臣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3]吴毓江.墨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3.
[4]丁成泉.中国山水诗史[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
[5]王国璎.中国山水诗研究[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
[6]王建生.山水诗研究论稿[M].台北:华艺数位股份有限公司,2011.
(责任编辑 孔占奎)
I207.22
A
1008-7257(2015)04-0030-04
2014-11-19
旷丹(1991-),女,湖南衡阳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