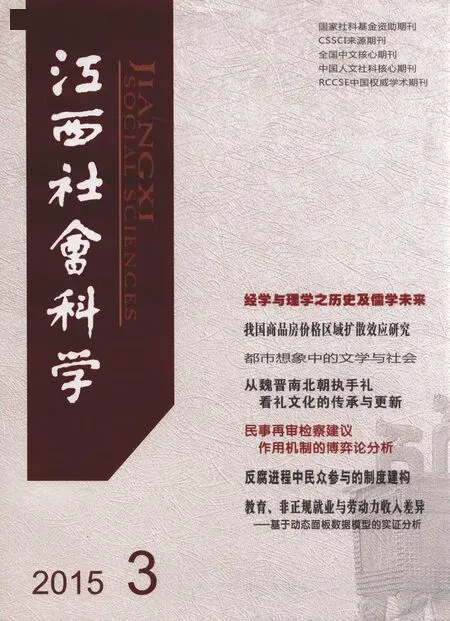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与存在主义的开启
2015-04-14李娉
李娉
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与存在主义的开启
李娉
克尔凯郭尔的哲学是在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中产生的,他对黑格尔哲学的体系、方法、历史哲学与宗教哲学等给予了彻底批判与颠覆,表达了对黑格尔哲学思辨抽象与忽视个人的不满。作为对黑格尔的反叛,克尔凯郭尔将哲学思考的重心转移到了对单个的人、对个体生命的体悟和沉思,开启了在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存在主义之先河。研究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能够使我们在一个更宽广的视野中把握黑格尔哲学的遗产以及存在主义的产生。
克尔凯郭尔;黑格尔;哲学体系;历史哲学;宗教哲学
李 娉,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在站博士后。(北京 100875)
在19世纪初的欧洲尤其是受德国文化影响的地区,黑格尔的哲学有着巨大影响,引起不同国家众多学者的追捧。就在黑格尔哲学如日中天的时候,一股反黑格尔哲学的潮流也开始涌动。克尔凯郭尔就对黑格尔哲学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他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既抽象思辨,又败坏社会道德。出于对黑格尔哲学的强烈不满,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哲学发起了全方位的批判。正是在对黑格尔的批判中,克尔凯郭尔开启了存在主义的先河。研究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有利于我们在一个更宽广的视野中把握黑格尔哲学的遗产以及存在主义的产生。
一、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批判
众所周知,黑格尔建构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试图对万事万物都做出解释。黑格尔非常自信地认为随着他的哲学体系的建立,哲学也达到了顶峰。对此,克尔凯郭尔是十分反感的。他讽刺体系的制造者建造了华丽无比的巨大宫殿,自己却不住在里面,而是至多居住在宫殿旁边的屋棚里。在克尔凯郭尔看来,黑格尔建造了一座只能观看而不能居住的体系,却声称他的体系是绝对真理的体现,这是哲学家的不诚实与自欺。克尔凯郭尔指出,体系的制造者以终极的、绝对的体系为名吸引人们的关注,他们这样盘算着:“如果在书的扉页上和通告里,我把自己的作品叫做为真理坚持不懈的斗争,那么谁会来购置我的作品或钦佩我呢?但如果我把它叫做体系、绝对的体系,那么每个人肯定都想要购置这个体系了。”[1](P92)克尔凯郭尔认为,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虽然无用却以其完备而得到当时人们的追捧和兜售,危害甚大。人们都满足于制造抽象的哲学体系,而忽视了哲学研究真正应该关注的是个体的人。因此,克尔凯郭尔的哲学思考不再追求建构完美的体系,而是倾其全力去思考存在的个体。
克尔凯郭尔之所以激烈地批判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原因是在他看来,存在体系是不可能的,只有逻辑体系才是可能的。他说:“对上帝来说,生命本身是一个体系;然而对任何存在的心灵来说,它不可能是一个体系。体系和终结是彼此呼应的,然而生命本身却正相反。……存在是将生命与体系分离开来,而体系作为终结恰恰是要将二者联结起来。”[1](P100)这就触及了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一个重要观点的批判,即存在与思维的同一性。黑格尔为了摆脱近代哲学的二元论传统而坚持一元论,但他所坚持的一元论是客观唯心主义一元论。在黑格尔看来,整个世界的发展就是绝对理念发现自己、认识自己、回到自身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绝对理念的自我运动,现实的客观存在和外在世界无非是精神、思维的“异在”。这实质上是用思维来统摄存在。克尔凯郭尔认为这种用思维统摄存在、将思维与存在等同起来的做法非常荒谬。
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只有人才能被称为“存在”,人的存在不同于任何物,只有人、并且是单个的个体才是他所指称的意义上的“存在”①。这种只有人才配称的“存在”是不能被归结为思维的,也不可能与思维相同一。克尔凯郭尔指出:“黑格尔体系中的理念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然而,存在却与此相反,它恰恰是上述二者的分离。这并不意味着存在是轻率的、没有思想的,而是指它为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之间设置间隔。就客观的认识而言,思维就是纯思维。在认识过程中,思维所指向的客观对象其实就是思维自己本身,而真理就成为思维与它自身的一致。这种客观思维与存在的主体没有任何关系,主体被当作一个纯粹抽象的主体,与真实的个人毫无关系。存在的主体越来越被稀释进稀薄的空气,最终成为一个思考存在与思维关系的纯粹的抽象意识,一个纯粹的主客同一,一种同语反复。”[1](P105)克尔凯郭尔认为,黑格尔这种基于思维与存在相同一的哲学体系只是一场发生在哲学家头脑中的智力游戏,而对真正重要的即个体的存在却毫无触及;哲学被体系所紧紧束缚,以至于遗忘了进行哲学思考的真实的自我。
二、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批判
“逻辑学”是黑格尔哲学的核心,它是黑格尔哲学方法论的集中体现。黑格尔在 《逻辑学》中通过一系列范畴、概念的抽象演绎,提出了一套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运动法则和规律。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的“逻辑学”给予了彻底的批判与否定。
首先,克尔凯郭尔批判了黑格尔以 “纯有”作为哲学的开端。他指出黑格尔以“纯有”作为绝对的开端是独断和抽象的,这个开端本身不是现实的,而是借助纯粹的思维达到的。克尔凯郭尔认为黑格尔所设定的没有任何规定性的“纯有”只是思维的产物,与真实的现实毫无关系。他说:“一个逻辑体系不能自夸有一个绝对的开端,因为这样的开端像‘纯有’一样,只是纯粹的幻想。”[1](P95)克尔凯郭尔指出,黑格尔体系的绝对开端是一种 “坏的无限”和 “无限的反思”,依靠反思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开始;要想真正的开始,就必须做出决断,正如哈姆雷特的反思只有通过决定或决断才能终止。
其次,克尔凯郭尔认为黑格尔《逻辑学》中关于运动发展的法则,如否定、中介、过渡等都是骗人的。我们知道,黑格尔在其逻辑体系中提出了一种否定的辩证法,认为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会逐渐被相反的更高一级的事物否定,通过中介转化而过渡到更高的阶段,这个更高的阶段是对先前阶段的扬弃。黑格尔以其强大的逻辑力量勾勒了一幅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运动图景,在这个逻辑演绎的过程中必然性是压倒性的,没有力量可与之抗衡,一切都是必然如此。对此,克尔凯郭尔表示轻蔑与不屑。他认为,黑格尔所谓的否定根本就不是否定,否定最终都被轻而易举地过渡到肯定中,否定在整个过程中不发生实质性作用,最终都被逻辑的必然性予以取消。在克尔凯郭尔看来,黑格尔所谓的否定、过渡、中介的运动只是伪装了的、可疑的动因,它们以平静的、置身事外的态度相互中介转化着,没有丝毫的骚动和紧张,其实这些运动只是发生在哲学家的头脑中而已。然而事实是,一个存在的个人是不可能被以这样一种平静的运动转化的,而是每时每刻都需要做出艰难的抉择与努力;生活中不存在黑格尔式的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简单过渡,也不存在“既……又……”的最终收纳与统一,而是充满了“非此即彼”与“矛盾冲突”。存在的个人是骚动的、紧张的、斗争的,他需要不断的抉择与奋争,而不是如黑格尔的纯思维那般平静如水和取消矛盾。
在克尔凯郭尔看来,黑格尔的逻辑学只是一场发生在思维领域的运动,是一种 “纯思维”与 “抽象的思想”,它完全没有触及现实存在的个人。同时,从黑格尔的逻辑体系中也不可能过渡到对现实的认识,因为它始终在思维的领域内打转。克尔凯郭尔在日记中说:“如果黑格尔在写完他全部的 《逻辑学》并且在前言中说明,它只是为了论证做一次思想实习,其间多处他回避了某些东西,那么他满可以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像他现在这个样子实在是滑稽可笑。”[2](P118)出于对黑格尔的反叛,克尔凯郭尔将思考的重点转移到了对个体生命的叩问和领悟。在他看来,每一个个体生命都现实地面临着选择与抉择的痛苦。这就涉及克尔凯郭尔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选择”。克尔凯郭尔认为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人拥有选择的自由,但也正是这一自由给人带来无尽的压力和苦恼。你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克尔凯郭尔认为对存在的个人而言,真正重要的是选择和行动,而不是黑格尔所谓的中介、转化、过渡。
三、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批判
黑格尔将世界历史理解为“绝对精神”、“理性”的自我展开与自我实现,认为“理性统治世界”。在黑格尔看来,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并不是表面的个人动机与意图,而是隐藏在人们行动背后的起支配作用的精神力量,即理念、世界理性,个人只是“世界精神”的实体性事业的活的工具。个人在黑格尔的历史观中不具有重要性,而只是服从“世界理性”、“绝对精神”普遍性力量的工具,只是达到世界历史目的的手段。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有着明显的目的论指引和能动辩证法的渗透,他站在所处的时代将过去的全部历史融合进一部绝对精神的发展史,将历史看作成是有着最终目的、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
黑格尔的这种历史观是强调个人存在的克尔凯郭尔所不能接受的。他把黑格尔这种高扬理性、只承认普遍性与必然性的世界历史观看作是时代的不道德的根源所在,是捍卫现存世界的最后智慧。首先,克尔凯郭尔批判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将“个体”混同于“类”、“时代”。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当时的时代是一个过集体生活的时代,个人迷失在诸如“类”、“我们的时代”、“19世纪”等抽象字眼中,而忘记了自身的存在。他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不道德。我们时代的不道德可能不在于享乐、享受和耽于声色,而在于对个体的人的肆无忌惮的轻视。在对我们的时代、19世纪的欢呼声中,隐藏着一种对个人的轻蔑;在沉浸在对我们这一代人的自满中,有着对做一个个人的绝望。”[1](P298)他认为当时的人们由于害怕面对自身的存在而自愿融入群众、集体中,这就好比沙漠中的旅行者由于害怕野兽和强盗而结伴同行。克尔凯郭尔认为黑格尔的哲学要为这种时代风尚负责。他指出,思辨哲学家把自己混同于普通群众,通过对世界历史的哲学沉思,使个人淹没在群众之中,越来越丧失个性与独特性。这种世界历史观的最大谬误就在于他将世界历史看作是哲学家头脑中的哲学沉思,而将个体混同于 “类”、“时代”、“群体”,每个个体都沦为世界理性、普遍精神的工具。克尔凯郭尔批评黑格尔说:“(思辨哲学家)作为旁观者以世界历史的轻蔑瞥着世世代代的剧目,就像大海中的鲱鱼群:单个的一个鲱鱼是不值一提的。旁观者麻木地盯着森林中的树木,然而他看到的只有森林,而不是一颗一颗的树。在世界历史体系的上演中,只有人类和国家扮演着角色,单个的个体却微不足道。”[1](P133)作为对黑格尔的反叛,克尔凯郭尔极力强调人的个体性。他认为任何个人都不能被归约为“类”,人优越于动物之处就在于每个个体的独特性,每个个体都高于抽象的“类”本身。克尔凯郭尔认为黑格尔是以“绝对理念”、“普遍性”的专断权力抹杀个体的独特存在和真正意义。
其次,克尔凯郭尔批判黑格尔坚持必然性的世界历史观抹杀个人自由,让个人受制于必然性。他指出,在黑格尔的世界历史中,历史终结了,剩下的就是进行不断的中介和转化。哲学家身在事外,以一副旁观平淡的态度对世界历史轻轻一瞥。他不参与,也感受不到世界历史上无数个人生前的挣扎与苦痛;他安详地坐着并且听着往昔的歌慢慢变老,听着由中介所带来的各种和谐之音。过去发生过的所有斗争、矛盾在哲学家的中介中变得极其次要和不值一提。历史在哲学家那里达到了最终的完满和终结,而人们也相信了哲学家的判断和预言。然而,哲学家的错误在于混淆了“思想”的层面与“自由”的层面。克尔凯郭尔认为,黑格尔对世界历史所做的总结属于“思想”的层面,它是发生在思想家头脑中的不停转化,历史与时间在思想家那里停滞了,它们只是一个个环节,等待思想家去不断中介。对于“思想”来说,对立面是不存在的,一方必然被另一方所吸收,进而被统一到更高的统一体中,前面的历史必然被后面的历史在思想中予以整合。而对于“自由”,对立面则是存在的。因为对立面的双方相互排斥着,它需要的是意志的决断,而非理性的中介;需要的是非此即彼的抉择,而非既是又是的整合。“自由”恰恰是要面对善与恶的斗争,而“思想”则能将善与恶都驯服于更高的统一体中。在克尔凯郭尔看来,黑格尔坚持必然性的历史观让个人在历史面前失去自由,而成为历史的被动接受者。
最后,克尔凯郭尔批判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容易出现混淆善恶、善恶不分的倾向。既然黑格尔将历史理性看作具有必然性的自我展开,任何历史个体都不能左右历史理性的自我运动,那么就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混淆,似乎善与恶服从一个量的辩证法,善恶在成千上万的个人与整个人类身上有着固定的程度和数量,不管是善还是恶都服从历史理性的必然法则。如此一来就会产生这样的怠惰,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人犯错或作恶就会找到自我安慰的借口;而一个具有足够重要性的历史伟人,却能以世界历史为借口将自己的错误和罪过说成是善的、好的。克尔凯郭尔认为这是对善恶的颠倒与对责任的推卸。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具有无限的扬善弃恶的责任,不能以任何借口去推诿,这恰恰与黑格尔认为的“恶推动历史进步”的观念相反。克尔凯郭尔指出个人在善恶面前有着非此即彼的选择,不能以结果的好坏来将恶的说成善的,否则就是诡辩。事实上,歌德也曾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有过这种担忧,在黑格尔晚年与歌德的一次谈话中,谈到辩证法时,歌德说:“但愿这种精神艺术和才能不致经常遭到滥用,不致被用来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才好!”[3](P181)
出于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不满、对黑格尔历史哲学所产生后果的愤慨,克尔凯郭尔几乎放弃了对宏大世界历史的思考,而专注于探究个体的选择、自由、责任等,这些都构成了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命题。
四、对黑格尔宗教哲学的批判
黑格尔既反对启蒙理性也反对虔信意识对待宗教的态度,他要使理性与宗教、知识与信仰统一起来。在黑格尔看来,“宗教是精神自我认识的一种样式”[4](P659)。在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中,神就是精神、理念。黑格尔将宗教的对象与思辨哲学的对象等同起来,认为它们都是关于“理念的意识”。黑格尔还认为神或精神的本质就是理性。他说:“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共性。”[5](P80)由于理性是世界的本性,因此神对人的启示或人对神的认识才成为可能,他说:“理性乃是神向人启示其自身的精神场所。”[6](P38)在将理性与信仰、哲学与宗教调和起来后,黑格尔还完成了基督教与世俗国家的和解。在黑格尔看来,基督教与现代国家应当相互承认,宗教应当看到国家是它的理念的实现、是精神在尘世的呈现。对于黑格尔的宗教哲学,杨寿堪曾指出:“他(指黑格尔)宣称:宗教是理性最高最合理的作品,必须确认并承认宗教是合乎理性的。并断言‘人是要信奉一个宗教的’。企图建立一种所谓‘理性主义宗教’,使普鲁士国家和基督教神学调合起来。”[7](P339)经过黑格尔的改造,神学事实上成了哲学,上帝变成了精神、理念;国家具有了至上性,基督徒必须与世俗生活取得一致。
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的宗教哲学既气愤又痛心,他认为黑格尔要为基督教在19世纪的堕落负责。正是由于黑格尔对理性与宗教、哲学与神学的调和,才使得人们都以一种客观的知识论态度对待基督教,而忘记了基督教本质上是关乎个体生存激情的。他认为,基督教所面临的最大危机就在于真正的基督教已名存实亡,而人们却硬要相信他所信奉的就是基督教、他天生就是一个基督徒。这种自欺的最大表现就是黑格尔以理性来解释基督教,将基督教哲学化和科学化。克尔凯郭尔指出,即使往日那些对基督教再刻薄不过的种种非难,在指认基督教是什么方面也还是比较诚实的,而“黑格尔最危险之处在于他篡改基督教——以使它和他的哲学相一致”[2](P121)。在克尔凯郭尔看来,黑格尔的所有构想都局限于 “纯思”,是在思维的范围内玩弄各种把戏;黑格尔不知道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人的生存,更不知道基督教本身就是关乎个体生存的。克尔凯郭尔认为,当黑格尔以其狂妄的抽象理性歪曲宗教时,完全忘记了宗教本身是关乎生存激情的,它是个体生存激情的表现。这种激情关乎个体每时每刻的生存状态,而非在纯思的理性天空中漫无边际地遨游。黑格尔不仅没有看到这种激情,更坏的在于他要以哲学去挽救神学。“神学痛苦地坐在哲学的窗边,巴望着哲学的惠顾,向哲学大献殷勤。”[8](P28)克尔凯郭尔认为以哲学去代替信仰是哲学的不诚实,哲学应当清楚地知道自身的界域和自身应当提供什么,而不能也不应当为我们提供信仰的根据。
按照克尔凯郭尔的理解,黑格尔对基督教的理性主义改造既没有触及基督教本身,也没有触及人的存在本身,而只是一个没有生活经验的教授的思维游戏。在他看来,基督教关乎的是生存意义、精神信仰的问题,而非诸如神性与人性相统一、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等逻辑描述;它的核心就在于承认上帝存在并且去信仰上帝,信仰与唯理论是不同的。克尔凯郭尔认为,基督教本质上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是要“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的问题,而不是“基督教是什么”的问题;不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行动的问题。
克尔凯郭尔否弃了黑格尔所强调的客观性与客观真理,而坚持主观性与主观真理。他说:“客观性的重心落在说了什么之上,而主观性则落在怎样说之上。”[1](P170)就真理而言,不存在客观的真理,存在的只是主观的真理,对我而言的真理。也就是说,“真理即主观性”。真理在克尔凯郭尔那里具有了与信仰相同的意义,真理与信仰都是内在的,宗教表现的就是一种内在的悲怆,而非外在的大声嚷嚷。他认为真理需要每个人自己去体会:“真理的内在性不能是像亲密伙伴那样,肩搭着肩一起前进,而是分离的,每个人自己通过存在去体会。”[1](P208)上帝只面对单个的个人,成为基督徒是一个关乎个人的问题,而不是他人、群体可以代劳的。因此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所达到的基督教与国家的和解也深恶痛绝。在他看来,基督教之所以名存实亡,就在于它与世界、国家混同起来了。克尔凯郭尔的反拨就在于他将所有热情都倾注在个体身上、倾注在单个个体与上帝的直接沟通上,将信仰看作是个体主观性的一种激情投入,而否定了包括教会、教义、牧师等在内的一切外在权威与组织。克尔凯郭尔晚年公开与丹麦国家教会进行斗争,事实上也是对黑格尔宗教哲学的进一步批判和反抗。
综上所述,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哲学的体系与方法、历史哲学与宗教哲学给予了有力的批判与颠覆。在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过程中,克尔凯郭尔走出了一条与黑格尔迥然相异的哲学道路。概括起来就是:一是突破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迷雾,使哲学不再是发生在思辨哲学家头脑中的思维游戏;二是关注被黑格尔所忽视的现实的、个体的人,使哲学实现一种生存论的转向。基于这条道路,克尔凯郭尔将哲学的重心转移到对孤独个体的沉思,终其一生都执拗地思考人的个体性、主观性与内在性,为后世的存在主义思潮奠定了基调和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我们也要看到,在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批判与拒斥的同时,他也丢掉了黑格尔哲学的诸多可取之处,如否定的辩证法、巨大的历史感等。这也启发我们注意到,克尔凯郭尔代表了一条与马克思截然不同的对黑格尔的批判路向。众所周知,马克思也曾激烈地批判黑格尔,但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历史观等不是决然地拒斥,而是继承性地改造。这与克尔凯郭尔对待黑格尔的态度是迥然不同的。作为同时代的人,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都从批判黑格尔出发建构各自的哲学,却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效应和结果,一个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一个开创了存在主义。
注释:
20世纪产生很大影响的存在哲学就是受了克尔凯郭尔对“存在”理解的启发和影响。雅斯贝尔斯称克尔凯郭尔为存在主义的 “存在”概念的发明者和首次使用者。
[1]S.Kierkegaard,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to the PhilosoPhical Crumbs,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Alastair Hanna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2](丹麦)克尔凯郭尔日记选[M].晏可佳,姚蓓琴,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苏联)阿尔森·古留加.黑格尔小传[M].卞伊始,桑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4](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M].张国清,朱进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5](德)黑格尔.宗教哲学讲座·导论[M].长河,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8.
[6](德)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7]杨寿堪.黑格尔哲学概论[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
[8](丹麦)克尔凯郭尔.恐惧与颤栗[M].一谌,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龚剑飞】
B534
A
1004-518X(2015)03-0025-06
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基金项目资助“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的批判”(SKXJS2014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