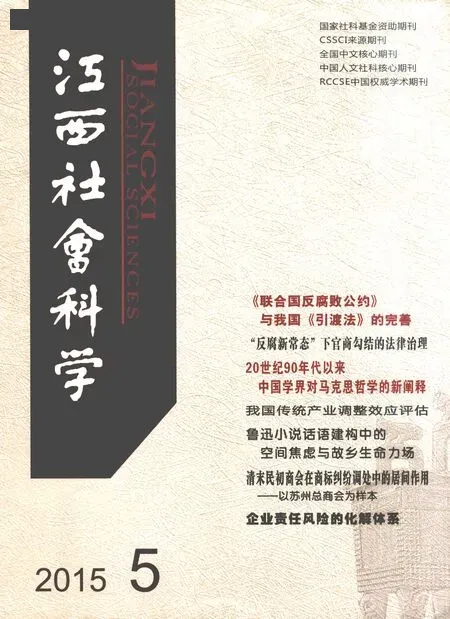清末民初商会在商标纠纷调处中的居间作用——以苏州总商会为样本
2015-04-14■尹萍
■尹 萍
商会是近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国最早的商会1904年出现在上海。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商会“没有遵循自然演进的路径,而是一种合力的结果”[1](P196)。就商事纠纷的解决机制而言,近代商会产生以前,商事纠纷在国家层面主要是由官府通过民事诉讼方式加以解决。此外,在传统的封建行会中,如公所、会馆也往往通过“公同议罚”、“同业公议” 的办法调处某些行业内的纷争。[2](P122、P466)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商会简明章程》首次明确赋予商会调处中外商事纠纷的权力,而北洋政府1913年的《商会公断处章程》以及随后相继颁布的一系列法律的授权,使商会获得了调处商事纠纷的权力。
苏州总商会 (初称苏商总会)成立于1905年,1914年成立商事公断处。苏州总商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便将商事调处作为其主要职能之一。同时,由于官府衙门在受理商事纠纷中的种种弊端,诸如主事官吏不谙商情、办案敷衍拖沓等,使得商民遇到商事纠纷时往往首先会寻求商会救助。从苏州商会档案资料看,商会在商事纠纷的解决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同属商事纠纷的商标纠纷讼案上却颇显另类:(一)从数量上看,商会受理的讼案以钱债纠纷、违约纠纷居多,而商标纠纷却不是很多;(二)从态势上看,商会受理的涉商标讼案呈现日渐萎缩的态势,1923年以后商会基本没有再受理过商标纠纷;(三)从地位上看,商会调处商标纠纷讼案从最初的居中公断者逐渐演变为只扮演诉求传递者或者代为申诉者的角色,地位越来越低,最后趋于缺位。本文试以苏州总商会为样本,对商会在商标纠纷的解决中发挥的作用进行梳理并分析其原因。
一、商标法制的外来性决定了商会在商标纠纷调处中的居间角色
中国传统上并不存在近现代意义的商标,清政府制定商标法规的最初动力和目的都不是为了维护中国商人的权益。商部在奏拟《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的呈折中就称“中国开埠通商,垂数十年,而于商人牌号,向无保护章程。此商牌号,有为彼商冒用者,真货牌号,有为伪货掺杂这,流弊滋多,商人遂不免隐受亏损”[3]。中国的商标制度可以说完全是清政府在与外国列强签订通商条约的过程中,在列强的多次催促下制定的。因此,“保护商品商标不受别人仿冒的动机,最初起源于外国商人;制定商标法规的最初目的,也是以保护外国商品商标为主,而绝不是中国商品商标”[4](P11)。另外,中国商标立法的内容基本是西方商标立法的翻版。最早拟定的《商标挂号章程》原始稿是当时海关副总税务司、英国人裴式楷受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指派,按照1902年中英两国签订的《继续通商航行条约》第七款的有关约定起草的。“由于办理商标注册,保护商标注册人的商标专用权不被侵害等此类工作。在本世纪尚属破天荒之举动,商务部当时没有此项工作经验,更没有现成的商标法律规则可供参考”[4](P72),清政府在《商标挂号章程》的基础上,结合当时中国工商企业使用商标的实际情况,包括各国驻华公使的建议和意见,最后才形成了中国商标史上第一部商标法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因此,相对于传统的钱债纠纷而言,中国上至政府官员下至一般商人,对商标纠纷都十分陌生。
而商会的商事调处权,如上所述是来自于清末民初政府法律的授权。政府之所以要赋予商会以一定的商事调处权,是明白商会不是一个孤立的组织,而是“一个开放性的复杂社会组织系统”[5](P156)。在商会周围存在一个“在野市政权力网络”,通过这种网络,商会控制了相当一部分的市政建设权、司法审理权、公益事业管理权、社会治安权以及工商、文教、卫生等多方面的管理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6](P155-156)这个网络范围广、社会根基深,即使政府也不敢小觑,而政府的政令、司法机关的民事裁判往往也要经过商会才能得到切实的执行。正因为这样,商会才在商事调处中拥有了虽然只是辅助但又不可或缺的地位。
然而,商会只能对它所熟悉领域发生的纠纷进行有效调处。虽然在江南一些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过去也曾有过保护商标的实例,如道光五年(1825),上海的土布商为保护各自商标权益,由绮藻堂布业总公司制订了“牌谱”,规定“各牌第一第二字,或第二第三字,不准有连接两字相同,并不准连接两字内有音同字异或音形相同之弊”[7](P2)。但同近代商标法规相比,这些行业规范明显简单和粗糙。对商会来说,依法调处商标纠纷几乎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正是商会与商标立法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商会在调处商标纠纷时,与政府只能保持一种特别的合作关系。
第一,与商会直接调处大多数其他商事纠纷不同,商会对商标纠纷的调处主要为代商申诉和辩护。这也是与商会职能相符合的。《奏定商会简明章程》第七条规定“凡商人不能申诉各事,该总协理宜体察属实,于该地方衙门代为秉公申诉”。由于对商标法律的陌生,中国商人遇到商标纠纷时,往往会呈请商会代为申诉,以维法权。如1914年苏州总商会就接到福建商人林作仁的呈请,请求商会就防止商标被假冒一事,致函吴县知事、苏州警察厅准予给示严禁。尤其是在华洋商标侵权诉讼中,商会基于保护国货的考虑,大多会据理为华商辩护。1922年“英商白礼氏公司诉宝昌蜡烛厂冒牌案”中,华商宝昌蜡烛厂被诉该厂“太公”商标冒牌英商白礼氏公司“水牛烛”商标。无奈之下,该商呈文苏州商会,请求商会出面解决此事。商会为此多次与吴县知事公署交涉,并极力为该厂辩护。虽然最终以该厂改变其商标告终,但商会在其中所做的努力仍得到了该厂的认可。[9](P698-705)
第二,商会能为商品是否注册向司法机关提供证明。当然,这里所谓的“注册”并不是1923年《商标法》实施后的真正意义的注册。按照清末商部的解释,“凡遇公司、行号、铺店愿意赴商部注册者,应报明就地商会,该商会将呈词抄录存案,仍将原呈加盖图记,并公费银两随文申转本部核办,听候注册给照,咨行地方官保护”[10](P34-35),商会应该是掌握有当地商品注册的情况,现存档案资料中也存有这方面的记载,如1921年5月的苏州“丝边业商标注册清册”里就记载着“华伦”、“兴华”、“久纶”等10个注册商标。[9](P68)在上述“英商白礼氏公司诉宝昌蜡烛厂冒牌案”中,苏州商会在为陈述宝昌烛厂并未冒牌理由致吴县知事公署的函中称:“经会审核照复,奉准注册,给照营业各在案。是该商所用太公牌商标,业已呈明贵县,尊例注册。”[9](P700)
第三,在商标纠纷诉讼中,商会通常会扮演居间劝解的角色。鉴于商会在当地广泛的影响力和强大的组织网络,各商民和官府都不会无视商会的存在,即使商民选择了官府解决纠纷,但一般都会同时向商会呈文说明情况,争取商会对自己的支持。而官府也会随时致函商会通报案情,以期商会协助。在这期间,商会通常会秉承和解息讼的理念,尽量劝解侵权方停止侵权。如1920年的“戎镒昌诉馀昌祥仿冒商标案”中,馀昌祥广货店为渔利,冒用戎镒昌已注册之“五月九日”圆形商标,将该商标用于质量低劣的同类商品上以伪乱真,冒抢生意,致使戎镒昌信誉、经济均受损。苏州商会一面应戎镒昌请求将馀昌祥代为诉至吴县公署,一面召集相关执事和两造到商会,调查案情,指出被告方确有仿冒之嫌,并敦促其速改商标。最终,馀昌祥表示愿意改用图章式样,以分区别。[9](P690)商会之所以能有效发挥劝解的功能,原因即在于它所拥有的强大的“在野权力”。
商会具有近现代新式商人团体的属性,其组织结构和影响力也非传统行会可比拟,并且商会商事理案权在清末民初获得了法律上正式的认可。但在商标纠纷方面,商会所起的作用并非想象中那样大,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二、社会商标意识的淡薄限制了商会调处作用的发挥
商标作为商品的标志,是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虽然中国的商标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印信[7](P2),但近现代意义上的商标却是到了明末清初,伴随着沿海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而出现的。尤其是20世纪后,随着“类皆附有商标”[11](P3)的外国商品大量涌入,中国工商业者的商业经营意识才逐步转变,开始意识到商标之于商品及营销的重要性。但值得指出的是,这种转变更多的是出现在以上海为代表的一些对外开放的通商大埠 (这也是清末《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将商标挂号分局设在津、沪两关的原因之所在),对于广大的中国内地,传统的农业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虽然在进入清代以后,地处长江三角洲腹地的苏州工商业有了很大发展,并且苏州还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较早的地区。但“传统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加之沿海与内陆交汇点的经济地理位置,使近代历史上的苏州在许多方面仍长期保持着传统商业消费城市的特点。较诸邻近的最大通商口岸上海,苏州带有更为浓厚的传统色彩”[5](P7)。 太湖流域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使得旧式的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经济结构上仍居于压倒性优势地位。传统经济结构下人们大多固守传统的经营模式,秉持“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思想,商标意识淡漠。
(一)注册商标以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淡漠
当时的一些工商人士在与洋商打交道的过程中注意到,洋商由于利用了商标来推销商品和保护权利,能够在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于是开始逐步认识到商标的重要性,并积极进行商标注册。当时因《商标注册试办章程》颁而未行,国内华商主要是通过到政府相关商标管理部门注册的部中备案制度进行商标的“预注册”。从20世纪初至1923年5月北洋政府按 《商标法》正式受理厂商商标注册前,通过部中为国内工商企业办理机制国货商标备案约1000多份。当时国内知名企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就向农商部一次呈请了11件卷烟商标的备案。中国近代著名日用化学品生产企业——上海永和实业公司也是将商标呈请部中备案的。1919年5月,农商部向该公司颁发了第665号批文:“呈悉该公司制售牙粉,拟用月里嫦娥图为商标,请予备案。应即照准此批。”其他如“兵船”牌面粉商标、“三角”牌毛巾商标等,均向农商部呈请了机制国货商标备案,以寻求政府保护。[12]但华商中注册的多为上海等工商业较发达的大都市的知名企业,而且与洋商通过海关挂号的三万多件商标相比,华商呈请注册的商标总数非常有限。
对于苏州这样一个传统型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城市,大多数工商业者主要靠商界信用和顾客口碑销售商品。即使有商标注册的情形,所占比例也很小。虽然当时苏州到底有多少工商业者进行了商标注册,目前尚无史料给出具体数据,但在苏州商会自1905—1919年近15年间的档案资料中,涉及官府衙门为保护商标事项致苏州商务总会的仅2件,除此以外再无记载。
(二)对侵害他人商标权的法律后果认识模糊
商标是商品身份的标记,商标权是一种凝结着人们智慧的知识产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近代以来,商标成为法律加以保护的特殊权利客体。西方各国纷纷通过相关立法对商标进行保护,并对商标侵权行为进行处罚。而传统中国并没有“权利”概念产生的土壤,国人并不知道何为“权利”。直到清末民初,随着洋务运动尤其是清政府在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列强要求订立商标、专利和版权互保条款,商标权等知识产权概念才在中国传播开来。正因为这样,1924年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总事务所在探究华商注册商标甚渺的原因时,首先就将其归咎于“华商于权利观念,素形淡漠”[9](P260)。
对自己的权利淡漠,对他人的权利更不会太在意,加之对商标本身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对侵害他人商标权行为的法律后果就不可避免地显得无知或麻木。这首先表现为侵权手段拙劣。侵权者往往仅私下里简单地刻一枚相同的印记冒牌附在自己的商品上。侵权事实通常毫无争议。如苏州商会1905年受理的一起商标侵权讼事中,开参店的彭葆生就私刻图章,冒充同业丁秉钧、丁秉常参店的福来康牌(即商标)在各路航船上销售。该纠纷经船伙王永华中证,侵权事实清楚,商会很快结案,并请县衙给示,永禁冒牌。[10](P593)其次表现为对侵权行为的不以为然。在前文提及的戎镒昌诉馀昌祥仿冒商标案中,在商会调处以后,馀昌祥表示“‘五月九日’之图有碍他家皮件营业,为此区事,小号将后皮件不用此图”[9](P691),竟将侵权视为“区事”,让人哭笑不得。
三、商会成员的绅商属性削弱了商会对商标纠纷的调处效果
商会档案资料显示,清末苏州商会成员大多是兼具各种功名职衔的“绅商”。以1908年的苏州商务总会为例,其总理、协理中有2名为中书衔;会董中有16名分别为二品职衔、候补试用知府、候选同知、同知衔、候选郎中、员外郎、候选县丞知事、监贡、禀及武生等;会员中有44名也分别有各种功名职衔。[5](P223-224)绅商是近代中国崛起的一股新兴势力,由绅士与商人合流而成。其形成不外乎两条主要渠道,一是由绅而商,二是由商而绅。苏州总商会中的一些著名绅商即是由官绅和科举仕途转为投资经营民族工商业。更多的绅商则是商人通过捐纳报效得到一定的功名虚衔。[5](P225-228)
清末的绅商虽然主要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有紧密联系,不同于传统绅士和旧式商人,但仍然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那些由绅而商的,过去为获功名苦读多年,那样的知识背景和成长经历对他们的影响自不待言,即使是由商而绅的,就算他们是靠新式工商业起家,能想到要花钱去买个功名,这本身就说明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也正是如此,商会在商事纠纷的调处方式上也表现出新旧混搭的特点。“新”是指商会在理案程序上不同于传统中存之既久的民事调处息讼。前文提到,清末商会之“公断权”是由法律明文规定,通过制定专门的章程和特定的程序规则,并配置专职的理案人员来行使的。北洋政府的《商会公断处章程》和《商会公断处办事细则》更是对公断程序进行了详尽规定,如规定了公断处接收两造诉书,须于三日内具通知书,嘱令两造于某日到场;公断之开始,必须两造到场,不得有缺席判决;处理商事争议时,以评议人三人或五人行之[8](P369),等等。“旧”则是由绅商的属性决定的,主要表现为:
第一,商会理案或公断通常不是依据法律条文,而是更多地按照传统调处民事纠纷的做法,依据习惯、情理等来理案。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民商事法律的缺位造成的,但在主观上,商会绅商们认为,既然商事纠纷属民事纠纷的范畴,那么依商事习惯甚至情理调处就是必然的。关于这一点,即便是当时的司法机关,在审理相关商事诉讼案件时,也会考虑商事习惯的援用。
这种做法在调处一般商事纠纷时无疑是有效的,因为近代的商法归根到底是从商事习惯演变而来的,商法被称为“商人习惯法”。尤其商会的议董都是当地有着极高声望的商界精英,有着丰富的从商经验,熟悉当地的商事习惯,他们调处案件能切中要害,提出的调解方案对双方当事人来说往往是最可接受的,而且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由商会调处的案件一般都能及时结案。但涉及商标侵权的案件与一般的商事纠纷有所区别。一般的商事纠纷,如钱债、违约等,各地商界长期以来形成了大量的商事习惯可供依据,但商标方面的习惯却极少。从清末民初政府组织的两次较大规模的民商事习惯调查资料来看,涉及商事习惯调查的内容十分广泛,林林总总有几百个问题,而涉及牌号及商标的只有区区12个问题。[13](P210-228)因可依据的习惯十分有限,若遇到简单的冒牌影射案件,商标侵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商会还勉强可应对,若遇到复杂一些的案件,需要判定是否为近似商标时,商会仅凭习惯或情理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第二,商会在调处商事纠纷时对律师的排斥,使得商标权利人难以获得专业的救济。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制度是民国时才建立的。律师作为专业人士在诉讼中出场,对维护和争取当事人的权益来说至关重要。但在商事争讼中,商会却极力反对律师的介入。虽然司法、工商部所颁《商事公断处办事细则》第47条规定:“公断期限当事人应亲自到场说明事件原委并自己主张之理由,但以不得已之情形为限得委托代理人行之前项,代理人若于该事件无解决之权威或无演述能力者,彼造得声请评议员拒绝之。”[14](第一回)但苏州总商会在其随后的商事公断处办事细则的第四章“公断程序”第26条中却规定:“本处公断,两造当事人均须亲自到场陈述。如遇不得已事故时,应由当事人申请核办,惟不用律师制度。”[8](P374)
不仅苏州商会,其他商会对待律师的态度也大抵如此。究其原因,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在商人及其组织看来,律师是贪婪的化身、挑唆生事的主谋、上下钻营的狼狈之徒”[15],从深层次讲是因为近代绅商在观念上仍受传统息讼、厌讼、贱讼甚至惧讼、避讼思想及将诉讼代理人视为 “讼棍”的深刻影响。“在中国传统的法文化中,诉讼被认为是官吏德化不足和缺乏政绩的表现”[16](P278-279), 而讼师在中国古代是为人们所鄙弃的。《大清律例》甚至规定:凡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与犯人同罪。
商标纠纷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的商事纠纷的案件,商标的注册、管理,商标权人的权利、义务以及近似商标的认定标准等都由法律明文规定,特别是商标权属认定的专业性极强,非专业机关和人员无法胜任。正是死抱着这些传统的观念和调处方式,才使得商会对商标纠纷的解决效果大打折扣,遇到复杂一些的案件就只能退而充当官府与当事人之间信息传递者的角色,最后在《商标法》正式颁行以后完全停止了行使对商标纠纷进行调处的职能。
四、结论
苏州既不是上海那样的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标杆性城市,也不是传统经济的典型代表。这与清末民初中国经济新旧二重性的特点相吻合,正因如此,该地区商人的商标意识恰恰能反映近代中国商人的一般状态,该地区商会在商标纠纷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内在原因,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考察清末民初中国商会商标纠纷解决机制的一个窗口。通过对清末民初苏州商会在商标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商标诉讼案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方,商民使用商标的情况越普遍,商标讼案自然也多。但清末民初,国人对商标品牌的观念还处于初级阶段,中国自己的民族品牌还很少,与传统的其他民商事纠纷相比,商标纠纷也不是很多。
其二,商标讼案的审理方式会影响到商民对解决商标纠纷途径的选择。尽管当时的商事法律还很不完善,但商会基本还是按照 《商会法》和《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等法律法规来运作的。不过商会对商标纠纷的调处主要是采用较传统的方式,依据的大多是历来的商事习惯,也很少通过律师来解决,这说明近代的中国商业组织还没有摆脱传统的息讼观念以及对律师仍然存在排拒态度。这也是商会在调处商标纠纷中的地位越来越低,直到最后缺位的重要原因。
其三,近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间并不完全是一以贯之的政治国家吞噬社会的关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尽管这种互动的程度尤其是社会作用于国家的方面并不够强烈或不是十分有效,但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仍不能排除、更不能忽视或轻视社会力量的作用和价值。因此,研究中国法制现代化包括商标法制发展的进程不能只关注国家层面,以商会为代表的社会力量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和参与者。今天的法治中国建设依然迫切需要正视和重视社会力量的智识和贡献。
[1]刘光华.商会的性质、演进与制度安排[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M].上海:三联书店,1959.
[3]商部奏拟订商标注册试办章程折[N].(上海)申报,1904-08-18.
[4]左旭初.中国商标法律史(近现代部分)[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5]马敏,朱英.辛亥革命时期苏州商会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6]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1993.
[7]马东岐,康为民.中华商标与文化[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
[8]马敏.苏州商会档案编丛(第二辑)[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9]马敏.苏州商会档案编丛(第三辑)[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0]章开沅.苏州商会档案编丛(第一辑)[M].第2版.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11]金忠圻.商标法论[M].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35.
[12]左旭初.民国时期商标管理概况[J].工商史苑,2011,(2).
[13]眭鸿明.清末民初民商事习惯调查之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14](清)阮湘.中国年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8.
[15]付海晏,匡小烨.从商事公断处看民初苏州的社会变迁[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2).
[16]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