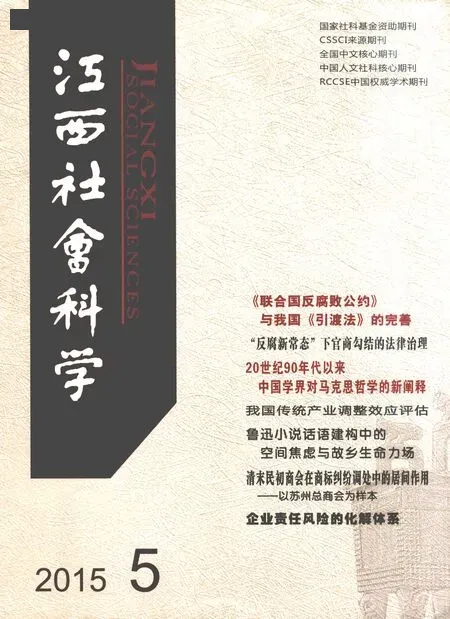亚里士多德“城邦优先于个体论”的共同体主义阐释
2015-04-14田道敏
■田道敏
自然主义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也是贯穿他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在《政治学》第1卷中,亚里士多德清楚地表达了他的政治自然主义的一个重要主张:城邦在本性上优先于个体。城邦之于个人的优先性常常使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主张遭受极大的误解和批评,围绕这个主张,后世学者给出一系列阐释并展开激烈争论。本文从亚里士多德共同体主义的视角,尝试论证“城邦在本性上优先于个体”这个主张的合理性。
一、城邦在本性上优先于个体
在《政治学》第1卷中,亚里士多德提出政治自然主义的前两个主张“城邦由于自然而存在”、“人类本性上是政治动物”之后,紧接着提出第三个主张:
我们现在就进而论述城邦,城邦(虽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和家庭),在本性上则先于个人和家庭。就本性来说,全体必然先于部分;以身体为例,如全身毁伤,则手足也就不成其为手足,脱离了身体的手足同石制的手足无异,这些手足无从发挥其手足的实用,只在含糊的名义上大家仍旧称之为手足而已。我们确认自然生成的城邦先于个人,就因为(个人只是城邦的组成部分,)每一个隔离的个人都不足以自给其生活,必须共同集合于城邦这个整体(才能让大家满足其需要)。[1](P8-9)
事实上,这个主张与前两个主张都是有关系的,“城邦在本性上优先于个体”可能与城邦的本体论地位以及“人类本性上是政治动物”相关联。同时,这个主张的论证也存在一些困难。例如,亚里士多德将城邦与人的身体进行比较,其中的“优先性”、“同音异义(含糊的名义)”和“功能(实用)”等概念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都有不同的意义,我们必须明确,在这个论证中,这些概念该采取哪一种含义。此外,亚里士多德在论证中把城邦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比作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还须明确个体在什么方面是整体的一部分。
当然,亚里士多德的这个主张导致的最严重后果是极权主义的指控。例如,卡尔·波普(Karl Popper)就认为,亚里士多德是极权主义者和平等主义的反对者。[2](P96)事实上,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也的确容易导致极权主义,在他的上述命题中就含有这样一层意思,即统治是一种自然观念,但他的论证没有对自然统治的范围做出任何限制。城邦优先于个体,意味着个体是城邦的一部分,就像手是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国家占有个体;人本性上是政治动物,也即人本质上是公民,公民依赖于国家,所以人也依赖于国家;成为一个人,就是成为国家的公民。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意指人就像机器上的齿轮或发动机上的火花塞,是国家的一部分。
二、凯耶特的解释及其问题
作为当代研究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大卫·凯耶特(David Keyt)对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在本性上优先于个体”给出一种解释。他认为,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一个事物先于或后于另一个事物的许多种情形,其中与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之于个体的优先性论证相关的是以下三种优先性:实体上的优先性、形式上的优先性和自然上的优先性。一个事物在实体上先于另一个,当且仅当,一个事物比另一个事物更充分地发展或更充分地实现。因此,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原则,在产生上靠后的东西却在实体上是在先的。例如,成人在产生上后于孩子但在实体上先于孩子,所以城邦在产生上后于但在实体上先于村庄、家庭和个体。凯耶特认为,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的自然性的主要论证也依赖于这个事实。[3]一个事物在形式上先于另一个,当且仅当,这个事物在另一个事物的形式中提到,而不是相反。例如,直角在形式上先于锐角,因为锐角是小于直角的角。因此,根据亚里士多德关于人和城邦的定义,两者都不是在形式上先于另一个。既然人是政治动物,人的形式就提到城邦,而既然城邦是自由人的共同体,城邦的形式也就提到人。一个事物在自然上先于另一个,当且仅当,一个可以没有另一个而存在,而不是相反。例如,太阳自然地先于任何植物,因为太阳可以没有植物而存在,但植物不能没有太阳而存在。实体上的优先性和形式上的优先性都不蕴涵自然上的优先性。比如,房子在实体上先于构成它的砖和石头,但在本性上后于砖和石头,因为砖和石头可以没有房子而存在,但房子不能没有砖和石头而存在。因此,城邦在实体上先于个体并不蕴涵它在自然上也先于个体,城邦也不可能在形式上先于个体。[3]
在凯耶特看来,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本性上优先于个体”的主张是《政治学》中最具挑战性的断言,他将亚里士多德得出这个结论的论证称作“有机论证”。[3]在凯耶特看来,亚里士多德一开始想证明城邦在本性上优先于个体,但是他后来得出的结论似乎使这个论题等同于“城邦由于自然而存在”。这样问题就变成,这个论证是证明了两者,还是仅仅进一步证明城邦的自然性?凯耶特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优先性原则有多普遍,换言之,就是“整体必然地先于部分”这个原则是应用于每个整体,包括自然的和人工的,还是只应用于自然整体。[3]如果这个原则只应用于自然整体,那么,只要假定城邦是一个自然实体,就可以应用这个原则。否则,它就不能用来证明城邦由于自然而存在。所以,如果优先性原则只应用于自然整体,那么有机论证的结论就必定只是优先性论题。
凯耶特认为,亚里士多德提出“城邦本性上优先于个体”这个主张意味着当个体与城邦分离时,个体就丧失了他的人性,因此,这个主张显然是错误的。凯耶特进一步给出一个反例说明这一点。假如有一个人叫Philoctetes,他被毒蛇咬伤且不可治愈,因而与城邦分离开来,被迫孤立地生活。假设Philoctetes不是神,也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讲的“本身是自给自足的,因而不需要城邦”的那种人。那么,在凯耶特看来,优先性论题就蕴涵任何给定的城邦可以没有Philoctetes而存在,而不是Philoctetes可以脱离城邦而存在:“说Philoctetes不能脱离城邦而存在不是说他像一只蜜蜂与蜂群分离开来,没有城邦将会死去,而是说,他不再成为一个人而堕落到低等动物的水平。换句话说,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由于这个人与城邦分离开来,他就不能称为一个人,只是名称上的人而已。”[3]
而且,凯耶特认为,根据亚里士多德自己给定的原则,优先性论题的结论也是错误的。按照凯耶特的看法,A不能做B要分两种情况:A可能缺少做B的能力或技能,或者A可能有这种能力或技能,但缺少做B的机遇。比方说,未经木工训练的人与没有工具的工匠都不能建造房子,但原因不同:未经木工训练的人不是工匠,而没有工具的工匠仍然是工匠。凯耶特借此认为,孤立生活的Philoctetes就像没有工具的工匠,他是由于不幸,而不是由于缺少与其他人一起生活的能力才与城邦脱离,所以他仍然是一个人。[3]既然优先性论题蕴涵相反的结论,所以必然是错误的。
但是,凯耶特的解释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凯耶特没有说清的一个问题是:城邦是本性上优先于个体且由于自然而存在,还是城邦仅仅在本性上优先于个体。按照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论述,“我们确认自然生成的城邦先于个人,就因为(个人只是城邦的组成部分),每一个隔离的个人都不足以自给其生活,必须共同集合于城邦这个整体 (才能让大家满足其需要)”[1](P9)。按照凯耶特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断定,城邦在本性上优先于个体并且城邦由于自然而存在。然而,亚里士多德在什么程度上可以将城邦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扩展到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呢?“就本性来说,全体必然先于部分。”[1](P9)在凯耶特看来,亚里士多德在这个论证中只想证明城邦之于个体的优先性,城邦由于自然而存在的观点只是某个更早论证的结论。凯耶特认为,亚里士多德在这个论证中辩护了优先性原则:每个自然整体在本性上优先于它的部分。例如,人的身体死去了,手和脚就不再是手和脚,只不过音形相同而意义不同,因为手脚不能没有身体而发挥作用。因此,亚里士多德这个主张的理由只能是,个体不是自给自足的,他是城邦的一部分,如果脱离了城邦就不能发挥作用。
其次,凯耶特给出的Philoctetes的反例也不令人满意。事实上,Philoctetes并不是变得不像人,而是他未能实现作为人的全部潜能。亚里士多德没有说不归属城邦的人就是鄙夫或超人,他只是说本性上不归属城邦的人才是鄙夫或超人。与他人孤立开来的人不能在共同体之外实现他的潜能,因为没有人是自给自足的,每个人都需要城邦。因此,亚里士多德真实的意思是说:根据人的定义,人都需要城邦,如果一个活的存在物在本性上不需要城邦,那么这个活的存在物就不是人,并不是简单地说脱离城邦的人就丧失了人性。
三、米勒的解释及其问题
弗雷德·米勒(Fred D.Miller)是当代研究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另一位重要学者,他对亚里士多德自然主义政治哲学的解释也是我们不能回避的。[4]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在本性上优先于个体”,米勒提出了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分离中的优先性”。根据这种解释,亚里士多德关于这个主张的论证的关键在于,他把活的事物和器官与城邦和公民进行类比。胳膊在分离上后于整个身体,也即是说,身体可以没有胳膊而存在,但胳膊不能没有身体而存在。“在另一意义上灵魂就不先于全体,因为它不能离整个动物而存在;因为在一个活动物身上时是一个指,但一只死指就只名称是‘指’,而实际已无复‘指’的真义了。”[5](P144)同样,城邦可以没有公民而存在,但公民不能没有城邦而存在。换言之,城邦在分离性上是优先的。
米勒的第二种解释是“完整性上的优先性”。根据这种解释,城邦在完整性上优先于公民。城邦是完整的、自给自足的,而脱离城邦的公民则不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自给自足是城邦的属性,不是个体公民的属性。个人只有通过合作、与他人生活在一起才是自给自足的。所以,城邦在完整性上优先于个体。[6](P50)因此,根据这种解释,城邦是自给自足的,公民则不是,所以城邦在完整性上优先于公民。个人在极端条件下脱离城邦也能存在,但脱离于城邦时,个人只是名称上的人。
关于Philoctetes的问题,米勒借用亚里士多德对不同层次的潜在性和现实性的区分来说明。处在第一层次的潜在性的Philoctetes拥有学会德性的能力,可以生活在城邦之外,但他不能脱离城邦而提升到第二层次的潜在性 (或第一层次的现实性),也即实际上学会德性,因为这需要教育和习惯才能做到。他也不具备在脱离城邦的情况下提升到第二层次的现实性,也即成为有德性的人,因为他需要城邦才能做到这一点。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除非Philoctetes在某个时间点上生活在城邦之中,否则他既没有处在第一层次的现实性,也没有进步到第二层次的现实性。而在米勒看来,处在第一层次的潜在性或第一层次的现实性的Philoctetes不再像人,因为他没有实现他的潜能。[6](P52)
米勒也认为亚里士多德政治自然主义的第一个主张“城邦由于自然而存在”与第三个主张“城邦本性上优先于个体”之间有关联。第一个主张是说,城邦为了促进公民的自然目的而获得自给自足;第三个主张则意指人类不能没有城邦而实现他们的目的。第三个主张没有暗示城邦是实体或有机体,而是依赖于共同体原则:人只有在城邦中才能够实现他们的潜能。城邦是一个共同体,所以它才是一个整体,它的目的就是每个个体都要达到的目标。
米勒解释的问题是,他没有认识到这个论证中“同音异义词”的重要性。米勒认为,脱离城邦的个体只是名称上的人,就像脱离于身体的手。但是,两者之间的类比是不一样的,因为手不再是手,但人仍然是人。此外,关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哪一种“优先性”意义适合于“城邦本性上优先于个体”主张,以及这个主张面临的各种误解,米勒都没有明确地解决。
四、共同体主义的解释
针对凯耶特和米勒的解释存在的问题,笔者主张一种共同体主义的解释。共同体主义是指这样一种观点:共同体先于个体,我们应该通过共同体来讨论个体。在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本性上优先于个体”的论证中,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他这里的“优先性”是指什么意义上的优先性,换言之,在什么意义上城邦优先于个体?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和《形而上学》中曾对“优先性”概念有过详细讨论,并做出不同涵义的区分。
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区分了五种类型的优先性。[7](P45-46)第一是时间上的优先性,也即一个实体比另一个实体更古旧,这是严格意义上的优先性。我们通常认为一个事物优先于另一个事物时,也经常指时间上的优先性。但是,显然城邦不是时间上优先于个体,因为个体必定先于城邦而存在。第二是存在的涵义方面的优先性。例如,“一”先于“二”,如果“二”存在,那么“一”就存在,反之则不然。显然,城邦也不是在这种意义上优先于个体,因为城邦可以没有个体而存在,个体也可以没有城邦而存在。第三,顺序上的优先性。例如,字母先于音节,演说的开头先于结论。显然,城邦也不是在这种意义上优先于个体,因为这种意义的优先性只用于语言和语词。第四种优先性是由于自然的优先性,它是最不严格、最不科学或最不符合逻辑的优先性。亚里士多德将这种类型的优先性称作自然的优先性,即城邦比个体更自给自足,城邦自然地优先于个人,所以这种意义的优先性最适用于亚里士多德的这个主张。第五种优先性是指一个事物先于另一个事物,如果前者导致后者存在或导致后者成为某事物。经此分析,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谈论的第四种意义的优先性最适合解释“城邦本性上优先于个体”的主张。
除了在《范畴篇》中讨论这五种意义的优先性之外,亚里士多德还在《形而上学》中区分了四种类型的优先性。第一是时间上的优先性,也即绝对或相对地接近于起点,或者更远离或更接近现在。例如,更接近于第一推动者的事物有优先性,更强力的实体是优先的,排列上的优先性。显然,这种意义的优先性不适用于城邦与个体的关系,因为城邦不是在个体之前存在,城邦也不是更接近于主要的推动者,城邦也不比个体更强大,城邦也不是在某个排列当中先于个体。第二是知识上的优先性,它与定义有关,例如,共相先于殊相。显然,这种意义的优先性也不适用于城邦与个体的关系。第三是属性上的优先性,例如,“线”的属性先于“面”的属性,因为“线”先于“面”。然而,城邦和个体都不是属性,所以这种意义的优先性也不适用于城邦与个体的关系。第四是实体或自然的优先性,即某事物在实体或自然的意义上先于另一个事物,如果前者可以没有后者存在,而不是相反。例如,整体在产生方面可以没有部分而存在,而不是相反;部分在毁灭方面可以没有整体而存在,而不是相反。第四种意义的优先性最适用于城邦与个体的关系。
在阐明“优先性”的意义之后,我们讨论亚里士多德的论证中涉及的另外两个重要概念:同音异义与功能。“就本性来说,全体必然先于部分;以身体为例,如全身毁伤,则手足也就不成其为手足,脱离了身体的手足同石制的手足无异,这些手足无从发挥其手足的实用,只在含糊的名义上大家仍旧称之为手足而已。”[1](P9)亚里士多德将城邦与个体的关系当作全体与部分的关系并以身体和手足的关系来解释,他这样做的基础和根据是什么?毕竟,城邦与身体不是相同类型的整体,个体与手足也不是相同类型的部分。我们显然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这种类比,这种比较还要涉及字面背后的意义。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就认为“部分”是同音异义的,也就是说,“部分”这个概念虽然在不同的用法中音形相同,但意义不同,例如它有时指称潜在性,有时指称现实性。指称潜在性的部分是不能脱离整体而存在的部分,例如动物的部分,“因为将动物各个部分分离,各个部分便不能独立自存;分离后所有各部分只是物质”[5](P156)。指称现实性的部分是可以脱离整体而存在的或自身也是整体的那些部分。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证中,“手足”是指称潜在性的部分,而“个体”则是指称现实性的部分。“全体”同样有不同的类型:
“全”(全体)的命意(一)是说这个作为一个天然的整体,不缺少应有的任何部分,(二)这个包容了成为一个整体所必需包容的事物;这所包容的各事物可以本各是一而合成为整一,亦可并非各一而合成整一。(甲)以类为“全”,同类诸物原是各成一物的,但总持起来,以全类作一整体说也是真确的,例如人、马、神等本各是一生物,因此用一个普遍名词为之作成统称。但(乙)以各个不同的部分组成为一全体,延续而有外限,其部分只是潜存而未实现的事物(已实现的事物作为部分而包涵于全体之中也是可以的)。关于这些事物,其天生为“全”的较人造的“全”为高,这是我们在上面释“一”时已说过了,“全体性”实际上就是“统一性”之别格。[5](P112-113)
因此,根据不同的统一程度,最统一的整体是拥有潜在性部分的整体,最不统一的整体是拥有现实性部分的整体,也即现实性的部分可以独立于整体而存在。因此,“手足”与“身体”这种“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不同于“个体”与“城邦”这种“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换言之,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论证中是同音形但不同意义地使用了这些概念来进行类比。手足确实依赖于身体,不能脱离身体而存在,但个体不依赖于城邦,脱离了城邦的个体仍然继续存在。
当然,个体与城邦之间仍然存在某种关系。个体离开城邦就不能实现他的功能,即表达德性的理性活动,但他并没有丧失实现这种功能的能力。也就是说,脱离城邦的个体只是没有机会而不是没有能力来履行他的职能。此外,脱离城邦的个体也不是自给自足的。这些都表明脱离于城邦的个体只是名称上的人。这一点也预示将其比作手足和身体的不同之处:脱离身体的手足确实丧失了实施其功能的能力,更没有实施其功能的机会。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当一个事物能够实施其功能时,它才真正是它自身,才完全是它所是,而不是名称上的。如果事物不能实施其功能,它就不是它自身。因此,脱离于城邦的人并非不是人,而只是名义上的人,因为离开城邦就不能实施他的功能。人作为政治动物,必须依赖城邦来实施他的功能。个体之于城邦并非简单如机器上的螺丝钉,而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并且是现实性的实体部分。城邦在自给自足的意义上优先于个体。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表达了许多共同体主义的观点,他认为个人不能在城邦之外实现他的潜能,个体需要生活在城邦当中才能繁衍下去。在《动物志》中,亚里士多德将“政治动物”定义为 “拥有某个共同对象作为功能的动物”[8](P8)。“城邦在本性上优先于个体” 同样意味着共同体是至高无上的。可见,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在本性上优先于个体”主张确实支持一种共同体主义的观点。不管我们如何理解 “优先性”这个概念,城邦的优先性至少排除了个体主义的观点。此外,亚里士多德的“人类本性上是政治动物”的主张也支持了共同体主义,因为政治动物总是朝向某个共同目标,人只有在与他人的共同体中才能获得最好的生活,而城邦在塑造其居民性格的过程中也发挥很强的作用。“优良的立法家们对于任何城邦或种族或社会所当为之操心的真正目的必须是大家共同的优良生活以及由此而获致的幸福。”[1](P353)此外,亚里士多德还主张善优先于权利,个体应该积极地参与政府。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2](英)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M].杜汝楫,戴雅民,译.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
[3]David Keyt.Three Fundamental Theorems in Aristotle’s Politics.Phronesis,1987,(1).
[4]田道敏.亚里士多德城邦自然存在论的比较阐释[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6).
[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6]F.D.Miller.Nature,Justice and Rightsin Aristotle’s Pol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范畴篇 解释篇[M].方书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8](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4卷)[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