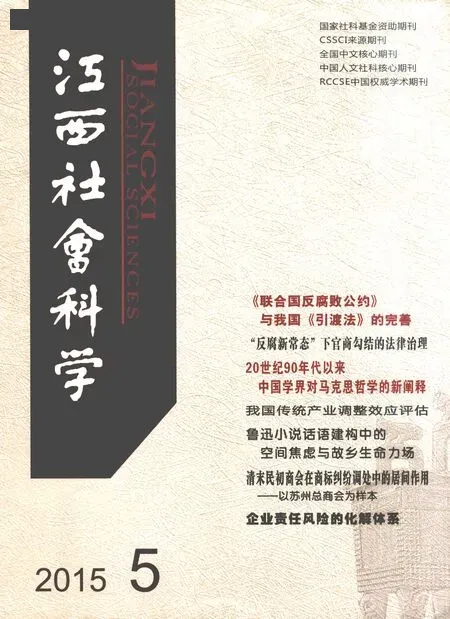《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引渡法》的完善
2015-04-14马德才
■马德才
反腐法治专题【三篇】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有力地惩治腐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反腐之道在于标本兼治,既要高压反腐,又重制度建设,最终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为此本期从当前反腐工作面临的现实难题出发,推出三篇关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引渡法》的完善、官商勾结的法律治理、反腐视角下的犯罪论体系与证据体系一体化的文章,探讨制度建设、法治反腐等相关问题。第一篇文章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视角分析了当前猎狐行动主要方式——引渡的困境,并提出了相应的《引渡法》完善意见;第二篇文章从实证出发剖析了官商勾结的成因,并提出加强市场效率、改善权力配置等对策;第三篇文章从反腐案件的实证分析出发,针对多元犯罪论与一元化司法实践的冲突,提出了犯罪论体系与证据体系一体化构建的思路。
一、“猎狐行动”与引渡困境
十八大以来,我国一方面持续保持国内反腐高压态势,另一方面高度重视反腐败国际追逃工作,外国不能成为一些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腐败分子哪怕逃到天涯海角,也要将他们缉捕归案及绳之以法。因此,为了推进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布局,为了策应中央反腐败工作大局,2014年7月22日,公安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从即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集中开展“猎狐2014”缉捕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先后从69个国家和地区共抓获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680名,是2013年的4.5倍。在这680个人中,全国公安机关直接缉捕归案的有290人,规劝投案自首的有390人,其中有332人是在《通告》发出后投案自首。从涉案金额来看,千万元以上的有208人,超过亿元的有74人。从潜逃境外时间来看,抓获潜逃5年以上的有196人,其中10年以上的有117人,逃跑时间最长的有22年。
虽然“猎狐2014”专项行动作为一个阶段性工作已经结束,但是缉捕逃犯的工作并未终结,即“猎狐行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只要有一名逃犯尚未归案,“猎狐行动”就应当一刻不停地、继续全面深入地推进。2015年1月14日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明确指出,加强国际合作,狠抓追逃追赃,把腐败分子追回来绳之以法。2015年3月26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召开会议,研究部署2015年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决定启动“天网”行动。该行动是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部署开展的针对外逃腐败分子的重要行动,由多个专项行动组成,分别由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人民银行等单位牵头开展,其中公安部牵头开展“猎狐2015”专项行动,重点缉捕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和腐败案件重要涉案人。为此,公安部于2015年3月31日召开全国公安机关“猎狐2015”专项行动部署会,决定从2015年4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组织开展“猎狐2015”专项行动,重点对象是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外逃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涉腐败案件的外逃人员,并在重点国家开展缉捕工作。而且,按照“天网”行动统一部署,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于2015年4月22日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加大全球追缉力度。
可见,“猎狐行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手段和方式。从上述“猎狐行动”来看,我国海外追逃一般有四种方式,即引渡、遣返、异地追诉和劝返。在上述各种追逃方式中,引渡方式是其中较为一种正式的方式,[1](P49)其他三种方式是引渡的替代方案。但是,引渡方式在海外追逃中却存在诸多困境,即缺乏从欧美国家引渡逃犯的法律依据、严格适用双重犯罪原则滞障引渡合作、政治犯不引渡原则阻碍引渡合作、死刑不引渡原则妨碍引渡合作。
二、“猎狐行动”中引渡困境之具体分析
(一)缺乏从欧美国家引渡逃犯的法律依据
根据国际法,一国没有必须引渡的义务,除非负有条约的义务。[2](P339)双边引渡条约可以为我国海外追逃工作提供极大的便利,因为双边引渡条约使引渡合作有章可循,大大提高了引渡的成功率,可以使缔约各方据以克服在引渡合作中遇到的法律困难或者问题,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简便了引渡的程序,明显提高了引渡合作的效率。例如,我国于2000年8月22日依据《中蒙引渡条约》将杨彦军从蒙古引渡回国;我国于2002年4月30日依据《中俄引渡条约》将王德宝从俄罗斯引渡回国;2002年12月26日依据《中泰引渡条约》将陈满雄和陈秋圆从泰国引渡回国。[3](P79-82)在“猎狐2015”行动中,我国于2015年2月3日依据《中意引渡条约》将张某从意大利引渡回国。
自我国和泰国于1993年签订第一个双边引渡条约以来,截至2014年11月我国已与外国签订了39项双边引渡条约,其中29项已经生效。相对而言,我国缔结并生效的双边引渡条约数量并不充足。可见,如果逃犯潜逃至和我国签订有双边引渡条约的国家,那么我国的海外追逃工作就容易了。但是,逃犯却往往潜逃至欧美国家,而这些国家多数又没有和我国签订双边引渡条约,而且有些国家坚持双边引渡条约是向请求引渡国提供引渡合作的前提条件,即持“条约前置主义”的态度。
首先,美国是持此种态度最为典型且严格的国家。基于此,我国早在1997年就开始在各种场合向美国提出缔结双边引渡条约的建议,但是美国却对此一直未给予积极的回应。正是因为如此,截至目前,我国还没有正式从美国引渡过一名逃犯,这显然是一种非正常的情形,而这种情形遂使得美国成为我国逃犯的最佳躲藏地。其次,荷兰不仅持“条约前置主义”的态度,而且在引渡问题上还不接受互惠原则,引渡只能依引渡条约进行。我国没有和荷兰签订双边引渡条约,所以我国就很难从荷兰引渡逃犯。例如,“红色通缉令”1号嫌犯杨秀珠外逃后,于2005年5月在荷兰落网。而要想将杨秀珠缉捕归案,对她诉诸引渡程序已然不可能,只能走遣返非法移民之路。再次,英国曾经是持“条约前置主义”态度的典型国家。我国和英国未签订任何司法合作的双边条约,也不存在从英国引渡逃犯的先例,而我国有一些重大经济犯罪案件的嫌疑人就躲藏在英国。第四,加拿大也奉行“条约前置主义”态度。我国和加拿大未签订双边引渡条约,加拿大也未向我国正式引渡过逃犯。厦门远华走私案的主要案犯赖昌星于1999年8月潜逃至加拿大,正是由于我国和加拿大之间没有双边引渡条约关系,因此我国没有启动引渡程序而却选择了遣返的方式。[4](P6-8)2011年7月23日,赖昌星被加拿大遣返回我国。
总的来看,我国缺乏从欧美国家引渡逃犯的法律依据。尽管2007年我国与澳大利亚签订了《中澳引渡条约》,但是由于澳大利亚议会尚未批准,因而该条约尚未生效。这样,当逃犯外逃至这些国家且我国向该国提出引渡请求时,该国可能会以没有引渡条约或引渡条约尚未生效为由拒绝引渡。
(二)严格适用双重犯罪原则滞障引渡合作
双重犯罪原则,是指依照请求引渡国和被请求引渡国的法律,引渡客体的行为是犯罪行为。该原则要求“一个人的行为按照请求引渡国的法律是犯罪,而且按照被请求引渡国的法律也是犯罪,才能准评引渡”[2](P342)。该项原则得到了有关引渡立法及国际条约的确认,是引渡制度中一项不可动摇的刚性原则[5](P23)。它之所以被确立,主要是因为:罪刑法定原则在国际刑事合作领域的适用;相互尊重主权;保护引渡客件的基本人权;互惠基础。[6]我国《引渡法》第7条也确立了双重犯罪原则与双重可罚性原则。
鉴于腐败的全局性和全球性,第58届联合国大会于2003年10月31日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并于2005年12月14日正式生效。我国于2003年12月10日签署并于2005年10月27日批准了该《公约》。《公约》第43条第2款确认了双重犯罪原则,即在引渡合作事项中,引渡请求中所指的犯罪行为在请求缔约国和被请求缔约国的法律中都是犯罪。
但是,如果该原则的适用过于严格,亦即既要求按请求引渡国和被请求引渡国的法律引渡客体的行为必须构成犯罪,而且还要求犯罪应受刑罚处罚,那么引渡客体则同样难以被引渡。1928年的布莱克墨引渡案(Blackmer case)和1933年的因索尔引渡案(Insull case)均采取了严格适用双重犯罪原则的立场。[7](P309)其次,适用该原则过于严格还表现在要求请求引渡国和被请求引渡国在罪名和犯罪类别方面相一致。[7](P310)最后,适用该原则过于严格还表现在要求请求引渡国和被请求引渡国在犯罪构成要件方面相一致,如1949年的艾斯勒引渡案(Eisler case)就是明证。[7](P309-310)显然,这种严格适用双重犯罪原则的做法会影响国家之间的引渡国际合作。
相比之下,我国和外国的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法律制度等各异,在认定犯罪问题上的标准不一样,因此有些行为在我国看来是犯罪行为,而在外国看来则是非罪行为,即使我国和外国均认定为犯罪,但是,犯罪类型或犯罪构成也可能不尽相同。如果外国严格适用双重犯罪原则,那么当逃犯外逃至外国且我国向其提出引渡请求时,它就可能会以其引渡请求不符合双重犯罪原则为由拒绝引渡。
(三)政治犯不引渡原则阻碍引渡合作
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是指被请求引渡国根据其本国法律如果认为请求引渡所针对的犯罪构成政治犯罪的,就拒绝请求引渡国的引渡请求的一项引渡原则。现代引渡制度的诞生即是以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产生为主要标志的,它源自古代自然法思想和现代人权保护理论的接榫,也符合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惯例。[8]该项引渡原则已经得到了各国的公认。我国《宪法》和《引渡法》也分别确立了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前者第32条第2款规定:我国可以给予那些因为政治原因而要求到我国避难的外国人以受庇护的权利;后者第8条第3项规定:我国应当对于那些因政治犯罪而请求引渡的或者我国已给予引渡客体受庇护权利的人拒绝引渡。
但是,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法律等方面所存在的较大差异使得国际上目前还没有一个关于政治犯罪的统一概念,即“政治罪”的概念还存在着严重的困难[2](P344-345),因而在决定哪些犯罪行为属于政治犯罪是由各国自由裁量。这样,腐败犯罪就有可能被一些国家认定为政治犯罪,加之,腐败类犯罪的嫌疑人一般又都是公职人员,且这些犯罪嫌疑人到国外后,大都提出政治避难的要求,[4](P53)那么,当逃犯外逃到认定腐败犯罪为政治犯罪的国家,当我国提出引渡请求时,它们就会以政治犯不引渡原则为由拒绝引渡。因此,政治犯不引渡原则遂成为我国引渡外逃犯罪嫌疑人的障碍。
(四)死刑不引渡原则妨碍引渡合作
死刑不引渡原则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第二次废除死刑运动的高潮出现而产生的,现今几乎各国有关引渡的国内法和引渡条约都规定了死刑不引渡原则,亦被有关国家的引渡实践所采纳。[9](P86-94)它对于保护引渡客体的人权、进一步促进国家废除死刑、保障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意义重大。其中,在废除死刑方面,国际法层面和国内法层面均已成为明晰且难以逆转的潮流。一方面,包括《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定书》在内的多项国际法文件已禁止适用死刑;另一方面,已有约140个国家在法律文本上废除了或者在法律实践中不再适用死刑。[10]虽然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种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但是我国刑法典中尚有55种死刑罪名,这在现今保留死刑的国家中仍然居于前列,特别是其中属于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罪名还多达30余种。[11]这样,我国法定刑中死刑数量过多,特别是腐败类经济犯罪法定性死刑较多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追逃目标的实现。
在确立死刑不引渡原则的引渡条约中,既有废除死刑国家之间的引渡条约如《澳大利亚与荷兰引渡条约》,又有保留死刑国家之间的引渡条约如《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引渡条约》。2005年的《中西引渡条约》第3条第8项、2007年的《中法引渡条约》第3条第7项、2007年的《中澳引渡条约》第3条第6项对死刑不引渡原则作了相同规定,亦即根据请求方法律,引渡对象可能因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被判处死刑,除非请求方保证不判处死刑,或者在判处死刑的情况下不执行死刑的,应当拒绝引渡。所以,该原则是被请求引渡国拒绝请求引渡国引渡请求的原因之一,它已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绝大多数请求引渡国难以实现引渡请求的一个障碍。
三、“猎狐行动”中的引渡困境的因应对策
(一)加紧和美国等欧美国家签订引渡条约及采取引渡替代措施
我国已经和法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意大利、葡萄牙等西方发达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不过仍然未和美国、英国、荷兰、加拿大等国签订引渡条约,而这些国家一般持“条约前置主义”态度,所以为了将逃犯从这些国家引渡回国,应当加紧与美国等欧美国家签订引渡条约,只有在签订双边引渡条约的情况下才能和它们开展引渡合作。
与此同时,必须努力探寻引渡的替代措施,以解决在无稳定引渡合作关系的情况下如何将外逃罪犯缉捕回国。归纳起来,引渡的替代措施通常包括遣返、异地追诉和劝返。[4](P12-19)例如,由于中美之间没有双边引渡条约,双方只能寻求其他机制以缉捕在逃人员,即根据移民法被遣返、被驱逐出境,如2004年4月16日,余振东被遣返一案曾被舆论认为是在尚未签订引渡条约的背景下中美司法合作的成功范例。近年来,中美之间此种司法合作更为积极,如2015年3月17日外逃贪官乔建军和他的前妻赵世兰因为涉嫌欺诈和洗钱,被美国加州联邦检察官正式起诉。2015年4月9日至10日,美国国土安全部约翰逊部长访华期间与中方达成一致意见,美方同意精简遣返中国贪官流程。即同意精简遣返收到最终递解令的中国公民的流程。美国海关与移民执法局将与中国公安部密切合作,核实申请旅行证件的中国公民的身份,同时确保安排定期包机计划,促进遣返工作。中美双方将与有关执法部门一道,开展密切合作,就追逃与遣返案件加强信息分享,就证据充分的重点案件定期交流工作进展,就遣返逃犯、核查非法移民身份积极开展合作。中美双方同意,任何一方都不会为逃犯提供庇护,将在各自法律范围内,努力将其实施遣返。显然,中美两国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妥协,美国同意精简遣返中国贪官的流程,对藏匿在美国的中国贪官来说,将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打击。
另外,我国还可以援引多边公约和那些与我国没有引渡条约的国家开展引渡合作。例如,我国和加拿大之间没有签订引渡条约,和澳大利亚的双边引渡条约尚未生效,但是在此种情形下我国并非无计可施,而是完全可以援引我国和澳大利亚、加拿大共同参加的国际公约如《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以开展引渡合作,因为根据条约必须遵守原则,缔约国有遵守国际条约的义务,如《公约》第44条对引渡机制作了详尽规定,所以我国可以援引《公约》中的引渡条款与它们开展引渡合作,以解决我国与它们没有双边引渡条约或双边引渡条约尚未生效的尴尬境地。
(二)完善《引渡法》
1.规定罪名和犯罪类别相一致及双重犯罪原则的例外
鉴于双重犯罪原则的严格适用会阻碍引渡合作,故而各国在适用双重犯罪原则上出现了弱化趋向,即同一行为如触犯了请求引渡国和被请求引渡国的刑事法律,就可以认为符合双重犯罪的条件,即使其罪名和犯罪类别方面存在差异。在此方面,《公约》出于有效惩治腐败犯罪,也突破了要求罪名和犯罪类别相一致的传统双重犯罪原则,其第43条第2款规定:不论请求缔约国和被请求缔约国的法律是否在犯罪类别或者犯罪名称方面规定相同,只要请求缔约国和被请求缔约国的法律两者均认为是犯罪就可认定符合双重犯罪原则。但是,在不要求罪名和犯罪类别相一致的问题上,我国《引渡法》并未予以明确规定,这既和双重犯罪原则的普遍做法不尽一致,又和《公约》所规定的不要求罪名和犯罪类别相一致存在差异,所以为了依据《公约》第65条第1款的规定切实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在修正《引渡法》的时候,应当作出如下补充性规定,即只要某一行为按照请求引渡国的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均作为犯罪予以处罚亦即符合双重犯罪原则,而勿需强调其罪名和犯罪类别的一致性。
而且,为了防止严格适用双重犯罪原则带来的弊端,产生了双重犯罪原则的例外,亦即在特殊情况下,引渡客体的行为即使按照被请求引渡国的法律不构成犯罪,也可被引渡。《公约》出于有效打击腐败,其第44条第2款对双重犯罪原则的例外作了规定,即在缔约国本国法律允许的情形下,缔约国可就本公约所涵盖但依本国法律不予处罚的任何犯罪准予引渡。相比之下,我国《引渡法》对双重犯罪原则的例外则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同样地,这既和双重犯罪原则的发展趋势和普遍做法不尽一致,又和我国承担的《公约》义务相悖,所以,为了与《公约》的规定相符合,我国的《引渡法》应当确立双重犯罪原则的例外,亦即依照请求引渡国的法律认为是可罚的行为,而根据我国的法律是不可罚的,我国仍然可以准许引渡。
2.明确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适用范围限制
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确立后随着国际社会对打击恐怖主义犯罪、腐败犯罪等的重视,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12],其表现之一是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适用范围受到限制。正是因为如此,有关国际条约如《公约》、《制止恐怖主义爆炸公约》等对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限制都作了规定。其中,为了加强国际合作,防止腐败犯罪分子利用政治犯罪作为护身符逃避惩处,《公约》明确将腐败犯罪排除在政治犯罪以外,其第44条第4款规定腐败犯罪不适用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然而,我国《引渡法》对此却未作规定。这既不利于防止某些犯罪分子借政治犯罪逃避本该承担的刑事责任,同时也与我国承担的《公约》义务背道而驰。因此,从善意履行条约义务的角度出发,我国《引渡法》对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限制应当作出规定:对于那些因政治犯罪而请求引渡的或者我国已给予引渡客体受庇护权利的人拒绝引渡,但是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不认为是政治犯罪的除外。
3.增设死刑不引渡原则
《引渡法》并未明确规定死刑不引渡原则,即既没有把死刑不引渡原则列为《引渡法》第8条的绝对不引渡情形,也没有将死刑不引渡原则规定为《引渡法》第9条的相对不引渡情形。这不仅与大多数国家的引渡法明确规定死刑不引渡原则的普遍实践不一致,而且与死刑不引渡原则作为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不相称,会影响我国与外国开展在引渡领域的国际合作,同时会影响我国与其他国家签订引渡条约的进程,继而会影响我国请求引渡外逃腐败犯罪者。因此,为了避免出现上述的窘境,《引渡法》理应理直气壮地规定死刑不引渡原则,即根据请求引渡国法律,引渡对象可能因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被判处死刑,除非请求引渡国保证不判处死刑,或者在判处死刑的情况下不执行死刑的,我国应当拒绝引渡。该原则可作为《引渡法》第8条“应当拒绝引渡”中的一种情形。实际上,《引渡法》对死刑不引渡原则的明文规定,还可克服妨碍我国行使刑事司法权的困境。因为,如果我国规定死刑不引渡原则,那么我国可以将罪犯引渡回国,只是不能对其判处死刑,或者即使判处死刑也不能执行而已,然而我国毕竟可以对其行使刑事司法权。反之,如果我国不规定死刑不引渡原则,则被请求引渡国可根据死刑不引渡原则,根本就不会将罪犯引渡至我国,那么我国连行使刑事司法权的可能性都完全丧失了。[13](P179)亦即《引渡法》规定死刑不引渡原则,不仅不会妨碍我国刑事司法权的行使,反而还可克服妨碍我国刑事司法权行使的困境。
[1]黄风,赵林娜.境外追逃追赃与国际司法合作[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2]詹宁斯,瓦茨.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二分册)[M].王铁崖,李适时,汤宗舜,周仁,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3]黄风.引渡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4]黄风,赵林娜.国际刑事国际司法合作:研究与文献[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5]黄风.中国引渡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6]M.Cherif Bassiouni,International Extradition:A Summary of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Practice and Proposed Formula,Wayne Law Review,1969,p.733.
[7]赵秉志.国际区际刑法问题探索[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8]章成.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法理基础探索[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
[9]马德才.国际法中的引渡原则研究[M].北京: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2014.
[10]赵军.死刑存废的民意维度——以组织卖淫可罚性观念的测度为中心[J].法学研究,2015,(2).
[11]赵秉志.死刑改革新思考[J].环球法律评论,2014,(1).
[12]马德才.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发展趋势探析——兼论我国《引渡法》的完善[J].江西社会科学,2009,(2).
[13]赵秉志,陈一榕.论死刑不引渡原则[A].高铭暄,赵秉志.当代国际刑法的理论与实践[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