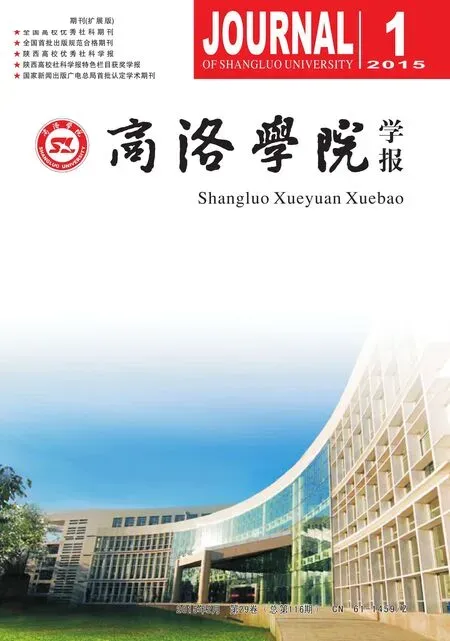鲁迅小说创作的意义转换方式探析
2015-04-11韦文韬
韦文韬
(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重庆400715)
鲁迅小说创作的意义转换方式探析
韦文韬
(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重庆400715)
对鲁迅小说的形式研究颇多,从“形式分析进入意义”固然可以增加对鲁迅艺术创造力的理解,但是意义之间的转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点,它涉及人物命运的转折和故事意义的深化。就小说的转换方式这个视角对鲁迅小说进行研究,可以取得对其小说创作方面的了解。
鲁迅小说;意义;转换
1923年,茅盾高度评价鲁迅的小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1]。确实,不仅是《呐喊》,连《彷徨》一起,每一篇都是不同的。足见鲁迅小说的创造能力很强。然而这25篇小说故事究竟有怎样的一个内在意义的转换?明白小说中故事的转换,也就明白茅盾所谓的“鲁迅的小说一篇一个形式”的问题。故事的转换当然有赖于一个人的思想穿透能力和艺术技巧的运用能力。这些和鲁迅早年的经历及其丰富的学识有着密切关系。童年的家庭变故,国家的分崩离析,民众的愚昧病苦都是他感觉敏锐的基础,而“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常识”[2]则是他艺术技巧创造的来源。于是《呐喊》和《彷徨》应运而生,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产生。
从比较上来看,《呐喊》和《彷徨》有很大的不同,即《呐喊》多是施害者和受害者以及叙事者“我”的关系,也常常体现为“时间”“空间”的关系。但是相反,《彷徨》则除了《祝福》一篇外,都是人物与人物之间对话的、对比的、心灵自觉表现的关系。笔者认为,主要有时间的巧变暗示、空间铺展回缩、人物关系的直接呈现等意义转换的技巧。
一、时间的巧变暗示
时间是物质本身的持续性,物质运动的时序和前后联系。而文学中的时间常常是主观上的时间,即“心理变形”,就是在作品中感受到了时间,故意扭曲时间,使其延长或缩短,甚或是遗忘,使读者通过产生对时间的意识来对故事中人物命运的观察、认识和感受。鲁迅小说中的时间常常呈现为前后对应的变异,此类小说如《孔乙己》《药》《祝福》。《孔乙己》中对孔乙己这一个封建文人的叙述是“蜻蜓点水式”的勾勒。但是在最后一段“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了中秋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这一段照应了中间一段“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老板和孔乙己两个人都对时间有了一个共同的忠诚信任,直到老板再也没提起的时候,说明孔乙己便已经死掉了。一个人物的命运就此转换,故事也从中自然而然地转换。《药》中的最后一部分“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天明未久。”这些暗示性时间词语都在说明另一个故事的若隐若现,即夏瑜以及他的革命志士不为民众理解的可怜悲哀。故事的重迭突兀,日常时间和小说时间交叉,使人始料不及,这在其它小说中是不存在的。《祝福》中的祥林嫂是要靠时间的倒叙设置来深化人物的命运的。历来对祥林嫂的人物命运都不能极尽。但是若注意到了倒叙的时间,则明白故事是如何的迷离深刻。如开端一部分中的“一想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那是下午……”,后文提到祥林嫂被柳妈等人讥讽欺骗,被封建思想敲剥“关于死后的事”,于是把最后的钱捐去买了一道门槛。一个人物的生前死时的被残酷剥削的现实境况,整个社会的愚昧麻木,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也就表现得历历在目。
时间是小说的生命线,心理上的时间感受是每一篇小说都必然存在的。只有通过时间感受本身,才能自由进入绵缈的时间里,使作者读者获得超越于现实束缚的解放,沐浴在审美的文学艺术世界中。时间可以起到转换故事意义的作用。尤其是在拉丁美洲,中短篇更受读者的欢迎,许多长篇素材都被压缩凝练。或者是在经济发展迅速的当下时代,时间常常被做了各种各样的变形,凸显出其中趣味性的哲理。爱因斯坦在其《相对论》里认为,“如果时间接近光速,那么其体积沿着运动方向的广延性便会缩小”[3]。这和鲁迅的短篇小说很像,体积小却寓意深刻。智利评论家阿里埃尔·多弗曼认为:“生活的意义在于运动,纯粹在于时间的痉挛式的……它向我们揭示的是人物的唯一命运,尽管都不在正常时间的范围之内,但都要跌入死亡的牢狱,或者坠入茫然和无限的冰冷的空间里去,而结尾的时间几乎消失了”[4]。鲁迅正是变形了时间,才能在茫茫无期的黑夜里,遥遥无期的虚空中,去感受到个人的命运和中国国民的命运。
二、空间的铺展回缩
马克思哲学上的“空间”意义为运动中的物质的伸张性和广延性。而文学中的“空间铺展回缩”则是指空间的频繁设置转换或者空间的周围环境挤压,使得人物的故事随着空间的变化而逐渐变化,形象开始成型,主题渐而突出。从本文研究鲁迅小说的意义转换方式来说,“空间转移”即是“地点转移”。
关于“空间转换”,1945年约瑟夫·弗兰克在《西旺尼评论》上发表了他的很重要的论文《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此文认为,“T.S.艾略特、庞德、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等人的作品是空间的,他们用“同在性”取代“顺序性”,现代主义作家“试图让读者在时间上的一瞬间从空间上而不是从顺序上理解他们的作品”[5]。弗兰克主要从物理上的空间变换来阐发一个作品的多种意义结构,并且认为读者也是从心理空间上来接受作品的深层意义的。该论文甚至被认为文学空间形式的滥觞之作。不管如何,“空间转换”是伴随着时间流动而存在的,只是时间在此已转化成了空间。中国古代和现代的诗歌中之所以频繁地出现“空间转换”,是因为古代诗歌直接地缺席了“吾”,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以物代人”。现代诗歌虽然有“我”的存在,但是为达到诗意的形象化象征化,以物代人,托物言情是基本的手法。鲁迅是一位优秀的诗人,显然小说中受到影响。王富仁在论鲁迅的《呐喊》《彷徨》时说:“只有我们把鲁迅同二十年代青年文学家的作品放在一起加以感受,我们就会知道,鲁迅更加重视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6]。这虽有些偏颇之见,但证明了鲁迅对空间的重视。然而本文不谈他的“空间意识”,而简要探讨他的空间转换对小说意义变化的作用。如《明天》中的单四嫂子抱着小孩去看病,“接过药方,一面走一面想。她虽是粗笨女人,却知道何家与济世老店与自己的家,正是一个三角点;……孩子又不住的挣扎,路也越觉得长。”这地点的变化是要了孩子的命的。它改变了故事,使得孩子死了,很多人相继趁吃趁喝。夜晚,单四嫂子在屋子里接受着空间的压迫,久久难以入睡,实际上这里移植了鲁迅的生命感观。鲁迅常常感觉到周围环境对自我的压迫,空间造成了人的孤独、虚无和郁闷。同时,鲁迅早年四处奔波,为理想为生活为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改变,备受各种压力,冒着生命之危险逃难,“地点的频繁转换”已逐渐化入了他的小说创造之中。《示众》一文更是从“空间转移”上逐步地揭露了看客的不同面貌,展示了中国旧社会无聊愚昧的病源所在。当然最有深刻意义的当属于钱理群教授所认为的中国知识分子那种无处落脚的漂泊之感。如《故乡》《祝福》《酒楼上》《孤独者》等。“我”是离了家回了家又继续离了家的始终为生计为理想而漂泊着,无依无靠。这种“空间转移”,把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的徘徊、迷茫和绝望揭示得深刻、透彻,直指那个年代里一种悲凉无奈的人生。
三、人物关系的直接呈现
所谓的“人物关系的直接呈现”是为了下文的论析需要,本人创造出的一个概念。“人物关系的直接呈现”是《彷徨》小说中的主要艺术形式。它主要反映了施害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它不需要诉诸于时间的巧妙设置和空间的有意转移,而是直接地从人物的对话中或通过叙事者的叙述语言中展现了人的故事,从而转换了故事的意义。这种转换方式更为直接地描写出愚昧的民众、邪恶的封建卫士以及虚伪的知识分子等一批国民形象,并且使他们相互对比,呈现矛盾,这是这批小说的特色之处。
(一)对话的呈现人物关系
《彷徨》里的很多小说的人物故事都是在具体的直接的场景对话中逐步呈现出来的。场景对话在具体的转换故事中,起到单刀直入的作用。如《肥皂》《弟兄》《长明灯》《高老夫子》《离婚》《头发的故事》《风波》《端午节》等。这些人物形象及其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在对话中自然而然地映现的。《肥皂》中的四铭、《长明灯》中的阔亭、四爷、方头等,《弟兄》中的益堂、沛君、月生等,《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离婚》中的庄木三、爱姑、七爷等,《头发的故事》中的前辈先生,《风波》中的赵七爷、七斤、九斤老太等,《端午节》中的方炫绰等,都是在对话中体现了个性,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九斤老太说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从中嘲讽了现在的社会,暗换了故事的内核。后面的对话“皇帝坐了龙庭没有呢?/他们没有说/咸亨酒店的人没有说吗/也没人说。”就在这对话中,把故事的变化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但是这些文本之间又有着具体的不同,那是在时间和地点上的处理技巧不一样,故事的收尾也纷呈多彩。
(二)叙述的呈现人物关系
高行健认为:“一部小说的展开、结局乃至整个结构,主要是通过叙述语言来体现,人物的对话不是不重要,可人物的对话较叙述语言终究要单纯得多”[7]。所谓“叙述的呈现人物关系”只是作者的叙述,叙事者和人物分离,甚至是没有人物的对话。作者想借人物去表达某种观念性的东西对人的一种迫害或者影响。如《白光》《一件小事》《兔和猫》《狂人日记》《伤逝》等。这些小说在大体上相同,但是由于作者批判的点散向各处,所以形式各异。作者有时候在批判施害者一方,如《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作者是寄予同情的,其另一面是社会、国家和民众分别对知识分子的歧视,造成了知识分子人格的分裂和死的哀怜。《白光》中的陈士成也是受作者同情的。陈士成的最后之死是举试未可,并且受了“白光”的诱惑后跳水死亡。更多时候作者在批判施害者一方的同时,也在批判了受害者一方,正如“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狂人”在反抗社会吃人的时候,却在最后发现自己也在吃人。但他继续呼吁救救孩子,这是绝望中的批判与反抗。鲁迅往往在批判受害者一方的时候,有一个共同点,即寄予了一定的同情。如孔乙己有一个强于他人的地方在于从不拖欠酒钱,而阿Q是一个无名无姓无房的无产者。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社会对底层者的不公,是不公造成了一个人的精神胜利法的根源之一。“叙述的呈现人物关系”在转换故事的时候,注重于叙述中的转换,如“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从中可以明白,故事的意义已悄然转换。
(三)“我”介入的人物关系
这两个小说集有很多“我”的掺入方式。“我”的介入方式不仅仅是叙事者叙述方式的问题,而且更多的是意义呈现方式的问题和诗意穿透的问题。鲁迅是一位诗人,其小说也是充满了诗意的。有时他需要在小说人物身上寄予生命的思考,有时候他需要“我”的介入,直接抒发对生命的感悟。钱理群认为:“鲁迅式的沉思是鲁迅小说的一个突出的特点”[8]。它使鲁迅将自我的生命链接了大众的命运,是鲁迅对生存与死亡、背叛与反抗、希望与绝望等作一个综合的考察,意味悠长。例如《故乡》的最后一段“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时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从小说的一开始“我”的回乡到看见家乡的情形,小说让人物的性格自行出现,这里没有具体的言语对抗,只有个人面对这个现实的残酷与无奈。最后闰土的变化让“我”明白一个对于人世的思考,即其时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于是,因为“我”的介入,小说变得更加抒情,也更具哲理。
时间的巧变暗示、空间的铺展回缩和人物关系的直接呈现常常互相渗透,共同地依存于一个故事的构造之中。尤其是在鲁迅这么短的小说篇幅里,没有独特超常的艺术手段,是很难表达如此深刻的思想并且化入诗一般的艺术境界的。鲁迅曾自我认为,这些小说是改了又改,尽量简洁,能准确表达意思就可以了。而他心目中的好小说则是“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可见,不对题材了然于胸,不综合地运用现代的各种技巧,很可能无从下笔或者小说面目全非。尽管很难辨清具体的小说意义转换方式,但细读文本,细加揣摩,仍然可以区分各自在小说中的作用和分量。其中总有一个独特显明的转换方式把小说推入高潮,完成小说的意义升华。这就需要读者也能跟随鲁迅深入其中故事的背后,抓住那些妙不可言的具体手法和整篇小说的结构设置。
[1]茅盾.茅盾文艺理论批评选[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23.
[2]鲁迅.鲁迅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415.
[3]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M].杨润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3.
[4]阿里埃尔·多弗曼.略萨与阿格达斯[M].张建平,陈余德,译.北京: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3:237.
[5]程锡麟.叙事理论的空间转让[J].江西社会科学,2007(5):30.
[6]王富仁.时间·空间·人(四)[J].鲁迅研究月刊,2000(2):3.
[7]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10.
[8]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50.
(责任编辑:罗建周)
A Study on Meaning Transformation Pattern in Lu Xun's Novels
WEI Wen-tao
(New Poitry Research lnstitute of 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
There are many studies on forms of Lu Xun's novels,"formal analysis into meaning"may increase the understanding of Lu Xun's artistic creativity,but the conversion in meaning is a very important research point,it relates to the fate of the characters and the turning point of the story of meaning.The study of Lu Xun's no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version can achieve a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novel creation.
Lu Xun's novel;meaning;transformation;
I206.6
A
1674-0033(2015)01-0037-04
10.13440/j.slxy.1674-0033.2015.01.009
2014-10-21
韦文韬,男,广西罗城人,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