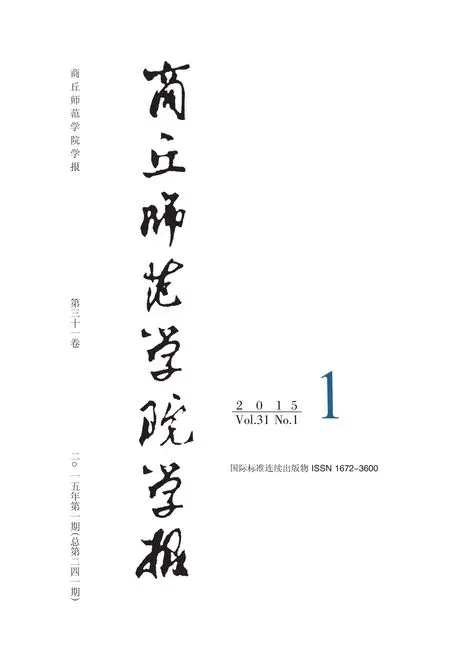论涉外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规则
2015-04-11王济东
王 济 东
(商丘师范学院 法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论涉外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规则
王 济 东
(商丘师范学院 法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跨国劳动力流动大量增加,反映在国际私法立法方面,就是劳动合同法律适用规则的创设和完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与最密切联系原则是确定劳动合同准据法的最主要方法。但是,随着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的不断加强以及弱者利益保护原则日益得到重视,强制性规则对劳动合同法律适用的影响显著增强。劳动合同法律适用规则呈现出复杂化、精细化、体系化等多种发展趋势。我国《法律适用法》有关劳动合同法律适用的规定,虽然体现了多数国家的一些普遍做法,也有利于提高审判效率,但它排除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贯彻也不彻底,导致过多地适用本国法,值得反思。
涉外劳动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强制性规则;法律适用法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随着各国经济交往的不断增加,跨国劳动力流动现象也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1]。当劳动合同具有涉外因素时,就会转变成涉外劳动合同。如果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因涉外劳动合同发生争议而诉至法院,法院就需援用冲突规则解决具有涉外因素的劳动合同争议。
面对涉外劳动争议日益增多的现实,许多国家都制定了劳动合同法律冲突规范,但不同国家所制定的劳动合同法律冲突规范也是内容各异,或完备或疏简。仔细考察不同国家劳动合同法律冲突规范,可以发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是最主要的法律选择方法。此外,由于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的不断加强以及弱者利益保护原则日益得到重视,强制性规则对劳动合同法律适用的影响也显著增强。
一、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源远流长。16世纪,法国学者杜摩兰在其著作中已经提出该原则[2],其成为合同准据法选择的基本原则,也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尤其是二战之后,国际经贸交往飞速发展,国际民商事法律冲突更为普遍,传统冲突规范由于本身具有的僵硬性,越来越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为了更好地解决法律冲突,各国纷纷对传统冲突规范进行软化处理。意思自治原则首先强调的是当事人合意在法律选择中的作用和地位,能够适应纷繁复杂的跨国民商事争议,因此倍受青睐,在各国国际私法中纷纷得到采纳。
(一)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劳动合同法律选择中的运用
劳动合同脱胎于传统民事合同。“劳动合同的准据法原则上与一般合同相同,也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3]3111900年比利时《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前,由于各国视劳动合同为传统民事合同,从逻辑上讲,适用于一般涉外民事合同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也应适用于涉外劳动合同。
在20世纪晚期和21世纪初的一些国际私法立法中,大都把意思自治规定为劳动合同法律适用的主要方法。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于2008年6月17日通过的《关于合同之债法律适用的第593/2008号条例》(以下称“罗马Ⅰ条例”)第8条第1款明确规定:“雇佣合同①,依当事人根据第3条规定所选择的法律。”其实,当事人意思自治一直是欧洲国际私法在(劳动)合同之债领域解决法律冲突的首要原则。1980年《关于合同之债法律适用的罗马公约》(以下称“1980年《罗马公约》”)第6条就已把当事人意思自治规定为劳动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罗马Ⅰ条例第8条基本上重申了1980年《罗马公约》第6条的规定,只是措辞略有不同而已[4]171-176。此外,2001年修正的《韩国国际私法》、2007年日本的《法律适用通则法》等都把当事人意思自治规定为劳动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方法。
(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适用的限制
凡原则皆有例外。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解决劳动合同法律冲突时也会受到一定限制。一方面,当事人意思自治有可能被当事人滥用;另一方面,作为劳动合同当事人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相比处于弱势,形式的意思自治未必能充分体现劳动者的选择自由[5]。
在劳动合同法律适用领域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方式主要有:(1)对当事人选择法律的形式进行限制。有些国家或地区的国际私法要求当事人以明示的形式选择劳动合同的准据法,如1987年奥地利共和国《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第44条第3款规定:“只有明示的法律选择才有效。”(2)对准据法的范围进行限制。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121条第3款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劳动者习惯居所地国家的法律,或雇主的营业机构所在地、住所地或习惯居所地国家的法律。”该条把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范围限制在劳动者习惯居所地法律、雇主的营业机构所在地、住所地或习惯居所地国家的法律之内②。(3)当事人的选择不得违反国家的公共秩序。(4)当事人不得选择冲突规范。(5)当事人的选择不得排除各国专门保护受雇人的强制性规范和国际劳工法的公法规范[6]285-286。罗马Ⅰ条例第8条第1款在赋予当事人选择自由的同时,又规定此种法律选择的结果,即不得剥夺未进行法律选择时依照本条第2款、第3款和第4款规定应适用的法律中那些不得通过协议加以减损的强制性条款给雇员提供的保护。
目前,在劳动合同法律适用领域,多数国家都赋予当事人合意选择法律的自由,但同时也会对当事人意思自治施加或多或少的限制。适当的限制能够防止当事人滥用意思自治原则,从而有利于更好地发挥该原则的功能和作用。
二、最密切联系原则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已成为许多国家或地区国际私法解决劳动合同法律冲突的首选方法。但是,在当事人未作法律选择时,应当如何确定劳动合同的准据法呢?从现有国际私法立法来看,最密切联系原则已成为在当事人未进行法律选择时确定劳动合同准据法的重要方法。
(一)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劳动合同法律选择中的运用
在劳动合同领域,最密切联系原则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奥地利共和国《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基本原则规定了下来,它可能适用于冲突法的所有领域,当然也包括劳动合同领域。其第1条开宗明义地规定: “与外国有连结的事实,在私法上, 应依与该事实有最强联系的法律裁判。本联邦法规所包括的适用法律的具体规则, 应认为体现了这一原则。”第44条第1款、第2款规定:“(1)劳动合同,适用受雇者经常工作地法律。受雇者如果被派往他国工作,仍应适用该法。(2)如果受雇者通常在一个以上国家工作或者无经常工作地点,则适用雇主的惯常居所(或者第36条第2句所指的营业所)所在地国家的法律。”根据第1条之规定,如果涉外劳动合同案件的准据法依照第44条第1款、第2款来确定,则该准据法的选择也体现了最密切联系精神。土耳其共和国《关于国际私法与国际民事诉讼程序法的第5718号法令》第27条第1款首先规定劳动合同依当事人选择的法律,第2款和第3款规定了在当事人未作法律选择时如何确定劳动合同的准据法③,而第4条又规定“如果根据当时的情况,劳动合同与另一法律具有更密切联系,则劳动合同适用该另一法律,而不适用本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可见,根据第44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所选择的劳动合同的准据法,在通常情况下是体现了最密切联系精神的,第4款规定只是在例外情况下起到矫正作用,意在彻底贯彻最密切联系原则。此外,瑞士等国的国际私法也规定在当事人未选择法律时,劳动合同适用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二)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具体化
最密切联系原则本身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它仍然要采用连结因素作为媒介才能确定劳动合同的准据法。不过,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固定连结点,而是弹性的联系概念。一个合同之所以适用某国法,不是因为该国是合同的缔结地或履行地,而是因为该法与合同存在的联系。这就提高了法律适用的灵活性,有利于国际交往和公正合理地对待当事人的利益。但由于其适用需要法官对国家、社会、当事人的利益及其客观标志进行综合考察,因而给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易于导致主观随意性,减损法律适用结果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并影响案件的公正[7]365。为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为法律选择提供具体标准,各国立法都采取了相应措施[8],对最密切联系原则需要进行具体化,以便在法律适用的灵活性与确定性之间保持适度平衡。
在劳动合同法律适用领域,各国国际私法在对最密切联系原则进行具体化时,通常考虑以下连结点:(1)劳动者惯常工作地。对普通劳动合同来讲,劳动者通常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国家或法域履行劳动合同,完成工作任务,该地即为劳动者惯常工作地。劳动者在惯常工作地履行劳动合同,日常活动也在本地开展,其工作和生活都要受本地法律的约束。而且,劳动者长期在惯常工作地生活,对本地法律制度和风土人情相对也更为了解,这对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是较为适宜的。对于用人单位来讲,劳动者惯常工作地既是劳动合同实际履行地,也是其对劳动者开展日常管理的实际地点,必须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因此,劳动者惯常工作地法律通常被各国立法者认为是与劳动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如1998年《突尼斯国际私法典》第67条、2007年日本《法律适用通则法》等即采取这种规定。(2)雇主的营业所所在地、住所地或惯常居所地。有些劳动合同并无劳动者惯常工作地,如国际航空公司、远洋货轮运输公司与它们的雇员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因为国际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或远洋货轮运输公司的海员的实际工作地点往往难以确定[4]177。对于这些劳动合同,有些国家立法规定适用雇主营业所所在地国家的法律,或者无营业所所在地时,适用其住所地或惯常居所地国家的法律。
当然,对最密切联系原则进行具体化所选取的连结点所指向的法律,有时并不是与劳动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因此,许多国家在对最密切联系原则进行具体化的同时,又规定了例外条款,明确规定如果总体情况表明,劳动合同与另一国有更密切联系时,则适用该另一国法律,如2005年保加利亚共和国《关于国际私法的法典》第96条就采取了这种做法。
三、强制性规则
一般认为,强制性规则的大量出现是20世纪中后期国家频繁干预经济生活的结果。国家力量介入经济生活后,传统的公私二元划分的法律体系界限日益模糊,出现了大量兼具公法性质和私法性质的经济法。就经济法的公法性质而言,经济法具有严格的属地效力,不可能与外国同类性质的规则产生“冲突”;然而,经济法毕竟具有大量的私法性质,对当事人的私法活动会产生直接的法律后果。国际私法必须对经济法在私法上的法律效果作出回应,于是这部分规则就进入了国际私法的视野[9]257。因此,从产生基础上来讲,强制性规则主要存在于经济法领域。那么,在劳动法律领域是否存在强制性规则呢?
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讲,在人类历史上,长期以来并没有专门的劳动法规,劳动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19世纪初期的事情[10]16,而劳动合同法的出现更是20世纪的事情。在19世纪以前,劳动关系主要由传统民法调整;而在20世纪以前,劳动合同也主要由传统合同法来调整④。劳动法规的大量出现也是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讲,劳动法的发展历史与强制性规则具有一定的同步性。因此,我们不妨说劳动法规本属于经济法范畴,在劳动法领域也应存在大量强制性规则。其实,国外早就有学者指出,强制性规则适用的领域应当包括劳动法,如瑞士学者维希尔在1992年出版的《国际私法的一般过程》(General Cours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中就认为强制性规则包括保护劳动者的法律[9]267-268。在我国,2013年1月7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0条第1款也对劳动法领域存在强制性规则进行了肯定⑤。
在劳动合同法律适用领域,强制性规则的存在固然是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结果,但这种干预从根本上来讲是为了保护劳动者正当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即源于对弱者利益进行保护的需要。保护弱者利益是国际私法人文关怀的体现[11]。在学者们看来,“弱者”的内涵和外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从理论上讲,国际私法的任何领域均有弱者存在,但学者们一般认为,企业(雇主)与劳动者(雇员)是现代社会的“强者与弱者”身份的典型表现之一[12]149,企业中的雇员属于通常意义上的弱者。因为相对于企业,尤其是相对于跨国公司而言,雇员无论在经济、知识、能力等各方面都处于弱势;对大多数劳动者而言,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接受企业提供的苛刻条件,特别是在订立劳动合同时,很多情况下是企业方面提供格式文本,企业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减少开支,压缩成本,往往在格式文本中订入有利于企业、不利于雇员甚至剥夺雇员主要权利的条款。现代法律不能仅仅强调形式平等,更应注重因人的身份和地位的不同而予以区别对待,正如罗斯科·庞德所言,20世纪法律史的演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从契约到身份”的运动过程[13]46。20世纪的法律已经开始注意区分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人,有区别地进行保护,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从普遍的意义上讲,对弱者利益进行特殊保护是整个法律体系的任务;国际私法作为法律体系中的重要部门,当然也应当将保护弱者的利益、追求实质正义作为其重要的价值取向。
强制性规则是国际私法对作为弱者的劳动者利益进行保护的有力工具,它可以矫正依冲突规则适用的准据法对劳动者造成的不公平,对劳动者提供“最低限度的救济”。如前文所述,强制性规则对意思自治原则具有限制功能,即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不能剥夺当事人未选择法律时本应适用的法律对劳动者提供的保护。当国际劳动合同的当事人因劳动合同发生争议时,如果依双方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会产生对劳动者不利的结果,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就不能适用或者部分不能适用。这种当事人未选择法律时本应适用的法律中对劳动者提供保护的规则,就属于强制性规则,它体现了国家保护劳动者的意图,具有明显的公法色彩,不允许当事人通过合意予以排除适用。
四、劳动合同法律适用规则的新发展
伴随着国际私法的改革、发展和编纂,劳动合同法律适用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对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都会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劳动合同法律适用规则逐渐成为国际私法的独立条款。传统国际私法的调整范围多局限于债权、物权、婚姻、家庭、继承等领域。现代国际私法的内容已大大扩展,涉外劳动关系已成为其调整对象之一[14]22。长期以来,人们把劳动合同作为传统合同的一部分来看待,劳动合同法律冲突也囿于传统合同法律冲突的解决路径,所以在早期的国际私法中很难觅见专门的劳动合同法律适用规则,即使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私法把劳动合同作为传统合同的一部分,对劳动合同未制定特殊的法律适用规则。然而在世纪之交制定的国际私法中,尤其是法典化的国际私法中,不少已把劳动合同法律适用规则予以专门规定⑥。
其次,劳动合同法律适用规则趋向复杂化、精细化、体系化。从各国国际私法的立法现状来看,多数国家国际私法关于劳动合同法律适用的规则比较复杂,呈现出精细化、体系化色彩,这尤其反映在欧洲国家和欧盟的国际私法立法中。罗马Ⅰ条例第8条在继承1980年《罗马公约》第6条的基础上,对劳动合同法律适用规则进行了修订和完善,规定了一套层级递进的法律适用规则体系[15]244:首先,适用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当事人意思自治对国际劳动合同具有优先适用效力;其次,在当事人未作选择时,适用劳动者为履行劳动合同从事惯常工作地国家的法律,若无此种国家,则适用雇员为履行劳动合同从事惯常工作的出发地国家法律;再次,如果不能确定劳动者为履行劳动合同从事惯常工作地国家且也不能确定劳动者为履行劳动合同从事惯常工作的出发地国家,则劳动合同适用雇主的营业所所在地国家法律;最后,在当事人未作法律选择时,根据整体情况,合同与前述规则所指定的国家之外的另一国家有更密切联系,则适用该另一国的法律。通过法律适用规则的体系化构建,提高了罗马Ⅰ条例在劳动合同法律适用领域的可操作性:法院在适用法律时既不会出现法律选择的空白领域,也不会出现法律适用规则的顺序紊乱。
最后,在特定方面,赋予劳动者以单方意思决定劳动合同法律适用的权利。国际私法在劳动合同法律适用问题上,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但一些国家大胆创新,赋予了单方当事人尤其是劳动者在某些方面可以单独决定是否适用某些法律的权利。2007年日本《法律适用通则法》第12条第1款规定:“即使依第7条或第9条规定选择或者变更应适用于劳动合同的成立及效力的法是该劳动合同最密切联系地以外的法律,只要劳动者对用人单位表示过应适用该劳动合同最密切联系地法中的特定的强制性规定的意思时,关于该强行规定的事项,也适用该强行规定于该劳动合同的成立及效力。”根据该款规定,与劳动合同有最密切联系地法中特定的强制性规则并非当然适用,而是取决于劳动者的单方意思。赋予劳动者单方选择权,本质上还是为了保护弱者(劳动者),实现实质正义[16]56。
劳动合同法律适用规则的新发展,反映了现代各国弱者利益保护意识的增强。致力于保护劳动者权益,维护公平正义,更从根本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面对日益频繁的劳动力跨境流动,积极立法予以应对。
五、我国涉外劳动合同法律适用立法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国际私法立法处于停滞状态;而且受当时国际政治环境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劳动力的跨境流动很少发生,劳动合同法律适用立法完全是空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私法立法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伴随着对外开放,劳动力的跨境流动日益频繁,涉外劳动合同纠纷也逐渐增多,劳动合同法律适用问题开始受到重视。
2010年10月28日,我国颁布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它标志着我国国际私法从分散走向集中,立法模式由专章专篇式进入单行立法式,我国国际私法立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该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对涉外劳动合同法律适用问题作出规定。《法律适用法》第43条规定:“劳动合同,适用劳动者工作地法律;难以确定劳动者工作地的,适用用人单位主营业地法律。劳务派遣,可以适用劳务派出地法律。”至此,从理论上讲,我国法院审理涉外劳动合同争议案件时,法律适用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解决途径。然而,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发现,《法律适用法》第43条之规定尽管有其可取之处,但其不足之处也应引起人们的注意。
涉外劳动合同,在通常情况下都有明确和固定的劳动者工作地;即使在个别特殊行业,劳动者工作地有时难以确定,但用人单位主营业地往往是确定的,所以我国法院依据《法律适用法》第43条解决劳动合同法律适用问题很少发生准据法落空的情况。而且,从其他国家国际私法立法来看,在劳动合同当事人未作法律选择时,往往把劳动者工作地法律作为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适用于劳动合同;在劳动者工作地难以确定的情况下,把用人单位主营业地作为最密切联系地也符合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此外,法院在审理涉外劳动合同争议案件时,解决法律适用问题的压力会大大减轻,有利于提高审判效率。因为就大多数涉外劳动合同纠纷案件来讲,如果外国人来华工作,劳动者工作地在我国,法院就可以适用劳动者工作地法律,即适用我国法律;如果我国公民到国外就业,根据相关规定⑦,必须与国内的劳务输出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由劳务输出公司将其派出到国外,劳务派出地也在我国,法院可以适用劳务派出地法律,也即我国法律。这样,法院查明和适用外国法的困难和障碍就大大减少。从某种程度上讲,《法律适用法》第43条之规定与多数国家国际私法关于劳动合同最密切联系法的普遍规定相一致,又符合我国现阶段审判实践的需要。然而,《法律适用法》第43条之规定,仍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首先,在劳动合同法律适用领域排除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国际合同领域,当事人意思自治是法律适用最主要方法,而劳动合同从本质上讲仍是合同,其法律适用仍应遵从合同法律适用的一般规则。而且,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关劳动合同法律适用的立法多数还是赋予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权利,如保加利亚共和国的《国际私法》、《土耳其共和国关于国际私法与国际民事诉讼程序法的第5718号法令》、罗马Ⅰ条例等,而完全排除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则不多见。其次,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贯彻不够彻底。涉外劳动合同纠纷案件是多种多样的,劳动者工作地法、用人单位主营业地法或劳务派出地法并非总与劳动合同有最密切联系。当与劳动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是其他法律时,根据第43条规定,最密切联系的法则无法适用。最后,导致我国法院受理的涉外劳动合同争议案件过多适用中国法。外国人在我国就业适用劳动者工作地法律,中国人在外国就业可以适用劳务派出地法律,而两者均为中国法律,就会导致法院在审理涉外劳动合同纠纷案件时,尽量适用中国法。本国法的大量适用,导致法律适用“回家去趋势”的回归,在根本上损害国际私法的地位,而且中国法未必就对劳动者有利。
注 释:
①雇佣合同是劳动合同的上位概念,包含劳动合同,两者之间的重叠部分应适用劳动法的规定。参见许军珂:《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涉外劳动合同中的适用空间》,载《政法论丛》2009年第1期。
②之所以做出如此限制,是因为瑞士国际私法在法律适用领域赋予了最密切联系原则基本原则的地位。最密切联系精神贯穿了该法法律适用规范的始终,虽然该法赋予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权利,但当事人所选择的准据法还是受到了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制约,即当事人不能随意选择与案件毫无关系的法律。从第121条第3款为劳动合同当事人所限定的选择范围来看,可选择的法律都与案件有着某种联系。
③该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未选择法律时,劳动合同适用雇员从事惯常劳动的工作地法。雇员临时在另一国从事劳动的,则该工作地不得视为惯常工作地。第3款规定:如果雇员持续在多个国家从事劳动,而不是在一个特定国家从事惯常劳动,则劳动合同适用雇主的主要管理机构所在地国家的法律。
④我国更是直到2007年才制定了专门的劳动合同法,而1994年制定的《劳动法》虽有专门关于劳动合同的规定,但只有区区20个条文,实践中不少案件尤其是涉外劳动合同案件不得不援引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⑤该解释第10条第1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当事人不能通过约定排除适用、无需通过冲突规范指引而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条规定的强制性规定:(一)涉及劳动者权益保护的;……。”
⑥2005年《保加利亚共和国国际私法法典》第96条、2007年《马其顿共和国关于国际私法的法律》第24条、2007年《土耳其共和国关于国际私法与国际民事诉讼程序法的第5718号法令》第27条等,都属于专门的劳动合同法律适用条款。
⑦参见《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21、23条等。
[1]Mackinnon Jacquelin. Dismissal Protections in a Global Market: Lessons to Be Learned from Sercon LTD v Lawson[J]. 38 Indus. L.J. 101 (2009).
[2] Mo Zhang.Party Autonomy and beyond: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f Contractual Choice of Law[J].20 Emory Int'l L. Rev. 511 (2006).
[3]黄轫霆.日本新国际私法中合同准据法相关规定评释[M]∥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第8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Franco Ferrari and Stefan Leible (eds.). Rome Ⅰ Regulati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the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in Europe[M]. European Law Publishers GmbH, 2009.
[5]Catherine Walsh. The Uses and Abuses of Party Autonomy in International Contracts[J]. 60 U.N.B. L.J. 12 (2010).
[6]张仲伯.国际私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7]刘卫翔,余淑玲,郑自文.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理论与实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
[8]许光耀.论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利弊得失[J].法学评论,1999(1).
[9]宋晓.当代国际私法的实体取向[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10]关怀,林嘉.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11]徐冬根.人文关怀与国际私法中弱者利益保护[J].当代法学,2004(5).
[12]徐冬根.国际私法趋势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3]屈广清.国际私法之弱者保护[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4]韩德培.国际私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5]C. M. V. Clarkson and Jonathan Hill. The Conflict of Laws: 4th ed[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6]Symeon C. Symeonides.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Progress or Regress?[M].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0.
【责任编辑:李维乐】
On the Legal Applicabl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bor Contract
WANG Jidong
(Law School,Shangqiu Normal University,Shangqiu Henan 476000)
The reflection of the prolif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bor mobility in the legislation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s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conflict rules on labor contract. Party autonomy and the most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principl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methods to determine the applicable law of labor contract. As the country continue to strengthen intervention on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an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weak benefit protection principle, overriding mandatory rules begin to exert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applicable law of labor contract. Conflict rules on labor contract become more complicated, more elaborate and more systematic, etc. The Chinese Applicable Law Act provisions on labor contract adapt some common practice in most other countries, and is favorable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trial, but it excludes the application of party autonomy, and its implementation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principle is not complete, causing too much application of national law, which should be rethought.
party autonomy; the most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doctrine; the weak benefit protection principle; mandatory rules; Applicable Law Act
2014-11-14
王济东(1964-),男,河南睢县人,教授,主要从事民商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研究。
D922.52;D997
A
1672-3600(2015)01-01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