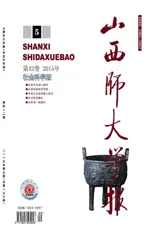“理解”与社会学的现象学转向
2015-04-11张小龙
张 小 龙
(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 211100)
20世纪30年代,以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又译许茨)的《社会世界的现象学》一书出版为标志,现象学社会学得以确立。但遗憾的是,尽管现象学社会学已经成为社会学领域的主要分支学科,但直到今日对很多人而言,现象学社会学仍不是一个熟悉的概念。当然这一状况与现象学社会学的自身发展密切相关,正如吕炳强所指出的:“就现象学社会学的关注而言,社会学里的现象学到了60年代以后已经全面终结。”[1]然而,不能据此以为现象学社会学就是一个过时且失去其价值的学科。事实上,在现象学的影响下,时间、意向性以及身体等概念已经成为社会学中的主要概念,受到了人们愈来愈多的关注。特别是在我国社会学各分支学科不断取得重大成果之时,促使人们不得不思考,现象学社会学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它对今日我国的社会学发展或者说对研究我国社会现状有什么重要价值?这些问题实则构成了人们正确认识上述判断的基本前提,更是了解现象学社会学的首要途径。在本文看来,从狄尔泰到韦伯再到舒茨,他们三人对待“理解”概念的不同态度是现象学社会学之所以从理解社会学脱胎而出的关键原因。
一、“理解”作为精神科学一般方法的确立
狄尔泰第一次从哲学角度分析了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本质上的不同,他不仅如维科等人一样指出了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方法不能适用于精神科学研究,更首次提出精神科学的方法只能是理解。狄尔泰对理解作为精神科学方法的论述其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甚至可以说狄尔泰与理解概念已经是不能分割了——谈到狄尔泰必谈理解,谈到理解也必然要谈到狄尔泰。殷鼎曾对此描述说:“当代学者常怀感戴的心情,称誉威廉·笛尔塔为人文科学中的牛顿,承前启后。也颇类似康德,开启现代哲学之先绪,当代解释学的几乎所有问题,都可在笛尔塔的思想中找到绪端。”[2]233大概也是基于这个理由,有学者将狄尔泰称之为“理解社会学之父”。
狄尔泰对理解做了不止一次的定义和解释,但总是与生命、时间、体验相关。因此对于狄尔泰而言,“理解不是一种简单的、理智上的辨别力,而是我们认识自己和自己所创造的社会和历史的能力。精神科学的真正认识论之基础是体验,是由生命的整体内在对社会和历史真实性的体验。理解就是通过对体验的再现而认识和把握生命。”[3]具体而言,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认识狄尔泰的理解概念:“首先,理解是对于人们所说、所写和所作的东西的把握,这是对语言、文字、符号以及遗迹、行为——即所谓‘表达’的领会;第二,理解是对于意义的把握,这是对一般表达所包含的观念或思想的领会;第三,理解是对人们心灵和精神的渗透。”[4]107从这一概括不难发现,狄尔泰的理解不能被简单地视作一种方法,或者至少这种方法本身也是对生命的自我塑造。
狄尔泰的哲学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以生命为其哲学的出发点,在他看来,生命首先是作为在历史中存在的人的生命。因此,它除了是自然进化的生物体之外,更是一种精神存在。进一步讲,生命还是一种由个体生命所组成的共同生命。个体生命和作为共同体生命的历史就其本质而言都是精神,在精神的世界里,有着独特的价值、意义和目的。正因为如此,如果使用普遍的理性概念来把握理解生命将是不可能的。因此在狄尔泰看来,康德的伟大是因为他使用普遍理性概念完整地分析了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但如果将之应用于把握生命是不合适的,而康德本人确实也没有给出历史认识论在他的概念框架下可能之答案。在狄尔泰看来,生命首先“以时间性作为其首要的范畴规定,它是其他范畴规定之基础”[5]5。“生命与时间之充盈处于最密切关系中,它的完整特征,其中易朽性关系,以及它还同时构建关联并且在此拥有一个统一体(自我),这都受制于时间。”[5]45既然时间之于生命如此紧要,那么生命的时间性规定到底表现了什么?狄尔泰用了一个词叫生命流程。怎么理解流动中的生命或者说“生命流程”呢?狄尔泰认为,生命所经历的时间不同于物理时间。物理时间是线性的时间,是可分割的时间,而与生命相关的时间则是为我存在的时间。狄尔泰不赞同康德将时间和空间当作是先天的纯粹直观形式,在狄尔泰看来,“时间被经验为现在的不息前移。”他在“现在”、“过去”和“未来”三个维度中看待时间,而“现在”是关键。“其中现存之物不断变为过去,而未来之物变为现在。现在是一现实性充满时间瞬间,……我们生活在我们的现实性之充满中。”[5]5而且狄尔泰还明确说:“在体验中时间概念找到最终的充实。”这说明对时间的把握最终要回到体验。
体验同样是狄尔泰生命哲学里的一个重要概念,狄尔泰认为,生命流程中以过去、现在、未来构建了在场单元之物,这些具有单元意义的最小单元就是一种体验,而且“诸生命部分的每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单元通过对生命流程的共同意义被连接,我们随后进一步称之为体验,即便这些部分被中断性过程彼此分离”。[5]6—7因此体验是生命本身的意义统一,在这个统一的意义整体中才能达成生命的理解。也因此“一旦理解抛弃了词语及其意义的领域并且不寻求符号意义,而寻求生命表现深刻的多的意义,这就是普遍方法”。[5]51作为方法的“理解”的确立进一步加强了狄尔泰认为的“生命原本就是对自身及他人的生命表达进行着的理解,因此,理解并非只是精神科学的方法程序,而且也是生命的一项基本活动”。[6]
然而,狄尔泰试图以理解概念达到对客观精神的认识,充分显示了他的历史客观主义理想,或者说他一生以摆脱实证主义确立精神科学的认识论基础为目标,最后成功地确立了作为一般方法的“理解”,为后来社会科学中著名的“理解与解释之争”埋下了伏笔,但他最终实际没有完全摆脱实证主义的束缚。直到经由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对理解进一步阐释,才确立了理解的本体论地位,理解不再属于主体,“理解属于被理解的东西的存在”。这与本文所述理解概念作为一种普遍方法的含义的转变有所不同。
二、韦伯对理解与解释的整合及其缺陷
韦伯是公认的理解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他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有着高度的重视,并多次就方法论问题进行探讨。当然,这种方法论的自觉也受到他所处的历史环境的影响。
盖伊·奥克斯在韦伯《批判施塔姆勒》一书导言[7]16—20中详细论述了韦伯所处的时代氛围。1883年,卡尔·门格尔出版了《社会科学方法特别是经济学方法研究》,在这本书中门格尔针对德国历史学派的观点做了大量的辩驳,在他看来,对于方法论的作用不能夸大,社会科学的方法与理论宗旨与物理学中经典力学的方法和宗旨并无本质差别。也正是这一年,狄尔泰出版了《精神科学导论》第一卷,提出了其康德式的历史理性批判构想。而古斯塔夫·施莫勒则对门格尔和狄尔泰都做出了评论,他的立场则是历史学派的立场。由此可见,方法论确实是此一阶段人们关注的热点。事实上,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韦伯等人参与其中,当然到韦伯参与其中时,他们关注的问题也从经济学方法论转向到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上来。盖伊·奥克斯还指出,韦伯作为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却令人惊讶地在方法论的作用问题上站在了门格尔一边,认为其作用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韦伯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阐述大都十分零散。但就其内容而言,韦伯还是更多坚持了历史主义的立场,从狄尔泰那里吸收了理解概念,将其作为自己社会学的方法。
事实上,从前述方法论争论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出韦伯在方法论上的态度之端倪,他没有坚定的沿着狄尔泰等人走历史主义的路线,而是试图在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之间取得超越。这一点还可以从他对社会学的定义中明显看出。韦伯认为,“社会学(就这个高度模糊的词语在这里的意义而言)是一门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并对其进程与结果进行因果说明的科学。”[8]92与迪尔凯姆将外在于人的社会事实这样的整体性概念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不同,韦伯把社会行动看作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社会行动的本质特征就是“只有当主观态度针对的是他人的表现时,他们才会构成社会行动”[8]111。韦伯进一步区分了社会行动的四种类型:工具理性的、价值理性的、情绪的、传统的,这就意味着社会行动不仅仅受到行动者个体情感和价值判断的影响,更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韦伯的社会学才顺理成章地推导出理解可以作为社会科学方法。
那么,韦伯的理解概念到底有什么特点呢?韦伯把理解分成两种,首先是对既定行为主观意义的直接观察理解,包括对观念、情感、行动等的直接观察理解,例如他举例说我们通过直接观察就能理解“2×2=4”的意义,这就是对观念的直接理性观察。其次是解释性的理解。主要是指人们能根据行动者的动机来理解其行动的意义。与狄尔泰不同的是,韦伯始终认为理解意味着解释性的把握意义,韦伯使用意义与理解两个概念某种程度上没有严格区分。不管是对于逻辑命题还是人类情感等都可以就其意义获得理解。但是理解要获得确定性,应该保证其基础是理性的且能够进一步划分出逻辑或数学的特性,然而这也正是狄尔泰所反对的。在韦伯看来,“任何解释都在力求清晰和确定性,然而,一种解释本身从意义角度看上去无论显得多么清晰,他都不可能因此而宣称是具有因果效力的解释。”[8]98因此理解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而因果关系的解释在社会科学中也应该具有重要地位,他由此一直试图把意义的理解和因果性解释结合起来,还专门阐述了统计学意义上的事实统一性构建可以理解的行动类型。
严格来讲,尽管韦伯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有很多论述,但应该说这只是其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不得已而为之。韦伯并不愿意对在他看来是复杂现象的理解做出细致的分析,他所关注的问题是社会科学中切实的解释现实问题。这就使得理解概念在他的社会学中发生了细微的变化,而且没有将这一概念的哲学基础详细展开,这就失去了理解概念在狄尔泰那里和生命相连接的最为核心的要素,从而也失去了根基。舒茨就是看到了韦伯理解社会学的一些核心概念没有得到基础性论证,从而他引入了胡塞尔的现象学,这才促使现象学社会学从理解社会学中独立出来。
三、舒茨对“理解”的现象学分析
舒茨在《社会世界的现象学》一书前言中开门见山地指出:“这本书是根据我个人多年来对韦伯理论著作的强烈关怀而形成,在这段研究时间中,我深刻地体认到韦伯的研究途径是正确的。”[9]ⅸ但同时舒茨也指出韦伯存在的问题,认为韦伯的一些基本概念还缺乏足够严密的基础论证,因此他要为其确定哲学根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与狄尔泰、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才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劳伦斯·纽曼将现象学社会学看作是理解的社会科学的类型之一[10]98,而理解的社会科学正是以韦伯和狄尔泰为代表的。
对作为社会科学方法的“理解”的哲学分析在舒茨的理论里占有重要地位,舒茨“很多年的学术努力无不是围绕着对于韦伯‘理解’方法的哲学奠基工作以及对于这个方法的运用展开的”[11]182。前面已经提到韦伯将“理解”分为两种类型:对主观意义的直接观察式理解和根据动机把握行动者赋予行动的意义的说明理解。但在舒茨看来,由于韦伯没有区分对于行动者而言的主观意义和客观意义,导致“韦伯对观察了解与动机了解的划分是相当独断的,在他的理论中并无任何逻辑基础”。[9]27舒茨还指出,这一区分的错误在于突出了客观意义,而丝毫不见主观意义的理解,同样也是因为韦伯没有对意义与动机做出正确的理解所导致的。
在舒茨看来,人们对理解概念的认识向来是模糊的,各自都有不同的解释,如韦伯强调理解的主观性是因为目的在于发现行动者通过他的行动意味着什么。而舒茨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原因在于大家都没有正确区分理解概念的三个层面的含义:“(1)‘理解’作为关于人类事件的常识知识所具有的经验形式;(2)‘理解’作为一个认识论问题;(3)‘理解’作为社会科学所特有的一种方法。”[12]59在第一个层面和第三个层面上,韦伯与舒茨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认为常识下的理解大都是不成问题的,而作为方法的理解确实反映了社会科学的独特性。但在第二个层面则表现出了他们两人的根本区别,舒茨认为,理解作为一个认识论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甚至还没有引起哲学家的注意是难以理解的,这是一种“哲学的耻辱”。
在舒茨看来,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回到理解现象本身去为自己寻求基础,而在柏格森的时间概念和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下,他认为时间即充满具体事件的历史时间,它具有内在时间意识的性质,在这个时间意识中个人构成自己的根本的经验意义。因此舒茨讲道:“在时间流中,个人透过生活体验,而构成自己的经验意义。唯有这个最深层的经验方能为反省所触及,才是意义与了解现象的根源。”[9]10其次,理解的难点在于“我们只能透过自己对他人的经验来诠释那些本属于他人的经验”。[9]126对此进一步深究将涉及到主体间性及生活世界等概念。在舒茨这里,生活世界中的人们在相互理解中才构建了一个文化世界,因此生活世界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主体间性的文化世界,同样只有主体间性的理解才是真正的理解。
因此对于舒茨而言,他在对理解概念做了足够详细的阐释基础上,批判了韦伯理解概念的不足,指出“由于他对基础问题的分析尚嫌不够深入,以致人类科学的许多重要问题仍悬而未决。……所有这些问题几乎都和时间经验(或内在时间意识)的现象密切相关,而时间经验唯有经由最严谨的哲学反省才能加以研究。”[9]ⅸ这样,就为作为社会科学一般方法的理解寻找到了哲学基础,这个基础是他回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后才找到的。由此可以明确,现象学社会学正是在舒茨回返到胡塞尔现象学那里为韦伯的社会学寻求哲学根基的情况下确立的。事实上,这一回返有着内在的必然性。一方面舒茨看到了胡塞尔对时间特别是内在时间意识的严谨分析,认为胡塞尔对内在时间意识的分析是建立人类行为的深层基础,而这将涉及社会科学对象即社会行动的准确描述,其重要性是优先于方法的。另一方面,舒茨找到胡塞尔的重要原因还在于,胡塞尔受狄尔泰启发,确认了他使哲学成为一门严格科学的奠基性作用的信念,并确认“唯有现象学的本质学才能够为一门精神哲学提供论证”[13]52。而对于胡塞尔与狄尔泰之间的关联,海德格尔在《时间概念史导论》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海德格尔认为狄尔泰对于人文科学独立方法的探求研究提出了一种回到事实的提问方式及认识结构,与胡塞尔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狄尔泰没有如胡塞尔那样表述出来。舒茨就是看到了胡塞尔现象学的优势所在,或者更准确地说,舒茨看到了在理解社会学与现象学之间内在的一致性,才选择性地使用了胡塞尔现象学中的一系列重要概念并运用了现象学方法,他的这一成果还得到了胡塞尔的高度赞赏。舒茨能建构现象学社会学或者说现象学社会学能够从理解社会学中分离出来,正是因为舒茨回到胡塞尔之后做出了一系列卓越成就。
四、结语
如前所述,狄尔泰的理解是通过体验而对生命本身的把握,韦伯则将理解与行动、意义等概念结合,认为理解是解释性的把握行动意义,舒茨则抓住他所认为的韦伯的不足,不仅区分了三个层面的理解概念,还将理解与时间问题联系起来,试图以现象学的方式为理解奠定哲学基础。从现有文献来看,韦伯对舒茨的影响是明显的,但狄尔泰对于韦伯有多大影响还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说狄尔泰对韦伯的影响是建议性的,那么他对于舒茨则更多是通过胡塞尔以一种特殊的提问方式产生间接影响的。
舒茨能够以胡塞尔的现象学为基础,批判韦伯的理解社会学,进而构建现象学社会学,除了上述他为作为一般社会科学方法的理解概念找到现象学的基础之外,还包括了比如意义、行动以及理想类型等很多重要概念的现象学分析,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奠基之作《社会世界的现象学》一书就是直接围绕韦伯的这些概念来展开分析的,对这些概念的分析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在能够称之为整体的意义上,才能进一步讲现象学社会学是如此这般的。当然,强调整体并不能抵消理解概念作为社会科学一般方法被人们用来把握现象学社会学建构的重要性。
毫无疑问,当代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取得了很多重大的突破,但毋庸讳言的是,对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基础性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从“理解”这一重要概念出发,本文返回到理论原典,从哲学层面分析了社会学研究的现象学转向的基本理由,一方面让人们重新思考“理解与解释之争”,另一方面也促使人们深入地以不同于自然主义的社会研究方式去进一步开拓今日的社会研究领域。
[1] 吕炳强.现象学在社会学里的百年沧桑[J].社会学研究,2008,(1).
[2] 殷鼎.理解的命运[M].北京:三联书店,1988.
[3] 谢地坤.狄尔泰与现代解释学[J].哲学动态,2006,(3).
[4] 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5] (德)狄尔泰.历史理性批判手稿[M].陈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6] 卢云昆,朱松峰.以生命把握生命——狄尔泰哲学方法论初探[J].世界哲学,2010,(4).
[7] (德)韦伯.批判施塔姆勒[M].李荣山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8] (德)韦伯.经济与社会[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9] (奥)舒茨.社会世界的现象学[M].卢岚蓝译.台湾:久大文化有限公司,1991.
[10] (美)劳伦斯·纽曼.社会研究方法[M].郝大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1] 范会芳.舒茨现象学社会学理论建构的逻辑[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9.
[12] (奥)舒茨.社会实在问题[M].霍桂桓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13] (德)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科学[M].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