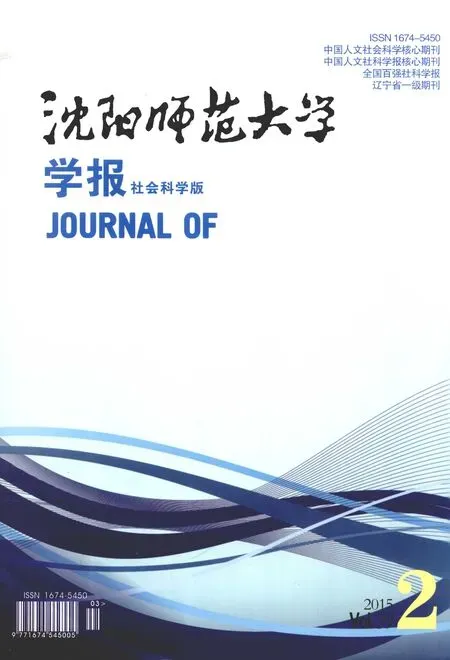审美功利:从积极自由实现到消极自由维护
2015-04-11张强
张强
(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审美功利:从积极自由实现到消极自由维护
张强
(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经由审美达至自由是审美功利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取向。在精英文化时代如此,在大众文化语境下,这种期待仍然具有现实性,只是实现自由的取向不同。在精英文化时代,人们寄望于审美实现的是一种积极自由;在大众文化时代,人们寄望于审美实现的是一种消极自由,后者显然比前者在当下更具现实感。审美积极自由取向靠感性生命的无限张扬来实现自由;审美消极自由取向依靠一种有限理性来透视美的表象以实现一种有限的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取向是一种昂扬的战斗姿态,消极自由取向则是无奈之下的逃避姿态。前者更多的是一种是理论姿态,而后者则是一种大众实践状态;前者寻求无根基的超越,后者寻求超越无望之后的批判。
审美功利;积极自由;消极自由;感性张扬;理性批判
一、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
积极自由(free to)和消极自由(free from)概念是英国学者以赛亚·柏林在《自由论》一书中提出来的。消极自由是指,“主体(一个人或人的群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1]170从消极自由的角度来看,不被干涉和控制的领地越大,消极自由的实现就越充分。积极自由是指“个体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的愿望。我希望我的生活与决定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取决于随便哪种外在的强制力。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意志活动的工具”[1]180。
自以赛亚·柏林提出这两种诉求以来争议不断,本文的目的不是穷尽这些争鸣和论辩,而是试图阐释这两种自由同审美功利研究有着重要的关系。审美功利研究的积极自由取向试图通过审美来实现主体充分的积极自由,从而实现自己的自由意志。审美功利研究的消极自由取向不试图相信通过审美能够实现主体的积极自由,而是保守地认为,在当下的大众文化语境中,不再对审美功利能够实现的积极自由抱有太多的幻想。审美积极自由论者认为审美是通往积极自由之路,如在康德的理论视域中,审美是不涉功利的自由;在席勒的理论中,审美是自由的练习;在马尔库塞的理论中审美本身是通往解放的道路,等等。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而兴起的对大众文化反思的理论也日渐丰厚,这些理论不在冀望于审美能够带来的超越和主体性的自由,而更关注以审美开路的大众文化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很多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取向更倾向于认为:通过揭穿大众文化的审美表象来实现一种在感性审美泛滥的情况下的清醒性的自由。如果说,积极自由的取向是在审美中实现对现实的超越而自由,消极自由的取向就是通过对审美现实的清醒观审实现的自由。前者是试图在审美中实现的自由,后者是试图不在审美中迷失而实现的自由。在大众文化语境中,在积极自由难以保障的情况下,正视和注重消极自由的意义和价值就会凸显。
二、审美功利研究的积极自由实现
在大众文化兴起之前,对审美功利性的研究着力于通过审美能够实现一种积极自由。这类观点试图用诗性来取代现实性、用情感来冲毁理性、用神秘来对抗技术,其中有几个主要的理论预设:
第一,实现主体完善的自由之路。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就旨在通过审美来建构人性的完善。在分工日益细密和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完整的人性分裂了,变得日益片面和碎片。他充满忧虑地写道:“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就把自己培养成碎片。”[2]15面对这种情形,人如何实现自由,如何走向完善,乃至如何变革社会?席勒给出的答案是“审美”。他说“让美走在自由的前面……为了解决经验中的政治问题,人们必须通过解决美学问题的途径,因为正是通过审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2]4。审美成为了拯救人心的良药和政治自由的前提。如何实现审美自由呢?席勒给出的答案是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的完美结合。首先是感性冲动,“它来自人的肉体存在或他的感性本性,它努力要把人放在时间的限制之中”[2]4。第二就是形式冲动,“它来自人的绝对存在或人的理性本性,它竭力使人得到自由……它扬弃了时间,扬弃了变化”[2]37。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相互规定、相互趋近、相得益彰。二者互动最理想的状态是“游戏冲动”,“所指向的目标就是,在时间中取消时间,使生成与绝对存在相协调,使变化与同一性相协调。……感性冲动要求被规定,它要求接受它的对象;形式冲动要求自己来规定,它要求创造它的对象”[2]43。游戏就是一种自由的状态,在此情况下“一切在主体和客体方面都不是偶然的,而无论从外在方面还是从内在方面都不受强制”[2]46。席勒像其他浪漫派一样,把审美的能量无限地放大,把太多的希冀寄托于审美,开启了重要的美育传统。这个传统强调人的审美能动性,并通过审美实现主体的完善进而实现社会的完善。这是很典型的审美的积极自由取向。
第二,实现感性生命强大的自由之路。感性生命的强大在理性过度的西方社会成为了人们实现自由的希望和路径。这些理论试图通过感性的无限扩张而实现生命空间的强大、绵延与阔达。尼采的美学理论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他把艺术作为强力意志的一个重要形态。强力意志是一种意愿,“虽然是一种欲求,但它并非以幸福和情欲为目标,而是以强力为目标”[3]47。这种意愿不断地超出自己、命令自己、使自己强大。强力意志是一种以身体为基础的强烈情感形式,其重要表现形式是“醉”,通过醉可以实现强力意志,可以实现感性生命不断充实和强大,进而实现一种生命的自由。“所有极为不同类型的醉都具有这种力量:首先是性冲动的醉,这种最为古老、最为原始的醉。还有随着一切强大欲望、一切强烈情感而出现的醉;节日的醉,竞赛的醉,表演的醉,胜利的醉,一切极限运动的醉;酷刑的醉;破坏的醉;在特定气象影响下产生的醉,如春天的醉;或者在麻醉剂的影响下产生的醉;最后,还有意志的醉,一种积蓄的、膨胀的意志的醉。——醉的本质乃力的提升与充沛之感。”[4]海德格尔总结尼采的陶醉时讲到“审美的基本状态乃是陶醉,这种陶醉本身又可能受不同方式的限制、触发和提升”[3]113。艺术的生产就是对这种醉的生产,在这种醉的生成和传达过程中,作为感性和审美的强力意志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实现。尼采把艺术作为实现强力意志的重要形式、作为自己用锤子从事哲学的重锤、作为击碎虚无主义和基督教道德的重锤,用这感性和身体之锤去捶打和拷问一切,理性的桎梏就会松动,生命的自由便可生成。
第三,实现人性解放的自由之路。审美积极自由取向试图通过审美乌托邦来实现人性的解放,用海市蜃楼般的希冀来激发人性解放的可能。解放的目的就是实现自由。马克思对解放给予深切的关怀。他的解放理论注重从社会实践入手进行建构,注重批判的物质性取向。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他相信,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就是实现解放的途径。马克思对于解放的理论热情和魅力,深深地感染了后世的理论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的解放志向,但是却提出了不同的解放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解放的目的是要摆脱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造成的扭曲、异化和压抑。他认为资本主义使人成为单向度,成为资本和消费的奴隶,并对人的“爱欲”进行压抑,造成了人的扭曲,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工具的一部分。马尔库塞把解放的动力寄托于人性的本质,他用新感性来标明这种本质。“人之为人,应该发现自己被现实社会局限,应该清楚自己的感性被现实的局限歪曲,因此,革命首先在于以人的本质为基础发展生成与人的本质相一致的新感性。这种新感性必然与由社会总体性所支配的现实感性相对立,必然产生出对现实感的否定,从而产生对现实的否定。”[5]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马克思认为批判最大的动力源泉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物质高度发达之后已经基本上从物质层面消失了。这就导致了批判的力量逐渐丧失,在此情况下,马尔库塞希望新感性可以成为单向度社会的对抗性力量,从而生产人性解放的可能。
三、审美功利研究的消极自由维护
审美功利的消极自由取向的理论姿态是防御性的,对美不再那样相信,甚至是怀疑美本身。消极自由的生成语境是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它的任务也不是通过审美而实现积极自由,而是对经由美或者美本身可能带来的宰制保持清醒的姿态。审美功利的消极自由取向有几个理论预设:
第一,免于感性蒙蔽的自由。消极自由取向同积极自由取向相反,面对的不是去唤醒感性的困难,而是感性泛滥的灾难。浪漫主义的兴起乃是人的主体精神对社会全面理性化的反拨,浪漫主义成为了试图平衡感性和理性失衡的企图。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极具理性化的行动偏要拉上审美从而进入大众视界。也就是说,虽然文化生产环节是极尽理性化的,但生产出来的产品确是充满感性的,各种各样的文化样本中充满着各种叙事,唤起着各种各样的情感,触动着各式各样的心灵。人们在这样无处不在的感性之流中左右摇摆,欲罢不能。这些感性较之理性更易让人接受,又从不像理性产品那样枯燥无味。但是,心灵老是被感性左右,特别是被有特定生产目的的感性产品所左右,就不会是一个令人期待的结果。现在的问题是,经过理性计算的感性产品太多,人们在审美打扮过的感性表象下是很难对审美本身进行反思的。当下审美功利的意义就不是在如同传统美学那样告诉我们如何在审美感性中陶醉和充盈,而是增强大众对于感性表象下的理性意图的认知。感性泛滥的冷静观审也是美学的应有之义。大众文化发展到今天,对感性泛滥带来蒙蔽的反思成为了消极自由实现的重要可能。
第二,免于被统治的自由。当审美自律理论遭受到大众文化和文化研究理论的剧烈解构,审美就无法再向审美实践者保证曾经允诺过的审美积极自由可能。审美在一个充满结构化的社会中是无法逃脱解构的。无论是审美的生产、传播和消费环节都受到意识形态和市场的双重规定,审美不是自由的舞者,而是带着镣铐的舞蹈。既然审美自律被广泛地怀疑,人们就从对美的无条件相信走向了对美本身地怀疑。首先是对知识分子的怀疑。布迪厄认为,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他们属于统治阶级,这是因为他们拥有大量的文化资本并因而拥有权力与权威,这种权力来自于他们提供或取消社会秩序的合法性能力。但是,与拥有政治或经济权力的人相比,他们又处于被统治地位。”[6]254他怀疑先前对于知识分子的判断,比如“把知识分子的特征界定为‘具有对于神圣之物的非同寻常的敏感性,对于宇宙本质与统治社会的法则的非同寻常的反思能力’……这些观念基本上表达了今天关于庞大的文化生产者阵营(从艺术家、作家、教授到律师、工程师、管理者以及国家官员)的特征的看法”[6]252。他不认同知识分子处于统治阶级的对立面,知识分子对统治阶级的批判不是来自于为某个群体,特别是弱势者代言,而是来自于自身的资本实现。福柯的知识即权力理论也对美的独立自足性进行了颠覆。他认为知识和权力从来都密不可分,权力需要知识来进行合法性论证,权力又隐性地决定着知识言说的方式,反过来,一个时期特定的权力类型也是决定着知识合法性的基础,在某个特定的权力氛围中只能容许出现特定的知识类型。在很多大众文化理论中都强调了文化与统治阶级合谋来为统治阶级的合法化进行服务。既然审美话语的生产者和统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审美话语本身的自足性也就受到质疑,继而审美能够实现的积极自由也就受到质疑。审美消极自由的实现不是试图不被统治,而只能是试图不被统治得这样强烈,或者说期待一种更加让人觉得舒服、易于接受的统治。
第三,免于被欺骗的自由。大众文化兴起以来,特别是视觉文化成为大众文化的主导之后,关于真实与虚假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一书中认为,景观取代了实在成为了我们生存于其中的世界。当下,各种影像奇观充斥着我们的世界。特别是美国电影中的高科技手段,能让人们的思想形象化,这在先前是不可想象的。无论多么和现实不着边际的事物都可以形象地呈现,无论多么虚假的事物都可以通过影像变得逼近现实,乃至超越现实。波德里亚认为,真与假发生了内爆。假完全可以实现一种超真实,超真实比真实显得更加真实。在广告中,任何产品都变得美轮美奂,都变得完全值得拥有,每天都用各种各样的诉求和形象来试图打动受众。大众陷入了这些影像之流中,人们难以再超越这些影像之流,包括人的思想,已经被影像限制,无论是虚假的还是真实的影响都是思想的现实和边界,人们再也难于超越。此时,文化的启蒙功能受到怀疑和忽视,很多理论话语转而关注文化的欺骗性,文化不仅仅被认为是人类进步的台阶和精华,还是权力的统治工具。面对这种可能存在于文化当中的欺骗,消极自由取向的审美不在妄图相信通过审美能够制止欺骗,而只希望能够减少被欺骗的可能。
第四,免于过分被动的自由。当下的审美主体每天都被大众文化包围着,已经不能够奢望可以在大众文化中完全自主、不受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够针对过分被动而展开行动。菲斯克、德塞托等人的理论具有代表性,他们认为受众在大众文化中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能够对大众文化所传达的意义进行再生产。这种意义再生产不试图能够通过意义再生产实现某种积极自由,而是要在这种再生产中实现一种不过分被动的自由。在菲斯克的理论中的受众的能动性是有限的能动性,是在受众被动的大前提中实现的有限能动论,是无力者、弱者、被统治者的自得其乐式的能动论。“弱势者通过利用那剥夺了他们权力的体制所提供的资源,并拒绝最终屈从于那一权力,从而展现出创造力……即生产出属于自己的社会体验的意义所带来的快感,以及逃避权力集团的社会规训所带来的快感。”[7]在菲斯克的理论中,快感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自由实现可能,可以用快感来对抗社会的规训。但是快感绝不是要冲破种种理性规训,而只能是尽可能地避免规训,而不是消除规训。对于逃避规训的具体方式也是消极的,德塞托具体地指出了在被动中实现有限主动的策略,如换超市价签,顺手牵羊带点东西,只逛商场不买东西等。这些审美的消极自由预设是大众文化时代审美功利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
四、从积极自由实现到消极自由维护转换的语境规定
审美功利研究从积极自由的实现转向消极自由维护有几个重要缘由。首先,文化语境的转换。审美功利的积极自由实现取向是在精英文化语境下开展的,审美在人类其他文化样式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有可能被寄予厚望,也有可能实现一定的厚望。但在大众文化语境下,人类各种知识门类日渐丰富、科技不断发达、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心灵理智化程度提升,美学能够唤起的热情越来越有限,自然实现其积极自由价值的可能也就更加有限。当人们意识到,文化结构的压制性是无历史的,是不会随着社会和制度的变迁而完全改变的,人们也就更容易发现审美的功用已经不是带来积极自由,而只能是在消极自由层面生发挥功能。
其次,文化实践主体的转换。积极自由取向的审美实践主体是文化精英。从渊源上看,康德、费希特、席勒都是不折不扣的文化精英;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审美文化来看,王国维、朱光潜、蔡元培等等都是文化精英。但是在大众文化实践中,文化实践的主体是大众,大众的审美实践同精英理论发生了脱节。精英理论难以对大众产生有效影响,大众依据大众文化自身的逻辑进行文化实践。大众文化的平均化逻辑很难让审美具有太过超越的可能,必然也就不依靠审美来实现一种积极自由。大众的文化策略能够实现的只是对文化压制的被动又无奈的抵抗,这种抵抗实现的就是消极自由价值。
再次,审美价值的转换。在积极自由取向中,总是相信“美”,认为“美”就如同其名称本身一样是美的,对社会和个体是有好处的。不仅“美”本身是美的,而要实现“美”也要经由审美的过程。但是到了大众文化时代,“美”不一定就是美的,“美”可能是某种权力的外在表象,可能是消费主义的开路先锋,可能是意识形态的华丽衣衫。“美”不仅仅是相信的对象,还是被怀疑的对象,美的合法性本身受到怀疑。既然“美”本身可能靠不住,就只有权且利用美毕竟还有用的一面,就是娱乐和激发快感,在娱乐和快感中求得消极自由。
最后,实现自由的路径不同。在大众文化语境下,审美由本体的地位滑落到了工具的地位,因为审美的本体已经不再是现实的人得以生存的家园,人们宁愿把美视作一种工具,一种能够给人带来娱乐、快感和消遣的工具。后者显然比前者在当下更具现实感。审美积极自由取向靠感性生命的无限张扬来实现自由;审美消极自由取向依靠一种有限理性来透视美的外衣以实现一种有限的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取向是一种昂扬的战斗姿态,而消极自由取向则是无奈之下的逃避姿态。前者更多的是一种是理论姿态,而后者则是一种大众实践状态。前者寻求无根基的超越,后者寻求超越无望之后的批判。
[1]以赛亚·伯林.自由论[M].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2]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张玉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3]海德格尔.尼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尼采.偶像的黄昏[M].李超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75.
[5]张法.20世纪西方美学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217.
[6]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M].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7]约翰·菲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王晓珏,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49.
【责任编辑赵颖】
I01
A
1674-5450(2015)02-0120-04
2014-11-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DZW 004)
张强,男,辽宁铁岭人,辽宁大学文艺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