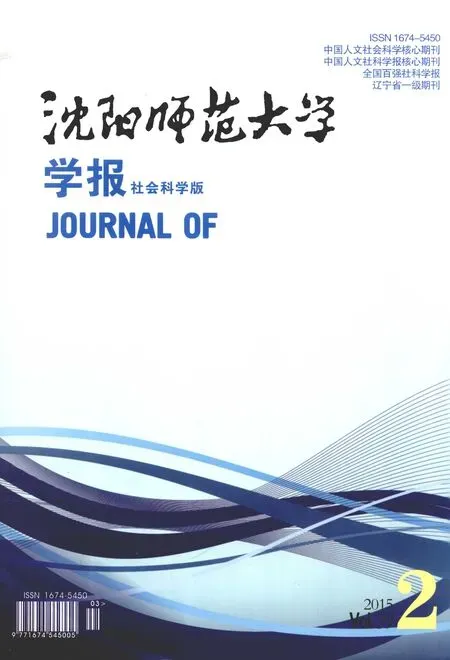德国近代哲学中神秘主义传统形成的逻辑演进
2015-04-11肖宁
肖宁
(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德国近代哲学中神秘主义传统形成的逻辑演进
肖宁
(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与英法哲学不同,德国近代的本土哲学在与宗教及神学的交织中始终保持着独有的思辩主义与神秘主义特征。埃克哈特的“心灵之光”、库萨的尼古拉的“有学识的无知”、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雅各·波墨的“神智学”依次构成了神秘主义传承过程中的各个递进环节。最后经耶可比的“直接知识”奠定了德国哲学的神秘主义的主基调并注入到德国古典哲学之中。
德国哲学;神秘主义;思辩主义;传承与演进
在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发展中,辩证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理论作用,黑格尔正是用辩证法打通了本体界,最终完成了整个宇宙的理性化从而实现了对于西方形而上学的缔结。事实上,辩证法本身在德国近代的本土哲学中有着悠久的理论传承,神秘主义中蕴含的“思辩”特色一直以来在德国本土的哲学发展中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完成,最终这种理论传统注入到德国古典哲学之中构成了辩证法形成的理论前提。因此,德国古典哲学与德国近代以来自身的哲学发展密不可分,辩证法与德国近代本土哲学中的神秘主义存在着内在的理论关联。本文试图通过考察神秘主义在德国近代本土哲学中的发展和演进逻辑,从而还原德国古典哲学中辩证法的历史“原像”。
一、蕴含于信仰之中的神秘主义开端
埃克哈特是将德国神秘主义哲学化的开启者,正如德国哲学史学家采勒所说的:埃克哈特的思想是“德国哲学的一种最初尝试,是德国精神的严谨性的首次表现”[1]27。埃克哈特神秘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是“心灵之光”。“心灵之光”是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介,是人与上帝实现神秘合一的依凭。“心灵之光”的根源在上帝。神性是纯粹的“无”,同时也是“一切”。上帝通过“流溢”创造世界。“心灵之光”本身是一种神秘理性。上帝内在于一切被造物之中,最为本质的是表现在人的灵魂之中,成为灵魂的根基——“心灵之光”。因此,“心灵之光”的活动不是一般的认识活动,而是一种宗教式的灵修活动,这是“一种并不完全是哲学的活动,它需要沉思,甚至可能需要出神……这是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它需要哲学论证与随后的神秘实践之间的一种连续性”[2]。同时人必须向往神,与上帝联系最终达到合一,在这一过程中既直观到了上帝,又拯救了自我。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呵护好“心灵之光”。为此,人必须进入一种新的伦理化生活,而不是仅仅依靠理智上的反思(知识论意义)和形式上的忏悔(宗教仪式意义)。由于人只能凭借灵魂才能与上帝合一,而“心灵之光”本身是神秘的、不可认识的,因此在“心灵之光”中实现人向上帝回归的过程也是超理性、超自然的隐秘体验,这就通过“心灵之光”的神秘性划定了理性的有限性,得出“理性绝对不可能在上帝的深不可测的海洋中去把握上帝”的结论[3]。既然理性是受限的,而且上帝也只能以否定的方式加以认识,那么通往上帝的方式就不是增加知识的“有知”,而是减少知识的“无知”,在神秘的无知中体验上帝并与之结合。由此可见,埃克哈特在神学的框架内将理性排除在认识上帝的神性之外,强调“爱”的神秘体验和宗教灵修,这就为近代德国本土哲学定了神秘主义的基调,也开启了德国神秘主义哲学的传统。
如果说埃克哈特的贡献主要是把神秘主义引入哲学领域并致力于神秘主义的思辨的话,那么库萨的尼古拉则进一步把神秘主义推向了认识领域并过渡到思辨的神秘主义,成为对认识论进行创造性思考的第一位德国哲学家。“有学识的无知”是库萨的尼古拉认识论思想的核心,也是其以认识论方式表现神秘主义思想的重要命题。按照这一命题,上帝显示自身的方式以及人认识上帝的方式在本质上都是神秘的,认识论最终落到信仰的地基上,而“这种信仰则更为确定地是通过有学识的无知而得来”[4]57。在库萨的尼古拉看来,信仰高于认识、高于理性,接近上帝的根本前提是上帝的自我显示,也就是上帝出于它的恩典愿意启示自身,这就在认识论上陷入神秘主义的天启。对于上帝,人之所以是无知的,在于人的知识都是进行比较的结果,使用的是类比的方法。但比较之所以可行,乃是因为有限的被造物本身就是可比较的。但上帝作为无限的绝对者或绝对的无限者,是“绝对的、纯粹的、永恒的、不可言说的真理自身”[4]5,是超越于一切有限事物之上的,他们之间的区别不是相似度的差别,而是根本没有比例可言,这样也就不能用比较的方式加以认识,因而上帝是我们无法认识和把握的。库萨的尼古拉以这种素朴的形式表达其辩证法思想,带有明显的神秘主义色彩。把认识论建立在信仰之中,让真正的认识指向精神活动与上帝之间的联系,这种认识对象内在化的哲学倾向最终通过宗教改革获得实现。由此可见,库萨的尼古拉将理性和信仰分开,将理性归结为认识自然的“有知”工具,而理性超出自然去理解上帝则会导致“无知”,神秘主义于是保留在信仰之中,这就为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做好了理论上的铺垫。
二、宗教改革中完成了神秘主义的社会化进程
马丁·路德作为新教的创始人,其思想在本质上表征的是宗教改革,而非哲学构建。他把神秘主义还原到宗教信仰领域,更多地“表现出一种信仰至上和神秘主义的倾向”[5]。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思想,一方面排除了教会的中介作用,表现出对“善功称义”的反驳;另一方面,把对上帝的信仰安放到个体的理解之中,尤其是通过一种谦卑的虔敬主义,在上帝主体化的过程中完成了信仰的神秘化。人之所以得救,靠的是上帝的恩典,而不是理性和自由意志,人在神面前只能保持绝对的谦卑,只能诉诸虔敬的信。于是,神秘主义顺利地回到作为个体的“我”的信仰之中。
当时天主教会的教条宣称,人要得救的前提是上帝的恩典,要获得上帝的恩典就必须行善功,而善功的多少以及其能否得到救赎,则完全由教会进行考查、给予确认、最终决定。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教会垄断了信徒“称义”的权利,甚至滥用权威、乱施恶行。这种被歪曲的信仰生活终于引发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马丁·路德把上帝拉回到人的内心之中,强调在心灵中体验我与上帝的关系,主张一种坚固的“信”。这种“信”的内在化和主观化在于非中介的直接性,即人的获救乃是基于上帝的恩典,因上帝赐予的信仰而被上帝称为义人,这是一种内心信仰力量的直接作用,在自己的精神和灵魂中直接与上帝会合,而不必凭借教会的中介作用,也无需通过理性的工具作用。人不是因为有自由意志才信仰上帝,不是因为教会的允许才接近上帝,而是因为已蒙神恩才有了坚定的信仰,有了对神的信仰才获得了真实的自由。“人在上帝面前不能凭自己的能力、功劳或善行称义,乃是因基督的缘故,借着信,白白地得称为义,就是相信因基督的缘故得蒙恩宠,罪得赦免,他藉着死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上帝在自己面前就算这为义。”[6]55这一由恩而生信、由信而称义、由义而得救的逻辑,明晰地支撑起“唯独信仰”“唯独圣经”“唯独恩典”的神学主张。上帝及其恩典,即一个人何以蒙神恩典和预选,这是神秘不可揣度的。“上帝的一切作为都很难寻,也很难述说,而人的知识和能力也不能把他们发现出来。只有信仰不借人的能力或其他辅助方能把握他们。”[6]129与上帝的神秘性相对应,人在神秘的信仰中直接地把握神圣的本质,既不需要权威的指导,也不依靠理性的引导,而是完全诉诸灵性即内心生活的修炼,在精神的自由中个人与上帝直接融为一体,实现神秘的人神合一。由此可见,路德将神秘主义归为个人的信仰,从而废除了教会的权威,这是将神秘主义引入到政治领域,起到了推动宗教改革的重要作用。正是由于宗教涉及到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于是神秘主义就随着宗教改革而泛化到整个当时德国社会之中,这就为神秘主义的传承提供了社会化的普遍基础。这种神秘主义传统不仅仅反映在宗教改革之后的信仰之中,它必然在哲学领域得到提升,这便促成了雅各·波墨的“神智学”的确立。
三、神秘主义传统的形成与确立
雅各·波墨被黑格尔称作“第一个德国哲学家”,其思想蕴含深刻的神秘主义,并且为这种神秘主义确立了德国特色的东西。在哲学意义上看,他第一次完成神秘主义与哲学的融合,构建起一套具有德国气派思辨性的宗教哲学,其特点是“与宗教直接统一,产生于宗教哲学,即神秘主义。于是当培根、笛卡儿分别作为近代经验论与理性论哲学的创始人出现在世人面前时,与他们同时代的德国人波墨向世人展示的则是神秘论哲学”[7]。雅各·波墨把神秘的信仰启示、深刻的思辨理性与粗野的语言形式结合在一起,构成带有神秘主义性质的“神智学”。雅各·波墨超越传统神学对最高本体的空洞抽象的看法,揭示神的形体化过程,也就是自我实现的过程,而对这一过程的描述是通过“三位一体”的辩证原则完成的。圣父蕴含生命原则于自身,只不过尚未实际展开,他超越于所有被造物的理性,既是有限的理智所无法把握的,也是常规语言所无能为力的。圣子是圣父在自己身上进行了区分,使自身成为他者,以有形化、形体化——世界万事万物的方式揭示自身。圣灵是光明与分离者及力的统一,出自圣父和圣子又回到圣父之中,充盈着整个圣父。圣灵的洋溢和沸腾,不是为了离异,而恰恰是为了返回。至此,“三位一体”彻底显露出神从自身出离再向自身回溯的完整循环。从思辨理性的角度来看,这一原则无疑受到黑格尔在探析自我意识时的重视,并将这种粗糙的形式加以精致化和进一步发挥。
作为与康德同时代的哲学家,耶可比反对康德哲学,尤其对康德所推崇的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持有批判态度,主张一种“直接知识”以区别于康德的批判哲学。耶可比所说的“直接知识”实际上就是信仰。在耶可比看来,哲学的理论论证模式本身就是值得批判的,因为论证作为手段只能接近较近的目标,但永远达不到最终的目标,而最终的目标对于我们来说才是根本的。上帝就是最终的东西,以理性认识上帝,实际上是将上帝贬低为有限的东西。信仰作为信仰,既不依赖于理性,也不需要通过理性来证明其真理性。从某些哲学命题出发来达到对上帝的信仰,或者把信仰转化为理性论证,无疑是“头脚倒置地走路”。通过这种对比,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及其论证)就成为一种“间接知识”。“直接知识”就是心灵的直观,是思想对客观性的一种独特态度——信仰,而且是带有反理智主义或非理性主义色彩的信仰,“必须走出心智的范围才能停留于真理的王国”[1]181,这就是一种神秘主义的感觉和情感。实际上,“直接知识”不是通过概念而是通过感觉和直观来把握绝对、把握存在、把握上帝、把握宗教,这就是一种直觉主义,最终成为一种神秘主义。对此,黑格尔评论道:“自从耶可比以后,凡是哲学家(如弗里斯)和神学家所写的关于上帝的著作,都建筑在直接知识、良知的知识这个观念上面;人们也称这种知识为天启。”[8]由此,一种“天启”的神秘主义成为德国哲学的一种特点。可见,耶可比在真正意义上划定了理性与信仰、哲学与宗教、理性与超理性之间的界线,并将人类理性之上的超理性归结为神秘主义领域,从而形成了德国神秘主义的基本向度和思维范式。
综上所述,从埃克哈特到耶可比的思想关联与发展,勾画了德国近代哲学中神秘主义传统形成的逻辑演进。从总体来看,德国近代哲学神秘主义的主基调是:首先,信仰高于理性,神秘主义是对于理性的超越;其次,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神秘主义是对理性的提升;最后,神秘主义与思辨主义相契合,与辩证法相结合。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宗教就是神秘主义[9]9,宗教在德国文化与社会中的地位决定了德国哲学与神秘主义的内在关联;在特定的意义上,神秘主义就是信仰或情感经验[9]9,这就构成了与理性的张力关系。于是,德国近代哲学在进入德国古典哲学之后,哲学家们就必须对神秘主义作出回应:康德区分了现象界与物自体,将上帝推至物自体领域,成为不可知的神秘对象。黑格尔对宗教的解读则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雅各·波墨的理解方式,但黑格尔认为宗教不过是“绝对精神”的表象表达方式,“三位一体”不过是以宗教的方式再现了“绝对精神”,从而让宗教的神秘消融于辩证理性之中,完成了宗教的理性化。
[1]高宣扬.德国哲学通史:第一卷[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2]Dieter Henrich,Between Kant and Hegel:Lectures on German Idealism[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70-71.
[3]埃克哈特.埃克哈特大师文集[M].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72.
[4]库萨的尼古拉.论隐蔽的上帝[M].李秋零,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2012.
[5]赵林.论德国哲学的神秘主义传统[J].文史哲,2004(5):128-133.
[6]马丁·路德文选[M].马丁·路德著作翻译小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7]李毓章.德国近代泛神论繁荣的精神缘由——以埃克哈特与斯宾诺莎为中心[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1-7.
[8]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248.
[9]王晓朝.神秘与理性的交融——基督教神秘主义探源[M].杭
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赵颖】
B516
A
1674-5450(2015)02-0040-03
2015-01-05
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专项项目(ZJ2013003)
肖宁,女,辽宁鞍山人,辽宁大学外国哲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