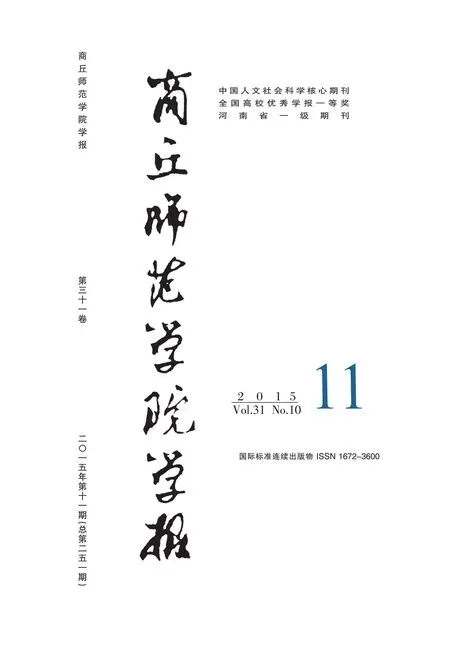焦虑情绪与母体回归
——《紫色》中西丽与莎格的关系新解
2015-04-10孟喜华
孟 喜 华
(商丘师范学院 外语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焦虑情绪与母体回归
——《紫色》中西丽与莎格的关系新解
孟 喜 华
(商丘师范学院 外语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爱丽丝·沃克的《紫色》是美国黑人文学中的一部经典作品,其中,西丽与莎格的关系曾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焦虑”概念为解读二人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弗洛伊德认为,人类自身的生产过程使人与母体分离,形成了人类焦虑情绪的原型,人在无意识之中就有了回归母体的本能冲动。在《紫色》中,主人公西丽遭遇了诸多不幸,焦虑情绪也一直伴其左右,回归母体的愿望在其内心深处不断酝酿。莎格在西丽的生命中就像一位母亲,她的出现为西丽回归母体提供了契机,并帮助西丽逐渐克服了自身的焦虑情绪。
焦虑;母体回归;《紫色》;生存
一、研究背景
爱丽丝·沃克的作品《紫色》是美国黑人文学中的一部杰作,自其出版之日起就广受赞誉,对它的研究更是经久不衰。目前在国内《紫色》就有六个中译本[1]20,相关研究更是层出不穷,足见这部作品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国界。这部作品主要以书信体的方式讲述了主人公西丽的成长历程,她从一个逆来顺受的黑人女孩成长为一个自立自强的黑人女性。而在其成长过程中,莎格无疑发挥了重大而积极的作用,所以西丽和莎格的关系一直是评论家在解读这部作品时关注的焦点,很多评论家都曾试图探究她们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西丽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期寻找到黑人女性发现自我、成就自我的途径。
多数研究者倾向于将西丽与莎格两人的关系界定为同性恋关系、姐妹情谊或者妇女同盟,这些观点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同时又都有其明显的片面性。西丽与莎格过于亲昵的行为容易让读者以为二人之间有同性恋关系的存在,进而认定“正是西丽和莎格的女同性恋关系促成了西丽奇迹般的转变”[2]62。可是,同性恋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恋人关系,一般是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的,同性恋者大多是不会和平地接受一个第三者的存在的。而在《紫色》中,西丽并不是莎格唯一的爱恋对象,莎格还同时爱着不止一个男人,西丽并没有因此而疏远莎格或者断绝与莎格的关系。所以,二人之间虽互相仰慕,却并没有同性恋人之间的那种爱恋,二人之间所谓的同性恋关系至少在严格意义上难以成立。而将二人之间关系看做姐妹情谊或者妇女同盟的观点也值得商榷,因为这种关系要求双方拥有相对平等的身份或处于较为类似的生活境遇,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情感共鸣并最终结成同盟以实现共同的目标。可是在二人的关系中,西丽很明显更加依恋莎格,而莎格相对比较独立,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有自己明确的愿望与追求,两个人在美国这个大的生存环境中都有着作为黑人女性的类似地位,并且在西丽的家这个小的情境中,她们的地位却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处处受到奴役的小媳妇,而另一个却是个统领一切的大女人。更为关键的是二人之间并不平等的情感关系,西丽大部分时间里把莎格看成了生命的全部,西丽一直是仰视莎格,依恋莎格,而莎格只把西丽看做生命的一部分,她虽然也欣赏西丽,但是她更多是俯视西丽,以近乎长辈的身份来引导、帮助西丽,使其在心智各方面得到成长,所以将二人的关系定义为姐妹情谊或者妇女同盟也显得不够妥当。
这些观点之所以不能揭示出西丽与莎格的关系的本质,主要是因为它们都是将两个人物放在了一个背景广阔的大的社会语境中来加以审视,更多是从二人关系的外在表现上去界定二人所承载的社会意义的,并没有跳出美国黑人文学研究的窠臼,还在延续着黑人文学研究的传统,刻意地去探讨美国黑人在一个白人主导的社会语境中的抗争与话语表达。它们过多强调了莎格在帮助西丽成长中的作用以及两人同为黑人女性的身份认同,而未能深入挖掘西丽成长过程中其个人内在心理状态的发展历程,从而忽视了在无意识层面促使两人建立起亲密关系的深层因素。无论西丽还是莎格,她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黑人,而人类的很多应激反应更大程度上是基于特定社会语境下形成的个体心理状态,只有找到了人物内在的心理状态,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发现人物各类自觉行为的根本动机。
本文正是在对前人研究成果反思的基础上,结合弗洛伊德分离焦虑理论,提出对西丽和莎格二人关系的新认识。由于西丽所处的生存情境对其自身的生存带来严重挑战,其生存本能致使其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持续而强烈的焦虑情绪,进而促使她在无意识的层面更加倾向于回归母体,用那种原始的安宁情境来消弭现实的焦虑情绪。而西丽对莎格的依恋其实是对作为母亲形象出现在她的生命中的莎格的依恋,是对母体的依恋,是对母体回归的向往和本能冲动。
二、分离焦虑理论
“焦虑是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概念,精神分析对焦虑的研究也最为系统和深入。”[3]36奥地利著名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对于焦虑理论有着深入的研究,他指出:“焦虑这个问题是各种重要的问题的中心,我们若猜破了这个哑谜,便可明了我们的整个心理生活。”[4]315可见,焦虑在人类心理活动中的重要地位。“所谓焦虑(anxiety),是指由紧张、不安、忧虑、恐惧等感受交织而成的复杂情绪状态。”[5]458焦虑是人类一种非常普遍的情绪经验,它存在于我们生命中的方方面面,并伴随我们一生,“无论何人都有时亲身经验过这个感觉,或说正确点,这个情绪”[4]314。弗洛伊德认为,焦虑跟神经官能症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但是焦虑与“神经过敏”(nervous)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为了区别“焦虑”和“神经过敏”,他曾经将焦虑分为两种类型:真实的焦虑和神经病的焦虑。前者是人类普遍经历的一种情绪,而后者是出现症候的病态情绪。在两种类型中,前者更具有普遍意义,是所有人都无法完全避免的情绪体验,只是因为没有表现出神经官能症的各种症候,这种情绪并不是病态的表现,所以未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可是“真实的焦虑”却因其普遍性而具有更加广泛的研究意义。根据弗洛伊德的解释,“真实的焦虑或恐怖对于我们似乎是一种最自然而最合理的事;我们可称之为对于外界危险或意料中伤害的知觉的反应。它和逃避反应相结合,可视为自我保存本能的一种表现”[4]315。可见,真实的焦虑是人类生存的本能,是对于可能给自己带来生存威胁的情境和事物的正常合理的知觉反应,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当然,如果这种焦虑情绪处于持续高压的态势而得不到缓解就有可能导致神经病的焦虑。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生产过程是所有焦虑情绪的起源和原型,由于生产后新血液的供给已经停止而外在情境突然变化,从而产生了出生时的焦虑经验,而这种经验“可再现于恐怖或焦虑状态之中……后来几乎总是与一种情感相伴而起”[4]317-18。幼儿作为一个脆弱的机体,其与母体自然分离之后,进入一个充满生存威胁却又无能为力的生存情境之中,焦虑情绪就会产生并植根于每个人的无意识之中。弗洛伊德的学生兼同事奥托·兰克(Otto Rank,1884-1939)在弗洛伊德的资助与影响下也走上了心理分析的研究道路,其在《出生创伤》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弗洛伊德这一焦虑理论,“认为影响个体未来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出生时与母亲分离的‘原初焦虑’,无论是神经症的还是正常的焦虑都源自于出生,源自于同母亲子宫这个安全地方的原初分离”[6]50。当一个人遇到类似的情境变化和可预知的危险时,在他的潜意识中就会自然地唤起与母体分离时的焦虑情绪。“第一次的焦虑是由于与母体分离而起,也很令人寻味。我们自然要相信有机体经过了无数代,已深深埋有重复引起这第一次焦虑的倾向,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免得掉焦虑性情感。”[4]318人类的焦虑根源于生产过程造成的与母体的分离,从一个舒适、安全的情境进入一个陌生的情境,焦虑情绪就产生了。由于出生而产生的分离感是一切后来出现的焦虑情感的基础,所以,当人们面临生存威胁时就会唤起无意识中的记忆并产生焦虑情绪,而每当焦虑情绪再次出现的时候,人们总会不自觉地产生回归母体的本能愿望。
三、西丽的焦虑情绪的形成
弗洛伊德对“真实的焦虑”的界定也恰恰说明,焦虑其实是人的一种生存本能,当生存情境可能给人类自身带来生存威胁的时候,焦虑情绪就会作为人类不自觉的一种知觉反应而出现。在《紫色》这部作品中,主人公西丽的生命中充满了不幸的遭遇,母亲的去世和继父的欺辱让她在家里的生活如同炼狱,嫁人后丈夫的打骂更是让她在男人面前唯唯诺诺、噤若寒蝉,种种不幸遭遇让她真切感受到了周围的情境给她生存带来的严重威胁,面对真实存在的各种潜在的生存危机,她首先的知觉反应其实就是弗洛伊德所谓的“真实的焦虑”。生活对她来说充满了艰辛,她几乎每天都生活在焦虑的情绪之中,每一分钟都感受到外在的生存情境中存在的各种危险与生存威胁。
1.母亲的去世
西丽首要的焦虑来自于母亲的去世,这一变故顷刻间使她本来就非常恶劣的生存情境进一步恶化,这种情境的变化自然地引起了她的焦虑情绪。在小说的一开始,西丽就讲述了她母亲的去世,似乎预示了这一事件是她一生中所有不幸的开端,是她焦虑情绪的直接动因。虽然她的母亲因为她未婚先孕而一直咒骂她,她还是非常爱自己的母亲的。西丽说:“可能因为我妈妈咒骂过我,你就以为我生她的气了。其实我没有。我替妈妈感到难过,因为她相信他(西丽的继父)编造的故事,气死了。”[7]5西丽的母亲至死都不知道西丽怀的是谁的孩子,而是相信西丽的继父的话,认为西丽是一个不检点的女孩。可是西丽不敢将继父奸污自己的事情告诉自己的母亲,在小说的开篇有一句话点明了原因:“除了上帝之外,你最好对谁都别说,不然的话,那会害死你的妈妈。”[7]1这句话没有标明说话人,但是读者可以推测出这是西丽的继父威胁西丽的话。正因如此,西丽没有将实情告诉自己的母亲,这样做虽然让母亲一直误会自己,但是西丽却认为这样做保护了母亲,如果不是出于对母亲的爱,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是不可能守住这样的秘密的。
弗洛伊德在分析儿童焦虑症时发现,儿童习惯于“一个亲爱而相熟的面孔,主要是母亲”。[4]326-27因此当儿童离开母亲的时候就会莫名的焦虑。对于西丽来说,母亲的去世不仅是与“一个亲爱而相熟的面孔”的分离,更是与一个可憎又凶狠的面孔的朝夕相对,这是外在生存情境的一次巨大的变化。母亲在世的时候,她是唯一一个可以给西丽带来安全感的人。因为她的继父奸污她的时候都是趁她的母亲不在的时候,所以有母亲在场的时候,她就是安全的。如果说人类生产的过程是母体分离焦虑的原型,那么母亲的去世无疑是对母体分离焦虑的一次重现。所以,母亲的去世,无论在表层还是在深层都给西丽的内心带来了无尽的焦虑情绪。
2.男人的威胁
西丽的另一个焦虑主要来自身边的男人,尤其是她的继父和她的丈夫艾伯特。她的继父污蔑她在教堂里对一个男孩抛媚眼的时候,她在写给上帝的信中辩解:“我从来不会去看男人。真的。不过我会瞧女人,因为我不怕她们。”[7]5显然,西丽害怕男人,当然她之所以害怕男人是因为她的继父给她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这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创伤记忆。由于继父对她的伤害,西丽对男人一直都是又恨又怕,生怕受到他们的伤害。她对男人的害怕其实是其焦虑情绪的一种表现,是面对可能的生存危险的知觉反应。
随后,西丽嫁给了艾伯特,一个有着四个孩子的鳏夫。西丽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而有丝毫的改善,艾伯特把她当牲口一样吆喝,当保姆一样使唤,稍有不顺心,无论是不是西丽的原因,抓住她就是一顿猛揍。艾伯特揍西丽不但频繁而且狠,当他的儿子哈泼问他为什么总是揍这个后妈的时候,“某某先生说,因为她是我的老婆。还有,她太倔了。女人的用处只是——他没把话说完”[7]18。“某某先生”就是西丽的丈夫艾伯特,因为他经常虐待西丽,所以西丽在自己的心中不愿意也不敢说出他真实的名字,而是称他为“某某先生”。可见,在西丽生活的情境中,男人的存在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她作为女人的生活的安全和快乐,西丽这时候甚至说艾伯特那副模样使她想起了她的继父,她将两个男人的形象合在了一起,因为她发现男人的存在总会威胁到她的生存,带给她无尽的苦难,所以,只要她生活的情境中有她的继父和丈夫这样的男人,她的焦虑就不会停止。当艾伯特打她的时候,西丽把自己想象成一棵树,她甚至因此推断“树是怕人的”[7]18。这说明西丽对男人的恐惧已经深入骨髓,男人成了她生命中的一个潜在的生存危险,成了她焦虑情绪形成的又一个重要根源。
与母亲的分离、遭受继父的奸污和丈夫的殴打,这些都是西丽经受的重大创伤性事件,这些事件逐渐成为了其内心深处的创伤记忆并直接影响了她在现实生活中的知觉反应,于是西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对创伤再现的焦虑情绪。
四、母体回归的本能冲动
弗洛伊德认为,人生的每一次焦虑体验都会在潜意识里唤起对最初的焦虑情绪的记忆,而我们最本源的焦虑体验就是生产过程中与母体的分离。所以,焦虑中的人们都有重回母体的冲动,希望在那种最原初、最安全的情境中重新获得那份伊甸园般的安宁,从而远离现实的焦虑。西丽的生活中一直充满着焦虑情绪,在她的内心深处对母体的依恋从来没有停止过,回归母体更是她内心深处强烈的愿望。莎格的出现正好迎合了西丽的这一心理需求,正是西丽对于回归母体的本能冲动使得她很好地接受了莎格,并对莎格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依恋,所以本应水火不容的情敌却最终成为了无话不谈的至交。
在西丽还没有见到莎格本人的时候,莎格就已经作为母亲的形象烙在了西丽的印象中,她第一次见到莎格的照片就不自觉地把她与自己的母亲联系在了一起。在西丽与莎格真正相遇之前,西丽就听说了有关“某某先生”的这个情人的各种风言风语。“某某先生”喜欢上了西丽的妹妹耐蒂,当他来向西丽的继父求亲的时候,莎格的照片从他的钱夹里掉了出来,西丽看到照片里的莎格不禁感叹:“莎格·艾弗里是个女人,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她比我妈妈还要漂亮。比我要漂亮上一万倍。”[7]6西丽在看到了莎格的照片之后认为莎格比自己漂亮,这一点容易理解,因为西丽也知道自己长得很丑,可是她却将其与自己的母亲相比并认为她比自己的母亲还漂亮,这一方面说明了西丽确实认为莎格是个漂亮的女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西丽感觉莎格是个像母亲一样的“亲爱而相熟的面孔”。这时候的西丽对莎格应该没有丝毫的反感。这一段讲述看似一个无意的插曲,其实却在西丽的内心深处留下了印迹,揭示了在西丽的潜意识之中莎格与母亲形象之间的本初联系,也为后来她对莎格的依恋埋下了伏笔。
后来,当西丽真正遇到莎格的时候,她发现莎格在她的生活中发挥着与自己母亲类似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改善她的生存情境,从而减轻她的焦虑情绪。莎格在的时候艾伯特就不会揍西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莎格在的时候西丽就会一定程度上免于遭受艾伯特的性暴力,这让西丽的焦虑情绪有了很大程度的缓解,就像当年她妈妈在的时候她的继父才不会对她下手,她因为害怕继父而产生的焦虑情绪就会有所缓解一样。西丽不仅仅把莎格看做了自己的亲人,更是把她视为母亲一样的形象,所以当西丽给莎格梳头的时候,西丽感觉到:“她好像是个洋娃娃或者是奥莉维亚——又或者她好像是妈妈。”[7]53当莎格说要离开她们去出门闯江湖的时候,西丽非常失落,“我什么话都没说。我难过,同耐蒂走的时候一样”[7]74。这个时候,西丽已经非常依恋莎格了,不希望她离开。西丽没有将莎格的这次离去比做母亲的离去,而是比做耐蒂的离去,这并不能说明西丽与莎格之间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姐妹情谊,她之所以选择耐蒂的离去而不是母亲的离世进行类比,是因为她与莎格的分离和与耐蒂的分离在表现上更具相似性,都是生离,而她与母亲的分离是死别,无法在这里进行类比。同时,这恰恰说明了作为母亲形象的莎格的即将离去给西丽带来的强烈的分离焦虑。因为西丽和她的妹妹耐蒂之间关系亲密,所以这个类比充分说明了在西丽内心深处,莎格和耐蒂一样都是她“亲爱而相熟的面孔”,而她不舍莎格的原因其实不是亲情的难以割舍,而是对分离后外在生存情境变化产生的生存威胁的焦虑,说到底还是对一个相对舒适的生存情境的留恋,更是对一个母体的依恋。
真正让西丽体会到回归母体的宁静,感受到一个没有焦虑的情境的时候就是当她和莎格睡在一起的时候。有一次,“我们睡得很香。她背靠着我,我搂着她的腰。有点像小时候跟妈妈睡觉的样子,不过我简直不记得跟妈妈一起睡过觉。又有点像跟耐蒂一起睡觉,不过跟耐蒂一起睡没有这样美。……我觉得像在天堂里一样”[7]114。很明显,这里西丽已经明确地说明了她跟莎格睡在一起的感觉与跟耐蒂不一样,而是更像跟妈妈一起睡觉。西丽跟耐蒂的姐妹关系非常好,是非常深厚的姐妹情谊,西丽在这里将她跟莎格在一起的感觉区别于跟耐蒂在一起的感觉,这种描述直接表明了西丽与莎格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姐妹情谊,而应该是对母体的一种依恋心理,是对回归母体的宁静情境的向往。西丽把跟莎格睡觉的感觉比喻成在天堂里一样,对于笃信上帝的西丽来说,天堂是一个宁静祥和的情境,那里的人们无忧无虑,自然就没有现实生活中这些真实的焦虑情绪。在莎格的怀抱里,西丽暂时摆脱了内心深处的焦虑情绪,体会到了生存情境片刻的安宁,这正是母体回归的本能愿望的暂时实现,而这种幸福的感觉让西丽在心理上更加依恋莎格。
伴随着西丽心智的成长,她最终克服了自己的焦虑情绪和母体回归的情结。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总是伴有深深的焦虑情绪而沉浸在母体回归的快乐中,她将永远也无法获得完整的人格并成长为一个独立的个人。西丽为了摆脱让她焦虑的生存情境,最终跟随莎格来到了孟菲斯,在莎格的帮助下,她发掘了自己裁剪衣服的天赋,创立了自己的服装公司,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成功地找到了获取独立人格的生存方式。她不用依赖任何男人而获得生存资料,也不再为自身的生存情境而担心,焦虑情绪也就随之淡化。当一个人的焦虑情绪减弱甚至逐渐淡化之后,她对母体的依恋、对母体回归的向往也就随之尘封在茫茫的无意识之中。所以,当莎格爱上了一个十九岁的男孩子并准备远行的时候,西丽虽然非常伤心、失落,但是她并没有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心碎而死,反而可以独立地和周围的人进行交往,尤其是和她曾经的丈夫“某某先生”。在这个过程中,她逐渐地融入社会之中,树立了自尊,也赢得了别人的尊重,甚至前所未有地得到了“某某先生”的爱慕,生活变得越来越舒适了,她发现“没有莎格也能活的很快活”[7]283。这一切正说明了西丽的成熟,她不再依赖男人,也不再依恋母体,而她的焦虑情绪也越来越淡了,回归母体的愿望也就不再强烈。这种成长使得她可以离开母体正常地生活,甚至活的更好。
五、结语
西丽在与莎格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其的依恋情绪,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抗拒焦虑情绪而形成的,产生于内心深处不自觉的自我抵御机制。在焦虑情绪下,西丽在无意识中回忆起了焦虑原型,即生产过程中的母体分离,从而产生了对回归安宁的出生前情境的向往和对回归母体的本能冲动,这才是西丽对莎格依恋的真实动因。西丽与莎格之间的这种依恋不是同性之间的爱欲,也不是姐妹之间的情义,而是西丽对母体的无意识的向往,是幻想通过回归母体来克服自身焦虑情绪的生存本能。其实,在西丽的内心深处,她很少将莎格看做同性的爱恋对象或者平等互助的姐妹,而是更多地将其视为自己的心灵的依靠,是一个像母体一样可以为焦虑中的孩童提供安慰与安全感的存在。
由于不幸的人生遭遇产生的焦虑情绪,西丽一直都在追寻一份安宁,直到她遇到了莎格,体会到了母体回归的快乐。莎格就像是西丽的生活中的精神母亲,给了她第二次生命,莎格用自己的言行成功地将西丽从一具行尸走肉转变成了一个鲜活的生命,使西丽成长为个性独立的个人,而不再是男权社会的玩偶。在莎格的帮助下,西丽勇敢地跳出了那个承载她所有焦虑情绪的情境,逐步树立了自尊、自强、自立、自助的信念,彻底克服了原有的焦虑情绪。随着西丽内心深处的焦虑情绪的淡化,她对母体的依恋也就逐渐消融了,她回归母体的愿望也慢慢淡化了,她对莎格的依恋也就不再像以前那么强烈了。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西丽与莎格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西丽在焦虑情绪下对回归母体的向往以及对于作为母体象征的莎格的依恋,而正是莎格的存在帮助西丽逐步摆脱了现实的焦虑,使其成长为一个可以自由应对生存情境的正常人。
[1]李红玉.译者的性别意识与翻译实践——谈性别视角下的《紫色》四译本[J].中国比较文学,2008(2).
[2]薛小惠.《紫色》中的黑人女同性恋主义剖析[J].外语教学,2007(5).
[3]刘海宁.弗洛伊德焦虑理论书评[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09(1).
[4]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5]张春兴.现代心理学:现代人研究自身问题的科学:第3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6]司群英,郭本禹.兰克:弗洛伊德的叛逆者[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2.
[7]Walker, Alice.TheColorPurple:harvest edition [M]. Orlando: Harcourt, 2003.
【责任编辑:郭德民】
2015-06-03
孟喜华(1982—),男,河南虞城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I106
A
1672-3600(2015)11-009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