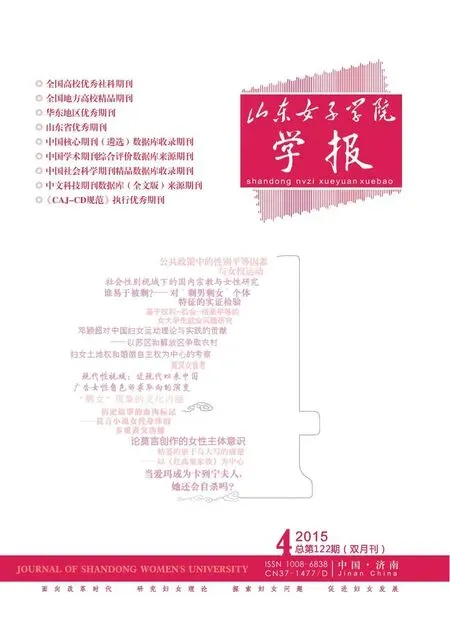论莫言小说中的母亲形象
2015-04-10赵思奇
赵思奇
(河南大学,河南 开封 475001)
·女性文化视野下的莫言创作专题研究·
论莫言小说中的母亲形象
赵思奇
(河南大学,河南 开封 475001)
作为一位从乡村走出来的作家,莫言创造出大批寓意深远的作品,其中的女性形象是莫言小说中耀眼的闪光点,尤其母亲形象,更是千姿百态。莫言从一位男性作家的角度审视母亲的生存和心理,同情她们的命运,不仅表达了他对“母亲”的复杂感情,同时也对男性中心主义表现出否定和质疑。
母亲;身体;女性意识;意识形态
作为一位从乡村走出来的作家,莫言创作出了大批寓意深远的作品。这些作品塑造的人物众多,性格各异,展示了璀璨的历史长廊和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人生百态。其中的母亲形象,更是千姿百态,各异的人生轨迹和迥然相异的命运,形塑了“母亲”的伟大和坚忍,在特定的时代和政治环境的重负下,她们不仅承载了个人命运的无法承受之重,同时也承载了历史的驳杂和苦难。
一
综观莫言的小说创作,他笔下的母亲形象大致有几种类型。
第一,传统的母亲。这类母亲勤劳、善良、忍辱负重,有着博大的胸怀和无私的爱心,即使时代风云变幻,即使兵戎相见、硝烟四起,也无法止息她们对子孙的爱护和付出。如《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被当作讨价还价的“商品”嫁入上官家后,就开启了她血泪的人生。丈夫没有生育能力,却把不能传宗接代的责任归咎到她身上,在经历了多次暴虐之后,她终于认识到“女人,不出嫁不行,出了嫁不生孩子不行,光生女孩也不行。要想在家庭中取得地位,必须生儿子”[1](P594)的残酷真理,开始了屈辱的“借种”历程。她先后和于大巴掌、赊小鸭的外乡人、江湖郎中、高大膘子等人,生下8个女儿和1个儿子。上官鲁氏的生命力如此坚强,在河沿被4个败兵强暴后,她忍住了死的欲望,活了下去。在教堂被鸟枪队员强暴,亲眼目睹牧师马洛亚跳楼身亡,她又一次活了下去。不管女儿嫁给土匪、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不管她们之间因政治立场不同如何斗争,上官鲁氏均毫无阶级成见,一如既往地爱护她们,对于她们的后代,上官鲁氏一视同仁地尽心抚养。面对着子孙因饥饿、战争、生病一个个死去,上官鲁氏用坚忍和不屈与命运抗争。活着,把生命传递下去,是她唯一的希望。她的一生犹如千疮百孔、多灾多难的旧中国历史。再如《粮食》中的梅生娘,因丈夫是富农,又毒死了社里的耕牛,犯了大错,被送到劳改营,家里的生活重担就落到了她的肩膀上,她要养活3个孩子和1个痴呆的婆婆。可是在饥饿的年代,只能靠挖野菜、吃树皮填饱肚子,当野菜也稀缺的时候,她只好让全家人吃观音土。她即使饿得双腿肿胀透明,干起活来仍然尽职尽责。后来她听从了同在磨坊里推磨的婆娘“这年头,人早就不是人了,没有面子,也没有羞耻,能明抢的明抢,不能明抢的暗偷,守着粮食,不能活活饿死”[2](P108)的劝说,偷拿粮食塞到裤腰里,准备回去让嗷嗷待哺的孩子们吃,但遭到了负责磨坊的王保管的侮辱。寻死不成的她从呕吐中得到启发,再推磨时就将粮食囫囵吞下,回到家中再吐出来,正是靠着这种方法,让婆婆得以高寿,让孩子发育良好。《姑妈的宝刀》中的孙姑妈,有两个儿子,但就像她的丈夫一样,从未露过面,只有3个孙女大兰、二兰、三兰跟着她生活,她从未抱怨过生活的不公,把3个孩子拾掇得妥妥帖帖。闹饥荒的时候,为了填饱肚子,二兰偷吃了生产队里的萝卜,遭到了生产队长王科皮带抽打,孙姑妈“捯着小脚,直逼到王科前面”,用威慑的口气说:“王队长,小心着点,别闪了手脖子”[2](P150)。这类母亲形象最突出的特点,是隐忍付出、任劳任怨。
第二,叛逆的母亲。这类母亲个性鲜明,敢爱敢恨,野性奔放。如《红高粱家族》中的“我奶奶”戴凤莲,她痛恨贪财的父亲为了一头骡子将她许配给有麻风病的单扁郎,回门时在高粱地里大胆地和东北乡雇工余占鳌野合。单家父子被杀,对簿公堂之时,她机灵地认县长做干爹,逃过一劫。掌管单家后,她安抚伙计,清洗庭院,把烧酒生意做得轰轰烈烈,让众人心服口服。当余占鳌移情别恋时,她既没有哭闹也没有忍气吞声,而是用以牙还牙的方式捍卫自己的爱情。17岁的姑娘玲子,被余占鳌叔叔余大牙强奸,为了笼络任副官这个人才,她要求余占鳌枪毙余大牙以肃军纪。当冷支队长和余占鳌商讨抗日谈僵时,她深明大义,“左手按着冷队长的左轮枪,右手按着余司令的勃朗宁手枪”,劝说两人“有本事对着日本人使去”[3](P24)。日本鬼子进村向她靠近时,她机智地把罗汉大爷的血抹在脸上,又一把撕散头发,疯疯癫癫地跳起来,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模样,躲过了日本人的魔爪。她设计用铁耙扎坏日本人的车轮子来伏击他们的汽车队。为了支持抗日,她让唯一的儿子前去战场,也把自己的生命埋葬在高粱地。戴凤莲一生“大行不拘细谨,大礼不辞小让”,“敢于反抗,敢于斗争”[3](P118)。再如《檀香刑》中的孙眉娘,母亲去世早,她从小跟着父亲的戏班跑遍九村十八屯,长到18岁,成为高密东北乡最美丽的姑娘,“一颗熟透了的果子,一个青春健美的身体”[4](P145),“螳螂脖子仙鹤腿”[4](P21)。跑江湖的人生经历养成了她泼辣豪爽、野性十足的个性,她的风骚多情让县城的浮浪子弟垂涎。但风流成性的父亲没有给女儿裹脚,孙眉娘成了“大脚仙子”,“看了上半截把人想死,看了下半截把人吓死”[4](P21),她后来委屈嫁给了愚笨的屠户赵小甲。当婆婆颠着小脚拿着剔骨的利刃修理孙眉娘的“天足”时,眉娘忍无可忍,骑在婆婆身上一阵拳打,争来了当家作主的权力。儒雅潇洒的知县钱丁到任后,孙眉娘对他一见钟情,害了严重的相思病,差点没把命搭上,她虽明白“这场烈火一样的单相思,注定了不会有结果”[4](P156),但还是忍受着卑贱的出身和一双大脚带给她的自卑和痛苦,不顾一切地投到钱丁的怀抱,“能与你这样的一个男人有过这样一段死去活来的情就知足了”[4](P303)。她执着于无结果的无妄爱情,在家仇、国恨、爱情和亲情的挟裹下,身怀六甲的她最终拿起刀,杀死了“大清第一刽子手”,完成了为父报仇的壮举。综观这类母亲形象,她们身上充溢着鲜活的生命力,她们美丽丰腴,反抗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追求自由爱情,勇敢表达自身诉求。
第三,敢于担当的母亲。这类母亲有着坚强的性格和顽强的生命力,不管生活多么无奈,命运多么无情,都压不垮她们的脊梁,也磨灭不掉她们对幸福追求的信心。面对不幸,她们从来不会自暴自弃,而是不屈地挺起头,制造出理想,给自己的生活以“盼头”。如《白狗秋千架》中的暖,“鼻梁挺秀如一管葱”“牙齿洁白”“婷婷如一枝花,双目皎皎如星”[5](P221-222),17岁那年是学校宣传队骨干,歌声让英俊的蔡队长都入了迷,许诺年底征兵把她征去。可暖没有等到那一天,在一次秋千事故中,她的右眼被一根槐针扎瞎,只得嫁给了王家丘子的哑巴。哑巴丑陋剽悍,脾气暴躁,性格多疑,暖生了3个儿子,不幸都是哑巴。暖被残酷的生活腐蚀得面目全非,她忍受着生活的痛苦,“该遭多少罪都是一定的,想躲也躲不开”,“这就是命,人的命,天管定,胡思乱想不中用”[5](P227-228)。当10年后与青梅竹马的“我”在村里相遇后,暖对“我”提出一个请求,帮她生一个会说话的孩子:“你答应了就是救了我了,你不答应就是害死了我了。有一千条理由,有一万个借口,你都不要对我说”[5](P238)。再如《四十一炮》中的杨玉珍,丈夫跟情人私奔,她忍受着痛苦和压力,带着儿子发愤图强,艰苦创业,为的就是争一口气,“咱要干出样子让他看看,也让村子里的人看看,没有他咱们比有他过得还要好”[6](P16)。虽然杨玉珍一直承受着巨大的精神苦痛:“有多少次,我把绳子都搭到梁头上了,不是有个小通牵挂着,有十个杨玉珍也死光了”[6](P108),但当无处投奔的丈夫归家后,她原谅了丈夫,接纳了丈夫和情人的女儿,让村里的人钦佩,“杨玉珍这个女人不简单,能吃苦,有耐性,有远见,明事理,是一个肚子里有牙的厉害人物”[6](P175)。为了更好地发家致富,她说服丈夫跟着老兰干,自己也成了华昌总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
第四,被阉割的母亲。这类母亲有做母亲的强烈愿望,也有做母亲的预期和准备,但由于主观或客观的原因,无法得以实现,只得将这种欲望暂时压抑,然而这种愿望从不曾消逝,会由于某个特殊的机缘,或隐或显地表露出来。这种母亲类型在莫言的小说中不常见,可以《蛙》中的“姑姑”万心为代表。万心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容貌出类拔萃,1950年代毕业于卫生学校,在公社卫生院做妇产科医生,整个家族都以她为荣。她与多才多艺的空军飞行员王小倜建立了恋爱关系,可到了谈婚论嫁时却发生意外,王小倜因不堪忍受“太革命太正派”的万心这个“红色木头”,驾驶飞机叛逃到台湾,娶了貌若天仙的歌星陶莉莉。这个变故对“姑姑”的打击是巨大的,她认为这个人“毁了她”,尤其在阶级斗争甚嚣尘上的年代。事实上,“姑姑”内心承受的痛苦不仅仅是政治方面的。她将全副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借以麻醉自己。在乡生育高峰期,她“既当医生又当护士”“连续几天几夜不合眼”[7](P53),到了计划生育高潮期,她又挨家挨户宣传党的政策,带着助手和徒弟强制给超生家庭节育,面对诅咒和人身伤害,她毫不惧怕,“姑姑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党指向哪里,我就冲向哪里!”[7](P89)一直到退休,“姑姑”都用工作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再不曾触摸感情,她的形象也从“出水芙蓉般”变成“衣袖高挽,身体胖大,白发苍苍,像一个‘文革’后期的县社干部”[7](P89)。多年的计生工作,使得她内心对孩子产生了一种矛盾感情,她渴望做母亲,渴望过正常的家庭生活,然而她又不得不狠下心为超生孕妇做堕胎手术,这些未曾出世的婴儿,在“姑姑”内心留下了深深的空缺和忏悔,当她在似梦似幻中听到“蛙声如鼓”“仿佛是成千上万的初生婴儿在哭”“仿佛是无数受了伤害的婴儿的精灵在发出控诉”[7](P221-222),以至于被一只青蛙吓得“口吐白沫、昏厥倒地”,最后嫁给了祖宗三代捏泥娃娃的艺人郝大手,以弥补内心的歉疚。“姑姑”是一个悲剧人物,造成她悲剧命运的,有性格的因素,更是时代使然。
二
莫言对母亲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对母亲性和生殖能力的描述。莫言曾说:“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作品,但你如果要了解我,应该看我的《丰乳肥臀》。”在《丰乳肥臀》中,莫言欣赏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本色英雄司马库,另一个就是母亲上官鲁氏,“母亲”在莫言的作品中有特殊含义。她是多产的,富有生育能力的。小说一开始,就是上官鲁氏生第七胎的情景,作者别出心裁地将她的生产和黑驴的生产放在一起,鲜血、吼叫、腥臊,电影式的特写镜头,震撼人心。她“将褂子尽量地卷上去,袒露出腹部和乳房”,她那“大得出奇的肚子”上“暴露着弯弯曲曲的蓝色血管和一大片凹凸不平的白色花纹”[8](P6),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对女性生育能力的崇拜,从远古象形文字、绘画和陶器中已能初见端倪,从文学作品中也可发现类似于“母神”的“地母”形象,如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悉多和中国神话故事中的女娲。“母神”是人类蒙昧初开之时产生的第一神,她不仅是人类的始祖,也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创世之神、生育之神,她不仅象征着五谷丰收,更表征着生命的延续和生命力的蓬勃兴旺。
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言凸显母亲的性能力和生殖能力,正是表达了对“美”的追求。他在作品中用很多生动的词汇不厌其烦地描写母亲的乳房,“宝葫芦”“欢快的白鸽”“瓷花瓶”“一对小鹿”……“胖的,瘦的,大的,小的,白的,黑的,黄的,红的,咧嘴的石榴歪嘴的桃”[8](P533),这乳房的狂欢和乳房的盛宴,在淋漓尽致地表露对“母亲”无以复加的依恋和俄狄浦斯渴求的同时,也为他带来了批评和质疑之声①。事实上,男性作家在描写女性时,最先进入的层面往往是女子外在的容貌和形体,“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翩若惊鸿,婉若游龙”“风吹仙袂飘飘舞,犹似霓裳羽衣舞”,由姣好的容颜自然而然进入心理层面的刻画。莫言也不例外,他早期笔下的女子是唯美爱情的化身,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发生些许改变,到了《红高粱家族》则完全放开,这部小说在当时中国文坛引起了巨大轰动,尤其1987年张艺谋执导的由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获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让莫言成为读者和批评家关注的焦点,“莫言也正是从此成了文坛上不可忽视的人物”[9]。
母性的伟大是莫言在作品中反复歌颂的主题,他的很多小说都围绕着这个主题,这源于他成长过程中母亲无私的关爱和付出,他以此表达对母亲的深爱和感激。他笔下的母亲是坚强不屈的,是吃苦耐劳的,是感情充沛的,是具有鲜活生命力的。为了凸显母亲的这些特质,莫言甚至不惜鞭挞男性角色,比如《丰乳肥臀》中上官寿喜没有生育能力,《檀香刑》中的赵小甲也是如此,《红高粱家族》中单扁郎是个麻风病患者,《姑妈的宝刀》中父亲则彻底缺席。当下女性小说②在描写两性关系时,为了彰显女性的坚强和成熟,倾向于用“大女子主义”去批判、压制男性,甚至不惜扭曲男性的形象和他们惯常的偶像地位。这种叙述模式在男性作家笔下并不常见,而莫言却擅长于此,他的出发点和上述女作家们或许并非一致,然而却殊途同归。莫言笔下的母亲往往不“安分守己”,她们游离于伦理之外,体验世俗无法接纳的感情和性,然而作者并未把她们置于道德的砧板上反复拷打,而是另辟蹊径,追根溯源,用新历史主义的叙事模式构置一波三折的情节,淡化世俗意义上的说教,表征母亲对男权桎梏的反抗和对个性解放的追求,于是,“婚外情”抑或“偷情”便成了她们对抗和叛逃的武器。莫言不惮于在作品中批判男性的不忠,比如《红高粱家族》中余占鳌移情恋儿,《四十一炮》中罗通和野骡子私奔,《蛙》中王小倜为逃离姑姑不惜政治叛逃。从《诗经》开始,就有了描写弃妇的诗篇,“女也不爽,士贰其行”“条其啸矣,遇人之不淑矣”“无我恶兮,不寁故也……无我丑兮,不寁好也”。但莫言笔下的“弃妇”不再是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柔弱女子,她们有自己的心机和策略,有自己的理想和担当,她们的行为甚至已经表露出懵懂的女性意识。
莫言对母亲形象的塑造渗透着一定的女性意识。“其实是一种女性主义意识,也就是女性意识到男性在现实的社会体系和语言体系中对她们的压迫,或歧视和排挤,对接受这种安排产生怀疑和幻灭的感觉,对规定的性别角色有抛弃和叛逆的念头”[10],然而莫言笔下的“她们”的叛逆总被放置在男女之间的情感争夺,女性感情受伤,她要教训甚至惩罚男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不惜自虐,这种争风吃醋式的战争往往随着男性的“归来”戛然而止。这是一个怪圈,如果将之说成是女性宿命的悲哀,不免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淖,说成是两性关系的悲哀,又有武断之嫌。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言的作品和女性小说还是有实质性的不同,虽然女性小说往往不能达至两性和谐的完美状态,但其视角是女性主义的,以强调女性意识为旨归,不论描写女性的身体还是心理,这是她们对抗这个让她们伤痕累累的男权社会的利器,恰恰在这一点上,莫言流露出了作为男性的“窥视”姿态,即使面对母亲形象。可以肯定的是,莫言对作品中的“母亲”无意识表现出的懵懂的女性意识是同情的、理解的,他直言《红高粱家族》中的戴凤莲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3](P12),这一方面源于他内心对母亲真挚的感情,同时也表露了他对男权社会的反思和某些不认同,比如他以戏谑的语言调侃“我爷爷”余占鳌的恋爱历史,得出“爱情的过程是把鲜血变成柏油色大便的过程,爱情的表现是两个血肉模糊的人躺在一起,爱情的结局是两根圆睁着灰白眼睛的冰棍”[3](P262)的结论,有指责余自食其果的意味在其中。
女性经由女儿、妻子的角色,过渡至母亲,莫言笔下的绝大多数母亲都循着这条路径,不管在实现母亲身份的过程中,经历多少曲折,有多少难言之隐。但《蛙》中的“姑姑”是个例外。她是莫言作品中为数不多的被打上政治意识形态烙印的女性,当然,这是那个时代存在的必然,恰恰这一点,让她偏离了作为世俗意义上的女性的正常轨道。作品中有很多语言描述“姑姑”,她“是个阶级观念很强的人,但她将婴儿从产道中拖出来那一刻会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7](P19),她写下血书“我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7](P51),“党让姑姑爬刀山,姑姑就去爬刀山;党让姑姑去跳火海,姑姑就去跳火海”[7](P51),甚至当她看到传单时的自杀举动,也并非是因为王小倜感情上的背叛,而是王小倜给她政治上抹了黑。王小倜正是因为拒斥和“姑姑”步入“同志式”的婚姻,渴望恋爱和浪漫,才最终实施政治的叛逃。这是发人深省的,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时代里,文艺的泛政治化,模塑出女性样板,“英姿飒爽”的英雄气概,男性化的行为举止,坚定的革命意志,女性失去了传统的审美意义,温柔多情、敏感细腻之类的阴柔之美被剔除,她无性、无情、无爱、无欲。“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11]。从这个意义上说,“姑姑”的悲剧正是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是步入男性化社会的革命功利主义的典型,莫言此处的批判之意不言自明。
注释:
① 参见石颖的《莫言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嬗变》和罗慧林的《当代小说的细节肥大症反思——以莫言的小说创作为例》。
② 以女性视角来表现女性世界的女性作家作品,创作客体表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参见吕晓英的《难觅和谐——当下女性小说两性关系描写的缺憾》,《南方文坛》,2004年第5期。
[1]莫言.丰乳肥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2]莫言.与大师约会[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3]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4]莫言.檀香刑[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5]莫言.白狗秋千架[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6]莫言.四十一炮[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7]莫言.蛙[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8]莫言.丰乳肥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9]石颖.莫言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嬗变[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174.
[10]周乐诗.笔尖的舞蹈——女性文学和女性批评策略[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60.
[11][德]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309.
The Image of Mother in Mo Yan’s Novels
ZHAO Si-qi
(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China)
Grown up in the rural area,Mo Yan has created a large number of works,from which come various fascinating female characters,especially the mothers.From a male writer’s perspective,Mo Yan examines those mothers,tough existence and their psychological conditions.In this way,Mo Yan not only expresses his complex feelings towards his mother,but questions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mother;body;female consciousness;ideology
I206.7
A
1008-6838(2015)04-0080-05
2015-05-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项目编号:13&ZD122)
赵思奇(1982—),女,河南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