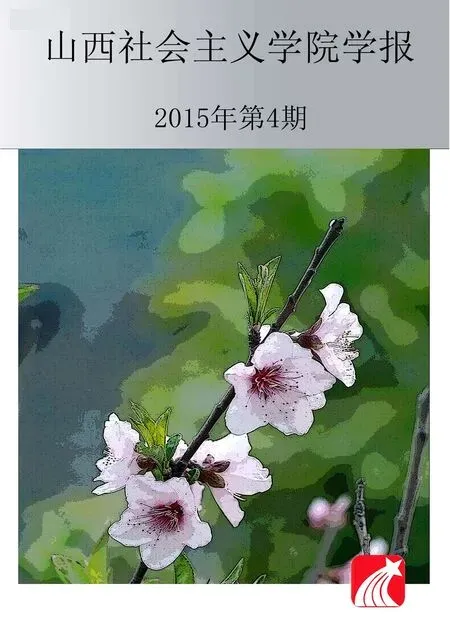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路径
2015-04-09崔华前
崔华前
(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新视阈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路径
崔华前
(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与根基,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批判继承、推陈出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古为今用;批判继承;推陈出新
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体现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肥沃土壤和丰厚滋养。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要求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充分发挥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功能。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精去糟、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要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育与形成的传统美德,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取精去糟、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可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批判继承、推陈出新。
一、坚持古为今用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依赖性,同时社会意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社会意识的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意识在内容上主要是反映现实的社会存在状况,同时也保留着历史上形成的反映过去社会存在状况的某些意识材料;在形式上不断增添和主要采取新的具体方式,同时也继承了以往既有的某些方式、方法和手段。正是这种历史继承性,才使得社会意识的发展呈现出前后相随、持续不断的状态,社会意识有其可以追溯的历史线索,才使得一些先进思想意识与优秀文化成果能够不断传承积累,形成穿越时空的超越性价值,具有强大生命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由古代贤哲所提出的,是传统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的反映,服务于传统社会的发展需求,同时又保留传承着许多先进的、合理的、进步的文化内容与形式;是历史,属于过去,作用于过去,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对于维护中国传统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推动中华民族的发展与进步曾起过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同时又是现实,内存于现实之中,是历史在现实中的沉积,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土壤,经过世代传承、不断积累、发扬光大,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精神风貌和精神财富,成为全人类所共有和共享的文化珍品,具有跨越时空的价值,构成一种强大的现实力量作用于当前乃至未来。例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夙夜在公”(《诗经·召南·采蘩》)、“天下为公”(《礼记·礼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国耳(而)忘家,公耳(而)忘私”(《治安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后出师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的无私奉献精神,“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病起书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辨法通论·论幼学》)的爱国情操,“一而不傥”(《庄子·马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权利不能倾,群众不能移,天下不能荡”(《荀子·劝学》)、“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礼记·儒行》)、“男儿自有守,可杀不可苟”(《古意》)、“松柏死不变,千年色青青”(《答郭郎中》)的人格独立精神,“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舍身而取义”(《孟子·告子上》)、“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乌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石灰吟》)的英勇献身精神等,在历史上对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产生过十分积极的影响,即使在今天,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极其珍贵的内在价值,绝不能只满足于把它们捧在手里,细细把玩、品味与欣赏,必须把它应用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伟大实践中。马克思曾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指出:“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这里,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充分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另一方面又明确要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坚持古为今用,“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决不仅是为了“解释世界”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改变世界”、实现“古为今用”。要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以客观审视,从现实的角度紧盯其现实价值,花大力气总结、提炼、发掘包含于其中具有当代价值的东西,找到其现实价值,有针对性地用它来涵养、滋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坚持批判继承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孙中山也曾指出:“一般醉心于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毛泽东也强调:“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江泽民也曾强调:“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地发扬光大。”这些论述,都旨在强调对于历史上的思想文化遗产应坚持批判继承。
中华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曾产生过巨大的积极影响,也曾发生过不容忽视的负面作用,是精华与糟粕的复合体。如中国传统“孝”道,倡导尊老、养老、爱老、助老、护老,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强化了社会生活中子女对父母应尽的责任,体现了中华民族“孝敬父母”的传统美德,有利于维护传统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历史进步作用。但中国传统“孝”道是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及男性家长制有着直接联系的,其中也含有如“移孝为忠”、“父为子纲”、“子为父隐”等内容。又如,“仁义礼智信”这“五常”,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与核心价值观,对于锤炼中华民族性格、培育中华民族精神、规范中华人际关系、确定中华文化的发展路向,都曾起过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它是建立在以小农经济为主要形式的封建制生产方式、以皇权政治为主要特点的封建制政治关系、以地主阶级压迫农民阶级为阶级实质的封建制阶级关系基础之上的,具有其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最为典型的是“五常”中的“礼”,它兼具道德与法律的双重功能,既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规定了传统社会的礼仪、礼节,为中华民族赢得了“礼仪之邦”的美名,又强调“辨尊卑,别等级,使上不逼下,下不僭上”、“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规定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权与广大劳动人民的单方面义务,肯定了男尊女卑与亲疏有别,具有扼杀人的自由和独立性的一面。
对于精华与糟粕并存的传统文化,应批判其糟粕,继承其精华;舍弃其消极成分,吸收其积极成分;否定其不良部分,肯定其优秀部分;既不能全盘肯定、过分赞美、颂古非今,又不能全盘否定、完全抛弃。“一方面,对其丰富深刻思想中的宝贵遗产要注意继承和借鉴。对其谬误和偏见,在批判其思想内容时,也不要忽略借鉴它所提供的理论思维中的经验教训。坚决摒弃对待人类文明思想成果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对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们都要积极继承和发扬。另一方面,要看到以往社会历史理论中由于受社会历史发展程度、阶级偏见和思维认识的限制,存在着根本缺陷。这就是:它们只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探究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决定一切社会关系,因而也是决定人们思想动机的根源;只看到个人的历史作用,没有看到人民群众的作用,由此决定它们不可能科学地揭示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即使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由于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也必须结合时代精神和现实需求,对其批判继承、加工改造,才能更好地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坚持推陈出新
只有坚持“推陈出新”,不断“吐故纳新”,才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富有特色的民族形式不断向前发展,充分发挥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功能。
一要找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合点。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现实可能性,二者具有“结合点”。所谓“结合点”,指的是被结合的双方具有相融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借鉴、吸收、融合了人类历史上各种价值观的合理、进步、积极的因素,特别是传承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精髓与精华而形成的一种迄今为止最科学、最先进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树必须深深地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选择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为广大老百姓所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概念、范畴来加以表述,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价值观话语体系,才能生动形象、亲切可人、“接地气”,易为广大老百姓所“内化”与“外化”,才能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重要源泉,才能很好地实现自身的现代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为自身在新的时代寻找到新的出路、焕发出新的光彩。这种相互融通、相互促进的关系决定了二者之间必然会有很多结合点。例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管子·霸言》)、“民贵君轻”(《孟子·尽心下》)、“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民主”、“和谐”之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喻牛辞相”(《庄子·秋水》)、“不为物役”(《庄子·逍遥游》)、“物无贵贱”(《庄子·秋水》)、“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无偏无颇”“无偏无党”“无反无侧”(《尚书·洪范》)、“公义胜私欲”(《荀子·修身》)、“去私心行公义”(《韩非子·饰邪》)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公正”之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敬事而信”(《论语·学而》)、“敬业乐群”(《礼记·学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己亥杂诗》)、“养心莫善于诚”(《荀子·不苟》)、“诚之为贵”(《礼记·中庸》)、“意诚而后心正”(《礼记·大学》)、“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后汉书·王荆传》)、“讲信修睦”(《礼记·礼运》)、“言而有信”(《论语·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以信接人,天下信之”(《物理论》)、“兼相爱”(《墨子·兼爱上》)、“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之间,均存在着相互契合之处。
二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换。所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不是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旧瓶子”贴上“新标签”,而是站在时代高度,结合时代发展需求,深入挖掘和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精髓与超时空价值,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换。这是实现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功能的必要环节,绝不可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如“实事求是”一语最早见于班固的《汉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人颜师古注释该语曰:“务得实事,每求真是也。”从此注释可知,古人对“实事求是”的理解,已含有求真务实的朴素唯物论合理因素。毛泽东同志看到了其中的合理因素,站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对此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新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通过对中国古老朴素唯物论命题的马克思主义改造,生动形象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堪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现代转换的典范。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征引孔孟所言,阐述共产党员加强道德修养的必要性。“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封建思想家在这里所说的是他自己修养的过程,他并不承认自己是天生的‘圣人’。另一个封建思想家孟子也说过,在历史上担当‘大任’起过作用的人物,都经过一个艰苦的锻炼过程,这就是‘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共产党员是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更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修养。”刘少奇对先秦儒家优秀文化成果的现代转换,使其一下子放射出新的时代光彩,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与修身学说。
三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李长春同志曾经指出:“如何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通融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价值观话语体系,就必须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可用“仁者爱人”来诠释社会主义友爱精神,用“和而不同”、“礼之用,和为贵”来诠释社会主义和谐理念,用“讲信修睦”、“言而有信”来诠释社会主义诚信准则,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来诠释社会主义爱国情操,等等。这种诠释,既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又可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平易近人、栩栩如生、彰显其特色之维;既可以增强价值观宣传的主动性,又可以增强价值观宣传的实效性。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5]刘德华主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著作导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王怡敏)
D616
A
1008-9012(2015)04-0061-05
2015-11-14
本文为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非主流社会思潮对大学生主流价值观认同的影响及对策”(项目批准号:14JDSZK078)、浙江省教育厅科研资助项目“非主流社会思潮对大学生主流价值观认同的影响及对策”(项目编号:Y201432094)的阶段性成果,2015年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多党合作与“四个全面”专项课题成果(项目编号:zdzx1533)。
崔华前(1969- ),安徽合肥人,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思想政治教育教研部主任,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高级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