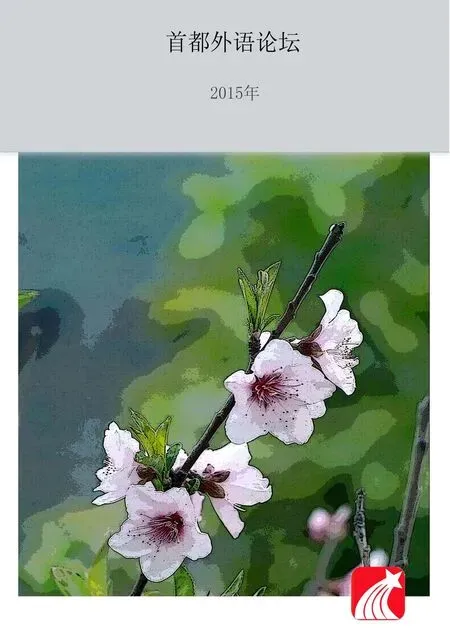抗争与归宿
——石黑一雄小说《去日留痕》的女性主义解读
2015-04-08费云枫
费云枫
抗争与归宿
——石黑一雄小说《去日留痕》的女性主义解读
费云枫
石黑一雄小说《去日留痕》通过回忆的形式,讲述了在即将没落的英帝国父权制社会里一个男管家将自己的人生奉献给了侍奉雇主达灵顿勋爵的故事。通过斯蒂文斯和肯顿小姐这两个悲剧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塑造,小说向我们阐释了父权统治对个体自我的压制以及带给两性关系和女性生存状况的伤害,并通过肯顿小姐自我意识的觉醒、与父权压迫的抗争以及最终的人生选择,揭示了父权意识的顽固以及女性化弱势群体追求自由独立的艰难。
《去日留痕》父权制女性自我意识
引 言
石黑一雄是当今国际文坛令人瞩目的日裔英国作家,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去日留痕》(1989)更是里程碑之作,获当年英国文学最高奖项“布克奖”。《去日留痕》通过回忆的形式,向我们展开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达灵顿府为缩影、即将没落的维多利亚父权制社会价值体系下的英帝国社会画卷,讲述了在这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一个英国男管家将自己的人生奉献给了侍奉达灵顿府主人达灵顿勋爵的故事。小说自问世以来,获得广泛关注,众多研究者从叙事学、历史语境或伦理学等各种不同角度和理论对它进行了阐释,却一直少有人涉及女性主义视角的解读。①Parkes,Adam.Kazuo Ishiguro's The Remains of the Day.New York: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Inc.2001.Childs,Peter.Contemporary Novelists:British Fiction since 1970.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2005.Beedham,Matthew.The Novels of Kazuo Ishiguro. 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2010.Sim,Wai-chew.Globalization and Dislocation in the Novels of Kazuo Ishiguro.New York:The Edwin Mellen Press.2006.Sim,Wai-chew.Kazuo Ishiguro.Oxon:Routledge.2010.Groes,Sebastian.&Lewis,Barry.Kazuo Ishiguro:New Critical visions of the Novels.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2011.而正如米勒特在《性的政治》中所言,文学是对父权的集体意识的记录②Guerin,Wilfred,L.&Labor,Earle,etc.A handbook of Crit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p.199.,在《去日留痕》这部作品里也深含着女性主义意味:在以达灵顿府为象征的父权社会体制下,被浪费生命的不仅仅是男管家斯蒂文斯,还有斯蒂文斯的工作搭档和爱人、女管家肯顿小姐。作者通过对斯蒂文斯和肯顿小姐这两个主要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塑造,向我们阐释了父权统治对个体自我的压制以及带给两性关系和女性生存状况的伤害,并通过肯顿小姐自我意识的觉醒、与父权压迫的抗争以及最终的人生选择,揭示了父权意识的顽固以及女性化弱势群体追求自由独立的艰难。
一 达灵顿府:父权制的象征
西方女性主义者认为,父权力量在历史上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无所不在。根据生态女性主义者伊内斯特拉·金 (Ynestra King)的观点,西方文化的主要权力结构是一种统治和被统治的等级体系,这种等级体系决定了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结构。而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是压迫性等级关系的基本范式:统治一方被看作是男性的,而服从的一方被看作女性。女性化是文化、政治造成的,女性化的过程是弱势个体学会服从的过程。①刘岩、马建军:《并不柔弱的话语——女性主义视角下的20世纪英语文学》,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1页。在父权体制下,整个社会由男性支配,从家庭到社会和国家都是由男性占主导地位。这种二元世界观根植于《去日留痕》中以达灵顿府为缩影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即将没落的英帝国社会生活之中。达灵顿府是一座真正“宏伟的”(grand)英式贵族宅第 (6,124),②Ishiguro,Kazuo.The Remains of the Day.New York:Vintage Books,Division of Random House,Inc.1993.p.6,p.124.建于17世纪,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宏大”(magnificence)的建筑风格和建筑内技艺精湛的石雕拱形门令前来参观的美国人威克菲尔德太太难以置信 (124);而雄伟壮观且承载着悠久历史传统的达灵顿府矗立在柔软平坦的、修剪整齐的花园草地之中,恰恰象征着强势的男性力量对弱势的女性力量的统治。达灵顿府的主人达灵顿勋爵属于掌控英国乃至国际政治外交风云的少数贵族精英分子,也是整座府邸的家长,是斯蒂文斯精神和社会意义上的“父亲”。小说中一再反复出现教堂和高耸的教堂尖顶的形象,也具有深刻的隐喻意义,象征着“西方二元对立理论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 (phallogocentric)的父权话语至高无上的支配权”。③刘岩、马建军:《并不柔弱的话语——女性主义视角下的20世纪英语文学》,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9页。斯蒂文斯在小山丘上远眺英格兰的乡村景色时,映入眼帘的是绵延起伏的乡村田园风光,还有矗立的教堂、高耸的教堂尖顶以及田野里四处点缀着的绵羊,斯蒂文斯将这种风格定义为“伟大”,并且指出“伟大性”源于“自我克制”的品德 (self-restraint)(28),无不喻示了父权话语无所不在的统治,也暗示了男管家斯蒂文斯和女管家肯顿小姐的命运被笼罩在严密坚固的父权秩序的压迫之下。
父权意识统治的社会里,男性力量起决定作用,女性的存在不是被动的,就是可有可无的。达灵顿府曾多次筹划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密谈,在英国政治生活中承担重要角色;府内仆人成群,先后有两位男主人,却极不相称地从未出现过女主人的身影。这意味着在达灵顿府所象征的父权制家庭和社会生活里,即使是贵族身份的女子也是不被重视的,她们的声音也可以被抹去。这种状况在小说中并不是孤立的:斯蒂文斯与同是管家身份的父亲一脉相承,也提起过一个哥哥,却从未提起过自己的母亲——老斯蒂文斯的妻子;斯蒂文斯在途中曾求助于一幢维多利亚式大房子,这幢高大传统的建筑物里只有主仆两个男人生活,也是一个女性缺失的男性世界。
父权社会里,社会生活中的一切追求都属于男人,女性身份被降低至生育职能,其主要功能是传宗接代,完成父权体系的延续。这一点在小说中也得到充分体现。在达灵顿府最为重要的会议期间,斯蒂文斯被达灵顿勋爵委以重托,向即将成婚的小卡迪纳尔先生传授“生命的基本知识”(the facts of life)(82),斯蒂文斯以交配期的白鹅和花园里万象更新、禽畜繁衍的自然现象向小拉迪纳尔先生暗示,婚姻之实无非就是生儿育女,繁衍后代。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认为,在父权体制下,女性往往被分派人类再生产 (生育)以及和自然直接相关的工作,女性被认为是较接近自然,而男性自认为是较接近文化的。①刘岩、马建军:《并不柔弱的话语——女性主义视角下的20世纪英语文学》,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6页。小说通过斯蒂文斯的意识行为,生动地体现了父权意识形态认为女性和自然同属于低等的、被统治一方的价值观念。但是新一代的小卡迪纳尔先生却始终无法体会到斯蒂文斯的用意,枉费了父亲老卡迪纳尔先生的良苦用心。这种对女性的刻板印象 (stereotype)并非有权有势的贵族家族男性所特有。当斯蒂文斯向随主人来访的男管家格拉姆透露自己对肯顿小姐休息日外出的疑惑时,格拉姆脱口而出,“我一直在想还会等多久……你的肯顿小姐,我相信她现在有,呃,34岁?35岁?已经错过了生育最好年龄,不过还不算太晚。”(170)从格拉姆斯口中飞出的这句话,直白地揭示出男权文化的统治下,生育功能是评价女性的首要标准。这种价值评价不仅为男性掌握,而且也已经被内化在大多数普通女性的意识里。小说中有一个小插曲:斯蒂文斯在一条山路上遭到一只母鸡挡住去路,停下车来。母鸡的女主人闻声而出,对斯蒂文斯一再道谢,其主要理由是这只母鸡下的蛋个儿特别大。无名的村妇对这只名叫“奈丽”的母鸡赞不绝口,宠爱有加,在作者笔下这只下蛋能手母鸡的形象里,重叠了当时社会普通农妇对男性文化为她们规定的母亲身份的默认。
在小说所呈现的这个男性社会里,对女性性别的歧视无所不在,体现在家庭观念、语言以及政治生活等各个社会方面。当斯蒂文斯询问来自美国的新主人法拉第先生如何安排来访客人的夫人时,性格比较开放的法拉第先生随即开始了调侃,“你何不领她去附近农场的马厩消磨时间呢?”(15),嘲笑的语气里流露出对女人的不屑,也较隐蔽地将男管家斯蒂文斯纳入了“具较低价值”的女性群体。斯蒂文斯由于自己对管家身份的错误理解,已经在父权体系中丧失了主体性,却又和其他男性一样,对弱势群体的女性抱有偏见。当初来乍到的肯顿小姐对地位低于自己的老斯蒂文斯直呼其名时,斯蒂文斯尖锐地指责肯顿小姐“像你这种地位的人怎能直接叫我父亲的名字”(53),女性在男性面前显示出优势和权威是斯蒂文斯绝不能容忍的事情;斯蒂文斯对其他女仆的态度也很恶劣,哪怕是那位看护在父亲临终病床前的厨娘,斯蒂文斯也因她围裙上的油味儿对她产生了难以克制的厌恶感。即使对于社会地位高于自己的贵族女性,斯蒂文斯也很吝惜自己的尊重。在达灵顿府的重要会议期间,斯蒂文斯对战败国代表德国女伯爵携带的庞杂行李很不以为然,对女伯爵的发言也不屑倾听,无故离开了会议室,这与他对达灵顿勋爵和老卡蒂纳尔先生发言的用心体会和感动落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达灵顿勋爵的那些政要伙伴们更是把自己看作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精英分子,对女性嗤之以鼻。斯宾塞先生在达灵顿勋爵的默许下,考问斯蒂文斯对时局政治的看法,以此证明斯蒂文斯所属的阶层是没有资格参加国家管理的,此举嚣张地贬低了斯蒂文斯的身份和价值,令斯蒂文斯从内心深处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斯宾塞先生最后还自以为幽默地将国会的辩论比作是“就像让妈妈联合委员会去发动一场战争那样”(196),嘲笑女性的能力,在他的极具强权意味的男性话语里,充斥着对女性身份和价值的贬抑,也将斯蒂文斯的性别进行了女性化,因为“女性化就是弱势个体学会服从的过程”。①刘岩、马建军:《并不柔弱的话语——女性主义视角下的20世纪英语文学》,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1页,第125页。被女性化了的斯蒂文斯盲目追随达灵顿勋爵的“男性理想”,压抑了自己的情感,既没有在父亲临终前尽孝,也克制了自己对肯顿小姐的爱意,最终也和父亲以及弟弟一样,成为“伟大的”父权制度的牺牲品。
二 肯顿小姐:女性主义的觉醒和抗争
在二元对立的父权社会里,权力集中到男性统治方身上,作为被统治方的女性必然丧失了主体性,不可能拥有独立的身份。正如老斯蒂文斯在草地上徒劳地寻觅“丢失了的珍宝”那样 (50),斯蒂文斯父子丧失了的“自我”永远也找不回来了。父权体制将女人定义为“非男”,认为“高尚、完美的女性应具备的特征是天真、纯洁、顺从,是家中的天使”。只有纯洁顺从、乐于牺牲奉献自己、缺乏主体性的女性才符合男性的“天使”标准,而不肯屈服于父权、有能力学识、有独立自主意识的女性则被贴上“妖妇”的标签。作者笔下几位女性形象的命运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斯蒂文斯在旅行途中遇到母鸡的女主人是“天使”的典型代表。斯蒂文斯在和这位农妇交谈时,看到远处赫赫有名的萨布斯布雷大教堂的尖顶,向她打听,村妇却回答自己从未去看过教堂,也没有兴趣去看。农妇不关心教堂,也更不可能对教堂的象征意义提出任何质疑和挑战。像农妇这样的普通女性群体从不去思考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她们默默无闻,甚至都不需要有自己的名字,她们的生活轨迹与社会几乎没有交集,终日囿于家庭事务之中,顺从地扮演着父权制度规定下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她们是男性眼中的“天使”。
作者在小说中塑造的另一个典型女性形象是女仆丽莎。丽莎是一个没有工作经验却很聪明的年轻女孩,也许是肯顿小姐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执意聘用了她。在肯顿小姐的精心调教下,丽莎很快显出了令人吃惊的才干。不料丽莎却很快爱上了一个男仆,和他私奔了。肯顿小姐深受打击,深深痛惜丽莎不明智地毁掉了“很有希望的前途”(158)。丽莎在留下的信中,一再强调自己和男仆的爱情是真挚的,她为自己辩解道,“在这世界上没有比和心爱的人一起生活更重要的事了”(157),却丝毫未提及肯顿小姐在自己工作能力上的用心栽培。丽莎是一个叛逆者,她挑战了父权制度规约下的“妇道”,勇敢地遵从了自己内心的呼唤,做出了属于自己的人生选择。她用自己的私奔行为向世人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妖妇”形象,但是她那赤裸裸的爱情宣言也必定唤醒了潜藏在肯顿小姐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也许就是从那一刻起,肯顿小姐开始对自己的事业追求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而女管家肯顿小姐则是整部小说的灵魂人物。她像那一束刚刚从清晨花园里采摘的鲜花,将给斯蒂文斯和达灵顿府上死气沉沉的生活带来亮丽的色彩和怡人的芬芳,但却可悲地被斯蒂文斯无情地拒之于门外。肯顿小姐的遭遇引人深思。细读斯蒂文斯回忆的絮片,可以发现其中贯穿着两条线索,明暗交错,推动着情节发展,它们的交集点形成了斯蒂文斯反复强调的“一系列转折点”(turning points):其中一条线索是斯蒂文斯追随达灵顿勋爵一步步走向“伟大”事业的“巅峰”,而另一条线索则是斯蒂文斯和肯顿小姐的情爱关系渐行渐远,走向幻灭。在达灵顿府首相和德国特使进行密谈的晚上,小说迎来了整个故事发展的高潮:肯顿小姐终于痛下决心决定放弃对斯蒂文斯的爱,接受本先生的求婚;而斯蒂文斯则违心地弃黯然神伤的肯顿小姐于不顾,为达林顿勋爵安排的密谈充当忠实的“看门狗”。两人的世界从此被一道门永远地隔开,肯顿小姐在门内暗自哭泣和斯蒂文斯终于有了“获胜的感觉”(a sense of triumph)(227,228)形成强烈对比,宣告斯蒂文斯和肯顿小姐的爱情最终可悲地沦为斯蒂文斯追求父权社会虚妄理想的牺牲品。
肯顿小姐和老斯蒂文斯差不多同时来到达灵顿府。肯顿小姐很快在工作中显出了卓越的才能,同时她也是一个热爱生活、有高雅趣味的女人,当她看到斯蒂文斯的房间阴暗单调、缺乏生气时,多次想送花改变房间里的氛围。但是这一切都遭到了斯蒂文斯的排斥。斯蒂文斯不但拒绝了肯顿小姐的好意,而且无端挑剔肯顿小姐的工作表现。在父权意识的灌输下,斯蒂文斯对女性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偏见。斯蒂文斯指责地位高于自己父亲的肯顿小姐“像你这样地位的人怎么能直接叫我父亲的名字呢!”(54)因为在父权制社会里,“主动”和“权威”都是属于男性专属的特征,如果女性显示出这些特征,会给人带来恐惧和不快的感觉①刘岩、马建军:《并不柔弱的话语——女性主义视角下的20世纪英语文学》,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5页。。像肯顿小姐这样有着优秀履历、工作表现出色的女管家,都受到斯蒂文斯的再三挑剔和刁难,意味着在父权体制中女性的能力是很难得到公正的评价和对待的。但是肯顿小姐是一个自信的、思想独立的女性,她与斯蒂文斯的男权思想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并通过自己优异的工作表现向斯蒂文斯证明女性的能力。肯顿小姐也是一个头脑清醒、有独到见识的女性。当肯顿小姐向斯蒂文斯指出他的父亲已经衰老、不能胜任现有职责这个事实时,斯蒂文斯却仍然大言不惭地夸赞父亲,维护父亲的形象和身份,反而指责肯顿小姐愚蠢之极。两人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当父亲病危时,斯蒂文斯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伟大”的管家,弃亲情于不顾,肯顿小姐却不计前嫌,主动提出帮助照料,从中也可以看到肯顿小姐难能可贵的善良品质。在达灵顿府解雇犹太女佣的事件中,肯顿小姐更是展示出独具一格的人格魅力。当斯蒂文斯遵照达灵顿勋爵的指令宣布解雇两个无辜的犹太女佣时,肯顿小姐反应非常激烈,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做是错的”(149),并且威胁斯蒂文斯自己也要辞职;无奈肯顿小姐的声音太微小了,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女性个体,又怎能有力量改变父权统治者的决定呢。肯顿小姐没有辞职,为此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一再受到斯蒂文斯并无恶意的奚落。一年后,达灵顿勋爵为解雇女佣的行为感到后悔,当斯蒂文斯和肯顿小姐谈起此事又提及她的辞职威胁时,此时的肯顿小姐已经沉默了很多,神情中也增添了几丝疲惫,她向斯蒂文斯袒露了自己的心声:“当我想到真要离开达灵顿府另谋一份职业时,我感到很害怕,我仿佛看到自己在那儿,没有人了解我,也没有人关心我。而那就是我要为我的崇高原则付出的代价。我为自己羞愧”(153)。从肯顿小姐的心声里,我们可以真切地体会到职业女性在男性社会里的处境是多么尴尬和艰辛。在解雇犹太女佣事件中,斯蒂文斯充当了父权统治者达灵顿勋爵的忠实傀儡,完全失去了自己的道德判断,而肯顿小姐却表现出强烈的是非观念,坚持自己正义的道德立场,发出了斯蒂文斯被抑制住了的声音。当斯蒂文斯承认自己也为这件事感到难过时,肯顿小姐的声音立刻就变了,变成一种“全新的声音”(an entirely new voice),肯顿小姐问斯蒂文斯,“为什么?你为什么总是在装呢?”(154)肯顿小姐也许应该明白,斯蒂文斯的心灵早已被父权体制奴役,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在父权制度压倒一切的压迫和束缚下,肯顿小姐那微弱的声音也终将被淹没,女性自我势单力薄的挣扎终将是徒劳的,小说也迎来了它的苦涩结局:肯顿小姐不得不在社会现实面前退让,无奈地放弃了对斯蒂文斯的爱,放弃了自己的事业追求,选择嫁给了自己不爱的本先生;斯蒂文斯的人生和与肯顿小姐的爱情都成为了即将没落的父权体制的陪葬品。
三十年后斯蒂文斯收到了肯顿小姐的来信。屡次从婚姻家庭中出走的肯顿小姐在信中表达了对和斯蒂文斯一起共事的日子的强烈怀念。当斯蒂文斯再次见到肯顿小姐时,本太太——昔日的肯顿小姐——依旧端庄优雅,扬头的姿态里依然带着一丝挑战的意味 (232),但是她的行动慢了下来,在本太太的身上,曾经闪烁的活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生活带给她的疲惫;斯蒂文斯甚至在本太太的表情里“看见了某种忧伤”(233)。短暂的相见、温馨的回忆之后,留给斯蒂文斯的是旧梦再次破灭后的无限惆怅和伤心。肯顿小姐告诉斯蒂文斯,在此次离家出走的日子里,她重又思考了自己的“正确位置”(the rightful place)(239)。肯顿小姐又一次为自己余下的人生做出了重大选择:她已经无力抗争命运的摆布,她的“正确”位置只能是回到家庭中,回到丈夫身边去,继续去履行父权社会里女性“应有的”职责,在剩下的生命里,她也只能以帮女儿抚育后代来填满生活的空虚。
斯蒂文斯的外出旅行结束了,他的回忆也结束了,他和肯顿小姐的故事也结束了。以第一人称叙述者身份出现的斯蒂文斯通过大量的内心独白,仍能以自己在父权统治下的软弱无能和为虎作伥的行为赢得了读者的同情。但是,作者在男管家斯蒂文斯的人生里巧妙地嵌进了一个女管家肯顿小姐的故事。细细比较作者对斯蒂文斯和肯顿小姐这两个人物的塑造,我们不难体会到作者的匠心所在。在父权体制对个体自我的强势压制下,有着崇高理想追求的斯蒂文斯被套上了时代的枷锁,沦为制度的奴隶;而弱小的肯顿小姐却从未失去自己独立的人格,在她的身上女性自我意识已经苏醒,她坚守着自己的道德底线,不屈从于父权统治,敢于大胆表露爱情、追求有意义的生活,却又有着审时度势、为自己选择人生道路的理性和魄力。肯顿小姐是作者在小说中安排的另一个斯蒂文斯,斯蒂文斯的理想自我,她代为斯蒂文斯发出了消失在内心深处的反抗之声。肯顿小姐的最终归宿也证实了在父权强权统治的社会里,弱势个体尤其是女性争取自由的道路还很漫长。但肯顿小姐是值得尊重的,在肯顿小姐身上,投射了作者对历史变迁中的个体所寄予的价值判断和道德立场。
结 语
时间走到了20世纪上半叶,伟大的“日不落帝国”即将迎来它生命中的日落时刻,维多利亚时代父权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也开始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斯蒂文斯和肯顿小姐也共同迎来了可以回首过往岁月的人生中的黄昏。在肯顿小姐的来信间接而有效的邀请下,斯蒂文斯离开了禁锢了他大半辈子人生的达灵顿府,踏上重寻旧梦之旅,才得以用外面世界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曾经的人生追求和情感历程。在旅途中穿插的回忆里,斯蒂文斯的灵魂一再受到拷问。肯顿小姐在信中发出疑问,“……不知怎样才能不虚度自己的余生……”,(49)这也是灵魂已经深深迷失在达灵顿府所代表的父权社会体制中的斯蒂文斯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通过斯蒂文斯和肯顿小姐的故事,作者向读者揭示了一个真相:个体想要挣脱父权体制的束缚并非易事,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如同那幢矗立在落日余晖中的古老而宏伟的达灵顿府邸那样,维多利亚父权制社会传统的价值体系对个体意识的控制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间轻易连根拔去。肯顿小姐再次向男性社会做出了退让,重新回到了婚姻和家庭之中,回归到男性社会为女性规定的妻子和母亲的社会角色中。然而,肯顿小姐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为了爱情和人格独立所作的挣扎却从斯蒂文斯的记忆中凸现出来,就像黄昏时从二楼穿过肯顿小姐房间的窗户投射到阴暗走廊里的橙色阳光,明亮而温暖,落在了斯蒂文斯被蒙蔽的心灵上。小说结尾,斯蒂文斯站在彩灯闪烁的桥墩上,面向大海,终于获得了痛彻心扉的醒悟。他将带着对“调侃”(banter)和主仆关系的新认识,重新回到达灵顿府的新主人法拉第先生的身边去。希望他在达灵顿府的余生也将添上一丝暖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