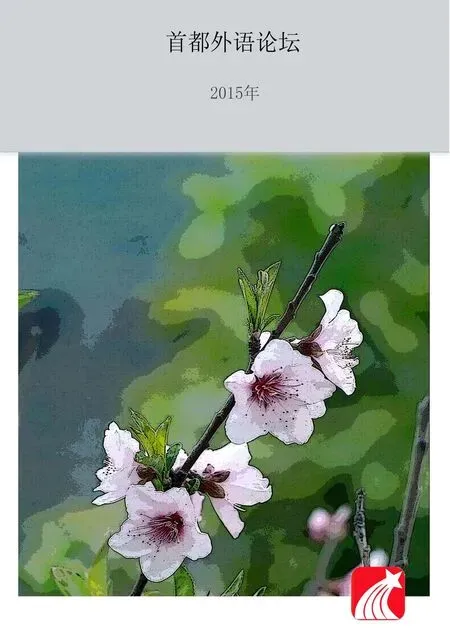《简·爱》与《呼啸山庄》在20世纪上半期中英两国的接受分析
2015-04-08朱瑞党陈卫红
朱瑞党 陈卫红
《简·爱》与《呼啸山庄》在20世纪上半期中英两国的接受分析
朱瑞党陈卫红
同为文学史上不多见的著名女性作家的经典作品,《简·爱》与《呼啸山庄》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和英国的接受情况却是大不相同的。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文艺界重视《简·爱》而轻视《呼啸山庄》的态度非常明显;而在同时期的英国,情势则完全相反,对《呼啸山庄》的评价均在《简·爱》之上。本文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对两部作品在同时期两国的不同接受倾向进行解读和探讨。
《简·爱》与《呼啸山庄》20世纪上半期中英两国接受接受美学
一 20世纪上半期《简·爱》与《呼啸山庄》在中国的接受
1917年林德育所写的《泰西女小说家论略》一文应是关于《简·爱》与《呼啸山庄》最早的介绍性文章。此后,谢六逸的《西洋小说发达史》对勃朗特姐妹的生平和创作进行了介绍性的描述。文中作者认为“姊妹皆富创作力,可谓奇特”,但“爱米尼 (Emily)的天才赶不上却洛特 (Charlotte)”。①谢六逸:《西洋小说发达史》,《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6号。其后,郑振铎又在《文学大纲:十九世纪的英国小说》一文中对两部小说做了更为详尽的介绍,其中还对《简·爱》的故事梗概进行了描述。文中这样评价道:“蔡洛特在佳人才子的普遍恋爱小说之处,另开了一条路。这条新鲜的路,立刻有许多的模仿者来走,但俱没有蔡洛特的琪恩·伊尔 (Jane Eyre)成功。”②郑振铎:《文学大纲:十九世纪的英国小说》,《小说月报》1926年第17卷第6号。对于艾米莉·勃朗特,郑振铎认为“爱美莱成就则不如蔡洛特。”③郑振铎:《文学大纲:十九世纪的英国小说》,《小说月报》1926年第17卷第6号。而对于《呼啸山庄》的介绍也仅限于“伊有一部Wuthering Heights”④郑振铎:《文学大纲:十九世纪的英国小说》,《小说月报》1926年第17卷第6号。,甚至连此书的中文译名也没有给出。中国文艺界重《简·爱》,轻视《呼啸山庄》的取向于此处可见一斑。1929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韩侍珩辑译的《西洋文学论集》一书,在本书的《十九世纪的英国小说》一文中,《简·爱》同样被当作一篇具有“极普遍人性的、是可以诉向大部分人类的”⑤韩侍珩:《西洋文学论集——十九世纪的英国小说》,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第129页。小说来加以介绍,《呼啸山庄》又受到了冷落和忽视。1935年12月,周其醺、李末农、周俊章在他们的《英国小说发展史》一书中专辟出一章来介绍了勃朗特姐妹以及她们的作品。文中对夏洛蒂的生平、创作动机以及《简·爱》一书的内容、人物形象都做了详尽的描述和点评。指出“夏绿黛的创作是英国写实主义的复兴”,著者这样写道“有一次夏绿黛告诉爱弥莉她不应采用小说中常因袭的女主角,并且说:‘我要写一个女主角给你看看,她和我一样矮小而貌不惊人,然而这个女主角和你所写的一样能引起读者的兴趣。’”⑥周其醺、李未农、周俊章:《英国小说发展史》,国立编译馆,1935年,第368页。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也被著者以一种具有“离经叛道”的反抗主义精神的形象加以描绘,介绍给了当时的中国读者。反观文中对《呼啸山庄》的介绍,则寥寥如下:“就是爱弥莉·布朗蒂在狭路冤家 (Wuthering Heights)里也务必使她的女主角娇美可爱,虽然没有这样赶于极端。”①周其醺、李未农、周俊章:《英国小说发展史》,第368页。此后,在金东雷所著的《英国文学史纲》中,也有关于《简·爱》的专门评述,“真爱尔 (Jane Eyre)是以爱和恨为基本描写的小说,很有莫萝悲剧的风味,极得社会的好誉,作者因之成了当时小说界上第一流人物。”②金东雷:《英国文学史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421页。金东雷还从中国古代文论中优秀作品多为“忧愁发愤之作”这一观点出发,认为《简·爱》也是小说作者本人在困苦、逆境中的“愁苦之言,发愤之作”。③金东雷:《英国文学史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420页。对于《呼啸山庄》,文中仅作了如下描述:“她的妹妹爱米离著有神怪小说和善林·哈慈 (Wuthering Heights)。”④金东雷:《英国文学史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420页。轻描淡写之下透露出一种对《呼啸山庄》明显的轻视。另外,《妇女杂志》在1937年刊登了仲华的《英国文学中的白朗脱氏姐妹》一文,对勃朗特姐妹作了全面地介绍。这里,《呼啸山庄》也是作为《简·爱》的陪衬而出现的。
二 《简·爱》与《呼啸山庄》在同时期西方的接受
与中国重《简·爱》、轻《呼啸山庄》的倾向相比,西方同时期在两部小说的接受上有着一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批评家对《简·爱》那种比较浅显的社会批判和思想内容失去了兴趣或者认为已经不再合乎口味;而对《呼啸山庄》那斯芬克斯谜一般的耐人寻味的深刻思想内涵和表现手法显示出了极为浓厚的兴致。
这一时期较早对勃朗特姐妹进行深入研究的首推英国著名女作家、文学评论家玛丽·奥古斯塔·沃德,她在与克莱门特·肖特合著出版的《勃朗特姐妹生平与作品》中认为:“《简·爱》纵然令人钦慕,却很难达到《呼啸山庄》那种兴之所至、挥洒自如和毫不费力的雄浑刚劲的水平。”①玛丽·沃德:《勃朗特姐妹生平与作品》,伦敦:哈波兄弟出版社,1900年,第244页。1925年7月,赫伯特·里德在《耶鲁评论》上发表了《夏洛蒂和艾米莉·勃朗特》一文,他认为《呼啸山庄》“达到了少有的古典悲剧的风格”。②斯坦利·埃德加·海曼:《批评的实践》,纽约:文泰奇图书公司,1956年,第76页。同年,英国女作家、文学评论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撰写了《〈简爱〉和〈呼啸山庄〉》一文。伍尔夫在肯定《简·爱》价值的同时,对《呼啸山庄》极尽赞美之辞,“《呼啸山庄》是一本比《简·爱》更难理解的书,因为艾米莉是一个比夏洛蒂更伟大的诗人。”③弗吉妮亚·伍尔夫:《普通读物》,伦敦:霍加斯出版社,1942年,第201页。作者认为在文学作品中再也没有一个比希斯克厉夫更活灵活现存在着的年轻人了,《呼啸山庄》中的两个凯瑟琳是英国小说中最可爱的女子。1934年,伦敦康斯塔勃公司出版了英国评论家戴维·塞西尔的评论文集《早期维多利亚小说家》,在这篇论文集里,作者洋洋洒洒数万字论述了《简·爱》和《呼啸山庄》。其中,对于《呼啸山庄》塞西尔可谓是不惜笔墨,采用多种手法进行称颂。塞西尔认为《简·爱》“这部小说情节发展所依据的主要事件,没有一件是可信的。”④戴维·塞西尔:《早期维多利亚小说家》,伦敦:康斯塔勃公司,1934年,第307页。除了作品形式上的错误,塞西尔还认为《简·爱》中有些段落是模糊不清、装腔作势和滑稽可笑的。至于小说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人物刻画上,塞西尔写道:“她只是从当时的平庸小说中抄袭一个粗制滥造的典型罢了。而她的缺乏技巧使她的抄袭比原样更加粗劣。”⑤戴维·塞西尔:《早期维多利亚小说家》,伦敦:康斯塔勃公司,1934年,第312页。当然,作者也从其他角度对《简·爱》有嘉许之词,“除了狄更斯和她的妹妹艾米莉之外,她的想象力是英国小说家中最强烈的”。⑥戴维·塞西尔:《早期维多利亚小说家》,伦敦:康斯塔勃公司,1934年,第317页。让我们将目光移向《呼啸山庄》上来,作者又是如何的一番评论呢?文章开篇伊始,塞西尔就这样写道:“《呼啸山庄》是唯一一部没有 (即使是部分的)被时间的尘土遮没了光辉的小说。惟有它,今天仍和写成之初一样使我们激动。”①戴维·塞西尔:《早期维多利亚小说家》,伦敦:康斯塔勃公司,1934年,第328页。这是何等充满着崇敬和爱慕之情的评价!他还将《呼啸山庄》与《哈姆莱特》和《神曲》并列,说“世界上没有一本小说有比它更为宏大的主题。”②戴维·塞西尔:《早期维多利亚小说家》,伦敦:康斯塔勃公司,1934年,第344页。关于《呼啸山庄》的形式,作者认为它是可以和其主题超群相比的,“它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小说许许多多的色彩各异的画幅当中一件完美无缺的精品,它庄严而与众不同地矗立着,像一个已经消灭了的氏族留下的唯一的纪念碑。”③戴维·塞西尔:《早期维多利亚小说家》,伦敦:康斯塔勃公司,1934年,第362页。这一时期,西方对于《呼啸山庄》的研究和评论可谓浩如烟海,对于《呼啸山庄》的各种解释更是如雨后春笋,反观对于《简·爱》的评介和解释,则明显少于《呼啸山庄》,并且几乎所有的评论均把《呼啸山庄》放在远远超越《简·爱》的位置。1948年,英国当代小说家萨默塞特·毛姆应美国《大西洋》杂志之请,向读者介绍世界文学十部最佳小说时,他选了英国的四部小说,其中之一就是《呼啸山庄》。
三、中西方20世纪上半期《简·爱》与《呼啸山庄》接受中不同倾向的探讨
接受美学认为:“一部作品的意义,主要是读者赋予的”,④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7页。“在读者的接受之前,作品除了其媒介的物质形态是既定的之外,其意义、价值等等都有待读者的读解才最终完成”⑤杜书瀛:《文艺美学原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70页。。让我们拿起“接受美学”的放大镜,透视《简·爱》与《呼啸山庄》在中英两国20世纪上半期不同接受倾向的成因。
从垂直接受 (历史维度)的角度来看,“作品跟时间——历史具有一种不可隔绝的人文关联。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环境的变化,读者也产生了变化,具有了新的人文品格、审美情趣,对过去的作品产生新的理解。”①杜书瀛:《文艺美学原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78页。与《简·爱》相比,《呼啸山庄》在英国的接受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走过了一条崎岖坎坷的道路。《简·爱》初一问世,就立刻引起了文学界的注意和重视,夏洛蒂也因之而一夜成名。而《呼啸山庄》在出版之后,评论界则反应冷淡,仅有的个别评论也是极为尖酸、刻薄的讽刺和挖苦。它被斥为“一部骇人听闻、荒谬绝伦、毫无意义的作品”,“一部恐怖的、令人作呕的小说”。②宋兆霖:《呼啸山庄》,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序言”,第1页。《呼啸山庄》在当时的悲惨命运,主要在于当时英国的历史文化环境,当时的英国正处于维多利亚时代,尽管华兹华斯已经在湖畔动情地吟唱“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拜伦也在怒吼“谁要获得解放,就必须自己动手”;宪章派诗人要把“浪漫主义的进步倾向引向批判现实主义”③石璞:《西方文论史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09页。;但小说却是当时最流行的文学主流形式。而在那个清教道德要求相当严格的时代,几乎所有的小说家都遵循“说教的美学”原则来进行创作,不敢越雷池半步,萨克雷就曾哀叹“再也不能像18世纪那样描写人了”。对于接受者来说,在其阅读任何一部作品之前,他的头脑中并非像一张白纸一样是一片空白,而是已经存在着一种先在理解或先在认知的状态,即接受美学里通常所说的期待视野。接受者的期待视野是基于个人审美经验和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的,但更重要的是,它也处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下的,要受到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时代思潮、政治、文学传统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的。夏洛蒂是典型的维多利亚作家,她对社会、家庭、爱情、责任的看法都是和这一时期紧紧相连的,这些看法也都在《简·爱》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而艾米莉的《呼啸山庄》却与同时代的小说明显不同,小说里所描写的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感情也是违反维多利亚时代道德标准的,它“破坏”了这种统治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这种另类叛逆的小说自然立刻招来口诛笔伐,难免导致被打入冷宫的遭遇。
20世纪,西方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生产力提高,科学技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同时战争和革命所造成的动荡也迫使人们对宇宙、对人生、对人的命运进行了更为积极地思考和探索。种种哲学思潮和批评方法便应运而生,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存在主义、意识流……,你方唱罢我登场,英国的接受者无疑在这一时代语境下深受影响,他们的期待视野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而当作品意味“超出、校正了读者期待视野的时候,读者往往会兴高采烈,认为它提高了自己的审美水平,……为自己建立了新的审美标准”。①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7页。这样,作品的美学价值也就显现了。《呼啸山庄》在维多利亚时代之所以受到冷落和批判,就是因为其虽然超越了当时读者期待视野,却违背了统治整个英国社会的道德标准,而同时又无力校正读者的期待视野,自然不能给读者带来审美的愉悦。随着读者期待视野的变化,英国这一时期的批评朝着更科学、更准确的方向进行。批评家们所努力追求的是一种更“客观的”、更“抽象的”文学批评,和哲学上的“认识论”或“本体论”联系在一起。随着社会文化语境和接受者期待视野的转变,“某个时代的典范之作可能会在后来的时代中变得湮没无闻,而长期得不到同时代读者承认的作品可能会在隔代读者那里大放异彩。”②杜书瀛:《文艺美学原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79页。《呼啸山庄》在经历了被长久的不公平对待之后,终于浮出冰面。 《呼啸山庄》的伟大之处很大程度上是在于艾米莉超越了时代的限囿,以精湛的文学技巧戏剧性地表现了后来弗洛伊德所说的人的本能冲动。它是一部超前的著作,它的精妙、匀称的构思,奇特的性格塑造手段,怪异的情节发展过程都是夏洛蒂的《简·爱》所远不能及的,而“作品本身的诸因素具有‘潜藏意义’,这些意义并非一时一刻能被人理解,人们要理解它,需要相当长时间。”③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8页。也唯其如此,《呼啸山庄》才难以为其同时代的人所理解。正如姚斯所说:“历史是一个不断被读者理解和认识的过程,由于各种原因,如政治、经济、文化风尚、审美需求,限制了一个时期人们的理解和认识,到另一个时期,人们克服了这种限制并进行了新的认识,发现了那些被历史埋没的优秀作品”,①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8页。随着20世纪英国读者在接受中期待视野的改变,《呼啸山庄》那深藏在其中的巨大价值才得以展现。这部“人间情爱最宏伟的诗”立即成为英国接受者的一部宠书。《简·爱》那平淡无奇的故事情节、庸俗的爱情故事、老套的说教、波澜不惊的批判价值随着读者期待视野的转移,也丧失了其昔日的地位。
从水平接受 (共时维面)的角度反观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救亡图存、抗战兴邦是整个时代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和奋斗目标,当时的我国的文学主流是“反帝反封”、“个性解放”、“革命主义”、“爱国主义”,肩负着厚重社会历史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要求有能直接对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起到鼓舞和启迪作用的艺术形式。瞿秋白曾提出:“我们绝不愿意空标一个……主义来提倡外国文学,只有中国社会所要求我们的文学才介绍——使我们中国社会里一般人都能感受都能懂的文学才介绍”。②谢天振、查明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9页。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时代语境之下,对一部外国文学作品的接受情况,主要就取决于它能否契合当时国内历史文化语境,能否有利于解决中国当时诸多的实际社会问题。我国这一时期对英国文学的译介和接受很广,其中小说是最为全面的文学类型,尽管二三十年代我国对英国文学的接受曾一度呈现出多元化选择的局面,但这一时期中国广大接受者基本的期待视野大体相同的。传统的文艺美学思想在中国读者心中根深蒂固,“温柔敦厚”、“哀而不伤”一直以来就是中国的艺术精神及审美理想,也即读者的期待视野;同时,这一时期,受西方文化思潮及国内现实的影响,中国读者的期待视野也在发生转变。《简·爱》描写了一个捍卫个性、追求自由与幸福的独特的女性形象,她完全靠个人奋斗,建立起了与他人平等的社会地位,并得到了自己的幸福,这正暗合了当时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所追求的目标;另外,小说中以批判现实的笔触所揭示的社会矛盾也是极具现实意义的。而《呼啸山庄》却是一部强调自我精神、对传统观念大胆反抗的小说,它是一部“激烈坦率”、“超越世俗”③杨静远:《勃朗特姐妹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329页。的小说,是一部充满了神秘与恐怖气氛的小说。小说中所反映的冲突也不是人类间善恶是非的冲突。在这部“小说里很难找到与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相关的痕迹。”①杨静远:《勃朗特姐妹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330页。《简·爱》与《呼啸山庄》都超出了我国读者的期待视野,但不同的是,在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简·爱》显然有助于读者校正自己的期待视野,其小说主题契合我国当时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民主、自由思想,我国读者能从《简·爱》中感受到新的体验 (男女平等、女性自强、自立,这正是当时国人所积极追寻、探索、渴望的理想),丰富了并拓展了自己期待视野。而《呼啸山庄》虽远远超越我国读者的期待视野,但我国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显然不允许读者且读者也不会单纯地从审美艺术的角度去接受它。沈雁冰就曾指出:“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果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是更注意些的目的……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艺术我们应是不承认的。”②谢天振、查明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8页。《呼啸山庄》强烈的爱与恨在当时的中国读者看来都是难以理解的,它本身结构的复杂性和超前性,它复杂的内涵也与都与读者的审美能力有着太大的差距,丝毫无助于校正读者的期待视野;这样一部既与读者期待视野冲突,又不注重伦理道德、不关注社会现实、毫无裨益于中国社会问题解决的“神怪小说”,自然很难引起当时中国读者的共鸣,受到轻视是理所当然的。由此看来,在建国前的中国出现重《简·爱》轻《呼啸山庄》这一倾向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