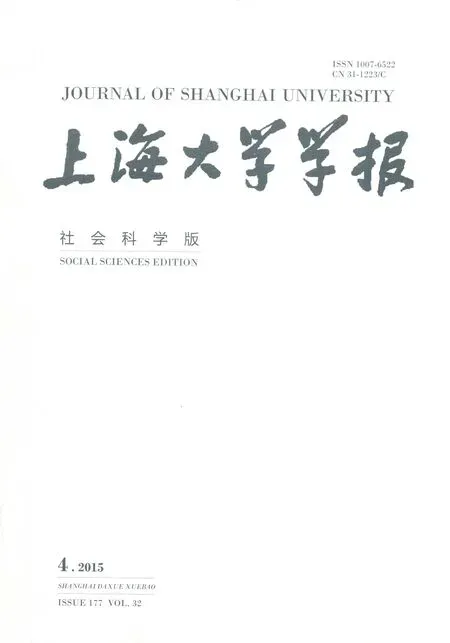靖康之难的成因是什么?
——从南渡时人的认识说起
2015-04-03冯志弘
冯 志 弘
(香港教育学院 文学及文化学系,香港)
靖康之难的成因是什么?
——从南渡时人的认识说起
冯 志 弘
(香港教育学院 文学及文化学系,香港)
宋室南渡,时人并未归咎于士大夫沉溺山水。他们认为,靖康之难的因由,“内忧”远大于“外患”,即朝廷腐败的“远因”远大于外族南进的“近因”,并且认为,北宋乱事“本于君子小人之混淆,君子常不胜”。这都有别于宋亡以后把靖康之祸归咎于天子沉溺娱乐、政策失误的论调。
靖康之难;宋室南渡;君子小人之辨
宣和元年(1119),蔡京之子蔡攸语宋徽宗曰:“所谓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几何,岂徒自劳苦!”徽宗“深纳之。”[1]500元代以后,徽宗的失德与朝政昏乱,往往被视为靖康之难的主因。《宋史》说:徽宗“奉身之欲,奢荡靡极,虽欲不亡得乎?”[2]3478王夫之《宋论》谓徽宗朝“有财而不知所施,有兵而不知所用……唯不知人而任之……无往而不亡矣。”[3]151近年来,学者较多从国家政策分析靖康之祸。臧嵘认为:北宋的致命伤在于“防内甚于防外,防民甚于防敌”;[4]23游彪指出:宋开国以来重文轻武、文人统兵、“异论相搅”等祖宗家法,是北宋灭亡的远因。[5]17、18、96-97
那么,经历靖康之难的南渡时人如何理解祸患的成因?①本文所说的“南渡时人”,指的是在靖康之难以前进入青少年时期,对于北宋局势有基本体验,并且曾经在南宋生活的宋人。其中有几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第一,若干高宗朝时人,如朱敦儒、李纲、赵鼎,一方面痛陈靖康之弊,否定“奢靡”,另一方面则追忆“宣和全盛年……歌舞赏清妍”[6]218《次韵季弟善权阻雪古风》之乐,反映了他们认为“奢靡”与“太平为娱”观念有所不同。第二,像淳熙年间《题临安邸》诗讽刺君臣耽乐山水的观点,固然影响深远,但查看《全宋文》所收录南渡初年文献材料,特别是政论文章,鲜有批评君臣沉酣湖山之乐的言论。那么,南渡时人认为靖康之难的原因是什么?第三,宣和七年(1125),陈东提出“六贼”之名,翌年,国子祭酒杨时说:“今日之祸,实(王)安石有以启之。”[2]12741这些说法在南宋初年广为人接受的原因又是什么?第四,靖康之难的诠释,是史实和国策问题,也是思想史的课题。南渡时人析论靖康之难的成因与宋亡以后人不同,反映了南渡时人的思维定势。其中有些观念,颇可和北宋中叶以来的思想联系,十分值得留意。
一、 认为“侈靡太甚”、“风教败亡”促成靖康之难,但不否定“太平为娱”与“山水之乐”
宋代诰令和奏议常有批评“侈靡”的话,批评的重点几乎都紧扣两个关键理念:一是“侈靡”风俗与国家的“风教”密切相关;二是要遏抑侈靡,必须实践儒家“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7]的传统精神,以皇室和士大夫敦实俭朴的榜样,感化天下。金人侵宋以后,“侈靡”被进一步视为国家衰亡的主因之一。李纲在宣和七年(1125)指出:“比年以来,搬运花石,舳舻相衔;营缮宫室,斧斤不辍。”这导致两个恶果,一是“上累大德,下失群心”,二是“蠹耗邦财,斩刈民力”。李纲认为,正因为徽宗朝的腐败和内耗,才导致金人之患,其事“非偶然也”。[6]498《上道君太上皇帝封事》靖康元年(1126)侍御史孙觌等批评蔡京执政之时“倡为穷奢极侈之风”,中国由是空虚,“敌人侵侮,无所不至”,[8]836-837论述重点同样在于朝廷的挥霍无道。建炎三年(1129),叶梦得上书力陈“宣和致寇之失”,其中提到“声色”和“奢靡”两项,认为高宗若能“一切尽反之”,国家就不会“终屈其弱”。[9]1191《奏应诏大询状》
奏折批评针对皇室和士大夫,朝廷的禁令也主要针对儒家传统的“君子”阶层。相反,百官对于豪族或民间风尚偶有批评,对于老百姓的奢侈行为,却鲜有明令禁止。原因是时人认为风俗流于奢靡放任,负最终责任的应当是在上位者。即使后世被讥为佞臣的周紫芝,其《正俗论》也说:“天下之治乱,风俗之美恶,未有不出于上之所化……未有化之以不正,而天下自治者也。”[10]319这段话体现了传统“风教”的观念。
宋孝宗朝以后,出现了不少对沉醉湖山歌舞的批评,例如《题临安邸》:“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①田汝成辑:《西湖游览志余》卷2《帝王都会》:“君相纵逸,耽乐湖山,无复新亭之泪。士人林升者,题一绝于旅邸云:‘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的《题临安邸》内容虽无点明嘲讽南宋君臣,但就《西湖游览志余》前述的“君相纵逸”一语看来,这种解读仍然反映了编者的成见。《西湖游览志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4页。明代宋廷佐《武林旧事跋》:“可恨者当时之君臣,忘君父之仇,而沉酣于湖山之乐。”[11]520有学者把这种批评视为徽、钦以及高宗朝时人所论靖康之难的成因之一。②参冯志弘:《〈东京梦华录〉是否“著其盛,正著其所以衰”?──兼论宋人的“华胥之梦”》,《人文中国学报》2015年第21期,即将出版。但根据《全宋文》所录南渡初年的材料,南渡时人并不认为沉溺山水是靖康之难发生的因由。
南渡时人对“太平为娱”观念少有贬抑,相反,他们肯定歌舞升平,也肯定游乐闲适的志趣。绍兴十二年(1142)《议加徽宗谥号诏》谓徽宗“绍累圣之丕基,当四海之全盛”。[12]22李纲对于徽、钦时政每有激烈批评,谓之“颠倒是非,变乱白黑,政事大坏,以驯致靖康之变”。[6]800《奉诏条具边防利害奏状》另一方面,他在《次韵季弟善权阻雪古风》,坦率表达了“忆昔宣和全盛年……但将歌舞赏清妍”[6]218的情感。李清照的“中州盛日,闺门多暇”、[13]朱敦儒的“惜昔升平泪成阵”,[14]都反映了南渡时人认为徽宗朝是“升平”时代。就南宋初年文献看来,大量关于燕游、饮酒歌舞的记述,反映了南渡时人始终肯定徽宗时期的“娱乐”。周紫芝撰作《升平谣》,以为秦桧执政“但闻群贤岁歌舞,寿曲声中玉觞举”,[10]170这固然是阿谀奉承的话,可是韩世忠绍兴十一年(1141)罢枢密使后,也同样“时跨驴携酒,从一二童奴,游西湖以自乐”。[8]1067李纲比韩世忠更多写“酒醉”和“美人”,有“半醉佳人酒未消……尊前还唱早梅词”;[15]908《一翦梅》“深院美人慵困,乱云鬟”[15]908《水龙吟》等词句。和李纲一样力主抗金的赵鼎向往“结庐傍洓水,永与山作伴”[16]693《己亥秋陪伯山游中条……》的写意生活。他的《浣溪沙》描述美人风韵,谓之“艳艳春娇入眼波。劝人金盏缓声歌。不禁粉泪搵香罗。暮雨朝云相见少,落花流水别离多。断肠争奈此情何”。[15]943这些婉约文字出现在“气作山河壮本朝”[2]11294-11295的赵鼎笔下。他认为,山林饮酒之乐,以及欣赏、述写美人歌舞的行措,并不与他“净扫妖氛”的愿望相违。[17]又如李光在《武陵春》写“陈逢时置酒宾宴堂,仍携爱姬”,歌之曰“神女解相随”;[18]506多慷慨之作的张元干,也写过“好拥笙歌,长向花前醉”[19]《醉花阴》的句子。
从李纲、赵鼎、韩世忠的论述可以看到,他们并不认为“侈靡”和“娱乐”是同一个平面的问题。南渡时人,无论政见如何,基本上都没有否定“太平为娱”,更没有把靖康之难归咎于此。无论是李纲等力主“监崇(宁)、(大)观之失,以刷靖康之大耻”[6]644《十议·议政本》的抗金名臣名将,抑或如周紫芝般政见不同的士大夫,都把靖康之难的成因和“娱乐”分别开来。这是南渡时人和孝宗朝以后人对靖康之难的认识的主要区别。
二、 “非夷狄有常胜之势,盖中国御之失其道尔”
因着各种因素影响,南渡时人分析靖康之难的侧重点往往有差异。但这一时期的相关论述,仍然体现了一个鲜明特征,就是认为靖康之难源于国家“内忧”,远多于“外患”。 赵鼎说:“国家陵迟衰弱之渐,人皆谓敌国之为患,其亦知有以致之乎?”他认为,金人所以能够南侵,本身实力还是次要,最重要的是它觑准时机,乘宋国之“虚”而入。而靖康之失,归根究柢,是北宋末年朝廷“以善恶是非之倒置,公论久郁而不明也。其来久矣,祸胎至深,固宜痛心疾首”。[16]639-640《论明善恶是非疏》另一方面,就《全宋文》收录的材料看来,如赵鼎所言“人皆谓敌国之为患”的论述反而较少见;更多的,是如宋高宗的说法,批评靖康诸臣“苟偷岁月之安,驯致国家之祸”。[20]765《耿南仲落观文殿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制》南渡时期,主战、主和人物,抑或不同政治群体的士大夫,他们讨论靖康之难成因时,大都聚焦国家自身的问题。叶梦得斥责徽、钦朝谋臣误国,没有深考“晋成帝当苏峻之变而不避,故危;梁武帝当侯景之乱而不避,故亡”的历史教训,“徒袭宣和末议……又复决意谓虏必不再至”,[9]1190《奏应诏大询状》终岁只逞纸上谈兵的口舌之争,终致大祸。吕本中《无题》诗云:“胡虏安知鼎重轻,祸胎元是汉公卿”,[21]认为北宋官员祸国,耽误国事,才是金人能够长驱直进的根本原因。李清照说:“夷虏从来性虎狼,不虞预备庸何伤。”[13]221《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批评北宋未能有备无患。就这些说法看来,赵鼎、吕本中等都如胡铨所云,认为“非夷狄有常胜之势,盖中国御之失其道尔”。[9]4530-4531《论中国御夷狄失道奏》
对于这个问题,说得最多的还是李纲。他剖析“金寇之祸,乘间而作”[6]1330《中兴至言序》的几个原因:其一,是中了金人的“诡计”,谓之“挟诈谋以款师,待以不疑,堕其奸计”,[6]1653《勑榜诏》又说:“金人一岁之间,再犯都城,信其诈谋,终堕贼计。”[6]1673《勑榜独留中原诏》问题是,为什么以中原谋臣之多,竟不能够察觉金人的企图呢?这又引申出他对北宋朝廷第二点的批评:“邪正相杂揉,盈庭事纷纭。机会一朝失,安危自兹分。愚儒不远虑,贼退已安眠。”[6]350《夜霁天象明润成百韵》他认为肉食者未能远谋,未能防患未然,才是导致金人能够轻易渡江的原因。其三,李纲认为在谋臣的众多失误中,以“倡和倡战”议而不决,最为致命。他在《抚谕河北河东诏》中指出:“但以讲和一事,终至宗社阽危”;[6]1662在《十议·议国是》中说:“靖康之间,惟其国是不定,而且和且战,议论纷然,致有今日之祸”;[6]637《靖康传信录序》说:“去冬致寇,其病源于去春,失其所以和,又失其所以战……故令虏志益侈。”[6]1574-1575正是朝廷内部的矛盾,为金人南侵提供了最好的机会。
上述论金人南侵的文字,往往粘附着对宋朝廷的批评。他们鲜有强调金人的谋略和兵力,这一方面是避免“长他人志气”,同时李纲、韩世忠等在一些战役中也确实抵御了外侮。无论如何,南渡初年对于靖康之难的诠释,明显体现了王十朋所谓“王者将欲治外,必先安其内”[22]《论广海二寇札子》的治国理念。
三、 “靖康以来,所遭之变……本于君子小人之混淆,君子常不胜,而小人常胜”
另一个值得留意的现象是:南渡时人认为北宋沦陷是积患所致。他们也讨论徽宗朝的一些事件,但更热衷讨论北宋后期如何“朝奸乱政”,“小人祸国”,并且认为北宋乱事,“本于君子小人之混淆,君子常不胜”。[6]1164《与李泰发端明第二书》江伯彦说,北宋末年“王政沦废”的原因,在于“朝奸变乱于旧章”。[20]1192《进建炎中兴日历》谁是“朝奸”呢?建炎三年隆佑太后说:“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贯起边事,所以招致金人,养成今日之祸。”[1]1442在钦宗继位之时,蔡京、王黼已经备受时人唾骂。甚至因为二人在朝的势力巨大,人脉连结关系错综,宋高宗在即位之初,也不得不说:“蔡京、王黼当国日久,孰不由其拟受?”[23]337《蔡京王黼所用人许自新复用诏》蔡、王位高权重,靖康之难的责任,他们首当其冲,自然可以理解。李光说:“方蔡京、王黼相继用事,朝纲隳坏……”;[18]510《论梁师成札子》陈与义《邓州西轩书事十首》其六云:“杨(炎)、刘(晏)相倾建中乱,不待白首今同归。”南宋胡稚注谓此二句“疑谓蔡京、王黼”,[24]这个说法为《陈与义集校笺》的编者白敦仁所采纳;这些意见都把蔡、王视为徽宗朝最大的罪臣。甚至如邓肃所认为,正因为朝廷对于“王黼、蔡京等罪,不肯果决,费台谏一年之力”,才导致“边事有失防闲”,他认为必须定蔡、王之罪,以立朝纲,“以慰天下之望,而快二圣之怒。”[25]《辞免除左正言第四札子》
军事上,徽、钦朝臣以童贯罪名最大。李光说:“自童贯秉军政二十年,将士零落殆尽,开边生事,取笑四夷,旋致今日之祸。”[9]3802《乞不用内臣管军札子》这段话同时指出童贯殆无治军之能,且主动挑起边衅的双重罪名。张浚的说法和李光完全相同:“昨因内侍童贯,首开边祸,遂致敌骑历岁侵陵。”[23]451《讨苗刘檄》李纲说:“自童贯、高俅主兵以来,其(兵)制始坏。”[6]661《乞修军政札子》这些论述,都把整个北宋的败坏,归咎于个别关键人物。
其余受批评的徽、钦朝臣也不少。建炎元年,高宗《诏责李邦彦等》批评李邦彦、吴敏、蔡懋、李梲、宇文虚中、郑望之,李邺,“或料敌失宜,自成懦弱之势;或过听误事,复忘备御之方。用起兵端,以误国计”。[20]751李纲在宣和七年(1125)上钦宗的奏状指责朱勔“运花石竹木以敛民怨”,李彦“豪夺民田,掊敛财贿,剥下奉上,依势作威”;[6]507这二人都在陈东“六贼”名单之列。绍兴六年(1136)李纲又提出批评:“靖康末……以唐恪、聂山、耿南仲父子用事,专以离间为进身固宠之资。”[6]1484《道君太上皇帝赐宋·御书跋尾》同样以人臣道德的亏欠,作为批评的标准。《三朝北盟会编》载靖康元年臣僚之言:首先指出“自崇宁初,蔡京辅政”,破坏旧章,排斥异己,用人为私;接着批评了许多大臣,如邓洵武、范致虚、何执中、余深、林摅、薛昂、赵挺之、刘逵、张康国、郑居中、刘正夫、蔡卞、蔡攸。这篇论述认为,正是因为这些乱臣贼子,使“太上皇帝每下诏书,施行善政,皆为此辈壅遏”。[20]361这个观念,沿袭了汉代以来批评时政止于官吏,而鲜及君王的原则──其实都跳不出小人“邪说利口,足以惑人主之听”[6]800《奉诏条具边防利害奏状》的老套。
在斥责“朝奸”祸国之后,南渡时人仍然要问:为什么在徽宗朝,一时间竟出现了这么多的“小人”?这些“小人”当然是一个关系网,均“出蔡京、王黼之门”;然而,为什么这个事情能够在这个时候发生?尤其是开国百年“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26]《上执政书》,且有北宋中叶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臣典范出现,何以北宋朝廷会出现后来的局面?其转折点何在?
针对这个问题,若干南渡时人提出祖宗法度作为衡量善恶的准则。正如赵鼎所说:“自熙宁间王安石用事,肆为纷更,祖宗之法扫地而生民始病。”“生民始病”中的“始”字,反映了赵鼎认为北宋祸患起于王安石变法。紧接其后他说:“至崇宁初,蔡京托名绍述,尽祖安石之政以致大患。”[27]2771绍兴六年(1136),陈公辅首先以仁宗朝的政事作为大公无私的典范,说:“嘉祐以前,朝廷尚大公之道”;然后说:“熙(宁)、(元)丰以后,王安石之学,著为定论,自成一家,蔡京引之,挟绍述之说,于是士大夫靡然而同,风俗坏矣。”[27]3117因此,蔡京虽然是徽宗朝的“大奸”,但溯源寻本,靖康之难的始作俑者仍然是王安石。这个看法,成为南渡时人的主导思想。
靖康元年,国子祭酒杨时指出蔡京和王氏学说的关系,由此说明,徽宗朝朝政腐败的远因正是熙宁变法:“蔡京用事二十年,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安石……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他认为王安石最大的罪名,是变乱祖宗法度,使君子之政中断:“安石挟管(仲)、商(鞅)之术,饰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杨时甚至认为花石纲的因由,王安石也难辞其咎:“其后王黼、朱勔以应奉花石竭天下之力,实安石自奉之说启之也。”[27]2527“六贼”中的三人,就这样和王安石扯上了关系。赵鼎同样认为王安石变乱祖法是北宋乱事的开端:“有王安石者用事于熙宁之间……肆为纷更,祖宗之法,扫地殆尽,于是天下始多事。”[16]638《论时政得失》这句话的批评重点也是王安石的“更变”。因着这个思想,绍兴六年,在一篇以高宗名义公布的讲制中,就明确把“王氏之学”与“今日之祸”联系起来:“王氏之学行……邪说横兴……陵夷至于今日之祸。”文中甚至以孟子所谓“杨、墨之害,甚于猛兽”[23]1605《刘大中兼侍讲制》来比类“乱臣贼子”王安石如何祸国殃民──批评十分激烈。
以王安石为靖康之难的祸首,意味什么?李光说:“夫(司马)光与(王)安石,行事之是非,议论之邪正,皎若白黑。”[18]519《论王氏及元佑之学》李光认为:王氏之学与熙宁变法,正是北宋“是非”、“正邪”变化的分水岭,也是君子抑或小人主政的天壤之别。在宋代批评王安石的材料中,固然有不少针对变法的批评,但最后“总其辞”的论述,大部分都归到王安石道德败坏这一点上。好像北宋吕晦(或作吕诲)著名的《论王安石疏》的十个总评中,其中九个与王安石的“德行”、“专政”有关,包括:慢上无礼、好名欲进、要君取名、用情罔公、挟私报怨、怙势招权、专威害政、凌轹同列、朋奸之迹。只有最后一句“未见其利,先见其害”,[28]勉强算是不针对王安石。这个评价思路,也为南渡时人所继承。李焘《请以司马光苏轼等从祀疏》说:“司马光及苏轼风节弥高,其学术专务格君心,安百姓,其欲正人心,息邪说”──和上面引述的《刘大中兼侍讲制》一样,李焘也把苏轼反对王安石的论述,比喻为“决洪水,辟杨墨”;又慨叹:倘若温公、苏轼“其言早听用,宁有靖康之祸?”[29]这些说法,都指向一个共同想象:君主“亲贤臣、远小人”,则天下得治。
四、 “朝廷既正,君子道长,则所以捍御外患者,有不难也”
熙宁变法未必乏善可陈,但是,正邪不两立的观念,是南渡时人分析时局的根据。建炎三年《责罚朱胜非等诏》说:“国之纲纪,当辨忠邪。”[20]946或如向子諲所说:“君子小人之进退,实安危之所系”,[30]《赴审察入奏大略》都反映了这个观念。李光在绍兴元年所写的《乞辨君子小人札子》,正说明了他把“君子小人之辨”视为当世急务。他指出,仁宗之世“天下大治,夷夏乂安”,是由于仁宗专任韩琦、富弼、范仲淹等君子执政,“不使小人参其间”。而南宋之初正值艰难之际,虽然“可言之事未易悉数”,但“所谓端本清源之术,臣愿陛下辨君子小人而已”。[9]2051“而已”二字,说明李光认为君子之辨的重要性压倒一切“可言之事”。
把靖康之难归咎于未能明辨君子、小人,是否过于迂阔?李纲在钦宗朝所写的《谢赐裴度传札子》回应了这个问题:
臣窃见诸葛亮《出师表》,其言明于治体,以谓亲贤臣,远小人……夫君子小人,于用兵之际,似不相及,而亮深以为言者,诚以寇攘外患,有可以扫除之理;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浸长难去,其患有不可胜言者……臣窃观陛下嗣位之初,适遭金虏入寇,宵旰忧勤,励精图治,思刷前耻……然君子小人尚犹混淆于朝,翕訿成风,殊未退听,谓宜留神照察,在于攘逐戎狄之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长,则所以捍御外患者,有不难也。[6]547
李纲这段论述有几个重点:第一,以名臣名篇的论述为据,说明“亲贤远小”,是识者之见;第二,“亲贤远小”,是治世的根本基础;第三,“小人在朝”的祸害,尤甚于外患;第四,“小人在朝”看似与金人南侵风马牛不相及,其实正因为北宋内政“其患有不可胜言者”,金人才可乘虚而入;第五,即使君主励精图治,倘若朝中君子小人相混,为人君者尚且不能够察纳雅言;第六,“亲贤远小”,是捍御外患,釜底抽薪的方法;第七,国家政事纯全以后,攘逐戎狄并非难事。
惟有“辨别君子小人”,亲贤远小,才能够兴复国邦──这显然是李纲政治、军事主张的中心思想。他有《论君子小人》一文,认为“诚能别白邪正,使君子小人不至于混淆”,则“天下可为”。他引安史之乱杨国忠“动为身谋,不顾社禝计”的史事,指出“利于己而不利于人”、“害于国而不害于家”是“小人之常”。相反,惟有君子,才值得君主推心置腹,因为他们“以公忘私,以义忘利”。所以李纲认为要成就“中兴之功”,当务之急就是要“知人”,“察于君子小人之间”,则“天下不胜幸甚”。[6]677在《论建中兴之功札子》中,他又认为“中兴之于用兵,止是一事”;在用兵之前,当以“信赏刑、明是非、别邪正”等为先,并认为:“数者既备……用兵岂有不胜者哉!”[6]915在《澧州与吴元中书》中,他分析靖康之事与西汉王氏之祸,李唐武氏之变的相似之处,认为其时皆是小人当道,“其兆已存于宫中”,由是慨叹:“小人之乱邦,必至于国家俱敝而后已。”[6]1049另一篇文章《桂州与吴元中书·别幅》先引述杜牧“上策莫如自治”之说,接着指出:“自治之术,以进君子、退小人为本。”[6]1054《与李泰发端明第二书》的表述更直接:“自靖康以来,所遭之变……其实本于君子小人之混淆,君子常不胜,而小人常胜。”[6]1164这些材料说明了李纲认为“进君子、退小人”,是影响国家治乱最关键的因素。除了李纲外,在南渡文人的论述中,也时时可见强调辨别正邪的论述。赵鼎《论时政得失》认为王安石执政时期政事日坏,是由于“奖小人,抑君子”,使国家“日入于乱”。[16]638周紫芝建炎元年《上皇帝书》建议高宗使天下皆知晓君主“忠义者必赏,奸邪者必诛”,且说崇宁、大观以来,奸臣用事既久,以致“朝无端人,祸及四海,至使潢池(夷狄)兴敢拒之师……究其祸根,实出于此”。[10]408
可以看到:“忠邪之辨”、“亲贤远小”,不仅是南渡文人的常语,也是他们分析国家问题的基本准则。同时,他们认为,“小人当道”是靖康之难的主要成因。正因如此,南渡文人往往根据这一想象,以为只要“监宣和致寇之失,而一切尽反之”,[9]1191叶梦得《奏应诏大询状》并且革“君暗臣邪”[9]3056张浚《进王朴平故事奏》引王朴之论之弊,国家就必然复兴。这个思想范式,特点是“由上而下”,“由内而外”、“重理论多于具体”──这些特点,体现了南渡文人阐述靖康之难的思维定势。
五、 “人事尽,则天悔祸”
南渡时人析论靖康之难成因的又一特征,是用“天志”诠释国家祸患。“敬天之怒,无敢戏豫”[31]《板》是《诗经》的说法,但建基于南宋初年否定王安石“天命不足畏”观念的背景,时人提出“畏天戒”的主张,就更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金人侵宋以后,徽宗手诏已有“灾异谪见而朕不悟,众庶怨怼而朕不知”的话,他“下令以求直言,修政以应天变”。[32]这里的天变兼指灾异和国家危难。张浚建炎四年撰《乞修德选贤以消天变疏》,以为“必欲昊穹悔祸”,为人君者就要“亲君子,远小人,去谗佞……”,[9]3958他在建炎三年所撰的《请明教化严赏罚疏》说得更具体:“今日之事,皆因风教败亡,淳朴雕丧,侈靡太甚,天实恶之。”这个说法把北宋祸患视为“天意”。“天实恶之”的意味是:金人的武力不过是上天的工具,因此宋朝廷倘能“反本还淳,去华就实”,必然可以感动天心,“以此而化天下,积久而行之,则可以动天下,可以格人”。据此,张浚劝喻高宗“早暮见天,无忘诚祷”,俾使“淡然漠然,与道为一。”[9]630惟有君臣修德,才能感动上苍,使“昊穹悔祸,甿庶获安。”[9]3958《乞修德选贤以消天变疏》这个说法沿袭《论语》“天之未丧斯文”[7]579之说,今天看来也许是迂论,却反映了有人是从道德层面解释靖康之难的。
当然,南渡时人所以认为王安石是靖康之难的祸首,在于他主张“不敬天地、不宗祖法”。李纲说:“后世导谀之臣谄其君,以天地之变不足畏……遂使时君世主不复畏天,而肆情于民物之上,稔成祸乱……”句中的“导谀之臣”,明显指向王安石。李纲接着又质问靖康之祸:“是岂一朝一夕之故哉?”最后明确说:“其本在于不知畏天,驯致使然也。”[6]1307《乘闲志序·灾异志》由此进一步指出,王安石(不是蔡京)不知畏天,才是北宋由盛转衰的关键。李纲《乘闲志序·征兆志》又从“天人之际,其理一也”的观念,演绎“天人相应”的内涵。他指出:“自古有国家者,兴衰之数,曷尝不系乎天,然而或过其历,或不及期,则人事存焉尔。”此说认为人事足可影响天志。对于明君良臣,则“天启其心”,对于暗君劣臣,则“天夺之魄”,“天”和“人”相互影响。据此,他批评某些“言天者,以谓一切分定,而废人事;言人者,以谓悉由智力,而废天命,二者交失也”。文章最后指出:“靖康之初,夷狄以微”早有天兆。“知数者,形于谶纬,多能预言……若合符节。天之所以告人者甚明,顾弗察耳。”[6]1307-08这进一步指出,是“天志”与宋朝廷失德──而不是金人──才是导致靖康之祸的原因。
由于强调“天志”之于国难的关键作用,李纲在《奉诏条具边防利害奏状》“昧死”进言的六事中,除了信任辅弼、公选人材、变革士风、爱惜日力四项外,第五、第六项即为“务尽人事”和“寅畏天戒”。他阐析“人事”一条,即说“天人之道,其实一致”,“人事尽于前,则天理应于后”。他说的“天道”和“天理”,不仅指四时运作的自然理,而是实指上天会通过灾异昭示天志,也会通过天象辅成人事。前者如“灾惑失次,太白昼现,地震水溢”等,都是天意的“叮咛反复,以致告戒”;后者如光武以三千兵力决战王寻、王邑百万大军,“适雷电风雨,遂有昆阳之胜”,“而中兴之运启者天也”;赤壁之战孙权军兵“适风顺可以纵火”,“而鼎足之势成者天也”。金人的强悍,并不是靖康之祸的主因。北宋朝廷上失天心,下违人意,才是国家祸患的因由。李纲由此推论,南宋中兴的关键在于“务尽人事以听天命”,因为“人心即天心也,下得人心,上合天心,则无不成之功”,“恢复土宇,剪屠鲸鲵,迎还两宫,必有日矣”。[6]798,801-802所以他认为要兴复国邦,君主必须“亲贤臣,远小人”。这样,就能够做到“人事尽则天悔祸”,[23]949权邦彦《中兴十议》或者如吕颐浩所说:“宗社有灵天悔祸”;[33]《送张德宣抚川陕二首》之一这些说法,都把国家的安危归因于“天意民心”。[6]645《十议·议修德》把天意天命视为靖康之祸成因的说法,在宋亡以后甚为罕见,更不是当代学者认定的靖康之难的原因。但在南渡初年抨击“天命不足畏”的时代背景下,是理所当然,并且是冠冕堂皇的理由。
六、 诠释国难:思想史的观点与意义
吕中《中兴大事记》记载南宋初年,尽管有人批评靖康元年二月敌退之后,“士大夫争法新旧,辨党邪正”,以及高宗即位“首诏修宣仁谤史”是“治不急之务”──张栻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宣仁之功”,正在于“拨乱反正之宏纲”,这是“古今人心之天理”,足以“开(建)炎、(绍)兴之运哉!”《中兴大事记》作者附和张栻的看法,并认为“当熙(宁)、(元)丰小人相继用事之后……则中原之祸,不待靖康而后见”。[34]这条记述指出,“北宋”末年“绍述”的“国是”虽然已有改变,但是“辨党邪正”为国家第一急务的观念,仍然屹立不倒。就本文的讨论看来,这种“辨别邪正”的主张,不仅是张栻的看法,还是南渡文人的主流观念──因着对于明主、君主形象的崇敬,他们亟欲建立“君子执政”的形象。于是,君主、士大夫“好奢侈”被视为失德、君暗臣邪;相反,执政者好俭、抑奢靡,被视为契合天意,是国家必然中兴的兆头──南渡时人认为这些形象的象征意义很大,是南宋是否能够恢复故土、迎还二帝的关键。
另外,比较南渡时人、宋孝宗朝以后、宋亡以后以至当代学者分析靖康之难成因的各种叙述,可以看到它们的异同。南渡时期强调天意人心、君子小人之辨,抨击侈靡,但不否定“娱乐”。宋孝宗朝以后,出现了文及翁“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15]3138这样批评士大夫沉溺山水的言论。这些意见从“环境”消磨“心志”的思考模式立论,强调了“外因”的影响,翻出新意,但始终认为,承担北伐中原使命的,仍然是君臣,而不是老百姓。这个诠释准则的影响力很大。直到清末民初,因着梁启超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35]3271《痛定罪言》的话,概括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36]的意见,才出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说。
宋亡以后,抨击宋徽宗侈纵昏庸的话愈来愈多。本文开篇引述《宋史》、《宋论》的话都是典型例子。这些意见自然不可能在南渡时人“缅怀二圣”的论述中找到。但如果注意《宋史》、《宋论》的措词,例如“虽欲不亡得乎”、“无往而不亡矣”等话,仍然可见史家往往强调北宋覆亡的某种必然性。这种以汉民族治乱为本位、甚少关注“金人国力和谋略”的立论方式,与张浚所说“今日之事,皆因风教败亡”有一致性。
当代学者在继续关注徽、钦二帝和北宋后期人物的同时,愈来愈多从制度和战略角度解释靖康之难的成因,见前人所未见。臧嵘、游彪分别指出北宋“防内甚于防外”、“异论相搅”的国策,是靖康之难的成因。廖隆盛认为,宋钦宗固守真宗时期“衅不我始,北界和平确有可恃”的观念,致使国家疏于武备,和、战立场摇摆不定。[37]罗家祥认为钦宗时期始终围绕学术、国是、用人三方面激烈争论,贻误国事。[38]陶晋生认为靖康之祸的主因是北宋未能固守盟约,容纳叛将张觉,给予金人入侵的口实。[39]张天佑、李天鸣较详细地分析了金人的侵略心势和军事能力。[40][41]这些意见突破了古人析论靖康之难成因的畛域。
另外,当代学者对靖康之难提出了一些“假设”,例如,张邦炜认为若非北宋末年太上皇徽宗和钦宗内讧,北宋王朝或许尚能延续。[42]梁伟基认为其时金国宗望、宗翰两路军队有矛盾,如果宋朝廷能够接受宗望“帝姬和亲”的屈辱盟约,未始不能促成和议。[43]王曾瑜指出导致开封城失守的关键事件,一是部分护龙河被金军填平,二是郭京六甲神兵出战。他认为金人不耐酷暑,不擅雨战;只要开封城守御得法,捱过春天,金军只能退兵。[44]李天鸣认为如果开封第二次攻防战由李纲守城,情况会大大改善。上述学者突破了宋人的思维定势,论述焦点和结论也和南渡时人强调天命、“君子小人之辨”大不同。问题是:指出南渡时人分析靖康之难的思维模式与宋亡以后有所不同,这对宋史研究有何意义?
第一,它有助打通“以人为中心”和“以事为中心”的述史模式,并且贯穿“观念史研究”和“史实研究”范畴,因而也有助于解释南宋国策的种种思想根据。这方面,西方汉学界已经提出了一些深刻的观点,例如包弼德(Peter Bol)指出,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政见虽然南辕北辙,但他们都使用同一套政治话语,以之作为他们治国的理据。李瑞(Ari Daniel)分析宋徽宗时期不同政见官员的政论,认为他们都使用诸如忠奸善恶、君子小人、为公为私等判语来批评政敌,这些用语纯粹是道德性的。本文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思想史研究扩至“南渡时人析论靖康之难”此一具体问题。虽然南渡时人竭力否定王安石、蔡京、童贯,但他们以“辨党邪正”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论述政事,其实正沿袭了北宋风尚,就是说,无论新党旧党,他们都重视道德之于治国的价值,道德的重要性凌驾于具体问题的分析之上。明显的例子是,不少宋人视“奢靡”为朝纲败坏的象征,因此,到了南宋,革除“奢靡”成为重建朝纲的核心概念。尤其在高宗即位之初,“抑奢崇朴”时常是朝廷诏令的大主题。建炎元年(1127)《禁州县用乐诏》,批评“州郡官吏歌乐自若,殊无忧国念民之心”;[11]6544建炎五年(1131)《诏修国政》重申“抑末作,去浮靡”的主张,[20]751-752这都体现了“务敦实而去浮华,止奔竞而崇静退”可使“廉耻之风,忠厚之行,蔼然著明”[6]455《诫谕士大夫敦尚名节诏》的成见。这种“救国”方式相当迂曲,但对南渡时人来说,是釜底抽薪。
第二,今天看来,分析宋代“祖宗家法”,以及靖康时期各种决策的成败得失,无疑十分重要。但是有些选择不可能是宋人能够想到的。这不是智力问题,是成见问题。例如,在南渡时人的思维里,“国家政策、御敌计谋”是现实问题,“君臣契合、尽力斯民”是理想的伦理范式和道德问题。他们认为,只要遵从祖宗家法,则“人事尽则天悔祸”,这是一种古老而根深蒂固的信念。析论靖康之难成因时,他们几乎置金人于不顾──这是认为上天必然护佑“尽人事以听天命”者的“汉文化中心论”。由于他们这样理解国难,南渡时人不大可能在制度改革上有突破。他们认为,朝廷拨乱反正,复兴传统儒家“君子治国”的精神,这才是“迎二圣,归京阙,取故地”[45]《五岳祠盟记》的不二法门。这种观念,使得宋人在国力不如人的情势下,仍然维持着汉民族的高度自信。
第三,靖康之难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各种制度与思维固然左右北宋后期政治,不少国策与谋略的失误也贻误大局。靖康之难的发生,是这些因素汇合的结果。笔者唯一不同意的,是以“命定论”来解释靖康之难。例如说:宋代强干弱枝国策,必然导致国家走向衰败覆亡;或者说北宋军备废弛,注定无法敌挡金人。这些观点,无法解释何以在南渡初年,继承上述国策与军备的高宗朝廷尚且足以负隅顽抗。如果说南渡初年有许多偶然因素使宋朝廷可以稍作喘息,那为何这些偶然因素“注定”不可能在靖康时期出现呢?这样,“命定论”的理据更可能是一种倒果为因的分析:“因为靖康之难发生了,所以它必然会发生。”这种说法,无助于解释充满偶然性的历史和现实。不过有意味的是,以“天实恶之”解释靖康之难,却是不少南渡时人的信念。
从南渡时人诠释靖康之难的成因可见:研究观念史,除却可以了解古人的思想历程,更是论析历朝政局不可绕过的蹊径。同时,了解南渡文人始终坚持的理念,也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南宋的政治和思想。这对于深化宋代文化研究,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1] 冯琦,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M]∥历代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97.
[2]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 王夫之.宋论[M].北京:中华书局,1998.
[4] 臧嵘.“靖康耻”是怎样造成的?[J].史学月刊,1965(2):21-26.
[5] 游彪.靖康之变──北宋衰亡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6] 李纲.李纲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4.
[7] 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866.
[8] 徐自明,王瑞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M].北京:中华书局,1986.
[9] 杨士奇,黄淮,等.历代名臣奏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0] 周紫芝.太仓稊米集[M]∥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1] 周密.武林旧事[M]∥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北京:中华书局,1962.
[12] 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13] 李清照.李清照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50.
[14] 朱敦儒.朱敦儒集[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269.
[15] 唐圭璋.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6] 赵鼎.忠正德文集[M]∥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7] 陆游.老学庵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9:2.
[18] 李光.庄简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9] 张元干.芦川归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00.
[20]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1] 吕本中.东莱先生诗集[M]∥四部丛刊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85:7.
[22] 王十朋.王十朋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620.
[23]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4] 陈与义.陈与义集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411-412.
[25] 邓肃.栟榈集[M]∥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14.
[26] 范仲淹.范仲淹全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212.
[27] 毕沅.续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8] 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181.
[29] 李焘.爱日斋丛钞[M]∥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43.
[30] 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别集[M]∥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69.
[31] 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448.
[32] 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M]∥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510.
[33] 吕颐浩.忠穆集[M]∥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27.
[34] 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85:3.
[35]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4:3271.
[36] 黄汝成.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757.
[37] 廖隆盛.从澶渊之盟对北宋后期军政的影响看靖康之难发生的原因[J].食货月刊,1985(6):15-31.
[38] 罗家祥.靖康党论与“靖康之难”[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74-80.
[39] 陶晋生.对于北宋联金灭辽政策的一个评估[M]∥宋辽关系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社,1983:203-215.
[40] 张天佑.宋明史研究论集──宋明衰亡时期[M].台北:华世出版社,1977:55-91.
[41] 李天鸣.靖康之难──宋金第二次汴京之役[J].故宫学术季刊,2007(4):25-70.
[42] 张邦炜.靖康内讧解[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69-82.
[43] 梁伟基.从“帝姬和亲”到“废立异姓”——北宋靖康之难新探[J].新史学,2004(3):1-46.
[44] 王曾瑜.北宋末开封的陷落、劫难和抗争[J].河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1-4.
[45] 岳飞.岳飞集辑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18.
(责任编辑:梁临川)
On the Causes of the Jingkang Disaster——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Then Song People Who Moved to the South
FENG Zhi-hong
(TheDepartmentofLiteratureandCulture,TheHangKongInstituteofEducation,HongKong,China)
As to the Royal Song Family′s moving to the south, the then Song people did not ascribe it to the scholar-bureaucrats′ obsession with sightseeing entertainment. Rather, they held that the “internal worries” of the Jingkang Disaster far outweighed the “external troubles”. That is to say, the court corruption as the “remote causes” far outweighed the southward invasion of foreign nations as the “near causes”. Besides, they believed that the chaos in North Song Dynasty “originated from the confusion of gentlemen with petty men, and gentlemen are usually outmaneuvered”. These perspective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ost-Song Dynasty views that the Jingkang Disaster is incurred by the Emperor′s wallowing in entertainments and faults in policy decisions.
the Jingkang Disaster; the Royal Song Family′s moving to the south; the gentleman-petty man debate
10.3969/j.issn 1007-6522.2015.04.009
2015-01-22
冯志弘(1978- ),男,香港人。香港教育学院文学及文化学系助理教授,香港浸会大学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及思想、中国文化与宗教等。
K244
A
1007-6522(2015)04-009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