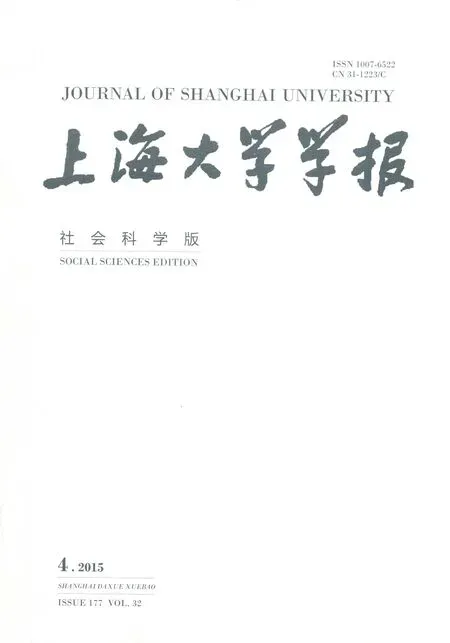中国新常态与智慧城市战略问题
2015-04-03刘士林
刘 士 林
(上海交通大学 城市科学研究院,上海 200240)
中国新常态与智慧城市战略问题
刘 士 林
(上海交通大学 城市科学研究院,上海 200240)
由于政策红利刺激和消费社会的巨大需求,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在整体上有可能不遵守“经济新常态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的普遍规律,而是扮演一种逆势上扬、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角色。智慧城市新常态将呈现出三大基本特点:一是在较多起伏变化中保持相对高水平增长。二是结构性调整难以避免,但绝非朝夕可成。三是数据更加开放的同时也更加封闭的矛盾长期存在。在新常态背景下需要研究和确立适合国情和时代需要的战略框架。
新常态;智慧城市;战略
一、 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突出问题与大背景
2012年是我国智慧城市的规划与建设一个特别需要关注的节点。截至这一年的6月底,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和地方政府签约合作建设智慧城市的总数超过320个。同年11月22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正式发布《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并印发《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和《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这些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正式被纳入国家战略框架。2015年4月7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联合发布了第三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新增包括北京市门头沟区在内的84个城市(区、县、镇)。截至2015年6月,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已达277个。
和前些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相似,这种智慧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大跃进”,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和系统安排,必然出现粗放式开发建设、过度依赖投资、硬件与软件错位、重形式轻内容等问题,直接影响到智慧城市的建设质量和可持续发展。针对这些不正常的问题,2014年8月27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确保智慧城市建设健康有序推进”。这既是对智慧城市建设无序和不健康现状的委婉批评,也是一个新的战略部署和要求。什么样的速度、规模、节奏和模式才是健康和有序的;在发展方式上是继续升温、加速,还是主动调整、换挡,成为智慧城市建设进入新常态必须思考和解答的首要问题。
在中国整体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我国智慧城市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主观上建不建的困惑。在过去的快速扩张中,城市信息基础设施投资规模逐年增大,信息技术研发成果层出不穷,智慧产业公司遍地开花,但实际上并没有使城市运转真正“智慧”起来,“需要的没有,不需要的太多”,成为信息服务和消费的普遍现象与突出问题。再加上国家只给“智慧城市”名分而没有资金投入,越来越缺钱的地方政府无力开展具体的建设。二是客观上如何建的困惑。在过去,很多城市都一哄而上,准备大干一场,但由于智慧城市建设投资大、见效慢,主要是一种公共服务而非盈利行为,再加上开发商普遍面临资金链吃紧甚至断裂,使不少智慧城市建设协议、契约、项目化为一纸空文。或者是开发商只选有效益的项目做,使智慧城市建设被肢解得支离破碎,城市信息化进程中的不对称、不均衡现象有增无减,由此产生了大批的“烂尾楼”工程,让地方政府“食之无味”又“弃之不舍”。所以,要“确保智慧城市建设健康有序推进”,必须首先解决以建不建为主题的信心问题和以如何建为中心的战略问题。
客观而言,对经验不足又急于求成的城市和企业,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这也是我国信息化进程必须缴纳的昂贵学费。但从发展趋势上看,2014年3月16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政务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和“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便捷化、产业发展现代化、社会治理精细化”等为重点,“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这表明建设智慧城市的基调没有改变。2014年5月4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印发〈智慧社区建设指南(试行)〉的通知》,将智慧城市建设推进到更加具体的社区层级。2014年1月15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加快实施信息惠民工程有关工作的通知》,将信息惠民工程明确在“社保、医疗、教育、养老、就业、公共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社区服务、家庭服务等九大领域”,这意味着智慧城市建设在内涵上更加完整和精确。[1]同时,随着人口城市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智慧城市的市场和需求还在扩大。如2013年8月14日,《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15年,信息消费规模超过3.2万亿元,年均增长20%以上,带动相关行业新增产出超过1.2万亿元,其中基于互联网的新型信息消费规模达到2.4万亿元,年均增长30%以上。”[2]如2014年6月23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12个部门将深圳等80个城市列为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中央财政安排部分启动资金予以支持,同时国家还将根据建设成效以后补助方式给予支持。这就在根本上回答了要不要建的问题,同时也为如何建作出了必要的指引。由于政策红利刺激和消费社会的巨大需求,在“十三五”期间,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在整体上有可能不遵守“经济新常态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的普遍规律,而是扮演一种逆势上扬、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角色。
二、 我国智慧城市新常态的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
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适应新常态的观点。同年11月9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主旨演讲,将“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概括为三大特点:在速度上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在结构上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在发展动力上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一方面,新常态是认识我国基本国情和把握发展主流的核心范畴和解释框架,智慧城市当然亦概莫能外。但另一方面,由于“中高速”中“有升有降”,“结构优化”中“有难有易”,“创新驱动”中“有成有败”,所以比洞悉、遵循新常态总体规律更重要的是:如何明确、把握智慧城市自身在新常态中的得失和损益,是确立战略目标、形成战略路径的大前提。
从智慧城市的建设现状和趋势看,我们认为其新常态将呈现出三大基本特点。
一是“在较多起伏变化中保持相对高水平增长”。在经济“中高速增长”成为新常态的背景下,智慧城市建设将不断受到“下行”和“降温”的压力和考验,直接影响规划实施、项目建设、投融资等方面,并引发较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但在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加速融合的大背景下,智慧城市建设的降温、减速和动荡是相对的,而保持较高发展速度的基本态势是绝对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是来自市场的巨大消费需求。从宏观上看,“十二五”以来,我国三百余城市建设智慧城市的直接投资合计超过3 000亿元,预计未来还有可能带来2万亿的产业机会。从微观上看,有预测表明,未来5年,我国的电脑等数字化机器将由目前的60亿台上升到400亿台。[3]这是尽管智慧城市建设成本增高、盈利模式并不清晰,但仍有越来越多的信息通讯企业义无反顾投身其中的主要原因。其次是出自政府城市治理服务的需要。在大数据时代,要想管理和调控人口、经济、社交活动越来越密集频繁的城市,必须借助信息通信、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及产业,很多城市已经启动的智慧交通、智慧农业、智慧水务、智慧医疗、智慧城管、智慧政务等,也不可能因为遇到障碍和困难就半途而废。但由于区域经济和城市发展水平的差异,既不排除在某些阶段和区域出现持续向好的局面,也不排除在另一些区域和阶段出现暴涨暴跌的情况。由此可知,由于政府和市场存在着交互需求,所以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仍会有很大空间。同时,由于在总体上已进入“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犬牙交错”的状态,所以,未来一段时期的智慧城市建设将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局面和生态。
二是“结构性调整难以避免,但绝非朝夕可成”。和1995年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中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样,智慧城市建设也面临着“如何实现精明增长”的转折关口。由于过去“铺摊子、上项目、占山头”的做法,智慧城市的结构性和生态性问题已经浮出水面。(1)在智慧城市和城市之间,信息化建设(如数字城市、信息化管理等)主要由信息技术企业主导,片面追求高技术应用或推销企业产品,使信息化基础设施与城市其他板块和功能严重脱节,偏离了城市总体战略目标。“虽有利器,无所用之。”(2)在智慧城市内部,缺乏顶层设计规划,部门各自为战,企业多头并进。此外,信息“孤岛”和“碎片化”问题日益严重,如同外表华丽但并不宜居的大都市,“成本很高,获得感很差”。(3)在智慧产业技术系统,缺乏兼容物联网、云计算、互联网、大数据和3S等关键技术以及能够满足多种需求、实现多种功能的集成化主平台,无法适应大数据时代进行跨部门合作处理复杂、多样化数据的需要,“局部亮点很多,整体乏善可陈”。(4)在信息公共服务领域,主要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供给导向型模式,对市民的需求考虑不多。相关信息化工程也主要是为了方便政府部门的办公和业务,较少基于市民和企业的角度进行规划和布局。一些样板工程往往成为“中看不中用”的摆设。如同城市改造和重建,在“城市大跃进”背景下出现这些结构性和生态性问题很容易,但在日益复杂的城市建成环境中,要实施改造和重建非常麻烦,成本高昂。对此,既要有打攻坚战、啃硬骨头的准备,更要依赖创造性的智慧和针对性的具体方案。
三是“数据更加开放同时也更加封闭的斗争长期存在”。在大数据时代,信息开放是主流和大趋势。随着我国各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的不断加大,大型电商获取市场化数据能力的迅速提高,以及社会各界对信息孤岛、信息不对称的声讨及舆情压力,数据开放正呈现出一片喜人景象,比如:国家数据(NationalData.gov.cn)、北京市政务数据资源网(BjData.gov.cn)和上海政府数据服务网(DataShanghai.gov.cn)等大型数据服务平台的投入使用,新浪微博(Weibo.com)、大众点评网(DianPing.com)、百度(Baidu.com)等互联网公司逐步开放其数据资源,共享知识(Creative Commons)、开放知识基金会(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开放获取(Open Access)、开放街道地图(Open Street Map)、开放数据中国(Open Data China)、城市数据派(Urban Data Party)等国内外开放数据组织的兴起。[4]总之,不管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我国数据开放的力度和范围将持续加大和加速,为智慧城市及相关行业提供丰富的生产资料。但另一方面,这绝不意味着数据开发共享已大功告成。首先,与数据更加开放相对的是“数据更加封闭”。由于长期形成的部门、行业的数据割据现状,也包括一些涉及国家和城市安全、商业和市场价值的数据普遍存在,使数据开放和封闭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在一些特殊背景下还会愈演愈烈。也可以说,在一些容易开放和共享的领域实现了开放共享之后,我们的信息化建设才开始逼近改革开放的深水区。这不仅是矛盾复杂且十分敏感的数据核心区,同时也是最难攻克的数据堡垒。如何打破这个僵化局面,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时间。其次,是“数据的可获得性”与“人的获得感”的矛盾将长期对立。获取数据的技术和渠道越来越多,但由于数据的不完整并与个体需求不对称,所以可以预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将不断重复“得来全不费工夫”和“回头试想真无趣”的反复轮回。
三、 在新常态背景下确立适合国情和时代需要的战略框架
我国的智慧城市规划与建设,既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及主流保持了高度一致,也面临着如何适应新常态、驾驭新常态的战略自觉及选择问题。在新常态与旧结构相互缠绕、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持续增多的关键时期,主动适应城市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的历史必然要求,深入研究并不断丰富对新常态的本质认识,为把握和应对智慧城市建设的深层次矛盾及挑战提供理论工具,在此基础上研究和确立适合我国国情和时代需要的精准战略战术,为智慧城市建设应对经济波动、改善生态结构、减少协同阻力等提供有效有力的支持。
第一,对新常态开展逻辑界定和学术建构,在充分吸收并超越其经济学阐释的基础上,探索和完善有中国话语特色、符合国情民意的新常态理论。
新常态这一概念肇始于对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和趋势的总结。由于经济发展具有基础和主导性作用,再加上目前对新常态的研究解读主要集中在经济学界,一种带有浓郁“经济学口音”的新常态,很快渗透到政治、意识形态、生态文明、社会发展、文化建设等社会生产的各主要部门,成为理解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趋势的关键范畴和解释框架。这里最需要警惕和关注的首先是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不同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新常态、文化发展新常态等,既与中国经济新常态相通相关,也有基本的和重要的差别。只有充分研究并揭示它们各自的规律和特点,才能为适应新常态、驾驭新常态提供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其次则与我国经济学自身的致命缺陷相关。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反复证明,以西方理论及学科框架为母体的相关经济学研究,由于在观念、方法、价值上过于“崇拜和迷信市场”,并不适合中国国情,很多解释和预测都是错误和相反的。为确保新常态在解释中国经验时的合法性,并在实践中符合当代中华民族的生存利益和发展需要,有必要启动一种去西方经济学的先验批判程序,为新常态这个纯粹中国概念正本清源。由此可知,开展新常态基础理论研究,正确和全面认识新常态特有的丰富内容与内在机制,更好地发挥其理论指导和价值引领作用,是一件比任何具体领域的工作都要更紧迫的理论任务。
在中国全面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建立有中国话语特色、符合国情民意的新常态理论,对包括智慧城市在内的战略研究至少具有两大作用:一是“立”,即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明确自己的新常态是什么;二是“破”,即通过去西方经济学的先验批判来规避各种伪新常态的陷阱。
第二,回到中国文化和历史语境,新常态可对应于《易经》中的乾卦,其内在本质和发展进程均可以“龙飞之象”来代表和显现。
目前对新常态的各种解读,在方法上都属于西方的概念分析模式,从现象、经验出发归纳本质和一般性。这当然有其长处,但也容易导致“屁股决定脑袋”,站在什么立场和视角,就会归纳出什么样的新常态,很难找到真正的一般性和普遍性。不同于西方的理性文化,中国文化本质上是诗性文化,其特有的诗性智慧不仅比概念分析方法直截了当,也更适合解释中国在人口、空间、发展阶段与层次、历史与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复杂性。在中国文化和历史语境中,新常态的精神实质即《周易》中的“乾”卦。“乾”取象于“草木初生上出时冲破阻力掀开泥土刚健通达之状”,[5]是宇宙新事物、历史新阶段、社会新形态、生命新境界在发生发展时期刚健进取、生机勃勃的象征,这与西方哲学把发展等同于从低级到高级的机械过程不同。由于新事物、新阶段、新形态、新境界从“旧”中产生并被后者困扰、纠缠、挤压,所以需要结合不同的阶段和处境,处理好精进与渊默、开拓与蛰伏的矛盾,既不能任性恣意,也不要自暴自弃。正如“乾”卦所昭示的,在弱小阶段要“潜龙勿用”;在快速发展阶段,既要“终日乾乾”,又要忧惧警惕;而在鼎盛阶段,则要避免走向物极必反等。所以说,中国诗性智慧更深刻地认识到发展阶段和处境的复杂性。
这一来自《周易》的诗性智慧,不仅高于任何的概念分析及琐碎描述,同时也是对新常态固有精神实质的深刻把握。从诗性文化出发,我们可以把新常态描述为“龙飞之象”。在经济新常态下衍生的“中国外交新常态”“社会建设新常态”“政治新常态”“文化新常态”等,不仅在理论上没有超出“乾”卦的范畴,在实践中也只有遵循其基本原则才能实现各自的“元亨利贞”。而一个大国在从弱变强,从匍匐于地到“飞龙在天”这个过程中面临的复杂局面和矛盾关系,也远非西方经济学“不是政府有问题,就是市场有问题”这种简单二元对立思维所能吃透和指点的。由于政府、市场和个人的需要与需求叠加在一起,智慧城市建设与我国以发展为精神实质的新常态高度一致。但同时也要看到,不同城市和区域的信息化程度、条件、需求不尽相同,研究和制定一种资源和条件可支持、社会和个体可承受、中短期和长期利益可衔接的发展战略至关重要。
第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途光明”而“道路曲折”,应取象于“乾”,确立总体理念和基本原则。
“十八大”以来,“刚健进取”渐成主流,我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金融等都在走高变强。正如“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的鲲鹏,大国腾飞需要集聚的巨大物质能量与精神条件,是国内外各种矛盾被充分搅动并日趋尖锐化的根源。在这种特殊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正确研判形势、制定战略方针至关重要。西方文化是理性文化,理性文化基于感性与理性、主体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在进取与保守、“向左”与“向右”、“不是生,就是死”中只能两者取其一,这是各种基于西方文化和价值的战略研究多半“中看不中用”的根源。以“乾”卦为代表的中国诗性文化,作为一种超越二元对立、刚柔相济的战略思维,为我们思考和适应新常态提供了返本开新的哲学基础。从“乾”的卦象看,“乾”由六根阳爻组成,均呈刚健进取之态,充满光明和力量。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和处境中,无论如何都要生长、拓展。由此可得出一个总体理念即“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发展。这个“生”的实质是刚健进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积极有为,反过来说,就是绝不能后退保守,“不管怎样都要发展”,并确立藐视一切艰难困苦的斗争勇气和文化自信,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中国在新常态中必须坚持的战略方针。但与此同时,还应研究和充分关注发展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以“乾”卦的六爻为例,一方面,由于都要发展,发展的需求过于强烈,不仅发展和退缩,甚至彼此发展过程中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层次,都会相互缠绕,相互矛盾,相互斗争;另一方面,由于发展阶段和条件不同,发展的目标和需求也不尽相同,如“乾”卦的六爻所揭示的,越在下面和开始的阶段,承受的压力就越大;而到了“中上层”和发展的高级阶段,局面就会完全不一样,直到完全占据有利和主动。由此可以确定新常态的六项基本原则:一是“潜龙勿用”,即处于弱小、不利局面时,要韬光养晦,徐徐图之;二是“利见大人”,在战略机遇期,要敢于“亮剑”,并突出和表现自己,彰显作为大国的责任和担当;三是在“刚健进取”中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四是在基本面向好的情况下,偶尔出出格,试探一下,也不会有大问题;五是在形势大好时,必须好好表现和发展;六是一旦发现过热,就要及时检点反省,并准备软着陆。由于“道通为一”的原因,这些基本原则,既是国家之道和城市之道,也是企业之道和个人之道。
中国有句老话:“三岁看到老。”西方也有一句格言:“起源决定本质。”由“乾”卦代表的发展理念和基本原则,在深层正对应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也可以说,由于自觉不自觉地遵循了《易经》中的诗性智慧,我们国家才有了今天的发展成就和气象。与之相对,凡事喜欢出风头,做过头,一味逞强任性的美国,则与其经由欧洲大陆继承的古希腊理性智慧密切相关。从诗性智慧解读新常态,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总结,也揭示出我国未来发展战略应遵循的理念与基本原则。同时,这也为我们每个当代中国人补了一堂生动警醒的人生哲学课。现代百年以来,由于西方文化殖民的原因,这种祖先的智慧已被我们遗忘得太久了。
第四,从诗性智慧出发,把表面上的经济问题转化为深层次的文化问题,有助于在新常态背景下把握住智慧城市建设的本质和未来。
在全球范围看,智慧城市建设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以数字科技为中心的科技型智慧城市,重点是先进信息通讯技术研发及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是提升了城市的信息化水平;二是以市政管理为中心的管理型智慧城市,重点是信息通讯技术在政府管理服务中的应用,这也不同程度提升了城市管理水平和运营的效率。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在很大程度上照搬和复制了西方。如2000年以来,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主要围绕着地理信息系统、遥感、三维仿真、数据建库等开展,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先进,一些大都市在这方面甚至超过了英美发达城市。与此同时,为了应对快速城市化进程的挑战,特别是为了提高管理、交通、治安等方面的行政效率,基于数字化技术的数字城市、数字政府、数字交通等政务平台纷纷上马,在提升政府效率、方便市民工作生活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推进,这两种模式固有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其中最令人痛心的是2014年底的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上海的信息化建设水平多年来一直居于全国前列,但并没有防止灾难的发生,说明仅仅“有钱”和“有技术”是不够的。从深层次上看,是因为科技型和管理型智慧城市模式都基于西方理性文化,把智慧城市建设完全等同于技术、资金和管理问题,导致了“技术”与“社会”、“信息化城市”与“城市有机整体”的对立与脱节。
基于这种反思,我们提出应规划和建设以人文科学为基础的人文型智慧城市,其重点不是“技术发展和资本增值”,而是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应用手段,有效提升城市的宜居度和人文关怀。尽管目前科技型、管理型智慧城市依然是主流,但随着文化城市[6]在全球的风起云涌,以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注重人文城市建设”的大背景,智慧城市的文化功能,或者说人文型智慧城市的规划与建设也开始起步。这与城市的本质在于提供一种有价值、有意义、有梦想的生活方式是高度一致的。从诗性智慧出发,有助于把智慧城市从一个经济问题转化为文化问题,以及从西方文化问题转化为中国文化问题,超越科技崇拜和市场迷信,使智慧城市自身完成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转型升级。
第五,不稳定和不确定是新常态的基本属性,我国智慧城市战略规划应以人文智慧城市为发展目标,同时持守“蹄疾而步稳”的策略和建设节奏。
城市建设的最高目标是:既要有物质与技术的便利,有制度和秩序的保障,还要有人的幸福和梦想。与之相应,智慧城市发展的理想形态是科技型、管理型、人文型智慧城市的有机结合和包容发展,全面满足城市化的物质基础、制度文明和人文精神需求。而单一型的智慧城市规划与建设,由于只能解决局部问题,必然导致城市片面发展,这是当今很多智慧城市建设频现问题和危机的根源。随着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技术和管理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人文型智慧城市才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最高目标。把“不可缺少的手段”与“不能抛弃的目的”有机结合起来,结合我国城市信息化水平不均等,城市管理和应急处置任务繁杂的现实,在“十三五”时期,我国智慧城市在总体上应确立以智慧科技为重要基础,以智慧管理为主体形态,以智慧文化为理想目标的战略定位和基本思路,为把我们的城市早日建成“有意义、有价值、有梦想”的城市提供全面的信息化支持。
在西方有句谚语:“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也可以说:智慧城市也不是一天可以建成的。在中国新常态下,由于经济波动会影响到城市建设,而结构调整也不知会“调整到谁”,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智慧城市建设不宜过于激进和急切。同时,由于经济波动和结构调整往往也是巨大的发展机遇,所以也不能完全袖手旁观,观望等待。这是一个最需要开展战略观察、战略判断和做出战略决策的时期,在此背景下可以把“蹄疾而步稳”确定为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战略原则:“蹄疾”是步子一定要快,慢了就会脱离“第一方阵”,以后追赶起来就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步稳”是稳扎稳打,不断建立根据地,特别是要防止“左倾冒进”,不要超出了资源、机制和现阶段的承受水平。只要能把这两方面的要求统筹协调好,就有可能开拓出一条具有战略性突破意义、彻底变被动为主动的发展道路。
[1]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加快实施信息惠民工程有关工作的通知.[EB/OL].(2014-01-14)[2015-05-30].http:∥govinfo.nlc.gov.cn/gtfz/xxgk/gwyzcbm/fgw/201401/t20140114-4577718.html?classid=439&new=1.
[2]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EB/OL].(2013-08-15)[2015-05-30].http:∥www.js.xinhuanet.com/2013-08/15/c-116951133.htm.
[3] 李开复.李开复病后首场演讲:数字革命的5大趋势[EB/OL].(2015-03-03)[2015-03-09].http:∥scitech.people.com.cn/n/2015/0303/C1007-26625761.html.
[4] 茅明睿.大数据时代的城市规划[EB/OL].(2014-05-26)[2015-03-15].http:∥www.planners.com.cn/share_show.asp?share_id=618Cpageno=1.
[5] 邓球柏.白话易经[M].长沙:岳麓书社,1993:1.
[6] 刘士林.特色文化城市与中国城市化的战略转型[J].天津社会科学,2013(4):122-127.
(责任编辑:魏 琼)
Strategic Issues of China′s New Normal and Smart Cities
LIU Shi-lin
(InstituteforUrbanScience,ShanghaiJiaotongUniversity,Shanghai200240,China)
Owing to the stimulation of policy dividends and enormous needs of a consumption society, the building of smart cities in China on the whole may run counter to the general law of “economic new normal from the high to the medium-high speed”, but “rise upstream”, acting as a new role of leading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new normal” of smart cities will take on three basic features. Firstly, comparatively high level of growth will be maintained in vicissitudes and changes. Secondly, structural adjustments are inevitable, but by no means accomplished overnight. Thirdly, a struggle between more open data and more closed data will remain in the long run.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normal, a strategic framework suitable to the national condition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should be explored and established.
new normal; smart cities; strategy
10.3969/j.issn 1007-6522.2015.04.002
2015-05-04
上海交通大学斐讯智慧城市研究中心2014—2017年系列委托研究课题(SJTP2014-17-01);上海交通大学文理交叉项目(14JCY07)
刘士林(1966- ),男,河北曲阳人。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G127
A
1007-6522(2015)04-0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