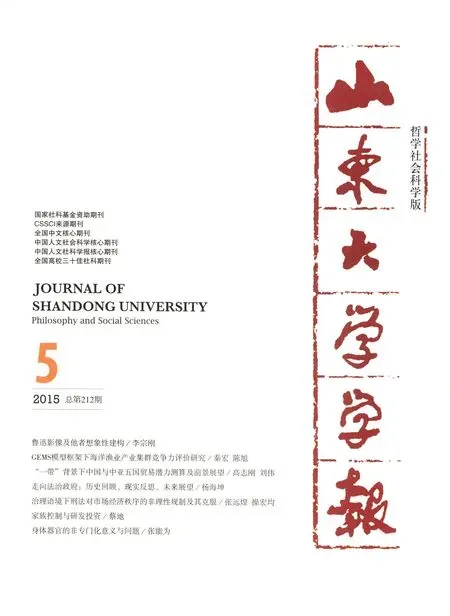治理语境下刑法对市场经济秩序的非理性规制及其克服
——以企业家犯罪实证考察为视角
2015-04-03张远煌操宏均
张远煌 操宏均
治理语境下刑法对市场经济秩序的非理性规制及其克服
——以企业家犯罪实证考察为视角
张远煌 操宏均
透过企业家犯罪现象,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现阶段我国刑法在市场经济领域日益扩张的现实。企业家犯罪罪名结构表明刑法介入市场经济领域的泛化趋势,企业家犯罪发案方式表明刑法越位介入市场经济领域,企业家犯罪的罪刑失衡表明刑法介入市场经济领域显失公平。这种现象体现了传统社会管理模式下“泛刑法化的思维模式”与“刑法浪漫主义情怀”,这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大相径庭。体制性缺陷是刑法非理性介入市场经济领域的根本原因,刑事立法缺陷为刑法非理性介入市场经济领域创造了前提条件。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刑法作为法律体系中的强力法和保障法,需要因应新形势、新要求而保持应有的理性,努力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之间取得平衡。为此,我们应该确立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平等保护的刑事政策观念,刑法立法应主动适应市场化改革的进程,通过能动的刑事司法过滤掉刑法规范中的非谦抑性因素。
国家治理;刑法非理性规制;企业家犯罪视角;对策思路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刑法在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经济社会稳健发展中立下了“汗马之功”,然而基于刑法秩序维护功能的线性思维,极易形成“刑走天下”的社会心理,使刑法的工具价值走向极端。在日益强调社会治理的语境下,这不仅无助于社会的善治,而且还会阻碍市场秩序的建立,危及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企业家”①本文中的“企业家”作为统计分析概念,是指从事企业经营管理的高端职业群体,包括企业内部具有决策权和重要执行权的高级管理人员。这一新的具有巨大社会能量的社会阶层,这一社会阶层的特殊使命和能量是“能够把经济资源从生产率较低和产量较少的领域,转移到生产率较高和产量较大的领域。”②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83页。由于企业家是市场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市场要素,因而企业家犯罪问题很大程度上成为反映刑法参与国家治理是否理性、是否顺应市场经济规律的一面镜子。
根据近三年来对企业家犯罪案例的统计分析,企业家有成为高发犯罪人群的趋势。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自2012年起依据系统检索的媒体报道案例,连续发布《企业家犯罪分析报告》,2012和2013两年间共收集712个企业家犯罪案例,涉案企业家875人,其中涉案民营企业家510例(占企业家犯罪案件总数的71.6%),634人(占企业家犯罪人总数的72.5%)。2014年通过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收集企业家犯罪案件657起,被判决有罪的企业家为799人,其中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548例(占企业家犯罪案件总数的83.41%),677人(占企业家犯罪人总数的84.73%)。本文中的统计数据和案例,除另有注释外,均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授权《法制日报》的“法制网”和《检察日报》的“正义网”发布的2012、2013、2014年《中国企业家犯罪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企业家犯罪的特殊性在于,作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社会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企业家犯罪不仅意味着企业家作为社会稀缺资源的减损,还意味着其所累积的企业家技能没有用于增进社会财富,而是起了反向作用——对社会经济体的深度危害。同时,在企业家犯罪的背后,还涉及企业的发展和职工权益及有业务往来的关联方的利益,其负面扩散效应十分巨大,以致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影响社会安定的现实因素。面对较为严峻的企业家犯罪形势,现行刑法参与市场经济秩序建立的观念与制度设置如果得不到切实改进,势必会阻碍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顺利推进。
一、新形势下刑法参与国家治理语境的解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这是国家最高决策层首次以官方文件形式确认了“治理”话语体系。有人统计,“治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先后出现了24次,有关治理论述的自然段字数相当于《决定》全文字数的1/10左右。①张小劲:《数解〈决定〉文本中的治理论述》,《人民论坛》2014年10期。可见,当前执政党的治国理政方略已转向“治理”之道。刑法作为国家治理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如何因应新要求、履行新使命,已成为难以回避和必须着重探讨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国家治理
治理理论肇始于西方社会,20世纪90年代初期被引入国内。“西方的政治学家和管理学家之所以提出治理概念,主张用治理替代统治,是他们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既看到了市场的失效,又看到了国家的失效。”②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5期。它是国际社会在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性上做出的一次深刻的认识转变与新的路径选择。与管理、统治概念相比,治理理论所体现出来的理念,与现代民主、法治精神不谋而合。
首先,治理的主体除了政府之外,还包括社会组织、公民个人,体现多元共治的精神,而管理的主体仅限于政府。也即,治理语境下政府对公共事务大包大揽的格局将被打破;并且治理更加强调各主体之间的联动与协调,政府不再只是治理的主体,它同时也是被治理的对象,而社会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对象,也是治理的主体。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稳步持续推进,已然催生了“企业家”这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最新统计表明,截至2013年底,全国实有各类市场主体6062.38万户,实有资本总额101.20万亿元③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二○一三年全国市场主体发展分析》,http://www.saic.gov.cn/zwgk/tjzl/,2014年12月15日访问。,并且呈现出增长势头。在治理语境下,如何充分调动这一主体的积极性,发挥其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事关市场机制能否真正建立和经济平稳发展的大局。
其次,治理的对象更加广泛,包括所有事关社会各方的公共事务领域。就经济领域来看,我国市场经济历经初步建立到发展壮大再到不断完善的艰辛历程,企业、企业家已经成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企业与政府、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如何用好政府“有形之手”、放活市场“无形之手”和完善社会“自治之手”,将三者有机统一,实现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已经迫在眉睫。传统的管理、领导对象往往局限于单一行为个体,已经无法满足实践的需要,而在治理语境下这些问题可以得到体系性的解决。
最后,就实现方式看,由于管理权往往来自于间接性的人民授权,其运作模式以单向性、强制性、刚性为特色。相反,治理的多元主体,决定了治理必须按照各个主体共同认可的规则进行,并且人民主体地位的认可使得相当一部分权力直接由人民行使,所以治理的运作模式往往体现出“复合、合作、包容、自治、共治”的特点。而治理的这一层含义更是与市场经济本质内涵相契合。因为市场经济尤为强调契约精神,注重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强调签约各方的协作共赢。面对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大趋势,更要求“政府要在公共管理中扮演催化剂和促进者的角色”,要“掌舵”而不是“划桨”。①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周敦仁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1 3页。
因此,在治理语境下,刑法如何为深化市场经济改革保驾护航,已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时代主题。
(二)国家治理对刑法参与的新要求
传统刑法作为国家惩治犯罪的“刀把子”,其主体、对象及手段都与治理所倡导的理念存在较大差距。在由国家管理公共事务全面转向多方合作共理的大趋势下,刑法参与国家治理也必将被赋予新的内涵与意义。
一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要求刑法必须兼顾政府、民间组织、社会各阶层等治理主体的意志,更加注重民意,吸收和切实反映多数人的诉求。为此,刑法不仅要成为惩恶扬善的风向标,而且也要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坚强保障。诚如德国刑法学家冯·李斯特指出:“刑法既是善良人的大宪章,也是犯罪人的大宪章。”②F.von Liszt,Deterministische Gegner der Zweckstrafe,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rafrechtswissenschaft Volume 13, Issue 1(Jan 1893),pp.325 358.同时,在“包容”语义引领下,刑法还要通过“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两条腿走路,来确保刑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作为最后手段的该当角色得以协调推进。
二是治理对象的广泛化,必然要求刑法除了要注重对已然犯罪进行“合正义性”制裁之外,还应当注重未然犯罪的防范,通过理性的制度设计和构筑合理的刑罚阶梯来进一步拓展社会防卫空间,最大限度地发挥防患于未然的功能。
三是治理手段的柔和性,要求刑法最严厉的刚性特征应当予以消减,适用的范围应该严格控制。在现实生活中,“凡是能用民事手段、商事手段、行政手段解决的矛盾纠纷和一般违法问题,就决不能动用刑法手段。”③高铭暄:《〈企业家犯罪报告〉的刑法学启示》,《法制日报》2013年1月30日,第12版。当然,强调限缩刑法刚性并不意味着摒弃刑法参与国家治理的正当性。申言之,“在没有穷尽非刑事手段之前,一定要慎用刑事手段。”④高铭暄:《要重视企业家犯罪现象的研究》,载张远煌、陈正云主编:《企业家犯罪分析与刑事风险防控2012 201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序言第4页。尤其是处理发生在市场经济领域的犯罪时,要更为慎重。因为,一方面,企业家群体对实现我国经济腾飞做出了特殊贡献,并且已经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拥有特殊能量的重要主体,不应也不可能还将其仅仅作为计划经济语境下的管理对象来看待;另一方面,企业家的犯罪多为法定犯。法定犯与自然犯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主要是基于国家管理上的便利和秩序的维护而设置的,一定程度也可以说是被立法者“制造”出来的,其因时因地而变的时代性和政策性特征十分明显;后者则表现为对社会共同体的基本价值进行粗暴践踏,因而具有为所有文明社会均认为是犯罪的稳定性。⑤张远煌:《犯罪学》(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2页。所以,刑法在参与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及时进行观念更新,主动适应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新要求,努力避免对市场秩序的非理性干预,那么刑法将会阻碍这一改革的顺利推进。
二、刑法非理性规制市场经济秩序的主要表现及对国家治理的消极影响
透过我国企业家犯罪的罪名结构、罪刑处置、发案方式等统计特征,不难看出当前我国刑法在参与经济领域治理中已经呈现出非理性的一面,集中表现为刑法介入市场经济领域的泛化、越位与显失公平。
(一)企业家犯罪罪名结构表明刑法介入市场经济领域的泛化趋势
从企业家犯罪罪名结构来看,国有企业家犯罪主要集中于公权力滥用领域,其触犯罪名主要为贪污贿赂型犯罪①通过对近几年来国有企业家犯罪罪名进行梳理,发现主要涵盖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私分国有资产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职务侵占罪、单位行贿罪等腐败犯罪,且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三罪名始终处于整个罪名体系的“前三甲”。,而民营企业家的犯罪则主要集中于市场经济领域,所触犯罪名集中于刑法分则第三章规定的相关罪名。在2012年、2013年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所涉及的73个具体罪名中,触犯频率最高的罪名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职务侵占罪、诈骗罪、合同诈骗罪、集资诈骗罪和非法经营罪。
从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犯罪的罪名结构,不难看出我国刑法正在以较为迅猛的态势强力进入市场经济活动中。统计显示,作为代表市场力量的民营企业家,其犯罪的罪名分布不仅远比国有企业家触犯的罪名更为广泛(国有企业家触犯的实际罪名总共为30个),而且民营企业家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受到刑事追究并最终被标定为“犯罪”的73个罪名中,有近三分之一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和非法经营罪。这些罪名的一个共性特征就是,刑法或者相关司法解释对其罪状采取了明文列举加含义模糊的兜底性条款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规定,从而为司法实践中根据需要扩大罪名认定的范围大开方便之门。具体而言,不仅刑法第225条规定的为民营企业家触犯的高频率罪名——“非法经营罪”时,采取了列举与概括相结合的规定方式,而且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解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模式时,在具体列举10种行为方式后,也追加了第11种行为模式,即“其他非法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样,2001年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在就“金融诈骗罪(此罪名为一个类罪名,包含集资诈骗罪,笔者注)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进行解释时,也是在列举6种可以直接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情形后,追加了第7种情形,即“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尽管这类“兜底式”规定或解释是出于适应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形势考虑,但它客观上使这些罪名有了很大的延展性和扩张性,使原本在公平竞争中处于劣势的民营企业家群体,更容易落入法网。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企业家触犯的罪名总数来看,还是从司法实践对“兜底条款”的“青睐”程度来看,当前我国刑法规制市场经济秩序时已经呈现出泛化趋势。而刑事法治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作用的边界和干预经济社会生活的力度理应被放置于国家治理体系之中来考虑。当前我国刑法规制市场经济秩序中呈现的这种泛化趋势,无不表明刑事手段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一面独大”的固有观念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市场。显然,这种过于倚重刑法调整而忽视其他治理手段的现状,不仅严重阻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而且与治理理念所倡导的“包容、合作”等精神内涵相违背,尤其是它将严重阻碍经济治理现代化的顺利推进。毋庸置疑,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基本目标,但它并非唯一价值目标。在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下,现代企业家作为“创新者”的代名词,是市场要素中最为核心的要素,只有充分激发这一群体的市场活力和创造力,才有助于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而刑法在介入市场经济领域所呈现出的泛化趋势,实际上传递的是一种“限制市场自由”与“越位规制”的价值导向,它会使企业家群体产生“创业有风险,入市需谨慎”的刻板印象,进而畏手畏脚制约其创新精神的发挥。更何况,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在不少方面仍然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势必会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对于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一味强调刑事规制,不仅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也与刑法处于其他部门法保障法的地位不相匹配。因此,当前刑法介入市场经济领域的泛化趋势,不仅与国家治理所倡导的“包容、合作”等基本价值理念相违背,也与国家经济治理应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和企业家创新力的基本要求不适应。
(二)企业家犯罪发案方式表明刑法越位介入市场经济领域
前述罪名结构已经表明,民营企业家的高发罪名多属于法定犯范畴,而法定犯更多是“基于行政取缔目的被认为的犯罪”②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黎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9页。,具有很强的行政法依赖性。因此,对发生于行政规制框架中的行为进行评价时,首先应该进行是否“合行政目的”的评价,而不是直接进行刑事评价,即对于法定犯罪认定,必须有一个从行政评价到刑事评价的中间环节。同时,被动性作为司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已被普遍认可,而被动性的基本要求就是刑事司法不能越位。然而,企业家犯罪的发案情况显示,现阶段我国刑法在介入市场经济活动时常常出现因过于“积极”而越位的情形。
对9种企业家犯罪案发原因的调查统计显示,“被害人报案”、“相关机构调查”和“举报”是企业家犯罪案发的最主要原因。如2012年的58例民企企业家犯罪案件中,有37例(占32.2%)系“被害人报案”而案发,有32例(占27.8%)系“相关机构调查”而案发,有15例(占13%)系“举报”而案发。①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课题组:《2012年中国企业家犯罪分析报告》,载张远煌、陈正云主编:《企业家犯罪分析与刑事风险防控2012 201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页。同样地,在2013年306例民企企业家犯罪案件中,有115例(占37.6%)系“被害人报案”而案发,有79例(占25.8%)系“相关机构调查”而案发,有65例(占21.2%)系“举报”而案发。②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课题组:《2013年中国企业家犯罪分析报告》,载张远煌、陈正云、张荆主编:《企业家犯罪分析与刑事风险防控报告201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页。这种现象表明,对于发生在市场经济领域中的各种纷争,无论是当事人还是代表国家实施监管的相关主体,其首先想到的解决途径都是刑事司法,这种人为的主观倾向使得本来应该处于最后保障位置的刑事手段过早出现在幕前。尽管早在18世纪贝卡里亚就指出,应该尽可能缩短犯罪与刑罚之间的时间间隔,进而达到在人们心中强化犯罪与刑罚这两个概念的联系的目的。③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7页。但是,如果一个行为在是否构成犯罪都还存在争议的前提下,就贸然启动刑事司法程序,显然与贝氏所强调的“刑罚及时性”的原意相违背。实践中,由于刑法的强制性最强,不少所谓的犯罪“受害人”,寄希望于通过刑事手段来解决经济、民事纠纷,将经营中的一般法律纠纷作为刑事案件报案,由此引发刑事追究甚至有罪认定。在当前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尚不够清晰的大背景下,发生于市场经济领域中的犯罪,往往存在着法律、政策界线不明、民事与刑事交叉的情形。因此,在此种情形下,如果刑事司法不能坚守最后手段性的底线,强力介入,实则有以刑事手段代替民事、经济或行政处置之嫌,其结果可能是破坏了而不是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
显然,刑法越位介入市场经济领域,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破坏不仅体现在其角色错位,即对其他治理手段该当角色的僭越,也反映出“刑法万能”观念的根深蒂固,以及由此衍生出对刑法过度倚重的客观现实。在治理语境下,更加强调治理手段的多元化、柔性化,而不是只注重单一化、刚性化的强制手段,刑法最严厉的刚性特征注定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不能无限放大,更何况,刑法始终逃不掉它是一种“必要的恶”④西原春夫:《刑法的根基与哲学》,顾肖荣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3页。的本质,一旦控制不力,运用过度,不仅会伤及无辜,破坏人们对刑法正义的信仰,而且还会严重干扰正常的市场秩序,阻碍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因为,在经济治理中如果动辄启动刑事手段,不仅有将强调多方合作与多元共治的国家治理偷换为形式单一与制裁刚性的刑事治理手段的嫌疑,而且将直接制造经济领域的“警察国家”现象,使市场主体时刻处于刑事风险的风口浪尖,进而严重打消企业家群体的创新热情。此外,过度适用刑法来规制市场经济秩序,则意味着其他治理手段发挥作用的空间遭受挤压,从而危及经济秩序良性发展的社会基础。
(三)企业家犯罪的罪刑失衡表明刑法介入市场经济领域显失公平
同样地,对于那些确实应当科处刑罚的市场违法行为,如果不能在犯罪与刑罚之间建立起内在的、均衡的对应关系,这种刑事介入实际上是有失公平的,甚至是具有反作用的。从刑事古典学派为了防止使犯罪人遭受超出报应程度的制裁而基于个人本位提出的报应刑论,到近代刑事实证学派为了强化对社会利益的保护而基于社会本位提出的目的刑论,人们逐渐认识到,对行为人科处刑罚,不仅要与行为的客观危害性相适应,还要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真正做到“严厉的刑罚分配给严重的犯罪,轻微的刑罚分配给轻微的犯罪,中等程度的刑罚分配给中等程度的犯罪”①哈特:《惩罚与责任》,王勇、张志铭、方蕾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55页。。同时,“如果对两种不同程度地侵犯社会的犯罪处以同等的刑罚,那么人们就找不到更有力的手段去制止实施能带来较大好处的较大犯罪了”②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第19页。。
无论是就国有企业家触犯的高频率罪名(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罪)来看,还是就民营企业家触犯的高频率罪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职务侵占、诈骗、合同诈骗以及集资诈骗罪)来看,除了被判处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企业家,在犯罪所得与所判处刑期之间基本体现了罪与罚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之外,其他犯罪的处罚情况均没有体现罪与罚之间的均衡关系。如2012年《报告》中收集的案例显示,在其他量刑情节大致相当的情形下,受贿金额为3497万元的企业家被判处无期徒刑,而受贿金额为3000万元的企业家则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同样,挪用公款2051万元的,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而职务侵占383万元的,也是判处15年有期徒刑。③此处所列的案例,请参见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课题组:《2012年中国企业家犯罪分析报告》,载张远煌、陈正云主编:《企业家犯罪分析与刑事风险防控2012 2013卷》,第14 18页。从犯罪性质看,前者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犯罪,后者属于非国家工作人员犯罪;从犯罪数额看,前者远大于后者,但处刑却相同。这些类似情形不仅表明原本应该发挥重要量刑意义的“犯罪数额”这一要素对于行为人刑罚裁量的意义几乎丧失,而且刑罚的适用在横向比较上也显失公平。尽管决定行为人刑期长短的因素并不限于犯罪所得这一单一指标,但是发生在市场经济领域中各种行为都具有谋利性这一重要特点,如果连能够反映这一重要特点的关键指标“犯罪所得”,都无法成为企业家犯罪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无疑是令人费解的。
显然,刑法介入市场经济领域显失公平的这种现状,不仅与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基本原则相违背,也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应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这一基本价值追求背道而驰,由此会引发一系列社会恶果。首先,刑法通过强力介入来维持市场经济秩序,虽然可暂时平复犯罪行为对于市场秩序的侵害,但因处置上的显失公平,会为引发深层的社会矛盾埋下祸根,容易使国家治理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尴尬境地。其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充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市场经济有序发展。如果刑法介入市场经济领域的公平保障不足,其功能就会发生异化:不是在促进经济发展,而是在阻碍经济发展。再次,“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说到底就是国家治理的法治体系……包括了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为基本要求的动态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④莫纪宏:《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精神”》,《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也即,作为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建立的基石,不仅要有法律文本中的“公正”,更要在司法实践活动中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公正”,而刑法介入市场经济领域显失公平状况则明显与之抵牾。
三、刑法非理性规制市场经济秩序的成因
刑法在参与国家经济事务治理过程中所出现的非理性表现,固然有企业家个体性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现实因素。面对越来越突出的企业家犯罪现象,显然已超越了孤立的个人为满足私欲对抗现行秩序的表面释义,只有立足于企业家犯罪与相关制度设计和制度运行的相互关系,才能真正揭示出企业家犯罪的症结所在。
(一)体制性缺陷是刑法非理性介入市场经济领域的根本原因
我国现行刑法诞生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自身带有较为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在法律的规制方面对公有经济(国有企业)与非公经济(民营企业)自然会形成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在规制市场领域相关行为时,注重公共财产的保护而对私有财产保护不足。正是这种体制性缺陷衍生出国有企业家与民营企业家两种不同的犯罪生态。
《报告》显示,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成为涉案国有企业家的“三大标志性罪名”。如2012年在85例涉案国有企业家触犯的30个罪名中,处于前三位的罪名为受贿罪39例、贪污罪24例、挪用公款罪8例①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课题组:《2012年中国企业家犯罪分析报告》,载张远煌、陈正云主编:《企业家犯罪分析与刑事风险防控2012 2013卷》,第11页。;2013年133名涉案国有企业家触犯频率最高的三个罪名依次为:受贿罪(56人次)、贪污罪(39人次)和挪用公款罪(22人次)②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课题组:《2013年中国企业家犯罪分析报告》,载张远煌、陈正云、张荆主编:《企业家犯罪分析与刑事风险防控报告2014卷》,第13页。;2014年122名犯罪国有企业家触犯频率最高的三个罪名依次为:受贿罪(56人次)、贪污罪(19人次)和挪用公款罪(13人次)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编制:《2014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企业家刑事风险防控网,http://www. cecpc.cn/newsshow-22-73-1.html,2014年12月31日访问。。其根源在于国有资产所有权人缺位这一制度性缺陷。一方面,在市场资源配置上对国有企业的政策性倾斜和“照顾”,形成了国有企业在相关行业中的垄断地位,使得国有企业家群体成为手握特殊经济资源的特殊阶层,获得了类似于政府官员的经济控制力,从而具有了利用这种控制力进行设租和寻租的条件;而当其他市场主体想要获得相应经济资源时,又会产生对国有企业家的贿赂动机。两厢结合,贿赂犯罪就容易多发。④张远煌、张逸:《从企业家犯罪的罪名结构透视企业家犯罪的制度性成因——以245起案例统计为基础》,《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另一方面,非清晰化的产权界定,导致国有企业家对自身的国有资产管理者的角色认识错误,往往将自己视为国有资产的真正老板。此外,国有企业中的企业家的利益可能与企业的利益不一致,也助推了国有企业家将其管理下的国有企业作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
就民营企业家犯罪现象看,“摸着石头过河”的市场经济探索模式,使得官方不敢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放开手脚,新兴民营企业长期处于政府“父爱式”的监管之下,加之多数民企“本小利微”,除面临激烈市场竞争被淘汰风险外,还时常面临资金不足、融资难等体制性困境。同时,受根深蒂固抑商文化的影响,导致在“官尊民卑,公尊私卑;国企受宠,民企受挤;国企旱涝保收,民企自负盈亏;国企亏损免责,民企风险自担”⑤皮艺军:《中国企业家犯罪的文化进路:历史性的抑商情结在现实中的展开》,载张远煌、陈正云主编:《企业家犯罪分析与刑事风险防控2012 2013卷》,第68页。的制度化格局中,现阶段的民营企业实际上还处于受挤压的劣势地位。《报告》显示,在企业家所触犯的罪名中,诸如公司资本类犯罪、涉税类犯罪、融资类犯罪乃至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几乎被民营企业家所“包揽”。如在2012年的245例企业家犯罪案件中,国有企业家触犯的罪名涉及到这四类犯罪的,仅有集资诈骗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各1例,而民营企业家触犯的罪名涉及到这四类犯罪的,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31例、集资诈骗罪11例、信用卡诈骗罪3例、骗取贷款罪3例、贷款诈骗罪1例、抽逃出资罪3例、虚报注册资本罪3例、逃税罪3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7例、虚开发票罪各1例、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1例、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7例。⑥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课题组:《2012年中国企业家犯罪分析报告》,载张远煌、陈正云主编:《企业家犯罪分析与刑事风险防控2012 2013卷》,第11 12页。同样地,在2013年的463例企业家犯罪案件中,133名涉案国有企业家仅仅触犯这四类犯罪中的融资类犯罪7人次(即集资诈骗罪1人次、贷款诈骗罪3人次、骗取贷款罪2人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1人次),而483名涉案民营企业家触犯的罪名涉及到这四类犯罪的有:公司资本类犯罪19人次(即虚报注册资本罪10人次、抽逃出资罪9人次)、涉税类犯罪36人次(即逃税罪9人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20人次、虚开发票罪4人次、非出售发票罪2人次、虚开用于抵扣税款的发票罪1人次)、融资类犯罪97人次(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64人次、集资诈骗罪21人次、骗取贷款罪6人次、贷款诈骗罪1人次、欺诈发行股票罪5人次)、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9人次(即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9人次)。①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课题组:《2013年中国企业家犯罪分析报告》,载张远煌、陈正云、张荆主编:《企业家犯罪分析与刑事风险防控报告2014卷》,第13 14页。尽管这些罪名并非针对民营企业家专设,但是由于相关制度性安排的不良,使得这些罪名沦为非公经济的代表者——民营企业家的“专属品”。
(二)刑事立法缺陷为刑法非理性介入市场经济领域创造了前提条件
犯罪“既是一种社会危害事实,又是一种社会评价”②张远煌主编:《犯罪学》(第2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235页。。现阶段的企业家犯罪现象表明,正是我国市场经济领域刑事立法本身的不科学,为刑法非理性介入市场经济领域创造了前提条件。
首先,从立法模式来看,我国采用的是刑法典立法模式。这种立法模式虽然有助于人们直观把握一个国家关于犯罪规制的整体情况,但也存在缺陷,即刑法典将刑事犯与行政犯放在一起规定,容易模糊两者间的界限,不利于人们对两类犯罪本质的把握。同时,基于“法安定性”的要求,刑法典立法模式注定了其不可能朝令夕改、频繁增删,而发生在市场经济领域中的危害行为,更多涉及到法定犯的问题,其具体内容与范围必须随着前置性行政法规的变化而变化。一旦刑法更新不及时就会出现当罚不罚或者不当罚而罚的窘境。为了调和刑法典稳定性与法定犯变化性之间这种冲突,概括性规定大量出现,从而增加了立法的模糊性,导致罪与非罪、刑事与民事边界不清晰的问题。
其次,刑法在规制市场经济秩序的同时,也规定着企业家犯罪生成的可能规模和种类。刑事立法作为一个动态过程,是随着社会价值体系的演变和政治、经济及犯罪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当立法者对某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了更强烈的认识时,其反应方式就趋于强劲,表现在立法技术上,就是增加新的犯罪类别,为原有犯罪编织更加严密的法网,或者降低犯罪命名的实体规格或程序标准。无论哪种形式都会使法网所囊括的行为范围和深度得以扩展,从而成为增加社会犯罪总量和犯罪率升高的一个重要的潜在性前提因素。反之,当立法上确认某类行为的危害性已经降低,在反应强度上就会相应减弱。在立法层面就相应表现为罪名所包含的行为样态的减少或认定标准的提高,从而可以被命名为犯罪的行为范围就趋于收缩。③张远煌:《犯罪解释论的历史发展与当代趋势——社会反应与犯罪关系论要》,《法学家》2004年第5期。例如,1979年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共计15个法律条文,17个罪名。自确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经济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我国现行刑法共有451个罪名,其中刑法第三章规定了8类犯罪,共计108个罪名,占总数的23.9%,这种繁杂的罪名体系使得企业家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被标定为“犯罪”的可能性大为提高。
再次,不科学的立法,还会成为诱发甚至制造犯罪的因素。这方面,企业家犯罪也提供了可供分析的适例。发生于市场经济领域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属于私法范畴,其往往强调意思自治,争端解决机制也应是多元的,但我国长期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维护经济秩序”的大旗下,刑法不合理地强力介入私法领域的现象较为突出。由此引发的一个负面效应就是,对诸如非法经营、社会筹资、合同纠纷以及高利放贷等行为的刑法规制缺乏必要的谦抑性,相关罪名设立的门槛较低,为人为地扩大犯罪化的范围提供了制度性的支持。
以集资诈骗罪为例,《报告》显示,2012年该罪位列当年民营企业家触犯的73个罪名的第四位; 2013年也处于当年民营企业家触犯的“十大罪名”之列。集资诈骗罪之所以成为民营企业家的高频率罪名之一,除了有金融管制阻塞了民营企业的合法融资渠道这一体制性原因外,其直接原因就是对于“诈骗”的规定④目前,对集资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主要依据三份法律文件:最高人民法院于1996年颁布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出台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经超越了属于自然犯的“诈骗罪”中“诈骗”一词的应有含义,采用的是一种事实推定的定罪模式,这就为扩大认定该罪名大开方便之门。更为严重的是,1993出台《公司法》时,基于交易安全和保护债权,对公司注册资本采用了较为严格的法定资本制①法定资本制,又称为确定资本制,是指在公司设立时,一是要求公司资本总额必须明确记载于公司章程,使之成为一个具体、确定的数额;二是要求章程所确定的资本总额在公司设立时必须落实到人,即由股东全部认购和缴足股款,否则公司不能成立。参见李由:《公司制度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10页。,与此相适应,《刑法》也设立了“虚报注册资本罪”和“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鉴于实缴制的公司资本制度挫伤了市场经济主体的活力,2013年修改《公司法》时废除了实缴制,将公司注册资本制度修改为“认缴制”。②即企业股东承诺认缴多少就是多少,企业登记部门不再收取验资证明文件,也不再登记实收资本,以此简化企业设立流程,避免资金大量闲置,提高资金利用率。在前述两罪名已经失去前置性立法基础的情况下,现行《刑法》并未对立足于旧《公司法》规定的罪名予以及时废止或修改,不仅使得这些罪名成为悬在企业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阻碍了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而且无异于将已经没有社会危害性或危害性已经显著降低的行为仍然作为犯罪处理。
(三)刑事司法的越位使刑法扩张介入市场经济领域成为现实
能否恪守刑法谦抑精神,严格把握经济纠纷、一般违法与犯罪的界限,直接决定着立法缺陷在现实中的反映程度。例如,为了消解1979年刑法典“投机倒把罪”这一“口袋”罪,1997年刑法典取消该罪,规定了“非法经营罪”,但该罪罪状中“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这一概括条款的规定,为扩大适用该罪名留下隐患。如果执法过程中对该兜底性规定又不予以严格解释,“非法经营罪”又会成为新的“口袋”罪。实践证明正是如此。这也正是该罪成为企业家犯罪的高频率罪名的重要原因。这也反映出面对民事违法、经济违法、行政违法与犯罪的界线不够清晰时,司法机关迫于某种形势或压力,将一些可以或应该通过行政处罚或者民事途径处理的经济纠纷升格为刑事案件进行处理的客观现实。这不仅是贬损了刑法的权威和正义,而且形成了对市场秩序的不正当干预,并与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直接对立。
四、国家治理视角下刑法理性规制市场秩序的对策思路
针对前述我国刑法非理性介入市场经济领域的困境,立于“国家治理”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时代性要求,刑法在参与市场经济秩序的治理过程中,应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相适应,在规制经济领域中的犯罪时,消除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二元对峙的立法观念,消解反映“官尊民卑、公尊私卑”观念的制度安排。这是充分发挥刑法维护市场基本秩序与激发市场活力功能的基本前提。同时,在具体规制市场秩序方面,无论是罪之设立还是刑之配置,都要切实反映市场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并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坚持“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同时并进的双向运动,主动适应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新形势,以此提升立法的科学性,为刑法适用恪守只有在穷尽其他法律治理手段之后才能考虑介入市场经济领域的本分,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一)确立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平等保护的刑事政策观念
尽管我国宪法第12、13条的相关规定,已经体现出国家对两种不同性质经济同等重视的价值取向,但是企业家犯罪的现实生态则无不表明,在实践中人们对于二者仍然持差异化对待的客观现实。就这一现象的根源来看,人们仍然按照以往的“重公有、轻私有”的惯常思维来处理市场经济领域的相关问题。
然而,面对非公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已经不再处于附属、边缘的位置,其经济贡献力不断增强,对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作用的现实,以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深化改革要求,刑法在规制市场经济秩序时,首先应在刑事政策观念上与时俱进,摆脱“重公轻私”的思维定势,切实尊重市场经济基本规律,顺应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要求和体现“公私财产平等保护”的宪法精神,切实担当起新时期刑法为建立市场经济新秩序、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保驾护航的重要使命,并将这一基本理念贯穿于整个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之中。
(二)刑法立法应主动适应市场化改革的进程
对于刑法立法要实现立法与改革决策之间的有机衔接,必须增强刑法适应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主动性,坚守刑法作为社会治理手段中“最后的、迫不得已的手段”的本位角色,并以此确定刑法在当下介入市场经济领域的应有边界,坚决切除“越界”部分。只有如此,才利于将市场秩序治理的重心放到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等一系列前置性问题上,摆脱在完善市场经济秩序过程中对刑法调整的过分依赖,进而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决策落到实处。
首先,在犯罪圈的划定上,应该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结合维护基本市场秩序的客观需要,及时协调推进立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刑法作为国家最严厉的强制性措施,其介入经济领域所要实现的合理预期应当是:一方面利于促进诚实信用与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形成,另一方面利于实现对市场主体行为的良性约束功能。这是刑事立法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与企业家行为规范化的必要前提和基本保障。但是,法律自身的时滞性缺陷却削弱了其正面的规范指引功能,“法律的这些缺陷,部分源于它所具有的守成取向,部分源于其形式结构中所固有的刚性因素,还有一部分源于其控制功能相关的限度。”①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19页。刑法的这种固有缺陷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在市场经济领域往往会被进一步放大。
一方面,企业家犯罪,尤其是作为市场力量重要代表的民营企业家犯罪多为法定犯罪。而法定犯罪具有“侵害法益程度的易变性较大”②张明楷:《刑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95页。的特性,立法的当时可能某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大,但随着经济或产业政策的变化,其危害性又显著降低;另一方面,企业家群体作为社会创新的重要引擎,面对市场的风云变幻,其经济行为在样态上往往具有不断推陈出新的趋势,尽管从结果上看,一些适应市场要求的新型行为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可能是正向的,但行为本身可能与现行规则是不相符合的。这两方面的结合,使企业家原本符合市场规律的行为乃至预示着市场改革方向的创新行为与守成性的刑法规范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从而加大企业家的刑事风险。为此,刑法要想最大限度地避免因自身的守成性和调整的刚性所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成为激发企业家活力和促进市场化改革的现实力量,就必须在确定介入微观经济活动的范围与力度时,切实遵循以下原则:其一,对于严重侵犯作为市场经济基石的诚实信用与公平竞争准则的危害行为,一旦确认通过追究民事、经济和行政责任,已不足以遏制其发生时,就应果断将其纳入到自己的调整范围;其二,对于随着形势变化其社会危害性已经显著降低的行为,则应及时排除其犯罪性或进行轻刑化处理;其三,对于与现行规定存在冲突,但其发展方向与法律性质尚不够清晰的行为,刑法不应立即介入,而应让位于其他法律先行调整。
其次,在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上,应充分考虑企业家犯罪的特点,重视非监禁刑罚方法和非刑罚处罚方法的运用。由于企业家犯罪容易引起对企业和关联方的连锁式负面影响;同时,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企业家犯罪的谋利性动机十分突出、犯罪的“成本—收益”概念也较一般社会成员更为清晰。有鉴于此,在不违背罪刑均衡的原则下,针对现行《刑法》在规制此类犯罪时仍然偏重于自由刑的缺陷,对犯罪的企业家应重视缓刑、资格刑、财产刑等非监禁刑罚方法的运用。尤其是在罚金刑方面,由于罚金的数额往往远远低于犯罪的收益,而且在罚金刑的适用上也没有对自然人和较之个人经济实力要强大得的单位进行适当区分,以至于罚金刑难以发挥遏制非法谋利动机的功效。此外,具备相应的生产经营资格和经济实力,往往是企业家犯罪的前提。基于刑罚再犯预防功能的考虑,还应重视通过非刑罚处罚的方法,限制或剥夺其生产经营资格和经济实力。
最后,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总体目标下,刑法规范的设立与适用,应注意与其他法律部门保持协调,实现对企业家经济行为的体系性规范。具体而言,对企业家的职业行为,应尽量通过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法规、行业管理制度和企业章程等进行规范。这是在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企业家犯罪现象的理性之策。对刑法而言,必须坚守自己的谦抑性,着力于改进刑法与相关部门法衔接不畅的问题,避免出现如“虚报注册资本罪”和“虚假出资罪、抽逃出资罪”这类与公司法修改脱节的现象。①2013年12月,我国公司法对公司资本制度进行了全面修订,直接动摇了相关罪名存在的基础。但2014年的企业家犯罪报告显示,“虚报注册资本罪”与“虚假出资罪、抽逃出资罪”依然为民营企业家触犯频率较高的罪名。在这种情形下,刑法所发挥的正是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负功能。
(三)通过能动的刑事司法过滤掉刑法规范中的非谦抑性因素
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保障法与最后法的地位,决定了“刑法并不须对于所有违法行为均以刑罚为之,亦即不要采取傲慢的态度。”②中国刑法学中的“刑法谦抑”是一舶来品,学者考证它来自日本,最早由宫本英修教授提出。转引自许福生:《刑事政策学》,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第71页。面对刑法在市场经济领域调整上的“越位”现实,在刑法尚未修改之前,应通过理性司法消解刑法逾越对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首先,对于相关的“兜底性条款”的适用,应作严格的限制性解释。由于兜底性条款的开放性、用语上的模糊性,在适用时应当恪守刑法谦抑精神,遵循“只含同类规则”,即兜底性条款只能限于未列举的同类情形,其他行为即便违反了有关规范市场主体活动的法律、法规,甚至因此扰乱了市场秩序,但如不属于列举的同类性质行为,就只能追究其相应的经济或民事责任,而不能以犯罪论处。
其次,对于冲击现行市场秩序的各种新型市场行为,应力戒轻易进行刑法评价。当今时代,市场经济领域瞬息万变,在企业家创新精神的驱动下,一些“新情况”不断涌现,作为治理手段之一的刑法对此不应该简单粗暴地打压,因为“刑法并非是将所有侵害重要法益的行为都作为刑罚处罚的对象”③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页。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95页。,在深化改革和需要充分激发市场活力的形势下,如果对所有形式上违反刑法的“新鲜事物”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就会严重制约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战略布局的协调推进。④例如,我国现阶段的互联网与金融结合,形成了包括P2P网络借贷、众筹融资以及基于互联网的基金销售等金融创新业态,客观上对传统金融市场形成了较大冲击,也显露出种种现实的金融风险。但出现新的金融机构和新的金融产品,是深化发展的必然需求。对这类创新行为,在其他部门法律尚未作出具体规制之前,刑法评价不能提前越位介入。同时,面对市场开放程度的逐步提高,对高利借贷与非法吸存、超范围经营与非法经营等容易引发争议的情形,刑法的评价也必须慎重。有关这方面的详细分析,参见张远煌、陈正云、张荆主编:《企业家犯罪分析与刑事风险防控报告201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5页以下。
总之,国家治理的要义在于,在社会公共事务领域要革除政府包揽一切的观念和制度体系,确立与全面深化改革相适应的国家—社会二元治理的主体格局,形成多方合作、多元并举、多管齐下的治理机制,以此整合各方力量达成善治之目的。企业家的犯罪现象,无不显示出刑法正在逾越本位对市场秩序进行非理性的干预。这不仅会严重限制市场主体应有的自由与活力,阻碍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而且会压缩刑罚以外的社会治理方式发挥作用的空间,抑制国家—社会二元治理主体格局的形成,从而使刑法成为阻滞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和危及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力量。这正是刑法逾越本位的实质危害之所在。作为政治决策者(立法者)和司法者,对于计划经济时代形成并沿袭下来的这种刑事手段扩张和滥用惯性,在当下不仅应保持足够的警惕,而且应着力矫正刑法在市场经济领域的现实逾越现象。
The irrational regulations of Criminal Law on the order of market economy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cit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irical study of entrepreneurs crime
ZHANG Yuan-huang CAO Hong-jun
(Law School,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P.R.China)
It is clear that the Criminal Law is constantly expanding in the field of market economy presently through the phenomenon of entrepreneurs’crime.The structure of entrepreneur crime shows that the Criminal Law is comprehensive intervening in the market economy,and the incidence mode of entrepreneur crime show that the Criminal Law is offside intervening in the market economy.Also the severity of punishments cannot commensurate with the crime committed by an entrepreneur,which shows that the Criminal Law is unfairly intervening in the market economy. This phenomenon reflects that the traditional thinking mode of criminal law expansionism is still prevails in our society recently,which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idea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The fundamental reason of the Criminal Law irrational intervene in the market economy is the systematic defects,and the defects of criminal legislation is the precondition for the Criminal Law irrational intervene in the market econom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city,the Criminal law should cope with the new situation and meet the new requirements,and ought to keep being rational,as well as make a balance between the protection of the order of the market economy and give a fuller play to the basic role of the market in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In view of these facts,we should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criminal policy that equally protects the public ownership economy and the nonpublic ownership economy,and the criminal legislation should initiative adapt to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process,as well as through active criminal justice to filter the non-restraining factors of the Criminal law.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city;irrational regulations of Criminal Law;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s crime;countermeasures
[责任编辑:李春明]
2015-01-12
张远煌,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理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100875);操宏均,国家检察官学院教师,法学博士(北京102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