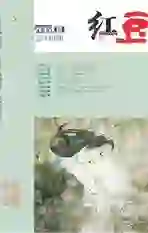病中母亲
2015-04-02金化伦
金化伦,广西天峨县人,文学硕士,散文作家,广西作家协会理事。散文作品《故乡剪影》荣获2012年度《广西文学》“金嗓子”文学奖,出版有散文集《雪泥鸿爪》。
一
2011年是我48岁的本命年。按照民间说法,本命年是多事之年,要穿戴护身符才能消灾免祸。我长期在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工作,信奉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为这种说法荒诞无稽,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因而一直未予理会。但妻子是无党派人士,对此迷信说辞比较在意,早在2010年秋季,就抽空到商场为我买下两条红色内裤,拿回家里存放起来。到了兔年春节,便吩咐我轮换着穿在身上避邪。可想而知,这种防范措施只能在心理上安慰自己,并不能阻止任何与我有关的灾难发生。当年5月下旬至8月上旬,73岁的岳母、72岁的满姑、55岁的表哥先后因长期高血压引起并发症,或撒手人寰,或生命垂危。我刚从接踵而至的成串打击中缓过劲来,又一场因高血压导致的灾难不幸降临我母亲头上。
9月14日早晨8点多钟,我正在自治区党校崇信园餐厅用餐,准备投入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报告的起草工作,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打开接听,电话那头传来二妹焦急的声音:“二哥,家里出事了!昨天下午,妈妈顶着毒辣的太阳,从我们老家巴斯一路爬坡,翻过板栗洞的高山,前往麻洞五姑家参加表哥的‘满七祭礼。因路上走得太急,还没爬到山顶就开始头痛,勉强走到五姑家。休息一阵子后,头痛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厉害,晚上只得住下来。今天凌晨4点钟左右,妈妈起夜解手回到床上,突然觉得天旋地转,全身大汗淋漓,不久左边嘴角歪斜,左手左脚失去知觉。现在还躺在床上,情况非常危急,你看该怎么办?”
二妹这番话,把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同时勾起了我对父亲去世情形的伤痛回忆。那是1997年元月7日上午,一向嗜酒如命的父亲起床后,就忙着洗净偏厦房里平时用来煮猪潲的大圆锅,在灶台下摆好酒坛,在灶锅里架上甑子,把用酒曲发酵过的玉米舀入其中,盖好盖子,再把一根竹简的一头插入甑子中部的开口处,用毛巾密封;另一头对准酒坛上部的敞口,然后往灶膛里添加木柴,生起大火烤酒。酒还没有烤完,父亲突然觉得一阵紧似一阵的眩晕,便挣扎着爬到火炕上,头靠板壁坐着休息。坐了一会儿,突然两眼一黑,颓然跌落到炕下的地板上,顿时左脸青肿,左手左脚失去知觉,虽然还能勉强说话,但很多发音已含混不清。通过延请村医治疗,当天尚能吃些稀饭。缺乏医学知识的家人以为父亲的病情已趋于稳定,既没有送县医院抢救,也没有打电话通知在南宁工作的我和弟弟。第二天晚上9点多钟,忙碌了一天的家人正围坐在堂屋吃饭,突然听到父亲的房间里传出一阵响亮的鼾声。他们闻声急忙进房察看,发现61岁的父亲已寿终正寝。我和弟弟接到噩耗夜以继日风尘仆仆赶回故乡,只见父亲已静静地躺在一口黢黑的棺材里,看不见我俩含泪的面容,听不到我俩哽咽的呼唤。想到贫穷的父亲东挪西借,好不容易把我们送入大学培养成才,还没怎么享受我们的报答就变成一具无声无息的僵尸,这实在令我难以接受,更成为我一生挥之不去的遗憾。如今母亲的病症与父亲去世前的情况大致相同,由此判断,她可能也得了脑溢血。当年因为延误抢救我们失去了父亲,这次决不能因为延误抢救而失去母亲。于是我吩咐二妹,让妹夫马上与县医院联系,请他们火速派出医生护士和救护车前往麻洞,争分夺秒把母亲接来县医院检查治疗。
挂断电话,我一刻也不敢耽搁,立即向报告起草小组的负责人请假,出校门打车赶回南湖桥边的自治区党委办公大楼,到二楼的建设银行取了一笔钱,再乘电梯上到15楼,向办公室主任求助,请他派车把我送回天峨,然后赶回家收拾行李。一切准备妥当后,已是上午10点钟左右,司机拉上我朝着天峨飞奔。一路上我和妹夫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要他及时报告母亲病情。车过都安,妹夫打来电话说,他已到达麻洞,经过医生紧急处置,母亲的身体状况没有恶化,意识还算清醒,说话也比较正常。上车之前见姑姑已做好午饭,她还说肚子饿了,要求喝碗菜汤再走,估计可以抢救过来。接完电话,我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紧张的心情方才有所缓解。
车轮滚滚,我的思绪也跟着翻滚。在母亲69岁的生命历程中,这已是她第三次遭受灭顶之灾了。第一次遭灾是在1977年秋季,时年35岁的她在地里劳碌了一整天,刚收工回到家里,突然感到肚子疼痛,没吃晚饭便躺在床上休息。躺了两个多小时,疼痛非但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严重,似乎有人拿着剪刀在绞扯她的肠子。无比坚强的母亲再也忍受不住了,嘴里低沉的呻吟变成了一阵凄厉的哭喊。做事一向慢条斯理的父亲见状也慌了神,赶忙找来村医诊治。村医经过一番望闻问切,无法判断她得了什么病,只好给她开了一些止痛药服下,服过药的母亲病情仍然没有丝毫好转。捱到第三天早上,母亲的脸色越来越苍白,哭喊声越来越微弱,眼看就要扛不住了。父亲急忙请亲戚跑到7公里以外的老鹏村,打电话请县医院派救护车前来接人,自己则用木棍扎成担架,和乡亲们一道抬着母亲急行15公里山路,来到通了公路的五福村村部,送上等候在此的救护车。救护车拉响警报,一路扬起满天尘土,把气若游丝的母亲送进了县医院。
经过紧急会诊,医生们判断我母亲得了肠梗阻,农村俗称“鬼翻肠”。上把她送上手术台,剖开腹部,把其中一段已经发绿坏死的肠子割掉,再把两端缝合,这才复燃了她行将熄灭的生命之火。主刀医生说再晚到个把小时,我母亲的性命就保不住了。
做完手术,母亲在医院住了十几天,身体尚未完全恢复,父亲就先行回家操持家务。父亲一走,性急的母亲再也坐不住了,成天闹着出院回家帮忙。医生无奈,只好同意放行。出院时母亲身无分文,又无熟人帮助联系搭乘顺路车,只好抄小路步行回家。走小路虽然比走公路略近一些,但要经过大大小小几十个山弄,坡陡弯多,崎岖不平,即便身体健康的人也要走上整整一天。可怜的母亲拄着拐杖,拖着虚弱的病体,一步一挪爬坡下坎,渴了就捧起路边的泉水喝上一口,累了就坐在树荫下歇脚。当天走到老鹏村的大峒子,天完全黑了,只好投宿在我满舅的岳母娘家,第二天一早继续赶路。就这样走走歇歇,一直走了整整两天,方才走完那条通往家乡的漫漫山路。回到家里,母亲累得近乎虚脱,一直在床上躺了好几天才慢慢缓过劲来。
出院时医生反复交待,回家后一定要安心静养,决不能再干农活了。如果劳累过度,旧病极易复发。一旦复发,后果不堪设想。可那时农村还过着大集体生活,乡亲们在生产队劳动时计算工分,秋收和年底按分数分配粮钱,多劳多得。我家共有8口人,奶奶摔伤后一直瘫痪在床,我们几个大点的孩子都在学校读书,最小的妹妹嗷嗷待哺,只有父母两人是劳动力,母亲不出工,全家的工分就少了一半,粮钱收入随之减少一半,全家人虽不至于喝西北风,但挨饿受冻在所难免。因此,要强的母亲在家休息了十来天,就把医生的忠告抛诸脑后,仍然一如既往地起早摸黑,在田间、在地头、在家中忙个不停。除了吃饭睡觉,几乎一刻也没有闲着。由于劳累过度,医生的预言不幸成为事实。就在我考上大学的1982年冬季,母亲的肠梗阻再次复发,又被父亲和乡亲们火速送到县医院,再次开刀割去一段肠子方才抢救过来。
令人惊叹的是,母亲的生命力十分顽强。第二次手术之后,尽管剩下的小肠不足原来的三分之一,消化吸收功能大受影响,但她的身体竟然恢复得不错,近三十年来除了感冒拉肚之类的小恙之扰,并无大病来袭。俗话说天道酬勤,我以为勤劳的母亲从此已经远离病痛,能够安度晚年。谁知人算不如天算,现在母亲突发重症,再次命悬一线。自从大学毕业以来,我并未遵循孔夫子“父母在,不远游”的遗训,一直在外地闯荡谋生。早年在宜州当老师时,每年还可以利用寒暑两个假期分别回去一次,每次在家里住上半个月左右,帮父母干点农活。后来进了区直机关,每年陪在老人身边的时间只有春节假期那么短暂的几天,每次给完零花钱和保健品,我就当起啥事不干的甩手掌柜,过着饭来张口的舒适生活,仿佛母亲只是我们家请来干活的佣人,而我则是利用假期带着礼物走访亲戚的客人。乌鸦还懂反哺,羊羔尚知跪乳,我作为一名长期研习中国古代文化的读书人,深谙“百善孝为先”的传统观念,熟悉从“虞舜孝行感动上天”到“黄庭坚涤亲溺器”的古代二十四孝故事,却不能追步前贤,躬行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想起来真是汗颜。如今时光转身,我已长成顶天立地的中年人,母亲却变成了病魔缠身的白发小孩,我必须使尽浑身解数,调动相关人脉资源,把她从鬼门关前拉回来,以报答她的养育之恩,避免“子欲养而亲不在”的遗憾。
下午两点多钟,经过马不停蹄的行驶,我终于赶到天峨县人民医院,见到了躺在病榻之上的母亲。母亲已做过CT检查,手上打着点滴,正处于深度睡眠之中。我不敢惊扰母亲,就在县里的兄弟陪同下,来到走廊另一侧的医生办公室,向主治医生小张询问病情和治疗方案。小张取出脑部CT扫描图片挂到墙上,指点着片子给我们讲解:阿姨因高血压导致脑出血,出血点位于脑部右侧,出血量为6毫升左右。这样的出血量不算很大,不必做引流手术,主要是用药物降低血压,防止再次出血,同时进行脱水治疗,促进溢血吸收。只要在一个星期之内脑部不再出血,老人家就度过了危险期。我不懂专业医学知识,无法对治疗方案进行评判,为慎重起见,我当即掏出手机,打电话给广西医科大学党委组织部长张志勇博士,向他报告我母亲的病情和医院的治疗方案,并询问有无必要马上转送南宁。志勇博士虽然身居要津,但他很珍惜我们在自治区党校中青班长达半年的同窗情谊,并未像考核提拔干部一样公事公办,而是热心地找到附院神经内科主任秦超教授咨询。大约10分钟后,志勇回复我说:秦主任认为,治疗方案无误,为避免长途奔波加重病情,应以就地治疗为宜。秦主任是广西神经内科学术带头人之一,他的评判无疑具有权威性。我把秦主任的意见反馈给小张,并让县里的兄弟安排晚宴,与林院长、李副院长和小张等相关医生餐叙。觥筹交错之中,我叮嘱医生们不必顾虑费用问题,尽管动用最好的药物和最先进的手段进行治疗,务必保住我母亲性命。
刚住院那几天,母亲因半身不遂,成天躺在病榻上动弹不得,连翻身都需要人协助,因而神思恍惚,情绪低落,担心逃不过这场劫难。这种精神状态对她身体的康复十分不利。我每天一到病房,就和妹夫轮番按摩她的左手左脚,同时反复鼓励她说:妈妈你命大福大,以前你曾经得过两场大病,但每次经过治疗都恢复得不错。这次你不能胡思乱想,一定要振作精神,安心接受治疗。只有这样,你才能好好地活下去。在我们的耐心开导下,母亲的情绪慢慢恢复了平静。几个妹妹则轮流值班,侍候母亲洗脸洗澡、拉屎拉尿、穿衣吃饭,尽可能把她照顾得周到一些。家乡的亲戚朋友闻讯,持续不断地赶来探视,用亲情乡情的温暖把病房包围起来。沉浸其中的母亲获得了莫大的安慰,进一步增强了战胜病魔的信心。
国庆前夕,经过半个月的悉心治疗,母亲的生命体征已经趋于平稳,没有出现致命的二次出血,压在我心中的沉重大石终于落地。但我仍然心有不甘,因为母亲左手左脚的功能尚未恢复,如果让她一直躺卧在床,生活无法自理,不仅她自己活得痛苦,还会给家人带来沉重的负担,苦命的满姑就是前车之鉴。几年前她因高血压诱发脑溢血,虽然经过抢救没有性命之虞,但那时康复治疗尚不流行,县级医院更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出院之后一直行动不便,天长日久,右手右脚的肌肉逐渐萎缩,饮食起居全靠姑爹和表妹两口子照顾,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每次我去探望她,她都泪眼婆娑,长吁短叹,让我觉得十分难受。作为母亲的长子(我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所以在兄弟们中排行老二),我想自己必须发挥带头作用,倾尽全力继续救治母亲,决不能让满姑的凄凉晚景在她身上重演。基于这种想法,我带着母亲的CT片子和病历本返回南宁,通过志勇同学再次找秦超教授咨询。睿智干练的秦主任看完全部材料,微笑着说:前期的治疗取得了一定效果。如果你们子女有经济能力,不妨把她送来我们医院作全面检查,如有隐患就对症治疗,没有隐患可作康复训练,以便恢复生活自理能力,减少你们家属的后顾之忧。遵照医嘱,过完国庆长假,我通知二妹夫开车把母亲送到南宁,在秦主任关照下住进广西医科大学神经内科病房。
二
交完住院押金,办好住院手续,我向报告起草小组的领导续假,暂时放下手头所有工作,全程陪同母亲做各种检查。CT扫描证实,母亲的颅内还有血肿,仍需进行消肿治疗。我一边陪着母亲治疗,一边祈祷她的身体没有重大隐患。然而通过血管造影检查发现,母亲还患有脑动脉血管瘤,情况非常凶险。主治医生建议转神经外科治疗,并让我跟参与会诊的神经外科冯大勤副教授接洽。
根据主治医生的建议,我跟冯医生通了电话,并按预约时间来到他办公室。高瘦清爽的冯医生立即放下案头工作,热情接待了我。他向我详细介绍说,脑动脉血管瘤就像隐形炸弹,常常会随着颅内血压的升高而破裂。一旦瘤体破裂,死亡率和致残率极高,必须及时治疗。治疗方式分为两种,一是开颅夹闭,二是介入栓塞。前者属于传统手术,费用较低,总费用在5万元左右,但创伤较大,高龄老人不一定承受得住。后者属于新兴的微创手术,不必开颅,而是运用高科技医学材料经股动脉深入脑血管,对瘤体进行拴塞,患者痛苦较小,但费用高昂,单是材料费就需7万—8万元,加上药费、手术费和其他费用,共需12万元左右。如做开颅夹闭,我们科主任黄玮教授很有经验,完全可以承担。如做介入栓塞,为确保手术的成功率,对你母亲负责,需外请专家主持,我们协助。两种治疗方式各有利弊,综合评估,我们建议做介入栓塞。到底采用何种治疗方式,请你们家属尽快商量决定,以便我们早做准备。冯医生介绍完毕,又把我带到黄主任办公室,向他继续咨询。黄主任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他的意见与冯医生完全相同。显然在约见我之前,他们已仔细研究过治疗方案。
考虑到母亲年近七旬,已经开过两次刀,如今腹部还留有两道醒目的手术疤痕,再在脑部动刀恐怕连手术台都下不来。一旦手术出现意外,就会导致人财两空,好心办了坏事。做介入栓塞虽然要多花成倍的钱,但成功率更高,还能减少痛苦。既然如此,我们做子女的别无选择,只能担当。虽然我们几兄妹家境都不富裕,但为了救治母亲,别说12万,哪怕20万也必须想办法筹集。走出黄主任办公室,我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打电话把我的意见告诉弟弟妹妹们。他们都很通情达理,没有提出异议。但弟弟贷款买房已欠下一大笔钱,二妹是全职太太,三妹在南宁打工,大妹在老家招郎入赘,满妹嫁在同村,他们手头都很紧张,没有什么余钱,希望我能先行垫支,以后大家平均分摊。我迅速盘算了一下:家里尚有十余万元存款,还够垫支。心里有了底,我没打电话跟妻子商量就慷慨地应承下来,我相信在人命关天的紧要时刻,通情达理的妻子能够理解我的独断专行。至于以后如何分摊,我想基本原则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的家庭条件相对较好,肯定要多出一些,两个嫁在农村的妹妹家境贫困,一年勤扒苦做仅能勉强度日,母亲痊愈回家她们出力照顾就行了,在经济上不必勉为其难。我把我们家属的意见告诉冯医生,并按要求预交了10万元治疗费,再把母亲转到神经外科病房,准备做介入栓塞治疗。
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科闻名全国,冯医生曾在此进修过,熟悉该院的介入治疗专家。经他联系预约,两位专家同意于10月21日乘机来邕,利用周末时间为我母亲和另一位患者动手术。22日上午11点,另一位患者做完手术后,我们家人和护工把母亲从住院部大楼十三层病房送到另一栋楼的手术室,扶她躺到手术台上,然后退回门外的走廊上等候。走廊里很安静,安静得可以清晰地听到自己粗重的呼吸声和“咚咚”的心跳声。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原本还算沉稳的我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担忧母亲能否挺得过去。为缓解心中的焦虑情绪,我不时踱步到手术室门外的玻璃窗前,踮起脚尖拔高身躯,朝室内正在电脑前忙碌的医生们张望。但除了医生们的背影,什么东西都看不到。经过度时如日的等待,下午3点钟,手术室的大门终于打开,我作为家属代表被请进室内,听天坛医院的专家介绍手术情况。专家激活已经休眠的电脑,调出一幅密密麻麻如蜘蛛网一般的脑血管三维图像,然后指着图像告诉我,你母亲大脑右侧靠近颈部的地方,比常人少长了一条重要的分支血管,导致邻近的血管压力增大,患上脑血管瘤不足为奇。不过,经过我们小心翼翼的手术,整个瘤体已基本拴塞,应该没有太大问题,请你们家属放心吧。
佛语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佛塔)。”按照佛教本义,施救者行善积德,并不指望报答,不过在我看来,获救者受人恩惠,不能无动于衷。听完专家介绍,我握过他的手,又抱拳向所有协助手术的医护人员行礼,代表母亲真诚感谢他们的再生之恩,并拟于当天晚上宴请参加手术的全体医护人员,以实际行动表达谢意。但大家都表示不必客气,以后有空再说。我见医生们忙碌了大半天,脸上写满疲惫,觉得恭敬不如从命,挑个闲暇日子再请更从容一些,可以推杯换盏,一醉方休。按照医生吩咐,我们又用轮椅把母亲从手术室里推出来,送回神经外科病房的重症监护室。
经过几昼夜的观察监护,母亲的身体没有出现意外情况,又转回普通病房继续治疗。一个星期之后,母亲病体初愈,可以出院。此前我已经打听过,同城的广西江滨医院擅长康复治疗,为实现让母亲能够自理日常生活的既定目标,我打电话给自治区卫生厅疾控处陈发钦处长,请他出面跟江滨医院领导联系住院事宜。发钦是我高中同学,外形节能环保,内心细致仁厚,办事能力极强,在江滨医院病房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他积极斡旋协调,帮助我及时把母亲转入该院做康复治疗。
三
像我们村所有出生于解放前的妇女一样,母亲没上过学,目不识丁,读不了书报,看不懂电视,打不了扑克麻将,没有任何娱乐生活,唯一的爱好就是劳动。入住江滨医院后,闲下来的母亲无事可干,只能像笼中之鸟一样困在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发愣,显得十分无助与孤单。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本想一直随侍在侧,但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已定于11月中旬召开,报告的起草进入了修改定稿的关键阶段,工作异常紧张忙碌,领导让同事打来电话,催我马上归队干活。这电话让我左右为难,思虑再三,我觉得自古忠孝难以两全,党代会报告事关全区未来发展大局,做好后续工作比陪伴母亲更为重要,我只能舍小家顾大家。于是我把母亲托付给专程从老家赶来的小妹夫和我们花钱请来的全陪护工照料,并交代妻子、弟弟和三妹多抽时间前往探视,然后回到报告起草组继续履行职责。但我心里又放不下病中母亲,便在参加党代会报告讨论修改的同时,尽量抽空来到病房,过问她的饮食治疗情况,陪她聊天解闷,扶她到院子里散步,接她到我正在重新装修的房子里看看,努力尽到儿子的一份责任。
12月下旬,经过近两个月的康复治疗,除了左手尚不能自如运动,母亲左脚的状态有了明显好转,不用人搀扶,不拄拐杖也可以走出一段距离,吃饭穿衣、洗漱解手等日常生活大致能够自理,我们预定的治疗目标基本上实现了,几兄妹对此感到特别欣慰。接母亲来南宁住院之初,我曾和妻子、弟弟专门商议,母亲出院后不必返回农村,就在我们两兄弟家轮流居住,不管新疾旧病,都可以及时送医院检查治疗,保证她能够颐养天年。现在母亲即将出院,是否让她跟随我们一起生活的问题又浮上脑海,搅得我心神不宁。我反反复复想了又想,最终觉得,我和弟弟都是劳形案牍、疲于奔命的上班族,上班时间不能自由支配,工作越干越多,没完没了,业余时间又喜欢在外面应酬娱乐,以缓解沉重的精神压力。在家跟文盲母亲谈论世界热点、国家大事,那是鸡同鸭讲,亵渎高堂,顺着母亲的心思聊那些鸡毛蒜皮的家务活,仔细照顾她的饮食起居,短期内固然可以做到,长期坚持下去未免力不从心。而母亲就像一棵行将枯萎的老树,长期扎根静谧的乡村,如果移植到喧嚣嘈杂的都市,已没有太强的适应能力,即使我们能够全身心加以照顾,也会因水土不服而缩短寿命。在康复治疗期间,当我们提出让她跟随我们两兄弟一起生活的想法时,母亲的态度十分明朗,坚决不同意,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综合两方面的因素考量,我不得不放弃先前的打算,准备让她再安心治疗到春节前夕,待左手的功能恢复到比较理想的状态,再接她出院,护送她回农村老家。但母亲一直惦记着煮饭喂猪之类的家务活,说大妹一个人在家忙不过来,三番五次闹着出院回家帮忙。我每次劝她,她总是摇头叹气说,我的病好得差不多了,再医下去没有什么用处,只不过是让你们白花冤枉钱。我天生就是劳碌命,回去以后就算干不了重活,做得家务事还行,哪怕像条狗一样看家护院也可以,反正不能让你们白养我。求你快点帮我办出院手续,送我回家吧。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不得不认真对待。从前我总认为,孝敬母亲,无非就是多给钱物,保证她衣食无忧,很少考虑她的心理需求。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我才逐渐体会到,孝敬母亲,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尽量满足她的心愿。虽然农村老家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她住了一辈子,清新的自然环境和亲密的人际关系,早已融入她的血脉,成为她生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早点回到她熟悉的生活圈子当中,能减少孤单与寂寞,对她身体的康复更有利,我不应该横加阻拦。12月25日是我的生日,我准备当天晚上安排一场饭局,把在邕的亲戚朋友们请来团聚,祝贺母亲逢凶化吉,大病初愈,感谢住院期间大家给予她老人家的关心照顾。我恳求母亲多呆两天,参加完我的生日晚宴再走。但母亲想家想得快要疯了,每天在病房里如坐针毡,浑身上下都不自在,不同意我的请求。看见母亲如此难受,我不敢强留,就于12月23日下午赶到医院结算费用,办理出院手续。第二天中午,母亲由专程从天峨赶来的两个妹夫接回故乡。
冯医生曾经说:你妈过了这道坎,只要按时服药,控制血压,注意饮食,适当锻炼,再活八年十年应该不成问题。母亲能取得如此良好的预后效果,当然与我们子女倾囊医治密不可分,我对此颇感自豪。唐人孟郊在《游子吟》里曾经感叹:“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一通俗易懂的千古名诗,道出了天下游子共同的心声。尽管母亲算不上慈祥,青壮年时期脾气暴躁,动辄跟父亲争吵,稍不如意,对未成年的子女非打即骂,甚至强令学习成绩优异的大妹辍学务农挣工分,断送了她的锦绣前程,导致母女两人的关系一直不太融洽,我对此也很有意见。从小到大,家庭留给我的印象不是温馨的港湾,而是不时弥漫着硝烟的战场,令我不胜其烦。直到我自己娶妻生子,当家作主,我才理解了母亲,知道那不是她的错,而是沉重的生存压力所致,不能过多地责怪她。试想在我们那个异常贫困的大石山区和子女众多的家庭,如果当年没有母亲以矮小瘦弱的身躯扛起如山的生活重负,我们几个子女能否长大成人都是问题。这次母亲突发重病,终于让宦游在外的我带领弟弟妹妹们好好孝敬了她一回,但不足以报答她的养育之恩。因为父母对子女的付出百倍于子女给予他们的回报,除了喂奶喂饭、把屎把尿把子女拉扯长大,还要操心子女上学、找工作、建(买)房、结婚、带小孩等一系列问题。终其一生,他们都在为子女操劳,“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就是父母为子女奉献一生的生动写照。如今暮年之母遭此一劫,身心俱损,状态不复从前。该是我们子女反哺母亲,保障她安度余生,既活出数量,延年益寿,又活出质量,少受折磨,避免庄子所谓的“寿则多辱”的时候了。我想,毕其功于一役,一曝十寒,并非完整的孝道,只有持之以恒,在生活上仔细照料,在心理上多加安慰,在医疗上周密安排,把关爱一直延续下去,才能真正实现我们的孝母心愿。农历今年三月初一是母亲七十寿辰,都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一生多灾多难的母亲活到这个年纪太不容易,值得隆重庆贺一番。春节在老家陪伴母亲期间,我已召集弟弟妹妹们商议,到那天要置办几桌酒席,把老家的亲戚朋友们请来,热热闹闹地为母亲祝寿。届时不管工作多么忙碌,我都要请假回乡主持这场寿宴,给风烛残年的母亲献上一份赤诚的祝福。同时我也衷心希望,那些和我一样在异地他乡打拚的游子莫忘根本,常回家看看,为生养我们的父母和照顾过我们的亲人送上自己的关怀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