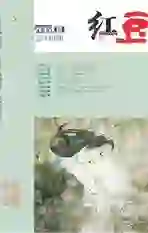陶瓷:隐忍或绽放
2015-04-02杨春山
杨春山,男,汉族,云南省作协会员,永胜县文联副主席。1975年出生于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三川镇,1993年参加工作。在《中国散文家》《西部散文家》《江河文学》《作家导刊》《文学月刊》《中外文艺》《边疆文学·百家》《滇池》《国家湿地》《中国减灾》《防灾博览》《社会主义论坛》《云南民族》《岁月》《丽江》《青草文学》《大理文化》《人民日报》《中国水利报》《西部时报》《云南日报》《内蒙古日报》《苏州日报》等各级报刊发表诗歌散文作品五百余篇,出版散文集《沧阳行吟》《情溢沧阳》两部。2013年获“天元杯”全国文学大赛散文三等奖、丽江市第四届文学艺术创作奖。现供职于永胜县文化体育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边屯之窗》双月刊杂志执行主编。
岁月之陶
静默的陶总是一言不发地蹲在角落里,用那抹幽暗的釉光,辉映着岁月扑面而来的漫漫烟尘。在时光的喧嚣和沉寂过后,陶的面孔,依旧朴素而从容。陶是泥土衍变成的精灵,它的灵魂里蕴藏着土地的敦厚与博爱。抱紧了土地的陶,依恋着土地的陶,有着隐忍和含蓄的内韵,即便在历史的跌宕起伏中,不经意被掩埋到土地深处,到出土之日,它们的面庞上仍然留存着那抹温润的亮色。
陶的出现是人类远古文明升腾的一个显著标志。当祖先们从土地里取出陶土,并用自己的手将它捏制成型,又经过高温的烧制,陶的身份,就开始和它的土地母亲有了区别。以坛、罐、盆、瓶等不同面孔出现的陶,决定了它们要以容器的姿态存在,陪伴人类年复一年最为简单而真实的生活。凡是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物件,总会具有宽容的品性,同时又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息。陶,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上了历史的舞台,贯穿了华夏文明上万年。时光一路流淌,陶的身影和姿态,就和时光一起淌到了当前。在华夏文明的江河里,陶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陶却从来不喜欢张扬,这也正暗暗扣合了陶来自土地母亲的特性,隐忍,宽厚,朴实。
陶曾经深深地介入了人类的生活,有了陶,人类的生存和繁衍就有了盛装的空间,但很少有人会注意到无声的陶。更多的时候,它们都只是沉睡在角落里,用孤寂而深邃的目光,注视着屋檐下飘红的辣椒、壮实的水稻、澄黄的玉米、纷乱的蛛网,还有菜地里一茬茬生长着的蔬菜,注视着一个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有了温暖的陶,有了生活中的那抹亮色,陶便用土地母亲般的深情,为人们的生活酿造出了久远的清香。
有了陶,文明的梁柱就有了坚实的支撑;有了陶,人类的生活就有了持久的依靠。烧制术、铸模术、上釉法、冶炼术,这些加快了人类文明进程的技艺,追溯其源头都来自古老的陶。彩陶、黑陶、红陶、褐陶,精美的纹饰,雅致的器形,让陶变得多姿多彩。每一个陶罐,在盛满了食物和水之后,它也就装满了时光和故事。一个抱着陶罐取水的女子,走在空旷的田野上,她的脚下是数不清的小草和野花,含黛的青山成为背景,不远处是升腾着炊烟的村庄,这是一幅多么自然清新的画面,而这也是我们祖先的一种生活常态。如今,祖先的身影已经走远了,只有那些朴实的陶罐,还隐藏在一个又一个乡村的庭院里,和人们相濡以沫。为此,我们要感谢陶对人类生活的滋养。有了陶罐,人类才发明了腌制术。在江河、湖泊或是古井里打上一罐清水,加入食盐、红糖、烈酒、蔬菜,在温热的阳光下酵藏一段时间,便可以腌制出生活中最醇最美的酸香。还有鱼类、肉食,在拌上各种调料之后,也可以装进陶罐里储藏,在腌制术的驱使下,逐渐幻化成味蕾上的美食。有了陶罐,母亲们就可以年复一年地用它腌制出一个家庭餐桌上的守望。
滇西北僻处边地,险峻的横断山、奔腾的金沙江虽然曾经无数次隔阻过外来的文明,但历史还是在某些时刻,把它撕开了一个又一个口子,在这里撒下了一把把中原文明的种子。陶也就随着嘶鸣的战马、屯边的军士、辗转的古道进入了这片高原红土地,原始的烧制术,在这里又找到了适宜生存的土壤,并逐渐生根发芽。为此,我不得不提起中洲——滇西北永胜县三川镇的一个小村庄,这里的制陶业已经沿袭了数百年。一个古老的村庄,能够把一种古老的技艺世代传承下来,不随时代大潮的改变而朝三暮四,我觉得这源自文化的穿透力。传统技艺中的精粹,一旦和人们的生活紧密铆合,那么,这种传统就会具有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那些已经消逝或正在消逝的传统,就是因为在时代的发展中,逐渐偏离了人们的生活轨道,从而被新生的事物替代、摧毁。文明从来都不是只顾着自己的更新与创造,而是在不断的甄别、磨合中互相碰撞,不断更替,从而引领着人类向着更先进的文明进发。中洲村的土陶器,至今依然保留着作坊式的生产。那些烧制好的陶器,一排排整齐地码放在庭院里,那莹润的釉光,简洁的器形,仿佛依旧在为陶诉说着已经历经了千百年的风雨沧桑。茶罐、陶坛、土锅、泥炉,被家乡的人们惦记着,触摸着,拥有着,它们就不会立即黯然失色。源于家乡人对生活质量的守望,一盅浓酽的苦茶,一碟酸香的泡菜,一碗红辣的腌参,还会在每一个家庭的餐桌上溢彩流光。如今,我虽然走出了乡村,在一座小城寄居,但母亲每年都要用陶罐亲手制作一坛又一坛通红美艳的诱惑,让我在一顿顿粗茶淡饭中体味家的温馨。有了母亲在陶罐里制作出的那些美食,前行的道路上艰难困苦再多,我也能够坦然面对,让生命中充满了自信与从容。
我多次在博物馆里关注过陶。这些陶来自于泥土,又回归了泥土,在土地母亲的怀抱里沉睡多年之后,因某种机缘,它们得以穿透历史和时光,重新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些曾经呵护过祖先们生活的陶,沉睡多年以后醒来,有的依然完整,有的却已支离破碎,经过专家们的巧手拼接,它们才勉强拥有一个完整的身躯。这些古朴的陶,懂得隐忍,懂得蛰伏,懂得宽容。精美的器形,质朴的本色,厚重的历史,隐藏的故事,让这些躺在博物馆里的陶,时隔千百年之后,还能展现出人类文明曾经到达过的高度。这些陶制的瓶、罐,曾经装过清水,装过粮食,装过烈酒,装过蔬菜,装过种子,装过祖先们艰辛而又惬意的生活。然而,在这些陶器里,最能体现生命和土地之间紧密联系的,是火葬罐。祖先们的躯体和灵魂,被一个个火葬罐收藏,重新回到了泥土里。只有在那里,祖先们的灵魂才可以不受任何的侵扰,长久地安息。掩埋过火葬罐的那片土地上,也许还在生长着庄稼,或者是一株正在绽放的向日葵。还有很多的火葬罐,至今依然长眠于地下。这些从久远时光里走出的陶,它们凝聚了千百年的风霜雨雪,又散发出了岁月的悠远清香。
朴实的岁月之陶,崛起于泥土,沐浴过烈火,穿越了时空。虽然它们的生存空间,在城市和文明背景的挤压下越来越逼仄,但它们信念永存,仍承载着乡村的生活与企盼,从一个个黑夜,坚定地向着黎明走来。
时光之瓷
瓷器碎裂的声音,刺穿了夜的寂寞与幽暗。那清脆的声音里,弥漫出一种隐痛,让藏在内心深处的瓷瞬间破茧而出。
瓷的质感、釉色、光泽,处处显露出高雅脱俗的品质。经过高温的锻造与洗礼,泥土开始脱胎换骨,成为高贵的瓷,散发出永久的体香。温润、莹白、纯净的瓷,美轮美奂的瓷,成为了厅堂的点缀、灵魂的依托。
我喜爱瓷,因为它来自泥土。凡是来自泥土的东西,都能彰显它们的高贵。譬如陶器。譬如庄稼。譬如树木。譬如花朵。随着信念的注入,泥土让一切有形无形的东西都拥有了灵魂。这样,向往瓷器,也就是期待着亲近泥土。泥土是万物的母亲,是我们精神的主宰。
从土地深处被人们挖掘出的高岭土,经过塑造,装饰,烧制,从此拥有了姣好的面容。瓷,来自底层,又脱颖而出,因为它的心中有着坚定的信念。很多事物都是因为有了信念而变得美好,人生也是如此。当一件精美的瓷器展示在你的面前,你在欣赏一件艺术品的同时,仿佛也从中看到了信念的力量。这些力量,隐藏在瓷的内部,并通过它的釉色和光泽一丝半缕地呈现出来,经久不息。
瓷因易碎而受到人们的珍惜。凡是易碎的东西,在人们的心里都是值得珍藏的。一次坠落就会终结一件瓷器的生命,一次坠落,有时也会毁掉一个人的一生。
我常常对着一件瓷器凝思。纯净的瓷,掩饰不住它的脆弱。而脆弱的外表下,瓷拥有的是高洁的灵魂。一件瓷器如果被时光和历史掩埋到地下,就会和泥土融为一体,因为泥土是瓷的母亲。在地下,它们互相依存,互不侵犯。几百年或是上千年,一旦出土,瓷依然保持着它原有的品性,在阳光下散发出纯净而耀眼的光泽。而坚硬的青铜,如果经此境遇,早已锈迹斑斑了。同样的隐藏,得到的却是不一样的结果。青铜的泪珠,残存在它斑驳的面容上;而瓷的笑容,镌刻在它宽厚的内心里。
瓷器的高贵,在于它不仅是帝王将相、官宦士子的玩物,而且还走进了寻常百姓家。碗、盘、碟、盆、杯、盏、壶、盅、瓶、炉……充斥着每一户人家的厅堂或庭院,让瓷的身影变得更加温和,让瓷的名声变得更加洁净。一户人家,如果有了瓷的点缀,平淡的生活也可以过得风生水起。瓷既可以成为阳春白雪,也可以成为下里巴人。上需要仰视,下可慰民生,它的谦和、包容、内敛、敦厚,成就了它的高贵,也在华夏文明史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件瓷器就是一个故事。一件瓷器记载着一段历程。秀外慧中的瓷,犹如美人出浴,又似少女含羞,浅浅的一笑,就明媚了多少春光。
半幅山水,数句诗词,一颗印章,洇开的淡墨,含笑的牡丹,悠游的锦鲤,山间的小溪,吐蕊的红梅,吟唱的小鸟,在平平仄仄的瓷器上,绽放出最美的韵律。
瓷的儒雅、大方、深沉,让瓷盛水则澄澈如镜,泡茶则清香四溢,装酒则甘醇如饴。
在午后的庭院里,摆开一张小桌,用一只精致的瓷杯泡上绿茶,静静地享受身边淌过的轻风,让花香与茶香弥漫在小小的庭院里,这是文人雅士的情趣;在黄昏的夕阳下,围住一个火塘,用几个粗犷的瓷碗倒满烈酒,腾腾地点燃内心泛起的火焰,让豪情与血性挥洒在低矮的屋檐下,这是高原汉子的胸怀。有了瓷,情感的交流就有了载体;有了瓷,心意的表达就有了温度。
瓷的气质在于它的心胸。不高高在上,也不自居其下,它的目光是清澈的,它的胸襟是坦荡的。这正是泥土的气质与心胸。很多时候,我看到瓷,就会想到泥土。瓷因承接了地气,而彰显出生命的活力。摆在条桌上的花瓶,供在神龛前的香炉,躺在小几上的茶壶,放在火塘边的酒碗,处处透出诗一般的意境,让人心生向往。一件瓷器,就是一团火,点燃了期盼明天的眼神与目光。
瓷器在举手投足间,不经意间款款扭一扭柳腰,就让生活中处处充满了唐诗宋词的韵味。农家小院里的静坐,山野寺院旁的对弈,荒郊野岭间的聚会,高宅华堂中的吟哦,都有瓷或隐或现的身姿。向往瓷,就是向往内心的洁净;向往瓷,就是向往灵魂的高度。
滇西北的永胜小城盛产瓷器。那些烧制好的瓷器,在阔大的地面上铺开,慵懒,宁静,自由。永北的瓷,曾经随着马帮的路途穿越了万水千山,也曾在长长的茶马古道上栉风沐雨,它们把家乡的名声传遍了四面八方;它们在横断山层层叠叠的皱褶中,用洁净的釉光,照亮了先祖们坎坷而艰险的行程。
敦厚而圆润的瓷器,在碎裂时会拥有尖锐的疼痛。因此,人们都会小心地呵护着瓷,因为它的美丽与忧伤,因为它的沉静与儒雅。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宣纸上走笔至此搁一半/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被私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洇开了结局/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
《青花瓷》如泣如诉的旋律低回,让我在如痴似醉中想到了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瓷。仰望瓷器,就是在回望我们曾经走过的路,把生命中遇到的坎坷与痛苦悄悄埋葬,用瓷器的一抹亮光,陪伴着我们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