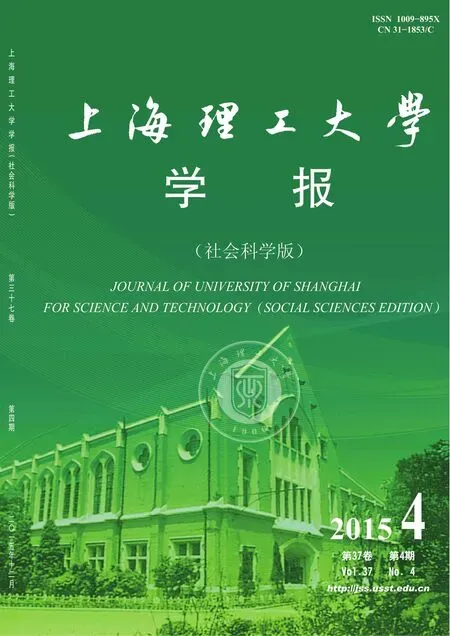中俄象征诗派“契合”观比较论
2015-04-02姚晓萍
姚晓萍
(浙江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杭州 310018)

中俄象征诗派“契合”观比较论
姚晓萍
(浙江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杭州 310018)
摘要:“契合”是象征主义诗学的核心所在,其哲学基础是“两个世界”的分开,而在中俄象征主义诗人的观念中,“两个世界”有不同的内涵,中国象征派诗人在潜在的心灵世界中寻求与客观世界的呼应,以期达到与万物冥合的境界,俄国象征派诗人则志于神秘的彼岸世界和永恒世界,在现实世界和神话世界的碰撞中形成了两种旋律,异质的“契合”观念决定了两种象征主义诗潮发展的不同路向。
关键词:象征主义;契合;两个世界
“契合”属于现代诗学美学范畴,它同时作为艺术表现手法和审美方式存在着。法国诗人波德莱尔通过一首诗《应和》赋予“契合”以不同凡响的意义,短短的十四行诗“带来了近代美学底福音”[1]80。“契合”论有三层内涵:首先,指人的各种感官之间相互交感的关系,这一点类同于“通感”的艺术表现技巧;其次,指人的内在心理世界与外在客观世界的感应交融,由修辞手段上升为审美意蕴;第三,指人的官感、精神世界与超验世界的契合,超越审美上升为哲学或宗教意义。
象征主义者认为,在可感的客观世界深处,隐藏着一个更为真实、永恒的世界,这就是波德莱尔所谓的“被揭示出来的天堂”,马拉美所谓的“抽象的领域”及兰波所谓的“未知”,人类只有凭本能的直觉才能领悟其中奥秘,而艺术地传达出这种秘密便是诗人的最高任务。
一、“两个世界”的哲学美学内涵
“契合”是象征主义诗学的核心所在,其基础是“两个世界”的分开,但在中俄象征主义诗人这里,“两个世界”有不同的内涵,决定了他们相异的“契合”观。
(一)物质世界与心灵世界
中国传统诗学讲究“境界”的生成,有“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之分。“境界”说的集大成者王国维有云:“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现代诗学在接受西方诗歌“经验”的影响下,以传统诗学为积淀,构筑了独特的“两个世界”。
穆木天的“纯诗”理论代表着中国象征主义的观念建树,他对于“纯粹诗歌”所阐发的“诗之物理学的总观”中,从诗的“先验”“律动”,认定所谓“纯诗”便是对灵感与潜在意识的强调,诗歌应是“纯粹的诗的Inspiration(灵感、感兴)”的表现,“诗的世界是潜在意识的世界”,诗人指出的纯粹的“表现的世界”,是所谓的“内生活”。诗的“内生命”的反射,是潜在的、无形的、在可知与不可知之间的深远的世界,是“诗的世界”,这一诗观如论者所言具有“西方象征诗美学存在的浓重的神秘色彩”[2]50,但仍可看作是新诗审美理想的古典再现,蕴有“疏影横斜水清浅”的朦胧之美。
穆木天提出的“潜在世界”是一种“情肠”,是“旋律”、“声音”、“光线”编织的“心灵世界”,它是外在世界在人的感性精神境域内的显现。由此,象征主义诗派人群在接受西方象征主义诗歌艺术影响的时候,努力寻求它与传统诗学之间的某种审美原则的“经验”。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新诗诗性的复活,但是其呈现的形态是片断式的,而非完整性的。
前人论及戴望舒的诗歌,也抓取其诗蕴含的合乎民族审美口味的“幽微精妙”发微知著:
戴望舒氏页(也,笔者注)取法象征派。……他也找一点朦胧的气氛,但然人可以看懂;也有颜色,但不像冯乃超那样浓。他是要把捉那幽微精妙的去处。[3]206
“幽微精妙的去处”如“镜中之花,水中之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这正是戴望舒毕生追求的“在表现自己和隐藏自己之间”的迷梦的境界。
梁宗岱作为法国象征主义诗学的中国传人,直接受惠于瓦雷里,在现代诗人中少见地触及了诗歌“超验”观这一话题,他曾指出:
有一派诗人,他底生命是极端内倾的,他底活动是隐潜的。他一往凝神默想,像古代先知一样,置身灵魂底深渊作无底的探求。[1]7
“内倾”正是外物世界对人的“心灵世界”的返照,它与西方“纯诗”理论神秘性相关联,梁宗岱对此有所感悟,他认为波德莱尔的《应和》“这首小诗不独在我们灵魂底眼前展开一片浩荡无边的景色——一片非人间的,却比我们所习见的都鲜明的景色;并且启示给我们一个玄学上的深沉的基本真理,即‘生存不过是一片大和谐’”[1]80,接近“超验”的真知,但他“受本土诗学和诗歌创作实践的影响,也有意或无意地对这种神秘性进行了消解”[4]142,从文艺传统与创造的关系着眼,中国象征诗终未进入神秘莫测的“彼岸世界”。
(二)现实世界与彼岸世界
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那里,真实的世界就是理念世界。现代西方思想界打破了柏拉图的魔咒,叔本华把康德主义和柏拉图主义及唯意志论相结合,宣称“世界是我的表象”,认为自然界是现象世界,人的意志才是存在的本质;尼采秉持非理性观,认为“只有作为审美现象,此在和世界才是永远有充分理由的”[5]19。从柏拉图,到叔本华、尼采等西方哲学家深深地影响了俄国诗人,这种影响从索洛维约夫开始。他发展了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柏拉图、奥古斯丁、谢林、黑格尔等人的思想,都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如他本人所说,对他影响最深的是康德和叔本华,在叔本华那里他“找到了……在他身上永不可磨灭的宗教需求的满足,他可以用宗教的观点理解生活和对待生活”[6]436。
俄国象征派诗人、理论家首先从“两个世界”开始建构他们的“象征”观。最主要的理论家别雷在《艺术形式》中说:“在一切宗教里都存在着我们的世界和另一个更好的世界之间的对立。”[7]199但这种对立并非不可跨越,其方式则是“象征”或“应和”。这种对立的世界结构图决定了俄国象征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神秘主义的,如瓦雷里所言诗人传达他所接受而未必了解的东西,这东西是“神秘的声音口授给他的”[8]37。可见,象征主义最终为了超越外在形式进入一个“理念”世界,这理念或者是诗人心中,包括他个人情绪和感情的理念;抑或是柏拉图的完美真实的超验世界的理念;甚或是斯威登堡意义上的宗教的神秘的彼岸世界。象征主义这种对神秘超验世界的追慕,使象征主义诗歌在获得形式自由的同时,又接受了一种更沉重的负担,即文学带着一种宗教仪式般的义务和职责,从而使文学自身变成一种宗教。因此可以说,“神秘主义和艺术对波德莱尔来说,只不过是同一种经验的两幅面孔”[9]。
勃留索夫的象征观,其主要的建构原则也是双重世界,他评价索洛维约夫的诗歌:“用索洛维约夫本人的术语来说,是存在两个世界:时间的世界和永恒的世界。前者是恶的世界,后者是善的世界。”[10]256他的诗作弥漫着对彼岸世界的想往和追寻。
我看不见我们的现实,
我不了解我们的世纪,
对我们祖国我也痛恨,
我只爱人的理想境地。
——《我看不见我们的现实》(顾蕴璞译)
诗人对现实世界极为不满,但他认为这只是时间史上必经的世界,而无论眼见的“现实”多么可恶,“世界”终将走向“预言的天堂”。诗人还把现实审美化,用奇特的想象构筑一个美的世界:
我在神秘的幻想中,
创造了一个天性完美的世界。
——《群山起伏》(黎皓智译)
现实与理想的对立,现实世界与完美世界的矛盾,贯穿在勃留索夫整个创作中。
诗人索洛古勃作为一个“厨娘的儿子”,饱经磨难,历经凄苦,但诗人宣称,“我撷取一段粗糙而贫乏生活,用它创造一个甜美的神话,因为我是诗人”(《创造的神话》宣言)。索洛古勃也否定现实世界,认为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个幻象。他对于尘世感觉无望,他嗟叹“活在人间多么累赘吃力”,“尘世间七情六欲的魅惑,/人生的欢乐我都已经看破。/什么战斗、节目和交易,/这一切喧闹是烟云而已”(《死神啊,我属于你!》),“在我的希望、信念之中,/没有辉耀,不见光芒”(《我生活在窄小的洞穴》)。于是他歌咏孤独、睡眠与流浪,他低吟:“世界上没有比睡眠更好的事物——它有它的美妙与宁静”,“永久的漂泊者今天在此处,/明朝在那里,重又去流浪,/我能为自己找到归宿”(《伏尔加河上》)。他的诗歌正是在两个不同的世界——现实世界和神话世界的碰撞中形成了两种旋律。
二、两个世界的契合
对“心灵世界”和“彼岸世界”的遁入,使中俄象征主义诗歌表现出“心与物冥”与“人神同一 ”的“契合”观。对诗歌“境界”的永恒追求使中国象征派诗人更关注“心灵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和鸣,更重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融通,俄国象征派诗人怀抱对“彼岸世界”的宗教向往,渴望现象世界中的“人”(诗人)与“神”合二为一,从而达至宗教神秘的精神界域。
(一)“心与物冥”的审美追求
“心”与“物”的关系是中国传统诗学的一个古老命题,也是中国象征主义诗学本体建构的一个核心问题。早在《诗经》开始,已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中“心灵”与“风景”的呼应,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专辟《物感》、《神思》等章论及,“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兴,物以情动”等都涉及心物关系问题。中国象征诗派植根于古典诗学传统,并接受波德莱尔、魏尔伦、马拉美、瓦雷里等西方象征主义影响,力图要达到的艺术境界是“心与物冥”、主客消融、天人合一。
“Correpondances”进入中国诗人的视野之时,经历了一番颇为焦灼的译介。1921年,田汉首译波德莱尔的《Correpondances》直接以“无题”代之,其后有穆木天译为“交响”,王独清译为“交错”,戴望舒、卞之琳译为“应和”,梁宗岱译作“契合”,还有“通感”、“交感”等等。
中国象征诗派对于新诗的直白浅露、过分注重写实的诗风甚为反感,穆木天曾如此回忆“五四”——“胡适先生一句一个‘白话’的讲演,听起来真令人生厌的”[11]238,并指责其提倡诗歌散文化,去掉了诗歌的审美内蕴,等于对诗歌的审美存在进行釜底抽薪。穆木天在《什么是象征主义》中指出:“声、色,熏香,形影,和人的心灵状态之间,是存在着极微妙的类似的。”[12]98这种“极微妙的类似”即是“人的心灵”与“诸样相”之间“冥合”的基础,穆木天《旅心》的诗句恰如“心”与“物”的“交响”:
落花掩住了藓苔 幽径 石块 沉沙。
落花吹送来白色的幽梦到寂静的人家。
落花倚着细雨的纤纤的柔腕虚虚的落下。
落花印在我们唇上接吻的余香 啊!不
——《落花》
“落花”、“藓苔”、“幽径”、“细雨”诸样景致无一不浸染着诗人的迷濛的愁绪,充溢着“游人不问春将老,来往庭前踏落花”的惋惜,“心”随花“落”,“花”落“心”幽,诗人把心物“交响”说美妙地实践在自己的创作中。然而,在梁宗岱看来,还未达到真正的“心与物冥”。梁宗岱针对朱光潜在《谈美》中说的拟人托物都是象征,“所谓象征就是以甲为乙的符号……”[13],其根本的错误在于把文艺上的“象征”和修辞学上的“比”混为一谈,依此论,穆木天笔下的景物仍显“固着我的色彩”,“落花”与“我”依然“各存本来的面目”,不算“象征底最高镜”。梁宗岱总结道:
象征之道,曰“契合”而已。[1]77
戴望舒化用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经验,粉墨浓重的古典诗词色彩,“为自己制了一双合脚的鞋子”。在《印象》一诗中,“幽微的铃声”耳闻已浅,“烟水”中的“小船”目视约隐,心境与物象化合为幽渺绵薄的灵境,诗意随“轻缓的音波”、“芳馥的外形”宛转,“营造出空灵的艺术境界,意化人象,象呈意境,情语景语合而为一”[14]144,渗透着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艺术精神。相比于20年代的象征主义诗歌,30年代的“现代”诗歌“显得更超脱、更轻盈,戴望舒也是一个典型,他们的诗歌含蓄又飘逸,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国读者的审美要求,实际上形成了新诗的诗意传统”[15]13。
卞之琳主要受泽于魏尔伦、瓦雷里、里尔克等诗人,“化欧”“化古”均见长。在理论和创作中始终践行“亲切与暗示”的长处,对于外物,“亲切”始能融入其中,“暗示”方可超然于外,“圆宝盒”装了“我的幻想”,又“掩有全世界的色相”(《圆宝盒》),“你”和“别人”掩映于 “窗”、“月”、“梦”融和的“风景”里(《风景》),如他翻译的瓦雷里的一首诗,“我把美酒洒在海水里面,酒消失了但味道还存在”,要在有形的世界中把握无形的东西,提炼、抽象、升华到“心物冥合”的灵境。
从本质上说,中国新诗接受象征主义的“契合”论有其独特性。象征主义的“契合”论本质上是一种“超验本体论”的神秘诗学,而中国新诗的“契合”论尚止于一种审美方式的范畴。梁宗岱提出的“宇宙意识”已经切近于波德莱尔、兰波等所谓的“超验世界”,但止于译介,并未实践。
(二)“人神同一”的精神旨归
在波德莱尔那里,“应和”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诗学方法和辞格,并不是或主要不是人的生理感官的同构现象,而是一种诗学主张、美学原则和世界观。俄国象征诗派在“契合”的论题上更接近于法欧象征主义,他们在建构起“人神同一”象征主义诗观。
别尔嘉耶夫谈到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俄国,“俄罗斯经历了诗歌和哲学的繁荣,经历了紧张的宗教探索,感受了神秘主义和通灵术情绪”[16]215。文化的复兴伴随着宗教的复兴,俄国象征派反叛现实主义的同时,成为神的寻求者、神秘主义者以及基督教改革者,他们与各派哲学家及神学家合作展开一个宗教运动。
在俄国象征诗派集体皈依宗教的倾向中,梅列日科夫斯基显得有些特别,“梅列日科夫斯基达到了基督教,但不是达到传统的,也不是达到教会的基督教,而是达到一种新的宗教意识”[19]219。在梅烈日柯夫斯基看来,象征是圣灵降临的过程和人灵在这一过程中的“心像火一样地燃烧”,以至于“现在担当不了”,象征世界的构成是基督的临世。“梅烈日柯夫斯基的象征主义不仅与神秘主义有别,也与其他象征主义有本质区别人而神与神而人的区别。”[17]77他在一首题为《上帝》的诗中写道:
我活着的时候——我就向你祈祷,
我挚爱着你,我因你而呼吸,
我死的时候——与你融为一体,
像星星融进初露的晨曦。
(汪剑钊译)
诗行间充满寻神的激情,渴求“人神合一”的新宗教的意旨,他比伯雷蒙“诗歌接近于祈祷”更甚,认为诗歌就是一种“祈祷”,人与神通过诗歌融合起来。与诗人共同致力于“自我神化”使命的还有他的妻子吉皮乌斯。
吉皮乌斯的诗富有音乐性、哲理性和抒情性,她在作品中“表现出对现实生活的迷惘,对悲哀、空虚的哀叹,对超验世界的描绘,对现实世界的怀疑以及对另一种‘不可知的真实’所表现出的信念和追求,还有在追求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主观神秘色彩,即宗教自我主义”[18]133。她最为著名的抒情诗《歌》,唱出了诗人迷惘的心灵:
哦,让虚无的东西成为现实,
让虚无成为现实。
苍白的天穹允诺显露奇迹,
允诺显露奇迹。
(汪剑钊译)
诗人悲怆的心迹弥漫在字里行间,“现实”使人厌倦,使人绝望,“天穹”显露“奇迹”成为永远的不可能,现世本就“虚无”。她还将“自我”圣洁化,无限向上帝靠近。吉皮乌斯的诗歌宗教意识异常强烈,据统计,在她的前两本诗集161首诗中,涉及宗教和上帝的就有50首之多,其中有11首诗是直接用祈祷的形式写的。在象征主义者眼里,所谓的现实世界不是“本真”境界,“理念的领域”是绝对性的庙宇,是唯一的“神袛”,是象征主义诗歌指向的最高境域。
三、结束语
如果我们从源头去寻找“契合”论的根基,那么要追溯到瑞典神秘主义者斯威登堡。“应和”概念发扬了柏拉图主义和中世纪宗教象征主义精神,也受到叔本华“唯意志论”和柏格森“直觉论”的影响,与瑞典神秘主义者E·斯威登堡的两个世界观也有较为直接的关系。斯威登堡认为自然万物之间,自然与人之间或人的各种感觉之间都存在神秘而内在的对应关系。由此可见,波德莱尔运用通感手法、发挥“应和”审美观的直接基础正在于此。其他象征主义诗人也认为感性世界与理性世界或神秘的超现实世界之间是对应的,因此,把诗歌与宗教和人类内在心灵联结起来,是象征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
参考文献:
[1]梁宗岱.诗与真[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80.
[2]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0.
[3]罗成琰.朱自清絮语[M].长沙:岳麓书社,1999:206.
[4]欧阳文风.通向感悟:梁宗岱对西方纯诗理论的醇化[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2):139-142.
[5][德] 尼采.尼采散文[M].杨恒达,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19.
[6][俄] 格奥尔吉耶娃.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代[M].焦东建,董茉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436.
[7]黄晋凯,张秉真,杨恒达.象征主义·意象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99.
[8]伍蠡甫.现代西方文论选[M].朱光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37.
[9]Lehmann A G,Phill M A D.The Symbolist Aesthetic in France,1885—1895[M].Oxfoxd:Basil Blackwell,1974:32.
[10]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第二册)[M].谷羽,王亚民,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256.
[11]穆木天.穆木天诗文集[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5:238.
[12]陈惇,刘象愚编选.穆木天文学评论选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98.
[13]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二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64.
[14]杨思聪.感应与冥合:中西象征主义诗论比较[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26(6):140-146.
[15]姜涛,张洁宇,张桃洲,等.困境、语境及其他——关于诗歌精神的讨论[J].中国诗歌研究动态(第三辑),2007:1-25.
[16][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M].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215.
[17]刘小枫.象征与叙事——论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象征主义[J].浙江学刊,2002(1):68-81.
[18]吴笛.论俄国象征主义的独创性[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34(4):131-136.
(编辑: 巩红晓)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oncept of “Correspondence” in Sino-Russian Symbolism PoemsYao Xiaoping
(Finance & Economics Oriental College,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China)
Abstract:“Correspondence” is a core concept in poetic symbolism,whos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lies in separation of “Two Worlds”.In Chinese and Russia poetic symbolism,the phrase of “Two Worlds” has different connotations:Chinese Simplistic poets seek for potential spiritual world with echoes of the objective world to achieve the realm of unity;while Russian Simplistic poets focus on both mysterious world and eternal world,forming two melodies in the collision of the real world and the world of myth.The heterogeneity in the form of “correspondence” has determined different development directions of two poetic symbolisms.
Keywords:Symbolism;correspondence;Two Worlds
DOI:10.13256/j.cnki.jusst.sse.2015.04.009
中图分类号:I 106.2; I 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95X(2015)04-0345-05
作者简介:姚晓萍(1978-),女,讲师。研究方向: 中俄文学比较。E-mail:yxp@zufe.edu.cn
基金项目: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研究课题(2010B24)
收稿日期:2014-0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