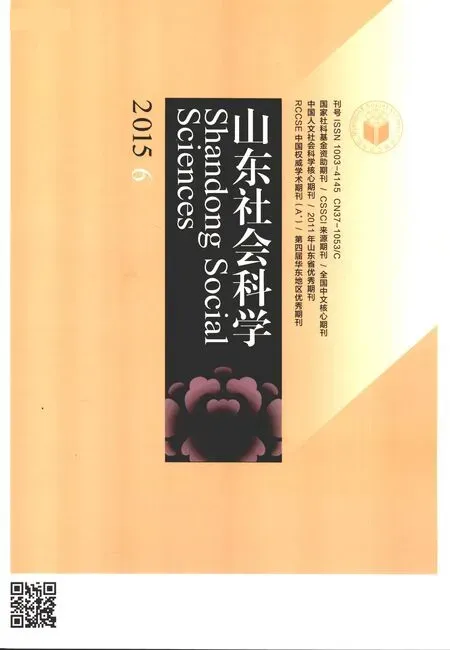刑法谦抑主义与规制缓和
——以日本金融犯罪的规制为鉴
2015-04-02张小宁
张小宁
(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山东威海 264209)
刑法谦抑主义与规制缓和
——以日本金融犯罪的规制为鉴
张小宁
(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山东威海 264209)
刑法谦抑主义主张以刑法作为保护法益的最后手段,只有在其他手段用尽但仍不能保护法益时才适用刑罚。这在金融犯罪的规制领域中体现地最为明显。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并促进本国金融市场的自我完善,近年来,日本将“规制缓和”理念运用到了金融犯罪的预防与惩处之中。该理念主张放宽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希望以行业自律实现对金融市场的控制,从而增强其自主性与自控力,并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和危机应对力。具体到金融犯罪的处置问题,该理念认为应当建立经济预防、行政制裁、刑罚与民事责任追究相结合的整体性规制模式,并且应当更多地运用非刑罚措施来预防和惩处金融违法行为,而仅针对最为恶劣的行为科处刑罚。换言之,在金融犯罪的规制方面,刑罚的适用应当更为谨慎与消极。而这正是刑法谦抑主义的体现。
刑法谦抑主义;规制缓和;金融犯罪
一、刑法谦抑主义与金融犯罪的制裁
刑法谦抑主义认为:刑法并不是保护法益的最初手段,也不是保护法益的唯一手段,甚至不是保护法益的最好手段。换言之,在保护法益时,应当尽可能地运用非刑罚措施,只有这些措施都已用尽但仍不能保护法益时,才适用刑法。刑法谦抑主义要求刑法应当具备补充性、二次规范性(宽容性)与片断性三个基本特征。①[日]平野龙一:《刑法総論Ⅰ》,有斐阁1970年版,第47页将刑法谦抑主义概括为“补充性”、“谦抑性”与“片断性”。其中的“谦抑性”意即“二次规范性”。[日]浅田和茂:《刑法総論[補正版]》,成文堂2007年版,第47页;[日]松宫孝明:《刑法講義総論[第4版]》,成文堂2009年版,第15页都总结为“补充性”、“二次规范性”与“片断性”。而[日]铃木茂嗣:《刑法総論[第2版]》,成文堂2011年版,第9-10页总结为:“补充性”、“片断性”、“宽容性”,铃木教授将其中的“宽容性”与“可罚违法性”相联系加以解释。同样的,[日]川端博:《刑法総論講義[第2版]》,成文堂2006年版,第55页也将刑法谦抑性解释为“补充性”、“片断性”与“宽容性”。该理论最早由边沁提出,边沁认为不应当适用刑罚的类型有四种:滥用刑、无效刑、过分刑、昂贵刑。②吉米·边沁:《立法理论》,李桂芳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3-374页。据此,日本学者认为,在运用刑罚时应当考虑如下四个条件:(1)是否存在受害;(2)动用刑罚是否引发严重的副作用;(3)刑罚以外的制裁手段是否可以制止该行为;(4)发动刑罚的成本是否过于高昂。③[日]林干人:《刑法総論[第2版]》,东京大学出版会2008年版,第24页。尤其是其中的第3个条件,鲜明地体现出了刑法谦抑主义的要求。与之相应,中国学者认为刑法的谦抑性包含三层思想内涵:(1)刑法调整范围的不完整性;(2)刑法统制手段的最后性;(3)刑罚制裁方式发动的克制性。④莫洪宪、王树茂:《刑法谦抑主义论纲》,《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1期。
德日刑法学一般将刑法谦抑主义列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①关于刑法谦抑主义即补充性或从属性与刑法的独立性的关系问题,前瞻性的论著有布伦斯的《从民法的思维中解放刑法》:Bruns,Die Befreiung des Strafrechts vom zivilistischen Denken,1938.日本学者则多在自己的刑法总论教科书中探讨这一问题。例如,[日]木村龟二:《刑法総論》,有斐阁1959年版,第71-72页,[日]藤木英雄:《刑法講義総論》弘文堂1975年版,第4页,[日]佐伯千仞:《四訂刑法講義(総論)》,有斐阁1981年版,81页。但[日]西原春夫:《刑法総論》,成文堂1978年版,第434页是在刑罚论部分谈到了刑罚的谦抑主义,似乎将其理解为刑罚的适用原则而非刑法的基本原则。,因此,该理论可以适用于刑法的各个领域。但在实际上,目前最成功的适用领域是金融违法犯罪的预防与惩治。原因如下:首先,金融犯罪属于法定犯,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时并不违反加罗法洛提出的“正直之心”与“怜悯之心”,换言之,金融犯罪的行为人并不具有自然犯的“自体恶”,不会产生强烈的罪恶感,也不容易因此而引发停止犯罪的“反对动机”。其次,既然金融犯罪人不会出现“反对动机”,那么,通过科处刑罚使之放弃犯罪的效果也不会理想。换言之,费尔巴哈主张的“心理强制说”在预防金融犯罪时的作用是受到限制的。再次,金融犯罪往往会获得巨额的不法利益,而刑法关于金融犯罪的法定刑一般较低。即,犯罪收益远大于犯罪后果,因而也刺激了犯罪人铤而走险。最后,金融犯罪的实行更为隐秘,获得犯罪证据的难度更大,犯罪人逃脱刑罚处罚的可能性也更大,而这也容易诱发犯罪。鉴于此,在金融犯罪的预防与惩处方面,美国、日本等金融监管体制发达的国家更倾向于采用非刑罚的制裁措施。即,更多地运用罚款、市场禁入决定、吐出违法所得等非刑手段,而只有在出现极为恶劣的犯罪行为时,才会诉诸刑罚。例如,美国法中规定了民事罚款(Civil Penalty)、民事没收(Civil forfeiture)、行政没收(Administrative forfeiture)、停止违法行为、吐出违法所得、三倍赔偿制度以及惩罚性赔偿制度等。而日本则规定有反则金②日文为“反則金”,是指作为罚金的替代措施而广泛地适用于轻犯罪行为与行政违法行为的罚款。其涵义与功能类似于中国法中的行政罚款,但适用范围广于后者。、课征金③日文为“課徴金”,意为“罚款”,最早出现于1977年制定的《反垄断法》中,目前是较广泛地适用于经济违法犯罪行为中的处罚措施。、加算税、加算金、取消或停止许可、公布等制度。因此,当金融犯罪事件被揭发时,监管机关并不是一味地追求严刑峻法来解决问题,而是首先考虑采用上述非刑措施加以处理。因为刑法终究是保护生活利益的最终手段,正因此,绝不能否定慎重适用刑罚这一问题。④[日]芝原邦爾:“行政の実効性確保――刑事法の視点から”,载《公法》第58号第259页(1996年)。也因此,在预防与惩治金融违法犯罪时,如何构建更合理的非刑措施来代替刑罚的问题,一直是经济刑法学研究的热点。
二、“规制缓和”理念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受泡沫经济崩溃的影响,日本金融业界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日本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改革方面提出了“规制缓和”理念。该理念的基本目的在于:实现经济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推进国际化,建立以自己责任与市场原理为基础的自由并且公正的经济社会,与此同时,在行政领域中实现由事前规制型行政向事后校验型行政的转变。⑤[日]佐伯仁志:《制裁論》,成文堂2009年版,第33页。在缓和与撤销不必要的事前规制的同时,日本政府也在为了自由且公正的经济社会积极地设置必需的规则。⑥[日]佐伯仁志:《制裁論》,成文堂2009年版,第33页。从改革规则的角度来看,一般也将“规制缓和”称为“规制改革”。
在金融犯罪的预防与惩处方面,日本目前的动向在于尽可能地采用非刑措施加以处理,而当出现重大的犯罪事件时,则诉诸刑罚。简言之,力图实现一种“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处理效果,而这正是刑法谦抑主义的体现。因此,虽然次贷危机的冲击也曾导致日本金融市场的激烈动荡,并由此引发了新一轮的投机狂潮,但日本金融商品交易委员会却仍坚持以民事与行政制裁作为主要的惩处手段,而进入刑事程序的案件极为少见。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日本金融市场经受住了次贷危机的考验,也借此提高了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因此,在金融犯罪领域中,关于如何审慎地适用刑法,如何利用非刑措施预防与惩处犯罪,如何促进市场以及市场主体实现自律等问题,日本的“规制缓和”理念颇有值得借鉴之处。
从处置金融犯罪的角度来看,“规制缓和”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⑦参见[日]佐伯仁志:《制裁論》,成文堂2009年版,第33页。(1)刑法处罚范围的变化,其中又包括去犯罪化现象与犯罪化现象两个方面。关于去犯罪化现象的典型例子是,修订后的《外汇及外国贸易法》实现了外汇业务的完全自由化,原本用于限制外汇业务的刑罚规定被完全删除。关于犯罪化现象,例如内幕交易行为被明文规定为犯罪,再如,毒品犯罪所得的洗钱行为也被规定为犯罪。(2)针对恶劣的金融犯罪行为,制裁手段进一步强化。例如,垄断行为的罚金额上限提升至五亿日元。此外,关于民事罚款的引入问题,已经在《反垄断法》、《金融商品交易法》、《环境法》、《劳动基准法》、《食品卫生法》、《建筑基准法》、《消防法》等的立法修订工作中展开了研讨。(3)规则的进一步明确化。为了实现从事前规制型行政向事后校验型行政的转变,对于金融刑法法规中的带有过度干预性质的条文以及含义不甚明确的条文,进行了相应的修订与删减。下文将对以上三个方面分别展开详细的分析。
三、“规制缓和”理念与刑法处罚范围的变化
如上所述,“规制缓和”导致的刑法处罚范围的变化可以分为去犯罪化现象与犯罪化现象两个方面。
(一)“规制缓和”引发的去犯罪化现象
“规制缓和”对于刑法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去犯罪化现象,具体是指,由于各种事前规制措施被撤销或废除,原本用于保障这些事前规制措施之实效性的刑罚法规也随之被删除。①[日]佐伯仁志:《制裁論》,成文堂2009年版,第33页。例如,在此前,当从业者申请参与金融交易时,其从业资格会受到严格的审查与限制,稍有不慎违反规定时,便可能受到行政刑罚的惩处。而伴随着从业资格审查机制的放宽与限制条件的取消,相应的行政刑罚规定也被废止或修改。其典型事例是《外汇及外国贸易法》的修订。关于外汇业务的申办,该法历经了一个由严格限制到完全放开的发展过程。具体如下: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受战时经济体制的制约,日本对于外汇业务实行严格的管控。1932年制定的《防止资本逃避法》首次确立了外汇监管机制。虽然该法随即便被废止,但取而代之的《外汇管理法》却对外汇业务进行了更为严格的控制。而在二战结束后的经济紊乱与低迷时期,为了稳定外汇市场、防止资本外流,日本又制定了《外汇及外国贸易管理法》,对于外汇业务实行“原则禁止,例外批准”的管控模式。直到七十年代末,因为外汇业务日渐兴盛,其管理体制也日趋完备,日本才对《外汇及外国贸易管理法》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对于支付的限制措施被大量删除,与之相伴的刑罚法规也被删除。因此,违法事件的揭发数目也急剧降低。②[日]鶴田六郎:“経済取引をめぐる各種経済関係法令違反事件”,载石原一言编:《現代刑罰法大系(2)経済活動と刑罰》,日本评论社1983年版,第132页。但是,受当时的金融经济背景的制约,此次修订难言彻底。具体而言,限制外汇业务的根本制度如外汇公认银行制度③只有经大藏省大臣授权的银行才可以开展外汇业务。类似于中国目前仍在实行的严格的外汇业务管控制度。、指定证券公司制度④日本国内投资者的对外证券投资以及外国投资者的对日证券投资必须提出事前的申请。该制度目前已被废止。以及兑换商制度⑤除经授权开展外汇业务的银行外,其他的金融机构如欲从事外汇兑换业务,必须取得相应的许可。该制度目前已被废止。等依然保留,而作为上述制度的保障措施的相关刑罚规定也继续有效。⑥[日]佐伯仁志:《制裁論》,成文堂2009年版,第34页。
进入九十年代之后,金融大爆炸时代⑦始于指英国在1986年由撒切尔政府领导的伦敦金融业政策变革,该变革旨在大幅度减少政府监管。改革后,伦敦金融城引入了更具国际化的管理作风,电脑和电话等电子交易方式取代了传统的面对面交易,金融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剧增。受此影响,日本金融市场于2001年正式启动了类似改革,核心是通过放松金融管制,促进金融自由化,其主要的法律依据是《外汇管理法》和《日本银行法》,业界一般称之为“东京大爆炸(Tokyo Big Bang)”。到来,国际金融一体化进程飞速发展,欧美各国要求日本加快实现外汇业务的完全自由化。因此,1997年,日本对《外汇及外国贸易管理法》进行了全面的修订,法律名称也变为《外汇及外国贸易法》。虽然名称中仅仅删除了“管理”二字,但却标志着外汇的监管理念实现了从“业者规制”向“市场规制”的转变。而在法律的内容方面,通过此次的全面修订,繁杂的营业许可程序被简化,限制营业资格主体的外汇公认银行制度等都被废止,与之相对应的刑罚法规都被废止,从而实现了外汇业务的完全自由化。而这一全面修订被认为是“规制缓和”理念在外汇领域的完胜,也标志着该理念开始在日本金融业界发挥主导作用。
(二)“规制缓和”引发的犯罪化现象
在金融犯罪的惩处方面,“规制缓和”理念强调改变以往的行政前导型控制模式而代之以市场自律型控制模式,为了保证市场自律机制的完善,首先需要的便是市场的公正化、透明化与健全性。那么,对于可能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尤其是危害严重的扰乱行为,便应当作为犯罪惩处。因此,首先,在反垄断领域,《反垄断法》中的适用除外制度被废止或被压缩,垄断行为受到了更为严格的管控。与之相适应,违反管控规定时的刑罚法规也增加了。
其次,在金融商品交易领域,旧《证券交易法》制定之初,并未将内幕交易行为规定为犯罪。虽然旧《证券交易法》第57条第1号也仿照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0条b项设定了关于禁止证券欺诈的一般性条款,但该条款的适用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因此,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在日本的金融商品交易市场上,内幕交易一直处于无法无天的状态。也正因此,进入八十年代后,当日本的金融市场和欧美开始接轨时,立刻便受到了此处是“内幕人员的天堂”的讥讽。直到1987年,终于出现了轰动全国的“塔泰豪化学工业事件”①日文为:“タテホ化学工業”。塔泰豪化学工业股份公司因债券期货投资经营不善而出现了280多亿日元的巨额亏损,在信息公布前,该公司的3名董事、2名大股东以及与公司有业务往来的阪神相互银行抛售了相关股票,大阪证券交易所对事件进行了调查,但因证据不足,加之证券交易法中欠缺内幕交易的规定而最终不了了之。。有鉴于此,关于内幕交易罪的制定工作终于提上了日程。首先,证券交易审议会提交了“关于内幕交易的规制方法”的报告。②[日]竹内昭夫:“インサイダー取引規制の強化(上·下)”,《旬刊商事法務》第1142号、1144号(1988年)。该报告的特色在于:以针对内幕交易的实效性的对应为出发点,将重点放在内幕交易的未然防止体制的整备问题上。其主要内容包括两部分:未然防止体制的整备与行政对应。③[日]横畠欲介著:《逐条解説インサイダー取引規制と罰則》,商事法务研究会1989年版,第4页。此外,关于刑事罚则的整备问题,报告中指出:(1)虽然针对内幕交易可以适用证券交易法第57条第1号的规定,但为了更为有效地规制内幕交易,还是应当设定相应的刑罚规定;(2)为了保证正当的交易活动不受阻碍,从将刑事处罚限定于合理且妥当的范围内的观点出发,应仅对真正值得处罚的行为设定罚则。④[日]横畠欲介著:《逐条解説インサイダー取引規制と罰則》,商事法务研究会1989年版,第4页。以上述报告为基础,证券交易法的修正案得以通过,内幕交易罪被明文化。
此后,2006年6月,日本国会再次对证券取引法进行了大幅度修订,并更名为《金融商品交易法》。此次大幅度修订的背景在于: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自此,日本经济历经了10余年的低迷期,为了弥补这“失去的十年”,有必要改革原有的过度依赖银行以作为经济增长支柱中心的金融机构,克服不良债权大量积压的现状,营造能使金融市场灵活运转的金融体系,刺激民众的理财方式由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该法主要特色为“包括化·横断化”、“柔软化”、“公正化·透明化”、“严正化”。⑤[日]松尾直彦、岡田大、尾崎輝宏:《金融商品取引法制の概要》,《商事法務》第1771号(2006年)。而隐藏在上述特色背后的立法理念正是“规制缓和”。而在该理念的影响下,2014年《金融商品交易法》又一次做了较大幅度的修订,其修订的指导思想仍在于通过促进市场的活性化与提高投资者对市场的信任度来提供日本金融资本市场的完善与发展。例如,关于上市公司持有大量股票时的报告义务问题,本次修订将持有自己公司股票的情形做例外处理。此外,当上市公司在流通市场上开示虚假文书时,关于该公司的损害赔偿责任,原先的法律中规定为无过错责任,但修订的法律规定为过错推定责任。上述缓和措施都是为了保证资金能够在资本市场上更为顺畅地流动,但并不意味着放松了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因为实践已经证明,课征金制度以及内部统制报告制度等规制措施的完备已经足以发挥遏制相关违法行为的作用。再者,在损害赔偿请求方面,原先的法律仅规定“取得者”即保有证券者可以提起诉讼,但修订后的法律规定除了“取得者”之外,“处分者”即已经卖出证券者也可以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
最后便是洗钱罪的修订。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公约》要求各缔约国将毒品犯罪所得收益的洗钱行为规定为犯罪。因此,日本在1991年制定的《毒品特例法》中增设了处罚毒品犯罪所得收益的洗钱行为的规定,并且规定了金融机关的可疑交易报告义务。虽然金融机关违规不报告时不会受到刑法的处罚,但监督机关可以命令其改善业务的命令,并且在违规行为严重时命令其停止业务。此外,根据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FATF)的意见,日本在1999年制定的《有组织犯罪处罚法》中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进行了拓展。此后,2007年,日本又制定了《关于防止转移犯罪收益的法律》,并将可疑交易报告业务的监督权转交给警察厅的防止转移犯罪收益管理官(JAFIC:Japan Financial Intelligence Center)行使。⑥[日]山口厚:《経済刑法》,商事法务2012年版,第121页。受此影响,可疑交易的报告件数也急剧增多,例如,1998年时仅有10件,而2007年时便激增为15万8041件。⑦[日]佐伯仁志:《制裁論》,成文堂2009年版,第36页,第37页注释(补1)。关于洗钱罪与“规制缓和”的关系问题,有学者认为:在规制洗钱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规则的大背景下,可以看到因经济交易的规制缓和而引发的正常经济与非正常经济的融合现象,为了保证经济社会的健全性,必须防止被犯罪污染的资金流入市场,而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准则。在该意义上,将犯罪收益屏蔽在市场之外的做法便是确保规制缓和后的市场的健全性的基本条件,而金融机关的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等也成为了保障市场健全性的重要手段。①[日]佐伯仁志:《制裁論》,成文堂2009年版,第37页。
四、“规制缓和”理念与惩治手段的改进
(一)改进惩治手段的指导思想
在金融违法犯罪的惩治方面,“规制缓和”理念强调如下两点:(1)从刑法谦抑主义的角度出发,应当审慎地发动刑罚,更多地利用行政制裁等非刑措施处理。并且,还需要通过“合规计划(Compliance Program)②从2002年开始,德国的巴斯夫股份公司(BASF SE)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计划,主要包括在巴斯夫价值观和原则基础上建立的“行为准则”、外部第三方热线、员工合规培训以及定期的沟通交流等内容。其主旨在于让每一位员工都了解他们的道德价值观并遵守法律方面的政策,保证其价值观能够有效地被员工在工作中予以体现。”等经济措施实现预防。(2)出现严重的金融犯罪时,则毫不犹豫地科处刑罚。并且,为了防止再犯,在实刑方面,刑罚的严厉程度进一步加强,以便震慑蠢蠢欲动者,更好地发挥刑罚的一般预防效果,而在财产刑方面,适用方式要更为灵活,罚金刑的数额也进一步提高,以期望更有效地剥夺犯罪人的再犯能力。
(二)改进惩治手段的理由
关于惩治手段的改进问题,一般认为其理由在于如下三点:(1)保护法益的重新审视;(2)市场参与主体的增多;(3)犯罪收益的增加。③[日]佐伯仁志:《制裁論》,成文堂2009年版,第39-40页。首先,关于保护法益的重新审视问题。一般认为金融犯罪属于法定犯,其保护法益比自然犯中的保护法益更为抽象,例如,在证券交易罪中,一般认为“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秩序是重要的法益。伴随着由行政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规制模式的转变,交易秩序的要保护性也被提到了更高的高度。为此,修订后的《反垄断法》与《金融商品交易法》都更明确地提出了保护竞争秩序的立法目的。而作为其保障手段的课征金与罚金的上限也被大幅度地提升了。其次,关于市场参与主体增多的问题。因为参与市场的资格限制被逐步取消,参与者的增多必然带来更为复杂的监管问题,况且,恶意投资者也必然会浑水摸鱼。因此,“公平、公正、公开”的信息开示制度等变得更为重要。也因此,企业决算公开制度也变得更为重要,而违反该制度的刑罚也变得更为严厉。例如,提交虚假记载有价证券报告书罪的法定刑在短短的几年之内被连续提升,自然人犯本罪时的刑罚由最初的单处或并处三年以下惩役或三百万日元以下罚金,提升为五年以下惩役或五百万日元以下罚金,并进而提升为十年以下惩役或一千万日元以下罚金,而针对法人的罚金刑则由三亿日元提升为五亿日元并进而提升为七亿日元。而在事后的监理机制方面,金融从业人员违反报告义务以及妨害检查等行为的法定刑也被提升。例如,经过修订的银行法规定,不向监管机关报告或做虚假报告时(第63条第2号),或者妨害监管机关的检查时(第63条第3号),自然人的法定刑由原来的五十万日元以下罚金提升为一年以下惩役或三百万日元以下罚金,而法人的罚金刑则由原来的五十万日元以下飙升为两亿日元以下。最后,正是由于犯罪收益增加,以往的财产刑已经完全不能起到抑制犯罪人产生犯罪动机的功能。所以,如上所述,在反垄断、金融商品交易以及银行业这些最为关键的金融领域中,法定刑尤其是罚金刑都被大幅度提升了。
(三)改进惩治手段的方式
改进惩治手段的首要方式便是非刑措施尤其是行政制裁手段的灵活适用,其次是针对严重的金融犯罪更多地适用财产刑。
1.非刑措施的灵活适用
根据刑法谦抑主义,财产性制裁并不一定要适用刑罚,还可以考虑更积极地适用行政制裁措施。因此,有研究者指出:日本关于金融违法犯罪的立法修订方向应当是改变目前的罚款制度,引入更具实效性的民事罚款制度,而仅在民事罚款无法充分发挥作用时才适用刑罚。④[日]佐伯仁志:《経済犯罪に対する制裁について》,《法曹時報》第53卷第11号(2001年)。民事罚款制度源于英美等国,在证券违法犯罪领域中早已被广泛适用,特别是在惩治内幕交易事件时,英美等国认识到传统的依靠刑事制裁的规制方法无法发挥充分的抑制效果,因而大量地适用该制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①[日]川口恭弘、前田雅弘、川濱昇:《インサイダー取引規制の比較法研究》,《民商法雑誌》第125卷第4·5号(2002年)。原因在于:刑罚的发动依赖于刑事司法程序,手续繁琐且举证困难,而民事罚款的处罚程序由具备专业知识的监管部门发动,程序简便并且举证难度低。因此,在反垄断、金融商品交易、环境治理、食品卫生、劳动基准、建筑基准乃至消防法等领域中,日本已经开始研讨引入民事罚款制度的可行性与途径。
而在犯罪收益的剥夺方面,除了刑法规定的没收与追征等刑罚外,课征金制度已被证明是有效的手段。该制度最早出现在《反垄断法》中,此后,《金融商品交易法》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制裁经济犯罪的主流改革方向应当是民事罚款与课征金制度的并用。②参见[日]神山敏雄:《日本の経済犯罪――その実情と法の対応[新版]》,成文堂2001年版,第114-117页。除此之外的非刑措施还包括:各监管机构实施的注销营业资格、命令停止营业、停止投标资格、违反者名单公示等,以及该经济团体例如证券从业协会做出的过怠金决定③日文为:“過怠金”。针对违反协会规约的证券公司,由证券从业协会做出的罚款决定。、停止交易决定与除名决定等。此外,还有研究者认为:应当仿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举报奖励制度”④以监控内幕交易为例,证券交易委员会将内幕人员每月提交的交易情况全部录入计算机,然后制作电子复印件,公开出售,并规定成功举报者可以获得丰厚的奖励。如此一来,内幕人员的交易情况就会被任何买主得知,很多律师会自愿地去追查其违规行为,证券交易委员会便可以坐等律师们带着收集的证据送上门来。所以,美国称律师为证监会的“看门狗”(watch dog)。但通过这种方法,内幕人员处处受到监控,根本无法实施内幕交易。,并完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从而刺激普通投资者积极地参与监管工作。
2.财产刑的灵活适用
针对金融犯罪,自由刑的处遇效果其实并不理想。虽然美国法针对白领犯罪也大量地适用自由刑,但日本法却并未如此。其理由可以归结为如下四点:(1)经济犯罪的保护法益大多是交易公正或交易制度秩序的维持等抽象法益,从罪刑均衡的观点来看不宜处以过重的刑罚。(2)在许多经济犯罪中,犯罪人都是为了本公司的利益实施犯罪,因此,主要责任应由公司承担,即使是要追求犯罪人的责任,也不应课以过重的刑罚。(3)对经济犯罪人科处自由刑时,效果往往过于残酷。因为自由刑给受刑人带来的痛苦会因人而异。即使刑期相同,但有前科的暴力团成员与普通白领遭受的痛苦却有天壤之别。(4)日本目前的刑事政策重视特别预防,因此,对于再犯可能性较低的白领而言,除去从罪刑均衡与一般预防的角度出发认为必须课以自由刑的情形外,实在没有必要将其投入监狱。⑤[日]佐伯仁志:《制裁論》,成文堂2009年版,第41-42页。所以,在金融犯罪领域,应当更为积极灵活地适用罚金刑。
关于适用罚金刑是否会导致刑罚功效降低的问题,研究者认为大可不必担心。原因在于:如果刑罚的本质在于让受刑人感到痛苦的话,那么,在理论上,自由刑与财产刑便是可以相互代替的了。刑法以自由刑作为原则,以罚金刑作为补充,但这其实是针对没有资力的犯罪人。而经济犯罪人一般是有资力的,所以可以将罚金刑作为原则刑罚适用。⑥[日]佐伯仁志:《制裁論》,成文堂2009年版,第42页。此外,当并处自由刑与罚金刑时,一般将自由刑理解为惩戒,将罚金刑理解为不法利益的剥夺,但其实完全可以将罚金刑视为独立的惩戒。为此,有学者认为:虽然目前日本量刑的排列顺序是实刑>缓刑>罚金刑,但可以在实刑与缓刑之间设置缓刑附加罚金刑,也可以在实刑中设置并处罚金时实刑减轻的刑罚模式。⑦[日]佐伯仁志:《制裁論》,成文堂2009年版,第43页。正是因为罚金刑在惩处金融犯罪时具有独特的优势,日本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不断提高《反垄断法》等特别刑法中的罚金刑的上限。例如,在法人犯罪时,《反垄断法》与《银行法》中的罚金刑上限已经被提升至五亿日元,而《金融商品交易法》中的罚金刑上限已经被提升至七亿日元。
而关于剥夺不法利益的问题,其实应当适用刑法总则的没收条款。日本刑法总则第19条第1项第3号的没收规定存在两个问题:(1)其对象仅限于有体物而不适用于存款债权等财产利益;(2)是任意规定而非强制规定,所以实践中几乎不曾适用。关于前者,《毒品特例法及有组织犯罪处罚法》中已经规定没收不限于有体物,受此影响,日本刑法也有类似的修订动向。关于后者,一般认为也应作出修订,采用《金融商品交易法》规定的原则没收模式。⑧[日]佐伯仁志:《制裁論》,成文堂2009年版,第44页。
五、“规制缓和”理念与金融规则的明确化
“规制缓和”理念要求行政由事前规制型向事后校验型转变,在金融领域,便是要求监管机关进一步放权,由金融交易主体更自由地采取行动。而为了防止交易主体的行为失范,便需要制定更为详细且明确的规则。此外,无论是从依法行政还是罪刑法定主义出发,都要求法规的明确化。关于该问题,日本的旧《证券交易法》曾经有过不足。例如,第57条规定了“禁止不正当行为”,但关于“不正当行为”的解释却过于模糊,所以本条在司法实践中几乎没有被适用过。再如,该法第166条第2项是关于内幕信息的规定,其中的第4号是补充规定:“除前三号外,关于该上市公司等的运营、业务或财产的重要的并对投资者的投资判断造成显著影响的事实。”在实践中,当出现无法纳入前三号中的重要事实时,监管部门便会积极地适用该补充规定①例如,在日本的首起内幕交易案件——日本商事股票事件中,法院便适用了第166条第2项第4号。案情及判决意见参见[日]《商事法務》第1518号(1999年),第41页以下。。但质疑声却一直存在:立法时是否确实曾经打算惩处类似的犯罪行为。关于这种涵义模糊的补充条款的适用问题,研究界一直保持着极为谨慎的态度。例如,有学者指出:补充条款的添加导致了法条适用的不明确性,有导致规制范围缩小之嫌。②[日]黒沢悦郎:《インサイダー取引規制における重要事実の定義の問題点》,《商事法務》1687号(2004年)。因此,类似的不明确条款都亟需修订。或者即使不能修订,也应当在实际规制时尽可能审慎地适用。此外,伴随着金融大爆炸时代的到来,金融衍生商品的交易必然会日渐重要,而既然是缓和规制,那么,关于交易主体及交易方式的限制也必然会逐步取消。与之相适应,关于怎样的主体具有交易资质以及怎样的交易才是合法交易的问题,都需要立法做出明确的解释。
关于规则明确化的方式,一般认为可以采取两种途径:(1)利用无异议函(No Action Letter)。详言之,当从业人员不明白自己将要实施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时,可以向相应的主管机关提出照会,由主管机关在一定期限内以公示的方式作出答复。但需要注意的是,法律的最终解释权属于立法与司法机关,因此,行政机关出具的无异议函对于法院没有约束力,虽然法院一般会尊重该无异议函的意见,但并不代表法院必须得出与之相一致的结论。当无异议函的意见与法院的结论相矛盾时,如果此前的从业人员是依据无异议函的意见实施了行为的话,可以利用其欠缺违法性意识或期待可能性的理由否定其违法性。而做出无异议函的行政机关当然不能反过来追究从业人员的责任。③参见[日]笠井修、高山佳柰子:《对无异议函的信任与民、刑事责任(3·完)》,《资料版/商事法务》第731号(2002年)第51-60页。(2)利用行政制裁。金融交易的特点是方式的多样化、技术化以及变革的迅速化,因此,即使相应的刑罚法规规定比较详细,也很难考虑周全。这就导致了金融刑罚法规容易抽象化,而处罚的范围也往往是模糊的。为了避免这种尴尬,更应审慎地发动刑罚,而更多地利用行政制裁等手段,由更了解该行业的监管机关依法自主地进行规制。关于这一点,日本有成功的先例。即,公正交易委员会作为独立的行政机关,专门负责垄断行为的禁止工作,该机关自设立以来,在利用行政揭发及刑事揭发而维护经济交易秩序并保护消费者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之相对,原证券交易等监视委员会(现金融商品交易等监视委员会)只是大藏省的下属机构,职权仅限于调查权,即,依据法院的许可状对涉嫌犯罪者进行强制性临时检查、搜查或扣押,而不像公正交易委员会一样拥有独立的行政处分权等,因此,金融商品交易等监视委员会的实际效能非常有限。有鉴于此,业界一直在呼吁赋予其类似于公正交易委员的独立职权。
六、“规制缓和”理念与中国金融市场的完善
众所周知,以面对金融大爆炸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目的,中国金融市场体系的改革工作已经进入深水区,其主要内容涉及市场主体改革、市场机制改革与市场环境改革三个方面。其中,市场主体改革的主要目标是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吸引更多的竞争者参与市场,市场机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汇率与利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与完善,而市场环境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完善监管措施并加强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换言之,从市场准入的放松、金融商品价格的市场化以及监管体系的完善三个方面入手,实现由政府管控为主向市场自律为主的转变。如果从不同行业的角度出发,在银行业,主要是实现从现在的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依赖型增长转向中小企业和新兴产业依赖型增长,在证券交易业,则是积极推动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入市,而在外汇领域,则是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使价格形成机制更为市场化。其中既蕴含着契机,也隐藏着危机。
首先,以银行业的监管体制为例,我们借鉴国外学者构建的金融监管治理评估框架,结合中国实际,设计了中国银行业监管治理指数的指标体系。中国银行业监管治理指数指标体系可以分为四个纬度:独立性、责任性、透明度和监管操守,每个纬度又细分为若干指标,总计47个指标。根据2011年的统计数据,在该指标体系中,独立性指数为63.16,责任性指数为82.14,透明度指数为68.75,监管操守指数为83.33,总体指数为72.34,①高明华:《银行业监管的进步与不足》,《董事会》2011年第4期。各项指数都据中上游,但却难言完善。例如,在独立性方面,银监会的主席由政府来任命,这便为政府干预银行业监管工作提供了便利。特别是在市场准入和日常运营监管方面,责权名义上统一于银监会,但是在撤销牌照、许可证等涉及市场退出方面时,银监会分支机构如果要对某些金融机构退出市场提出处理意见,必须先征得地方政府的同意才能上报银监会。而在责任性方面,《银监法》等法律法规虽然规定了银监会同其他监管部门定期磋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然而,这毕竟是一种松散型的监管合作方式,在目前实行分业监管体制而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逐渐盛行、金融创新日新月异的背景下,这种监管方式必然会出现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叠。由于监管责任、权利界定不清,各监管部门还有可能出现相互推诿的现象。②高明华:《银行业监管的进步与不足》,《董事会》2011年第4期。针对上述弊端,银行业监管的首要措施便是赋予银监会更独立的地位与职权,例如,仿效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与日本的公正交易委员会,使其在查处违规行为时不受制于各级政府以及其他监管部门。
而在证券交易领域中,虽然推动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入市是大势所趋,但目前的机构投资者在投资管理专业化、投资结构组合化以及投资行为规范化方面还存在着诸多不足,致使其投资行为仍不够理性,特别是受到散户的投机心理的影响,许多机构投资者更倾向于短线交易,而缺乏长远投资规划。因此,机构投资者的入市虽然降低了市场波动率,但降低幅度与原先的预期相差甚远。所以,只有完善证监会的监管职权,加大证券不法交易的监管与制裁力度,才能更好地推动证券交易主体的规范入市。例如,在证券犯罪的惩处机制方面,应当改变一味地诉诸刑罚的处罚模式,通过引入其他的非刑罚措施来加以遏制。具体而言,“刑事和解”制度、以民事损害赔偿为条件的刑事免责机制、以及暂缓起诉等制度在规制证券不法犯罪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③毛玲玲:《证券刑法的矛盾样态及反思》,《中外法学》2014年第3期。
最后,关于外汇市场的运营与监管问题,中国目前的外汇市场仍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外汇业务受到政府的各方面管控。因此,与外国发达的外汇市场相比,中国的外汇市场在交易主体的自由选择空间、交易的连续性、交易组织结构的完善化以及市场覆盖率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足。这不仅导致人民币的汇率始终处于被外国质疑的尴尬境地,而且也是目前的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的要因之一。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中国的外汇市场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整:(1)通过明晰产权结构,推动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2)引入外汇银行参与交易,形成良性的竞争模式;(3)放松外汇存货管制,确立人民币汇率与外汇市场的一致性,进而形成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4)与此同时,完善央行的外汇干预机制。其中的前三个方面涉及外汇市场的自我完善与发展,而第四个方面则是政府管控的加强。
总之,在金融市场体系的完善方面,如果想要确立以市场自律为主,以政府管控为辅的规制模式的话,那么,有必要借鉴日本的“规制缓和”理念,通过惩治手段的多样化、交易规制的明确化等方式推动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在预防与惩处金融犯罪时,应当尽可能地首先采用非刑措施,只有在出现重大的犯罪事件时,才诉诸刑罚。关于刑罚的审慎适用问题,早有学者指出:从刑法谦抑性的角度出发,刑事立法中应当推动“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双向并进,而在刑事司法中则应严格入罪界限,并倡导“非刑罚化”以及刑罚的轻缓化。但是,至少在金融犯罪领域,我们还无法看到上述思想的贯彻实施。此外,在金融犯罪的入罪方面,规定涵义并不明确的补充条款有被一再适用的危险。以操纵证券市场罪为例,汪建中的“抢帽子交易行为”最终被适用了刑法第182条第1款第4项的“以其他方式操纵证券市场”的规定。但如果从刑法的保护法属性以及谦抑主义的要求来看,这种以补充条款认定为犯罪的情形是并不妥当的。④何荣功、莫洪宪:《中国の証券犯罪に関する刑事立法の最新動向》,[日]《法律時報》第84巻第8号。与日本严格限制“篮子条款”的做法相比,中国法中补充条款的不断扩张适用让我们更深刻地感到了罪刑法定主义面临的严重威胁。仅从金融交易的角度来看,隐藏在这种威胁背后的深层原因便是金融交易秩序与监管体制的混乱、行业自律意识的淡薄以及自律机制的缺失。而这些问题却绝非单纯地加大刑罚力度便能够解决的。关于刑法在金融交易领域的扩张问题,我们必须明确的是,在金融领域不加区分地适用刑罚时将导致刑法资源的浪费与滥用,⑤毛玲玲:《金融领域刑事司法状况的实证考察与启示》,《法学》2014年第2期。更重要的是会造成市场活力的减弱与自律机制的缺失。
(责任编辑:张婧)
D914
A
1003-4145[2015]06-0164-08
2015-04-01
张小宁(1979—),男,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日本立命馆大学衣笠综合研究机构博士后研究员,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本文系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盘研究项目“东亚经济刑法研究”(项目编号:24530070)、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社会科学类青年培养项目“刑法谦抑主义在规制金融证券犯罪中的适用——以日本的‘规制缓和理念’为鉴”(项目编号:2014SQXM001)与山东省法学会2014年自选课题“刑罚论视角下的山东金融监管体制的完善”(项目编号:SLS2014G2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