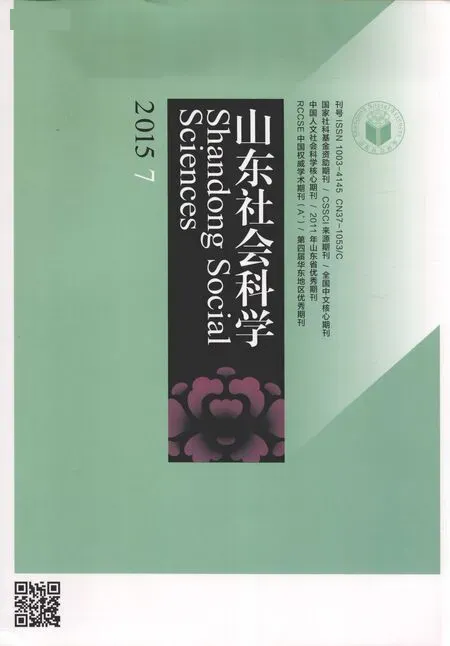《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历史、理论和文本
2015-04-02周嘉昕
周嘉昕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历史、理论和文本
周嘉昕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在1845年写下的“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但它的公开问世是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附录之中。自此,《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就承担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阐释的艰巨使命。恩格斯对于《马克思论费尔巴哈》的发表本身就是以建构不同于19世纪中叶欧洲流行的庸俗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为指向的。但是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成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向历史唯物主义推广运用的中间环节。与之相对的,是通过“实践”概念阐发某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不同尝试。为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批判性之间搭建逻辑桥梁,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推进同时为重新理解《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建构了新的理论平台,特别是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包括“实践”和“新唯物主义”在内的一系列概念范畴将在思想史的回顾、理论问题的梳理和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期文本的研读中展现出新的重要性和意义。
唯物主义;实践;辩证法;政治经济学批判
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是马克思文本中为数不多可以直接用来作为哲学本体论建构的依据。然而,正如既有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就“实践唯物主义”而言,《提纲》中对于“实践”概念的使用恐怕只能算作一个“孤证”;在“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和的基本的观点”理解基础上,学界更多关注的是马克思“实践”概念内蕴的社会历史性的前提或维度。近年来有关“生存论”马克思主义的探讨,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辩证唯物主义的辨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哲学的研究等等,都可以归结为这一诉求中结出的理论硕果。这也正为我们170年后重新阅读马克思1845年写下的这“十一条论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启了新的视域。本文尝试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复杂历程中去,结合马克思与唯物主义的关系,以及“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得失,寻求一种激活《提纲》文本和当代学术话语内在关联的可能。
一、《马克思论费尔巴哈》与“唯物主义”传统的建构
众所周知,《提纲》存在两个版本,一是马克思自己在1845年写下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二是恩格斯修订出版的《马克思论费尔巴哈》,1886年作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的附录出版。这两个版本中最先问世的反倒是后者。恩格斯自己是这样描述《提纲》的发现过程的:“旧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缺少对费尔巴哈学说本身的批判;所以,旧稿对现在这一目的(说明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同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关系)是不适用的。可是我在马克思的一本旧笔记中找到了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现在作为本书附录刊印出来。这是匆匆写成的供以后研究用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但是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3页。而前者,也就是马克思自己写下的提纲,却是到了1924年才由梁赞诺夫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1卷中公开发表。
也就是说,《提纲》本身作为研究的笔记,马克思并没有打算将其公开问世,而是由恩格斯出于理论总结和阐发的需要,才加工整理出版的。那么,这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恩格斯的《马克思论费尔巴哈》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间,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很多研究从文本变化的角度出发,围绕恩格斯对于马克思原文的修改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分析。但是笔者这里打算首先追问的是,暂且承认恩格斯无论在文字表述还是哲学理解上都与马克思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过了40年之后恩格斯才想起来要去重新翻阅《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为什么是在19世纪80年代这样一个特定时期,恩格斯才想到要回顾费尔巴哈这个位于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恩格斯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
虽然恩格斯自己用“没有过机会”这样的说法一笔带过,但是结合马克思本人是在创作《资本论》的过程中(参阅1858年马克思关于《逻辑学》的通信、1859年恩格斯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作的书评、著名的《资本论》第二版跋等)才重新“发现”或者说“回到”黑格尔的话,我们会发现:《马克思论费尔巴哈》的问世本身与恩格斯此时所肩负的理论重任有着密切的关联,这就是要在19世纪中叶庸俗唯物主义和新康德主义逐渐成为思想主流的背景下,通过强调黑格尔辩证法的重要性来捍卫《资本论》以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此过程中,恩格斯和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面对的理论任务是,既要说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差别,又要强调唯物主义辩证法与机械论的经验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不同。在这个意义上,借用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话说,“和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但是,他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①《卡·马克思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9页。;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2页。。
具体说来,恩格斯《马克思论费尔巴哈》的整理和出版面对的是这样一种思想史氛围:较之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写作《神圣家族》时期同“青年黑格尔派”的争论,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机械唯物主义、进化论)和实证主义思潮的兴起,“唯物主义”在19世纪中期以来正在产生越来越广泛的新的影响。因此,“唯物主义”首先不是一个可以源自所谓“朴素唯物论”的古老哲学传统,也并非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专利,而是一个正在建构中的哲学传统和社会思潮。例如,在被称为“唯物主义的19世纪60年代”里,新康德主义者朗格就曾专门撰写了一部名为《唯物主义史及其当代重要性的批判》的著作③参见Frederick Lange,The History of Materialism and Criticism of Its Present Importance,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Co,Ltd,1925,p.vi。。19世纪50年代以来普遍流行的是福格特、摩莱肖特和毕希纳的“科学唯物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庸俗唯物主义”),到了60和70年代,海克尔更是将达尔文的进化论纳入其中④参见Frederick Gregory,Scientific versus Dialectical Materialism:A Clash of Ideolog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 Radicalism,Isis,Vol.68,No.2(Jun.,1977),p.207。。面对这样一种社会历史语境,恩格斯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利用并改造这一传统的建构,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运用提供可能;同时,更加重要的是要在这一传统的建构中,将《资本论》中重新发现或是“头足倒置”过来的辩证法植入其中。在某种程度上说,恩格斯所阐发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唯物主义辩证法”都可以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第一批成果。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自己并没有怎么提过“唯物主义”的问题,而更多是在限定的意义上使用“物质的”这一表述,如“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物质生产方式”等。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艰苦的理论实践过程中,恩格斯特别强调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因为:首先,费尔巴哈是除英国的经验论者和法国的机械唯物主义者外,“德意志”唯物主义的重要代表(尽管费尔巴哈从来不会认为自己是“唯物主义者”),“他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其次,正是借助于费尔巴哈,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通过“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实现了“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也就是说,费尔巴哈是用来界划马克思同黑格尔方法的重要“中间环节”,但由于费尔巴哈在历史观上同样是“观念论”(唯心主义)者,因此这个“半截子的唯物主义者”也只能是一个“中间环节”。因此,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就责无旁贷成为恩格斯建构“唯物主义辩证法”,或者说一种全新的辩证的唯物主义理论传统的重要依据。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恩格斯直接投身于甚至可以说开启了通过参与建构“新唯物主义”传统来总结、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实践,但是就“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来说,恰恰不是恩格斯而是狄慈根、拉法格、普列汉诺夫等人打开了新的理论之门。正如有研究已经指出的那样,是普列汉诺夫第一个使用了“辩证唯物主义”概念。在他看来,“‘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它是唯一能够正确说明马克思的哲学的术语”①罗森塔尔主编:《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43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确立。众所周知,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Diamat),只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才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最终确立下来,标志是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文和米丁的哲学教科书。严格说来,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命名更多是“唯物史观”,只不过这种“唯物史观”的特征一是“唯物主义”,二是“辩证法”。经过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辩证论和机械论、米丁派和德波林派的争论后,今天作为常识意义上的“辩证唯物主义”才彻底替代了“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代名词。
在此过程中,随着“唯物主义”由“形容词”变为“名词”,被建构起来的“辩证唯物主义”传统也就被反向注入了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本的阐释之中,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义转变中的作用也就得到了更多的凸显。相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立过程就应该到马克思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中去寻求。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正统理解中,“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乃是他在前一时期(从1843年借助于费尔巴哈转向唯物主义到1845年初《神圣家族》的发表)提出的诸原理(辩证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进一步发展和总结;这个提纲也提出了新的问题,表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思想”②纳尔斯基等主编:《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1页。。这些所谓的“新思想”更多指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的“完整看法的唯物史观”。也就是说在传统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作为科学世界观的辩证唯物主义问世的标识是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合作出版的《神圣家族》,而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应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最终形成的。《提纲》这份“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不过是“推广应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已,而“实践”概念的理论作用也仅限于认识论之中。与此针锋相对的是,《提纲》和作为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概念的重要性反倒得到了所谓“资产阶级哲学家”更多的关注和强调。
二、一个“实践唯物主义”的文献“孤证”
纵观20世纪2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大多可以清晰地梳理出诸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研究的历史演进。如1932年后,随着《手稿》两个版本的几乎同时问世,很快在西方学界引发了“青年马克思”或“两个马克思”的争论,这种以人本主义逻辑争夺马克思思想解释领导权的倾向,在上世纪60年代后逐渐退潮。一方面是阿尔都塞对人本主义的批评,另一方面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成果的问世。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得到了凸显,并且逐渐替代《手稿》成为东西方马克思文本研究交锋的焦点话题,直至世纪之交仍然如此。与人本主义思潮相关,但又更为复杂的是《大纲》和《资本论》的研究,当然,《大纲》在文本上引发的争议最小,但却实际上构成了上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左翼话语中最为重要的马克思文本依据。
相形之下,《提纲》的研究似乎比较暧昧而尴尬。除了布洛赫之外,我们竟很难直接想起有谁专门讨论过《提纲》,即便事实上《提纲》本身是一篇不断被引用的文献,“实践”也是一个经常被提起的概念。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一方面是因为《提纲》自身格言式的写作方式给阐释者留下了太多可供发挥的空间,因而《提纲》本身在理论阐发中往往是“高大上”般的以某一条或某句话的深刻启发或创意改写的方式存在;另一方面,也更加重要的是,由于《提纲》“夹缝”式地存在于《神圣家族》和《资本论》之间,或者说《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高峰”(不管是马克思自身思想发展的“断块山”,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造成的“褶皱山”)之间,对于《提纲》的研究更多地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方法界定结合在一起,而非对《提纲》本身直接的研究。
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下,《提纲》是在首先确立唯物主义原则的“基础”,利用“实践”概念“补充”不同于机械论唯物主义(带有与辩证法相对立的“形而上学”属性)的辩证能动性。当然,这种能动性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作为前提。在笔者看来,这样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梅林和普列汉诺夫为典型的第二国际理论传统的系统化。在这样一种赋予费尔巴哈以优先地位的“诠释定向”①参见吴晓明:《形而上学的没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中,《神圣家族》被看作是“第一部公开发表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而其中的唯物主义基础和共产主义立场,马克思早在1844年初已然具备。
作为对这一梅林—普列汉诺夫“诠释定向”的直接批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理论代表如卢卡奇和柯尔施那里,《提纲》和“实践”则直接体现了黑格尔式的马克思思想阐释要求。在《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最后,卢卡奇指出:为了克服物化,“马克思在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所提出的答案在于使哲学变为实践。……这实践具有它的客观的结构上的前提,具有它的另一面,那就是认为现实是‘过程的集合体’,认为较之经验的僵化的物化的事实,历史发展的倾向代表的虽然是产生于经验本身的,因此决不是彼岸的,但确实是一个更高级的、真正的现实”②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97页。。为了阐发这样一种“作为哲学原则的实践”,卢卡奇还曾批判了恩格斯“把工业和实验看作是实践”的理解。柯尔施虽然也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称为辩证唯物主义,但他认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后期著作一样,强调了“新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哲学唯物主义”,即“通常的、抽象的和非辩证的唯物主义”之间的对比和区别。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发现:同卢卡奇和柯尔施所提供的《提纲》中“新唯物主义”和“实践”概念理解的遥相呼应,海德格尔也曾为马克思进行过辩护。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1946年)中,海德格尔写到:“唯物主义的本质不在于一切只是素材(物质)这一主场中,而是在于一种形而上学的规定中,按照此规定讲来一切存在者都显现为劳动的材料。劳动的新时代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已预先被思为无条件的制造之自己安排自己的过程,这就是通过作为主观性来体会的人来把现实的东西对象化的过程”③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83-384页。。
回到20世纪中叶的马克思思想研究中去,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手稿》中“马克思第二次降世”的思想语境,同时又受《手稿》的公开问世和“青年马克思”讨论推动的,是20世纪中叶在西方思想中普遍出现的一种人本主义思潮。与之相并行的,是“实践”与“异化”凸显为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两个理论关键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除了萨特有关“实践”问题的阐发和布洛赫对于《提纲》的“具体的人本主义”阐释外,应当说就是南斯拉夫“实践派”对于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批判和对实践辩证法的探讨。在此过程中,“实践”与“历史”、作为认识论范畴的实践(practice)与作为本体论范畴的实践(praxis)、“实践”与“生产”(劳动)之间的对勘构成了问题的焦点。从这一讨论出发,或者说作为这一讨论的延伸与回应的,是如何在彰显这样一个“实践”概念的本体论意义的同时,避免陷入一种对于“实践”的抽象的“唯心主义”理解。或者说,在反对苏联“辩证唯物主义”框架下作为唯物主义辩证“补充”的“实践”观基础上,又警惕这样一种“实践”沦为抽象的价值悬设,抑或缺乏社会历史内容的空洞的主体性,即卢卡奇所说的“抽象的、唯心主义的实践概念”。这一思考焦点回溯性地反映在马克思文本和思想的分期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大多数持这样一种“实践哲学”观点的学者来说,往往将《手稿》中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改造”同《提纲》中以“实践”为核心的新唯物主义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但与此同时,也特别注重通过《资本论》(拜物教批判)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广为流传并得到研究的《大纲》(“物化”问题),来为这样一种批判性的“实践”概念注入社会历史性维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尝试将西方学界曾经出现的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勾连,以及通过追溯哲学史上“实践”和“生产”的关联来为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奠基,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概念辨析,包括“资本逻辑”问题的探讨和《资本论》研究的复兴,看作是一种面对上述共同的问题指向,基于不同的思想资源和学术旨趣,多元并进的理论态势。有趣的是,在此过程中,《提纲》的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探索,都开始距离《资本论》越来越近,而对《神圣家族》持一定的谨慎态度。当然,一个有趣的例外是: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专家、MEGA2编者陶伯特曾经根据马克思《提纲》写作原文中,紧挨在“提纲”之前的四行文字和《提纲》的写作时间,来证明这“十一条论纲”更多是关涉《神圣家族》写作所引发争论的回应,而非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计划有关。对此,笔者的态度是:我们确实应该尊重文献学专家所提出的历史和文本事实,但也必须看到,文本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文献自身所决定的,而往往同研究者和诠释者的“理论前件”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不过,这一文献研究的成果所引发的争论,倒是提醒我们:从“实践”的文本依据出发或可提供一种对于在国内学界曾经引发广泛讨论的“实践唯物主义”问题的理论反思。
纵观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文本,套用一个考古学的术语,我们可以说:对于“实践唯物主义”来说,《提纲》只能算作一个“孤证”,缺乏充分而有效的文本依据来相互映衬和佐证。因为“实践”概念只是偶尔出现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文本之中。在以《资本论》为代表的大量成熟时期的著作中难以觅得“实践”范畴的踪影。因此,“实践唯物主义”较为明显地体现了“理论反注文本”的特征。熟悉马克思文本的学者同样会说,马克思没有使用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甚至很少使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较之马克思卷帙浩繁的著作,“辩证法”的出现也可谓是凤毛麟角,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辩证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也是一种“理论反注文本”呢?对于这一问题较为得体的回答可能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存在“理论反注文本”,而在于“怎样的”理论以“怎样的”方式反注文本。如果是抽象的设定或被动的接受某种教条化的理论,然后以“Ctrl+F”的方式寻得某些词句来证明,那么这种做法注定是要遭到摒弃的。但如果是在“通晓思维和历史的成就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文本考察和方法自省,而形成理论思维和文本证据的有机结合,那么,这种“反注”就不仅可行而且必要。在马克思写下《提纲》170年、恩格斯发表《马克思论费尔巴哈》将近130年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也呼唤着对于《提纲》的一种既不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Diamat)也不同于“实践唯物主义”的新的理论“反注”。
三、今天该如何使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概而言之,在《提纲》的阐释史上存在这样一种尴尬的逻辑交叠。一方面,是第二国际理论家以及苏联“辩证唯物主义”理论遵循恩格斯建构“新唯物主义”传统的努力,但却受到经济决定论思潮的影响,在“唯物主义‘基础’+辩证法‘补充’”的意义上来定位《提纲》。这也就导致了,这种理解模式虽然源于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阐释和捍卫的直接需要,但却在重塑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所谓的“一次转变论”观点甚至是“辉煌史观”的倾向①参见张一兵主编:《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序言,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纲》不过是此前“已经提出的诸原理”的进一步发展,并且“提出新问题”、“表述新思想”罢了。另一方面,基于对上述理解的不满,以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理论家,已经有意识地反对这种“唯物主义”的实证(物化)和直观色彩,更加强调“历史辩证法”,进而将《提纲》中的“实践”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在《手稿》和《大纲》公开问世之后,以及人本主义成为西方学术话语的显性逻辑的背景下,《提纲》的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较之苏联学者的看法,对《提纲》的理解反倒显得更接近于恩格斯的判断,“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这一点在布洛赫从《手稿》出发定义《提纲》的尝试中一览无余。然而,为了避免“重新陷入唯心主义的直观”(卢卡奇语),这种理解模式中的《提纲》却不得不以或隐或现的方式重新诉诸《资本论》及其手稿,特别是“价值形式”和“拜物教”批判,来为“实践的辩证法”或“实践哲学”提供一种唯物主义的属性。做一个不恰当的类比,就是“辩证法‘本体’+唯物主义‘属性’”。
回到今天的思想语境,重新阅读《提纲》、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第一个需要关注或者说自省的问题是:我们到底应该在何种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别是在“物质本体论”和“实践唯物主义”相竞争的意义上,应当如何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存在的对于社会历史过程的唯物主义分析与针对现实资本主义非人本质的批判之间的内在关联?或者换句话说,在事实分析的土壤上如何能够开出价值批判的鲜花?在这个意义上,包括俞吾金教授“实践诠释学”的阐发、张一兵教授关于《提纲》中“实践”以工业现代性为基础的观点以及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理解和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探讨,都可以看作是在后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竞争”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研究最新推进的理论问题映现。而这些成果也为我们重新阅读包括《提纲》在内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献,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科学性和批判性二者的内在关联,搭建了全新的方法论构架。在笔者看来,这一方法论构架的一个重要的外观就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具体而言,这一方法论构架的搭建显然并不是要我们像西方价值形式论学者巴克豪斯那样,直接性地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批判套用到对《提纲》特别是第四条的直接改写中去①参见Hans-Georg Backhaus,“Zur Dialektik der Wertform”,Beitraege zur marxistischen Erkenntnistheorie,Herausgeben von Alfred Schmidt,Suhrkamp Verlag,1969。。而是说,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实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这一批判从开始探索到最终形成的思想史历程,来理解以《提纲》为代表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对包括“实践”和“异化”在内的一系列概念范畴给出科学的评估。因此,对于《提纲》的理解,需要关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马克思的思想分期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上的阶段性划分与《提纲》的定位问题。这也是直接关乎《提纲》理解的一个重要问题,包括两个层面:
其一是从所谓“青年马克思”问题延伸而来的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与成熟时期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简单说来就是1848年之前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于《资本论》中资本主义批判科学理论制订之间的关系问题。尽管马克思自己在1859年已经提供了经典表述,恩格斯也给出了“两个伟大发现”的说法,但是由于19世纪资本主义现实的变化和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域的转换(从哲学到政治经济学),这一问题的讨论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复杂问题,并且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问题本身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模式中进一步复杂化了。可以说,到今天为止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仍需要我们继续不懈探索。
其二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理论转变问题。从前苏联学者强调“一次转变”和《神圣家族》,到西方“马克思学”推崇《手稿》和“青年马克思”,再到现在已经逐渐成为共识的“两次转变”和“《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确立的看法,我们会发现:《提纲》的定位发生着潜在的滑动,而且直接牵涉《提纲》与《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手稿》等早期文献之间的理论关系和文本梳理。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对《手稿》、《神圣家族》、《形态》这些文献之间的关系给出某种新的判断,那么关于《提纲》定位的尴尬或者说游移也许就会迎刃而解。
为了实现这一要求,一个比较切实的手段是对《提纲》中马克思所提到或使用的一系列范畴,而非仅仅是“实践”、“新唯物主义”、“改变世界”这样一些传统研究中不断被重复提起的词句加以仔细的甄别。考察马克思在《提纲》中对这些范畴的使用,以及追踪这些范畴在马克思早期文献甚至是《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使用情况,尤其是术语的转换和含义的改变,我们或许可以给《提纲》以新的定位,甚至可以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新的理解提供某种逻辑支撑。这也构成了今天重新阅读《提纲》的第三个需要关注并实现的问题。在笔者看来,除了“实践”等过去的研究中经常关注的范畴外,“对象”和“对象性活动”、“现实性”、“二重化”和“自我分裂”、“人”和“个人”(个体)、“市民社会”等范畴(按照在《提纲》中出现的顺序排列)就是这样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甚至是可以为我们带来“范式”转变的概念范畴。受篇幅所限,仅举“对象”(Gegenstand)和“个人”(Individuen)二例来说。
依照《提纲》原文,“实践”的含义是“对象性的活动”,而且马克思多次提到了从“实践”出发理解“对象”和“对象的(客观的)真理性”。而“对象”这一术语本身一方面是黑格尔,尤其是费尔巴哈著作中的关键词,另一方面在写作于《提纲》一年之前的《手稿》中也扮演了重要的理论角色(如对象化和异化的区分)。如果我们回到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强调“人”作为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是哲学的真正的出发点,以及马克思在《手稿》中“劳动的对象化”的具体展开和“黑格尔辩证法批判”中关于“对象性”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对象性活动”这一术语的背后,不仅是从对象“物”到对象性“活动”(实践)的推进,更重要的是“对象”和“对象性活动”背后的“社会关系”关联和“历史进程”维度。也就是说,“对象性活动”的术语所蕴含着的不仅仅是一种主客体相结合的行动,或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的抽象理解,而是面对“一定的”对象采取“一定的”形式的“一定的”活动。
当然,这一点仅仅在《提纲》的文本中是无法被直观的。但结合《手稿》,特别《手稿》的写作顺序,对于马克思批判“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部分中所发生的写作上与经济学内容的交叠和理论逻辑上的推进(从推崇费尔巴哈到肯定“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的环节”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附有按照手稿写作顺序编排的文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75页。)的说明,《提纲》中“对象”范畴的社会历史维度及其对于费尔巴哈用法的超越,也就不难理解了。同时,向后延伸到《形态》中有关“物质生产”的说明,作为“对象性活动”的“实践”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也就不难理解了。
另一个可以作为佐证的例子是马克思对“人”(Mensch)和“个人”(Individuen)的不同用法。毫无疑问,“人”或者更准确地说“人类”概念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一个核心概念,“人类解放”本身就是马克思孜孜以求的目标。但是1843-1845年间马克思所理解的“人类”显然带有强烈的费尔巴哈色彩。在《提纲》中为了与之相区分,马克思一是在第六条中特意强调“人类”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二是同时强调“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57页。。有趣的是,马克思在提到“市民社会”和费尔巴哈“直观的唯物主义”的时候,还是用了另外一个与“人类”不同的“个人”(个体)的说法。并且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失误就在于不能理解这一“抽象的个人”、“单个人”、“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的秘密。显然,这可以同“对象”概念理解上的推进有关。既然费尔巴哈的“对象性存在”缺乏一种社会历史的维度,那么他对于“人类”的理解就不过是一种“市民社会”基础上的“单个人”的直观。问题的关键则是对“社会关系”的考察。
对照《形态》的理论叙述(包括马克思自己的修改过程),正是在这一维度上,马克思才开始将“现实的个人”作为“历史的前提”,其内在指向是作为具有社会关系维度的“对象性活动”,即“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可以说,正是在“人类”和“个人”的理解及使用方式上,内在地体现了马克思青年时期的哲学探索,以及这种探索同政治经济学研究之间的复杂关联。
综上所述,《提纲》本身具有文本写作的特殊性——马克思笔记本中留下的十一条格言,概念术语带有同时代人相互影响的强烈痕迹;具有理论逻辑的特殊性——处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转型期,被恩格斯称作“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具有历史流传的特殊性——被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用作建构特定的思想传统、阐发哲学本体论的主要的尽管是相对略显单薄的文本依据。因此,在阅读《提纲》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格外谨慎,在历史、理论和文本的结合中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本质,进而对《提纲》的文本和逻辑本身进行阐发。可以说,无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实践唯物主义”范式下对于《提纲》的“反注”和“使用”都已经遭遇到了自身的问题困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或者说现实历史维度,与规范性或者说价值批判维度之间,无法提供一种令人信服的理论“接合”方案。那么,我们不妨透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所开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阐发的新的理论棱镜,在充分利用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提供某种关于《提纲》的新的可能的阐释。也正是在此过程中,马克思青年时期复杂的理论探索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唯物主义的关系、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物化现实的超越之路,或可以得到更为清晰的厘定。
(责任编辑:周文升)
B152
A
1003-4145[2015]07-0040-07
2015-05-26
周嘉昕,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驻院学者,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和当代西方激进思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