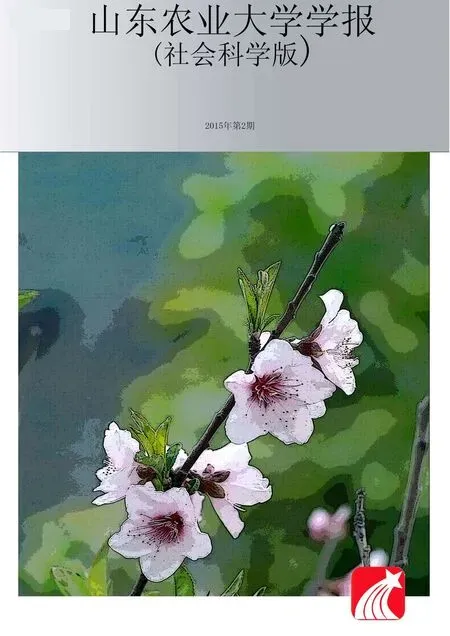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村妇女广泛参加生产劳动的缘由探析
——以山东聊城为中心的实证研究
2015-04-02林冬梅李先明
□林冬梅 李先明
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村妇女广泛参加生产劳动的缘由探析
——以山东聊城为中心的实证研究
□林冬梅 李先明
农业合作化时期,聊城广大农村妇女大都走出家门,积极参加劳动生产。聊城农村妇女之所以广泛参加劳动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生产观念的变化是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价值基础;农业合作社解决了小孩看管和家人的穿衣等家务问题使妇女参加劳动没了后顾之忧;而工分制和同工同酬制度的实施是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最为直接的经济动因。
聊城农村;观念变化;家庭因素;制度设计
众所周知,在传统中国,受儒家纲常伦教的挈制,妇女深居闺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从事单纯而又繁重的家务劳动。但新中国成立不久,特别是农业合作化时期,广大农村妇女却纷纷走出家门,积极参与生产劳动,为新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几年间,中国妇女缘何一反常态,从家庭“私”领域走向社会“公”领域,由从事单纯的家务劳动到成为农村农业、副业的主要劳动力,此中原因值得探讨。近几年来学界对此有所关注,但这些仅有的研究属于一种政策——绩效型的表达,未能从妇女自向的角度探讨妇女参加劳动的真正原因。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山东聊城地区农村妇女为主要考察对象,从观念上的变化、家庭因素、制度的设计与实施三个方面探讨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村妇女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的动因。
一、参加劳动光荣:妇女生产观念的变化奠定了妇女参加劳动的价值基础
新中国成立前后,在“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和“男尊女卑”传统思想制约下,农村妇女往往不愿参加生产劳动。她们认为“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要是自己劳动,就不用嫁个汉子了”,“劳动是迫不得已,……要是自己命好,就不用下地了。”[1]有的女同志还认为:男耕女织,参加生产不好看,存有依赖男人,自己不行的自卑思想;而有些妇女同志尽管走出家门参加了生产劳动,但由于她们缺乏技术,受到外界的讽刺嘲笑,因而其劳动情绪受到打击,如东唐乡前进社的9名妇女在掘金瓜沟时,就掘的深浅不一行距远近不等,行距不直,男社员见了便嘲笑,对她们冷嘲热刺,从而严重打击了妇女的生产热情。[2]
为了充分动员妇女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支援国家建设,从1953年开始,聊城各级党委和宣传部门对女性的自卑、依赖、享受思想以及对男性的尊卑观念进行批判的同时,还通过各级妇联利用多种场合大张旗鼓的宣传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意义。如阳谷县大布区党委为发动与组织广大妇女参加生产,特地召开了区委会,对妇女工作进行了专门研究。会议上经分析情况,检查原因,学习文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端正了态度,提高了认识。会后则采取具体措施在生产运动中加强了妇女工作的领导,并取得了很大成绩,其具体表现就是,经过宣传教育与动员,“全区有7100余人参加生产,出勤率占妇女整半劳力的83%。其中一类社5个,妇女出勤率达到85%左右,二类社6个,出勤率达到78%左右,三类社1个,妇女出勤率达到67%以上。她们积肥81000车,搬冰盖麦2130亩,浇麦4860亩,开村头荒,深掘深刨7910亩,改碱456亩,修大畦田22391亩,植树60亩,配合男社员打井540多眼,有的乡社还打了妇女井,植了妇女林,在生产运动中并健全了妇女组织,培养了大批妇女骨干,向妇女传授了科学技术,合理解决了妇女的切身利益问题,从而提高了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各社纷纷反映:“妇女的力量真了不起,不是把她们发动起来,任务难完成。”[3]
妇女生产观念发生变化和参加生产劳动以后,聊城各农业合作还社纷纷采取了制定计划,总结检查生产,组织评比,开展竞赛等方法,从而进一步提高其生产积极性。如东唐乡前进农社“总结检查小段计划的执行情况时,把妇女盛广凤10天记工85分,按计划可分212斤粮食,经过妇女算出工账与收入增加账,大家参加生产的劲头更大了,未参加生产的也纷纷表示参加生产。登学清说:我很后悔没有动员她们参加生产,这样下去全年少收5000多斤粮食,可不能再这样了。”[4]再如莘县燕店区杨二庄乡总结了妇女参加劳动对妇女有四大好处:一是,改善了家庭关系,提高了妇女在家庭中的政治经济地位。如李文兰过去家庭不管穿,自入社参加了劳动后,穿衣问题得到了解决,并由过去不和睦变成了和睦家庭。二是,增多了妇女受教育的机会与场合,提高了妇女的思想觉悟。如孙庄妇女社委会反映说:参加“不光多分粮食,还长了好多本事,懂得了好多新事情哩!”李玉梅则说:“过去地里的活咱不会干,现在也学会好些,咱有了本事参加劳动生产,才能达到男女真正平等哩!”三是,改变了旧有的“男耕女织”和“儿子的江山,闺女的吃穿”等重男轻女的封建残余思想和论调,发挥了妇女的潜在力。[5]这样,经过宣传、组织和动员,“劳动光荣”成为农村社会主要的价值形态,聊城各地大多数妇女参加生产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就连以前一些从不出门参加生产的年轻姑娘也纷纷参加了田间劳动。
二、解决小孩看管和家人的穿衣问题:妇女参加劳动没了后顾之忧
生产观念的转变奠定了妇女参加劳动的价值基础,但此时妇女尚有后顾之忧,即孩子看管和家人穿衣问题。在传统中国家庭中,妇女“围着锅台转,围着孩子转”,是家务劳动、孩子看管的主力。一旦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孩子的看管,家人的穿衣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消除妇女后顾之忧,使妇女积极投入生产,成为男女社员共同的要求。
(一)解决小孩看管问题
妇女参加劳动后,因为孩子无人看管,往往人在地里,心在家里,根本无法安心生产。“王奉、麻寨、元庄三个村四处老社,共337户,男劳力337人,妇女劳力347人。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有5岁以下的孩子257个,其中有奶奶看管的184个,既无奶奶也无姐姐哥哥看管的小孩73个。”[6]有亲属看管的孩子尚可让母亲放心,但这些无人看管的孩子无疑是母亲最大的牵绊,而且有的地方甚至发生过孩子因无人看管而发生意外事故死亡的事件,严重影响了妇女的生产积极性。随着互助合作组织的发展以及妇女参加农业劳动的日益增多,解决孩子牵累,消除其后顾之忧,组织更多的妇女劳力投入生产运动,已成为男女社员的迫切要求。针对上述情况,各合作社根据上级指示精神,通过组织和巩固农忙托儿所解决了妇女看管小孩的后顾之忧。如上面提到了三个村四处老社“共组织了16个看娃娃组,托管孩子73个,这样在春季即腾出58个母亲积极投入春季抗旱,保堤、锄麦、积肥、间苗、移苗等运动”。“王奉王峻海农业生产合作社从未参加过劳动的5个妇女,在解决了孩子托管后,春季还挣了48个工”。因此,妇女们均普遍反映说:“过去下地,人在地里心在家,惦记着孩子,这会组织了娃娃组,孩子不受委屈,下地生产也安心了”。[7]农忙托儿组成立后,妇女的生产思想是随着保姆看孩子质量的好坏而变化的。为巩固妇女参加劳动的决心,合作社采取了不断对保姆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及育儿知识教育的措施。其具体措施表现为:召开定期的母亲-保姆联席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好的及时表扬,密切保姆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并交流育儿知识经验,加强保姆的社会主义及集体主义思想教育。如“联盟社召开保姆母亲联席会,母亲对保姆郝尽孝家没有看好孩子,使孩子打架提出了批评,而对带好孩子的周绍青母亲当场进行了表扬,并介绍了她怎样带好孩子的经验,因此更加加强了保姆的责任心。在保姆的经常教育下,大部分小孩都懂得了卫生常识。范恩波3岁的小孩子,每饭前不洗手不吃饭,从而更进一步的巩固了托儿组。”[8]
农忙托儿组的成立减轻了妇女的家庭负担,在发动妇女参加劳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逐渐得到了民众的认可。在强调社员自愿互利的原则下,地方政府和合作社在农忙托儿所的组织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现了母亲、保姆都满意的目标。农忙托儿所的成立不仅解放了妇女劳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社会风气的变化。由于妇女参加劳动,增加了收入,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和睦。虽然这一时期农忙托儿所在幼儿教养方面没有太多现代色彩,但它因地制宜的灵活托管方式和保证幼儿身体健康的基本要求是符合当时农村社会实际需要的。
(二)解决家人穿衣问题
在“男耕女织”的传统生产方式的影响下,妇女在家庭纺织、缝纫方面担任重要角色。建国初期,像全国其他地区一样,聊城地区广大农民的穿衣问题大都依赖于妇女的“手中针线”。当地有一句俗话:老爷们在外面走,带着老婆的手,意思即指男人出门在外所穿衣服的好坏代表着家中妇女的制衣手艺。因此,解决人们的穿衣问题也是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必须面对的。为此,各社纷纷建立起了缝纫组织。“光隆、建国两个社,买了缝衣机两部,腾出时间参加生产,采用妇女劳动收入归家,家中负责丈夫子女穿衣等方法解决了20多户的推穿问题。”[9]缝纫组织随着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有了很大发展,对解决群众的穿衣穿鞋问题起了很大作用,但远不能满足群众要求。因此,各级妇联迅速和有关部门配合采取措施,使缝纫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各县市对群众的缝纫需要和现有的缝纫设备、人员进行了摸底排队,找出问题,全面规划,统一安排。根据当时缝纫机器少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以手工缝纫为主,机器缝纫为辅的方法,根据需要与可能,大力的组织手工与机器缝纫相结合的缝纫组织。手工缝纫人员除固定一部分骨干外充分发挥了孕妇和老弱妇女的潜力,使当时的缝纫组织都巩固下来,达到常化,缝纫价格制定合理,一般以公分折算,缝纫员的公分报酬和劳动定额也得到合理解决。
妇女是家务劳动和带孩子的主力,长时间以来,广大农村妇女一直被其所困扰,不能脱身,但通过解决带孩子问题和穿衣问题,使农村妇女参加劳动没有了后顾之忧,生产积极性不断提高,为农村生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工分制和同工同酬制度的实施是妇女参加劳动最为直接的经济动因
如果说观念变化是妇女参加劳动的软性措施的话,制度安排就是强制性措施。制度性安排是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逐渐创设的,主要有工分制、同工同酬制度。
(一)工分制度
工分制度是在传统变工互助的基础上出现的一种劳动管理和分配制度。初级社时期采用“土劳分配”的方法。土地报酬是指按土地质量评产入股,按股分红。一般而言,土地是以户主的名义入股,分红自然也是以户主的名义分红。劳动报酬则是按入社社员个人劳动工分计算。在这里,妇女不再跟随父亲、丈夫参加劳动,而是以个人身份参加劳动,劳动报酬也属于个人劳动所得。“如莘县燕店区杨二庄乡李兰枝家三口人(一个男劳力)参加了合作社,男劳力整天忙于乡内工作,母女二人下地劳动,现在已得七百多工分,到秋收种麦后还能干600多工分,每个工(以十分计算)预计能分到十斤粗粮,共约计分一千三百斤粮食、地租、肥料等收入还未计算在内。因此,全家生活也较为富裕。”[10]
这一时期,尽管妇女从劳动中提高了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但妇女参加田间劳动仍不普遍,“1955年妇女全年参加田间劳动的时间只有30-50个工作日。”[11]这种情况到高级社时期有所改观,由于高级社时期的土地完全归集体所有,工分成为社员生活的唯一来源。这种分配制度使得一个家庭的收入和生活质量完全取决于家庭劳动力的多少和工分的多少。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妇女尽管不情愿参加农田劳动,尽管有系列的家务劳动需要解决,但为了有粮吃、有衣穿、有钱花,缺乏劳动力家庭的家庭妇女别无选择地参加到农田劳动中去“挣工分”。1956年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写道:“从1956年开始,妇女除了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以外,在七年内,要求做到每一个农村女子全劳动力每年生产劳动的时间不少于120个工作日。”[12](P191)
(二)同工同酬制度
妇女被动员起来参加生产劳动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同工不同酬(一般男社员每天记工10分,女社员每天记工5-7分)。虽然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明确提出男女同工同酬的概念,1954年9月,男女“同工同酬”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但是,全面正确贯彻执行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还未在实际工作中成为各级领导上的自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男女不平等的封建残余思想继续在工作中作怪,因此,不少地区无故压低或扣留妇女应得工分的现象还相当严重普遍。“馆陶征东农业社规定铡草500斤给20分,而8个妇女一天铡草2000斤,应给80分,结果社里只给了62分。武城城关区宋庄社规定抬砖88块给1分,女社员王振香和袁秀云一下午抬砖1025块,每人应得工分5.5分,结果社内每人只给2.5分。”“例如撒菜籽,男社员吴炳柱与女社员做得一样多,一样好,但是给吴炳柱评了7分,给赵玉华却只评了2.5分。赵玉华说:‘做一天活得两三分,做两三天才抵上一个男的,不如给家里采猪草合算些。’”[13]同工不同酬严重影响了妇女的生产情绪,同时也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盲目提出男女拼体力的错误做法,以造成女社员因从事劳动过重,从而影响身体健康的严重恶果。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充分使用和发挥妇女劳力的作用,各农社根据聊城地委的指示精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落实男女同工同酬原则。如深入进行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的思想教育,提高思想觉悟,彻底克服重男轻女和排斥妇女社员的错误思想倾向;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纠正公分定额的办法,“过去小包工的生产任务中,女社员播下一升种子的地,只评50多分,现在改为80分,这样女社员劳动一天,一般可以得到七八分”;[14]同工同酬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妇女对于生产劳动的顾虑,使她们在生产劳动中找到了与男性同等的价值,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原先十天才能完成的生产任务,现在七八天就能完成了。例如在积肥中,原计划22个女社员三天割草300挑,共得600分,结果三天割了400挑,得了800分。”[15]
综上所述,农业合作化时期,聊城农村妇女之所以广泛参加生产劳动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首先,生产观念的变化奠定了妇女参加劳动的价值基础。经过各级组织的大力宣传和教育,妇女摆脱了儒家纲常伦教的擎制,“劳动光荣”、“男女平等”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妇女参加劳动后,有更多的机会学习先进经验和农业技术,增加了受教育的机会和场合,提高了她们的思想觉悟,也提高了她们在家庭中的政治经济地位。其次,家庭问题的解决,特别是带孩子和穿衣问题的解决,使妇女参加劳动没有了后顾之忧。各合作社成立了农忙托儿组织,加强了对保姆的政治思想教育及育儿知识教育,解决了农忙季节孩子的看管问题;建立了缝纫组织,购买了缝纫设备,解决了群众的穿衣穿鞋问题。最后,工分制度和同工同酬制度的实施是妇女参加劳动最为直接的经济动因。广大妇女尽管不情愿参加农田劳动,但为了有粮吃、有衣穿、有钱花,缺乏劳动力家庭的妇女别无选择地参加到农田劳动中去“挣工分”;同工同酬制度的实施,使妇女在生产劳动中找到了与男性同等的价值,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一言以蔽之,聊城地区农村妇女广泛参加生产劳动乃是在“劳动光荣”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的一项集体性举动。
[1]马玉秀,徐燕英. 新区怎样发动妇女参加生产[J].新中国妇女,1950,(7).
[2] [3] [4] [9]中共大布区委发动与组织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经验(1956年3月16日),聊城市档案馆:4-2-44-63.
[5] [6] [7] [8] [10]莘县燕店区杨二庄在扩建社中的妇女工作情况,1955年10月20日,聊城市档案馆:4-1-41-287.
[11]高小贤.“银花赛”:20世纪50年代农村妇女的性别分工[J]社会学研究,2005,(4).
[12]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191.
[13] [14] [15]专区妇联关于当前生产运动中妇女工作上存在的几个严重问题与今后意见( 1956年7月11日),聊城市档案馆:4-2-44-218.
2015-01-15
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273165
林冬梅(1990- ),女,山东临清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李先明(1970- ),男,山东济阳人,历史学硕士,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本文通讯作者。
F321;K
A
1008-8091(2015)02-009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