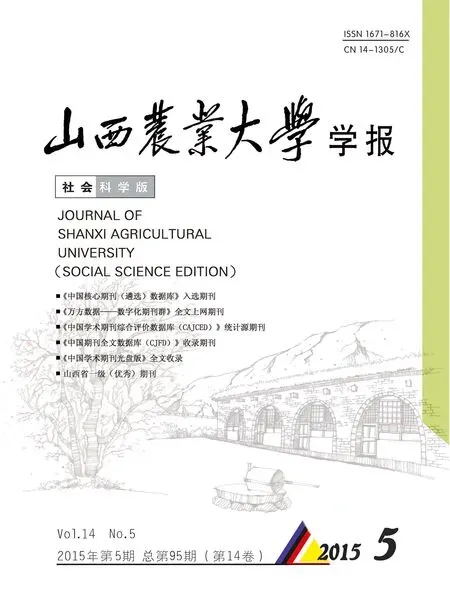从中国文化传播角度看汤亭亭的 《女勇士》
2015-04-02张树艳
张树艳
(内蒙古师范大学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010022)
从1976年出版处女作 《女勇士》开始,流散作家汤亭亭 (Maxine Hong Kingston)开始在美国文坛崛起,她的作品入选美国的权威文学选集,获得了众多文学奖项,她也成为在美国大学被讲授最多的作家之一。[1]她的作品中呈现出大量的中国文化符号,塑造了很多新的中国形象,尤其是在作品中使用和改编中国古典著作、唐诗与神话传说等,以文学为中介广泛传播这些中国意向和传统文化,其易接受性是其它翻译作品所不可比拟的。我国正处于文化向外传播的时期,分析作品中的这些文化意象,看作者如何利用独特的文化视角和传统文化因素,传承中国文化精神和传统,为从文学角度向欧美国家传播中国文化提供有益的启示,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
用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后殖民主义的关键理论中的东方主义、他者、身份、混杂性、“模拟”来分析 《女勇士》,特别是爱德华· 萨义德(Edward W.Said)的东方主义和霍米·巴巴(Homi K.Bhabha)的混杂性理论与第三空间理论。萨义德认为建立在东西方二元对立的基础上的东方学是西方用以控制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机制,这一层面上的东方学被称作东方主义,即西方是理性的、发达的、进步的、文明的;东方被矮化为非理性的、落后的、野蛮的、愚昧的。在西方文化霸权下,东方作为客体被西方虚构和异化了,并被局限其中。在二元对立与冲突中,东西方文化地位不平等,而且沟通被从根本上阻隔了。[2]霍米·巴巴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基础。他的混杂性理论打破了西方文化的核心地位,否定了文化身份的固定化,指出了建构混杂文化身份和文化第三空间的可能性,在当前的全球化背景下影响越来越大。[3]
一、汤亭亭的文化视角
研究汤亭亭的身份立场和视角,分析作者构建文化身份的过程,有助于我们探究作者在中国文化利用过程中的目的、角度和方式。
(一)中美两种文化影响下的双重视角
作为美籍华裔的流散作家,东西方文化间的碰撞使汤亭亭的世界观受到双重影响。汤亭亭1940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蒙士得顿市。1958年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文学学士学位。1970年起曾先后在夏威夷大学、东部密歇根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英国文学系教授,2001年起担任The Literature of California的主编。汤亭亭在学校中受到的教育都是在西方文化的大环境下,耳濡目染的是西方的世界观、西方文明和思想体系。另一方面,汤亭亭的祖籍是广东新会,她的第一语言就是广东的四邑方言。[4]与生俱来的中国血统,华人家庭和社区的影响,还有母亲用讲故事的方式让她了解中华文化传统,让她从幼年开始就从衣食住行、文化风俗、历史、传说等各个方面来了解和认识父母称之为家的中国。由于缺乏切身体验,父母在潜移默化中赋予她的中国文化有许多她无法理解的内涵意义,再加上截然不同的西方教育,使她的世界观充满了鲜明的文化冲突。双重文化背景和双重民族精神,带给她双重的视角,也带来了对自我身份的困惑。
(二)边缘人的立场
华人移民的第二代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中寻求平衡,在夹缝中生存。20世纪60年代之前,非白人的文化一直被美国主流文化排斥。作为少数族裔,其传统文化受到主流文化的冲击,位于社会和文化的边缘地位。少数族裔的身份也自然被边缘化。美籍华裔被界定为在美国的中国人,在中国又被看作是华裔的外国人。华裔女性还要面临当时的男权社会的压制,面临双重边缘化的窘境。汤亭亭成为一个 “文化边缘人”。但也正是这种身份困境为她反观两种不同文化提供了一个最有利的视角,反而成为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正如赛义德所言,“自从我有记忆起,我就觉得我同属于两个世界,不完全属于任何一方。同属于帝国分界线划分的两方,使人更容易理解双方”。[5]两种文化的冲击和疏离使她更容易摆脱任何一方的控制,对两者都能够进行客观的审视、评判与反思,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进行独立的思考。
(三)汤亭亭所处时代背景的影响
汤亭亭进入大学学习前后的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兴起了以黑人为主的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另外,一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后殖民主义兴起于西方学术界。七十年代后,西方的 “文化研究”开始关注以性别和种族为焦点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等问题上。美国不同种族、各阶层与女性的自我意识加强,弱势群体竭力为自己争取话语权。多元文化思想盛行。所有这些时代特色都为一直受到排斥的边缘文化提供了一个表述自我的大好时机。这些蓬勃发展的运动和新兴的文艺思潮对青年时期的作者影响深远。像汤亭亭一样的被双重边缘化的华裔女性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既渴望融入美国社会,也希望保持自己的中国文化传统,既要摆脱男权话语的控制,又要重新定义两性关系,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她们的文化身份构建需求就突显出来,其文化视角也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略显独特,并在文学作品中加以体现。
二、《女勇士》中勾勒的中国形象
(一)“模拟”东方主义话语下的中国形象
“模拟”(mimicry)是后殖民理论中一个关键词语。从后殖民的角度看,被征服者在被殖民之后被迫不断地对殖民话语进行模拟,在模拟的过程中也不断从内部对其进行改造,在殖民意识中发现,撕开裂缝,打破二者之间的二元对立,以抵抗西方文化中心论。[6]
汤亭亭在作品中,模拟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即描绘出东方主义话语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在实质上解构了东方主义话语。在 《女勇士》里,中国迷信愚昧、落后无知的一面,中国人的野蛮、怪异的生活方式与习俗都是刻板的东方主义的描写。例如,对蟾蜍吞月深信不疑的母亲形象,中国人如何生吃猴脑的细节描写。华人社区里满是言行神秘,说谎成性,在公共图书馆和电话里高声讲话的中国人。东方主义话语下旧中国形象,村民以集体为单位,没有自由的生活方式。作品中无名姑姑的婚外恋不是个人隐私而是人人得以诛之的集体行为。在完全不依靠法治的情况下,全村人可以依照传统做法对她处以私刑。这些对于中国人物形象和旧中国形象的刻板描述,是东方主义话语下,在西方文化霸权的视角下来审视的,以粗俗、野蛮、愚昧形象再现东方,使中国形象固定化。汤亭亭对东方主义话语的夸大模拟再现了其不合理性,在内部解构了东方主义。
(二)代表中西文化对立的母女形象与重构的华人新形象
对文化身份的建构,与建构者和被建构者密切相关。也就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如果说东方主义话语的 “模拟”在暗中间接解构了东方主义,那么对于二元文化对立的呈现,再加上对中国形象的重构,就是对东方主义的直接解构。
1.《女勇士》中的中西文化冲突是以母女形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移民母亲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美国出生的女儿代表着西方文化。母亲遵循中国的保守文化传统训导刚成年的女儿,希望通过灌输传统道德观念保护女儿不受伤害,所以在开篇告诫女儿不能把自己讲的无名姑姑的离经叛道的故事告诉别人。而女儿却把姑姑的故事写入小说中公布于众,使她摆脱被人刻意遗忘的境地,甚至用西方观念重新诠释姑姑的故事,把她想象成一个爱美,向往爱情和自由,大胆反抗男权社会的女英雄。母亲按照中国习俗把女儿的舌筋割断,希望她的舌头能够灵活地讲不同的语言,但是女儿认为这破坏了她完整的人格,反而使她更加与众不同,所以沉默不肯发声。
汤亭亭用边缘人视角,使中西两种文化平等对话,没有偏向任何一方,而是站在他者的角度去看待中西文化双方。用母、女两个中国形象向读者展现了异质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同时,汤亭亭用母女代际间的矛盾也表明了她的文化立场:无论何种文化都不能凌驾于另一种文化之上,二元文化对立状态对于面对双重文化甚至多重文化的任何人都会造成伤害,使其无所适从,陷于文化困境。
2.作品重构了华人新形象。小说第3章《乡村医生》塑造了一位独立、勇敢并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知识女性的新形象。母亲勇兰在广东乡村放弃了居家生活,独自来到广州学医,把“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世俗观念抛之脑后。母亲摆脱旧习,“有一技之长的女人不用夫姓,就用自己婚前的名字”。[7]母亲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母亲在深夜里敢在经常闹鬼的房间与鬼搏斗。她的勇敢、独立与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所有努力,塑造了新型中国女性形象,彻底颠覆了胆怯、懦弱、低眉顺眼、逆来顺受的被男权压制的传统中国妇女的刻板形象。现代版的 “花木兰”这个全新中国女性形象解构了东方主义话语下的中国形象,消解了固定化的概念与偏见。
(三)改编的中国神话人物形象
汤亭亭借用东西方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改编了中国神话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充分体现了霍米·巴巴的 “混杂性”身份理论与 “第三空间”理论。
1.中国神话人物形象间的杂糅
在 “白虎山学道”一章中,“我”是巾帼英雄花木兰和民族英雄岳飞杂糅起来的形象。“我”进入山中学习武功与战术,15年后学成回村,替父出征,斩妖除害,后又杀了当地的恶霸,复仇雪恨。出征前,父亲在 “我”背上 “刻上誓言和名字”。[7]“从镜子里我看到,我的背上满是一行行黑和红的字,像一排排士兵,我的士兵”。[7]其中还混杂了另一个中国民间传说孟姜女的形象。“我”登上长城,“我触摸着长城,摸着它一道道的石缝,寻找着修长城的人的指印。大家头抵着长城,把脸贴紧长城,像孟姜女一样放声恸哭”。[7]经过作者的杂糅,中国神话与历史间原本相距甚远的文化形象都出现在作品中的女勇士身上,这一创新形象传递出多重文化意蕴。
2.中西人物形象间的杂糅
《白虎山学道》中的 “我”不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 《木兰诗》中主人公的翻版,“我”不再是一个传统的华人女性,而是一个兼具现代西方女性的独立性与反抗性,也具有一些中国传统女性特点的一个新的华人女性形象。首先, “我”表现出一种突出的现代西方女性的独立性与主动性。“我”主动去白虎山学到了许多超自然的本领,目的是能够为家族复仇,而不是被迫替父从军,万般无奈。“我”可以与自己的丈夫并肩作战,不必因为家里有了可以上战场的男性成员就被替换。“我”能够带着襁褓中的婴儿征战,表示 “我”已经超越了生理与传统文化对女性的界定。女性的独立身份不再依靠男人的界定。甚至在孩子满月后, “我”让丈夫把孩子送回老家,继续在战场上厮杀。其次,“我”同时还有着中国传统女性的特点。“我”在战场凯旋后 “换上黑色刺绣的婚礼服,我像新娘那样跪在公婆面前。‘国事已毕,’我说,‘我要守在你们身边耕耘纺织,生儿育女’”。[7]“我”还可以做一名传统的中国女性,做家事,孝敬公婆,相夫教子。
中西文化混杂后的花木兰形象突显出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也表现出东西方文化不必一直是对立的状态,是可以交融的,这种混杂的方式更能取长补短,更好地被双方认可并接纳。
3.古今人物形象间的杂糅
现代深陷双重文化夹缝中失语的第二代华裔女孩与历史故事中蔡文姬形象融合在一起。蔡文姬的故事被作者改写,细节上着重突出了她结合胡乐与汉辞谱写出,并用清脆嘹亮的声音唱出胡人和汉族都能欣赏的歌曲。她的歌声既与异质文化的笛声合拍,又使用了本民族的语言,但最终异质文化的匈奴人和本民族的汉人都听懂了歌曲中发自肺腑的深切意蕴。《女勇士》的叙述者在现代相冲突的两种文化夹缝中无法找寻自己的身份和位置,在西方文化的大环境下完全失语,但最后找到了解决方法,与蔡文姬的形象重合,变为一体,大声唱出了自己的歌。歌声象征着不同文化间平等沟通、文化包容、甚至融合的愿望。华裔站在两种文化间,不能抛弃任何一种文化,如果抛弃西方文化,他们会失去生存能力,如果抛弃中国文化,他们会迷失自我。只有建构在平等基础上的文化融合的第三空间,才是建立文化身份最好的方式。
三、这些中国形象带来的中国文化传播的启示
(一)解构东方主义话语
汤亭亭在作品中 “模拟”东方主义的话语述说中国,对西方文化霸权发起挑战,解构东方主义。而作品中对西方的描绘,也是在 “模拟”“西方主义”,也是对东方主义的对抗与解构。荷兰学者伊恩·布鲁玛与以色列学者阿维赛·玛格里特的合著 《西方主义:敌人眼中的西方》(2004)一书中提到,非西方人也存在着对西方世界的偏见、报复性想象以及去人性化理解。[8]《西宫门外》一章中的月兰看到自己的美籍外甥们全无中国式礼仪礼貌,觉得自己 “来到了野蛮人的国度”。[7]她得出的结论是,这种野蛮地方污染了丈夫,这是其抛妻弃子的根本原因。可见中国文化传播过程中解构东方主义话语的必要性,也可以看出无论东方主义还是 “西方主义”对于文化交流和传播都没有积极影响。汤亭亭作品的视角永远是不确定的,不会孤立倔强地站在任何一个立场。这样,不同文化间的对话才能是平等的,才能展开对话与交流。站在一个他者的视角对两种文化都进行理性的反思和审视,在消解二元文化对立的基础上,开始重建自己的文化身份,并表述自己的文化观。从汤亭亭有效传播文化的范例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在促进中国文化向欧美国家传播过程中,首先要解构东方话语,破除中国刻板形象,但是也要注意不能本位化,不能走极端,不能无故贬低或完全排斥其他文化。
(二)创新的文化意向与传统文化本身
除了 《女勇士》,汤亭亭在其它的作品中有非常多经过改编、杂糅的中国神话人物、历史文化符号、古典文学作品和民间故事。这些重塑的中国文化形象,不但解构了对华人的东方主义印象,而且表达了作者,也就是华裔,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使这些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到欧美异质文化国家。
汤亭亭这种创新式的再创造也因其对中国文化符号进行改变,而受到了质疑。但是这些创新的文化意向并没有使中国传统文化失去其本真性与权威性,反而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意义,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面向未来发展的可行性。汤亭亭创新的文化意向使古老传统的中国文化更易于被欧美国家接受,使他们可以在感兴趣的同时接受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在西方语境下得以延伸和渗透。正像霍米·巴巴所说的 “文化是在与他者的接触中和碰撞过程中获得意义的,是在与异质文化的相互定义中被生产和确定的”。[9]由此看出,我们要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就不能使古老传统的文化封闭、静止,而要突破“非中即西”的思维局限。即使是西方的故事,也可以被用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书写华人历史。古老的中国神话、传说及历史符号等传统文化意向,因为封闭不变而不被欧美国家理解,甚至遗忘,绝非我们的初衷。我们可以通过创新式的改变使中国传统文化焕发独特的生机和活力。
(三)中国文化与 “世界小说”
《女勇士》叙述了美籍华人的生活经历,但涉及的题材广泛,有边缘人身份、女权主义、文化冲突等,展现了后现代文学特征 ——多元叙述视角、互文性、空间转换等。其中,采用的口述文本把中国的传统叙事技巧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写作风格融合起来,这是文化 “第三空间”的最好实践。这说明我们不仅可以通过描写文学形象和文化符号等主题思想的手段传播中国文化,而且中国有大量的古典、经典作品,选取其中可用的艺术手法融合后现代创作技巧,以创新的中国文化形象为主题思想,也是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有效方式。那么汤亭亭提倡的 “世界小说”的写作方向是可以实现的,作家可以用自由的创作态度和视角叙写审美理想,传播民族文化。我们可以通过世界小说的方式,用中国特有的艺术手法来创新、增补世界文学的艺术技巧,通过树立新的中国形象来言说普遍的人性,通过描述中国人的生活来体现世界性的生存状态,通过言说中国文化来支持文化多元性。
四、结语
从中国文化在欧美国家传播的角度来看,汤亭亭利用其流散作家的独特视角,对中国文学形象进行创新,对中国传统文化意象进行改写,解构了东方主义,实践了文化身份混杂理论与第三空间理论,更好地促进了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间平等沟通、交流和相互对话,也使中国文化在异质语境下更易于传播,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面向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对中国文化外播有启示作用。
[1]白丽.汤亭亭小说 《女勇士》的文化解读 [J].柳州师专学报,2010(6):60-64.
[2]黄秋晓.混杂中寻求 “第三空间”——窥探 《女勇士》中汤亭亭的文化观 [D].合肥:安徽大学中文系,2011:7-8.
[3]生安锋.霍米巴巴后殖民理论研究 [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2004:53-57.
[4]胡春梅.汤亭亭作品中文化 “身份问题”的思考 [D].西安:西北大学,2001:1-2.
[5]郑庆庆.站在边缘的女勇士对汤亭亭 《女勇士》的跨文化观读解 [J].外国语言文学,2005(1):59-64.
[6]陆薇.模拟、含混与杂糅——从 《蝴蝶夫人》到 《蝴蝶君》的后殖民解读 [J].外国文学,2004(7):86-91.
[7][美]汤亭亭著,李剑波,陆承毅译.女勇士 [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69,31,32,39,41,122.
[8]毛秋月.“东方主义”话语的建构与解构—— 《女勇士》中的中国女性形象评析 [J].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9):66-68.
[9]陆薇.走向文化研究的华裔美国文学 [M].北京:中华书局,2007: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