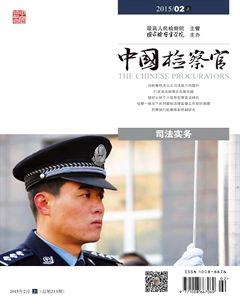假借职务便利侵占他人财物问题研究
2015-04-02赵煜
文◎赵煜
假借职务便利侵占他人财物问题研究
文◎赵煜*
国家工作人员假借职务上的便利,私自实施侵占他人财物的,其假借职务便利不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能构成贪污、受贿、职务侵占等职务犯罪,只能构成敲诈勒索、诈骗、侵占等非职务犯罪,并因其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从重处罚。
假借职务便利 侵占财物 职务犯罪
在贪污、受贿、职务侵占等职务犯罪案件中,行为人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相关行为,才能构成犯罪。实践中,对行为人假借职务上的便利,私自实施侵占他人财物的行为应如何认定,理论上存在争议。一种意见认为,行为人假借职务便利不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能构成贪污、受贿、职务侵占等职务犯罪,只能构成敲诈勒索、诈骗、侵占等非职务犯罪;另一种意见认为,行为人假借职务上的便利亦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可以构成相关职务犯罪。实践中,相关案件的处理亦存在不统一、不平衡的现象。对此问题,需认真研究解决。
一、认定为非职务犯罪的相关案例
[案例一]民警王某与李某(社会待业人员)商量,晚上去旅馆抓赌,收缴赌资。二人到某旅馆让服务员把各间房门打开进行查夜。当打开12房时,看见四人在打麻将,桌上每人身边放了一小部分现金。王某说:“我是民警,来抓赌的,你们把身上的赌资拿出来,免得罚款。”相关人员看王某穿着警服,即把钱拿出,共有6000元。其中有一人身上没有钱,王某把他带在身上的手机拿走,并表示:“要收据的话,明天来派出所领。今天没有带收据和扣押单来。如明天要来打收据,你们还要交罚款。”[1]
该案中,王某借执法之名,以威胁或要挟的方法使赌博的人感到恐惧、害怕,把身上的钱交出来,而王某声明身份、身穿制服,在外形上以执行公务表现出现,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威胁、恫吓,只是借公务执法之名达到非法占有别人财物的目的,其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关于“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实施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强索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的特征,应定性为敲诈勒索罪。对此,有学者指出,类似于假借单位的名义或者以执行职务为名,取得外单位或者个人的财物,不能构成贪污罪。因为所谓“职务之便”,是指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便利,而不是指行为人利用自己的职务去招摇撞骗或者敲诈勒索。行为人假借单位的名义或者以执行职务为名取得他人财物,并没有取得主管、管理、经手该财物的合法的便利条件,该财物不是行为人因执行公务而取得的,而是行为人招摇撞骗或者敲诈勒索所获得的赃款,其行为不具有渎职性,应以构成的其他相关犯罪论处。[2]还有学者认为,职务犯罪必须发生在履行职务行为当中,客观上要有履行职务的行为,主观上要有履行职务的意识。警察带不具有警察身份的人一起“抓赌”,如果仅仅是以警察身份相胁迫,没有使用暴力,就应定敲诈勒索罪。[3]
[案例二]田某某,原系中国银行某市分行建东支行某分理处出纳员。1999年8月至2002年1月,田某某采用自制“高额利率定单”,再盗盖单位储蓄业务专用章、同班业务人员印鉴,对外虚构银行内部有高额利息存款的事实的手段,共吸纳亲朋好友等人现金90万余元,用于归还个人债务,购买、装修房屋等。[4]
该案中,检察机关以田某某犯贪污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为:田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自制“高额利率定单”,再盗盖专用章、印鉴,对外虚构高额利息存款的手段,骗取现金90万余元,构成诈骗罪。主要理由是,田某某作为银行出纳员,向储户吸纳存款的业务并非其职权范围,且其所在银行并未开展高额利率存款业务,“高额利率定单”完全是其自造的。根据银行内部储蓄规定,存单须有出纳、会计共同审核盖章并加盖银行储蓄专用章后方能生效。田某某系出纳,只负责保管本人印鉴和银行储蓄专用章,并不负责保管其他工作人员的印鉴。“高额利率定单”上的公、私章均是田某某在同班人员疏忽大意完全不知的情况下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条件偷盖的,使他人误以为是银行存单。田某某的行为不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而是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条件,不符合贪污罪的客观要件,不构成贪污罪。
[案例三]姚某某,某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临时聘任人员。何某某,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临时聘任人员。冯某某,无业。2002年6月,冯某某利用姚某某提供的票面金额50元的两张“省罚没款统一收据”,两次找人复制印刷了1.6万余张假收据,总票面值达80余万元;冯某某还找人伪造了“省财政厅罚没收据专用章”、“市交通警察大队收据专用章”各一枚。此后,冯某某与姚某某协商,准备用假收据上路罚款。自2002年8月19日晚开始,姚某某勾结何某某,利用冯某某分四次提供的票面值共计1.62万元并加盖了假公章的假罚款收据,连续4晚对过往的煤矿车辆进行“违章罚款”12250元,直至8月22日晚被市公安局查获。查获时,收缴赃款2000元,其余10250元赃款,已被姚某某、何某某、冯某某分用。[5]
该案中,检察机关以姚某某、何某某、冯某某犯贪污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姚某某等人辩称,姚某某、何某某都是交通警察大队的临时聘任人员,二人持冯某某提供的假收据,未经任何人批准,趁下班休息时间超越执法范围私自查车罚款,不是职务行为,不应认定为贪污罪。法院经审理认为,姚某某、何某某虽然是市公安交警大队的临时聘任人员,并且是以警察身份实施犯罪,但他们的职务是在市区的交通警亭上纠正交通违章,没有权力到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乡村路段处罚过往车辆,不是其职务上的便利;以警察身份实施犯罪,正是诈骗犯罪中常见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之犯罪手段。贪污罪侵犯的是公共财物所有权,而姚某某、何某某侵犯的却是过往司机的私人财产所有权。姚某某、何某某、冯某某使用假罚款收据罚款12250元后私分,其行为构成诈骗罪。
[案例四]赵某系某县看守所民警,2003年至2008年,赵某先后与多名在看守所羁押的犯罪嫌疑人的家属或朋友联系,以在押人员要求改善生活购买食品,或帮助在押人员购买香烟等违禁物品的名义,让在押人员的家属或朋友给其送去现金。多名在押人员的家属或朋友先后将总额达数万元的现金交给赵某,委托其帮忙给在押人员购买食品或香烟等物,并要求赵某对在押人员给予照顾。赵某仅将在押人员的家属或朋友送去的现金的一部分给在押人员购买食品、香烟等物品,剩余款项被其本人占有。5年来,赵某共计占有上述款项3万余元。个别在押人员的家属虽然也怀疑送的钱多,没有用完,但因赵某是该在押人员的包号管教干警,所以一直未敢声张。[6]
该案中,对赵某的行为如何认定,存在受贿、诈骗、贪污等多种意见,后有关司法机关认为其行为构成侵占罪。主要理由是,赵某的职责是对在押人员进行监管,而并非受看守所的指派、委托负责经手、管理在押人员家属为在押人员所送的钱物,其收取在押人员亲属、朋友的钱款用于为在押人员购买物品,完全是个人行为。同时,监狱禁止罪犯消费烟酒等特定食品,也禁止警察为罪犯带进这些物品。赵某的行为是违背职责、超越职权范围从事与职权无关的行为,谈不上“利用职务之便”。有学者指出,如果认为此种情况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行为人的行为就可以被视为代表监狱所实施的行为,行为人侵吞的财物监狱就有义务进行赔偿,在案件处理上会带来不合理的后果。[7]
在上述案例的处理中,有关司法机关认为行为人假借职务上的便利所实施的行为,实际上系个人行为,不构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应以敲诈勒索、诈骗或侵占等非职务犯罪论处。
二、认定为职务犯罪的相关案例
[案例五]杨某系某市地税局二分局征稽管理科科长。2004年1月前,二分局所属户管单位申印税务冠名发票,由二分局指定印刷单位印制,二分局收取10%的监印费。2004年1月,二分局停止该项收费。杨某在本单位停收监印费之后,对外谎称原监印费改为以下属公司咨询费的名义收取,并先后收取97万余元予以侵吞。[8]
有关司法机关认为,该案应认定贪污而非诈骗。主要理由是,杨某有代表单位行使发票管理的资格和能力,有关单位有理由相信杨某有权收费。贪污罪中的职务不仅包括单位明确规定的职责范围,在特定情况下还包括行为人利用其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身份,冒用“职务”之便侵吞公款的行为。借鉴民法表见代理理论,杨某假借职务便利的行为,构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因此其行为构成贪污。
[案例六]某铁路局房地产经营管理中心修建段以通知方式公示了某社区参加集中供暖和暖气初装费标准。此后,经营管理中心修建段职工、社区水暖收费办公室负责人王某等人参与了对该社区住户安装暖气的摸底调查和测量工作,因该社区安装暖气的住户人员没有达到集中供暖条件,修建段未下达设计图纸,也未张贴收取暖气初装费的通知。但该社区要求安装暖气的12户居民自发将10万余元初装费交给了王某,后被王某挥霍。[9]
该案中,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对王某提起公诉。王某辩称其行为构成侵占罪。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王某作为水暖收费办公室负责人,收取安装费应是其职务的一部分。王某在没有单位授权的情况下,私自决定收取该费用,只能说明该单位管理上存在纰漏。如果不是王某的这种特殊身份,其不可能收取居民的暖气初装费。鉴于王某未使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让12户居民向其交出财物,不构成诈骗罪。王某与12户居民之间不存在合法的委托或保管关系,不构成侵占罪。王某的行为应以职务侵占罪论处。
在上述案例的处理中,有关司法机关认为行为人假借职务上的便利所实施的行为,属于表见代理,构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应以贪污、职务侵占等职务犯罪论处。
三、对假借职务便利是否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问题的分析意见
笔者认为,假借职务便利实施的个人行为不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也不宜认定相关职务犯罪,理由如下:
首先,不宜把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所实施的行为都视为职务行为。职务行为应当具备其职务性,即根据国家机关、国有公司等国有单位的授权、安排从事公务,而不是自行虚构公务事项。例如,国家工作人员根据国家机关的安排进行收费、罚款等活动,在履行公务中通过用虚假单据入账等方式将所收钱款占为己有的,应以职务犯罪论。但行为人在执行公务以外,擅自实施的个人违法犯罪行为,应由其个人承担法律责任,而不应视为其代表国家机关、国有单位实施的行为,并导致国家机关、国有单位承担政治、社会和法律上的不利后果。例如,在某案中,2000年,董某、岑某商定,利用两人在东方明珠电视塔公司工作的便利,伪造东方明珠塔观光券出售。后董某将伪造的观光券在东方明珠观光塔售票处出售,岑某则检票让购买伪造观光券者进入电视塔游览,共计职务侵占23.6万元。笔者认为,该案以职务侵占罪认定是正确的。董某利用了在售票处售票的职务便利,岑某则利用了检票的职务便利。相反,如果董某、岑某伪造观光券后在其他私人场合兜售,并未利用售票、检票的职务便利,则不能认定职务侵占罪,应当以诈骗罪认定。
其次,对于行为人假借执行公务、盗用职务便利所实施的行为,不宜套用表见代理理论。套用表见代理理论解决相关刑事犯罪认定问题,具有较大缺陷。关于表见代理,《合同法》第49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据此,表见代理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与有权代理一样,均由被代理人承担。笔者认为,表见代理属于民法领域中的概念,用于调整平等主体间的民事关系。但在刑法领域中,无论国家机关与其工作人员的关系,还是国家工作人员与其管理对象之间的关系,均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具有本质差异,民事上代理人实施相关行为的责任可由被代理人承担,但刑事责任则只能由行为人本人承担。如果认为行为人假借职务便利向管理服务对象收费属于代表国家机关实施的职务行为,则其所收取的费用即属国家机关代为管理的私人财物,这些财物一旦被行为人挥霍,国家机关将代为赔偿,这一结果显然是不合理的。同时,表见代理制度的目的在于维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而刑法领域要解决的则是行为性质的认定问题,二者出发点根本不同。例如,在表见代理中,被代理人取消委托后,应采取收回代理证书,通知第三人,或者发布撤销代理权的广告等措施,如果被代理人没有这样做,致使相对人不知代理权被撤销,仍与代理人为民事行为,则构成表见代理。但在刑法领域,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后,国家机关一般不会对社会发布公告。如果机械套用表见代理理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对外实施的行为,依然构成表见代理,应以职务犯罪论处,这显然是错误。因此,由于民事与刑事属性差异巨大,此类问题不宜套用表见代理理论解决。
再次,不宜因认定非职务犯罪存在困难,而选择性认定职务犯罪。这一问题在侵占罪的认定中比较突出。在侵占罪中,有时权利人因陷于认识错误而将钱款交给行为人,不存在索还的情况,因而也就不会出现行为人拒不返还或拒不退出财物的情况。如上述某铁路局房地产经营管理中心修建段职工、社区水暖收费办公室负责人王某一案中,就不存在12家住户向其索还钱款的问题,导致认定侵占罪存在一定困难,实务部门往往会倾向认定职务侵占罪。对此有学者认为,侵占罪中的拒不退还或者拒不交出,既可以是在权利人要求返还时拒不返还,也可以是在取得托管财物后逃匿而事实上不予返还,还可以是故意编造各种口实或制造各种骗局以达到不返还的目的。总之,其实质或核心在于,这些客观行为足以证明行为人具有永久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即可。[10]笔者赞成这一意见,应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对行为人假借职务上的便利,收取他人缴纳财物,隐瞒真相并具有永久占有故意的,也应以侵占罪认定。
最后,对假借职务便利实施的行为,以相关非职务犯罪认定时,应考虑从重处理。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134条规定,假借职务上之权力、机会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渎职罪)以外各罪者,构成不纯正渎职罪。对此,有学者解读认为,行为人只要利用职务上的权力、机会或方法而犯罪即为已足,而不以合法执行职务为必要,故公务员执行职务,纵非合法,若系利用其职务上的权力、机会或方法而实施者,可适用本罪处断。[11]最典型的不纯正特别犯,为公务员假借职务上之权力、机会或方法而违反之渎职罪章以外各罪者,此种非纯粹渎职罪因公务员之特别身份而依法加重其刑。[12]如县长利用职务上的权力押人殴打致死,适用轻伤罪并根据第134条的规定加重刑罚。可见,不纯正渎职罪并非独立的犯罪类型,而是因公务员身份而加重处罚的规定。公务员假借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犯罪行为,应当以相关职务犯罪以外的个人犯罪论处,但由于这种犯罪毕竟是利用了公务员的身份等特殊条件,在处理时应当加重刑罚。参考这一规定,对国家工作人员假借职务便利实施的行为,不宜认定为职务犯罪,可考虑以个人实施非职务犯罪论,并因其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从重处罚。
注释:
[1]尧在富:《警察私自抓赌如何定性》,http://www. 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02/10/id/14288.shtml,访问日期:2014年7月10日。
[2]孙国祥:《贪污贿赂犯罪疑难问题学理与判解》,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3]徐建波、杨涛:《实习警察伙同他人“抓赌”行为如何定性》,载《人民检察》2005年第7期。
[4]熊选国、任卫华:《刑法罪名适用指南(侵犯财产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4页。
[5]《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3年第5期。
[6]冀晓波、李红岩:《管教民警截留在押人员钱财受贿、诈骗、贪污,还是侵占?》,载《河南法制报》2012年8月2日。
[7]倪泽仁:《贪污贿赂犯罪案件重点难点疑点新释新解》,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年版,第210页。
[8]沈志先:《职务犯罪审判实务》,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53页。
[9]陈兴良、张军、胡云腾:《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旨通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08页。
[10]黄祥青:《刑法适用要点解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334页。
[11]林山田:《刑法各罪论(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4页。
[12]林钰雄:《新刑法总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页。
*中纪委案件审理室[10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