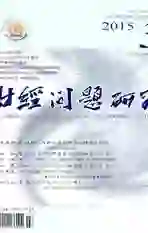基于经济指标构建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
2015-03-30孙琦峰
孙琦峰
摘要:本文选用人均GDP、GDP增速、基尼系数、物价指数和失业率等5项经济指标对社会稳定风险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国际横向比较,我国社会稳定程度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主要得分在高速的GDP增长、较低的物价指数和失业率方面;自身纵向比较,我国社会稳定风险近年呈加大趋势,主要失分在贫富差距扩大和通货膨胀压力上升方面。笔者的分析结果显示,确保在贫富分化项上不再失分甚至有所加分,即确保贫富差距不再扩大并力争有所缩小,对于保持社会稳定极其重要。
关键词:社会稳定风险;中等收入隐阱;经济指标
中图分类号:F124;F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3-0016-08
在中等收入阶段,国家最大的风险往往是社会稳定问题,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问题是经济发展问题。如果一国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很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贾冰[1]认为,社会稳定是指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等不同领域的稳定状态,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社会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从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一个动荡的社会不可能创造出经济繁荣的奇迹。而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的强大,进而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稳定。两者辩证统一,在中等收入阶段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有利于国家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
一、文献综述
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社会风险逐渐被社会学界所关注,贝克、吉登斯等均对社会风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有关社会风险的理论[2]。Bauer[3]在20世纪60年代运用指标引领社会预警研究的热潮,社会各界热衷于建立各种社会预警指标体系,其中包括经济与社会风险相关的指标体系。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要求,要“建立健全各种预警和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的能力”。2003年9月召开的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2003年“非典”是近期突发事件风险治理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处理突发风险事件的应急预案和规章制度等陆续密集出台完善。《中华人民共和突发事件应对法》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的出台和实施则从法律制度上提供了确认和保证。
虽然各级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都非常重视传统风险,但我国目前的风险预警和管理主要集中在自然灾害、社会治安等传统领域,对于因经济纠纷、贫富分化和腐败等问题引发的突发性事件则明显关注不够。
多种迹象显示,我国已进入社会稳定的高风险期。研究社会稳定的规律、寻找社会矛盾的成因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把握战略机遇、实现可持续发展十分必要。郭平和李恒[4]认为社会稳定受各种复杂因素影响,包括经济状况、人口素质、贫富差距、社会保障、国际关系、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等。但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是社会稳定的基础[5]。
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的构建
1961年,蒂里阿基安提出了社会动荡发生的经济指标,即城镇化进程、文化和社会道德的沦丧和宗教信仰缺失。宋林飞[6]提出了5大类49个指标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为了实用性他改进了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进一步细分为先导指标、同步指标和滞后指标。
本文从中等收入陷阱角度出发,根据研究需要设计了以经济指标评估社会稳定风险的5大类经济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对指标赋权评分,以此比较各国社会稳定风险大小和我国社会稳定风险的变化。结果显示:横向比较,我国社会稳定风险在国际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纵向比较,我国社会稳定风险呈现加大趋势。
(一)模型来源
国内外经验表明,有5项经济指标与社会稳定程度密切相关,即衡量总体国民富裕程度的人均GDP、衡量整体国民收入提高速度的GDP增速、衡量贫富差距大小的基尼系数、
衡量居民生活负担水平的物价指数和衡量社会就业状况的失业率。
1.人均GDP。人均GDP既代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又反映国民总体富裕程度。纵观世界各国,人均GDP高的国家,社会稳定程度通常也较高。一方面,高收入国家民众生活水平普遍较高,人心稳定;另一方面,经济并非孤立地发展,经济发展会促进社会进步,高收入国家的社会制度通常也比较完备,化解社会不稳定因素的能力也较强[7]。
2.GDP增速。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增长是改善社会稳定情况的重要因素。在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阶段,经济较快增长的国家,其社会稳定状况通常好于经济增长乏力的国家。
3.基尼系数。经济增长的成果并非总为经济各部门和社会各群体平均分享,分配不均尤其是分配不公势必会带来不同部门和群体之间的摩擦甚至对抗。而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利益格局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可能更为突出,社会稳定形势也就更为严峻。
4.物价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衡量居民生活负担的重要指标,居民生活负担急剧加大将造成社会成员的普遍不满。
5.失业率。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问题。无业不稳,无事生非。大量失业对社会稳定的威胁不言而喻。世界各国因高失业率引发的社会动荡屡见不鲜。
(二)模型的构建和权重的确定
本文选取的社会稳定模型由人均GDP、GDP增速、基尼系数、物价指数和失业率等5项经济指标组成。在本文中,指标经过无量纲化后的数值与其权重的公式如下:
其中,Imtk表示m经济体第t年第k项指标得出的分值,k=1,2,…,5,分别对应人均GDP、GDP增速、基尼系数、物价指数和失业率; Wk表示第k项指标的权重; Xkt表示第k项指标中所对应的在第t年的取值。
权重值的确定直接影响综合评估的结果,权重值的变动可能引起被评估结果的大幅改变。因而合理地确定综合评估社会稳定模型各主要因素指标的权重,是评估能够成功的关键。本文采用熵值法和专家调查法(德尔斐法)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权重,对5项经济指标计算得出的Imtk,并对Imtk进行取对数归一化处理得出I,分数区间为0—10分。
本文选取的社会稳定模型由五项经济指标(人均GDP、GDP增速、基尼系数、物价指数、失业率)组成。将某一类指标无量纲化后的数值与其权重公式如下:
其中,i=1,2,…,5;wl表示第l项指标的权重;xlt表示第i项指标中所对应的在第t年的取值。
权重值的确定直接影响综合评估的结果,权重值的变动可能引起被评估结果的大幅改变。所以,合理地确定综合评估社会稳定模型各主要因素指标的权重是进行评估能否成功的关键问题。
文章采用熵值法和专家调查法(德尔斐法)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权重,并对五项经济指标进行计算得出数值Iit,对Iit进行取对数归一化处理评分得出I,分数区间为(0—10分)。
(三)社会稳定程度的国际比较
根据这5项经济指标,
经济指标主要采用世界银行数据,多为各国官方数据;缺失指标采用美国中央情报局2011年《世界各国概况》中的评估数据。其中,人均GDP、基尼系数采用最新数据;GDP增速、物价指数、失业率采用2006—2010年的平均数。本文对全球人口超过500万的113个国家的社会稳定程度进行了评估,综合得分越高表明社会稳定风险越小。结果显示,发达国家社会稳定风险普遍小于发展中国家。综合得分前10位中有7个是瑞士、荷兰、丹麦和瑞典等北欧国家,排名最后10位中有9个是非洲国家。
我国排名比较靠前,名列第23位,表现好于目前受债务危机严重困扰的意大利(第26位)、希腊(第29位)、西班牙(第34位)和葡萄牙(第37位);我国在发展中国家中仅次于白俄罗斯(第15位)、古巴(第21位)和老挝(第22位)。
我国主要得分项是较快的经济增速、较低的物价指数和失业率。但我国官方失业率为4.1%,明显偏低。
国家发改委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6月底,全国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5%,连续4个月下降。这是我国官方首次正式发布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物价指数涨幅也未能反映房价上涨给居民生活带来的压力。若以10%的失业率计算,则我国排名将后移18位,名落印度、泰国、马来西亚甚至孟加拉国、柬埔寨和缅甸之后。
不过这几个国家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似乎也明显偏低,如印度和缅甸公布的失业率都是2%,泰国仅1.10%。
发达国家中,一些南欧国家综合得分较低,主要是因为近年其经济陷入衰退,失业率升至历史高位。发达国家中排名最后的葡萄牙2006—2010年GDP年均增长仅0.50%,年均失业率达到8.70%;排名倒数第2位的西班牙2006—2010年GDP年均增长仅0.90%,年均失业率高达13.20%;倒数第3位的希腊2006—2010年GDP年均增长仅0.30%,年均失业率达到7.40%。这些国家2011年经济普遍陷入衰退,若以最新的数据计算,其综合得分会更低,社会稳定风险明显加大。
2011年以来发生动荡的阿拉伯国家排名普遍靠后。最早爆发动乱的突尼斯全球排名第69位,苏丹第84位,利比亚第87位,也门第96位,叙利亚第55位,埃及第53位。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失业率较高,2006—2010年平均15.50%;物价指数涨幅也较高,2006—2010年平均8.20%;其经济增速倒并不慢,平均5.30%;基尼系数在发展中国家中也不算高,平均0.37。这些国家综合得分较低,社会稳定的基础较差,近些年这些指标逐年恶化,社会稳定风险加大,出现动乱并非偶然。
拉美国家除古巴和秘鲁外,全球排名均在60位之后,其中海地在全球排名倒数第3位。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普遍偏高,平均超过0.50,
基尼系数0.40被普遍认为是条警戒线,这大致相当于80%的居民只得到全国收入的40%;基尼系数超过0.50被普遍定义为“收入差距悬殊”;基尼系数超过0.60几乎不可想象,这意味着20%的富有居民获得了全国收入的80%。其中巴西为0.52,墨西哥为0.48,智利为0.52,哥伦比亚为0.56。拉美是世界上社会治安较差的地区,严重骚乱和政局动荡的频率也较高,显然与其经济指标较差,尤其是贫富分化相关。在基尼系数最高的海地(0.592),2008年以来多次发生严重骚乱和政局动荡,以至于需要联合国派出维和部队。
(四)分项指标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考察5项经济指标对社会稳定综合评分的影响可以看到,GDP增速与社会稳定的相关性最差,而其他4项指标都与社会稳定程度呈现明显的正相关或负相关。
本文研究并未显示GDP增长越快,社会稳定程度越高的态势,原因在于:首先,高收入国家经济增长通常慢于中低收入国家,但其社会稳定程度依然较高。其次,快速的经济增长通常也意味着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社会变迁和社会公众诉求变化的加快,由此加大了原有社会管理体制与新的社会条件产生脱节的风险。最后,经济增长较快常带来通货膨胀上升和贫富分化加大,由此抵消了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的提升作用。不少研究者认为,快速经济增长因推动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对传统的社会稳定结构的破坏作用大于促进作用[8]。
但坚持经济增长会促进社会稳定的研究者则强调:首先,经济增长总体上使社会个体的收入普遍增加,不同程度满足了人们提高生活水平和其他自我需求实现的要求。其次,经济总量增加意味着政府手中掌握的资源增加,加强了其处理社会经济事务和应对社会问题的能力。再次,经济增长能给民众以良好的社会预期,一个期待着将来能改善自身状况的人通常也是社会稳定的促进者。最后,在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上,经济增长较快的经济体还是对应着较高的社会稳定程度。
不过经济增长也并非越快越好,经济过热之后终将被迫调整,而经济波动会导致人们过高的收入预期落空,从而产生不稳定因素。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地区社会动荡普遍加剧,甚至连发达国家也频发大规模抗议活动和恶性社会治安事件,这也表明经济下滑会加大社会稳定风险。
人均GDP与社会稳定程度呈明显正相关关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相关性在人均GDP达到15 000美元之前并不明显,不少中等收入国家的社会稳定评分甚至不及低收入国家,这正是“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之一。主要原因在于,很多低收入国家处于相对静态的传统社会,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形成的传统社会有其平衡乃至压制社会矛盾的机制,从而具有一种低水平的稳定性。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必然引发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要求,相应的社会变革会引发大量新矛盾,这些新的社会矛盾超出了传统社会机制的应付能力,而新的有效的现代社会管理制度又未能建立,这种转型和改革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难以避免的,“中等收入陷阱”由此成为许多国家发展过程中难以跨越的一道鸿沟[9]。
拉美国家就曾普遍陷入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一些东南亚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也出现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非洲的南非和利比亚的人均GDP在1万—1.5万美元,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其社会稳定程度也明显低于“正常”水平[10]。
基尼系数、失业率
2014年6月国家首次公布的全国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5%,因为缺乏连续性,所以本文采用登记失业率或作者通过研究估算的值。和通货膨胀率与社会稳定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对此政界、学界均无争议。
总体来讲,全球范围来看,GDP增速对社会稳定并不能起到主导作用,甚至还不如基尼系数等指标的影响大。这说明如果经济增长加大贫富差距,加快物价上涨,同时又不能有效提高就业率,那么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的贡献很可能还不及其负面作用对社会稳定的损害,这对“GDP挂帅”的观念是个严重警示,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调整。
三、我国社会稳定风险态势分析
(一)我国社会稳定风险呈上升趋势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稳定评分总体快速提高,主要加分来自城乡收入差距
因缺乏我国基尼系数的连续数据,国内历年比较中我们选用了城乡收入比来反映贫富差距的变化。缩小和失业率降低。1988—1989年的严重通货膨胀使物价指数项得分为零,1989年经济增速下降又使GDP增速项丢分,导致总体得分陷入低谷,社会稳定风险骤增。之后我国社会稳定评分虽有波动,但至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又恢复到一个较好水平。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稳定评分总体稳中趋降,主要失分项是贫富差距拉大和通货膨胀压力加大。
不过,我国公布的失业率明显偏低,物价指数也未能充分反映房价上涨给居民生活带来的压力,这夸大了我国社会稳定评估的得分。考虑到这个因素,我国实际社会稳定程度的下降应该比稳中趋降更为严峻。以本文测算的实际失业率和居民生活负担水平推算,我国目前社会稳定风险已接近1989年时的水平。因此,中央所做出的我国进入“社会矛盾凸显期”的判断显然更符合实际情况。
(二)房价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在影响社会稳定的5项经济指标中,物价指数是波动最大的一项。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历了两次严重的通货膨胀,与之相对应,我国社会稳定评分也出现了两次低谷。之后我国物价指数相对平稳,社会稳定评分的波动也由此大为减小。在1988—1989年那次严重的通货膨胀中,我国物价指数涨幅超过18%,成为“六四事件”爆发的重要诱因。1993—1995年通货膨胀更为严重,物价指数涨幅在1994年超过24%,反而安然渡过。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后一次居民收入增幅比通货膨胀率更高,而1989年居民收入增长低于物价涨幅,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唯一一次居民实际收入出现负增长的年份。
21世纪以来,我国物价指数年均上涨2.40%,大大低于改革开放前20年超过7%的年均涨幅,表面上看为社会稳定加了些分,但实际上目前居民对物价上涨的承受能力反而不如从前,抱怨更多。主要原因在于当前物价指数已不能完全反映居民生活成本,房价的上涨对居民生活形成了更重的负担。2011年我国城镇家庭人均购房支出超过7 000元,相当于人均消费支出的40%,购房开支比重大大提升,已成为家庭开支的一大负担。即如果物价指数上涨5%,一个普通城镇三口之家的一年消费开支将因此增加1 700元左右;而房价上涨5%,则将使购房家庭骤然增加上万元的首付款,此外还将每年增加上千元的月供。由此可见,房价轻微的上涨也将使购房者收入的有限增加化为乌有,就此而言,相比一般物价的上涨,房价的持续上涨对我国社会稳定的威胁更大。
(三)贫富分化、分配不公已成为社会稳定的最大隐患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在我国经济连年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越发增大。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居民基尼系数约0.24,处于较低水平。2012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为0.47,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0。
21世纪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城镇内部居民收入差距还在加大。2000年,我国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79倍,2013年这一值已扩大到3.03,13年内就扩大了0.24个百分点。2000年,我国城镇占比1/10的高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是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的5.02倍,2013年这一值仍为4.93。在统计中未能反映出居民“灰色收入”,我国实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城镇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差距应该更大。据此推算,我国基尼系数接近0.50,这已是一个相当危险的水平。
21世纪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城镇内部居民收入差距还在加大。2000年,我国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79倍,相比改革开放初期的2.57倍,20年内提高了0.22个百分点,目前这一比值已扩大到3.13,仅10年内就扩大了0.34个百分点。2000年,我国城镇占比1/10的高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是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的5.02倍,目前这一比值已扩大到8.65倍
考虑到未能在统计中反映出来的居民“灰色收入”,我国实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城镇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差距应该更大。。据此推算,目前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已将近0.500,已接近危险的水平。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如果贫富差距加大因分配不公所致,就更容易激发民怨。21世纪初,北京一套百万元的房产,今天的价值可能已接近千万元,当时的购房者这10年无需为自己的房产添砖加瓦,即可收获数百万元的增值。普通的购房者尚且如此,房地产开发商的暴利更令人侧目。有人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就必然有人劳而无获或多劳少获。房价上涨大幅超过物价上涨,其背后实际上是资产的收益被抬高,而创造财富的劳动所得被压低。这一抬一压就形成了从财富创造者向资产拥有者的财富转移。这种财富转移算不上违法,却绝不公平,因为它违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11]。
资产的快速升值和劳动的相对贬值,实际上形成了大资产拥有者对劳动者创造价值的剥夺。比如一个城镇家庭本可用10年的劳动所得购得一套住房,
国际上通常认为,正常的房价收入比为4—6,房价超过家庭收入的6倍被认为是警戒线。现在要用20年的劳动所得才买得起房,另外10年的工作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即10年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被剥夺了。
我国贫富差距拉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的快速升值和劳动的相对贬值所致。贫富差距过大尤其是其背后所反映的收入分配不公,也已成为我国社会稳定最大的隐患。在经济增速下滑之际,贫富分化所造成的社会“裂痕”尤其值得高度警惕。
(四)实际失业率远超城镇登记失业率
我国官方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在4%左右,各界普遍认为这一数据低估了我国真实的失业情况,因为许多城镇户籍的无业人员并未登记失业,而大量未就业的非城镇户籍的农村富裕劳动力更无法在城镇登记失业中反映出来。2014年,国家发改委首次公布了调查结果:截至2014年6月底,全国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5%,连续4个月下降,这是官方首次正式发布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之前公布的统计指标中通常使用的是城镇登记失业率,而不是国际通用的更准确的调查失业率。此前,我国失业率数据长期被人忽视,因为它几乎常年不发生变化,但调查数据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等原因不利于研究问题,因而本文选择城镇登记失业率或通过其他方法估算实际失业率。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实际失业率已超过10%。2010年,我国劳动力年龄(16—61岁)人口为9.29亿,剔除该年龄段的在校生后,非学生劳动力年龄人口为8.59亿。当年我国统计城乡就业人数为7.61亿,剔除61岁以上就业人口,劳动力年龄就业人数为7.17亿。据此推算,目前我国劳动力年龄人口无业率高达16.60%(无业人数/非学生劳动力年龄人口),即使非学生劳动力年龄人口中有5%本身就没有就业意愿(因病残、全职照顾家庭、游手好闲等原因),我国失业率也高达13.40%,比10年前增加3.30个百分点。从绝对数来看,我国目前存在一只1.42亿人的青壮年无业大军,其中约1.09亿人想工作而没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每年净增就业人数呈减少趋势,“九五”期间全国年均净增就业804万,“十五”期间年均净增就业512万,“十一五”期间年均只净增292万。随着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GDP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明显减弱。“九五”期间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平均带动94万个净增就业,“十五”期间只能带动54万个,“十一五”期间进一步降至26万个。
我国就业形势的另一大特点是大规模的城乡就业转移。“十一五”以来我国城镇年均新增就业约1 250万,而农村就业人数年均下降960万,转移到城镇就业。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显然会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12]。
(五)社会稳定高度依赖经济快速增长
在我国社会稳定评分中,GDP增速在5项指标中贡献最大,21世纪以来平均占到三成以上,足见我国社会稳定高度依赖经济增长。
低失业率对我国社会稳定评分的贡献率也接近三成,但如前文所述,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明显偏低,由此测算的该项得分也被夸大。按“实际”失业率测算,该项得分对整体社会稳定评分的贡献率还不足5项指标平均的1/5。
改革开放以来共经历了4次经济波动,几乎每次经济减速期都出现了重大的社会不稳定事件。粉碎“四人帮”后,当时的中央提出“新的大跃进”,“大干快上”超出了当时的国力,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经济进入调整期,经济增速快速下滑,从1978年的近12%下滑至1981年的近5%,其间就发生了“西单民主墙”变质事件。1982—1988年,在前期“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基础上,改革开放的红利爆发,经济连续7年高速增长,1984年增速超过15%,但连年高速增长后,经济内在的调整需求加上“价格改革闯关”受挫,1989—1990年我国经济增长出现了第二个波谷,与之对应则发生了“六四事件”。第三个波谷出现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998—1999年,时值我国改革向“国企脱困”推进,国企改革中“主辅分离”使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法轮功事件此时发生也并非偶然。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增速也大幅下滑。我国社会稳定如此依赖经济快速增长,而目前经济又进入一个减速期,这正是令人担心之处。虽然迄今尚未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但近年恶性案件、群体事件尤其是网上群体事件明显增多,说明我国很可能正进入一个社会稳定高风险期。
(六)人均GDP提高依然任重道远
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2位,但人均GDP全球排名仍在百位之后,因而社会稳定最根本的经济基础还相当薄弱。据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测算,我国目前人均GDP约7 000美元,仅为美国的1/6。
按现行汇率测算,2011年我国人均GDP为5 380美元,仅为美国的1/8,差距更大。即使我国人均GDP能持续以7%的速度提高,也需要大约30年才能达到目前美国的水平,即该项满分的水平。
四、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社会稳定面临的挑战可能更为严峻。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有所下滑,通货膨胀压力将总体趋增,这两项得分下降趋势在所难免。就业方面,劳动力适龄人口虽将由升转降,但新增就业岗位将随经济增速下滑和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减少,就业压力依然较大,该项得分预计与目前大体持平。人均GDP虽将持续提高,但相距人均40 000美元的满分水平而言,该项得分提高的幅度将十分有限,不足以抵消经济增速下滑和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的失分。因此,确保在贫富分化项上不再失分甚至有所加分,即确保贫富差距不再扩大并力争有所缩小,这对于保持我国社会稳定极其重要。
(一)GDP将进入中速增长期
此轮我国经济增速的下滑,表面上看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实际上更多是由我国经济自身的问题所致。前些年高速增长所依赖的诸多红利因素正在迅速弱化甚至开始消失,如先期改革开放对生产力的释放作用、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廉价的土地和环境等。与此同时,一些“三不”因素则日益呈现出刚性制约,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已经刻不容缓,而我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与全球金融危机不期而遇,则加大和加快了我国经济减速。因此,我国经济很可能就此进入一个中速增长期,GDP增速将从“十一五”期间的年均11.20%降至“十二五”期间的8%左右,对社会稳定的贡献也将明显减弱。而且经济增速下滑也将减少新增就业岗位,从而拖累就业对社会稳定的贡献。
鉴于我国社会稳定对GDP增速高度依赖的现状,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防止GDP增速下滑过快,显然是维稳的基础任务。但我国经济连年高速增长之后反而出现社会矛盾多发也表明,单一的GDP增长并不能带来社会稳定的提高,构建和谐社会还需注重改善其他经济指标。
(二)物价指数压力总体趋升
21世纪的前10年,我国曾经历了一段“高增长、低通货膨胀”时期,期间年均GDP增速高达10%,年均物价指数涨幅仅1.30%。这一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廉价的土地、环境、劳动力和能源。前期的价格改革也功不可没,改革开放前20年我国大刀阔斧的价格改革虽然造成当时物价指数涨幅持续偏高(年均7.9%),并带来一些社会不稳定因素,但价格体系由此基本理顺,为此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重要的障碍。但
这些因素今后已很难整体再现,人口红利的拐点和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都要求加快提高劳动力价格;土地、环境的稀缺性日益凸显,必将更多地内化为发展成本;能源和矿产价格在金融危机后全球宽松货币的条件下也将总体趋高。因此,尽管我国经济增速趋缓,但通货膨胀压力却在趋升。
我国价格改革尚未完成,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仍是我国转方式调结构的一大障碍。容忍适度的通货膨胀(4%—5%)为深化价格改革留下一定的空间,总体上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对房价上涨则应保持高压态势,坚持房地产调控决不动摇。
(三)就业压力或将趋缓,但结构性压力依然严峻
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今后就业压力将有所缓解。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11岁少儿人口为1 400万,若其全部存活,这将是2015年我国16岁人口数,也就是新进入劳动力年龄的人数;考虑到少儿人口漏报因素,
为逃避计划生育处罚,人口普查中儿童人口漏报较多。比较2000年普查统计的6—15岁人口和2010年普查统计的16—25岁人口,后者反而多了1 165万,而考虑到死亡因素,后者应该比前者少才合乎逻辑。按这一年龄段通常的死亡率推算,2000年6—15岁儿童数应比2000年人口普查数多2 000左右。以此我们假定2010年人口普查中6—15岁的人口数(今后10年将陆续进入劳动力年龄的人口)也漏报2 000万。但此次人口普查质量可能有所提高,漏报较少。2015年新满16岁的人数可能比人口普查数每年多出200万,达到1 600万。而2010年我国56岁人口1 770万,在5年后将年满61岁,退出劳动力年龄。这一数字将超出届时将新进入劳动力年龄的人数。比较而言, “十一五”期间年均新增16岁人口和61岁人口分别为2 200万和1 170万。依据《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数据,2012年老年人口数量为1.94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4.30%,2013年老年人口数量突破2亿大关,达到2.02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4.80%。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的历史拐点,从2011年的峰值9.40亿人下降到2012年的9.39亿人和2013年的9.36亿人。考虑到因死亡减员的因素,我国劳动力年龄总人口很可能已经由增转降(即出现所谓“刘易斯拐点”),这也意味着我国总体就业压力将大大减轻。当然,人口红利的减弱和老龄化社会也将带来的新问题。
尽管我国总体就业压力减轻,但结构性压力依然很大[13]。前期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之际,高中、高校等学校的大规模扩招一时减少了实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高中、中等职业学校、高校合计在校生最多时一年净增超过700万。但这些学校的在校生净增人数近年急剧下降,2008年仅净增70万,对就业压力的缓解作用明显减弱。今后几年,尽管进入劳动年龄人口数将有所减少,但毕业进入就业市场的人数将持续增加,尤其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将更加突出。此外,今后我国还将有大量农村劳动力需转向城镇就业,如何充分吸收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仍将是我国就业问题的一大难点,因而加快城镇化进程显然是关键所在。
(四)缩小贫富差距应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主攻方向
贫富分化造成的社会裂痕是对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毕竟社会动荡直接受人们的不满情绪趋使,而最多的不满来自低收入群体。低收入者在平时是刑事犯罪的主体,在动乱时则是主力。在经济增长较快时,社会成员绝对收入水平总能有所提高,弱势群体相对收入下降而产生的失落和焦虑还能得到一定的平衡。一旦经济增速明显下滑,贫富分化所积累的不满情绪就会寻求宣泄渠道。尤其是低收入者或弱势群体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在经济不景气时承受的压力会更大,一些平时的良民此时也可能会铤而走险。
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和城镇居民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比已有所下降。今后加快收入分配体系改革、缩小贫富差距应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主攻方向,包括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加强农民工权益保障、加强工会维权职责、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推进最低工资增长、遏制垄断暴利、严惩贪污腐败和促进教育公平等[14]。
(五)和谐社会建设需要多管齐下
总体判断,未来若干年内,经济指标反映出我国社会风险将继续呈上升趋势。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经济指标虽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但综合评价社会稳定风险还需要包含政府治理水平、社会保障体系、国际关系乃至文化传统因素。因此,维护社会稳定除了在经济政策上要避免经济增速下滑过快、控制物价和房价上涨过快、力争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努力扩大就业之外,还必须在加强现代政府建设、改善社会管理、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大力发展文化事业等方面苦下功夫。我国已经进入改革深水区,目前大力倡导的反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但长久之计还应是将依法治国落实到位。参考文献:
[1]贾冰.论分配制度改革、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J].现代经济信息,2012,(2):6-10.
[2]李培林.和谐社会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25.
[3]Bauer, R. A. Social Indicators[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6.
[4]郭平,李恒. 居民收入分配规范函数及其福利评价——模型及实证分析[J]. 财经研究,2006,(8):17-26.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7-98.
[6]宋林飞.中国社会风险预警系统的设计与运行[J].东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69-75.
[7]马岩.我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及对策[J].经济学动态,2009,(7):42-46.
[8]胡鞍钢,王磊.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的双向效应[J].湖南社会科学,2005,(6):84-90.
[9]李实.劳动力市场培育与中等收入陷阱——评《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2011—2013》[J].经济研究,2014,(4):187-191.
[10]World Bank.East Asia and Pacific Economic Upadate 2010:Robust Recovery, Rising Risks[R].World Bank,2010.
[11]蔡昉.通过改革避免“中等收入陷阱”[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5):3-5.
[12]周毅.中国人口流动的现状和对策[J].社会学研究,1998,(3):83-91.
[13]陈宗胜,周云波.文化程度等人口特征对城镇居民收入及收入差别的影响——三论经济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J].南开经济研究,2001,(4):38-42.
[14]田春燕. 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J]. 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综合版),2011,(3):103-106.
The Social Stability Risk Assessment of Economic Indicators Construction
SUN Qi-feng1,2
(1.Schoo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China;
2.China Information Service,Xinhua News Angency,Beijing 100803,China)
Abstract:In this research, we used the economic index of social stability risk assessment system. Looking at the economic situation on the basis of social stability, we selected five economic indicators (per capita GDP,GDP growth rate, the Gini coefficient, CPI, and the unemployment rate) for social stability risk assessment.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by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the social stability in China at present has reached the middle-upper level, mainly benefiting from rapid GDP growth as well as low CPI and unemployment rates; by the longitudinal comparison, the social stability risk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shows an increasing trend, suffering from widening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s well as rising inflation pressures. The next few years will be critical to the success of transformation in the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its avoidance of the middle income trap.
Key words:social stability risk;middle income trap;economic indicators
(责任编辑:徐雅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