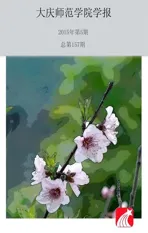援道入儒的一个侧面——略论王弼“成物”思想
2015-03-30张盈盈
作者简介:张盈盈(1985-),女,黑龙江黑河人,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古代哲学研究。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63(2015) 05-0010-05
收稿日期: 2015-03-04
DOI 10.13356/j.cnki.jdnu.2095-0063.2015.05.002
儒家“成物”的伟业起于先秦,“成物”即成就世界与改造世界。梁启超曾说:“天下学问,不外成己成物二端。” [1]34两汉时期,普遍的价值原则(名教)逐渐倾颓,“成物”思想在神学的洗礼下偏离轨道,当儒学本身出现问题时,人们把目光投向了道家。王充及汉末一些儒者都进行过“以道补儒”的尝试,但都没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王弼主张名教本于自然,援自然原则入人道原则,从根源上拯救了“成物”的偏离。在天人之学下,儒家主张“成物”,道家主张“则天”,从某种程度上说,儒家与道家持相反的价值原则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互补性,这就为王弼援道入儒提供了条件。
一、先秦儒道之异——“成物”与“则天”
在儒家传统哲学中,“物”泛指与人相对的他人或他物的存在。所谓“成物”,在不同层面的所指是不同的。在天人关系上,“成物”指人通过主体的活动与努力使自然打上人的烙印,即人类按照自己的意志与目的去改造自然。人与自然万物存在着实践关系,人类有能力促使天地生成、化育万物;在群己关系上,“成物”指自我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所构建的理想社会。这两个层面构成了人所面对的整个世界,“成物”即成就世界,建立一个纲常有序、自然和谐的世界体系。明确提出“成物”思想的是《中庸》,“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中庸》第25章)。“成己”即实现人的自我价值,也是化天性为德性的过程。“成物”即通过对德性的修养,而成就、促进天地万物的生成与发展。“成己”的宗旨在于“成物”,这相当于“内圣”与“外王”的关系,追求“内圣”是为完成“外王”的宏伟事业。“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第22章)人之性,就是天所赋予的性,尽人之性可以知天。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将其作用于天(赞天地化育),从而改造自然与构建社会。《中庸》描述“成物”的理想境界:“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畴。譬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中庸》第27章)圣人促使天地生成万物功能的完成,万物各随其性而不相害。在理想的至德之世,处处呈现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的景象。儒家主张“仁爱”,“仁爱”不仅是对人的态度,也是对鸟兽草木等物的关怀。“不知礼,无以立”(《论语·尧曰》),“礼”规范人的行为,也制约着人如何对待物。“乐著大始,而礼居成物”(《礼记·乐记》)。仁、智、礼、乐演变为普遍的社会规范,是物得以成的条件,是“成物”所要遵守的价值原则。儒家认为,人促进物成为物,并使物的生成合于人的目的。所以对万物进行教化与改造,既是必要的也是当然的行为。所以儒家倡导人道原则,为建立一种生生不息的秩序。在这个过程中,难免对万物的本性有所伤害,这正是道家所反对的。
与儒家的“成物”思想不同,道家以“则天”处世。道家的“天”是“自然之天”,是与“人为”相对而言的自然状态。“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16章》),人、天、地都要遵循自然之道,所以道家的“则天”亦为遵循自然原则,自然才是最理想的状态。人与物的天性也是自然(自然本性),任何人为的干涉都会破坏自然。人类应该顺乎自然,“以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万物自然而然的生长与消逝。人为的塑造和改变会伤害万物的自然之性,诸如络马首,穿牛鼻等都是对本性的戕害。道家“无以人灭天”的态度,与儒家的“成物”相反。《老子》认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老子·第18章》),仁义与智慧都是人为的结果,也是致使社会混乱与纷争的根源。“成物”在于成就世界与改造世界,这固然推动了社会进步,但也常常带来负面影响而后患无穷。所以,道家认为,一切都应以自然原则(则天)为依据,“依乎天理”,合于天道,才能达到完美的自然之境。与此相联系,道家面对世界所采取的是无为原则,虚静无为,才能合于自然。王弼正是吸取了道家的自然(无为)原则,对儒家“成物”思想进行纠偏,形成了自己的“成物”体系。
二、“成物”之本体——援“道”入“以天为本”
魏晋时期“人人自危”,若要“成物”,首先要为“物”找到本体论上的依据。先秦时期,“成物”思想的本体是“天”,“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对“天”的认识显然更加理性,但他也讲“天命”,认为“天命”是不可抗拒的,不同于殷周时期的宗教之天。孔子注重人道,“知其不可而为之”,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天命”的权威,削弱了“天命”的神学性。“成物”是人力的一种表现,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世界,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指人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尽人之职分,造福于社会。荀子的“成物”是指“裁万物,兼历天下”(《荀子·王制》)。儒家之“天”的权威在先秦时期显而易见,“天”是万事万物的根源。
两汉时期,儒术独尊,“天”的权威在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下被强化了。董仲舒把“天”看成是有意志与情感的人格神,“天者,百神之大君也”(《春秋繁露·郊祭》),自然现象、国家兴衰等都是天的意志的体现,儒学被神学化了。“天命”的核心就是君权神授,“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在董仲舒看来,“成物”就是“成仁”“以爱利天下”“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这说明“成物”并非人之本意,人只不过是神的“婢女”,顺从天的旨意而“成仁”,这也是名教体系(人道)虚伪化的主要原因。东汉时期,神学与谶纬使得“天命”成为至高无上、不容怀疑的体系,但同时也使“天”彻底失去了统摄力。“成物”也在谶纬神学中淹没了。“以天为本”的弊端逐一显现,于是人们开始进行反思。王符认为,“天呈其兆,人序其勋”(《潜夫论·本训》),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恢复了人之“成物”的能力。仲长统提出了“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他把“天命”看成是统治者夺取政权的欺人口号。“成物”失去了本体论的根据,汉末的批判家们只能从否定意义上去揭露“以天为本”的不足,并没有从建构意义上去解决“成物”的根据,自然也谈不上“成物”之宏志了。王弼不是像前人那样抨击“天命”,而是将道家核心范畴“道”注入儒家“以天为本”的思想中。“道”是老子哲学中的最高范畴,“有”“无”是“道”的属性,二者就道体的层面而言,“道”是无形无限的,因此是“无”,而无形之“道”是实存的,因而是“有”。 [2]王弼并没有照搬《老子》之“道”,他将“道”转换为“无”,提出“以无为本”的命题:“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老子注·第40章》)。一切事物皆“以无为本”,世界虽然发展变化万千,在变动不居的背后总会有着不变的根据。老子哲学中,“道”是万物的最高主宰,但“道”却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统摄万物。因为,老子的“道”具有一定的超验色彩, ①这样“道”与“万物”之间存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王弼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发展了《老子》之“道”是属性——“无”与“有”,将世界分为本体界与现象界,现象界(有)的存在,是以本体界“无”为本的。《老子注·第11章》中:“毂所以能统三十辐者,无也。以其无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寡统众也”。这表明“无”与“有”是存在于同一世界,又强调了“无”的统摄作用。如此,王弼克服了老子之“道”的缺陷。
王弼提出“以无为本”的主要目的是对神学化、谶纬化的“天”及“天命”进行纠偏。王弼用道家原则去除了汉代“天”的人格神的一面,消解了“天”的神秘性:“天不违道,乃得全覆,法道也”(《老子注·第25章》) ;“天地虽广,以无为心”(《老子注·第38章》) ;“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老子注·第5章》)。曹操曾说:“性不信天命之事。” ①这说明汉魏之际的人们对谶纬化的“天命”已不再信服。王弼厘清了“天”的内涵之后,又提出“天命无妄”,认为人们是应该遵循“天命”的。但是这种“天命”已非两汉时期的“天命”,“以淳而观,则天地之心见于不言,寒暑代序,则不言之令行乎四时。天岂谆谆者哉”(《论语释疑·阳货》),“天命”就体现在自然规律中。王弼通过“以道补儒”的方法,为“成物”找到了本体上的依据,其意义在于:本体“无”一方面克服了道家之“道”的超验性;另一方面,摒除了“天命”的神秘性。同时“成物”所遵循的价值原则(名教)存在的合法性重新得到了认可。王弼“援道入儒”的思路不仅体现在对“成物”的本体之追寻上,同样体现在“成物”的途径之中。
三、“成物”之途径——援“辅物”入“以名正物”
“成物”是为了构建理想的社会,促使人与人、人与物共同发展。所以儒家自觉地、强烈地追求秩序,并形成系统的思想与具体的主张。所谓的理想社会,就是一种秩序的安排。从“成物”的途径来看,儒家强调对万物(百姓)的“有为”(教化与改造),这主要体现在“以名正物”上。早在大禹时期,人们就认识到“名”的重要性。“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尚书·周书·吕刑》),这是“名”的最初始意义,即从“名”是认识事物的基础的角度来说的。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秩序混乱,孔子提出“正名”以求达到长幼有别、君臣有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孟子将其发展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由“正名”发展为“五伦”,可见“以名正物”之名,逐渐发展为完善的体系。在“以名正物”的过程中,孔孟都是以“仁义”为原则,认为社会成员各安其分,就是社会太平,人民安定。荀子则从礼治的角度,丰富了“名”的内涵,“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治本也”(《荀子·王制》)。“礼”是划分、维护等级的重要工具。儒家认为,以“名”的体系规范万物,将万物置于所设定的秩序之下,才能实现良好社会的建构而达到“成物”的目的。过于强调对万物的施为,即便是推己及人这样的美德,未必不是对万物之本性的干涉与伤害。
到了汉代,董仲舒将先秦儒家“名”的内涵发展为“三纲五常”。“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他对三纲没有详细说明,“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作为一个整体的规范,是人与物所必须要遵循的。况且,董仲舒以神学化的“天”作为“三纲五常”的理论依据,“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这说明,董仲舒所指的纲常秩序是永恒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它也呈现出一种僵化的趋势。以这种僵化的模式“成物”,必定导致人与物在一种窒息的氛围中生存。然而,儒家“以名正物”的手段还远不止于此,东汉白虎观会议后,《白虎通义》提出“三纲六纪”。 ②几乎对个体的品德、言行、社会关系都进行了规定,并且重视道德在维护秩序中的作用,以“五常”来论证“三纲六纪”。可以看出,汉代之“名”的体系,无论是从内在的德性还是外在的规范,都成为僵化的规定,这促使名教的虚伪化与工具化。东汉末年,众多有识之士开始批判名教。“以名正物”的“成物”途径所具有的强制性、虚伪性,早已与“成物”的宗旨背道而驰。
在这一点上,王弼有清醒的认识。在道家看来,“无为”才能保证万物的自然本性。“以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老子·第64章》),“辅”的本义是车旁横木,使之能重载,意思就是辅助。以“辅”的对象是万物之自然,主体与对象不存在一方支配另一方的情况。“弗敢为”是因为“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老子·第29章》),但是道家一味地拒斥“有为”,崇尚“无为”的做法也是片面的。王弼则不然,援“辅物”入“以名正物”解决了“无为”与“有为”之间的矛盾。首先,他将“辅物”转化为“随物”:“随物而成,不为以象,故若缺也。大盈充足,随物而与,无所爱矜,故若冲也;随物而直,直不在一,故若屈也。”(《老子注·第45章》)“随”在《说文解字》释为“从”,有顺应的含义。“随物”即顺应物的“成”与“直”本性,不为达到目的而害之。“随物”与“辅助”虽然都有尊重万物自然本性的含义,但是“随物”着重点在对象上,成就对象多样性的存在,这与王弼的“成物”旨趣是直接相关的。对于“万物”来讲,有了宽松的生长环境,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物皆说随,可以无为,不劳而明,不劳明鉴,故君子响晦入宴息”(《周易注·随卦》)。“随”并不是没有原则的,必须要做到“随不失正”:“官有渝变,随不失正也”(《周易注·随卦》),即指正当地、合时宜地处理与物的关系。若随而失其正,不遵守应有的行为准则,则会带来灾祸。其次,王弼提出“导物”:“以方导物,令去其邪,不以方割物。所谓大方无隅;以直导物,令去其僻,而不以直激拂物也。”(《老子注·第58章》)所谓“方”即普遍的价值原则(名教),“导”即引导、导向、因势利导之意。“以方导物”即主体能动地改变世界,不以其伤害万物之性,这才是“大制者”所具有的韬略。“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无体,一阴一阳而无穷。非天下之变,孰能与此哉”(《明爻通变》)。“曲成”是不以“划一”的模式成就万物,“不遗”是指个体都能得到充分实现。“成之不如机匠之裁,故曰善成”(《老子注·第41章》)。不对万物的本性有所伤害才称为“善成”,这是最理想的“成物”方式,这样世界才会呈现和谐的状态。在王弼哲学中,能够“体无”并能“随物”且“导物”的只有圣人,故圣人也是当之无愧的“成物”之主体。
四、“成物”之主体——援“无待”入“感物”
王弼哲学以孔子为圣,认为孔子能“体无”并以“无”化育万物。汤用彤认为“王弼哲学立身行事,实乃赏儒家之风骨” [3]103,不可否认的是,圣人作为王弼“成物”思想的主体,其内涵同样是援道入儒的结果。这要从儒家圣人的发展演变谈起。
在儒家的传统中,孔子一方面认为“圣人,吾不得而见之”,即圣人只是理想中的人,另一方面又婉转承认现实生活是有圣人的,“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予斯文也”。有一点可以肯定,孔子眼里的圣人并未有多少神秘色彩。而后的儒学发展中,圣人被视为“人伦之至”(《孟子·离娄上》)的道德权威、又是“非圣莫之能王”(《荀子·正论》)的政治权威,因为只有圣人才能参与到天地万物之生生不息,能够“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中庸·第25章》)。《易传》认为:“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于天下利,莫大乎圣人。”综上可看出,在传统儒家的眼中,圣人是达道而知天命,博施广济的理想人格,因此圣人具有建构社会秩序(成物)的能力。然而,到了两汉时期,圣人在庞大的天人感应体系下发生了变化。董仲舒认为,圣人不同于常人,“故聪明圣神,内视反听,言为明圣。内视反听故独明圣者,知其本心”(《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在道德教化方面,君主通过自身修养,来影响整个社会道德境界的完善。董仲舒认为君王有感化万民的能力:“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圣人超凡,可以通过本心来认识天意,作为“天施符”者,其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的意志的表现。圣人已被董仲舒神化,在性情方面圣人是抽掉了情与欲的。“天有阴阳禁,身有情欲栣,与天道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圣人“抑情”发展到汉魏之际就成了圣人“无情”,“凡人任情喜怒,违理”(《景福殿赋》),圣人“无情”,又如何与物相感而成物呢?
王弼认为,圣人作为“成物”的主体,就要有与物沟通的能力,通过“感”的方式与物进行沟通。“天地万物之情,见于所感也”,“不以刑制使物,而以观感化物者也”(《周易注·观卦》),“感”即交感、感应。“感”物就必然产生喜怒哀乐等情感的外在表现,“感”物而动,动则生情。圣人以谦虚之心怀示物,与万物相交感体察万物的实际状况。“以虚受人,物乃感应”(咸卦注)。王弼认为,圣人有情才能与万物相沟通,但并不像常人那样为情所累。“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钟会传》附引何邵《王弼传》)其中巧妙之处在于,王弼将“成物”的主体圣人注入了道家思想元素。圣人以“虚”为主,能够“则天成化,道同自然”(《论语释疑·泰伯》)。圣人具有自然之性,体悟本体“无”的真谛,这表现为一种“无待”的精神境界,“无待”是《庄子》中所追求的人之至境,是对“道”的体验,“不以物易己”,“物物而不物于物”。圣人“无待”,虽与常人一样有“情”,与万物相“感”时能够应物而无累于物,这是“圣人有情”区别于“圣人无情”的关键所在。圣人之情是本体“无”与万物之间的桥梁,参赞天地,化育万物。“情”本身是动的,具有不稳定性,若“情”以“性”或“道”为指归,就达到一种“不失大和”的状态。圣人“无待”“以性正情”所以喜、怒、哀、乐能发乎“中节”。“感物”是为了体物之命、通物之情,这样才能达到“物情通顺,大道无违”的状态以援“无待”入“感物”充实了圣人的内涵。圣人是理想的统治者,德能双全,是现实君主效仿的典范。“成物”是圣人之德性,也是圣人所应有的使命。圣人除了有自然之德外,还有中、和、诚、信等德性。只有具备充足的德性,才能统治万物:“立诚笃至,虽在暗昧,物亦应焉。”(《周易注·中孚》)“处中诚以相交之时,居尊位以为群物之主,信何可舍?”(同上)“然德足君物,皆称君子,亦有德者之通称也。”(同上)圣人行以自然,将普遍的价值原则内化于万物,目的是使万物自然地合乎普遍的价值原则,这是圣人“成物”的价值所在。
结语
综上所述,王弼的“成物”思想,以“道”补儒,克服了儒家“成物”思想的缺陷,表现出一种士对社会的担当与自觉。儒家认为,“成物”是人所应有的宇宙情怀,“成物”就是成就人的世界,使人与物在社会伦常秩序中运行不息。然而,过分地强调对世界的“有为”,人与天地之间的和谐就会破坏,出现社会混乱、民不聊生的局面。道家在面对“物”(世界)时所持的“无为”(自然)的态度,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对世界的变革。王弼从“成物”的“本体”“途径”等方面援引道家思想,克服了儒家思想本身的种种禁锢。王弼把世界看作是刚柔相济的和谐的大系统,在乱象靡常中重建秩序,找到万物存在的根据,其目的是服务于社会生活的。“成物”的本质是使人与世界、君主与百姓都处于一个有序运行的规则中,这是乱世之时,人们所共同期望实现的状态。“援道入儒”的“成物”方式影响深远。朱熹认为,圣人“制下许多礼数伦序”(《朱子语类》卷70)以“辅相”天地万物,但要“抚临万物,各因其性而导之”(《朱子语类》卷14),这样万物才可以“全其性”而“遂其宜”,这不能不说是王弼“成物”思想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