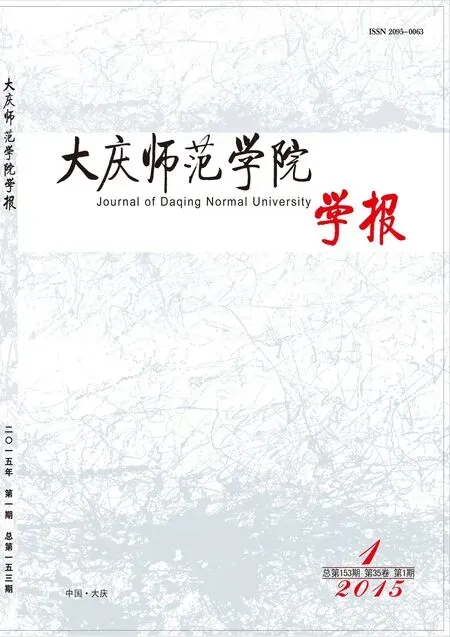一种艺术的两种消亡——余华《第七天》的一种解读
2015-03-30汪贻菡
作者简介:汪贻菡(1982-),女,天津人,在读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叙事学理论研究。
DOI 10.13356/j.cnki.jdnu.2095-0063.2015.01.019
想象,小说有两种读法:比如,阅读《呐喊》或者《彷徨》,你需要在暗夜里,斗室、青灯,怀一点小不平,徐徐展卷:“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再比如,阅读《小二黑结婚》,那就得是瓜田李下,把酒话桑麻,女人们围坐家常,男人们插科打诨,听满脸褶子和笑容的老头儿开讲:“这刘家峧啊,有两个神仙,一个叫二诸葛,一个叫三仙姑……”
这满脸笑容的赵树理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而在斗室里抽烟的鲁迅,则是小说的作者。这两者的区别因本雅明《讲故事的人——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随想录》 [1] ①一文而广为人知。所谓讲故事的艺术,当是前工业时代,一个穿州过府的工匠或是出海归来的水手,在与家人邻居围炉夜话的时候,闲闲地讲述自己亲历或道听途说的经验。经验是讲故事的关键词,与在孤寂中创作的作家不同,一个讲故事的人致力于传递的并非个体生命的困惑,而是集体的生存智慧。故事翻山越岭、更朝换代地口口相传,逐渐裹上厚厚的经验外衣,这经验便是独属于一个民族的教训、智慧、传统或曰:文化。可是机械印刷术诞生了,带来新闻、消息和长篇小说的兴盛。古老的经验由于不再能指导新鲜热辣的生活而被人遗忘,而小说家踟蹰在暗室里的独自苦思则一举打破了说者和听者共享经验的亲密关系,在小说家孤独而霸道的独语中,故事抑或经验均不重要,而讲述的艺术上升为主体。
与卢卡契将小说艺术视为罪恶时代的史诗不同,本雅明认为,小说是一种失去了光晕的现代艺术,非但不足以拯救现代性危机,反而加剧了现代性危机。而这种艺术的光晕只存在于史诗时代的故事当中。但事实上,小说与故事并非截然相隔。没有故事作为载体,小说是无法再现世界的;而讲故事的人为吸引听众而采取的讲述艺术,正是小说修辞法的圭臬。虽然后工业时代意味着讲故事艺术的衰退,但或许讲故事与写小说原本就可以融为一体,和平共处。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中,可以看到余华是如何出色地运用小说家技巧转述一个故事,作为小说的文本被读者反复揣摩,依托于故事改编的电影既赢了票房又获得口碑。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说者与听者都不复当初了。同样在骂声中大卖的余华新作《第七天》引发的批评迄今不绝于耳,而余华本人的沉默则意味深长。25年前,余华堪称先锋小说一员干将,今时今日,他的读者已然成长,读过很多故事,已经能够区分一个讲“故事”的人和一个“讲”故事的人了。
一、在故事、消息与小说之间
关于《第七天》,最大的争议是作者的故事素材均来自于众所周知的新闻热点。作品讲述的12种死亡集中了暴力拆迁、民工卖肾、警察暴力执法、商场火灾、打工者跳楼等若干矛盾丛生的民生主题。作为一个有道德承担的作家,余华如此作为无可厚非。可问题在于,他因此违背了讲故事和写小说的多重原则。
首先,他用消息来代替故事。在本雅明看来,消息的传播是讲故事的艺术日渐稀罕的罪魁祸首。其求真求快的特性与讲故事的精神背道而驰,在新鲜热辣的消息轰炸中,人们不再对遥远时空里的故事感兴趣,转而津津乐道于身边的八卦及其真实性,并在对其来龙去脉的反复渲染考证中放弃了经验,也一并放弃了故事结束时的听者追问一句:后来呢?——那种无须言喻的乐趣。在一个充斥了光怪陆离的消息时代,早已过时的经验传递和接受能力均快速衰退。而故事,即使在口口相传中也不会耗散自己,它不会如消息般以责因问果的方式将坊间传闻咀嚼成八卦,讲故事的人总是用自己或他人的经验来包裹和丰富故事,就像保留了藤蔓的瓜果,始终保持和凝聚一种活力。就像许三观卖血来救老婆的私生子,他却无法用高尚掩饰沮丧,因此一边吃着黄酒猪肝一边扯天骂娘;就像老福贵背负着家破人亡的巨大悲痛,但他仍然笑嘻嘻地赶着老水牛,冲着日复一日的空气和邻居的老女人开着老不正经的玩笑——故事不提供解释,讲故事的余华只是不动声色的讲述者,而故事背后的秘密就像被掩埋在金字塔深处的种子,给一千个读者重新阐释的可能。
因此,《第七天》引发争议的症结就在于此:作者将数十则过时的非正常死亡新闻以死魂灵的视角串联讲述,而原本,这每一种死亡背后,都凝聚了巨大的时代隐忧和群体焦虑,每一桩真相的披露都足够引发听者的持久反思。可惜在余华密集而又失去时效的消息罗列中,那些关于医疗、警民、弱势群体关怀等方面耳熟能详的控诉早已被媒体过度渲染、放大、阐释得通体透彻——而后:不了了之。公众已然知晓:除了谨慎的愤怒和独善其身的生存,看客难以解决任何问题。而在消息的深度考证与大肆渲染中,故事本身携带的世态人情被过早过多地释放出去了;故事理应产生的陌生化审美惊奇在消息声嘶力竭的过度加工中,被置换成司空见惯的公德厌倦。而作家,也因此背负了想象力缺失的骂名。对于小说而言,戏剧性是其叙事的真正原动力,在余华的作品中,常常因其结构和人物命运的戏剧性,而达到某种自动写作的境地,就像余华曾说的“叙述统治了我的写作,像一首民歌那样自动延伸出无尽的长度,绵延不绝的旋律”。可在《第七天》中,作者和读者同样深谙故事的高潮和结局,这限制了他从生活经验出发去填补人物性格,也因此他不再有办法让人物自身的命运牵动他的笔在纸面上狂奔。而对于读者而言,司空见惯的悲剧所引发的,连围观都没有,只剩下干燥的转述者所携带的、不可言喻的隔阂感。
其次,他用“讲”故事来替代小说之“思”。“讲”即意味着“听”的在场,所以“写”与“讲”的最大不同在于,故事讲完时,听故事的人总会追问:后来呢?而说者或微笑不语,或是用谚语与格言简短作结。这是说者与听者间和谐的密语,故事结束时他们共享经验,这经验无须言说,只待用生命验证和体悟,并因此成为故事意义诞生最漫长不可知的那部分。而写小说的人却是孤独的,他总是自言自语,追问并提供解释,在形成文本前他需要自圆其说,并由于听者不在场,这解释成为故事意义的主要发源所,但往往更深的意义也因此滋生:当听者与说者被隔开时,说者会更从容不受引导,并让理性介入经验,赋予故事智性的力量,从而在人生的呈现中把不可言诠和交流之事推向极致。这智性区别于故事经验的实践性,是后工业时代抵抗机械情感干枯的法宝。当然独语也有危险:如果作者在短暂的写作状态中陷入偏见或者短视,则隐含作者的形象就会陷入一场危机。
剥去《第七天》以消息为基础的故事核,小说其实蕴含了很多潜在的意义生长性:主人公的死魂灵穿梭于阴阳两界,在七天内遭遇了不公正的死亡和死亡后的不公正,这样奇妙的构思唤醒人们静下心来仔细聆听死魂灵对世界的控诉,而不是空怀旁观者的义愤填膺。而来自异世界的声音,哪怕是虚构的,终归会赋予真相另一种力量。可惜,《第七天》让读者的愿望落了空。比如,鼠妹因为男友给她买了一个假iphone而跳楼自杀,死魂灵解释说不是因为手机,而是因为男友骗她。可是死亡也掩饰不了鼠妹虚荣的本性,如若不是她对物质毫不掩饰地过度渴望,男友又何尝会用买假手机的方式来安慰她脆弱的虚荣心?生活艰难的底层人有很多,但超出自身的经济水平,渴望拥有非必需品,并未沦落至绝境却想要以出卖肉体来更快地换取更多的收益,这样的选择如果简单地归咎于社会不公,是无法让人接受的。从“活着”到“想要更奢侈地活着”,这当中世界发生了怎样的斗转星移和伦常的畸形变迁,以致引发如此荒诞的集体病症,余华并没能揭示出来。他过多地关注听者的反应,或者说他虚构了一种理想读者,即对其揭示的当代中国之怪现状有足够的关心和惊奇,从而对叙述者产生钦叹。这种密切关注听者反应的讲述方式是属于故事或新闻而非小说的,即便在读者批评受到足够重视的时代,小说的叙述也应当是自足圆满的,小说的意义才能够从作者完整的沉思中诞生出来。
可是,作为一个挖掘生活意义的小说家,余华却停留于感官表层经验上,用死者崩裂的牛仔裤渲染温情,用带血的温情替代小说家理应持有的理性,而这样的表层经验却构成整部《第七天》。又比如,主人公杨飞的所有亲人要么死去,要么离开,因此他在死后没有人为他祭奠或是哀悼,他连一块墓地也买不起,所以只能和那些没有墓地的死魂灵一起呆在“死无葬身之地”。为何没有墓地就难以安息?国人这种正在被瓦解却又生生不息、与农耕文明和乡土文化紧密纠缠的传统,在作品中仅被“这个是规矩”“小子,别想那么多”简笔带过;而“死无葬身之地”本应蕴含更多绝望、不公正的内涵,这里却只与墓地的有无即物质的多寡挂钩。而绝望的男友在鼠妹死后,通过非法出售器官来买墓地以证明自己真挚而卑微的爱情,更存在刻意营造悲剧的嫌疑。再比如,谭家菜馆的老板在厨房着火时堵门让食客交钱再走,却惮惮地放过了脑满肠肥的工商税务管理者,最后与就餐者杨飞一起被大火吞噬,这意味深长的场景背后,有着怎样浓重的人性悲哀?死魂灵委屈地解释:因为消防、税务、卫生、工商等部门各种税收让饭店入不敷出,他不能再亏本了。在公众的死亡和个体的利益面前,他必须选择后者,虽然他为此感到内疚。这本可成为一个发人深省的悖论,可是死魂灵却聚在一起,和平进餐。在死亡的觥筹交错中,作者营造了一个没有税收、没有不公、没有怨恨的世界,却不知:对恶的服从使得死魂灵本身也成为恶的一部分。而这正是面对地沟油、暴力拆迁、雾霾横行……的“中国式生活”的中国式态度:苟且、服从和遗忘。作者致力营造的究竟是死亡所引发的反思,还是全力塑造隐含作者忧国忧民的公知姿态,终究很可疑了。
再次,关于死亡。本雅明是推崇死亡的:人在弥留之际方才获得生命的密码,从而终于有机会借助时间的力量为自己一生的经验赋予权威——这权威便是故事的源头。在《第七天》的12种死亡中,余华本来有机会获悉生的密码。可他却津津乐道于展示一种又一种死亡本身。在与其创作经验不符的粗糙叙述中,余华营构了一个让死者永生和安息的场景,即“死无葬身之地”:这里尽是孤独或冤屈的死魂灵,然而一旦置身此地,就不再有愤怒、不甘或戾气。这里充满欢声笑语,没有苏丹红或地沟油,怨恨被阻挡在那个离去的世界里,人们在这个青草遍地、流水淙淙的空间里和谐共处,冰释前嫌,作者以虚构的乌托邦之境给在世的贫苦者勾勒了一个死后的福地。可是,这种虚构的温情反而消解了控诉的力量。比如,警察暴力执法背后,有着怎样的不得已?作为暴力政策的执行者,其忠于职守的“善”和缺乏思考的“恶”之间,该有怎样的罪与罚?警察张刚飞脚踢坏了卖淫者李姓男子的睾丸,在多年上诉无门、长期干扰社会治安无用之后,李姓男子刺死张刚,自己也被判处死刑。在“死无葬身之地”两个死魂灵相遇,而仇恨却被丢弃了,作者用这两个死魂灵间因不断悔棋而无始无终、无输无赢的和平对弈来暗示:死者已经相逢一笑泯恩仇,都是为了讨生活,各自都有各自的不得已。这两桩死亡的对错是永远无法说清的。可正是在这无理性的荒诞温情中,对暴力制定者的问责被抹杀,对平庸的恶的质疑被消解,对民间暴力的重视被忽略,作者本应展示的生命的困惑却被刻意营造的死亡的象征所抹平,故事因此轻飘飘的;而原本在此起彼伏的死亡中,在大动干戈又恢复平静的翻滚的历史流中,一个写小说的人是应该并可以为人们揭示深潜其下的生命密码的。
事实上,面对死亡,余华曾是个智者。他讲过老福贵的故事,他起伏跌宕的人生,他淡如静水的从容,他的历经重重死亡的活着的经验,在故事里与九死一生的中国听众相遇,感动遂绵远流长。可是,在《第七天》和《兄弟》的下半部,经验退却了,他陷入故事虚构者的冥想当中,他就像一个枯坐于电脑前的采风者,流连于网络和媒体丛中采撷信息、编织故事,沾沾自喜于“崩裂的牛仔裤”和“死无葬身之地”的命名,对痛苦浮光掠影,对死亡走马观花。而在每一条信息背后、在0/1编码的光速传播中,无数丰富的经验和活着的真理正被粗暴地埋没。
因此,当余华用小说家的方式传递消息时,他同时放弃了消息的新鲜、故事的丰满和小说的反思。而如果承载故事核的话语也令人吃惊得粗糙时,其可读性也就乏善可陈了。在斗室里,一个讲故事的人和一个不动声色的作家正在老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自我“东方化”的写作偏见下神圣的救赎姿态,以这种姿态作为讲述的基础,余华因此走向了价值的两个极端,在居高临下的讲述中,他把展示价值留给人物,把神圣讲述者的膜拜价值留给自己 ①。
二、听故事的人在哪里?
一个好的故事核是小说臻于精妙的必然前提。若能同时佐以作者独特的沉思所凝结的灵魂的经验,就能产生《活着》或《许三观卖血记》中震撼人心的效果。今日的文坛已不复是25年前了——讲故事的人正在消亡,听故事的人亦早已变迁。《活着》一文中,那个不动声色的采风者曾让人印象深刻,某种程度上,他才是作者真正的理想读者:沉默地聆听,忠实地记录。而一个说者,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听者。
本雅明《讲故事的人》引发了论者对故事区别于小说的兴趣,然而少有人关注听者:如果说讲故事是一门艺术,则讲述者一定需要一群同样懂得该艺术的听述者,他们心心相印、休戚相关。就好像——回到前面的比喻:一群插科打诨的村民是读不了《呐喊》或《彷徨》的,而一个心事重重的读者也是难以完全体会《小二黑结婚》中的山野之趣的。文学阅读的种种误会均源于此,因为你并非故事的理想读者。所以阅读赵树理,就应该是听故事的心态——自在、从容,随时准备放声大笑或热烈探讨;而阅读鲁迅,你知道他是位冷峻的作家,你不知道自己将面对什么,你时刻准备好,调动起全部的智慧攀登思想的崎岖险峰。——所以,你是怎样的听者呢?
一个讲故事的人,是个传递经验的人,而听故事的人总是渴望共享这些经验,因此应该同属于工匠或水手的阶层,逐日作息、平静生活,所以他们渴望异乡人或在路上的故事讲述者,通过故事了解世界、传播异闻。在故事的口口相传中,一个群体的智慧像糖衣裹在故事的外壳,以谚语或格言的方式被听者吸收,并最终以文化的力量渗透进听者的无意识深处。可惜,这样的听述者正在消失。今时今日,有闲暇的阅读者往往是有文化的城镇居民,他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用一台电脑与整个世界相连,在微信、微博夜以继日的信息轰炸中,听者不再对经验感兴趣,或者说已经拥有太多经验。所以他们能够轻易预知故事的走向:站在天台上的鼠妹一定会跳下来粉身碎骨的;伍超卖肾的窝点一定是非法的,他因此会万劫不复的;餐馆大火不管死了多少人,官方是绝不会如实报道的;杨飞娶了一个跟自己极不般配的美女是注定要遭受背叛的;而当杨飞执拗地行走在死荫之地寻找他善良而命途多舛的养父时,结局必然是催泪的。因为从王立强(《在细雨中呼喊》)到许三观(《许三观卖血记》),再到宋凡平(《兄弟》),余华的情感张力总是维系在“继父”身上。暴力、死亡、温情这三个核心要素,盘桓在对余华有巨大期待的读者心中,读者憋着劲儿等待作者激发泪点或是愤怒,可惜,似是而非的故事、似曾相识的细节,以及未经打磨或刻意打磨的粗糙,都一点点打击着读者的期待。
究竟怎样的真相才能震惊读者呢?与其说余华失去了想象力,不如说生活在光怪陆离的当代中国,已经很难有多少故事能够唤醒人们麻木的惊奇了。在虚构的不能承受之轻中,当发生在遥远时空里的人和事远不如身边的八卦新鲜热辣时,余华如果不能提供一个足够远离生活或高于生活的光明结局,那么这样的故事即便行走在死荫之地,也不过是日新月异的媒体负能量的又一次叠加。但事实上,被新闻喂养大的读者何尝不是用听新闻的心态阅读小说呢?因此,他们才不能容忍陈旧和虚构,他们宁愿用纪实报道的方式听取主人公自杀前的心路历程,最好由当事人主诉,有图有真相。
所以,这个时代大家都热爱怀旧,架空、穿越因此躬逢其盛。逐新的人们只有回到不熟悉的历史,才发现一些久违的伦理,一些动人的情感,一些能够重新燃烧听者的爱情与阴谋。而在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的重心由说者部分转移至听者。他们不再是分享经验、传承智慧的关系,亦不是一个沉思者与文字那头另一个沉思者的心有灵犀,他们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鲜明对垒,是一把一结的金钱交易。这就意味着,当听故事的人无暇聆听时,说故事的人无论说什么,都会卷入一场灾难。1985年,因《冈底斯的诱惑》等小说登上先锋作家之巅的马原,曾大踏步撤退,老老实实地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旧死》,以证明自己不是那个穿喇叭裤、跳迪斯科、唱港歌的时髦小伙,然而沉溺于先锋的读者并不买账; 1987年开始马原投身影视编导和高校教育,2012年携长篇《牛鬼蛇神》重出江湖,回到先锋的老路,可读者说他廉颇老矣; 2013年,心有不甘的马原再次回归传统,而面对他的长篇新作《纠缠》,读者则不再反馈了——在一个话语过剩的年代,沉默比恶评还让人不安。 [2]在讲述者取悦于听者的戏剧性变迁中,我们看到听者是如何损伤作者的野心和激情;而最让讲述者恐惧的,则是听者的消逝:有一天,讲述者会不会彻底地成为独语者?
作家要直面现实,就应包括直面读者变迁这一事实。当人们认识世界获取经验的方式不再只依赖于故事或小说时,故事讲述者就有理由培植新的讲述方式以吸引听众。听众是需要引导的。本雅明说:听故事的人的禀赋是百无聊赖。他设想的是一群工匠在老工匠的带领下做着活,或几个邻居围绕着老水手和快要熄灭的炉火,手、眼都被占据着,只有耳朵在聆听。这样百无聊赖的时刻,听者精神松懈、忘怀于己,他因此可以身心投入故事中,用自己的经验去消化和转化说者的经验,从而增奇附丽,完成说者与听者共同的艺术。可是诞生于孤独的小说隔开了听者与说者,他们的相遇成为偶然,他们的心境差别之大更是让彼此成为陌路。
如果说,口述时代人们因为无处消磨的百无聊赖而围炉夜话,那么文字过剩、视觉文化一统天下的时代来临,百无聊赖已成为让人恐惧的状态,因为这意味着离世俗的成功遥远,意味着反省而反省即指物质拥有量的对比,而结果总是让人沮丧的。因此人们调大电视音量、推迟睡眠、拼命灌酒,在等车的间隙也要刷一刷微博:一切都为了避免百无聊赖——虽然这一切喧嚣嘈杂的一切,都只会让临睡前的刹那更为彻底的百无聊赖。而正是在这样越放松越疲倦的怪圈中,我们丧失了听故事的能力。如果我们不愿听取妻子更年期痛苦的唠叨,也不愿打探孩子青春期苦闷的沉默,更不能容忍父母对衰老和被厌弃的恐惧,我们又如何可能安下心来、听取余华讲述那发生在虚无缥缈之地的陈旧的死亡呢?尽管这里面有卑微而无望的爱情,有残酷而充满温馨的亲情,有很多永不可解的仇恨——尽管就是这些爱与仇恨编就了我们雾霾遍布的当下生活。我们生活在当下却永不理解当下,八卦和“呵呵”是我们了解世界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在逃无可逃的精神困窘和物质丰富中,艺术分崩离析,善意烟消云散。文学已然时过境迁,故事又将何处安放?
今时今日,潜在的听述者终究很难成为作家的理想读者。他们经验丰富,他们不相信传承的经验足够应付当下的现实,他们有足够多的方式消遣炉火温暖的黄昏。而当经验退隐,作为载体的故事就只剩下一个内核,如果你对故事核有兴趣,那么还有精彩纷呈的视听技术可以加工这个故事:在视听的盛宴饕餮中一举击破你拼力生存也难以逃脱的百无聊赖。
三、结论
虽然,完全用一种理论来套解一篇文章是危险的,但以《第七天》为个案,可以清晰地领悟到:讲故事和听故事的艺术是同时衰落的。在一种艺术的两种消亡中,既难以苛责读者的心浮气躁,就不能对余华直击现实的努力全盘推翻。他终究是犯了一个虚构小说的非虚构错误,与其说他丧失了故事想象力,不如说是错误地使用了想象力展示的方式。他未能固守古老故事的讲述密码,在一个孤寂的写作者和一个走向大众的讲故事的人之间,他进入了暂时的迷失。至于能否走出这迷宫,所需要的仍然并永远只能是:时间。
如此似乎过于悲观。
但正像饿死诗人才是拯救诗歌的必然路径一样,在一个供大于求的时代,文学虽然边缘,却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比如说,如果你是个纯粹艺术论者,正好借着艺术光环的黯淡大踏步撤退,在世界的边境打捞词语的纯粹;又或者你是个入世论者,那么就直面事实,听众的需求总是被发现、继而被引导的。非虚构小说的写作,或许,是在讲故事与创作小说之间又一条险趣丛生的小径。也很难说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