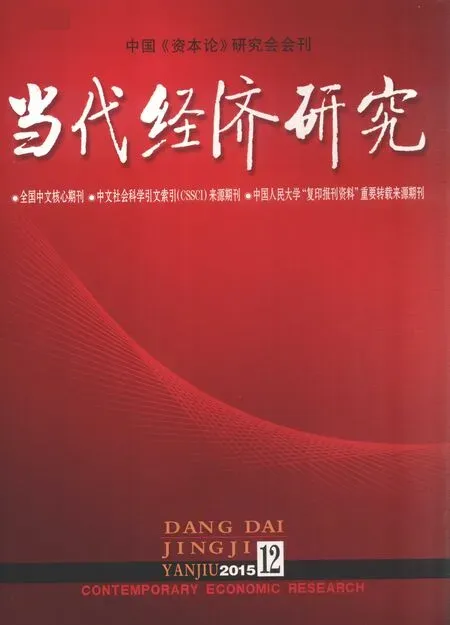国家作用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一个新李斯特主义的解读
2015-03-30严鹏
严 鹏
(1.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上海200433;2.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武汉430079)
编者按
国家作用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一个新李斯特主义的解读
严 鹏1,2
(1.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上海200433;2.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武汉430079)
编者按
李斯特经济学是系统揭示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体系之一,其关于欠发达国家幼稚产业保护思想得到了晚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肯定,并成为推动德国、美国等历史上后发国家通过抵御英法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而崛起的理论依据。新李斯特经济学是对李斯特经济学传统的创造性发展,其在继承李斯特有关国家是世界经济秩序的基石、生产力发展的活动特定性和经济政策的时空特定性等学说的基础上,对李斯特有关国富国穷的典型化事实提供了演化经济学的理论解释,并在重建世界经济新秩序、经济危机的治理等方面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建议。目前,中国正处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结构转型、谋求对外经济发展新空间的重要阶段,需要吸收、借鉴各种发展理论。为此,本刊设立了“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90周年”专栏,期冀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有所裨益。
摘要: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后发展国家,其工业化道路具有由国家主导的特征,偏离了工业化的“自然”模式。然而,国家参与工业化是世界经济史的常态而非例外,因为工业化本身是与民族国家建构联系在一起的,具有非经济的政治—军事维度。中国的工业化始于军事动机,但由市场主导并以私人资本为主体的工业化更具成效。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国家缺位阻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并激起了国家“凌驾”市场的反向运动。一种新李斯特主义的演化图式认为,工业化是由国际竞争引发的、国内具有不同观念的精英斗争的结果。精英可以具有多样化的动机。当那些具有整体及长远利益观的精英占据上风,并找到适宜的手段高强度地参与国际竞争时,工业化就能够启动并得以维持,这是国家作用于工业化的一般性机制。
关键词:工业化;国家;新李斯特主义;历史方法
自19世纪以来,工业化一直是各国竞逐富强的必由之路。由于工业化主要表现为一种经济现象,因此,不少学者主要从经济或者市场角度对工业化进行了分析。然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等学者早已揭示国家对于工业化具有重要作用。[1]这一论点尤其被应用于对所谓后发展国家工业化的解释。不过,部分以主流经济学为研究工具的学者,虽强调国家或政府的作用,但对其评价过低,并据此将中国百余年的工业化道路视为低效的路径依赖。[2]这一主流经济学建构的历史图景,既存在较多历史事实的错误,也未能真正理解国家对于工业化的意义。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呼唤着李斯特经济学的归来,而一种新的李斯特经济学也必然要对工业化的历史给予解释,从而得出现实的教益。[3]从新李斯特主义的角度来看,单纯的工业化已经不再能确保欠发达国家脱贫致富,这就使透过历史现象剖析经济演化机制显得尤为重要。[4]本文认为,工业化并非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一个李斯特式的政治—经济过程,其政治维度决定了国家不但是一个功能性存在,更是工业化的一个基本组成要素。而国家对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作用,与其说是历史的例外,不如说仍然反映了历史的常态。
定稿日期:2015-11-10
一、国家与工业化:历史的普遍性
李斯特作为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其研究方法的最大特色就在于“以历史与事物本质为依据”[1]8。这一历史主义方法论的优势在于对时空特殊性的重视,从而批判了主流经济学罔顾各国国情的空泛论说,进而抵制了那些无视经济发展阶段性的政策建议。然而,李斯特以及德国历史学派并未采取过度历史主义的立场,他们仍然相信具有普遍性的历史规律是存在的,只不过这种普遍规律会被不同的历史情境塑造成不同的样貌。因此,从新李斯特主义的角度出发,欲探讨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首先应该考察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是否具有某种共性因素。
一般认为,国家或政府在后发展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要大于起步更早的地区。例如,张培刚在构建其工业化理论时,区分了工业化的不同类型,将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工业化视为“由个人发动而开始者”,并认为这种工业化类型“符合工业进化的自然趋势”[5]。更为一般性的结论,则如格申克龙所言:“一个国家越落后,它的工业化就越可能在某种有组织的指导下进行。”[6]在这样的视角下,从19世纪开始,德国、日本等后起工业强国的道路就被视为偏离了“自然趋势”的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入工业化进程的后来者越多,例外国家的名单也就越长。然而,这种例外论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例外论潜在地假定了工业化只是一种经济现象,这就使国家所起的作用看上去偏离了常轨;二是例外论假定工业化可以具有不同的类型,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其分类是以国家为基础的,而忽略了无论是先行国家还是后起国家,其内部都存在着因产业、部门差异而导致的多种工业化路径。因此,通过某种典型化的研究方法,学者们建构出了以发展先后为标准的两种工业化类型,并将后发展视为偏离“自然”的例外,而所谓“自然”,又被假定为国家的不在场。但从一种更宽广的历史视角来看,例外论的两个立论基础都是残缺的。
从纯粹的历史角度看,国家是一种比工业化更古老的现象,因此,工业化并非是在一个无国界的制度真空中发生的。实际上,即使那些对国家作用持消极态度的学者,也不得不分国别来讨论工业化问题,这本身就暗示了国家的重要性。当然,那些质疑国家作用的学者,不可能从历史与现实世界中完全抹杀国家的存在,于是为国家安排了诸如“守夜人”这样的角色。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内核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史,更是将国家视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7]。然而,这些学者在本质上只是将国家视为一种功能性存在,是给工业化带来好秩序或坏制度的外生因素。在标准的新制度主义模型中,国家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是西方世界爆发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8]工业革命在这一模型中,主要是由私人资本推动的经济过程,国家虽然重要,但其作用仅在于为私人资本搭建了适宜的活动舞台。国家在新制度主义模型中的形象,与主流经济学传统的“守夜人”假设,并没有太大不同,只是由纯粹的背景因素,转变成了更具主动性的背景因素。然而,国家比工业化更古老这一事实,暗示了工业化很可能从属于由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进程,而非单纯的经济现象。在这一图式中,国家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为私人资本设置制度背景,相反,国家自身是与私人资本同等重要的行为主体,是工业化的积极创造者。而这一图式,较少割裂历史的延续性,并体现了更为普遍的共性因素。
新航路开辟以后,西方世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崛起”,但这一“崛起”是以西方世界内部的国家竞争为基础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欧洲国家间的竞争,其性质是政治性的,体现为领土兼并与大型民族国家的形成。至于竞争的手段,则具有多样性,涵盖军事、外交、经济等各个方面,而经济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各国统治阶层对国家财富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日益明了,于是产生了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这一特殊的政治—经济体系。按照赫克歇尔(Eli F.Heckscher)的经典归纳,重商主义作为增强国家权势的方法有两种:或者基于政治、军事需求直接将经济活动引导至特定目标;或者更为一般性地创造某种经济资源的蓄水池,供政权汲取所需。[9]赫克歇尔主要从经济手段角度审视重商主义,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则更准确地意识到重商主义不仅仅是手段,还是现代民族国家自我建构的进程。[10]因此,早在工业革命爆发前,欧洲各国在重商主义的指引下,已经成为积极的经济行为主体。也就是说,国家本身是有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与“意志”的,即使这种动机与意志只反映了统治阶层的利益诉求,并只由统治阶层代理执行。而从历史来看,重商主义国家的动机也确实产生了相应的行为。马格努松(Lars Magnusson)指出,近代早期的欧洲重商主义国家,能够广泛地运用各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来干预经济活动。[11]这一历史事实具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它表明欧洲国家在工业化时代采取的各种干预经济的手段,并非是工业时代的新产物,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国家已经是积极的经济行为主体,并非消极的“守夜人”,按照“路径依赖”理论,欧洲国家的这一属性完全有可能延续下去。事实也正是如此。而欧洲国家具有经济行为主体的属性,恰恰是由国家的政治—军事动机决定的,并由此产生了国家内部工业化类型的多样性。
如前所述,在重商主义时代,国家介入经济的动机主要是政治性的,甚至只是出于为军事竞争蓄积力量。当时,虽然以非生命能源为动力的现代工业尚未出现,但以手工劳作为基础的传统工业(traditional industry)已经成为了国家权势的重要基础。一方面,所谓的重工业部门,如冶金、火炮制造、造船等工业,直接为国家提供武器装备,是国家军事力量的构成部分;另一方面,直接面向市场的轻工业部门,如毛纺织、棉纺织、衣帽制造等工业,可以通过出口海外市场,为国家带来收入,从而为国家纯粹消耗性的军事开支提供资金支持。如此一来,重商主义国家对于发展工业抱有浓厚的兴趣,并采取广泛的保护主义政策。例如,通常被视为“自然演化”典范的英国,在近代早期曾通过授予本国企业特权及大量政府采购的方式,诱导资本进入军事工业。[12]因此,随着时间的推演,重商主义体系实际上促成了国家、工业与贸易之间的协同演化。一方面,积极培育工业的国家强化了其军事力量,通过殖民战争而在全球市场上获得了更有利的贸易地位;另一方面,这种经济优势反过来又使国家有了更多资源发展更强大的军事力量。正因为如此,主张自由贸易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将《航海法案》这一反自由贸易的重商主义法令称为英国最明智的政策。[13]581~583英国的《航海法案》是针对当时的霸权国家荷兰制定的。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史看来,英荷两国都具有完善的私有产权制度,相对于西班牙与法国,都属于竞争胜出的国家。然而,在英荷两国之间,英国战胜了荷兰,而从更长远的眼光看,法国在产业革命中也胜过了荷兰,这表明私有产权并非国家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从根本上说,近代早期欧洲国家间的竞争是综合性的,不是纯粹经济性的。而国家间的军事斗争,对于工业革命的技术突破有直接推动作用。由于蒸汽机使人类开始常态化地利用非生命动力,因此,比起纺织机械的革新,蒸汽机的改良才真正具有革命性。但从历史角度看,瓦特(James Watt)对蒸汽机的改良依赖于威尔金森(John Wilkinson)发明的镗床,而威尔金森镗床最初是用于制造火炮的。[14]这是政治—军事因素推进工业革命的显著例证。进一步说,最早启动工业化的英国,其革命性的突破,既得益于重商主义国家创造的全球市场,又受惠于国家的军事需求产生的技术外溢。无论从直接还是间接的方面来说,国家都在英国工业革命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使得英国的工业化看上去并没有那么“自然”。
当然,国家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并不表明国家对于每一个部门都发挥了相同的作用。只不过,传统上那种以棉纺织工业为中心审视英国工业革命的视角,有必要予以修正,才能完整地展现历史图景。历史的复杂性在于,即使在所谓重工业部门中,直到普遍被认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已完成的19世纪40年代,英国金属制品业仍大量存在使用手工劳作的小规模企业。[11]因此,一国内部是可以存在多种工业发展类型的,甚至在某个产业部门中,也并不存在单一、线性的进化模式。如果必须将纷繁的历史现象抽象为简化的模型,则似乎可以认为,各主要国家的工业化道路都存在着二元结构的现象,即:一方面明显存在着由国家直接或间接推动的工业发展,其力量集中体现于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战略部门以及规模巨大的企业,并较多地服务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动机,这种类型可称为“李斯特式发展”;另一方面,市场可能会随机性地诱导某些产业发展,但其发展形式具有不确定性,且可能因为演化的渐进性而保留较多的原始性,这也就是学界习称的“斯密式发展”。承认这两条道路可以并存有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对于某些政府明显主导了工业化的国家,如德国、日本等,由于其地域发展等各方面的不平衡性,很可能某些产业的演化会保留较多原始性特征,但不能据此而否定这些国家的“李斯特式发展”;二是对于那些看上去由私人资本主导工业化的国家,如英国、美国等,同样要看到其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能动性,这一点或许更为重要。
事实上,在上述二元结构中,两种工业化类型并非是对等的。由于国家主要是一个政治性存在,因此,对那些以独立生存为首要目标的大国而言,更具政治动机的“李斯特式发展”也就更具主导性。这种主导性不体现于单纯的规模或数量,而体现在对于国家独立自主的相对重要性。恰如斯密所言:“国防比国富重要得多。”[13]583不管棉纺织业如何主导了工业革命最初的进程,但支撑大英帝国的主要是冶金、机械、造船、火炮制造这些战略性部门,而没有这些战略性部门供给的“坚船利炮”,曼彻斯特的纺织品也无法撬开中国市场的大门。以通常同样被视为“自然演化”典型的美国来说,其工业发展伴随着高关税等各种国家干预,而其动机同样并非纯粹经济性的。在鼓励美国发展制造业的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看来,经济与军事息息相关,如果初生的美利坚合众国想要发展贸易,就必须尽全力组建海军。[15]曾与汉密尔顿针锋相对的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后来也改变了其早期观点,支持美国以保护主义手段发展民族工业,因为“反对民族制造业的人一定会让我们沦为他国的依附”,而“制造业对于我们的独立自主和幸福安康是不可或缺的”[16]。这种观点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利益,而是一种具有政治—军事视角的战略观。而这同样表明美国的工业化不那么“自然”。
因此,欧美早期工业化的历史表明,如果将国家的积极介入视为“非自然”状态,则经济史上根本不存在“自然”的工业发展。诚然,即使在那些国家明显起了更大作用的国家,也存在着主要由市场与私人资本主导的工业发展路径。但是,只要仍然以国别为基础考察工业化,就不得不承认工业化是嵌入于国家建设进程中的。究其原因,现代国家为了生存,有其自身的利益与动机,也就是国家理由。[17]国家理由是一种政治逻辑,而工业化只是国家为实现其利益而采用的经济手段之一。国家对于工业化的这种支配性关系,就各国尤其是大国历史而言,乃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共性因素。这种历史的普遍性,对于理解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至为重要。
二、中国工业化的成因与道路多样性
就现代经济发展而言,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后发展国家,因此,学者们在格申克龙理论的框架下考察中国工业史乃是极为自然的倾向。从这个角度说,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工业化道路具有“特殊性”而进行“再思考”,却得出国家“持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一结论,可谓了无新意。[2]然而,国家对于中国工业化的作用虽极为重要,但与经济一样,国家本身不是静态的,而是演化的。同时,中国工业化的内部也存在着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既构成抵消国家作用的力量,又成为强化国家介入的理由。
在西方经济史学界,有所谓“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理论。该理论旨在揭示工业革命之前欧洲制造业的演化机制。在部分地区,这些手工业一度发展出极为庞大的规模,并具有出口导向型等市场经济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原始工业化”的典型产业是纺织业等消费品产业。[18]部分学者认为“原始工业化”为真正的工业化拉开了序幕,但更多的研究表明,“原始工业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因地而异,实际上不能视为工业化的前提。[11]这一“原始工业化”理论后来被学者引入到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用以描述和解释明清时期中国部分地区具有市场导向性的手工业的发展。不管这些学者的动机与结论是否恰当,单从现象上看,明清时代中国部分地区的农村手工业确实具有与欧洲“原始工业化”相类似的特征。例如,在经济并非最为发达的湖北地区,农村纺织业生产的棉布大量远销四川、云贵、山陕等地区。[19]考虑到中国地域的辽阔性,这是堪与欧洲内部的国家间贸易相媲美的远程贸易,而且清朝庞大的国内市场和省际分工实际上降低了对海外贸易的依赖。[20]因此,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的传统工业已经有了相当发展。
然而,正如欧洲的“原始工业化”并未直接诱发工业革命,明清时代的手工业也无法使中国自然地演化出现代工业。现代工业与传统工业的本质差异不在于市场规模,也不完全在于生产组织,关键性的区别在于技术。而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一部分是在纺织工业等消费品工业内部自发演化的,大部分则体现为更具战略性的资本品工业部门的溢出。没有蒸汽机,英国棉纺织业的机械革新仍然是手工业性质的,并不能建立起相对于印度、中国传统手工业的绝对优势。而制造蒸汽机的重工业部门,不是欧洲“原始工业化”的典型产业,更为明清时期的中国所欠缺。所以,中国的传统工业在鸦片战争之前,不可能演化为现代工业。中国的工业化,起始于晚清政府对西方战略性工业的引进,是典型的国家理由支配的产物。
其实,从纯粹的经济角度审视,西方的现代工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不具备完全压制中国传统工业的竞争力。以工业革命的主导产业棉纺织业来说,英国用现代机器纺的纱,确实淘汰了中国传统的手纺纱,但是,机器织的布却很难取代手工织的布。实际的演化情形是,中国农民从市场上购买机纺纱作为手织布的原料。而手织布能够长期盛行,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粗糙的质地使其比机织布更耐用,更能满足收入较低的中国农民不经常更换衣物的消费偏好。[19]因此,从1840~1894年,机纺纱在市场份额上对手纺纱的排挤度达到25%左右,而机织布对手织布的排挤仅达14.15%。[21]以至于当中国的洋务派仿效西方开办现代纺织工厂时,一开始创办的机器织布厂都遇上了销路不畅的麻烦,不得不转而创办机器纺纱厂。[22]这一史实表明,在纯粹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即使当西方现代工业的产品已深入中国腹地时,中国传统工业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中国消费者对于现代工业产品也不存在绝对的需求。事实上,市场只会选择适用性技术,而非最先进的技术。由此反推,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具有一个相对自足的经济体系,尽管这一经济体系的技术程度不高,但其内部的产业循环大体能够满足国民需求,并有能力供养一个前现代组织的帝国政府,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对现代工业的经济需求。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十余年,中国对大英帝国的合法贸易仍然保持了出超。18世纪40年代,中国对英贸易平均每年出超350万镑,而到1850年代则增至900余万镑。为此,英国不得不继续走私鸦片来平衡贸易。然而,中国彼时尚未开始工业化,完全是依靠丝与茶等传统工业产品出口。因此,中国直到1860年仍不开始工业化,恰恰是市场经济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且中国生产者的行为方式高度符合一个理性自利但缺乏前瞻性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形象。
相对于由市场逻辑主导的消费品工业,清朝统治阶层在一开始对西方的资本品工业更为敏感。洋务派的所谓“师夷长技”,最初即着眼于火炮、军舰制造这些纯粹的军事工业,以对内平叛、对外御敌,而中国的工业化也肇端于他们创办的江南制造局等军工企业。在创办这些企业时,部分洋务大员确实有某种更为长远的经济眼光,意识到了现代工业不仅具有军事功能,还能够带来更广泛的经济变化。但囿于各种因素,最初的动机主要还是政治—军事性的。[23]对李鸿章等人而言,维护清朝的统治这一政治目标是根本性的,学习西方创办现代工业,只是一种手段,而且最初毫无经济上的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工业化不仅一开始即由国家主导,甚至在其早期阶段也根本不是一个经济现象。当然,工业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早期的军事企业开始对市场产生技术外溢效应,而且洋务派官员创办企业的兴趣也由纯粹的军火制造转向航运、纺织等民用部门。
但是,当时的中国还存在着其它的工业发展路径。如前所述,中国的传统工业具有强大的市场适应性,而且它们并非一直以传统面貌示人,相反,部分传统工业学会了运用现代工业提供的原料、设备乃至动力,呈现出向现代工业渐进演化的趋势。[24]这种变化,在沿海地区的造船等行业中,甚至可能不晚于洋务派兴办现代企业。[25]自然,这是一种纯粹受市场诱导的工业发展。实际上,在多数行业中,二元结构出现了。例如,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机械工业中,一方面,清政府的官员创办了江南制造局等具有现代性的大企业;另一方面,一些后来表现极为出色的企业,比如制造动力设备的武汉周恒顺机器厂,最初不过是为寺庙铸佛像的手工炉坊。然而,在周恒顺机器厂的案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江南制造局这一国营大企业向私人资本扩散了其技术乃至人才,促使后者得到升级发展。[26]至于在纺织、食品等消费品工业中,私人资本就更为活跃了,一些日后称雄市场的大企业,比如荣氏集团,基本上只是遵循市场需求而不断扩大投资,靠自我积累而非国家扶持成长壮大。[27]甚至于一批洋务派官员创办的企业,因经营不善,不得不租给私人资本经营。[28]因此,有学者将清末工业化描绘为一副主要由政府推动的经济社会连锁变化的图景,[2]与历史事实完全不合。不错,在晚清中国,国家创造了工业化,也推动了工业化,但国家远未能主导工业化。而国家的这种弱势地位,至少要延续到1937年。
综上所述,中国工业化的成因是政治—军事性的,但其内部的道路具有多样性。在工业革命之前,乃至于在工业革命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的传统经济都具有较强的自足性,整体上不具备自发工业化的经济动机。中国的工业化,最初是统治阶层基于国家理由而创设的政治—军事议程。然而,就清末的具体情形而言,国家的作用仅在于引进了现代工业技术与组织,到王朝覆亡之时,国家基本上未能对工业化进行有效引导。相反,清朝末年见证了某些主流经济学家更加喜爱的由市场和私人资本主导的工业化,以及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的渐进演化。因此,与在19世纪的工业化浪潮中成功应对了挑战的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国不同,中国的应对是失败的。如前所述,工业化本身是嵌入于国家建设的,因此,中国的应对失败,不是指纯粹作为经济现象的工业发展完全失败,而是这样一种工业发展与国家建设是脱嵌的。这种脱嵌,在20世纪前半叶最终阻碍了工业化的正常展开,并激起了更为强大的国家建设运动。
三、国家“凌驾”市场:体系演化的选择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说,在由民族国家构成的现代世界体系中,国家的存在是以其它具有竞争关系的国家的存在为依据的。[29]因此,国家建设也好,工业化也好,都是发生在世界体系内部的演化,受制于体系自身的演化机制。而世界体系的演化,最基本的动力就是各民族国家间的竞争。韦伯(Max Weber)称:“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斗争是个自然过程,哪怕斗争是在‘和平’的外表下进行。”[30]这可谓抓住了要害。因此,在整个20世纪,中国工业化道路中国家的作用不断强化,乃至于“凌驾”市场,并非某些学者所称的“利益集团”处心积虑设计的结果,[2]而是体系演化的自然选择,并且不乏经济合理性。同时,那种认为存在着某个前后一致的利益集团的历史想象,更是彻头彻尾的向壁虚造。
工业化嵌入于国家建构进程中,意味着不仅工业在变化,国家本身也在变化。例如,尽管欧洲国家在重商主义时代已经广泛采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等极具现代性的手段来管理经济,但往往效果不彰。究其原因,近代早期的欧洲国家在相当时间内仍然保持着传统的政治组织形式,缺乏高效的行动能力。在所谓旧制度下,即使君主专制国家的权力也可能是“去中央集权化”与“碎片化”的。[11]就国家直接参与工业化的动机来说,往往是因为资源禀赋的自然结构在市场引导下,无法将生产要素吸引到对国家有利的领域,也就无法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市场比较优势结构所施加的瓶颈,对后发展国家来说,又往往由于先行国家产业的竞争而得到强化。国家对于工业化的作用,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打破市场所施加的束缚,并提升工业活动的质量。然而,国家要发挥打破市场瓶颈的作用,就必须具有相应的能力。国家能力不是凭空存在的,它依赖于具体的人在一定的制度组织下去从事恰当的活动。制度组织就是国家的政治体制尤其是行政制度,它划定了国家汲取、分配与利用资源的基本渠道(制度组织不等于国家的政治体制,可改成:它依赖于具体的人在一定的政治体制下去从事恰当的活动,政治体制尤其是行政制度,它划定了国家汲取、分配与利用资源的基本渠道)。毫无疑问,某些制度作为渠道是不那么畅通的。然而,大量流于形式的制度表明,人的活动更为重要。而人的活动是受包括非经济利益在内的动机支配的,因此,思想意识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国家的行动能力,从逻辑上说,取决于统治阶层的眼界与意志,以及由此而设定的制度或形成的行为规则。
关于思想文化或意识形态对于工业化的作用,本非新论点。李斯特称“国家物质资本的增长有赖于国家精神资本的增长”[1],即已将思想意识纳入经济分析中。这一思考方式,此后被德国历史学派所继承并发扬[31],在凡勃伦(Thorstein B.Veblen)那里则与对制度演化的分析结合起来。[32]因此,新制度主义经济史将“信念及其演化方式”视为理解经济变迁过程的关键,[33]这诚然是该学派的最新发展,却不过是复刻了更“旧”的那些学派的精神而已。这一强调思想意识重要性的学术传统,能够用以分析国家参与工业活动的演化性。从一种新李斯特主义的角度看,世界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及民族国家间的相互竞争,构成了体系演化的动力,也是国家参与工业化的最主要动机。但这一动机并非某种均质的实体,而是精英阶层对国际竞争的性质的认识,以及对竞争的强度的感知。精英阶层对国际竞争性质与强度的判断,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结合在一起,会形成不同的演化组合。有些精英可能会认为根本没必要采取工业化作为竞争手段,因为他们根本不打算以较高的强度投身于国际竞争。例如,美国内战前,南方的种植园主会更倾向于依附英国工业,而为自身牟取经济利益。追根溯源,早在独立之初,美国统治阶层中的部分精英就不认为维持中央政府、常备军以及建立海军有任何必要。而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又基于不少精英认为隔开美国与欧洲的大洋确保了美国的安全。按这些精英的设计,美国只能成为一个由地方上的利益集团主导的软国家(soft state),经济上依附欧洲列强,缺乏基本的武备,与日后的拉美国家无异。但包括汉密尔顿在内的另一些精英则认为一个强大、独立的国家是有必要的。为了发展支撑富强国家的工业,汉密尔顿认为可以采用保护主义手段,适度牺牲眼前的局部的经济利益,来换取长远的整体性的收益。[34]汉密尔顿的观念后来赢得了他最大的反对者杰斐逊的支持,而杰斐逊的转向显然与1812年英国对美国的侵略有关。[35]因此,美国的历史极佳地诠释了一国精英阶层对国际竞争的认知与感受是如何塑造工业化路径的。进一步说,作为有能力推动工业化的精英阶层,并非铁板一块,国家作用于工业化的路径与形式,取决于精英阶层内部竞争的结果。在美国,这一竞争是以内战作为最终的表现方式并告一段落的。
因此,以国家为中心来考察,工业化实际上是由国际竞争引发的、国内具有不同观念的精英斗争的结果。精英固然是利益集团的实际构成者,但他们可以具有多样化的动机,其中某些动机并不局限于他们眼前的物质利益。当那些具有整体及长远利益观的精英占据上风,并找到适宜的手段高强度地参与国际竞争时,工业化就能够启动并得以维持。这是国家作用于工业化的一般性机制。然而,各国历史千差万别,是因为在完全偶然性的时空环境中,特殊的情境将一般性机制塑造成了不同的样貌,并赋予其合理性。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特殊性”,只能从这个意义上加以理解。
回到历史,显而易见的是,在清朝灭亡之际,中国的国家远未能“凌驾”市场,相反,整个国家的工业化看上去走上了主要由市场和私人资本支配的道路。辛亥革命以后,在北洋政府时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列强后撤,中国企业自动地获得了一个具有保护效应的国内市场,无论轻、重工业部门均欣欣向荣。而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军阀政权,从工业行政的角度看,没有太积极的作为,反而具有“掠夺型国家”的特征。因此,北洋时期中国工业的发展也经常被学者举为市场与私人资本优越性之证据。[36]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家缺位的危害就开始显现。主导性的轻工业部门棉纺织业,在“黄金时代”结束后迅速陷入结构性萧条,而中国企业在日资企业的威胁下难以取得发展。[37]日资在华企业的优势固然是技术性的,但不可忽视的是,直到国民政府时期,日资企业仍能在中国市场上获得国内税优待,从而化解了国民政府通过提高关税保护本国工业的努力。[38]而日本政府为了给本国企业争取在华特权,是不惜利用在华军队对国民政府进行恫吓的。[39]而在重工业部门中,一战后的不景气也极大地打击了中国企业,一批领军企业因为经营困境而被外资兼并,政府则缺乏扶助举措。[40]但是,同期的日本虽同样遭遇不景气的周期,其造船业等战略性部门仍通过政府的补贴与订单得以维持。[41]并且日本的战略性部门此后成为其侵华战争的物质基础。
然而,日本对中国持续不断的侵略,也成为中国国家建构与工业化进程的转折点,并使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看上去又有了某种“特殊性”。伍晓鹰认为,在南京国民政府于1927年成立后,主导了一场重工业化运动,并认为这一重工业化运动“相当顺畅地延续了”晚清洋务派的工业化路径,而其动因则包含了相关利益集团的“个人利益”。[2]这是彻底不符合史实的。首先,1937年之前由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导的重工业建设,是在国民政府内部的派系斗争中艰难推进的,根本谈不上是当时主导性的工业化路径。在1927年及之后的几年间,国民政府产业政策制定者的趣味相当符合比较优势原则,关注点集中于轻工业。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出于民族存亡的考虑,政府内部的蒋介石一系才创办了资源委员会,并开始从事侧重于军工的重工业建设。而一直到1935年,汪精卫一系的实业部部长陈公博还认为中国应该只发展轻工业,以免刺激日本。即使在蒋介石集团内部,也存在着“造不如买”的思想,并由此延误了资源委员会创办重工企业。[26]其次,在伍晓鹰的整个叙事中,仿佛清末以来中国一直有一个不曾断绝的利益集团,出于自己所在部门的私利而极力推动重工业化。但是,20世纪30年代推动重工业化的技术官僚,主要是怀着救国热情而从学术界进入政界的知识分子,是一批自命要当“新的官僚”的精英,他们不仅和晚清洋务派没有直接传承,而且瞧不起那些缺乏现代技术知识的前辈。[42]其中一些留学生如果继续留在海外治学,很可能会有更大的个人成就,而他们回国办工厂挫折不断,被人认为“后半辈子都浪费掉了”[43]。如果伍晓鹰更细致地阅读他所引的关于资源委员会的研究成果,就应该清楚他有意无意贬低的那个“利益集团”,在当时的官场是相当清廉的异类。[44]因此,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并没有很显著的重工业化运动。1933年,中国的机械、金属品、电器、交通用具、土石、水电气、化学品制造等7个制造业部门的总产值为488706000元,而在这7个部门中,有些细分行业是不属于重工业的。然而,轻工业中仅纺织业一业的产值就有879291000元,为前者的1.8倍。[45]当时中国的工业结构即如此。而推动重工业建设的技术官僚群体,如果非要将他们界定为一个“利益集团”,那么,他们也是和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汉密尔顿等人一样,是力图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体系中建设独立国家的“利益集团”。
由此看来,1927~1937年中国的工业化符合前述图式:在世界体系内部国际竞争的压力下,国家内部围绕着要如何应对竞争,产生了拥有不同观念的精英间的斗争。那些主张重工业化的精英,恰好是最具有超越个人私利动机的精英,体现了比较政治经济学所谓的“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46]但是,到1937年为止,精英间的内部斗争并未决出明显胜负,而日本已全面侵华。日本的侵略反而使中国的精英达成了要发展重工业的广泛共识,并成为某种延续至1949年后的逻辑。这一结论也符合伍晓鹰的推测,但在具体的历史因果关系上,他又错了。目前,学术界不乏一些研究,将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重工业优先战略以及计划经济手段的起源,追溯至抗战时期,[47]只是从抽离具体历史事实的逻辑角度看,这一观点具有合理性,因其抓住了某些类似现象背后共通的演化机制。但是,两个相似的历史现象即使在同一空间内相继发生,也不能认为前者一定会是后者的直接起源。所以,那种认为“很难想象”1949年后留在中国大陆的资源委员会人员不会因为自身利益而维护重工业化路径的论点,[2]也就只是一种“想象”了。历史事实是,尽管在解放初期,新政权吸纳了原国民政府重工业建设系统的大量人员,并对其高层授予要职,但这些前政权人员也仅仅只能起到提建议的作用,而其建议即使被采纳,在实际执行时也未必能落实。[48]旧政权人员的这种实际处境,本应是简单的常识,用不着去“想象”其它的可能性。中共在建政之初,统一全国的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因此,大量军事将领被安排在重工业等战略性部门担任领导,这些将领对于重工业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有极为直接的认识,而新政权也极为重视培养自己的技术与管理人才。[26]因此,新政权在观念上并不依赖旧政权人员,在行动上则采取了全面削弱旧政权人员作用的策略。这样一来,尽管历史确实存在着某种一致性的逻辑,却并不存在一个前后一致的“利益集团”,而基于那种想象中的“利益集团”作出的所谓逻辑一致的经济学解释,与历史无关。进一步说,国民政府留在大陆的重工业厂矿固然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准备了最初的物质条件,可一旦能够利用苏联提供的技术与设备,新政权就会放弃利用旧厂矿的计划,而将前政权的“遗产”安在相对次要的位置上。[49]
于是,一个更加历史主义的解释是: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的民族危机中,中国的部分精英形成了发展重工业来捍卫国家独立的共识,这种共识是超越党派的。而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发展缺乏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必须以人为手段扭曲市场要素的自然流动,将其导向重工业部门,这就是国民党技术官僚也会对苏联式计划经济表示认可的原因。[42]在战争期间乃至战后,甚至连希望政府救济的私人资本也主动请求国家采取某种程度的计划经济,[50]可见当时的思想氛围。直接师承苏联的中共在取得全国政权后采取的发展战略乃是大势所趋。其实,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内部也不是没有主张其它工业化路径的声音,但朝鲜战争这一体系性因素又强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共识。[51]此后,很明显的事实是,中国政府每一次强化重工业建设,都与国际形势有关。例如,三线建设是对越南战争升级的应对,而21世纪初的所谓第二轮重化工业化,就航空、船舶等工业而言是不能排除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等因素的。但是,这并不表示中国的重工业化缺乏合理性。重工业作为资本品工业部门,其优先发展,不过相当于一种涉及基础设施、技术设备等物质基础的先期投资。早在一战后,国民政府希望通过创建纺织机械制造业来带动纺织工业的发展,[52]已经具有此种考虑。新中国成立后,纺织工业部部长钱之光采取了自主发展纺织机械工业的战略,实际地促成了纺织工业的发展,加速了纺织品的扩大供应。[53]因此,中国近代以来的重工业化,虽然经常不符合比较优势,而且呈现出国家“凌驾”市场的“非自然”态势,但具有内在的军事—经济合理性,是超越私利的精英集团应对体系压力的产物。换言之,这种“反常”的工业化道路,乃是世界体系的演化机制作用于中国特定时局的产物。然而,如果对日本经济史加以考察,又会发现这一国家主导的重工业化道路,并不那么“独特”。[54]
综上,中国工业化道路中的所谓国家“凌驾”市场这一特征,就整个近代历史来看,并非是一直延续的结构,而是在特定时期被反复建构的行为。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20世纪30年代以后国家力量的强化,是世界体系内部国际竞争的结果,也是对此前国家衰弱的一种反应,自有其政治—经济功能上的合理性。然而,在新李斯特主义图式中不存在历史决定论,也就是说,中国并不必然走上目前所知的工业化道路。实际的工业化路径,是由具有不同观念的精英的斗争塑造的,而这种事关国家走向的斗争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只要认识到在抗日战争前夜,中国政府内部也好,社会舆论也好,都存在着基于经济理由要“将海军根本取消”的论调,[77]就可以想见这种斗争是何其激烈。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在20世纪后半期由国家“凌驾”市场的工业化道路,是国际竞争迫使精英阶层取得共识的结果,是世界体系演化的自然选择。
参考文献
[1]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商务印书馆,2012.
[2]伍晓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再思考:对国家或政府作用的经济学解释[J].比较,2014(6).
[3]贾根良.李斯特经济学的历史地位、性质与重大现实意义[J].学习与探索,2015(1).
[4]贾根良.新李斯特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何以成立?[J].教学与研究,2015(3).
[5]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89.
[6]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M].商务印书馆,2009:53.
[7]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4:20.
[8]道格拉斯·诺思,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华夏出版社,1999:192.
[9]Eli F.Heckscher.Mercantilism[M].Routledge,1994:31.
[10]施穆勒.重商制度及其历史意义[M].商务印书馆,1936:61.
[11]Lars Magnusson.Nation,Stat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The Visible Hand[M].Routledge,2009:41-45.
[12]李新宽.国家与市场:英国重商主义时代的历史解读[M].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129-130.
[13]Adam Smith.The Wealth of Nations[M].New York:Bantam Dell,2003.
[14]彭南生,严鹏.技术演化与中西“大分流”——重工业角度的重新审视[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3).
[15]Ron Chernow.Alexander Hamilton[M].New York:Penguin Books,2005:255.
[16]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32.
[17]弗里德里希·迈内克.马基雅维里主义[M].商务印书馆,2008:51-52.
[18]龙多·卡梅伦,拉里·尼尔.世界经济简史:从旧石器时代到20世纪末[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91.
[18]彭南生等.固守与变迁:民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农村手工业经济研究[M].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60-61.
[20]山本进.清代社会经济史[M].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32.
[21]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M].人民出版社,2005:282.
[22]陈旭麓.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六·上海机器织布局[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62.
[23]宝鋆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4册[M].中华书局,2008:1467-1468.
[24]彭南生.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M].中华书局,2007:232-239.
[25]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M].人民出版社,2012:1465-1466.
[26]严鹏.战略性工业化的曲折展开:中国机械工业的演化(1900—1957)[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41.
[27]荣德生.荣德生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5-32.
[28]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M].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8.
[29]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三联书店,1998:5.
[30]马克斯·韦伯.韦伯政治著作选[M].东方出版社,2009:11.
[31]季陶达.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M].商务印书馆,1978:346.
[32]托尔斯坦·凡勃伦.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M].商务印书馆,2008:59-61.
[33]道格拉斯·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5.
[34]Alexander Hamilton.Alexander Hamilton[M].New York: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2001:701.
[35]里亚·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468.
[36]杜恂诚主.中国近代经济史概论[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74.
[37]森时彦.中国近代棉纺织业史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82.
[38]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M].商务印书馆,2011:292.
[39]久保亨.走向自立之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的关税通货政策和经济发展[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72.
[40]严鹏.企业家精神、国际契机与民族国家建构——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机械制造业的发展(1900—1920)[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41]Yukiko Fukasaku.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Pre-War Japan:Mitsubishi Nagasaki Shipyard,1884-1934[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38.
[42]李学通.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M].中华书局,2009:234.
[43]吴大猷,黄伟彦.早期中国物理发展的回忆[M].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108-109.
[44]郑友揆,程麟荪.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史实与评价[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313-315.
[45]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M].商务印书馆,2011:95.
[46]西达·斯考克波.找回国家[M].三联书店,2009:10.
[47]卞历南.制度变迁的逻辑:中国现代国营企业制度之形成[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289-292.
[48]张柏春.民国时期机电技术[M].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223.
[49]关云平.中国汽车工业的早期发展(1920—1978)[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55-60.
[50]严鹏.中共建政初期同业公会与产业发展之关系:以上海机械工业为中心(1949—1956)[J].史学集刊,2015(2).
[51]Evan A.Feigenbaum.China's Techno-Warriors: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ic Competition from the Nuclear to the Information Age[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16-21.
[52]严鹏.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的技术管理(1946—1948)[M]//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17辑.上海三联书店,2014:117-132.
[53]钱之光传[M].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388-403.
[54]高桥龟吉.战后日本经济跃进的根本原因[M].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19.
责任编辑:蔡 强
作者简介:严鹏(1984-),男,湖北武汉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4ZDB122)
收稿日期:2015-10-11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5)12-0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