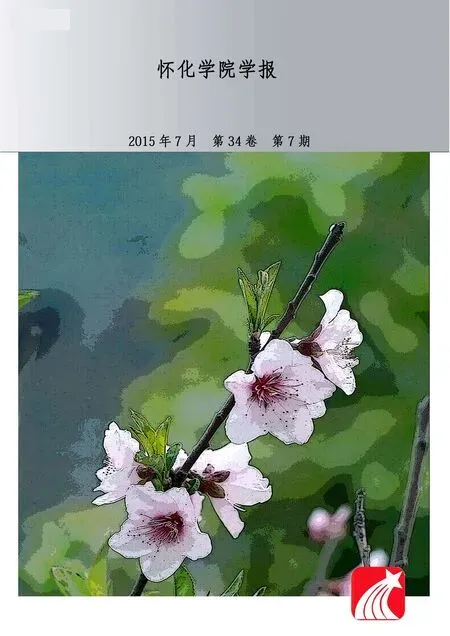“合同履行费用过高”适用研究
2015-03-29
(西南政法大学 民商法学院,重庆401120)
一、问题的提出
由于植根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契约必须严守”、“法锁”等理念,我国《合同法》在违约责任章中亦将继续履行①作为补救合同的首选措施。同时,《合同法》第110条②还对非金钱债务的继续履行规定了3种除外情形,以期获得制度与逻辑上的完满。但始料未及的是,在纷繁复杂的具体案例面前,《合同法》第110条第2项中关于“履行费用过高”的除外规定却无法大放异彩。
有关履行费用过高的规定存在先天性缺陷:(1)履行费用过高因缺乏具体的认定标准,其结果无疑拓展了法官遐想的空间,致使法官可能滥用自由裁量权;(2)无故摒弃故意违约、债权人的特别保护等考量因素,以经济合理性来判断违约方是否应继续履行,未免太过功利;(3)在特定案件中,经济利益并非合同目的的终极追求,合同目的所承载的除了物质利益外,尚包括无法量化的精神权利、精神享受等,而此时,若仅以合同履行费用过高为由排斥违约方的继续履行,不仅践踏当事人的真实意志,漠视合同特殊目的之保护,而且也很难对守约方进行公平救济。而更进一步的问题在于:(1)在合同纠纷中如何权衡故意违约、债权人的特别保护、履行费用过高等因素,以决定是否继续履行;(2)如何认定合同的特殊目的及特殊合同目的是否仅着眼当事人的精神利益;(3)履行费用过高是否应当绝对地排斥强制履行责任方式的应用;(4)若允许强制履行,则应具备哪些适用条件等。诸此问题,笔者将在下文进行系统阐述与逻辑展开,希冀对司法实践能有所裨益。
二、困境与出路:履行费用过高的认定难题及制度辨析
关于履行费用过高的认定标准,理论界非但未形成一致论调,反而众说纷纭。如顾全认为,履行费用过高,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1)债务人的履行成本与债务人的收益不对等,在经济上不具有合理性;(2)债权人的收益与债务人的履行成本之间的不对等;(3)如果履行时间过长,也不适合强制履行;(4)当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所需的财力、物力已超过合同双方基于合同履行所获得的利益时,应允许违约方解除合同,用赔偿损失来代替继续履行[1]。叶昌富认为,强制实际履行是一种违约的补救方式,因此这一方式是否适用,应考虑其经济合理性,如果在经济上极不合理,不但对当事人有害无利,对于社会也是一种浪费,此时大可不必适用强制实际履行[2]。王洪亮认为如果履行所必要的费用与债务人给付利益之间的关系严重不成比例的话,仍然要求债务人履行,不利于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也有违诚实信用原则[3]。再如Reinhard Zimmermann认为履行费用过高的比较标准可以有二,既可以是与另外一种补救履行所需费用相比(相对不合理),也可以是与债权人通过该特定的强制履行所获得的利益相比(绝对不合理)[4]。可见,学界对履行费用过高的认定标准模糊不定,且主要考虑经济合理性。
而反观司法实务界③,对履行费用过高的认定标准亦莫衷一是。实务者大多基于社会观念、自身经验、价值判断、经济分析等方法来确定履行费用是否过高。而在部分案例中,法官直接援引《合同法》第110条第2项中关于履行费用过高的规定来驳回当事人一方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用损害赔偿等救济措施来代替合同的强制履行。于是,囿于履行费用过高具体认定标准之艰难,法官在具体适用时大都对此避而不谈。
诚然,撇开具体的认定标准,我们仍可基于一般社会观念、价值判断、经济分析、审判经验等方式粗略地认定履行费用是否过高,继而促成合同纠纷的迅速解决,且在大部分案件中亦能实现判决公平。然而,将庄严而神圣的裁判说理路径托付给飘忽不定的认定标准和近乎误打误撞的现实可能,不仅难以实现裁判结论的稳定和个案公正,而且在理论与逻辑上亦难谓周延与完满。更显要命的是,若仅仅因为合同履行费用过高就武断地终结合同的继续履行,则在如下案例中必然让《合同法》第110条第2项有关履行费用过高之规定所残缺的存在合理性丧失殆尽。
在案例一中,就比较法而言,纵然能确切地证明继续履行的费用过高,但若B 属故意违约,则在美国法上可以依据“修复费用”计算A的损失,判令B赔偿,其结果与强制履行④相同(类似代替执行)。实际上,此类案件中应综合权衡的因素颇多,除了经济因素外,还包括应否惩罚故意违约?应否保护债权人的特别需要[5]610?进而,在类似案件中,绝不能再随心所欲地通过适用履行费用过高的规定来无理放逐合同的继续履行。
在案例二中,由于C仅支付了1 000元定金,理性的经济人E基于效率违约⑤的理念,同时援引合同履行费用过高的抗辩,必将镇定自若地拒绝履行合同,双倍返还定金即可。与此同时,若C 欲向E主张其他赔偿,则E 还将证明C所受损失的举证责任无情地附加给C 自身,但此时C 难谓遭受了经济上的损失。因此,有理由相信,即便最后对C 有其他赔偿,也更多地仅具有象征意义。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本案C 与E 签订合同绝非仅仅是为了取得钻戒的所有权,至为重要的目的在于携钻戒向D求婚,并收获极大地精神愉悦和人生最珍贵的记忆。此外,E 对自己的迟延交货亦有过错,对C的特殊合同目的更是知情。诚然,本案中法院强制E 履行因需要较长时间而不具实益,但并不意味着强调C的特殊合同目的无意义。此时,若一意孤行地支持拒绝履行,则必然会摧毁C的期待利益,放纵E的违约故意,助长不诚信和引发道德风险,反叛“一诺千金”的处事真谛,最终将使C为E的故意违约买单。
综上,合同的履行费用过高存在认定难题和规制缺陷,须以《中国民法典》⑥的编纂为契机,对之进行理论审思与制度甄别。同时,仅以合同的履行费用过高来判断合同是否继续履行的做法诚不可取,我们还应审查合同是否具有特殊目的、违约人是否存在故意、应否保护债权人的特别需要等因素。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过分倚重经济效益,必然变相怂恿商人不择手段地逐利,进而引发严重的信用危机和社会问题,扭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若违约方存在故意且守约方能对此加以证明,则应对违约方进行惩罚,即便履行费用过高,也应强制履行⑦。至于合同的特殊目的及保护债权人的特别需要等问题,将在下文展开论述。
三、甄别与完善:债权人的特别需要与合同特殊目的论
(一)概念难题:何谓合同目的
合同目的至关重要。合同目的在对重大误解和根本违约的认定上起着决定性作用,实乃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终极追求,集中彰显了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合同法》第60条、第62条、第94条、第148条、第166条等处多次提到合同目的,但纵观整部《合同法》,其并未对合同目的进行说明,进而引发概念与适用难题。
就比较法而言,英美法系国家的学者在谈到契约之要件时,认为其必须以发生法律关系为目的[6]5-6。日本学者认为债的目的在于给付,而给付分为五种:“特定物的转让、种类债权、金钱债权、利息债权和选择债权”[7]21-26,其中选择债权并不限于经济目的。尽管前述国家在表述合同⑧目的时的称谓与我国的表述略不一致,但其本质含义却是如出一辙,且它们都认为合同目的并不局限于经济利益抑或经济目的。
“银行说是上级行卡了规模,另外也觉得这笔贷款有风险。我向银行解释过,这家大企业信誉良好,回款及时,不会拖欠我们的款项,而且我自己企业的回款账户可以放在银行,还有什么担心的呢?但银行还是说不行。我觉得银行在风险评估手段上可以更灵活一些,仔细调研,不要一觉得有风险就干脆不做贷款了。”顾继宏说。
就国内学界而言,有学者认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追求的目标和基本利益不能实现[8]289。通过反对解释可知,合同目的即是指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所追求的目标和基本利益。亦有学者认为,合同目的是指合同双方当事人通过合同的订立和履行,期望最终得到的东西、结果或者达到的状态[9]。还有学者认为合同目的可以分为“一般目的”与“特殊目的”,前者指双方当事人各自欲实现的经济利益目的,它应当得到执行;后者则指出于特殊需求或者动机而产生的目的,必须是明示的、明知的或显而易见的[10]220-224。
综上,合同目的是指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所欲追求的目标和利益,其并不限于经济目的,尚包括精神权利、精神享受和其他特定目的。
(二)甄别难题:厘清关联内容
诚如前述,《合同法》并未对合同目的进行界定,进而导致司法适用上难题。现实的问题是,合同目的的适用在审判中依赖法官的解释与运用实乃权宜之计。同时,囿于法官法学素养和审判经验的良莠不齐,必然使类似案件的裁判结果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而更迫切的问题还在于合同目的与合同动机、附随义务等究竟有怎样的关联,如何对之进行甄别和厘清,以避免理论的混乱。
就合同目的与合同动机而言,笔者认为合同动机内在表现为需求,外在表现为诱因;而合同目的则表现为对预期追求结果的实现。在案例二中,C欲买钻戒在恋爱十周年纪念日向D求婚即为合同动机,最终C按时取得钻戒的所有权,并将之送给D且求婚成功和收获巨大精神愉悦则为合同目的。当然,在有的案件中合同目的与合同动机是难以区分的,只有结合法理、判例、惯例等进行综合认定。
而附随义务是指当事人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的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合同目的与附随义务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合同目的对附随义务的确定具有决定作用。
(三)适用难题:特殊合同目的之认定
笔者赞同将合同目的分为一般目的和特殊目的的做法。同时,笔者认为特殊合同目的主要包括但不限于精神利益、精神权利、精神享受⑨等内容,案例一中发包人A的预期目的即为著例(其为经济利益),此外,债权人的特别需要也可纳入合同的特殊目的,如此便可实现对守约方抑或债权人的充分保护。
然而,正义的天平诚不可无端倾斜。当事人的特殊目的必须在合同中进行明确约定(未在合同中明示,若有证据进行确切证明亦可),以合理保护违约方抑或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在《霍依与上海中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2002)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576号)的判决中,二审法院法官虽也认为上诉人(原审原告)买车的目的是作为“夫妻相识十周年纪念礼物”,其与一般的合同目的大不相同,理应受到法律保护,但最终判决并未支持上诉人的这一主张,理由就在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未在合同中对此进行约定,被上诉人亦未预见其违约会带来如此严重之后果。此时,若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这一请求,必将践踏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僭越居中裁判的法官角色。因而,笔者对二审法官的做法亦深表赞同。
综上,在具体司法实践中,面对合同特殊目的认定的问题时,应首先甄别当事人对特殊目的在合同中是否有明确约定,对方当事人对此是否知悉并预见后果(只要对方知悉且签订了合同,就应推定其已预见后果);若在合同中未进行约定而守约方能举出确切证据对此进行证明亦可;若既未对合同特殊目的进行约定又未能举示证据完成证明,则对守约方的请求将不予支持。此外,在对合同条款的理解发生分歧时,有关合同目的(尤其是特殊目的)的条款应具有优先效力,其有助于保证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和合法权益,促使合同的全面履行。
四、规制与发展:强制实际履行之适用条件论
(一)前提论
笔者对合同履行费用过高所生质疑与批判的目的绝非在于颠覆《合同法》第110条第1、2、3项之规定。同时,毋庸置疑的是在大部分案件中履行费用过高的规定确实能简化法律关系,化解合同纠纷,提高诉讼效率,其具有一定的操作性和存在合理性。而笔者唯一愤懑不平的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仅仅因为合同的履行费用过高就断然抛弃合同的继续履行(守约方自愿放弃继续履行的除外),转而采取损害赔偿等救济方式,漠视守约方的特殊合同目的与特别需要,致使履行费用过高的规定殃及无辜、诚信、满怀期待的守约人。事实上,在守约方未支付定金或未与违约方事先约定违约金,加上守约方自身很难证明其遭受了损失,遭受了多大的损失时,守约方的利益难以得到合理救济,况且在此种情况下,单纯的经济利益并不重要,特殊的合同目的才至为关键,若此时仍固执地排斥继续履行,必定会对守约方造成难以承受之痛。因此,本文是以此为基点进行逻辑展开的,其亦为后文论述的逻辑前提。
(二)要件论
诚如前述,《合同法》第110条第2项中关于履行费用过高的规定由于欠缺具体的认定标准,未考虑违约人的故意、合同的特殊目的等因素,致使其存在先天缺陷和适用难题。笔者认为,履行费用过高并不绝对排除合同的强制履行,而在此条件下,如何规定强制履行的适用条件抑或构成要件以助推其挣脱现行规定的羁绊,诚值研究。
笔者认为即便合同履行费用过高仍应适用强制实际履行的要件应包括如下内容:
1.违约方存在故意
诚然,我国《合同法》是秉承无过错责任之理念来构建违约责任的,质言之,只要违约方存在违约行为,则无论违约方是否具有过错,都应承担包括继续履行在内的违约责任。而此处之所以规定违约方应存在故意这一要件,实为提高履行费用过高背景下仍适用强制实际履行的准入门槛,增强违约方担责的正当性(在不存在合同特殊目的,仅有违约方故意且继续履行对守约方极为重要的情形下更是如此)。若因不可归责于违约方的事由导致违约行为发生时,绝不可再适用强制履行,应诉诸其他救济措施。须注意者,违约方存在故意与适用强制实际履行并非充要条件关系,即故意违约并不必然适用强制实际履行(有时可能考虑其他因素),强制实际履行也非仅有故意违约的缘故,有可能是基于合同的特殊目的保护。
2.存在特殊合同目的
如前所述,若当事人签订合同时对特殊合同目的进行明确约定,且对方当事人知悉此一目的并能预见违约所带来的非同寻常的损害后果,则即便履行费用过高,仍应支持守约方要求强制履行的诉讼请求,守约人应负担证明特殊目的存在的举证责任。至于在此情形中,强制履行与诸如损害赔偿等替代救济措施、情势变更、意外事件等的边界为何,尚待进一步研究。
3.强制履行仍属可能
首先,若合同事实上或者法律上不能履行,债务的标的不适合强制履行,则即使违约方存在故意、合同存在特殊目的、债权人有特别需要,我们仍应果断放弃继续履行,转而采取损害赔偿等救济措施,毕竟法不强人所难。其次,不可否认的是在部分特殊合同目的场合,强制履行似乎没有太大实益,如在案例二中,只要超过5月20日履行,即构成合同特殊目的不达,此时应在计算守约方损害的时候将合同特殊目的考虑在内,至于具体的赔偿额度,诚不可一概而论,应结合具体案例灵活确定。再者,实际上只有合同的特殊目的所承载的利益足够巨大时,强制实际履行或进行损害赔偿才具有意义,比如有关合同特殊目的的常见例子是异地恋者于情人节在网上为恋人买花,因为卖方的原因而未能按时送花,导致恋人感情出现裂痕,此时买方却只能索回订花时所支付的价款(如果提前支付的话),很难谓尚存在继续履行和主张其他损害赔偿的可能。
(三)小结
综上所述,在合同履行费用过高的情形下并不必然排除强制履行抑或继续履行的适用,而此时强制履行的适用条件为违约方存在故意、合同有特殊目的、履行仍属可能,须注意者,此三项要件并非要同时满足,而是在具体案件中可参照适用。
五、结论
《合同法》第110条第2项中关于履行费用过高的规定存在认定难题,其一刀切地排除继续履行的做法极不合理。在决定合同是否继续履行时,除了考虑合同的履行费用是否过高外,还应斟酌违约方是否存在故意、合同是否载有特殊目的、是否蕴含当事人的特别需要等因素。进而,履行费用过高并不绝对排除守约人要求强制实际履行的权利。在目前编纂《中国民法典》的大背景下,我们应对合同履行费用过高之规定进行理论甄别与制度完善,以期对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能有所裨益。
注释:
①有学者认为继续履行与强制实际履行同义,仅是提法不同,但继续履行这一字面含义却不能体现蕴藏其中的国家强制色彩,故该学者推崇并采纳强制实际履行这一表述,参见:叶昌富《论强制实际履行合同中的价值判断与选择》,载《现代法学》2005第2期第152页,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继续履行除了包括强制履行外,还应包括守约方请求违约方履行,而此种履行并不带有国家强制且此种履行请求较强制履行更具有普遍的意义,因为通常情况下守约方在违约方违约后应首先请求违约方继续履行而非径直诉诸法院或仲裁机关请求强制违约方履行。事实上,违约方并非都如“老赖”那般不堪,在守约方请求继续履行合同时,有的违约方会积极配合履行,最终实现合同目的。故笔者认为继续履行是包括强制履行的,二者存在差别。
②《合同法》第110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事实上不能履行;(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履行费用过高;(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
③笔者在北大法宝司法案例中检索“履行费用过高”关键词,筛选出的案例与裁判文书共484例,其中合同纠纷409例。在如何认定履行费用过高这一问题上,大都采取模棱两可的暧昧做法。
④须注意:强制履行与强制执行、直接强制有本质的区别,不可混用。强制执行乃缘于违约方对法院强制履行判决的拒不执行,而直接强制为强制执行的一种执行方法。
⑤大约在10年前,学界曾对效率违约展开过热烈讨论,并形成诸多学术研究成果。最终的结果是我国依然坚持将继续履行作为补救合同的首选,但适当借鉴了效率违约的某些理念。参见:孙国良《效率违约理论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5期;唐清利《效率违约:从生活规则到精神理念的嬗变》,载《法商研究》2008年第2期等。
⑥2014年10月23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编纂民法典,标志新一轮的民法典编纂工作正式扬帆起航,民法学界亦是斗志昂扬。目前,正在进行《民法总则》的征求意见稿工作,接着将着手制定民法分则部分,预计2020年左右会出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民法典》。
⑦强制履行发生在法院判决阶段,有可能被写入生效判决的主文,成为强制执行的依据。如前所述,若违约方对此判决拒不执行,则法院将会进行强制执行,依《民事诉讼法》理论,强制执行包括直接强制、间接强制(包括代替执行和执行罚)。此处,切不可将强制执行等同于直接强制。当然,若最终履行不能,则应提高对守约方的赔偿额度。
⑧在民法学说史上,亦曾有过“合同”与“契约”的区别。契约为个人法上法律行为之典型,合同行为为团体法上法律行为之典型,同时,从字面上看契约的概念比合同更确切。但新中国成立后,基于时代变革的大背景,契约一词逐渐被合同所取代,时至今日,在中国大陆从国家立法到日常用语,已普遍接受了“合同”这一概念,在我国台湾地区等地仍然适用契约一语。参见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版,第310—311页;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9—10页。
⑨须注意:此处因合同特殊目的不达所遭受的损害与因合同违约所遭受的精神损害并不相同,众所周知,《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并不承认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由于前者为当事人双方所明知且已成为合同条款,违约方对违约之后果亦有所预见,当事人理应受其约束,在合同特殊目的不达时,此部分应计入损害赔偿的计算,而不能仅仅因为其或多或少承载了精神利益,就以违约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为由进行驳回,否则守约方的利益必将暴露于外。
[1]顾全.合同法上强制履行的适用条件分析[J].人民司法,2012 (24):31.
[2]叶昌富.论强制实际履行合同中的价值判断与选择[J].现代法学,2005 (2):155.
[3]王洪亮.强制履行请求权的性质及其行使[J].法学,2012(1):112.
[4]Reinhard Zimmermann.The new German Law of Obligation: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102 (2005).
[5]韩世远.合同法总论 (第三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6]杨桢.英美契约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7][日]我妻荣.债法总论(新订)[M].东京:岩波书店,1991.
[8]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2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9]马忠法.“合同目的”的案例解析[J].法商研究,2006 (3):123.
[10]王信芳.民商事合同案例精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