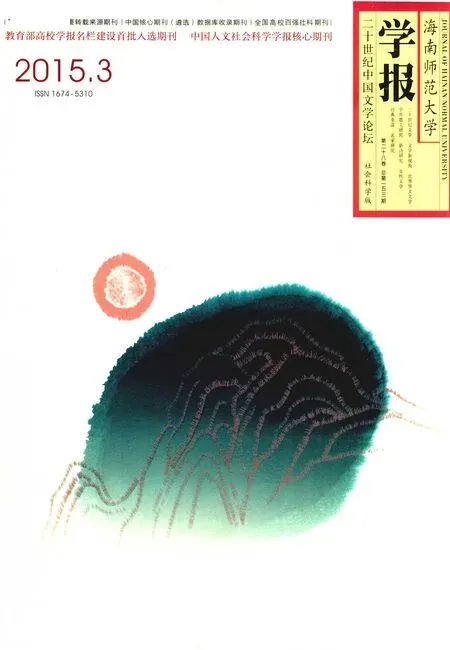汪曾祺散文的“自然之趣”
2015-03-29常恺蓉
常恺蓉
(河南省农业经济学校,河南 洛阳471002)
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说道:“在世界古代各文化体系中,没有任何系统的文化,人与自然,曾发生过像中国古代这样的亲和关系。这说明了我们整个文化性格的一面。”[1]的确,中国的文人一直以来都重视“智者乐山,仁者乐水”的美学命题,文人作品与山水自然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宗炳提到“至于山川,质而有趣灵”,可见山水在文人的心里是有“趣灵”的。其实,文人写山水,无非写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游山水的过程中,讲究的也是人与山水的默契、融合。王思任在《游唤·石门》中曰:“夫游之情在高旷,而游之理在自然,山川与性情一见而恰,斯彼我之趣通。”[2]当山水与个人性情相互契合,即作者发现了山水与个人气质旨趣相通的地方,这种旨趣相通或是从山水中得到内心的愉悦,或是由山水而获得内心的宁静,或是由风景而回忆起遥远的往事,或是由风景中的人文文化而得到心灵的升华。因此,自然山水对文人来说是“外供耳目之娱,内养仁智之性”,既可得到感官的乐趣,也可由人与自然的旨趣相通而达到“内养仁智之性”的目的。
汪曾祺在个人气质上是恬淡平和的,在为文上“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强调文章能滋润人心。他拥有士大夫一样的雅致情趣,对富有人情和趣味的生活有一种深深的向往,对闲适游心的境界有着深深的认同。
一、与山水的旨趣相通
汪曾祺写自然山水的散文,其一,能让读者感到心灵的安静、滋润。其二,读者能从他的山水散文中读出他的旨趣,他的闲散恬淡的气质。
从第一点来说,山水对汪曾祺来说是其所追求的精神宁静的载体。大自然的古雅、宁静、脱俗深深滋润着汪曾祺的心灵,使他在一处景观中或者从容地享受景色之美,如《南山塔松》中描绘塔松:“塔松极干净,叶片片片如新拭,无一枯枝,颜色蓝绿,空气也极干净。我们藉草倚树吃西瓜,起身时衣裤上都沾了松脂。”[3]234或者自如地怀念家乡,如在《伊犁闻鸠》中写道“伊犁的鸠声似乎比我的故乡的要低沉一些,苍老一些”;或者深深陶醉于某地的人文景观,如《伊犁河》中描写的古时废员流放的古城以及林则徐的传说与事迹、《天山客话》的记载等等。享受景色也好,怀念家乡缅怀历史也罢,自然的景物都给了汪曾祺浮世的安慰和精神的疗养。第二,汪曾祺总是能在自然中找到与自己精神相契合的地方,达到与山水的旨趣相通。如《桃花源记》作者游览桃花源时,一开始就表明他其实并不信陶渊明描绘的桃花源是个真实的存在,并坚持用自己的观察营造着属于自己的桃花源。作者饶有兴趣地讲述了当地的“擂茶”,擂茶怎么做,怎么吃,有什么功效,擂茶是从何时流传下来的,最早记载于哪里,作者一一道来,言之凿凿,引经据典。在游览山上的桃花观、秦人洞时享受风景,体味历史,末了赋诗:“红桃曾照秦时月,黄菊重开陶令花。大乱十年成一梦,与君安坐吃擂茶。”[3]273这个桃花源已被赋予了汪曾祺的旨趣,他的闲散,他的文人气,他透露出来的人生意境都在这片桃花源中显现出来了。他在桃花源中找到了与自己相默契融合的地方,又在看山看水看擂茶中看懂了人生,“与君安坐吃擂茶”何尝不是他体会到的人生的真谛!古时游记如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都于山水中寄托着自己政治上的失意,心态的冷清。如柳宗元在《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写道:“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4]文章充溢着孤凄失意之情。但汪曾祺的游记“上下四旁而言之”,不刻意表现什么,曲曲折折,在奇事异物、风土人情的记述中穿插自己对各种现象的评论和生活的智慧。他是在真正地享受山水带给他的乐趣,体悟生命,陶醉其中。
汪曾祺的气质和旨趣决定了他很少去关注那些具有宏大气势的景观。他陶醉的永远是小枝小节的地方,却让我们感受到无限情趣。他在《泰山片石》中说:“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泰山既不能进入我的内部,我也不能外化为泰山。山自山,我自我,不能达到物我同一。”[5]因此通篇几乎没有对泰山壮阔景色的描写,作者沉醉于考证泰山的山神碧元霞君,流连于泰山的那种“经石峪”的字体,因此他笔下的泰山没有刘白羽的《日出》那样的阔大峻美,只能于泰山老奶奶的考证和“经石峪”的年代版本中达到物我同一,于小枝小节的地方让我们感到无限情趣。尽管关注的是小枝小节,但是汪曾祺在面对山水自然时,善于联想,善于融贯古今,使自己小小园林式的文章超越狭小范围的限制,凝结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并展现出自己对这种历史文化意识的独到认识和体验。如在《伊犁河》中,作者以伊犁作为废员充军之所的历史文化为参照系,插入林则徐的历史传说,洪亮吉的《天山客话》,锡伯人的戍边迁徙,使人联想翩翩,情趣盎然。作者又适当地加入自己的感情和思想,使整个《伊犁河》充满了英雄的悲壮与浪漫氛围,这样的历史文化书写使汪曾祺的山水自然散文充满了理趣和情趣。
二、花鸟虫鱼的“天趣”
汪曾祺视花鸟虫鱼为“朋友”,为“知己”,他花了大量的篇幅来写花草虫鱼鸟兽,如《花园》《昆虫备忘录》《腊梅花》《葡萄月令》《草木春秋》等篇,在这些文章中,汪曾祺以无比浓厚的兴趣审视着大自然的一切生灵。
汪曾祺对自然生灵的亲近或许源自于童心,他曾说:“人上了岁数了,最可贵的是能保持新鲜活泼的,碧绿的童心。”[6]汪曾祺有着丰富的童年经验。所谓丰富的童年经验,是指童年生活很幸福,物质、精神两方面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生活充实而绚丽多彩。[7]汪曾祺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为清朝末科拔贡,父亲“是画家,会刻图章,会写意花卉”,“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汪曾祺受尽家族宠爱,拥有的是所有孩童都羡慕的童年。这种丰富的童年经验对他以后的创作和生活态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曾说:“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一个作家,童年生活是起决定作用的。首先要对生活充满兴趣,充满好奇心,什么都想看。要到处看,到处听,到处闻嗅,一颗心‘永远为一种新鲜颜色,新鲜声音,新鲜气味而跳’,要用感官去‘吃’各种印象。”而“趣”本身也是一种自然而然、无拘无束的心境,这种心境也是在儿童身上表现得最明显。袁宏道曾说:“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面无端容,目无定睛,口喃喃而欲语,足跳跃而不定,人生之至乐,真无逾于此时者。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盖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角最上乘也。”[8]“童心”之所以和“趣”相联系,是因为东瞧瞧西看看是孩子的本性。孩子总是对一草一木、一花一果好奇而忘情地投注他澄明的目光。而一个成年人对花鸟虫鱼的兴趣盎然应该就源于一种不自觉的自然而然的灵性,有了这种灵性,他才能用他的全部器官去感受花鸟虫鱼的世界,只有一颗完全自然、健全灵动的心灵,才会有这种至纯至美的感应,才会融入其中去描述一个个清纯的生命。试看汪曾祺在《花园》中对天牛的描写:“这小小生物完全如一个有教养惜身份的绅士,行动从容不迫,虽有翅膀可从不想到飞;即使飞,也不远。一捉住,它便吱吱扭扭的叫,表示不同意,然而行为依然是温文尔雅的。”视天牛为自己的朋友知己,视自己为大自然的一部分,这是一种物我两亲的观念。在这一审美层次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完全对应的,自然走向人,亲近人,愉悦人,成为人的知己。人类也忘却了自然的功利性,以纯粹的自然物象作为审美的对象。
有天趣的作品,多写山水田园生活,因为人在大自然及田园之中,能够较多地保存自己的真性情和自然面貌,容易表露天然的风趣。对花鸟虫鱼的关注表明汪曾祺的虚静之心。审美主体只有以空明虚静的状态去观照自然,自然才有悦身畅神的作用,即古人所说的“澄怀味象”,徐复观曾对此做过解释:“澄味”,即庄子的虚静之心。以虚静之心观物,即成为由实用与知识中摆脱出来的美的观照。所以澄怀味象,则所味之对象,即进入美的观照之中,成为美的对象。而自己的精神,即融入美的对象中,得到自由解放。汪曾祺用一颗虚静之心发现着自然之美,忘我地体味着大自然的乐趣。在他眼里,这些花鸟虫鱼、果蔬香茗莫不趣味横生。如《腊梅花》中,作者体会着腊梅花“热热闹闹而又安安静静”的不寻常的境界。并亲自“到后园选摘几只全是骨朵的腊梅,把骨朵都剥下来,用极细的铜丝,把这些骨朵穿成插鬓的花,我在这些腊梅珠子花当中嵌了几粒天竺果,把这些腊梅珠花送给他的祖母,大伯母等。黄腊梅,天竺,我到现在还很得意:那是真的很好看的。我应该当一个工艺美术师的,写什么屁小说!”[9]作者发现腊梅花的不寻常之美,也体味用腊梅做珠花的乐趣,在对一花一木的深沉静默的观照中,作者的心灵与万物冥合,使人的本体与自然本体融二为一,形成了清朗明净的审美境界。
汪曾祺对花鸟虫鱼天趣的关注与兴趣其实是一种对生命本身的关爱,如在《葡萄月令》中,他把葡萄的生长描绘成一个婴儿成长的过程,其间的拟人描写充满温馨与浓浓的孩子气:“一月,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三月,葡萄上架。葡萄藤舒舒展展,凉凉快快地在上面呆着”,“四月,浇水。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它真是在喝哎!漫灌,整池子的喝”,“九月的葡萄园像一个生过孩子的少妇,宁静、幸福,而慵懒”。这些文字中传达出了生命生长的氛围和境界。在作者笔下,葡萄已经超越了植物自身的生命范畴,它已带有人的思想,有了灵魂。在《葵薤》中如此说:“古人说诗的作用,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还可以多识草木虫鱼之名。这最后一点似乎和前面几点不能相提并论,其实这是很重要的。草木虫鱼,多是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对于草木虫鱼有兴趣,说明对人也有广泛的兴趣。”葵薤虽是普通之物,却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有其兴衰成败,可以让人生出一些感慨。这些话解释了汪曾祺对于草木虫鱼的品味态度,他对草木虫鱼的兴趣的本质是对生活和生命本身的关怀。将草木虫鱼的世界化作供人类获得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美文,娓娓道来,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
[1]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34.
[2]王思任.游唤[M].北京:中华书局,1991:112.
[3]汪曾祺.汪曾祺全集(三):散文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4]柳宗元.柳河东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94.
[5]汪曾祺.汪曾祺全集(五):散文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93.
[6]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六):散文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63.
[7]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J].文学评论,1993(4).
[8]袁宏道.叙陈正甫会心集[M]//袁宏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463.
[9]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四):散文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