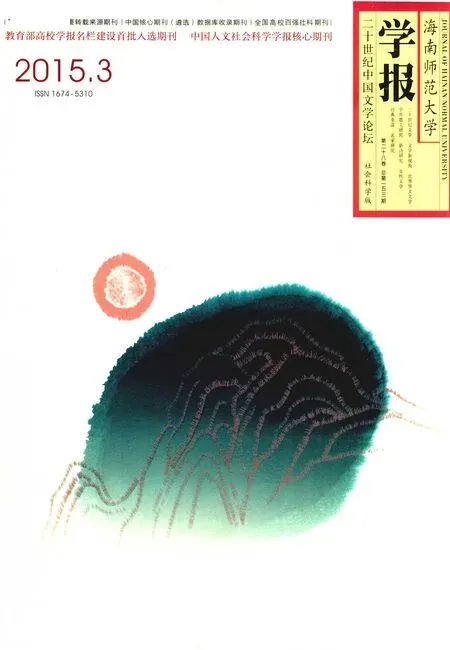慢,作为自然的节律——论刘亮程散文的生态意义
2015-03-29黄增喜
慢,作为自然的节律——论刘亮程散文的生态意义
黄增喜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刘亮程散文对文明、自然与时间三者关系的独特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慢”的哲学,与当代生态哲学思考存在着诸多契合。他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矛盾性认识,一方面体现了恢复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努力与可能,另一方面则肯定了自然的复杂性,以及人认识、融入自然的限度。他的思考植根于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或可对当代西方生态哲学、生态批评中若干争议的澄清作出贡献。
关键词:刘亮程;“慢”的哲学;自然的节律;共时化;人与自然
收稿日期:2014-11-20
作者简介:黄增喜(1981-),男,瑶族,广西富川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宗教文学、生态批评。
中图分类号:I207.6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刘亮程散文的生态内涵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不少学者尝试从生态批评的视角解读这些作品。①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周立民的《刘亮程的村庄》(《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摩罗的《生命意识的焦虑——评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期)、唐克龙的《当代生态文学中的动物叙事与生命意识的兴起》(《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刘涵华的《农业文明的歌者——苇岸、刘亮程散文创作比较》(《昌吉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胡新华的《生态与生活——对刘亮程部分散文的生态批评》(《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叶从容的《论新乡土散文的后现代生态意蕴》(《鄱阳湖学刊》2011年第3期)、和谈的《浅论刘亮程散文中的生态美学意蕴》(《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孙宵的《乡村叙事中“自然”情怀的分野——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与梭罗〈瓦尔登湖〉之比较》(《文艺争鸣》2012年第11期)、詹冬华的《新时期中国生态散文的审美精神》(《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等。遗憾的是,大部分研究者或因对生态批评理论不甚了了,或因仅限于对刘亮程散文作图解式的勾勒,并未能得出较精当或全面的认识。究其根由,刘亮程的创作与当代西方生态文学家如利奥波德、卡森、艾比、阿特伍德等不同,并没有在某种自觉的生态意识的指导下,刻意张扬某种生态伦理或生态实践,甚至几乎没有涉及生态问题。他与另一位从事自然写作的中国当代散文家苇岸也很不相同,后者明显受到西方生态文学家特别是梭罗的影响,而前者的创作中却看不到多少西方影响的痕迹。②参阅刘涵华《农业文明的歌者——苇岸、刘亮程散文创作比较》(《昌吉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该文对苇岸和刘亮程的思想资源作了宽泛的比较分析,其对两位作家的评价是值得商榷的。这就给我们的解读带来了困惑,而这一困惑也是当代生态文学研究经常遇到的:是不是只有那些具备明确而自觉的生态意识的作家才可称之为生态作家?那些并无只言片语直接论及自然或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是不是就应被排除于生态文学之外?这两个问题实际上都围绕“何为生态文学”的问题而展开,而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尤其是当我们援用当代西方生态批评理论来阐释某些中国文学作品时,往往会有方枘圆凿之感。因此,我们或可将其转换成另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文学能够为我们思索和应对生态问题提供正面的资源?如此我们便直接抵达问题核心,避免了在借鉴西方理论过程中的生搬硬套。以此目光去审读刘亮程的散文,我们发现,其中对文明与时间、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慢”的哲学,与当代生态哲学、生态批评理论之间存在诸多契合,蕴含着重要的生态资源。
一
甫一成名,刘亮程便被称为“后工业时代的乡村哲学家”[1];至于他到底是什么类型的哲学家,传达了一种什么样的哲学,则见仁见智。依我看来,刘亮程散文中最引人注目最富有意味的是他对“慢”的重视;“慢”几乎成了其中的一个核心意象、一个关键词。在他的笔下,时间仿佛放慢了自己的步伐,一切人和事物也都慢了下来,乃至停止了生长与变化。他这样表述自己的哲学:“我没有太要紧的事,不需要快马加鞭去办理。牛和驴的性情刚好适合我——慢悠悠的。”(《逃跑的马》)*本文所引刘亮程散文文本主要以2001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个人的村庄》和2013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个人的村庄》(典藏本)为依据。引用过程中只列出篇名,不再作注说明。他自称“闲锤子”,总是扛着一把铁锨,不紧不慢地在村庄四周晃悠(《我改变的事物》)。即便是动物,他也更喜欢慢的而不是快的:“我喜欢那窝小黑蚂蚁,针尖那么小的身子,走半天也走不了几尺……大黄蚂蚁也不咬人,但我不太喜欢。它们到处乱跑,且跑得飞快,让人不放心。”(《两窝蚂蚁》)刘亮程在多次访谈中也表达了自己对“慢”的情有独钟:“我喜欢慢事物。”[2]“我过的是一种慢生活,慢写作。”[3]*另可参阅张滢莹《刘亮程:作家的心灵应该更慢》,《文学报》2013年5月16日第5版。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慢性子,大部分慢性子往往对自己的慢处于无意识状态,有些意识到了的则可能为此苦恼。但当一个慢性子不仅认识到了自己的慢,并且有意识地保持慢、充分享受这种慢的时候,他的行为就可能不再仅仅是一种习惯,而是上升到一种人生态度或人生哲学了。刘亮程对“慢”的清醒认识和自觉选择显然就属于这种情况。表面看来,“慢”的哲学纯粹基于个人体验,但实际上它有着广阔的时代背景。
当今文明的飞速发展与现代人的时间观念密切相关。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秋收冬藏,严格遵循自然的节律而生活,人类的日常时间是与自然生态的时间和谐一致的。人类在自然中创造和演绎自己的文明,世界各地的时间节奏因自然环境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文明并未从自然中脱离出来,而是处处遗留着自然的胎印,这样的文明在物质积累上必定是有限的。近代机械时间观的出现,为人类文明的自我突破创造了可能。这种时间观与传统的时间观不同,它认为时间并不像自然的节律那样有快有慢,而是以均匀的质地运行于宇宙间、不同的社会中以及钟表之上。不论人类怎样活动,时间都在以自己的步伐不紧不慢地向前挺进。人类首先在均质的时间中形成了竞争关系:在有限的时间内,谁创造的财富越多,谁就走在世界的前列。与此同时,整个人类也与时间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关系:谁能在某个时间内完成或提前完成了某事,便赶上甚至超越了时间,而对时间的战胜又意味着对那些落后于时间的他人的取胜。毫不奇怪,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在一百年中创造的生产力,比人类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这种时间观念逐渐侵入日常生活,求新求快主导了当代人的思维方式。各民族国家希望一夜之间步入世界前列,明星们担心一夜醒来自己已经过时,而普通人同样怀着超越自我的欲望,亦步亦趋地追逐着时代的步伐。当今人类几乎生活在一个纯粹由人类文明构成的社会之中,其视阈所呈现的都是由人类自身制造出来的东西。自然的位置在哪里呢?自然早已被现代文明甩到了身后,沦为人类征服的对象、追逐财富的原料产地、文明戏剧上演的背景。
基于以上勾勒,我们无需思考太多,便可看出当代的能源枯竭、环境污染、物种灭绝等种种问题与现代时间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我们的文明发展得太快了,其节奏与速度远远脱离了自然的节律。当代德国神学家莫尔特曼说:“如果人类和地球的共同灾难毕竟还是可以避免的话,那么,当然只能通过使人类历史和自然历史共时化,并且,现代的实验应当按照与自然的协调一致来进行,而不是与自然相对立,以牺牲自然为代价。”如何实现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的共时化呢?他认为“重要的是‘冷却’人类历史,减缓其片面性的进步”。[4]
在令人眩晕的飞速发展过程中,人忘记了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企图在时间上脱离自然,但终究无法在空间上摆脱自然。既然人是通过时空的坐标来认识自己的,当他脱离了自然的时间而仅剩下空间的维度时,就必然迷失自我的身份和位置,在遗忘自然的同时遗忘自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态问题就不仅仅是单纯的生态危机,而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危机。奥地利习性学家康拉德·洛伦茨把当代人与人之间的恶性竞争称为“与自己赛跑”,认为它造成了当代人的种种精神疾病。他说:“即使地球人口不会按照今天的这种速度继续增加下去……单是这种人类内部在经济上的你追我赶已足以使人类彻底毁灭。”[5]因此,人类有必要适当放慢自己的脚步,对近代以来的文明发展模式做出彻底的反思,回归自然的节律,谋求人类文明时间与自然时间的共时化。
刘亮程并没有纵谈人类文明与生态危机,但他以个人的深切体验告诉我们:虽然我们的文明在不断抛弃自然,我们的身体却在反抗文明本身。其散文之所以能超出传统乡土文学,出人意料地引发广泛共鸣,就在于其“慢”的哲学道出了当代人被压抑的本能欲求——身体要摆脱当代文明的强制、回归自然节律的需要。他说:“许多东西需要我们慢下来停下来等。快生活是一种你追我赶的生活,像狗追兔子,狗和兔子都不能慢。但是,我们人类已经远远跑到了前面,需要慢下来等等了。”他觉得自己一直生活在传统农耕文明的时间当中,认为这种时间完全不同于现代城市的时间:“所谓农耕时间,就是一个大块时间,比如只有白天黑夜,或者只有上午下午,一日三餐,日出日落,不像城市的这种快时间,它把时间分成了一小时,一刻,一分一秒,时间一碎,自然就快了。农耕时间没有被切碎,所以在这种大时间里面人活的比较从容。”“农耕时间的缓慢,就是因为作物生长慢,人得耐心等种子发芽、等叶子长出、等花开花落,果实成熟,这个过程快不了。”[3]可以看出,正是对文明与时间关系的独特认识,为刘亮程“慢”的哲学提供了依据,并使他的散文与当代生态问题的思考勾连起来。
二
放慢生活的脚步,我们对于自己的位置、自然万物的身份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都会发生根本的改变。我们不仅开始重新关注自己,而且必然会开始关注周遭的动物、植物甚至是非生命物质,倾听它们那早已被人类遗忘在身后的声音。“人寂静下来的时候,就会听到远远近近,许多事物的声音,他们组合在一起,成为大地的声音,天空的声音。”(《黄沙梁》)惟有从喧嚣而躁动的竞争中缓和下来,我们的心灵才会重新发现自然之美:“有些虫朝生暮死,有些仅有几个月或几天的短暂生命,几乎来不及干什么便匆匆离去。没时间盖房子,创造文化和艺术。没时间为自己和别人去着想。生命简洁到只剩下快乐。我们这些聪明的大生命却在漫长岁月中寻找痛苦和烦恼。一个听烦市嚣的人,躺在田野上听听虫鸣该是多么幸福。大地的音乐会永无休止。而有谁知道这些永恒之音中的每个音符是多么仓促和短暂。”(《与虫共眠》)自然成为文明的镜子,久居文明中的我们也只有在与自然的重新亲近中,才能够看清楚自己的真实面相。在那篇真切感人的《对一朵花微笑》中,刘亮程说:“我活得太严肃,呆板的脸似乎对生存已经麻木,忘了对一朵花微笑,为一片新叶欢欣和激动。”其实,严肃呆板的人不止刘亮程一人,它是工业文明重压下的当代人共有的表情。但是再发达的文明,都无法彻底抹去人身上的自然性,后者总会在文明高唱猛进之时宣告自己的存在。
“人的灵魂中,其实还有一大群惊世的巨兽被禁锢着,如藏龙如伏虎。它们从未像狗一样咬脱锁链,跑出人的心宅肺院。偶尔跑出来,也会被人当疯狗打了,消灭了。”(《人畜共居的村庄》)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往往以人的自然性为代价,*参阅弗洛伊德《一种幻觉的未来 文明及其不满》,严志军、张沫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但人类无法摆脱其与生俱来的自然性;即便他穿上花哨的文明外衣,依然无法掩埋自己与自然万物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人类需要自然,二者构成世界的整全性存在。“每年春天,让我早早走出村子的,也许就是那几棵孤零零的大榆树、洼地里的片片绿草,还有划过头顶的一声声鸟叫……如果没有了它们,我会一年四季呆在屋子里,四面墙壁,把门和窗户封死。我会不喜欢周围的每一个人。恨我自己。”(《春天的步调》)在刘亮程看来,人与驴、马、狗、牛等动物都是时间中的存在,其境遇没有截然分明的界线,其感受也往往相通(《通驴性的人》《人畜共居的村庄》《卖掉的老牛》等);而且它们与其他万物构成着人的完整存在,离开了它们,人的存在将是破碎不堪的。“从每个动物身上我找到一点自己。渐渐地我变得很轻很轻,我不存在了,眼里唯有这一群动物。当它们分散到四处,我身上的某些部位也随它们去了。”(《通驴性的人》)“也许我们周围的许多东西,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关键时刻挽留住我们。一株草,一棵树,一片云,一只小虫。它替匆忙的我们在土中扎根,在空中驻足,在风中浅唱……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任何一棵树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任何一粒虫的鸣叫也是人的鸣叫。”(《风把人刮歪》)人与自然万物在共同的时空中承受着共同的命运,处于一种相依相存、荣辱与共的关系中:“驴日日看着我忙忙碌碌做人;我天天目睹驴辛辛苦苦过驴的日子……驴长了膘我比驴还高兴;我种地赔了本驴比我更垂头丧气;驴上陡坡陷泥潭时我会毫不犹豫将绳搭在肩上四蹄爬地做一回驴。”(《通驴性的人》)
此类思考不仅大量出现于刘亮程的作品里,而且在其访谈中也时有闪现。他曾说到:“……而人之外,世界丰富无比。这不仅仅是人的世界,也是一条狗、一只蚂蚁的世界,更是一阵风、一颗尘土的世界。”[6]在对共同命运的承载过程中,自然塑造着人(《村东头的人和村西头的人》《住多久才算是家》等),人也改造着自然(《我改变的事物》《坑洼地》等),二者是一种互动的共生关系,而绝不是现代文明所呈现出来的简单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以这样的视角去观照万物,必然会导出应当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问题。这既是刘亮程散文中最为人所称道的思想,也是最能与当代西方生态伦理形成直接对话的资源。
三
当代生态伦理学存在一系列争议性的议题:我们能否真正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能否真正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如何将保护自然与利用自然结合起来?如何理解和区分自然的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在大谈爱护动物的时候,我们又如何面对自己依然食肉的事实?在保护自然的过程当中,如何避免人类的不当干预或过度干预?等等,不一而足。*相关讨论可参阅戴维·贾丁斯《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林官明、杨爱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罗德里克·纳什《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杨通进译,青岛出版社2005年版;彼得·辛格《动物解放》,祖述宪译,青岛出版社2004年版。刘亮程充满诗性的文字当然没有也不可能对这一系列理论问题发表明确的看法,但我们依然能从中发现并总结出与这些问题密切相关的闪光思想。
在刘亮程的散文中,人与自然的相怜相惜、人对自然的感恩之情十分突出(如《通驴性的人》《老鼠应该有个好收成》等)。前述很多相关研究都主要(而且仅限于)围绕这些思想进行分析和论述,这里就没必要重复了。我们要重点讨论的是刘亮程对待自然的态度中被大部分研究者忽略了的一个侧面:人类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自然?
表面看来,刘亮程的态度显得有些含糊,甚至不乏矛盾之处。一方面,他强调人与万物之间的同源性和共生性,彼此的交流是可能的。“万物说话,人独不听。或者听不懂不愿听。心灵的语言可以相互听懂。人用心时能听懂鸟鸣风声,风亦能听懂人。”[7]这是刘亮程在一次接受腾讯微博公益访谈时说的;该看法在其散文作品中亦常有显露。但另一方面,他笔下的自然世界又往往呈现出神秘的特征,拒绝人的进入。在他看来,驴可能是一个“冥想着一件又一件大事”、“想得异常深远、透彻”的“智者、圣者”(《通驴性的人》),马“并不是被人鞭催着在跑”,而是奔逃在属于它自己的人所不知的路上(《逃跑的马》),天空和大地似乎都有自己的记忆(《大树根》)。尤其是在一个人独自面对荒野的时候,横亘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屏障显得异常的突兀:“真正进入一片荒野其实不容易,荒野旷敞着,这个巨大的门让你在努力进入时不经意已经走出来,成为外面人。它的细部永远对你紧闭着。”尽管花开烂漫的野草使刘亮程第一次在荒野中独自一个人笑出声来,使他认识到自己平日可笑的严肃,但最终他却发现:“我从草木身上得到的只是一些人的道理,并不是草木的道理。我自以为弄懂了它们,其实我弄懂了自己。我不懂它们。”(《对一朵花微笑》)
如何理解刘亮程对待自然态度的矛盾性呢?有论者也曾留意到这一点,但其复杂而丰富的意味却完全被略过了。在我看来,正是在这种矛盾性的心态中,刘亮程的散文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达了一种深刻的认识:人与自然在生存处境上的确没有本质的区别,但人毕竟又不能与自然完全等同;所谓“将自己整个儿地化掉”、“没有了自己的灵魂,没有了主体之我”,[8]只是将人与自然交流中的某些理想瞬间泛化、凝固化了,却没有看到长期浸染于文明中的人在面对自然时所必然具有的局限性。刘亮程一方面肯定人有必要放慢自己的脚步去关注自然,在与自然的交流中重新认识和定位自我,另一方面则注意到现代人不关注自然已经太久了,自然对我们而言已经变得陌生,因此我们要认清并接受自己的局限性,不要想当然地将人类的种种一隅之见、因袭之见加诸自然之上。
《三只虫》很贴切地指出了人类认识视域的局限:人总是想当然地去揣度万物。当一只小虫沿着作者的手指爬到指甲盖的边缘时,他认为小虫无路可走了。但正当“我正为这只小虫的短视和盲目好笑”时,它却没有掉下去,而是从指头底部慢慢悠悠爬向了手心,把羞愧留给了人。另一次,一只蚂蚁背着一条至少比自己大二十倍的干虫,人看得着急,就抓了另一只闲转的蚂蚁,让它去帮忙,结果导致了两只蚂蚁的互殴,帮了倒忙。作者从人的角度对蚂蚁的行为与心理作了种种令人忍俊不禁的猜测,却一错再错,最终只能喟然而叹:“我这颗大脑袋,压根不知道蚂蚁那只小脑袋里的事情。”人类认识的局限不仅源于不同族类间那不可化约的差异,还往往跟人类过于功利的态度有关。比如对待马:“我们对马的唯一理解方式是:不断地把马肉吃到肚子里,把马奶喝到肚子里,把马皮穿在脚上……我们用心理解不了的东西,就这样用胃消化掉了。”(《逃跑的马》)对待牛也同样如此:“我们需要牛肉的时候,牛的清纯目光、牛哞、牛的奔跑和走动、兴奋和激情,便只好当杂碎扔掉了。”(《等牛把这事干完》)我们以有用无用去区分万物,殊不知它们的存在可能有着更深刻的目的,拒绝人类狭隘的区分:“我们不清楚铃档刺长在大地上有啥用处。它浑身的小小尖刺,让企图吃它的嘴,折它的手和践它的蹄远离之后,就闲闲地端扎着,刺天空,刺云,刺空气和风。”(《风把人刮歪》)动物及其他非人类存在拥有着远远超出人类理解之外的目的,它们向人类呈示的往往正是人类想从它们那里获得的一小部分,至于它们不能为人所利用的更大部分,则远远地逸出了人类的视线。
这就告诉我们,由于功利性目光的局限,相对于传统的农业社会,自然对现代工业文明下生活的人来说不是变得更简单了,而是构成了一个更为巨大的认识深渊。它进一步提醒我们:我们必须以更为小心谨慎的态度去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人类的任何行为都可能深远地改变自然生态的样貌,而很多时候这种改变可能是不可逆的(例如物种的灭绝)。[9]我们的每一次误入丛林都可能引起一窝野兔的生活变迁(《野兔的路》),我们的每一次拓垦都可能加速一片土地的死去,并毁坏其间生物的生存环境(《坑洼地》)。在《最大的事情》中,刘亮程深刻地反省了人类可能施与自然的巨大影响和永久创伤:
如果我们永远地走了,从野地上的草棚,从村庄,从远远近近的城市。如果人的事情结束了,或者人还有万般未竟的事业但人没有了。再也没有了。
那么,我们干完的事,将是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大的事情。
别说一座钢铁空城、一个砖瓦村落。仅仅是我们弃在大地上的一间平常的土房子,就够它们多少年收拾。
……
不管多大的风,刮平一道田埂也得一百年工夫。人用旧扔掉的一只瓷碗,在土中埋三千年仍纹丝不变。而一根扎入土地的钢筋,带给土地的将是永久的刺痛。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消磨掉它。
刘亮程的思索是发人深省的。既然我们不可能彻底走进自然,而且我们的行为总是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自然的进程,那么在不能了解自然或不能预测自己的行为最终会导向何种结果之前,我们对待自然的恰当态度或许只能是敬畏,做一个自然的旁观者,而不是贸然的介入者。这样的态度固然谈不上多少建设性,但它至少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自然界不可修复的创伤。反过来可以试问:世间的很多伤害和破坏不正是由积极建设的人类行为中衍生出来的吗?现代文明有必要践行“慢”的哲学,控制急速冒进的步伐,降低行为的盲目性。这不仅有利于能源消耗速度的减缓,而且为我们的每一项决策增加了一个不可忽视的新维度——自然。惟其如此,莫尔特曼所说的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的共时化方可实现。
四
唐克龙先生指出,刘亮程的动物伦理是矛盾的,“从生态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村庄’这个题名其实是不恰当的,它反映的不过是刘亮程极其主观的内心,而把其他的有机村庄屏蔽了。从根本上来说它仍是刘亮程隐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表征”,因此,“他的境界也实际上比贾平凹高不了多少,甚至还要不堪”。[10]我在此不想追问唐克龙先生对于当代生态伦理学究竟有多少认识,也不想具体分析刘亮程是不是真的以“极其主观的内心”屏蔽了“有机的村庄”,但想对他给刘亮程扣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这顶帽子略陈一二。首先,“人类中心”固然是人类的一种错觉,但“人类中心主义”能否超越、如何超越,却依然是而且可能永远是一个悬而不决的问题;而学界围绕“强势人类中心主义”和“弱势人类中心主义”展开的辨析却告诉我们,所谓的“弱势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是不乏理论与实践意义的。[11]如果硬要给刘亮程加上这样一个名头,我觉得他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至多也是一种“弱势人类中心主义”,否则唐克龙先生也不会将他与苇岸、贾平凹、韩少功等人置于一篇文章中讨论生态文学的问题。其次,既然人类在看待自然时总难以排除“主观的内心”色彩,那么在无法超越视阈局限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否谈论自然?如何谈论自然?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刘亮程的散文对于我们面对这一困境是有启发意义的。
此外,不少论者本着现代文学传统的启蒙立场,批评刘亮程的作品缺乏现实批判的意识与力量。例如,张立国先生在肯定刘亮程之于土地情感的绝对真诚性的基础上指出,刘亮程的散文缺乏批判性的反思,过分美化了乡村生活,而对乡村的贫瘠与落后、人性的丑恶与复杂视而不见;“更何况刘亮程的乡村哲学明显具有反现代性的一面,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12]*类似的批评也见于詹冬华的《新时期中国生态散文的审美精神》,《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这种批评坚持旧式精英的文学观念,把文学与改造社会的任务联结起来,本亦无可厚非。然而,文学的价值与其承担社会责任与否并无必然的内在联系,文学的繁荣有赖于多样化格局的形成,这早已是文学批评的常识,我们无需再费笔墨。这种批评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其强势的现代性立场妨碍了论者对刘亮程散文真正意义的发现。事实上,对现代性的反思不仅早就在西方发达国家蔓延开来,而且也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引发了广泛而持久的讨论。*参阅汪民安等编《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张立国先生所谓的“反现代性”“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等术语在今天的语境中不仅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反面效力,甚至被赋予了诸多正面价值。刘亮程散文中最有价值的地方恰恰就在于他对现代性的反思,张扬了一种与现代文明节奏完全相反的“慢”的哲学。也正是这种反思,使刘亮程对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拥有了迥异于传统乡土散文的认识,为其散文赋予了丰富的生态意义。试想,如果说乡村的贫瘠与落后、人性的丑恶与复杂这些旧有问题依然需要我们继续思考,那么当今全球面临的生态问题是不是也同样应该得到文学的关注呢?当然,这牵涉到文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社会正义与生态正义的关系等复杂问题,已远远超出本文范围。恰可与张立国先生形成对话的是,周立民先生十分精当地指出,刘亮程不仅为乡土文学赋予了新的因素——对家园的满足感,更重要的是,他看重并保存了自然万物的自在状态,将这些事物从启蒙话语中带有象征意义的语境中还原出来,将它们自然、自在的感觉呈现出来。“将事物从附加的意义世界中解放出来,让它们回到最初,就像人洗去征尘又赤裸裸以本真状态回到了自己的家园。这是刘亮程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13]
的确,不论是在东方文学传统还是西方文学传统中,自然万物几乎都没有拥有过自己的自在身份,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抽象的道德符号形式依附于人类的主体抒情和叙事中,是人类文明的工具性存在。作为整个地球生态的参与者、分享者和铸造者,它们活生生的生命与感受一直被排除在人类文明之外,直到当代生态文学的出现。
自然书写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越来越受到重视。著名评论家谢有顺认为:“自20世界下半叶以来,中国作家没有一个人能写好‘风景’。关注生态,回到天空、大地和旷野,很可能是帮助作家重新发现自我的一个途径。”[14]与当代中国从事自然写作的部分作家不同,刘亮程不是直接受惠于西方的生态伦理资源,其思想更多地植根于中国传统哲学和农耕智慧。*参阅周毅《没谁能走到自己的恐惧跟前:刘亮程访谈》,《文艺报》2001年4月7日第10版;“好一个刘亮程”,http://www.china-culture.com.cn/zj/ft/20.htm。刘亮程散文的生态意味是从他对人生、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认识与体验中散发出来的,并没有表现出自觉的生态伦理意识,这正是在中国生态批评家们更看重徐刚、苇岸等人而不是刘亮程的原因。然而,也正是这种非自觉性,使刘亮程的思想在某些方面具有弥补西方生态文学之不足的可能。我们知道,不论是人还是动植物,都是自然的一部分,都应得到文学的适当关注;人除了其自然性外,还拥有文明的属性。传统文学因过分关注人、张扬人而导致了对自然万物的压抑和失语,反过来,如果今天的生态文学走向另一个极端,刻意强调自然、强调人的自然性存在,忽视人作为文明存在的向度,则可能会遭到文明的反抗,进而使生态文学的追求沦为乌托邦的想象。*典型的例子就是,罗尔斯顿因其激进的生态伦理学而被部分学者指责为“生态法西斯主义”。可参阅戴维·贾丁斯《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林官明、杨爱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221页。有关回应亦可参阅王诺《“生态整体主义”辩》,《读书》2004年第2期。刘亮程既强调人对自然的绝对依赖,又不忽视人在自然中的角色独特性;在肯定人与自然密切关联的同时,对人的文明属性及其合理欲求作了充分的考虑。无需什么使命意识,也无需什么鲜明口号,人与自然以彼此依赖又相互独立的姿态徐缓、自然地流淌于他的笔端。
基于这种独特性,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果说西方意义上的生态文学起点是奥尔多·利奥波德,那么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学的起点或许不是徐刚、苇岸等人,而是刘亮程。
参考文献:
[1] 林贤治.九十年代最后一个散文家[M]∥刘亮程. 一个人的村庄.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2] 明江.刘亮程:我的文字充满了新疆的气息[N].文艺报,2012-04-06(5).
[3] “文化如衣服,道德是天性”——刘亮程访谈[EB/OL].豆瓣网:http://site.douban.com/116356/widget/works/2361265/chapter/31625379/, 2014-05-16.
[4] 〔德〕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生态创造论[M]. 隗仁莲,苏贤贵,宋炳延,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2:192.
[5] 〔奥〕康拉德·洛伦茨. 文明人类的八大罪孽[M]. 徐筱春,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70-74.
[6] 周毅. 没谁能走到自己的恐惧跟前:刘亮程访谈[N]. 文艺报,2001-04-07(10).
[7] 关注《动物记》 关爱生命、弘扬人性[[EB/OL].腾讯网: http://gongyi.qq.com/a/20120301/000013.htm, 2012-03-01.
[8] 詹冬华. 新时期中国生态散文的审美精神[J]. 青海社会科学,2013(4).
[9] 〔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 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63-364.
[10] 唐克龙.当代生态文学中的动物叙事与生命意识的兴起[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3).
[11] 〔英〕安德鲁·多布森.绿色政治思想[M].郇庆治,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12] 张立国.乡村哲学的神话——有感于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N].文艺报,2001-05-13(6).
[13] 周立民.刘亮程的村庄[J].当代作家评论,2002(1).
[14] 任晶晶.“文学与生态——凤冈名作家笔会”举行[N].文艺报,2008-04-08(1).
(责任编辑:毕光明)
On the Ec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Liu Liangcheng’s Prose
HUANG Zeng-xi
(SchoolofLiberalArts,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Abstract:The unique cogni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ivilization, nature and time in Liu Liangcheng’s prose and the “slow” philosophy on such a basis correspond much with the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philosophical thinking. Liu’s cognition of contradictoriness a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mirrors the efforts and possibility of restoring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on the one hand and affirms the complexity of nature as well as the limitation in man’s cognition of and integration with nature on the other hand. Root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Liu’s reflection can somewhat be conducive to clarifying some controversy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ecological philosophy and ecological criticism.
Key words: Liu Liangcheng; “slow” philosophy; the rhythm of nature; synchronization; man and n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