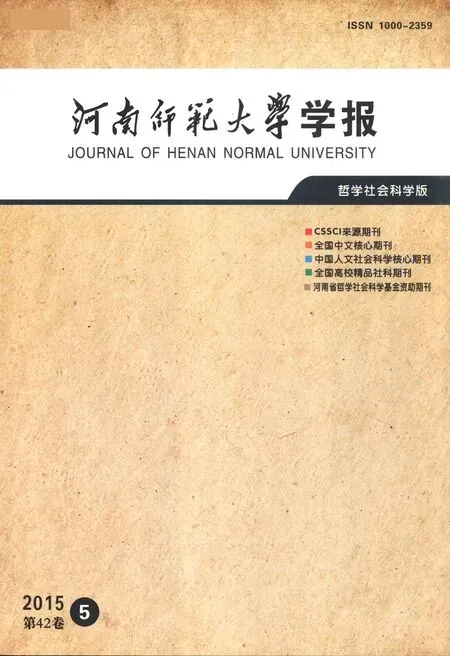论苏曼殊小说《断鸿零雁记》中的水云意象及其生成原因
2015-03-29朱兴和
朱兴和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200240)
《断鸿零雁记》是苏曼殊所作六部小说中最成功的一部,也是近现文学史上的人所熟知的经典作品。苏曼殊去世后不久,姚锡钧在悼诗中说:“生前身后总悠悠,蠹简残编一泪流。凭仗胡君好珍惜,《断鸿零雁》自千秋。”[1]209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断鸿零雁记》是“民初独标一格、最富诗情的小说”[2]。陈平原曾说:“相信不靠风流轶事,曼殊作品也能传世”[3],还认为“《断鸿零雁记》正是郁达夫自传式小说的先驱。”[4]近年来,关于《断鸿零雁记》的专论文章也有不少,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判断:(一)悲情小说、悲剧小说。(二)启蒙主义小说(认为其中包含着反包办婚姻的思想启蒙意义)。(三)才子佳人小说。(四)佛理小说。(五)第一人称限制叙事小说。综合来看,关于《断鸿零雁记》的研究,虽然角度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分析框架基本没有越出杨义和陈平原的论述体系:要么强调小说在思想史上的启蒙意义,要么强调小说在叙事模式上的突破与承前启后的作用。其实,抛开这些既定的分析程式,还可以有其他的解读视角。《断鸿零雁记》中存在大量关于水和云的描写,它们甚至被高度意象化。透析水云意象的功能和意蕴,也许可以加深对《断鸿零雁记》和苏曼殊的理解。
一
《断鸿零雁记》笔墨所到之处,皆有水云之迹。这些水云已非寻常景物,而是在场景设置、情节布局、节奏控制和气氛渲染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对小说的抒情效果产生重要影响的诗学意象。
《断鸿零雁记》开篇就说:“百越有金瓯山者,滨海之南,巍然矗立。每值天朗无云,山麓葱翠间,红瓦鳞鳞,隐约可辨,盖海云古刹在焉。相传宋亡之际,陆秀夫既抱幼帝殉国崖山,有遗老遁迹于斯,祝发为僧,昼夜向天呼号,冀招大行皇帝之灵。故至今日,遥望山岭,云气葱郁,或时闻潮水悲嘶,尤使人欷歔凭吊,不堪回首。”[5]这段文字交待了故事发生的原初场景。这是三郎受戒之所,也是整个故事的起点和终点。接下来的叙事几乎都在由云与水所布设的场景中铺陈开来:三郎在海云寺倚楼远望,但见“天际沙鸥明灭”,“海风逼人于千里之外”,于是,发生下山寻母之冲动,接着,受戒下山,化缘海边,遇到乳母母子,暂得栖身之所,“日与潮儿弄艇投竿于荒江烟雨之中”。不久,他得到雪梅的资助而赴日寻母,在海上翻译拜伦《大海》之诗,在“背山面海”、“流水触石”的板屋与生母相见。生母依阑观海,嘱托亲事,静子在海边主动示爱,两人在海边相互试探,最后在海边诀别,并将爱情信物投诸大海。但凡与海有关的场景描写,同时也涉及大量云气和天空的描写。可见,水云意象对于叙事场景的设置非常重要。
水云意象也在情节布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断鸿零雁记》在结构上形成一个首尾呼应的闭合回路:情僧三郎在受戒之际动了凡心,离开海云寺,下山寻母,在寻母过程中与雪梅、雪鸿和静子发生情爱纠葛,最后挣脱情网,在“弥天幽恨”之中,万念俱寂,“心如木石”,决心回归师父所在的寺庙。青灯古寺是“现代情僧”三郎的起点与归宿。在俗世与方外的对位建构中,水云意象的参与必不可少。譬如,开篇描述的海云古寺处于“云气葱郁”、“潮水悲嘶”、“沙鸥明灭”、“海风逼人”的意境之中。结尾处,三郎在“诸天曛黑”、“万籁深沉”的黑夜(可理解为天空和黑云的闭合)中“颓僵如尸”,渴望“了此残生”。《零雁记》的中间部分,水云意象也发挥着贯串情节的关键作用。最典型的是三郎与静子交换《崖山图》和《花燕图》一节。三郎《崖山图》所画景物是“怒涛激石”、“远海波纹”和“斜身堕寒烟而没”的一只沙鸥。静子觉得“此景沧茫古逸”、“爱之甚挚”。静子《花燕图》所画内容为一位临风观赏莲花和飞燕的妙龄女子。三郎的感受是“飘飘有凌云之慨”,叹为“行云流水之描”。由于两幅画作都带着强烈的身世之感,因此,彼此的叹赏使他们产生深度的精神契合,产生最浓烈的爱慕之情,小说的情节因此而达到高潮。
水云意象还在节奏控制、气氛渲染和情感抒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实,节奏、气氛、情绪是同位同构的。《零雁记》中的水云描写有阳舒阴惨之别。但凡急管繁弦之处,呈现的多是阴云惨恻、海水激石的景象,营造的气氛比较紧张,所抒发的也多是哀愁凄恻的情绪。但凡节奏缓慢之处,呈现的多是天高云淡、海浪悠悠的景象,营造的气氛比较和缓,所抒发的也多是怡乐舒畅的情绪。比如,当三郎为强盗所欺、走投无路、内心悲怆之时,出现的水云描写是“骇浪遽起,四顾昏黑”。当寻亲之旅成行时,三郎在海轮上的所见所感则是“风日晴美……茫茫天海,渺渺余怀”。叙事节奏由紧凑转为和缓,情绪由悲怆转为平静。与生母相见之后,目击所见或是“崦嵫落日,渔父归舟,海光山色,果然清丽。忽闻山后钟声,徐徐与海鸥逐浪而去”。或是“芙蓉峰涌现于金波之上,胸次为之澄澈”。此章的节奏、气氛、情绪,均呈和缓怡乐之态。在静子与三郎的恋爱故事中,水云意象大量出现,造成波谲云诡(情节)、张弛有度(节奏)、阴阳交替(气氛)和哀乐无端(情绪)的艺术效果。而且,随着情节的推进,关于水云的描写,已由外在的景物描摹,转变为景语与心语的紧密融合。比如,母亲提亲之后,三郎心里的波动很大,“仰视天际游丝,缓缓移去”。如果说这还是景语,那么,接下来的一段话,“浴毕,登楼面海,兀坐久之,则又云愁海思,袭余而来”,则已明显地将水云描写情绪化、意象化,转化为不折不扣的心语。至于崖山图中的海波和寒烟,自然更是主人公情绪的意象化。在三郎与静子互评画作之夕,月生西海,水波不兴,夜静风严,充满着浪漫喜悦的情绪和气氛,叙事节奏亦娓婉细致,从容不迫。在静子主动示爱而三郎退避的几节中,水云意象则开始变幻莫测:时而月色溟濛,美人如“横云斜月,殊胜端丽。”时而又“乌云密布”,忽然又“阴风怒号,声振十方,巨浪触石,惨然如破军之声。”当三郎困于情网一筹莫展时,只觉得“心与雪花交飞于茫茫天海间也”。当他决心逃离情网时,便觉得愁绪“万叠如云”。当二人诀别于海滩时,恰逢“海潮初退”,暗示高潮已经沉寂,故事即将落幕。此刻,静子“情波万叠而中沸”,天空亦呈现出阴惨之色。凡斯种种,颇难区分哪些水云意象是景语,哪些是心语,因为景语与心语早已融为一体,共同承担了场景设置、情节布局、节奏控制、气氛渲染和情感抒发等复杂功能。
二
在近代文学谱系中,苏曼殊最为独特的生存体验和存在感受是身体和灵魂的双重飘泊。
苏曼殊留给他人的印象基本上是一位行脚诗僧。近代文学史家钱仲联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和《南社吟坛点将录》中,称其为“天伤星行者武松”,认为他在《祝融峰图》中所绘的“行脚荷担”僧是其自我写照[6]。最早研究他的柳无忌说:“曼殊只像一个飘零的异僧,在人世间留下的仅是些渺茫的鳞爪,模糊的影痕。”[1]41画家陈小蝶认为苏曼殊“喜画衰柳孤僧,有万水千山,行脚打包之意。”陈氏《题曼殊上人遗画》诗云:“行脚无根类转蓬,能空诸相亦英雄。”[1]238与苏曼殊交谊最深的刘季平和陈独秀也有类似的印象。刘季平问候曼殊之诗云:“担经忽作图南计,白马投荒第二人。”将其看做远涉异域取经的僧人(第一人是指唐僧玄奘)。陈独秀怀念苏曼殊之诗亦云:“南国投荒期皓首”(《存殁六绝句》),着墨处也在“投荒”二字。
苏曼殊对飘零诗僧的身分也有很强的自我体认。他曾在另一重要自传文本《潮音跋》中自称:“马背郎当,经钵飘零。”亦曾多次在函札中自称“天涯行脚僧”[5]494或“天涯飘寄之人”[5]566。他的一系列笔名,比如,南国行人、行行、沙鸥、雪蝶、蝶、燕影生、燕子山僧、飞锡、昙鸾,等等,仔细玩味,无不透露出一种飘泊天涯的感受。“雪蝶”和“蝶”折射出飘泊中的疾病感受。“燕”是行踪不定的候鸟。“飞锡”意指手持锡杖到处云游。“昙鸾”则以昙花、鸾凤自喻。鸾凤是飘泊的象征,苏曼殊最喜欢的诗句之一即是龚自珍的“凤泊鸾飘别有愁,三生花草梦苏州。”他曾自言:“鸾飘凤泊,衲本工愁,云胡不感。”(《题百助照片寄包天笑》)此外,他还以“华亭鹤”、“孤飞鹤”、“雁”自喻。当然,最著名的自我譬喻无疑是“断鸿零雁”。自传体小说以《断鸿零雁记》为题,可谓意味深长。鸿雁也是不断迁徙的候鸟,小说中的“三郎”恰似一只孤零零的“鸿雁”。这个譬喻极具代表性。曼殊病逝之后,老友沈钧业在追念亡友的诗中说:“断鸿零雁无消息,谁向西泠访墓田。”[7]也将其视为孤飞的鸿雁。
综上所述,无论是他者的印象还是本人的自我体认,苏曼殊都是一位飘泊天涯的行脚诗僧。行脚诗僧与行云流水之间则存在着内在的关联。行云流水既是其生存空间的形象表述,也是其生存方式的形象譬喻。“行脚僧”亦称“水云僧”,因为游僧行踪不定,一如行云流水。在短暂的34年的生命历程中,苏曼殊的行踪遍及日本、中国东南(主要包括广东、上海、江浙、安徽、湖南和山东)和南洋一带,甚至远至缅甸、斯里兰卡和印度。平生经行最多之地是江南、岭南、日本和南洋(其中,曾到上海37次、日本12次、杭州13次、广东6次、苏州5次、南京3次、南洋3次)。这些地域属于太平洋西海岸一带。可想而知,曼殊在天海之间旅行,目击所存,非云即水。难免就近取材,联类感物,通过水云抒发情思和感受,直至将其意象化,转化为抒发情思的诗学密钥。
三
在身体与灵魂的双重飘泊中,灵魂的飘泊更为根本。身体的“在路上”源于灵魂的飘泊无依,亦即生命根基的飘浮不定,或者说“家”的阙如。苏曼殊的行脚天涯,如果从宏观方面追溯原因,可以说与古典世界的崩解和现代性的来临有关(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苏曼殊能在近代文学中激起的持久的波澜,原因在于他表达出现代人或多或少都普遍存在的飘泊感受,而现代人的飘泊感从根本上说与古典信念的崩解及新的生活方式有关)。如果从微观方面追溯缘由,则主要与苏曼殊特殊的身世相关。
按照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学理论,早期生命体验对人的成长至关重要[8]。苏曼殊之所以成为行脚天涯的情僧,根源在于早年生命史中的心灵创伤,而创伤之关键点则在于他常对友朋所说的身世有“难言之恫”。关于苏曼殊的身世有多种说法:生父生母均为日本人说,生父为中国人生母为日本妇人河合仙说,生母为河合仙使女说,生母为河合仙妹妹河合若说。其中,比较可信的是马以君的生母为河合仙妹妹一说[9]。根据马以君所作的《苏曼殊年谱》,苏曼殊一直将其生母河合若当作自己的姐姐。这意味着他至死都对自己的真实身世缺乏确切的了解。苏曼殊五岁离开河合仙和日本,远赴广东,而广东苏家人际关系复杂,对其造成极大的心灵创伤(主要是庶母的虐待和族人的冷遇)。安全感的缺乏使其神经异常纤敏、情绪复杂多变(这在《零雁记》中“三郎”的身上得到充分的展现)。爱尤其是母爱的缺乏造成了他持续一生的寻根冲动(《零雁记》叙事的原动力在此)。进入青春期后,生命寻根冲动(其实质是寻求来自女性的关爱)又分化出追求情爱的冲动,从而发展出一个以情为本位的现代主体。
早年的灵魂创伤还造成了少年出家的严重后果。出家其实是对寻根冲动的背反:由于对人世温情的绝望,年仅16岁的苏曼殊选择出家为僧,试图以背弃世俗生活和断绝情根的方式来解决心灵的苦痛。可以说,出家是情本体的激烈冲动,一旦出家受戒,便在生命中追加了佛家戒律与佛家智慧的双重规训。情主体在发育和萌动的过程中,开始与佛家规条发生强烈的内在冲突。为调和二者的冲突,苏曼殊发展出“以情求道”的理论。他曾经自言:“今虽出家,以情求道,是以忧耳。”[5]401视男女情爱为证道的一种方式。所以,他与众多女子的恋爱彻底、纯粹、大胆、猛烈,每次都有极深的灵魂介入。他追求的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甚至可与妓女同卧而不动性欲[1]143。可以说,苏曼殊的出家和“以情求道”是借助佛家智慧对生存困境的自我突围。但是,由于尘根未断、情执甚深,也由于对世俗生活(主要是真实的家庭生活)的畏惧,“以情求道”的自我突围并不成功。他曾自言:“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5]416其后果是,灵魂始终处于情与佛、色与空之间的两极震荡之中,换言之,始终处于“在路上”的飘泊状态(这里有很明显的现代性)。事实上,诗文和小说乃是无数次灵魂飘泊与情感震荡的附产品,也是一种自我发抒与自我疗治。
四
水云本是普通的自然物象,经过数千年的文化熏染,逐渐演变为内涵丰沛的文化意象。《易》云:“云形雨施,品物流形。”将水云视为滋养万物的生机之源。此后,在中国文化脉络中,哲人、艺术家、诗人大多喜欢以水云为媒介来表达至深的哲理、情怀或审美意趣。就其自然形态而言,水与云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流动不居,变幻莫测。水云意象因此生成流动的能指,为思想和情感的表达带来极大的自由与便利。在六朝以还的文学史中,水云发展为重要的诗学意象,成为诗人表达自由意志、超越体验、宇宙精神甚至内心神秘体验的重要意象。在唐宋诗词中,水云意象一度成为表达禅悟境界的诗学手段[10]。宋明两代覆亡之后,大批遗民在政治高压之下,曾在诗文、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中,凭借水云意象曲折地表达故国情怀和无国无家的漂泊感受。例如,著名琴曲《潇湘水云》即产生于宋元易代之际,寄托了浓郁的故国之思。从此,水云意象成为抒发历史悲情和飘零感受的经典意象。在文网密集的背景下,沧波烟水成为既能宣泄政治情感、表达流亡感受,同时又比较安全的诗学密码。
晚清时期,宋明易代痛史重新浮出历史水面,成为激烈青年知识人心灵、鼓动民族革命思潮的思想资源。苏曼殊深受影响,由此而对水云意象的古典内涵有了很好的吸纳。《崖山图》在苏曼殊的诗、文、画中的再三出现便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足以说明遗民痛史曾对苏曼殊的精神发育产生过重要影响。当然,苏曼殊与水云意象的关键接榫点不在于其中蕴含的民族意识,而在于其中悲怆飘泊的情味。它所包含的深情、凄怨、自由、飘泊等多种复杂感受,无不与苏曼殊的存在体验一一合拍,因而成为他独特而自觉的美学追求。有意思的是,“天风海涛”的美学表述,本身即与水云相关:天风所吹者,无非云也,海涛所卷者,无非水也。苏曼殊的诗与文,真是在在与水云相关。透过水云意象,苏曼殊的诗文呈现出一个多情、感伤而飘泊的生命。这是他在近现代文学史上的最大特质。
依笔者浅见,《断鸿零雁记》之所以具备哀感顽艳而回味无穷的诗性品质,离不开水云意象的重要作用。在苏曼殊笔下,水云意象既承续着古典诗学传统中的历史文化意蕴,又呈现出敏感心灵在近代境况中的飘零感受。由此一斑,可以窥见现代性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中的早期性状。
[1]苏曼殊.苏曼殊全集:第4册[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2]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57.
[3]陈平原.关于苏曼殊小说[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2).
[4]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79.
[5]苏曼殊文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
[6]钱仲联.当代学者自选文库·钱仲联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677.
[7]毛策.苏曼殊《断鸿零雁记》最初发表时地考[J].中国文学研究,1987(3).
[8]皮亚杰.儿童心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3.
[9]马以君.苏曼殊年谱[J].佛山师专学报,1985(2).
[10]景旭.唐宋诗词中的云水意象浅探[J].宜春学院学报,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