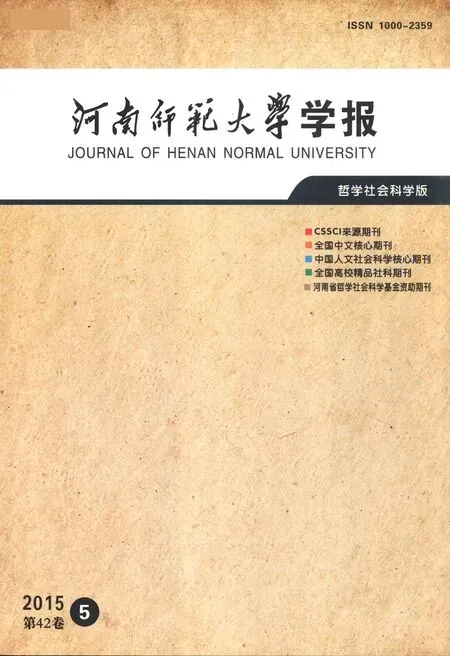王船山“己”、“物”关系视野中的儒家认识论立场——以《尚书引义·尧典一》为中心
2015-03-29陈明
陈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北京100732)
明清之际的学者王船山在其所著《尚书引义》(以下简称《引义》)的首篇《尧典一》中,即通过一系列核心问题之追问,重新检视与确认儒家的思想宗旨。船山从人之存在最为切近的实践问题出发,去追问人应当如何面对世界?人应以什么样的行动方式处事应物?人之行动的依据与原则是什么?又如何通过致知为学的过程获得行动的准则?为学致知如何才能不脱离实践,又真正能够有助于实践?既往儒学的致知工夫在传习中出现了哪些流弊,又应当如何加以克服?船山在这些追问的引导下,围绕己、物关系问题,不仅基于儒家立场对其论辩对象及主张展开批判性分析,并且亦将他所关注之义理问题及基本观点,以精要的方式加以说明。本篇论文即通过对《引义·尧典一》篇的细致解读,探求船山经由辨析“己”、“物”关系视野中各家观点之分歧,进而重新阐明儒家认识论立场的思想努力。
一、圣人与学
《引义·尧典一》中船山之论议乃围绕《尚书·尧典》开始的一段话而展开,即:“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1]34-37船山开篇曰:
圣人之知,智足以周物而非不虑也;圣人之能,才足以从矩而非不学也。是故帝尧之德至矣,而非“钦”则亡以“明”也,非“明”则亡以“文思安安”而“允恭克让”也。呜呼!此则学之大原,而为君子儒者所以致其道矣。[2]237
船山以重新诠释帝尧之德与学为导引,展开全篇之论述。由唐代韩愈在《原道》中提出,并为宋明儒所尤为看重之儒家道统,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这一传承序列中,帝尧被列于首位。船山正是希望通过对于帝尧之德性内涵及其成德之学的阐发,追溯儒家的精神起源,并由此重新确认儒学的核心价值与为学宗旨。
船山指出圣人虽天生所具之“智足以周物”、“才足以从矩”,但并非不需后天之学与虑。以圣人所禀赋之知、能,亦必虑以周物,学以成才。船山点出“知”、“能”二字,语出《周易·系辞上》“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在《周易外传》中,船山特别指出天地间人之可贵,即在于兼具天、地之知、能大用于一身。船山以“知”、“能”指示人初生即所禀赋的知、行能力,同时亦强调人应运用此两类德性能力,通过后天为学力行之工夫以渐成圣德。即使圣人之成德,亦有待于后天之学、思,并非初生完具,不假于学。在船山看来,帝尧之至德,乃其学问工夫所成,而《尧典》“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正是对于帝尧之圣德与其成德之工夫的精要概括。同时,船山认为《尚书·尧典》此句,也包含了儒学最根源性的价值关切与为学宗旨,由此治学用功方为儒者从学之正途。
船山又进而指出:
何以明其然邪?天下之为“文、思、恭、让”而不“明”者有之矣,天下之求“明”而不“钦”者有之矣。不“钦”者非其“明”,不“明”者非其“文、思、恭、让”也。“文”有所以文,“思”有所以思,“恭”有所以恭,“让”有所以让,固有于中而为物之所待,增之而无容,损之而不成,举之而能堪,废之而必悔。凡此者,明于其所以,则安之而允安矣。不明其所以,将以为非物之必待,将以为非己之必胜,将以为惟己之所胜而蔑不安,将以为绝物之待而奚不可。不明者之害有四,而其归一也。[2]237
在此段论述中,船山以简要的方式,揭明其义理观点,也呈现了全篇的整体结构与分析进路。船山指出“钦”、“明”与“文、思、恭、让”,为一彼此相依之整体,涵括了人之为学力行所不可或缺之要件,并以己、物皆得所安为目标。由船山后文之论述可知,在他看来,《尧典》所言“文、思、恭、让”即指人之处事应物的内心活动与外在行为,四者细分又有内外所指之分别,“思”与“恭”侧重于行事之际,内心的认知活动与道德状态,“文”与“让”则偏重在处理事物之行为方式与具体作为,四者内外相合,即指儒家所谓之“礼”。“明”则指如何通过致知穷理的为学工夫,达致对事理之明辨,而于处事之际可依具体时、地以为因应之道。“钦”则指理学存心持敬之工夫。后文中,船山对“明”与“文、思、恭、让”关系之讨论,涉及知行关系之问题,而有关“钦”“明”关系之讨论、“浮明”与“实明”之辨析,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由敬生明”、“以敬持明”的工夫主张,则与其对理学程朱、陆王两家认识论之反省密切相关。
在本段中船山指出:“‘文’有所以文,‘思’有所以思,‘恭’有所以恭,‘让’有所以让”,此乃“固有于中而为物之所待,增之而无容,损之而不成,举之而能堪,废之而必悔”,必“明于其所以”,方能“安之而允安”。在船山看来,人以“文、思、恭、让”处事应物,而其行动之依据与原则,实本自人性所固有之理。因此,必致知以明其所以然,方能处事以得安。船山之论看似相沿程朱“性即理”之故说,但对于性理之内涵,船山实有独特之界定。在船山看来,“性即理”之“理”字,以及《中庸》“率性之谓道”之“道”字,既不同于物性之理,亦非局限于道德原则,而实指人之处事应物之道而言,这从其所谓“固有于中而为物之所待”兼涉己、物以为言,即可见出。而其所谓“举之而能堪,废之而必悔”,则突显了性理所具有的实践性格。船山之论,一方面强调己、物之间相互依存不可割裂,另一方面又将处事应物之道归于人性之所固有,并以此作为致知之对象。同时,船山又提出警告,指出人如果不能尽心知性而“明其所以”,则“将以为非物之必待,将以为非己之必胜,将以为惟己之所胜而蔑不安,将以为绝物之待而奚不可”,陷入四种对于己、物关系的错误理解,由此对人所当为之实践将产生消极之影响。继此,船山基于其所持之儒家立场,对四种有关“己”、“物”关系问题所持之不同立场与主张,分别加以批判与分析。
二、有关“己”、“物”关系的四种立场
船山批评之第一种立场,即所谓“以为非物之必待”[2]237,乃指老庄自然之说。其大体主张“物固自治”,任其自然,不待人为,自得其治;人若以其“文”、“思”、“恭”、“让”而治物,则反将使物“琢”、“滑”、“扰”、“疑”,罹此“四患”徒“乱物也”,故老子有“绝圣弃智”、“不敢为天下先”之说。船山认为“物之自治者固不治”,所谓“不治者之犹治”,实乃自欺之言,即使能“苟简以免一日之祸乱,而祸乱之所自生在是也”[2]238。在船山看来,“物”必待人之治而得安,人亦因其治而得物之利用以免患。船山又特别指出“物自有之,待我先之而已矣”[2]238,物性虽自具其理而能为人所用,但必待人能明察其理、有所作为方能成其利用之道;同时,人之利用万物以成厚生之道,亦不可违于物性自有之理。由此可见,对于人作为实践主体之能动性与物性客观之存在,船山皆予以强调。
接下来,船山所批评的第二、第三种观点,则为建基于两种不同之历史观而抱持之政治实践主张。有关第二种立场,即所谓“以为非己之必胜者”[2]238,乃指刑名法术之论。持论者认为人在历史当中的作为,受制约于历史之时势,儒家理想政治的实现有赖于特殊优异的历史条件;而在历史常态中,由于不利之偶然性因素的存在,儒家的价值原则与政治理想未必能够实现,因此在政治实践中,应当“乘其时,顺其势”,“操之以刑,画之以名,驱之以法,驭之以术,中主具臣守之而可制天下”[2]238。船山认为论者所谓“道不可尽,圣人弗尽;时不可一,圣人弗一”[2]238,片面强调了历史中的偶然因素及外在时势对于人之主体作为的限制,但却放弃了政治实践者自身以其德性能力对历史施加积极影响的责任,也忽略了人以其所信奉之价值与抱持之理想导引历史方向的力量与可能。船山又举例指出“尧有不令之子,舜有不谐之弟”[2]238,圣人虽承受不善之命,但尧禅位于舜,成其让贤之美,舜终感化其弟,以免骨肉相残之祸。与之相较,秦亡于始皇淫昏之子,郑有庄公母弟叔段之叛,正是由于始皇之失教,庄公之养恶,终不能如尧、舜以其德行转不善之命而成其善道。此外,“夏有不辑之观、扈,周有不若之商、奄”[2]238,却因主政者之正确作为而转危为安,而汉成七国之乱、唐有藩镇之叛,则肇祸于“晁错之激”、“卢杞之奸”等人为因素。在船山看来,虽处于相似的历史境况,却因主政者德行之高下,而最终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船山进而强调“夫惟不得于天而后己可用也,惟见诎于时而后道可伸也”[2]238,不利的历史时势,对于承负现实政治责任的儒者而言,正是他们所必须面对的挑战。而通过君子不屈不挠的坚持与努力,化解现实中的政治危机,并将其导向儒家理想政治的方向,既是君子无可推卸的道德责任,也是其内在德性能力的切实展现。由此,船山提出“质立而‘文’必生,物感而‘思’必起;退而自念,则自作其‘恭’;进而交物,则不容不‘让’。内取之身,外取之物,因其自然之成,能以坐消篡弑危亡之祸”[2]238。船山认为君子修己治人,当刻责于己,而非苛责于人。不同于刑名法术之士但求自逸、专务绳人、以责速效的作法,儒者应当切己反躬,深思以求处事应物之道,并以礼乐文章之施为而待其自然之成,并使篡弑危亡之祸渐消于无形之中。
船山所批评之第三种立场,即所谓“惟己之所胜而无不安”[2]239,则与前一种面对历史的态度正好相反。以持论者之见,“圣人之所为,天无与授,地无与制,前古无与诏,天下无与谋”[2]239,乃专己自恃而独断于心,既不受时空条件之限制,亦不必因循历史之经验。因此“可以为而为之,圣人已为矣。可以为而为之,我亦为也。其未为者,彼之未为而非不可为也。非不可为,而我可以为矣”[2]239,其个人亦可全然不顾自身之德才与具体之时势,或以浅表之方式袭取圣人行迹、举措以张皇自大,甚或以为圣人亦无需效法,而可任意而独行。船山又以“蔡京以丰亨豫大为‘文’,曹叡以辨察苛细为‘思’,汉成以穆皇文致其慆淫,燕哙以禅授陆沈其宗社”[2]239为例指出,这些为政者自以为,人之政治实践与作为,仅凭主政者之孤见独行即可达成,既可以不顾具体历史形势与条件的限制,也无需参照历史经验或众人之见。而正是由于他们片面强调个人之主观意志,往往轻忽现实实践之复杂与困难,或自我张大以比肩三代,甚而取六艺之文以饰其非,不过自欺以欺人,终难逃败亡之结局。针对“惟己之所胜而无不安”之说,船山强调“惟己胜者之非可安”[2]239,虽然由于时势之嬗变,主政者非可简单因循先王之成迹,而应发挥其所具之德才因时以制宜,但政治实践仍有必当遵循之准则。在船山看来,“天无与授”,居位主政必有益于民生;“地无与制”,制器利用必当于物则;“前古无与诏”,考之必有相通之精义;“天下无与谋”,但成效必能服天下之人心。主政者当奉此为绳矩,通古察今以明其故,由此方能因时以为对待,决不可任意横行以图速效之成。
船山所批评之第四种观点,即所谓“绝物之待而无不可”[2]239,则为船山所理解之佛教立场。在船山看来,持此立场者大体主张“物非待我也,我见为待而物遂待也”[2]239,无论认为物之待我或我为物待,皆因执于物、我所起之妄见,而必使物、我交受其碍;若免此病,则需“内绝待于己,外绝待于物”,由此必致“废人伦,坏物理,握顽虚,蹈死趣”[2]239。针对于此,船山则就“物我相待而不可绝”之理,加以详细论述。船山指出人之“一眠一食,而皆与物俱;一动一言,而必依物起”[2]239-240,正是从人类生存与社会存在之经验的角度,强调己、物之间,本相因共存而不可割裂,人利用万物以为资生之具,物亦由人之利用得尽其效而免为祸患。在船山看来,物我相待而成此天下,若绝待于己、物,则物、我必交受其戕贼,而害将极于天下。
相对于以上四种立场,船山认为圣人之治必因天下之所待而有所授,“朴者授之以‘文’,率者授之以‘思’,玩者授之以‘恭’,亢者授之以‘让’。泰然各得其安而无所困”[2]240。若结合《引义》其他篇章之论,可知船山此处所谓圣人之所授,正指礼而言,其根源则本自人性固有之理。由此,船山强调人之处物待人“真有其可,而非其无不可”,“无不可者之必不可矣”[2]240,而人欲于行事之际得其定可,则必有待于为学之功以求其明。船山曰:
圣人之所以“文、思、恭、让”而“安安”者,惟其“明”也。“明”则知有,知有则不乱,不乱则日生,日生则应无穷。故曰:“日新之谓盛德,富有之谓大业”,此之谓也。“盛德”立,“大业”起,“被四表”,“格上下”,岂非是哉![2]240
船山认为圣人惟实以求明,方能得“文、思、恭、让”之真。而以船山之见,上文所述四种立场,无论批评“文、思、恭、让”以为不必有、不足为,抑或对“文、思、恭、让”有所误解与误用,皆因不能进学以求明所致。船山曰“明则知有”,强调人不仅应肯定天地万物之为实有而非虚幻,更需明确处事应物之道本为人性之所固有,故当运用其所禀赋知、能之才,即物穷理,明善以尽性。在船山看来,惟能如此,方可存心处事于不乱,而使其德日新,所应无穷,以达至《周易·系辞上》所言“日新之谓盛德,富有之谓大业”之境界。此外,对于上述四种有别于儒家之思想立场中,一些针对儒家后学传习中所见流弊而作之批评,船山实认真对待,并试图努力加以克服。船山于下文中,分辨“实明”与“浮明”之别,强调“钦”、“明”合一,其中所论大部分即针对儒家自身之问题,并求之以解决之道。
三、“实明”与“浮明”
正如上文所述,船山以“明”为达致“文、思、恭、让”的必要条件,正意在将人之处事应物之道,作为儒者致知穷理的对象与内容而加以明确。但船山接下来,则指出“明”有“实明”与“浮明”之别,必需加以分辨。船山曰:
虽然,由“文、思、恭、让”而言之,“明”者其所自生也。若夫“明”而或非其“明”,非其“明”而不足以生,尤不可不辨也。“明”、“诚”,相资者也,而或至于相离。非“诚”之离“明”,而“明”之离“诚”也。“诚”者,心之独用也;“明”者,心依耳目之灵而生者也。夫抑奚必废闻见而孤恃其心乎?而要必慎于所从。立心以为体,而耳目从心,则闻见之知皆诚理之著矣。心不为之君,而下从乎耳目,则天下苟有其象,古今苟有其言,理不相当,道不自信,而亦捷给以知见之利。故人之欲“诚”者不能即“诚”,而欲“明”者则辄报之以“明”也。报以其实而“实明”生,报之以浮而“浮明”生。浮以求“明”而报以实者,未之有也。[2]240
船山论“文、思、恭、让”由“明”而生,其所谓之“明”,乃特指与人之实践相关之智性德能,而非泛指一切知觉见闻。船山又进而指出“明”必与“诚”相资为用,方能有实。船山所言之“诚”、“明”,本出自《中庸》“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朱子《中庸章句》对此章之诠义,乃将“诚”与“明”分别界定为“性”与“知”,进而又将“自诚明”、“诚则明矣”与“自明诚”、“明则诚矣”,分属“圣人之德”与“贤人之学”[3]49。而船山有关“诚”、“明”内涵之界定,及对“诚”、“明”关系之理解,并非依照《中庸》原文之语脉,及朱子相关之解说,而是依其所讨论之问题而随文做出独特之诠义。船山曰“‘诚’,心之独用也;‘明’者,心依耳目之灵而生者也”,乃基于其对程朱、陆王致知工夫之反省,而从认识论角度,诠释心与耳目之关系,此亦为船山日后持续讨论并不断予以深化之议题。船山虽分别以“诚”为心官独用之思,以“明”为心依耳目之官所生之知觉,但并未将心与耳目两相对立,而是依心与耳目合用中,“心”所居主从地位之不同而区分两种情况。其一,乃“立心以为体而使耳目从心”。从“知”而论,由此可使“耳目之见闻”经与“心官之思”合用而深化为诚理;若从“行”而论,则于临事之几,心官之思据耳目之所察以为判断与抉择,从而可使心德所具之诚理,显见于外以因时致用。其二,乃“心不为之君,而下从乎耳目”,则将使心随耳目与外物之相感而浮动,不免因知见之利起意生心而为妄行。此外,人之为学若只贪鹜见闻广博,不能致思穷理以求有所心得,则当临事之时,亦不可能依具体时势境况,用心以求处事之宜,不过以其平日见闻所得之浅知敷衍应事。如此,在船山看来,即使行事者之动机并非起于贪欲逐利之念,但若察其隐微,实亦贪求见闻之知,捷取易获之利,以免于穷思致理、苦心深求之劳。论中,船山强调不可“废闻见而孤恃其心”,则明显针对陆王之学而发。但其曰“天下苟有其象,古今苟有其言,理不相当,道不自信”,则主要针对程朱后学之流弊,而加以隐微之批评。船山认为,人若不能于见闻之所得深求会通其理,仅据耳目所察、经典所载或前贤之迹以为行,则必不能使理势相当,因时致道。此上依心之为用不同所作之分殊,前者船山赞之曰“实明”,后者则贬之为“浮明”。船山曰:
在船山看来,前文所论列四种不同于儒家之立场,其各自之所主张皆本于“浮明”。而他们对于儒家“文、思、恭、让”之批评,其中切中儒家自身问题之合理部分,亦是由于儒门后进有失为学宗旨,不能实以求明,而依“浮明”以行所致。船山文中所举,崇尚虚礼浮文、凭空测度幽隐、失大本而苛细行、揣物情以为趋避,皆于“文、思、恭、让”似近而实非,亦同出于“浮明”。在本段后半部分,船山将批评之重点,放在对儒学自身传承脉络之反省。在船山看来,其所列举之扬雄、关朗、王弼、何晏、韩愈、苏轼,皆不能于儒学精义有所深得,或援佛、老之说以入儒,或私测象数以乱《易》,直至陆王末学以妙悟自矜而流于猖狂放肆,皆可归于“浮明”之害。
四、“钦”与“明”
针对其所批评之“浮明”,船山经由诠释《尚书·尧典》“钦明”之义,提出“由敬生明”,“以敬持明”的为学主张。而船山之论,不仅针对阳明“良知”之说,亦同时针对程朱存心主敬的工夫论。船山曰:
夫圣人之“明”,则以“钦”为之本也。“钦”之所存而“明”生,“诚则明”也;“明”之所照而必“钦”,“明则诚”也。“诚”者实也:实有天命而不敢不畏,实有民彝而不敢不祗;无恶者实有其善,不敢不存也;至善者,不见有恶不敢不慎也。收视听,正肢体,谨言语,慎动作,整齐寅畏,而皆有天则存焉。则理随事著,而“明”无以加,“文、思、恭、让”,无有不“安”也。[2]241
《尧典》“钦明”之“钦”,可以“敬”字为训。船山指出圣人之“明”,乃以“敬”为本,又以《中庸》“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之说,诠释“敬”与“明”之关系。船山所谓“‘钦’之所存而‘明’生”,乃“由敬生明”,近于孟子“深造自得”之义,或存理日久、融贯会通而得所新知,或随事体察以得因应之方,皆必以诚敬存心而致用。而船山必引“诚则明矣”以为诠义,则意在针对程朱虚静涵养以为持敬之说,强调敬之所存必与“诚理”相依,方能有所自得而应事无碍。船山所谓“‘明’之所照而必‘钦’”,乃言“以敬持明”。船山必引“明则诚矣”以为诠义,一方面针对阳明“良知”之说,强调君子致知,不可离于事物以求其明;一方面则针对朱门后学徒尚见闻之知,强调君子为学,必由见闻所得而深求其理,并需随时会通以求一贯之义,如此方能因应事物,致以实用。在船山看来,无论阳明后学从尚之虚悟,抑或朱门后学偏据之浅知,皆在其上文所讥“浮明”之列,故引“明则诚矣”之说,强调明不离诚、明必达诚之意。接下来,船山即专释“诚”之意涵,实则以诚摄敬,故不复再言“敬”字。船山曰“诚者,实也”,一方面相对其所谓异学之“虚”而言“实”,以突显实有之意;一方面则以“为‘道心’所充扩之‘实理’”界定“诚”之意涵。但船山所言“实理”,不同于朱子对性与理所作“实体化”之理解[4],故其有“性日生日成”之论,亦有“因势见理”,“理随事著”之说。在船山看来,“实有天命而不敢不畏”,不仅指人初生所禀受之天命,有生之后,天亦日有所命,故人必以戒惧敬畏之心,随时贞性以立命;“实有民彝而不敢不祗”,则强调饮食男女等民生日用之事,皆内在于伦理生活当中而有其常则,君子必敬察其理以制作礼度节文而为百姓所依循;“无恶者,实有其善,不敢不存也”,则言君子存养之功,非但无私情利欲之恶,更需实有为善之理,以为心之所存;“至善者,不见有恶,不敢不慎也”,则言省察之事,强调君子必能于行事之际,因应每一特殊境况,而将其为善之念,落实为具体之善行,方能显见其心实为至善而无恶;“收视听,正肢体,谨言语,慎动作,整齐寅畏,而皆有天则存焉”,则综括而言君子于动静语默之中,无时无刻不谨慎戒惧,必使其身心一致而皆与天则相依。船山强调必使“理随事著”,方能随事得安而为明之最高境界,正意在指出由于理势相因,理随势变,故处事之道难以尽择于先,即使学成德立,亦需即事通明,慎择以为因应之方。在船山看来,无论无事时之存主,抑或临事时之抉择,皆有赖于恒存“主敬之心”,以使“诚”、“明”相合而不离。
但有关存心主敬工夫之理解,船山则对程朱之主张予以批评。船山曰:
尹和靖曰,“其心收敛,不容一物”,非我所敢知矣。[2]241
尹和靖,名焞,乃二程门下之弟子,此处所引为朱子约括尹焞有关持敬工夫之主张。尹氏曾于伊川门下领受“主一持敬”之教,后根据其自身多年践行之体会,认为“只收敛身心,便是主一”,并指出“其心收敛,更着不得毫发事。非主一而何”。后来朱子即将尹氏之言,约括为“其心收敛,不容一物”,并作为尹氏持敬工夫之要旨。而对于尹氏主张,朱子亦加以肯定,曾将其与程子“主一无适”、“整齐严肃”,谢良佐“常惺惺法”等论敬之说同列,并赞叹道“此皆切至之言,深得圣经之旨”,“观是数说足以见其用力之方矣”[5]506。朱子对于程子主敬工夫之提倡,主要在其“中和”新悟之后。朱子对于《中庸》所谓“未发”、“已发”之问题,经过长久反复的体会与思考,最终得出结论。朱子认为人心尚未与外物相接之际,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即为《中庸》所言“未发”之境界。当此之时,保持知觉清明而不昏昧便是未发涵养之功,朱子以程门主敬工夫当之,并以“提撕警策”,“中有主宰”加以说明。
The crank slider mechanism in this arrangement has another essential constraint to ensure crank′s the existence condition,which is the guide groove should be symmetrically positioned on both sides of the crank rotation center l2=l1+x3, as shown in Figure 6.
船山针对程朱之说,指出《尧典》所谓之“钦”,非“非徒敬之谓也,实有所奉至重而不敢亵越之谓也”。船山认为讨论儒家持敬之功,需兼言“能敬”与“所敬”,不可离于“所敬之实”而徒言“能敬之心”。至于持敬之心中“所奉至重而不敢亵越”者,船山则有详细之阐述。他说:
“钦”之为言,非徒敬之谓也,实有所奉至重而不敢亵越之谓也。今曰“不容”,“不容”者何物乎?天之风霆雨露亦物也,地之山陵原隰亦物也,则其为阴阳、为柔刚者皆物也。物之飞潜动植亦物也,民之厚生利用亦物也,则其为得失、为善恶者皆物也。凡民之父子兄弟亦物也,往圣之嘉言懿行亦物也,则其为仁义礼乐者皆物也。若是者,帝尧方日乾夕惕以祗承之,念兹在兹而不释于心,然后所“钦”者条理无违,而大明终始,道以显,德行以神。曾是之不容,则岂非浮屠之“实相真如,一切皆空”,而“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亦其所不恤矣。[2]241-242
船山指出君子持敬之功,绝非“不容一物”,反实有其物而常存于心。船山于论中举列圣人心中常存之物,实借此以言君子致知穷理之范围。分析船山所列之物,实可分为两类,其一为自然之物,包括时令气候、地理风土、以及飞禽动植,此皆与百姓利用厚生之事密切相关,其中自有得失、善恶之理而为君子所当用心研求;其二则同社会伦理与政治相关,或载于经典而为“往圣之嘉言懿行”,或见诸实事而为当代之典章风俗,本乎仁义之性而见诸礼乐之道,皆为君子所当致思探究。在船山看来,此上所列之物,帝尧“终日乾乾,夕惕若厉”皆以敬承之,念兹在兹而无所懈怠,必使其心“条理无违,大明终始”以得一贯之道,如此见诸事行,方能随时尽道,德行以神。
相较于此,程朱主张存心虚明以为持敬之功,以船山之见则不免同于佛教“实相真如,一切皆空”之说。其实,探究程朱立说之因,正有见于人之本性为气质所限,不免感物动心而有私欲之蔽,故主张常于外物未接、私欲未起之际涵养虚明之心,以使感物应事之时,依然能够保持心境清明而不为私欲所汩。但船山复又针对于此,自设问答曰:
无已,其以声色臭味,增长人欲者为物乎?而又岂可屏绝而一无所容乎?食色者,礼之所丽也;利者,民之依也。辨之于毫厘而使当其则者,德之凝也,治之实也。自天生之而皆“诚”,自人成之而不敢不“明”。[2]242
船山反对将天理与人欲截然对立,强调“礼虽纯为天理之节文,而必寓于人欲以见”[6]911,“圣贤吃紧在……人欲中择天理,天理中辨人欲”[6]1025。在船山看来,食色、货利,实乃礼之所丽而为民之所依,故君子当致心其中,慎思明辨以求处物之道,由此凝德于心,制以威仪,以使百姓日用皆有所循,由此方能布政兴治而得诸实效。因此,船山强调万物生于天地,真实而无虚,故“自天生之而皆诚”;人之处事应物,诚有其道,亦真实无妄,但需为政者运用其所禀赋之才,知以明理,行以成治,故“自人成之而不敢不明”。
由此,船山综括全文之论,曰:
故以知帝尧以上圣之聪明,而日取百物之情理,如奉严师,如事天祖,以文其“文”,思其“思”,恭其“恭”,让其“让”,成“盛德”,建“大业”焉。心无非物也,物无非心也。故其圣也,如天之无不覆帱,而“俊德”、“九族”、百姓”、“黎民”、“草木鸟兽”,咸受化焉。圣人之学,圣人之虑,归于一“钦”,而“钦”之为实,备万物于一己而已矣。其可诬哉!其可诬哉![2]242
船山指出帝尧虽禀赋上圣之聪明,仍需日取百物之情理而研寻不怠,方能成盛德而建大业。在船山看来,《尚书·尧典》开篇所述帝尧成德之方,正可“归于一‘钦’”,而“‘钦’之为实”,不过“备万物于一己而已”。船山最终又将全篇落脚于心物关系之主张,即“心无非物也,物无非心”。以船山之见,惟有圣人成德之心,方能达至其所谓“心物合一”、“备万物于一己”之境界。至于儒家认识论中有关治学成德之方法,船山在对程朱、陆王之教法,慎加别择取舍的基础上,实有其独特之主张,诸多卓见,除本篇所讨论之《尧典一》外,亦见于《引义》其他各篇之中,对此笔者将另作专文予以详细之讨论。
[1]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王夫之.船山全书:第2卷[M].长沙:岳麓书社,2011.
[3]朱熹.中庸章句[G]//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4]陈来.元明理学的“去实体化”转向及其理论后果——重回“哲学史”诠释的一个例子[J].中国文化研究,2003(2).
[5]朱熹.大学或问:上[G]//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6]王夫之.船山全书:第6卷[M].长沙:岳麓书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