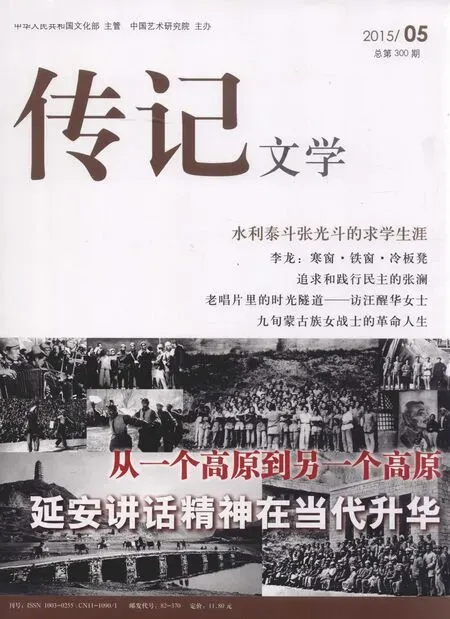正 见
2015-03-29陈玉圃
文 陈玉圃
正 见
文 陈玉圃

《双鹦图》局部 陈玉圃 作

《杜荀鹤诗意图》 陈玉圃 作
什么是正见?简单地说就是正确的知见,或者说是正确的认识。我们从事一件工作,如果没有正知见,就会变得盲目和愚痴。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在西学东渐的大气候下,传统中国文化和动荡不安的中国一起接受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强烈冲击。随着人们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崇拜心理,西方绘画及其审美观念便顺理成章地入主了中国画坛。在这种背景下,以西方绘画审美的视角看我们的传统绘画及其审美,将其判定为腐朽和落后而必须进行彻底改造以适应新形式。于是水墨浅淡渐变为色彩绚烂,清静自然渐变为热闹刺激,简逸古朴渐变为精工制作,乃至把西方素描、色彩教育作为了中国绘画的基础教学。这一釜底抽薪的举措几乎挖尽了中国画赖以生存的土壤。在艺术创新、中西合璧的旗帜下,水墨和宣纸成了中国画仅存的特征 (当然也有提倡革宣纸、水墨命的艺术家,干脆用油画布和色彩画所谓的中国画)。齐白石、黄宾虹之后,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画家已不多见,大多数中青年画家接受的是西方画教育,因而失去了对传统中国画的正知见。所以,如果要研究或者学习中国画,首先应该确立正确的审美观念。
经常有人这样发问:“中国画为什么崇尚水墨浅淡,造型又不严谨,它究竟好在哪里?”
其实绘画是一种文化现象。东西方文化差异导致了东西方绘画审美的种种差异,要树立中国画的正知见,还是应该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比较,以溯本探源,庶几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比方说,中国画重山水体裁,而西洋画重人物体裁;中国画尚浅淡,西洋画尚绚烂;西洋画人物内容多,为女人或裸体女人,甚至包括性体裁,而中国画人物多表现仙佛、高士、帝王将相,也画仕女,但从不画裸体女人。为什么?其实,东西方绘画在形式、内容上的差异可以从其文化特征中找到答案。
概括地说,西方文化是一种以工业文明为主流的文化。这种文化以极大地满足人的物质欲望为动力,以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理论为信条,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人类社会生存竞争的潜能,取得了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空前的经济繁荣。
西方绘画乃是西方主流文化衍生的艺术现象,是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在绘画领域的表现。所以,西方绘画审美之张扬个性,宣扬物欲,重视色彩,崇尚科学,鼓励创造,炫耀新奇,从内容到形式莫不与其科技文明的理念丝丝入扣。
中国画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艺术现象。中国文化是儒释道三派合流为主的一种文化。其价值观念恰恰与西方相反,主张淡化或节制物欲,以净化灵魂使精神升华;主张和谐,崇尚理想,以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的中庸之道为信条,最大限度地消解物欲膨胀给社会和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的破坏危机,最大限度地维持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因而能极大程度地消解由物欲竞争、肆意掠夺给人类乃至自然界带来的灾难,以延缓人类玩火自焚最终走向灭绝的速度。中国画正是这种传统文化价值观在艺术上的显现。所以,中国画尚简淡、平和,主张平中之奇,斥霸悍刺激为俗气;主张以少少许胜多多许,鄙薄精工制作为匠气。
《菜根谭》认为:“浓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异非至人,至人只是常。”一个“真”,一个“常”,说出了“平常心就是道”的人生,乃至艺术审美的真谛。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老子·第八章》)“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四十二章》)可知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是崇尚无为、礼让,甚至是示弱,这是中国传统绘画所以表现浅淡、平和、澄静格致的根本所在。时下中国画追求的所谓“张力”以图吸引视线的思想,恰恰是与传统中国文化价值观背道而驰。所以,从文化的角度去审视时下的这种主张,乃是商业文化在绘画上的反映,近似所谓的“广告效应”。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画是非功利性的,怎么可以把广告效应当作艺术审美的准则呢?这种在理论上本来就是荒唐可笑的说法,而竟会在当今画坛变得习以为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岂非咄咄怪事?如果我们具备了正知见,就不会为这种“诱人的时尚”所蒙蔽。
当然,中国画在艺术上也主张个性,如石涛所说:“我之为我,自有我在。”(《石涛画语录·第三章》)但这里说的“我”却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物欲张扬。释家认为“众生皆具如来根性”,道家认为“至人无为,圣人无作”,可知中国绘画主张的个性乃是“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的天人合一的大我思想的体现,是对宇宙大道认知的真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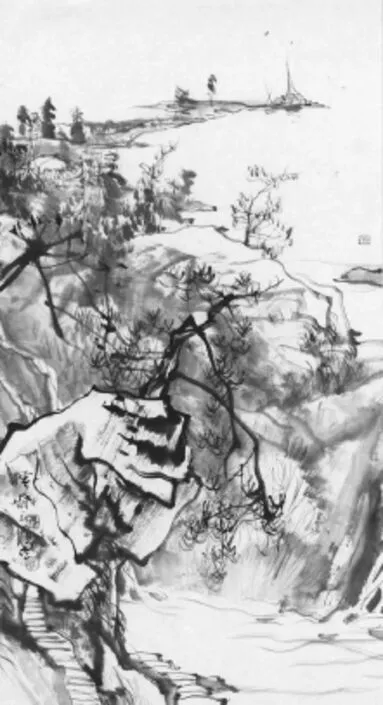
《溪山清幽》 陈玉圃 作

《降龙尊者造像》 陈玉圃 作
比如中国画“卓然不贵五彩”的色彩观。应该说中国人并不是色盲,也会看到五彩缤纷的客观世界,也会发现事物在光作用下的种种色彩之微妙变化。但中国画却不去追求色相的丰富变化,而崇尚“水墨简淡”,顶多也就是随类赋彩,仅作为补墨之不足罢了。这是因为传绕文化往往不是简单直观,而是用第三只眼睛去审视客观世界的真实相(真相无相,无不相)。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欲令人心发狂。”《全刚经》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这些告诉我们色相只是事物的表相,表相如梦如幻,瞬息万变,是靠不住的。所以不可以惑于表相而失去对事物的正知见。如果迷恋于表相(五色五音),就像瞎了眼睛,也就“不能见如来(即实相)”了。
中国画艺术形式的水墨简淡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唐朝的大画家王维最初是从李思训学金碧山水的,而后突然变法而改作水墨浅淡的画风,应该是王维从禅文化里接受“色空”观念的缘故。现代画坛多有以水彩、水粉技法改造山水画,变水墨浅淡为色彩绚烂的现象;亦多有以对境写生改造中国山水画,变意象为直观、焦点、透视,因而直观、通俗、绚艳大行其道。如果我们具备了传统艺术审美的正知见,当不会为其时尚所吸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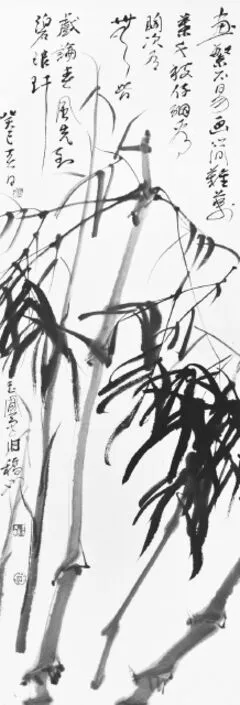
《画繁不易画简难》 陈玉圃 作
另外,时人尚奇,主张创新,以扭曲变形为能事,自诩为高雅艺术,不同凡俗,而一旦成名,天下仿效,谬种流传,殊不知夸逾其度,奇变为怪。曰新曰旧,皆属表相。《文心雕龙》认为:“今人之所谓奇者,或违其常形,或悖其常理,则曰:‘我能为人之所不敢为。’此特狂怪之耳,乌可谓之奇哉?”今人扭曲变形,做作卖弄,与烟花柳巷搔首弄姿何异?
苏轼论画说:“常形之失,止于所失,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这个常理就是道,也就是所谓象外之趣,岂可悖之哉。所以一个忘,一个变,似是而非,鱼目混珠,尤其需要正见法眼。不少人认为创新是艺术的灵魂。清代画家石涛是主张创新的,他说似乎:“古之须眉,不能生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我之腹肠。”“我之为我,自有我在。”众所周知,石涛是一位禅宗和尚,一定是精通禅门佛典的,而禅门重要经典《金刚经》明白表示:“凡一切相皆是虚妄。”即便是实相亦不可执,何况是新旧之类的梦幻表相?石涛无论如何也不会愚蠢到如此程度,其实石涛的本意是反对泥古,而反对泥古并不意味着创新。有清一代画家,以董其昌、“四王”为代表的主流派山水画,主张复古,要“和古人一个鼻孔出气”。而复古和创新同样都是在表相上作文章,实质上远离了艺术的真诚。
近年国人开始关注传统文化,也引起了绘画界对中国传统山水画的重视,大有以临摹仿效为能事者,似乎复古又变成了一种时尚。这对于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反传统浪潮之后,人们重新关注和认知传统绘画以延续传统绘画命脉的意义上说是很有必要的。但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清醒,传统绘画的命脉是文化,是一种文化精神,是对宇宙人生之道的默契与神会,而其外在形式是可以变化和不断完善的,切莫胶柱鼓瑟,矫枉过正。
由此可知正知见的重要性,那么,应该怎样去评判一种文化和艺术的价值观念是否属于正确的知见呢?当然,我们会把“真、善、美”作为正知见的准则。但这里讲的“真”,却不是物欲驱使的“真”,而是摒弃一切分别和对待的至真。这里说的“善”,也不是狭义局限的所谓的“善”,而是妙合至真,视众生与我同体的至善。这里说的“美”,也不是指虚幻表相之追求,而是与至真至善暗合道妙的不言之美——庄子所谓的天地之大美。这是从实际理念而言,如从具体事项而言,“真、善、美”的综合表现,应该是和谐天地万物与众生的根本利益。一切文化、艺术的价值观念的正确与否,都应以是否和谐众生根本利益这个支点来审视。凡符合这一准则的就一定是正知见,是至真至善至美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根本利益,不是指短视的眼前利益,从长远看,短期利益会造成败家损命的伤害。比方说,工业革命从近期利益上看可以说为人类带来了物质和经济的繁荣,但从根本利益上看,却会引发利益竞逐、民族矛盾、战争危机,乃至破坏自然生态平衡,直到毁灭人类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评论西方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时说:“从全球的视角看,我们的文明是一种疯狂的文明,是一种极具剥削性的文明。西方文明对地球一点好处也没有,西方文明应该灭亡。我是说作为个体的人,我们不应该灭亡,但我们现行的模式应该灭亡,需要出现一种新型文化。”他主张一种“以让其他众生也能生活的方式来生活”的全球伦理文化。
的确,西方工业文明的无限张扬物欲的价值观念给人类生存带来诸多危机,我们已经意识到,大气与饮用水的严重污染、恐怖主义、原子威胁等,足以在不远的将来把人类推向最终灭绝。西方主流文明价值观所衍生的西方绘画艺术,也在以五花八门的怪招不断派生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所谓的艺术派别,演示着躁动不安和物欲竞逐的理念。
反观我们的儒家文化,乃至道释文化的价值观念,恰恰也是西方智者极力追寻的与天地众生乃至万物和谐一体的全球伦理文化。以文人画为主流的传统中国绘画的审美观念,也在以单纯的水墨浅淡的艺术形式,向人们演示着宁静、和谐与安详。可以说,我们的儒道释三派合流的传统文化是从利益众生的角度流出的优秀文化。由此而派生出的中国传统绘画则是愉悦众生、澡雪精神、净化灵魂的优秀艺术,是献给这个疯狂星球、热闹众生的一剂凉药。
我们选择这种文化和艺术,继承之,发扬之,实在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情结,乃是从众生根本利益这个支点,经过认真审视和比较而选择的正知见。一旦坚信不疑,面对现在或者将来诸多时尚或者物欲的诱惑时,我们还会动摇吗?
责任编辑/斯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