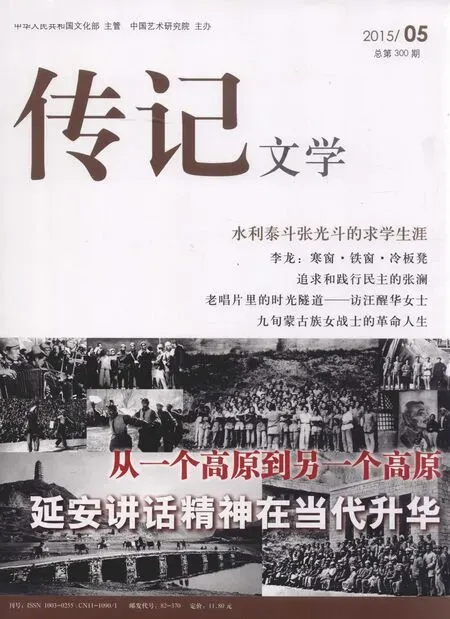老唱片里的时光隧道
——访汪醒华女士
2015-03-29孔培培
文 孔培培
老唱片里的时光隧道——访汪醒华女士
文 孔培培

由于工作的原因,这些年我开始与老唱片打起了交道。交道不打则已,开了头就发现自己掉入了一个“无底洞”。一张张薄薄的黑色唱片上萦绕了太多的学术信息,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声音学……件件都不是轻松的学问,纠结牵绊于一体,我不得不调整心态,督促自己做好打学术持久战的准备。近水楼台,为了弄清楚我的工作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馆藏老唱片资料室建设中的那些旧人往事,我决定对大半生投身唱片资料室建设的汪醒华老师进行一次采访。
汪醒华,1934年出生,退休前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音响资料室主任,著名戏剧理论家龚和德先生的夫人。经过龚老师的热情搭线,在一番简单的电话沟通后,汪醒华老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采访要求。
一个寒冬的下午,我来到她位于北京西坝河的家中。砖红的房子还是20世纪文化部分配的高级专家楼,与四周林立的高档楼盘错落在一起,显出几分陈旧,但是闹中取静,别有一番感受。汪老师与龚老师都曾在上海生活过较长时间,因此家中的布置虽不算奢华,但处处流露着刻在上海人骨子里的那种情调。龚老师客气地为我冲了一杯咖啡,浓烈的咖啡香气顿时充满了不大的房间。汪老师从卧室走到我对面坐定。她满头银发,思维清晰,语速不紧不慢,夹杂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让我顿时感到一种来自心底的舒服与放松。
1955年4月底,正是北京柳絮飘飞的季节。地安门后门桥,中国艺术研究院前身中国戏曲研究院的研究室与资料室就坐落在这里。年逾耄耋的汪老师对60年前那个春天的上午记忆犹新。21岁的她坐着解放军的卡车只身从汉中赶到西安,又辗转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北京投奔未婚夫龚和德。一路跟随她的只有一个随身的箱子和一个铺盖卷。从北京站出来,汪醒华四处张望,让她失望的是,未婚夫并没有前来接站,一个紧急的工作任务绊住了他们的约定。人生地不熟的汪醒华只好坐上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在她好奇又不安的眼神里,车子飞快地穿过北京的大小胡同,径直将她送到了中国戏曲研究院。

1959年,汪醒华在中国戏曲研究院门口留念

唱片组的工作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收购当时新出版的京剧与地方戏唱片以及市面上的老唱片;一是对新上演的重点剧目演出进行现场录制。汪醒华回忆:购买唱片在当时是有几个固定的渠道,有外文书店门市部,有中国唱片门市部,这是两个最主要的采购地点。每当有新唱片出版,或者有人处理掉一批老唱片,那里的工作人员就会第一时间给唱片组打电话。那时的旧唱片都是京城老戏迷和有钱人家购买了新唱片后处理掉不要的,门市部隔一两个月会集中代售。
由于资料库唱片储备实在薄弱,当时唱片组对可以获得的唱片几乎“饥不择食”,只要有唱片面世,便不加选择地悉数买下。当然,唱片组之所以能够如此“大手笔”地采购,背后得到了时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张庚、戏曲研究室主任郭汉城、党支部书记马绩(后改名马远)等几位领导的鼎力支持。在当时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中国戏曲研究院花费在老唱片购买上的经济投入相当巨大。此外,音乐研究室主任何为,研究人员张宇慈、吴春礼也对唱片库的建设起到了指导与帮助作用。唱片组的工作人员心里十分清楚,他们所从事的资料建设是为科研工作服务的,因此他们同音乐研究室两个部门之间联系十分密切。唱片组若是得到了什么珍贵唱片资料,会马上通知音乐研究室的科研人员前来鉴别使用;相反,科研人员在业务上有什么需要也会马上通知唱片组有目标地去收集。彼此信任、毫无保留,完全为了工作的需要,这就是那个年代宝贵的人格精神。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戏曲研究院与中国唱片社联合署名,在《光明日报》连续一个月刊登广告,面向社会大范围收集老唱片、名唱片,方式为现金购买和唱片交换两种。酬金由唱片社支付,唱片的选择、定价以及交换方式则由中国戏曲研究院制定。这一举动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响应。一时间老唱片从全国各地被收集至北京。与此同时,一批资深的唱片收藏家也出现在唱片组面前。其中,南开大学的华粹深和中国政法大学的吴恩裕两位教授在唱片收藏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特别是对老唱片很有研究,年轻的汪醒华在与两位教授的合作中受益匪浅。汪老师回忆说:“华教授在天津收藏界颇有名气,每当遇到好的唱片,我们两个从不谈价钱,只要对方需要,几乎可以无条件地交换或赠送。”这一轮全国性的收购行动持续了半年,中国戏曲研究院唱片组的家底迅速扩张。至“文革”前夕,库藏资料具有了相当的规模。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戏曲研究院馆藏老唱片的名气已经大到了大家都没有预想到的程度,江青居然开始派人到这里来调用唱片资料。在汪醒华的记忆里,江青对当时戏曲研究院老唱片的库存情况简直就是“一摸清”,她每次调用资料时提出的要求都非常具体、非常准确。汪醒华当时就住在与戏曲研究院一路之隔的宿舍里,好多个晚上,江青的提调任务一来,她必须随叫随到。也正是江青对戏曲研究院唱片的“重视”,在随之而来的“文革”中,这里的唱片几乎毫发未伤。
说到此处,汪老师情绪不免波动起来:“浙江金华有个仓库,听说那里有十几麻袋红卫兵抄来的唱片,我火速赶过去一看,唱片破损严重,一张都没有带回来。‘文革’中砸四旧,唱片是典型的四旧啊!太多的唱片被砸成碎片,堆积在废品站,这批唱片最后被塑料厂做成了钮扣!太心疼了,太可惜了……”
在中国戏曲研究院唱片室的建设历程中,还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扩张”事件。那是“文革”后期,汪醒华无意中得到了一个来自“上面”的消息:文化部有意要成立一个中国音响资料中心!她清楚地知道单凭戏曲研究院的力量,远不足以在全国范围内收集老唱片资料以完善唱片库的建设。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她通过组织给文化部提交了一封请命信,大意是说戏曲研究院唱片组有意去几个重要的唱片集中地搜集唱片,以完善当前戏曲研究院的唱片库,为将来的中国音响资料中心打好基础。让她始料不及的是,带着时任文化部部长于会泳亲笔签名的批复信很快就返回了戏曲研究院,文化部批准了这一请示!这封信如同尚方宝剑,汪醒华兴奋地一夜未眠。很快她踏上了前往上海的列车。
十里洋场上海滩,是20世纪唱片行业的集中地,国外许多有名的唱片公司,如百代、胜利、哥伦比亚都在上海设有代理洋行。一大批京剧名伶、时代歌曲明星也在此灌制唱片。收集老唱片,上海是最重要的一站。汪醒华带着她的“尚方宝剑”和对老唱片的一腔热情,来到了上海市文化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徐景贤随即批示:“请中央来的同志随便挑选,上海方面全力支持。”为了能够尽可能地完成好这次任务,汪醒华把唱片库里所缺少的唱片精心制作了一个目录。这个目录足足一厚沓!汪醒华心里打鼓,要拿走人家这么多唱片,人家能同意吗?当她来到上海图书馆门口的时候,醒目的黑板报标语彻底打消了她的顾虑——热情欢迎中央单位同志前来挑选唱片!于是,一切都进行得那么顺利,上海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把自己的家底和盘托出,并按照这份目录把她需要的唱片悉数奉上。
至此,中国戏曲研究院唱片资料库的规模初步建立起来。“文革”以后,新型录音载体不断出现,老唱片的收集工作也逐渐淡化下来。工作人员将这些唱片分门归类,一一誊写在册。在当时异常艰苦的保存条件下,资料室的工作人员细心呵护,每逢多雨季节都要用电风扇吹散潮气。
根据当前官方统计,中国艺术研究院共馆藏20世纪初以来胜利、百代等十余家唱片公司灌制出品的胶木唱片近80000张,包括钻针、钢针、密纹等不同种类、各种转速的唱片。其中戏曲唱片约35000张,涉及演唱、演奏家900多位。在14000张京剧唱片中,共收有570多位京剧演唱家的唱腔唱段,包括20世纪京剧鼎盛时期各流派名家的经典代表作,如“老三鼎甲”之后的谭鑫培、何桂山、陈德霖、陈彦衡、杨小楼、姜妙香、朱季云、王瑶卿、龚云甫等,以及“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前后“四大须生”、“南麒”、“关外唐”等。尤为珍贵的是,1904年前后最早一批在中国出版的黑胶木唱片、谭鑫培的“七张半”钻针唱片、余淑岩的“十八张半”等。另20000余张为各地方剧种唱片,包括130多个戏曲剧种。戏曲之外,另有30000多张音乐及曲艺类老唱片,包括民歌、民乐、宗教音乐等。
半个多世纪的积累,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中国艺术研究院馆藏老唱片,已经成为全国乃至世界人民共同的文化财富。
老唱片,一个记录了20世纪60多年的声音载体,在这里,静静地保存着,默默地等待着更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

本文作者与汪醒华老师合影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