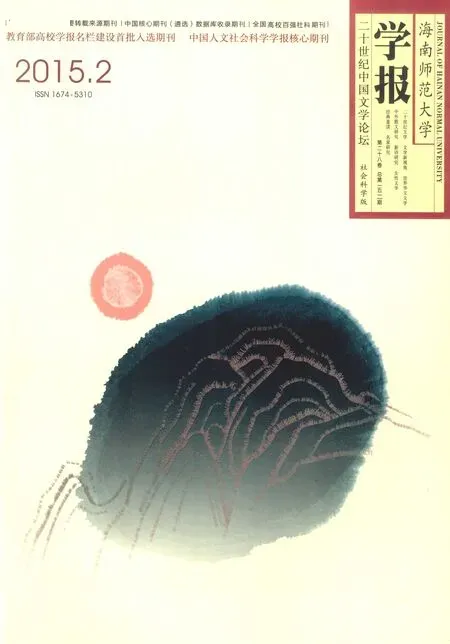讲述政治·批判现实·确立日常生活:80年代小说婚姻故事讲述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嬗变
2015-03-28王莉
基金项目:2014年大连民族学院人才引进科研项目启动基金“革命之后的话语重建——1980年代小说的爱情叙事”;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50—70年代与80年代小说的家国书写”(编号: ZJ12RWQN025)
收稿日期:2014-10-28
作者简介:王莉(1975-),女,蒙古族,辽宁北票人,文学博士,大连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研究。
爱情与婚姻这对如影随形的亲密词语在20世纪80年代小说的话语层面却是彼此对立的。如果说爱情是80年代人道主义、理想主义主流话语的主要载体,那么婚姻则显露了“由理想向现实降落”的话语转换痕迹。爱情的“彼岸”性承载着家国理想和乌托邦梦想,婚姻则与日常生活联结更紧密,婚姻的“此岸”性有助于80年代的个人主体从理想和激情中觉醒。本文意在考察80年代小说婚姻故事讲述方式的变化轨迹,概括地说,婚姻故事的讲法经历了政治风云的性别符号、拆解理想的现实存在、升起日常生活的旗帜三种变化,爱情意识形态向婚姻日常生活“降落”的过程同时也是以爱情为载体的理想主义话语失效的过程。
一、用婚姻故事讲述政治风云的变幻
70年代末80年代初,小说讲述婚姻故事的方法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叙事者们选择了用婚姻故事来讲述“文革”后期、改革初期政治风云的变幻。
韦君宜的《洗礼》以刘丽文对丈夫王辉凡的离弃和重新接纳来表现革命干部在“文革”中的正确与失误。刘丽文是个爱情和婚姻的理想主义者,性格勇敢又坚韧,无视一切世俗的地位、金钱、相貌,大胆追求个人的情感幸福。但她的爱情并非单纯指向个人欲望,而是包含了“文革”中的政治选择,她对爱情对象的价值判断基于其所具有的政治品德。表面上看来刘丽文掌握着爱情和婚姻的主动性和选择权,但实际上她在文本中的功能只是一个性别政治的符号,是作为丈夫王辉凡政治思想和身份的性别资源而存在。革命战争年代,王辉凡是个热情帮助学生的地下党员,刘丽文爱上了他,信赖他;“文革”前,王辉凡变得官僚、盲从,缺乏独立的思想,成了只知执行政策,无视人的生命尊严的政治机器,刘丽文与他再也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共同语言,因此离他而去;“文革”中王辉凡被打倒,反而因此接近了群众,灵魂经受洗礼,焕发出自身的光彩,刘丽文对他的爱情复活。二者婚姻的离合,成为王辉凡思想历程的折射,这种安排显然饱含着叙事者的价值判断。正如叙事者所言,“无论她自己和祁原的或是和王辉凡的爱情,都不是纯男女之爱,一个现代中国有思想的女性不可能有别样的爱情啊!”这种爱情和婚姻必然与时代、政治相连,“我写作不能完全不涉及政治,因为我本人就活在这种中国特有的政治生活中间。”(韦君宜《表现我的时代》)
张弦的《挣不断的红丝线》、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李国文的《月食》、王蒙的《蝴蝶》等文本也通过女性的婚姻选择来表达“文革”之后干部—知识男性政治地位的重新确立。
张弦的《挣不断的红丝线》用婚姻故事为“文革”后老干部的复出提供身份佐证。小说通过傅玉洁对老干部齐副师长前后不同的态度与婚姻选择来表达深层的政治内涵。以傅玉洁的视角来进行今昔对比,以她的心态变化来表达价值观的转换。开篇一段话定下了肯定老干部身份的基调。司机、轿车、庄严的铁门、洁净的水泥路、花坛、精巧的小楼、法国梧桐,这些混合着现代文明气息与老干部身份地位因素的物象一开始就赢得了傅玉洁的向往和读者的愉悦。“复出”后的老干部不再仅仅与革命相连,更与权势、身份、地位相连,家庭场景成为用来表达这种身份地位的首要方式。不会开车门令傅玉洁很窘迫,洗澡时,那洁白的瓷砖、浴盆、浴衣、浴巾、化妆品、香味与她原来想象的“黝黑、粗壮”截然不同,无与伦比的身心享受与闹哄哄脏兮兮的女浴室的对比联想使她否定了自己当初的小资产阶级爱情观。经历了“文革”磨难的傅玉洁与知识分子苏骏离婚,与老干部结婚,完成了对老干部由政治认同但文化排斥到文化认同而政治认同的转变,这个转变被叙述为婚恋观的变化。傅玉杰以婚姻的形式主动接续并完成了“与工农相结合”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彻底否定了自己的知识分子情结。《挣不断的红丝线》延续了《青春之歌》《创业史》《艳阳天》《金光大道》中的“改造+恋爱”主题。但我们要看到,《命运交响曲》与司机、轿车、小楼浴室、化妆品咖啡同为现代文明的元素,但前者属于精神交流,后者属于物质享受。对革命干部的文化认同更多建立在物质与权势、身份层面,以婚姻上的胜利者出现的老干部与自愿改造的傅玉洁之间仍有距离和缝隙。忽略80年代“非政治的政治性”这一巨大语境与文本特征,只在“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中解读张弦的作品中的人物与命运,显然是不够的。
70年代末80年代初,“受难—归来”的知识男性在“文革”后重新回到主流,被这一时期的小说建构为新时期民族国家的个人主体。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通过婚姻故事蕴含的政治话语来讲述新时期男性主体的转换和确立。《天云山传奇》通过两个男性——知识分子/干部罗群和干部吴遥对一个女性——宋薇的权力变化表现了新时期的男性主体由革命干部向知识分子/革命干部的悄然位移。吴遥主体地位的得到—失去以他对年轻姑娘宋薇的得到—失去来建立叙述。“反右”时,吴遥利用职权把情敌罗群打成“右派”,设计让罗群的恋人宋薇嫁给了自己。后来,吴遥压制罗群的平反问题受到上级批评,他在政治上失势的同时,也失去了对宋薇的占有和宋薇对他的服从。宋薇坚决地离开了他。罗群是个受难—归来的知识分子/干部男性主体形象,小说将其主体地位的得到—失去—复得表述为对初恋情人宋薇的得到—失去—复得。1956年,罗群担任天云山综合考察队的新政委,带领全队发现了天云山地区丰富的宝藏。察队的年轻女性宋薇爱上了他。1957年,罗群因为支持知识分子、科学建设被打成“右派”,失去了主体地位,遂失去了宋薇——她在组织压力下与罗群划清了界限。罗群平反重获主体地位时,重新获得了宋薇的爱。宋薇离开吴遥,重返天云山看望罗群并幻想嫁给他。吴遥以统治者/被统治者的传统性别规则对待知识女性宋薇,在主导/辅助的新时期性别规则面前已经失败了。文本以女性对科学、建设的奉献和崇拜实现了对知识男性历史主体地位转换的叙述。
二、批判婚姻对理想爱情的拆解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可以用来概括80年代前期小说的婚姻故事。叙事者站在“五四”的“启蒙”立场,用理想主义、人性来批判婚姻的“非理想性”,婚姻被叙述为埋葬爱情与理想的存在,家庭场景被叙述为麻痹心灵、束缚个性的空间。
80年代前期关注爱情婚姻的作家如张洁、张抗抗、张辛欣、王安忆等对婚姻都很悲观,让婚姻承担了拆解理想的叙事功能,用婚姻生活揭示了爱情神话的虚幻性,婚姻/现实呈现为荒凉冷漠的景象,流露出理想幻灭后的悲哀。如果说张洁在婚姻之外正面宣告了“理想爱情”值得追求,那么谌容在婚姻之内宣告了理想爱情的不可实现性。比起张洁的理想主义,谌容要冷静得多,她的《错!错!错!》讲述了理想主义的爱情观如何在美满婚姻之中遭受失败的故事。把张洁和谌容讲述的爱情故事连起来读,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80年代前期的婚姻故事。钟雨和老干部的爱情因无法进入婚姻而显得无比瑰丽,她对婚姻满怀理想主义的情结,宣称“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而汝青和惠莲在恋爱时尽享浪漫,婚后却冷漠得形同陌路,不得不认同“天底下,多的是失去了爱情的家庭,它们照样在地球上运转”。谌容讲述这个理想主义爱情的反题很彻底,她为汝青和惠莲的爱情排除了所有障碍,郎才女貌,既没有“革命”的规训,也没有婚姻道德的限制,又不存在世俗原则的干涉,俊男美女一见钟情,恋爱热烈而浪漫,汝青如饮美酒沉醉其中,自信进入了爱情的天堂。这样一个郎才女貌的爱情故事如果不“节外生枝”是无法继续下去的,谌容继而排除了社会因素对爱情的影响,没有让“文革”之类的社会事件或突发事件改变爱情的道路,让汝青和惠莲顺利地进入了婚姻。而且是美满婚姻,将汝青塑造为“模范丈夫”,洗衣做饭接妻子下班,洗尿布带孩子为妻子排解心理问题,总之,丈夫也没问题,双方也都没有喜新厌旧。然而汝青和惠莲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结局却是冷漠麻木,不再相信爱情,以至惠莲早亡。其原因汝青归结为惠莲只想要天堂般虚幻的爱情,不想要地上的婚姻。由张洁树起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理想主义大旗,时隔5年,谌容用“失去了爱情的家庭照样在地球上运转”的沉重现实把它放倒。谌容发表于1988年的《懒得离婚》再次讲述了爱情与婚姻分离的故事,爱情是存在的,但无关婚姻。
婚姻/现实作为对爱情/理想的扼杀者受叙事者抨击最激烈的是夫妻间“没话儿”的“凑合婚姻”。在80年代婚姻故事的讲述者那里,倍受婚姻生活折磨的主人公既受到批判又得到同情。“共同语言”是80年代农村青年择偶的重要条件,这是始自40年代的革命爱情观宣传渗透的结果。 [1]夫妻“没话儿”就是没有“共同语言”,显然不符合革命对爱情和婚姻的规训。谌容《懒得离婚》里的刘述怀是个苦中作乐的形象,他提出的“理想家庭”看似幽默,实则满怀苦涩。他说理想的家庭一要有两间房,夫妻一人一间,为的是彼此都有一个可以逃避对方的空间,各自要有朋友,因为彼此之间无话可说。“懒得离婚”道出了刘述怀的苦水,离婚的人活得认真,有勇气,他婚都懒得离,一辈子就“凑合”过了。凑合的婚姻就这样淹没了一个有生命力的人。谌容的另一篇小说《错!错!错!》里的汝青说不上比刘述怀幸运还是更加不幸。爱情幻灭后,汝青和惠莲夫妻俩同原本就没有爱情的刘述怀夫妇一样“无话可说”,一样对婚姻麻木忍耐,汝青比刘述怀更加痛苦,他不堪这麻木却要清醒地忍受这麻木,他们对离婚的看法如出一辙,“懒得离!”“离了又怎么样?还能再去寻找吗?”“算了,爱情算得了什么,何必去自寻苦恼?天底下,多的是失去了爱情的家庭,它们照样在地球上运转。就让我们这个不幸的家庭也加入进去吧。”费孝通对婚姻绝没有理想主义的认识,他指出恋爱的无我的感情的原则与婚姻的理性原则正好相反。“若是把恋爱训作两性无条件的吸引,把一切社会安排置之不顾的一往情深,(这是一种艺术,而不是社会事业)婚姻也必须是这种恋爱的坟墓了。真的坟墓里倒还安静,恋爱的坟墓里要求一个安静的生活却是不可能的。” [2]这番解说为汝青和惠莲的爱情幻灭与婚姻痛苦作了最贴切的注解。承认爱情的虚幻性对于刘述怀和汝青并非是幸福的事,无论是刘述怀最后对离婚的人表达的敬佩之情,还是汝青对亡妻惠莲的痛悔,都掩盖不了他们面对婚姻现实那种深重的失败感和绝望情绪。
80年代的叙事者们用婚姻的现实存在痛心又无奈地宣告理想爱情之不可实现的同时,也宣告了永恒、专一的爱情神话的破灭。叙事者意识到,人的感情并不是一种永恒的东西,承认夫妻间的感情是可变的,表现出“婚外情”、艳遇符合人性以及爱情、婚姻、性相互分离的价值取向。婚姻会受到外界环境的诱惑。陆星儿的《啊!青鸟》里,丈夫舒榛上了大学,视野更开阔,认识的同学更有品位,于是看妻子蓉蓉不够层次了。婚姻暴露了爱情喜新厌旧的本性。张笑天的《公开的“内参”》里,中年记者陆琴方尽管对妻子一往情深,但面对年轻热情的女大学生戈一兰仍然怦然心动,只是他不敢跨越雷池,因此受到奚落。叙事者借婚姻讨论了人性这个80年代的重要话题,透过婚姻场景看到了“人性”的丰富、复杂、多变,透露出婚姻故事讲法变动的消息:由愤怒的痛斥、无奈的冷嘲到承认婚姻的麻木与坚硬,叙事者逐渐由理想主义的高空降落到现实的大地上。
三、婚姻升起日常生活的旗帜
80年代前期,充满理想主义的叙事者还只是将婚姻视为爱情的坟墓而加以痛斥和批判,到1989年,池莉则用一地鸡毛般的婚姻生活升起了“日常生活”的旗帜,彻底完成了对“爱情”神话的解构,从而制造了即将到来的市场经济和消费时代的新的主流话语。
正是在新主流话语的意义上,戴锦华指出池莉始自《烦恼人生》的小说序列,显现了相当深刻的意识形态症候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写实主义”,尤其是池莉的写作,于不期然之间,成了对80年代——理想主义最后的黄金时代的送别;《烦恼人生》的发表完成了一次由理想而为现实的,看似突兀,实则从容的降落。 [3]戴锦华认为池莉的小说不是理想主义的绝望陷落,而是此岸人生的清晰显影。她准确地概括出池莉小说告别理想主义的精神向度,并肯定其彰显日常生活的话语价值。孟繁华在《1978:激情岁月》中说:“日常生活被表达的方式,取决于作家的价值目标和对日常生活的理解。” [4]池莉以婚姻家庭的世俗化叙事确立了日常生活消解一元意识形态的价值。在文学史的意义上,对日常生活的肯定是有其历史进步意义的。理想主义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核,在精神/物质、理想/现实、革命/日常的二元结构中,物质、现实、日常始终处于需警惕、被压抑的一端,未得到过正面的价值确认。即使到了80年代前期,思想界、社会生活中、小说里高擎的仍然是理想主义的大旗,人的价值主要在精神层面来实现。在池莉这里,人物追求的目标才发生了下移,由理想降落到现实,由爱情陷落到婚姻,她为普通人建立了一套日常生活话语。在笔者看来,池莉小说在80年代小说家庭叙事中的意义主要在于完成了对家庭价值,尤其是核心家庭的话语转换,由“五四”式的批判婚姻、家庭束缚个性、破灭理想转换为对家庭生活重塑人性的肯定与颂扬。池莉把婚姻、家庭之于每个普通人的意义推向神圣,从而制造了家庭神话。理想主义失落之处,正是日常生活升起的地方。池莉联结起80年代的“理想”与90年代的日常生活。她小说里的人物,认真地经营着他们的婚姻和家庭。
池莉对婚姻、家庭价值的确立从解构知识分子的爱情观开始。花前月下、海誓山盟、志同道合的爱情故事作为理想主义话语的象喻,成了池莉奋力撕裂的主要对象之一。在池莉那里,爱情是一种话语的虚构,谎言的网罗;人生的智慧在于窥破这美丽的谎言,获得一种对于并不完满的婚姻/现实的认可与坦荡。她在《不谈爱情》里选择了知识分子庄建非作为男主人公。庄建非的知识分子梦不再是罗群式的追求社会理想的“中国梦”,也不再是钟雨式的追求人性理想的“爱情梦”,他逐渐放弃浪漫的“爱情梦”,认同更为实在的“日常生活梦”,落脚在平实琐碎又无比重要的婚姻上。“知识”不再带来爱情的魅力,而蜕变为爱情和婚姻的障碍。文本从知识分子庄建非贬低和逃离他的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和妹妹)入手拒绝“知识”,走向“日常生活”。庄建非觉得知识女性王珞的“爱情”已经无法消受了,他拒绝了王珞。“爱情”已经由承载人的解放的理想化价值观蜕变为飘缈可笑的边缘个性,变成老姑娘的怪癖,宣告了理想主义话语已经失去支配生活的征服性力量。在理想主义话语之下,婚姻是被批判的对象,在池莉这里,婚姻则被提升为一个男性知识分子成长的空间和动力。庄建非遇到了已婚女人梅婷,在梅婷那里得到了性的启蒙和欢娱。在找到理想的爱人之前,主人公的身体和灵魂已经不纯洁了,在推崇“连手都没拉过”的80年代初的“爱情”理想主义者那里,这种场景是不可能出现的。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梅婷这个形象是“日常生活”的象征。她自身优秀,有优秀的丈夫和孩子,有美满的家庭,她启蒙了庄建非,使庄建非认识到婚姻和家庭比爱情重要得多。庄建非与梅婷的相遇使他放弃了浪漫的“爱情梦”,心甘情愿地钻进了花楼街的女孩吉玲精心编织的婚姻之网,因为他从吉玲身上体验到了过日子的味道。漂亮的妻子、独立的小家庭成为安放知识分子梦想的现实空间。主导90年代中产阶级的家庭梦想已经呼之欲出了。
池莉认可此岸婚姻,把婚姻家庭当作普通人成长和实现人生价值的空间,甚至怀着一种敬意书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前所未有。《不谈爱情》是庄建非的成长史,《太阳出世》是赵胜天夫妇的成长史。池莉以“太阳出世”命名了一对平凡的年轻夫妻所经历的一次平凡的生育。在此之前,尚没有一个中国大陆作家如此细腻、逼真而情趣盎然地记述了一个女人从妊娠、生育、抚育孩子的全部不无苦楚、有泪有笑的过程;记述一对尚不成熟的年轻夫妻如何“个中甘苦两心知”地度过了这一全新的寻常岁月。池莉将它呈现为一次学习与成长的过程,新婚一年间经历的辛酸、琐屑、困窘的日子使他们由任性、粗鲁、自我、惹事生非的小青年成长为负责、体贴的丈夫和奉献、宽容的妻子;儿子出世的欣喜、抚育后代的艰辛与欢乐使他们由无须操心衣食的儿女成长为尽职尽责的父母,进而形成了责任、宽容、进取、奉献的人生观,而这是各自的家庭不曾教会他们的。这部以武汉街头喜闹剧式的婚礼开始的故事,成为一个特定的、池莉式的成长故事。一如《不谈爱情》是男主人公庄建非在一次夫妻口角衍成的婚姻危机中认知了现实与妥协,因此而“长大成人”。
《烦恼人生》的主人公印家厚是位普通的男性,文本也采用了男性选择女性的结构来表达对日常生活、婚姻、家庭的认同。正如庄建非拒绝王珞,选择吉玲,是因为在吉玲身上体验到了过日子的味道,印家厚抵御了徒弟雅丽、幼师晓芬、初恋情人聂玲的诱惑,最终认可了“整天蓬松着头发的邋遢”妻子,也是由于他领悟到,婚姻是实实在在的热汤热菜热毛巾,从烦恼的现实人生中体悟到了比爱情更实在的东西,认同了妻子就应该是“粗粗糙糙,泼泼辣辣,没有半点身份架子”,更重要的是“这世上就只有她一个人在送你和等你回来”。这当然并非是他向往的“理想爱情”,甚至偶尔心中会产生瞬间的杀机(“手中的起子寒光一闪,一个念头稍纵即逝”),但他并没有像刘述怀那样“懒得离婚”,他无暇思考“没有爱情的婚姻是否道德”这个问题,他是一家之主,作为丈夫、父亲和儿子,他必须负担起家庭的责任和重担。对婚姻家庭负责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是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
池莉小说的意义在于在80年代末确立了婚姻家庭的价值并建立了日常生活话语,使人们正视理想、政治、民族国家之外的日常生活空间,从而有效改变了理想主义话语独白的局面。她为庸常之辈、为主流意识形态一度不屑一顾的家庭生活和寻常岁月辩护,并赋予它近乎神圣的尊严与价值,然而不经意间却落入“日常生活”的新主流话语轨道,中产阶级的婚姻家庭梦想成为个人追逐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