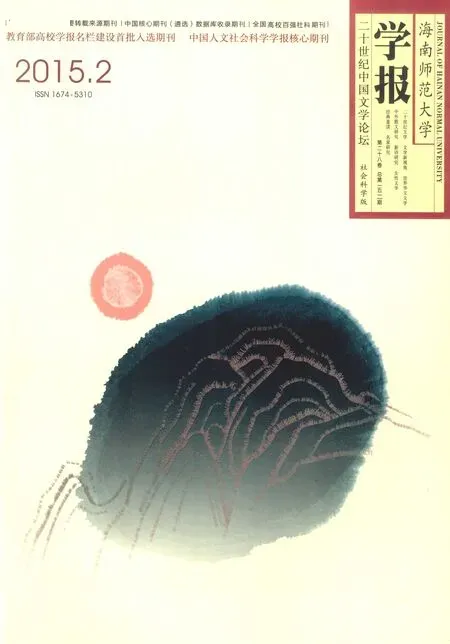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唐诗修辞概观
2015-03-28段曹林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模式和模板混合规划的会话生成研究”(项目编号: 61363032) ;海南师范大学博士教授科研启动项目“唐诗修辞研究”
收稿日期:2014-12-06
作者简介:段曹林(1968-),男,湖南炎陵人,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汉语修辞研究。
王安石曾赞叹:“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言语,已被乐天道尽。” ①此语虽不无夸张,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后人心目中唐诗修辞成就之超迈绝伦。诚然,正如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拥有崇高地位和伟大价值一样,作为诗歌成就的有机成分和必要前提,唐诗修辞的表现无疑也是卓著的,“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创意迭出,特质鲜明,价值突显,在诗歌修辞史上自有其一席之地。本文仅以概览的方式,从语音修辞、语义修辞、语法修辞、语篇修辞、风格修辞等五个侧面一展唐诗修辞的风采和神韵 ②。
一、唐诗的语音修辞
语音修辞方法 [1]的作用,一是建构诗歌的音乐美;二是以语音的特点和联系作为媒介或手段,借以增强表达的形象性、含蓄性、生动性、多义性等。据考察,各类语音修辞方法在唐诗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总体作用非常突出。
(一)唐诗的语音选择修辞
1.双声、叠韵、叠音形式的选用
无论是双声、叠韵还是叠音,任何一种形式单用的效果都并不突出,唐诗中也以配合使用为多,形成复叠、回环、变化之美,产生描绘、渲染等效应。
一种配合是在上下文多处用,但无一定之规。
另一种配合则是在上下句对应位置出现,形成呼应。尤其在近体诗中,双声、叠韵或叠音形式在对仗中往往成对出现,既强化了语音效果,又兼具各种语义表现功能。
杜甫尤为善用、多用这一类型的对仗形式,自觉程度远超前人,数量质量均是空前的,以至于清代洪亮吉不无夸张地说:“唐诗人以杜子美为宗,其五七言近体,无一非双声叠韵也。”(《北江诗话》)
2.响音字、细音字与衬音字的选用
唐诗对响音字和细音字都很重视。常见将响音字放置在韵脚位置,用于表现强劲高亢的声音和气势,而在表现低抑悲苦情绪时选用细音字做韵脚。比较一下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和《登楼》:一首表现突闻喜讯的欢畅,一首表现抚今追昔的悲哀;一首押七阳韵,韵字为裳、狂、乡、阳,一首押十二侵韵,韵字为心、临、今、侵、吟。不难见出诗人依据情绪特点取舍韵脚的用心,字为心声,声情并茂。
衬音字的选用,作用在于协调音节,使语句节奏整齐协调、急徐有致、匀称流畅,具有旋律美。唐诗对此的运用基本上见于古体诗中,常用的衬音字似以“兮、乎”等虚词为主,也有两个以上结合用的。
(二)唐诗的语音组配修辞
1.声韵调的协调与呼应
唐代古体诗和近体诗的成就都很高,押韵对两种诗体而言都是重要的修辞方法和音律要求,但实际运用中古体诗宽,近体诗严,二者的差别是明显的,也是必然的。
杜甫《石壕吏》较为典型地反映了古体诗押韵自由的特点:该诗记叙官差夜捕丁役事件的始末,伴随内容、气氛和情绪变化,随情应境、灵活用韵。每四句一转韵,韵脚均为开口度较小的字;起四句三用平声韵,写“夜捉人”;下十六句平仄杂用,写老妪诉苦,传出老妪复杂心情;最后四句转入声韵,写夜哭和伤别,应合悲氛哀情的表达。李因笃对此评价说“急弦则响悲,促节则意苦,最近汉魏”(《杜诗集评》) [2]。
平仄调配这种修辞方法在诗歌中的运用,在南朝沈约、谢脁、庾信等倡导和运用四声格律以前,尚处于自发状态,并无一定之规。唐代近体诗声律在初唐沈佺期、宋之问等人努力下最终形成,标志着中国古代诗歌在利用汉语声调特点寻求音乐美的表现形式上找到了一种成功的方案。
有些诗人,在平仄合律的前提下,还有格律之外的更精细的讲究:不但区分平仄,而且区分平上去入,平声还分阴阳(清浊)。仇兆鳌《杜诗详注》引了李天生的一句评论:“老杜自称‘晚来渐于诗律细’曷言乎细?律诗平声同一纽(声母)者,不连用;仄声上、去、入三者必隔别用之,无有同者。” [3]这种“细”到每个平声字声母、每个仄声字声调的讲究,只能算是形式美的一种极至。据我们考察,老杜虽然“晚来渐于诗律细”,但完全达到李天生标准的诗少之有少,非不为也,为不能也。
唐代古体诗明显受到了近体诗的影响,无论是格律化潮流或是刻意复古都是对此的反映,如平仄入律或避免入律、黏对、三平调、孤平等。这些既坚持了古风诗体的高古风格和自由优长,更代表了对于音乐和谐美的重视和探索,包含了对于诗歌格律的重要创新。
2.音节的协调与呼应
杂言诗在唐诗中只占极小的比重。但诗人们成功地利用了杂言句表意自由、形式不拘的独特优势将情感的起伏、气势的挥洒有机地融入句式的长短、松紧、整散的变化中。
近体诗忌同字对,音节呼应一般用于同一句中,且多见于首联、尾联。究其本源,则这种形式当“起自南朝乐府,唐人用以入律,便形成七律的一种别调。” [4]
古体诗音节呼应使用的频次更高,复现的字也不限于一个,复现频率也不限于一次。对应位置有时也不拘。更有甚者,韩愈《南山诗》连用51个“或”字句,中间夹杂18个“若”字句和4个“如”字句。
因为篇幅一般较长,古体诗需要通过修辞手段加强形式上的前后联系,词、短语、句子的重复就是其中一种重要手段,被重复的不仅仅是声音形式,也包括语义内容。因为承袭传统的缘故,古体诗往往套用乐府古题行路难、长相思、将进酒、蜀道难等及其诗体格式,安排某些词句,包括一些固定的引导语、感叹语等,隔句相对或遥遥相对。
3.音组的协调与呼应
就唐诗而言,音组的协调与呼应,一是构建对偶、排比、层递、顶真、反复一类及近似整齐结构;二是合理安排句子的语气变化;三是处置好句内节奏的一致性和变化性。
唐诗对句内节奏的处置,一是让句内意义节奏和韵律节奏保持一致;一是使意义节奏突破韵律节奏的约束,带来诗句内在的节奏变化。相比一般诗歌话语,后者尤具特色。
“变奏”的修辞意义,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为了使表意更便利;二是为了赋予句法结构(特别是对仗联各句诗)更多的变化,避免板滞和雷同;三是使近体诗各联,特别是对仗联,句法结构与语义结构互为表里,同中有异,从而增强诗歌语言的弹性和张力。
(三)唐诗的谐拟修辞
谐音修辞是利用语词声音相同或相近的条件,形成语义关联或衔接上下文,从而增强语言的表现力,构成含蓄、风趣、生动、强调等的表达。可细分为谐音双关、谐音仿拟、谐音关联、谐音假对、谐音歧义等。其中,谐音双关、谐音假对在唐诗中广为采用,地位突出。
(1)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李白《春思》)
(2)寻芳不觉醉流霞,倚树沉眠日已斜。(李商隐《花下醉》)
例(1)是常见的异形谐音双关,“丝”谐思,“枝”谐知;例(2)是同形谐音双关,“醉”兼指酒(生理)醉和心(心理)醉,寄情于物,情景交融,使表达含蓄而形象。
谐音假对是在严对中调和格律与表意间矛盾的一种修辞策略。在唐诗中使用不算太多,但也绝非个别现象。主要可以区分为三种情形:借为数目词、借为颜色词、借为其他义类词。这三个小类中,都包含了同形谐音假对和异形谐音假对两种情况,而后者占了绝大多数。
拟音修辞或选用拟声词,更多的时候则临时借用非拟声词形式,用以摹声、传情。在唐诗中,为了更完整生动地绘声,也较多地借助比喻、拟人、通感、联绵词等其他修辞手段,或者通过描写声音给人的感受或产生的影响来间接地表现声音。白居易《琵琶行》可为适例。
二、唐诗的语义修辞
唐诗在语义修辞方法运用中的突出特色和成功之处,一是注重同义言语形式的选择、创造和配置;一是反义对举、类义并用在对偶联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就其功用而言,语义修辞方法直接指向诗歌传情达意之修辞目标,突出彰显了古人在炼字、炼句、炼意中的高度重视和匠心独运,是诗歌语言人格化、陌生化、个性化的主要源泉。古往今来人们反复提及的一些唐诗的名句名篇,往往都基于语义修辞方法运用的成功。
(一)唐诗的同义选择修辞
1.着眼于表现附加意义的同义选择
据我们考察,唐诗在对同义言语形式进行选择时,最优先考虑的应该是通过选用增添或凸显附加意义,其中尤以彰显形象色彩、感情色彩、语体色彩、文化色彩等为主。
唐诗中常见以借喻或借代形式替代本体形式,以凸显形象色彩。
同一语词可能用于喻指不同的对象,如:“破额山前碧玉流”的“碧玉”借代水流,取其清澈寒凉。“碧玉妆成一树高”的“碧玉”比喻柳树树身,取其剔透晶莹。
不同语词也可能用来比喻同一对象,如:“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雁”和“蓬”指的都是“弟兄”。
借代在唐以前的诗歌中已大量运用,唐诗中愈发多用,大大高出了借喻使用的比重,指代关系也比前代更丰富多彩、复杂多变。与表现形象特征密切相关的主要有四类:以性状代物,以物代地,以物代时,以物代人。
唐诗用于突显感情色彩的同义选择,主要是以倒反形式替代正说形式,从而赋予反讽意味,委婉传情。如“不分桃花红胜锦,生憎柳絮白于绵。剑南春色还无赖,触忤愁人到酒边。”(杜甫《送路六侍御入朝》)这里的剑南春色明明是明媚美艳的,却说“不分”、“生憎”、“无赖”,究其用意,则是表明它“触忤”了后会无期、离怀难遣的“愁人”,愈发令其触景伤情!
以凸显文化色彩为主要目标的同义选择,主要是以用典形式替代非用典形式。唐诗比前代诗用典更多,方式更多样。究其修辞功用而言,又有所区分,大致体现在未必能够经常分割开来的三个方面:一是曲折达意,含蓄传情,如大量以汉代隐射当朝的典故;二是讲求典雅,在寻常的写景叙事中带入历史文化意蕴;三是对比烘托,增强对现实人事物的表现力度。
用典在唐诗中是大趋势,不过实际运用情况也因人而异。如王维诗歌用典数量在盛唐诗人中是比较多的,且合其自然心境,无做作之感。单《老将行》一首诗用了十多个典故,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刻画“老将”的艺术形象,这在诗歌史上也是少见的。而孟浩然的诗用典就很少,不过也留下了著名的范例,如“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以凸显语体色彩为主要目标的同义选择,在唐诗中也以典雅形式替代通俗形式为主,并呈现一定的反向追求:或为学习民歌,如李白、刘禹锡;或是记言、体物的实际需要,如杜甫;或出于诗作言语风格的另类取向,如元白诗派、韩愈、多数诗僧。
2.着眼于一语多义的同义选择
一语多义是指同一词句、话语表达多个理性意义,相比理性意义单一的日常形式,也是一种选择,诗歌曲折含蓄、模糊多义的表意追求促使诗人普遍倾向于做出以多义形式替代单义形式的选择。
上述包含借喻、借代、用典、倒反等的形式,也兼含字面意义和实际指称意义。“双关”则是一种典型的一语多义形式,也是唐诗中用得较多的一种多义形式。
唐诗的双关语最多见的是语义双关,即借助语词或语句的多义来构成,尤以直接利用词或短语多义进而形成句多义的为多。其次,也较多地用到了谐音双关,即借助语词间的同音、近音关系来暗含双重以上语意,含蓄传情。
此外,唐诗还用到了语形双关。“寻芳不觉醉流霞”的“流霞”既指花开绚烂流光溢彩,又指神话传说中一种名为“流霞”的仙酒,二者只是语形相同,不是一词或一语多义。
3.以“话外有音”为主要目标的同义选择
语带双关是言语形式一身二用,兼表多义,话外有音则是指言语形式依靠语境条件的帮助传递话语意义之外的其他意义,即言外之意。选择能够传递言外之意的言语形式,一是为了“以少少许胜多多许”,言少意丰;一是为了“含不尽之意于言外”,含蓄蕴藉。这种选择,对于诗歌,特别是对近体诗而言,因而显得非常重要。正如梅圣俞所云:“思之工者,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於言外。”(《艺苑卮言·卷一》)
在唐诗中,尤其是近体诗中,话语形式的选择与配置,很大程度上正是着眼于这两种修辞目标。当然,实际体现出来的修辞效果是经常结合在一起,很难截然分离的。其途径,一曰计白当黑,不言言之;一曰融情于景,托物言志。
不言言之,是说有所寄托或暗示,或是以自然喻人事,或是以寻常事象蕴含深奥的哲理,或是移情于物。如元稹《行宫》。
唐诗中,也每每可见景语情语不可分离,尤以景语替代情语为多,藉此形象传情、含蓄达意。如柳宗元《江雪》。
(二)唐诗的语义配置修辞
除上下义配置修辞外,唐诗对其他几类语义配置修辞的运用颇为频繁,分布非常广泛。最多出现在对偶联中,句内连用或间用、句间呼应的也占相当比重,具有互补、强调、对比、附加色彩等表意功能以及变化、衔接等谋篇功能。
1.着眼于语义强化的同义配置修辞
在唐诗中,同义配置修辞用得很多,特别多见两个同义形式连用和在对偶联中对用,在表达上主要起强调、互补、扩展、变化等作用。
同义词的对用或连用,往往还伴有反义词、类义词等的对用或连用,共处于两个同义句或类义句中,产生“格式塔”效应,使整体语义大于局部之和;同时又避免了话语形式的简单重复,使语言运用更为灵活自由,丰富多彩。
2.着眼于语义对比的反义配置修辞
唐诗中几乎就看不到所谓“反饰”,即由一个反义词语修饰另一个反义词语构成偏正短语的情形。无论就近体诗或古体诗而言,反义配置修辞分布频率最高的当属包含对仗的联句中。运用方式,则以句间对应位置对用的为多,其次是句内连用或句内间隔对用。
反义词语连用时,其主导用意一般不在对比,而在对时间、空间范围、方位等作完全概括,如下例的“先后”、“向背”;或是对动作行为、性质状态等作整体描述,有选择或涵括意,如下例的“去来”、“高卑”。
船争
先后
渡,岸激
去来
波。(储光羲《官庄池观竞渡》)
色因林
向背
,行逐地
高卑
。(李颀《篱笋》)
这类形式也就是通常所谓的“互成对”,连用的词语成对,进而与相对的词语成对,构成严对。不过,连用并不仅限于对偶联。“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杜甫《石壕吏》)“出入”也是反义连用,也有浑括作用。
反义配置还有一种特殊情形,只有一个成分表意,而另一成分语义临时虚化。“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的“日月”只有“日”表意。这类用法,首先是满足格律需要,而虚化成分虽然不表实义,仍有一定的映衬作用,能凸显实质表意的另一成分。
3.着眼于语义完足的类义配置修辞
唐诗中常见借助类义词构成正对或串对,也可见用于反对的联句中。其修辞主旨大抵在于并举有代表性的两个事物或方面,以少胜多,以点带面,相互配合,从而完足整体语义。
问姓惊
初见,
称名忆
旧容。(李益《喜见外弟又言别》)
“姓”、“名”可以看作互文,都有“姓名”意,分用而合指,省文而足意;“问”和“称”是言语行为,“惊”和“忆”是心理活动,连用一道,足以见出由外到内的整个变化过程。
细究起来,类义配置修辞也是自然界或人情世故的自然联系在言语中的正常体现。因而在对仗联中用于相对的类义语词,相比狭义的同义、反义语词,也更为常见。唐诗中非常受重视的颜色词对、数词对、名词小类对、虚字对等,大多可归入类义形式对举。
4.着眼于语义变异的异类语义配置修辞
同义、反义、类义都可视为同类语义配置。同类语义配置带来了言语组合体部分或整体的语义强化、语义对比、语义完足等修辞效果,而异类语义配置则能促生言语组合体部分或整体的语义变异。
异类语义配置修辞着眼于语义变异,方法多样,在唐诗中的运用,主要是通过语词超常搭配,构成比喻(暗喻)、移就、拈连、舛互、通感等辞格表达式,尤以构成比拟最为多见,而构成拟人的又占了构成比拟的绝对多数。
君为女萝草,妾作兔丝花。(李白《古意》)
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杜甫《漫兴》)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江雪》)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杜甫《石壕吏》)
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杜荀鹤《春宫怨》)
以上各例分别是基于暗喻、移就、拈连、舛互、通感的超常组合式。
而拟人式之所以在唐诗中多用,则源于其多方面的修辞功能:一是可化静为动,把静物写得鲜活跳脱;二是可把物人格化,令其识事理、通人情,代人传情,并更好地揭示事物特征;三是可借助拟人化写法,形象传情,宛转达意,创造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三、唐诗的语法修辞
(一)唐诗的词法修辞
唐诗的词法修辞,最具特色和研究价值的,无疑是近体诗在虚词选择和运用中的特点和规律。其次,词类活用修辞在唐诗中已经占据了词法修辞的重要位置,有必要深入挖掘。
“虚字在诗歌里的意义是,一能把感觉讲得很清楚,二能使意思有曲折,三是使诗歌节奏有变化。” [5]唐代近体诗用虚词的总量和平均到每句诗的数字,比起古体诗来自然有差距,但就其重要性而言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经过多重筛选后依然留在近体诗中的虚词,往往具有独特的传声达情或构形结体功能,使诗人不忍割舍。而古体诗对多音节虚词的使用和对虚词的连用,都明显要多于近体诗。
词类活用修辞是指临时改变词的语法功能,可分为词性变异修辞和功能变异修辞两类。总体看,词类活用修辞在唐诗中的使用频率不算太高。词性变异修辞主要用到了以下几类:动词词性变异修辞、名词词性变异修辞、形容词词性变异修辞。
功能变异修辞,特别值得注意的主要是两类情形:数词虚用与代词活用。据我们考察,唐诗继承了以往数词虚用的传统,并在虚用数词的数量和用法上有一定的新拓展。在使用数词时以虚用为主,大多数数词发生了功能变异,其中用于言其多的要远远超出言其少的用量。而虚化主要源于两种途径:一、以定数代不定数产生的语义虚化;二、借助数字对比或变化临时造就的语义虚化。唐诗的代词活用,主要是指你、尔、他三个主要人称代词,除本用即分别用于指称第二、第三人称对象之外,还临时用作指称其他对象。 ①
(二)唐诗的句法修辞
句法修辞方法可区分为句法变异修辞方法和句法选择修辞方法两类,两类方法表现形态和功能特征各异,在近体诗和古体诗中的实际运用也有别。二者分工合作、双管齐下,对两类诗而言都是经常性采取的句法修辞策略。总体而言,唐诗在句法修辞方法的运用上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首先,强调形式与内容并重。无论是对句法成分或句式的选择、安排、调整,还是对功能不同句式和形体不同句式的选择配置,在强调内容表现需要的同时都不忘讲究形式的变化、追求形式的美感。或侧重内容,或侧重形式,但并不偏废。而语气不同句式的选择和配置,本身就是既与内容又和形式相关的。
其次,追求结构和节奏的松紧有度。古体诗用连贯句的比例明显高出近体诗,而用本位句和紧缩句的比例则明显低于后者,这意味着面对同样的内容,古体诗更多地采取了相对松散的句法结构,节奏、语气等从整体上更显舒缓,语义密度也比近体诗小。
再次,重视表达的简明。古体诗强调简而明,句法成分间的结构和语义关系一目了然;而近体诗更讲究简而丰——形式简洁而意指含蓄丰富,句法成分间的形式或内容关系多半不那么清楚明确。
古体诗句法结构都比较完整,省略的成分较少,即使有省略一般也属于“可以补出来并且只有一种补法的”狭义省略;几乎不用由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包括偏正或并列短语)构成的独词句;句法结构都比较规范、单纯,极少出现近体诗常见的复杂谓语句和语序错杂的移位句;前后诗句之间联系往往比较密切,跳跃幅度不是太大,起衔接作用的句法形式用得明显比近体诗多。而近体诗在具体操作方面不如后者丰富多样,如近体诗不能利用句式长短的变化,也几乎不借助句法成分的重复。
四、唐诗的篇章修辞
(一)唐诗篇章修辞方法的运用
唐诗篇章层面的修辞,方法运用上也不外乎语音、语义、语法、语形等修辞方法的单用或合用,但同样的方法在适用性和实际用法上会有所差异。
1.篇章语音修辞方法的运用
语音修辞方法是韵文体通用的重要谋篇方法。这其中可大别为两类,一是遵从、变通诗体固有的格律模式谋篇;一是同时借助换韵、变音节数等其他语音修辞方法谋篇。近体诗以前者为主,古体诗则以后者为主。
就唐诗而言,不同诗体不同阶段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声律、韵律、节律的制约和影响,不过相比之下,近体诗格律更严苛,古体诗格律更宽松;近体诗定型之初格律相对宽松,古体诗在律诗出现后,因着力避免律句而形成了新的平仄律,增加了某些限制。也正因此,遵从各自的格律、寻求有限变通,也就成了几乎所有唐诗的第一选择,这几乎也就是对声韵调协调与呼应(同韵相合、平仄调配)、音节协调与呼应、音组协调与呼应这三类语音修辞方法的选择,只不过这种选择基本属于“规定性动作”。但任何创作都非机械重复,诗人在做出这种选择的同时,一般也意味着自觉,并会自主地做出某些适应内容和情感表达需要的变通。在此基础上,有些注重创新的诗人会走得更远,有意识地突破现有格律,以造就某种特殊风貌或格调。
古体诗由于格律带有更多的自由度,篇幅一般较长,语音修辞谋篇因而也更多地与内容、情感、格调等的表现有机统一在一起,形成表里协调的结构格局。其中尤以变换韵字平仄和韵部为主要方式,杂言诗还用到句子音节数目的变化(一般也意味着节奏的变化)作为区分语义段落、标志情感变迁等的形式手段。
2.篇章语法修辞方法的运用
唐诗常借助篇章关联词句、独立成分、管领词语、句式组配等语法形式或手段衔接诗句,形成连贯关系。
唐诗中运用的句法成分衔接手段主要可分以下三种:一、前后使用相同句法成分以统贯上下文;二、使用独立成分、管领成分或关联词句以强化或彰显诗句间的联系;三、采取分合呼应成分使前后成为一个整体。
唐诗的句式组配谋篇,主要体现为依据内容和形式的实际需要,对结构、语气、功能或形体等类别相同或不同的修辞句式的连续使用、间隔使用、对应使用。
3.篇章语义修辞方法的运用
唐诗中常用于谋篇的语义修辞方法有比喻、映衬、对照、互文、比拟、呼告等辞格和类义修辞方法。这些修辞方法出现在全诗或在超句(格律句)层面,构成结构紧密、语义连贯的修辞文本。
4.综合性语篇修辞方法的运用
这类方法同时利用语音、语义、语法、语形等多个因素,唐诗中较多用于谋篇的综合性修辞方法有对偶、排比、顶真、重语等几种。
(二)唐诗篇章修辞的审美效应
篇章言语形式的和谐,一方面通过不同诗语形式在同一诗篇中的形态变化与并存关系的融洽得以实现;另一方面是通过诗语结构要素的形体特征与共存关系的协调去达到。由此形成两种基本形态的言语形式和谐美:言语表面形体的齐一与变化美;言语内在关系的统一与对立美。
1.唐诗言语表面形体的和谐美
这类审美形态主要源于对偶形式、复沓形式以及均齐的篇章结构等的多样化统一,与之相应则有对称美、复沓美、均齐美等。
对偶这种看似非常严格规整的句法形式组合,实际上仍然蕴含了许多的变化。这些变化,归纳起来,大体有这么几类:一、对偶形式本身的多样化;二、对偶的两个句法形式同中有异;三、对偶形式存在各种变体。
顶真、排比、重语等熟悉的形式尽可归入复沓形式,包含没有规律的重复,不属于这些形式的,也应该包括进来。复沓的形式可能是一句诗,也可能是连续的多句诗。
整齐或均衡只有与各自的对立面处在一种以我为主的辩证统一的动态关系中的美,才是更具蕴含和深度、更具现实意义的和谐美。李泽厚对七律的评论事实上可以扩展到全部唐诗中:“七律这种形式所以为人们所爱用,也正在于它有规范而又自由,重法度却仍灵活,严整的对仗增加了审美因素,确定的句形可包含多种风格的发展变化。” [6]
2.唐诗言语形式内在关系的和谐
这类审美形态主要体现在诗歌内部联系的密与疏、断与续,节奏的张与弛、同与异等几对矛盾的有机统一。
唐诗并不一味地强调诗歌结构的紧密,更多地是无论局部或全篇都讲求疏密有致、断中有续、松紧结合。具体而言,或者仅在诗歌的局部使用密切结构联系的篇章修辞手段,或者对这些篇章修辞手段变通使用,以使整体上结构疏密有致。如总分式、离合式、排比式的篇法安排本身就是一种疏密有致的结构。
近体诗主要是靠对仗联和非对仗联以及本位句、连贯句、紧缩句的分工合作,古体诗则更多地借助形体或结构接近的诗句放在一起构成同言、顶真、回环、反复、排比等句群,以加强诗歌局部的联系,而在更大层次的诗段、诗篇中,通过相同(近)诗句的呼应或某些关键语词的贯穿来凝聚诗篇。
诗歌情绪节奏的语言表现很大程度上是由语音修辞来完成的。尽管节奏变化有时并没有结构变化那么明显,但唐诗的句内节奏、句间节奏、音乐节奏与意义节奏、整首诗不同部分节奏的同异、张弛的变化还是清晰可闻的,这种变化往往应和着情感的跌宕抑扬的波动曲线,显得谐调而自然。
五、唐诗的风格修辞
1.唐诗言语诗体风格的丰富和创新
唐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古体诗、近体诗的各种诗歌体裁形式都有佳作传世,在诗体承传和创新中也取得了突出实绩,诗体言语风格呈现出独特性和多样化。
唐诗言语诗体风格的总体特征。一方面,唐诗众体皆备,各类体裁形式全面开花,硕果累累,言语风格多样。正如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三指出的:“甚矣,诗之盛于唐也!其体则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与此同时,受诗体本身进化逻辑和时代生活的影响,各种诗体在不同历史时期发展并不均衡,这又导致诗歌总体言语风格的时代差异性。另一方面,唐诗在致力于继承、完善和创新各类诗体体制的同时,格律求变,修辞求新,不断谋求各类诗体言语风格的变革创新和个性化,使之呈现独特风貌。其中包括古体、近体之间的分道和互渗,也包括各自内部小类的诗体革新和发展,以及诗歌对其他文学体裁材料和手法的借鉴和引入等等。
唐诗言语诗体风格的分体特征。古体诗是旧有诗体,在唐诗体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言语风格上既从总体上有别于汉魏六朝,又在五古和七古两种分体上各具特质。唐人作古体诗,或是有意区分古体近体,或是不可避免地受到近体影响,都在格律和修辞上对古体诗体式选择和语言运用施加了某种影响,使古体诗由过去的完全自由体变成了处于格律诗与自由体之间的新诗体。并在学习前代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两种特有的体制:七言歌行体和新乐府。近体诗区别于古体诗首先是在声律体制的规范上,进而延及语言选择和修辞运用的方方面面。在确立体制规范和走向形式成熟的过程中,同时也在格律形式上追求变化和个性,由此带来了诗体风格的多样化。近体诗对于其他文学体裁形式也有所鉴戒,并产生了一些成功之作,引发了诗体风格的新生和变异,如晚唐律诗的骈文化。
2.唐诗言语时代风格的统一和变迁
与诗体风格的丰富和创新形成呼应,唐诗时代风格也呈现出丰富的变化和多样的统一。言语时代风格的形成取决于社会变革、思想渊源、文学传承、诗人才性等的合力作用,其具体表现也是多方面的:有综合的,如多种诗体不同时期集体呈现的风格共性和差异;也有个别的,如同一诗体不同时期各自呈现的风格共性和差异。不同诗体在唐代发展程度不平衡,各自的发展道路和演化轨迹也有别,由此造就了诗体风格的时代差异。
3.唐诗言语个人风格的独特和多样
前人关于唐诗的流派风格、时代风格、个人风格等论评甚多,简约概括,可取处不少,其中大体都包含、关联相应的言语风格。据前人总结和我们观察,受多方因素影响,唐诗在言语风格的浓淡、雅俗、工拙、常变、繁简、刚柔、直曲等倾向上各有所取、表现不一,但也存在相融相通、并存不悖的现象。蠡测管窥,足可见唐代诗人艺术才能之争奇斗艳、各擅所长,言语风格之异彩纷呈、独具貌相。
大致说来,常见的言语风格组别和类型,如刚健与柔婉、简约与繁丰、朴实与绚烂、明快与含蓄、庄重与幽默等,每一组乃至相对的每一类,其不同都可以从唐诗中找出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诗作。与此同时,这些不同组别和类型的风格,即便是对待的类型之间也并非截然排斥的,有可能统一于同一诗人、同一诗作中,并存不悖。着眼于唐诗总体,成对风格中存在明显或压倒性优势的,是刚健、简约、庄重,而朴实与绚烂、明快与含蓄大体难分伯仲。
基于诗作题材、诗体类型、诗学主张、美学旨趣等多方面的一致或接近,唐诗形成了特定的诗歌流派或诗人群体,主要有盛唐的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中唐的新乐府诗派和险怪诗派以及初唐诗人、大历诗人、晚唐诗人等,同一流派或群体主导风格相近,但受诗人才性禀赋、创作实践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在风格的实际构成上又存在一定差异。
即便是同一诗人,其作品言语风格也是同中有异。如李白、杜甫是公认的大家,都是流传诗作较多、才气横溢兼擅数体的诗人,言语风格因而也呈现出独特性和多样性。一方面,他们的才性和风格是独一无二的,李白以刚健自然为主调,杜甫则以凝炼含蓄为主调;另一方面,他们的才性和风格又往往具有兼容并包的多面性,不同诗体、不同题材、不同时期每每呈现不一样的风貌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