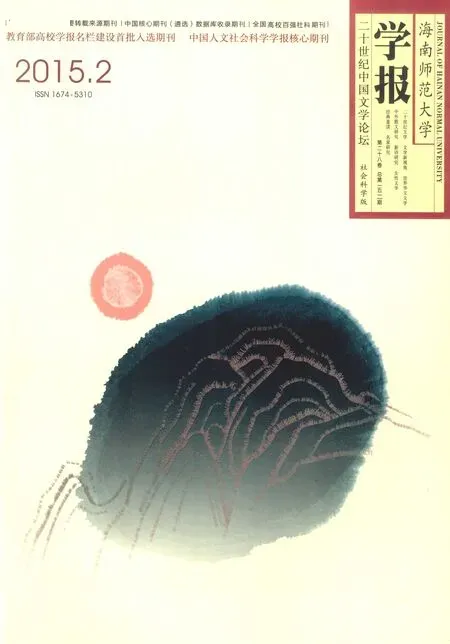黎族民族旅游中的地方性知识与女性旅游精英的成长
2015-03-28张秀伟
陈 丽 琴,张秀伟
(海南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海南 海口570228)
作为一种较高层次文化旅游形式的民族旅游,是以民族地域以及与民族特色相关的风土、风物、风俗、风景组合而成的奇异的、富有异域情调的民族风情为吸引物,吸引旅游者前往休息、观光、体验及学习等的旅游活动,是游客在与当地居民的接触中经历的一种文化体验历程。可以说,民族旅游是与民族特色紧密联系的一系列商品组合再现。[1]它与仪式、民俗、地理、跨文化比较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在时间上表现出某种类似于人类学家涂尔干、莫斯所界说的“神圣/世俗”的关系性质。因此,民族旅游业的发展,可以说是提供了民族地方性知识再生产的新语境,也为在民族旅游中担当主力的少数民族女性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更为广阔的平台,进而可能影响当地女性角色行为的变化,也会触及社会性别秩序以及其他方面的变化。[2]而作为民族文化集中代表的少数民族女性,正借助民族旅游的热潮激活着性别主体意识和身份价值的挖掘。本文试图通过对海南五指山女性旅游精英成长路径的考察,来阐述她们在民族旅游中如何成功对地方性知识进行重新利用和构造而成长的策略机制。
一、民族旅游与地方性知识的关系
(一)地方性知识
作为阐释人类学中心概念的地方性知识为吉尔兹所开创,但在他的著作中并未对这一概念作细致化的明确定义,只是模糊地指出这种知识的“发生经过自有地方特性,并与当事人对事物之想象能力相联系”。[3]后来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于地方性知识进行了论述,如Warren 认为:“地方性知识是一种本土的知识,即某一个特定社会或文化的一种特有知识。本质上,地方性知识有别于或相对于由大学、科研机构和大公司所产生的国际知识体系。”[4]Iirr 为了强调这种知识的本土性,更是将其最为简单的定义为:“地方性知识泛指当地人和特定社区的知识”[5];Grrenier 以较为学术的眼光把地方性知识定义为:“一种特有的、传统的、本土的知识,它是由一个特定地理区域内所世居的妇女和男人在特定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并存于社区中。”[6]从这些学者的定义可以看出,地方性知识的所谓“地方”特性并不仅仅特指某个特定的地域,而主要是相对于全球性知识或者说普同性知识而言的非“中央的,官方的,正统的”。因此,少数民族的地方性知识主要是指各少数民族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因其独特的生态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而积淀并传承下来的独特而深厚的本土知识,如宗教信仰、婚恋文化、民俗活动、歌舞表演、传统编织、特色服饰和建筑等民族文化。
(二)黎族民族旅游语境中的地方性知识
不言而喻,在强调民族旅游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时,必须同时强调它是一个具有多重性质的社会行为:一种集消费经济和社会权利象征并存的社会行为。作为经济的发展手段,它自然体现出了经济领域的某些性质,最明显的是需求决定供给,即“游客就是上帝”。也就是说,旅游者有什么样的需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旅游地会有什么样的产品,这不能不说是经济权力在现代性中之于旅游社会性的某种暗示。从这个角度来说,民族文化资源在旅游中历史性地变成一种交换商品,作为一种消费性社会价值特征,当地人很容易在市场浪潮中不由自主地把追逐经济利益作为主要动机。正如札哈里尔迪斯所言:“人们关注某个问题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某个问题的重要性,而是由于这个问题恰好能够解决一个与他们的价值观、信仰和物质利益相吻合的需求。”[7]因此,并不是所有的地方性知识都能在民族旅游语境中发展,只有那些适应市场需求的地方性知识才能作为资本进行广告宣传来吸引游客的注意。所以虽然黎族地方性知识有很多,但作为旅游资源在民族旅游语境中被开发、加工和利用较多从而形成旅游产品的主要有以下几项。
1.服饰文化
黎族服饰属于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以其鲜明的风格、精美的织锦、古朴神秘的装饰品令人推崇。黎族服饰,主要是利用海岛棉、麻、木棉、树皮纤维和蚕丝织制缝合而成,特色体现在黎族女性服饰中。黎族女性服饰织绣着精致的花纹图案,有些织绣品上嵌绣金丝银箔、云母片、羽毛、贝壳、串珠或铜钱等,显得鲜艳夺目,绚丽多彩。虽然随着时间不断地推移和各民族交往的频繁,黎族服饰变化了很多,但仍保留其民族风情习俗。与黎族服饰联系在一起的是黎族古老而先进的纺织技术——黎锦,它享有盛名,成为海南独具特色的旅游工艺品,深受游客喜爱。
2.建筑文化
黎族人民在千百年来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根据自然地理、气候条件、建筑材料及技术水平,因地制宜地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茅草屋。茅草屋主要有两种样式即船型屋和金字型屋,以船型屋最具有代表性,它是黎族人民传统智慧的结晶。船型屋属于传统的竹木结构建筑,以格子、竹子、红白藤和茅草为建筑材料,房屋的骨架用竹木构成,外形像船篷故得船形屋之名。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建筑技艺、无法替代的民族文化和“黎族最后的精神家园”,和黎族纹饰一样,船型屋在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歌舞文化
黎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除了各种节庆之外,海南许多景区、风情点以及一些宾馆,都会见到精彩的黎族歌舞,它可以自成旅游产品,也可以成为其他旅游产品的重要组成要素,因此黎族歌舞文化在海南文化展示中占有重要地位,如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三月三》、《打柴舞》、《竹竿舞》、《舂米舞》等。近年创作的黎族歌舞剧有《种山兰的女人》、《甘工鸟》等,在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等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黎族歌舞不仅热情地款待了海内外游客,还曾赴法国、日本、印度、土耳其等国进行友好访问和演出,被誉为南国一枝绚丽的奇葩。
4.饮食文化
黎族的饮食文化在热带地理环境下,具有独特的风格。黎族的特色饭有山栏米饭、竹筒饭、红薯饭、黄姜饭、山薯饭等,特色饮料有“并”(糯米酒)、玉米酒、番薯酒、芭蕉酒、山果酒、水满茶等,特色菜肴有“南杀”、“肉茶”、“鱼茶”等。黎族特有的饮食文化成为海南旅游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女性旅游精英的成长路径:地方性知识与市场要素的有机结合
借助民族旅游的特殊文化环境与市场条件,黎族女性从传统的农业生产中被置换出来,成为了旅游活动主体,旅游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活跃着黎族女性的身影,她们由此成为民族旅游发展的中坚力量和最大受益者。在这其中,一些女性凭借自身的知识和技能、魄力与胆识,抓住市场先机,依靠在旅游业中的长期实践经验累积获得了各种优势资源,率先走上了富裕之路,成为了在当地甚至全国都有影响的名人。根据社会分层理论和精英理论,我们可以把她们称为旅游精英。她们的成功虽然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总的来说,她们的成长都是对地方性知识与市场要素的进行了较好的结合利用。
【案例一】歌舞文化和品牌效应转化为创业资本
布鲁默认为,人的行动、行动客体以及社会群体在内的各种社会现象都是通过人的互动过程而不断形塑和建构起来的。因此,在民族旅游的开发过程中如何增强民族认同的价值,了解游客纷至沓来的目的,明白旅游经济交换背后的得失,并能在其中发现市场发展机会就成了一种重要的能力。ZGL 就是这种能力的拥有者和实践者。
ZGL 原是一名普通的黎族传统文艺爱好者,后凭借自己优异的唱歌、跳舞表演技能,在民族节庆活动和民族旅游的发展阶段利用每次表演机会展示了自己的才能,慢慢建立了美名,产生了品牌效应。之后ZGL 利用自己的品牌效应创办了自己的黎族风情园,该风情园将“原生性”、“生态性”、“文化记忆”、“公共社区”等理念融入,通过移植黎族文化的方式进行开发即以较小的比例再现黎族文化,将黎族珍贵的文化遗产融入旅游经济中,在实体景观的基础上充分体现活鲜文化,注重趣味性和观赏性,除了黎族的特色物质建筑外,还通过个性鲜明的主体和浓厚的文化氛围来感染游客,如用本民族的传统节日——三月三、嬉水节,定期举办有民族风情的大型活动,让游客在品尝美食之后还有可供观赏和亲身体验的娱乐活动,延长了游客的逗留时间。该风情园因为民族风情浓郁而深受游客的青睐。
可见,ZGL 个人在承继、发展黎族地方性知识的同时,也在旅游经济中很好的运用了本民族文化艺术,巧用民族特色并结合旅游产业化的运作达到了个人经济和民族文化发展双赢的目的。
【案例二】以饮食文化为基础成功创办了“农家乐”
CLQ 是在民族旅游萌芽时期,具有较强的市场意识,较早意识到了本地的饮食、瓜果、风俗、风景在旅游中蕴含的巨大商机,从开始小规模自己开发家庭旅游接待到现在带领全村人进行大规模乡村旅游接待。CLQ 农家乐的主要特色是将该地区的自然景观、地域特色、民族民俗风情融为一体,让游客通过与当地居民同吃同住,并参与简单劳作的生活中,饱览丰富的自然生态景观,欣赏浓郁的地方特色,领略一种强烈的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和亲切感,让游客在体验该地方原汁原味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充分体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丰富了村庄旅游的内容、拉动了村庄经济发展的基础上,CLQ 自己也成为了创业成功的女性精英。
分析CLQ 精英成长路径,就会发现她在创业的过程中策略性地利用了地方性知识,积极地进行着自身新的社会角色调适,并从中最大限度的进行自我价值的实现,同时为自己和家庭获取到更多的经济利益。
【案例三】将服饰文化进行市场开发直接转化为经济效益
2009年,“黎锦纺织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五指山市番茅村的LXL,被认定为黎锦纺织技艺传承人。此时LXL 的香兰织锦合作社已经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又兴建了一座三层的大楼,成员在不断增加中。出身编织黎锦世家的她,本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女性,以前一直以编织黎锦为副业。但随着五指山旅游业的发展和政府对这项古老技术的重视,她很快把握市场发展机会,凭借自身技术优势,开始把编织、出售黎锦工艺品作为精心管理的主业。在她的悉心经营、规范管理下,以黎锦这项传统艺术手工艺品为依托的纺织所生意兴隆,口碑甚佳。她得到了省、市以致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黎锦编织合作社越做越大。如今,她的纺织合作社不仅仅是纺织的场所,还在一定程度上是展示黎族风情和文化的场所:墙上泛黄的图片不仅向游客展示了黎族源远流长的编织技术发展历史,而且展示了与此相关的民族文化。在此基础上,LXL 利用个人影响力,联合家人创办了集养殖、娱乐、休闲为一体的度假中心,参与到了旅游行业的规模化、系统化发展中。在自己的经济收入源源不断增长的同时,她也为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致富道路,逐步成为了黎族女性中改革创业的精英,她的度假中心也成为了五指山旅游的示范项目。
四、地方性知识与社会资本的有机结合:女性旅游精英的成功之路
女性旅游精英的成功虽然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分析她们的成长路径,还是能发现其中的某些成功规律,那就是她们都较好地对黎族地方性知识进行了成功再生产和对个人社会资本进行了成功投资转换。
(一)对地方性知识的成功运用
有学者分析,精英之所以是精英是因为他们对资源的拥有或调动能力及其在社区中的较大影响力等,尽管精英不总是拥有资源,但他们能够利用自身影响力整合资源并将其投入使用;同时,精英能够实现资源效用利用的最大化。分析女性旅游精英的成长路径,就可得知正是她们对黎族地方性知识的成功运用和整合,再加上自身对资源的调动能力和品牌效应,才带来了她们的成功。虽然黎族的这些地方性知识在民族旅游语境中的再生产,与传统时期的无意识传承不同,是一种由来自政府、地区精英、游客等多种内外力量共同参与而有意识创造过程,是在旅游地政府、旅游开发商、旅游地原住民以及旅游者多方对话与市场选择中完成的。这种选择性不仅体现在对地方性知识形式与内涵有选择性保留、根据市场需要对原有文化进行加工和变革上,也体现在对汉族文化选择性的采借基础上。正是通过这种有选择性的传承、吸纳与创新,才使得黎族女性及其展示的地方性知识成为三亚和五指山市的核心旅游吸引物,有些女性也借此生存、发展,最终走上了富裕之路,增加了对所在环境的影响力和集聚了社会凝聚力。尽管有学者对传统的地方性知识在民族旅游中作为一种商品持有反感的态度,但是不能否认女性旅游精英在利用这些地方性知识谋取经济利益的同时,她们也对当地民族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更难得的是为民族文化的保存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和汉族文化的强势影响下,黎族的民族文化和传统技术正在不断消失或同化,而这些女性旅游精英出于对自身民族文化强烈的认同且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热衷保护,她们将具有民族风情的歌舞、技术、服装、特色饮食等融入到旅游发展中,无疑对本民族的文化保存、传承、宣传、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或不可缺少的作用。所以,女性精英这种既能带来经济利益又能促进民族文化保存和传承的双赢选择未尝不是未来民族文化发展的一条优选路径。
(二)个人对社会资本的成功投资、利用和再生产
根据布迪厄的观点,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的网络占有的密不可分的。”[8]可以说,社会关系网络是通过有意识的投资策略而形成的持久性的关系网络,在被制度化的建构之后,它以从变动不居的偶然联系变为具有稳定联系的关系网络,成为一种可以获得收益的可靠资源。另一位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将社会资本在投资、利用和在生产的自我增值特性经典的表述为:“社会资本不会因为使用但会因为不使用而枯竭。”[9]所以社会资本无论作为人际资源还是作为组织资源,都具有自我强化和增值的功能,越是经常使用,它的供给越是丰富,利用得越多,其价值就越大。将社会资本的相关理论运用到旅游与女性发展的关系中,就会发现旅游与作为最能体现民族文化内涵的女性发展实际上是一种包含了外在性内化与内在性外化的双向影响的互动实践过程:旅游为女性社会资本的积累提供了平台和支撑,而女性社会资本的积累又为旅游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和治理支撑。
在民族旅游活动中,女性旅游精英都很好地运用了社会资本的成功积累,并依此为依托对社会资本进行投资、利用和再生产从而扩展了自己的旅游事业。她们首先是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或者基础能力获得了少量的社会资本,如名气和良好的人际关系,然后充分利用她们个人所具有的人际关系达到互利的目的。和周围人合作的机会越多,就意味着围绕个人所结成的社会网络越密,资源交换的次数越来越多;资源交换的次数越来越多,就意味着她们个人拥有了更多的使用人际关系资源,编织了更加缜密的社会网络,然后她们都无一例外的对这些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进行了投资和再生产,利用到了自己的创业活动和场域转换中。如ZGL 在旅游表演和接待中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具有了一定名气,其社会关系网络也从亲属关系扩大到村庄邻居、朋友乃至市县政府,在地域性的社会联结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社会资本。她首先是确定了那些在短期内或长期内直接用得着的、能保证提供物质利润和象征利润的社会关系,如和县里的文艺团体、景区的管理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大家有表演活动自然想到她。久而久之,ZGL 将这些本来看起来是“偶然”的、泛泛之交的关系通过她自己经常的、有意识的“制度化”的建构,建立了长期的合作、信任关系,后来她将已有的这些社会资本进行投资、利用和再生产从而换取了新的成功:在创办风情园之时和之后,她通过各种社会交换和社会资本的联网,使自己的创业和经营之路颇为顺利。
当然,在众多从事旅游行业的女性中脱颖而出的女性精英毕竟只是少数,如何让更多的黎族女性在参与民族旅游的过程中利用地方性知识获得全面、可持续的发展,同时又能促进民族文化的延续与传承,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1]Van Den Berghe,P.L.Tourism and the Ethnic Division of Labor[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2(19):234-249.
[2]潘春梅.农耕社会中哈尼族妇女角色地位的演变——对元阳县箐口村的个案分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0(4):65-70.
[3]〔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M].王海龙,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204.
[4]K.D.Warren.Introduction:Emerging Principles in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M].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1983.
[5]Andrew Iirr.From Science as Knowledge to Science as Practice[M]∥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6]Lourise Grrenier.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translated by Catherine Porter[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
[7]〔美〕保罗·A·萨巴蒂尔.政策过程理论[M].彭宗超,钟开斌,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106.
[8]〔法〕皮埃尔·布迪厄.G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迪厄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02.
[9]〔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流行的狂热抑或基本概念[C]∥曹荣湘.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