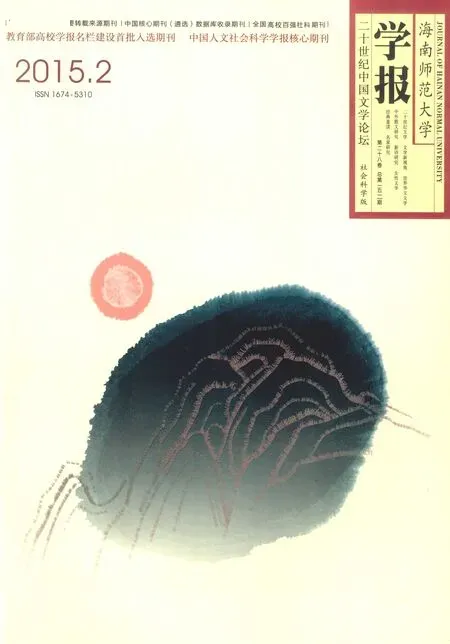历史小叙事中的温情记忆——程小莹长篇小说《女红》研讨纪要
2015-03-28杨剑龙荀利波
杨剑龙,荀利波,等
(上海师范大学 当代上海文学研究中心,上海200234)
引 言
程小莹先生有12年纺织厂的工作经历,他的长篇新作《女红》(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描写了转型后纺织厂工人的重谋生路,刻画了一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写出了不同命运的人物的自强不息。作家并不注重曲折跌宕的情节叙述,而把对生活、情感的回忆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细节中温情书写生活的记忆,在底层叙事中重现历史,以富有真味的语言叙写生活。他把大历史放进小叙事之中,打破了以往的启蒙叙事,推进了新写实小说的写实叙事,促进了方言进入小说创作。一个作家创作的最好动机可能是他不写不快,这种生活、情感、体悟等总积聚在心里,不写他总觉得这辈子都绕不过去。《女红》就是程小莹先生这种创作状态的作品。为了能对《女红》有比较全面的理解和把握,我们对该作进行了研讨。我们邀请到了作家程小莹先生、上海作家协会创联室副主任李伟长先生,参与研讨的还有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荀利波、王童、陈卫炉,硕士研究生金怡、赵敏舟、孙羽程、屠丽洁、丁莉华、严静、杨婷婷等。
一、故事讲述的独特方式
杨剑龙:小说从秦海花曾任厂长的纺织厂砸锭子写起,因砸锭激起秦海花的父亲退休老工人秦发奋的愤懑,导致秦海花的母亲老劳模吴彩球的心肌梗塞遽然离世。程小莹在设计这个惊心动魄的砸锭的开篇后,并没有将笔墨放在跌宕曲折的小说结构上,而是荡开一笔刻画人物性格、交代人物故事。砸锭的铁锤高高擎起却轻轻砸下后,作家以近似散文化的笔触叙写故事,将过去时的、现在时的和现在进行时的叙写交织在一起,写出了在纺织厂转型后纺织工人们的重谋生路。作家并不注重情节的曲折跌宕,而把生活、情感的回忆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
孙羽程:《女红》有几点非常特别:一是故事放置在上海市杨树浦,既有老上海的文化积淀,又深受改革开放的影响,主人公的活动带有上海人的独特个性。二是时代选择在20 世纪90年代初,中国步入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诸多企业转型、大量职工下岗,小说用一种比较温情的形式作了展现。三是行业聚焦的是纺织业,是90年代受到冲击甚大的产业。小说中反映出的设备老化、产品积压、市场混乱等,都是纺织业受到重创的原因。
屠丽洁:小说呈现出的不仅是上海的时代变迁,也是那个时代整个中国的时代变迁。作品聚焦于90年代初国企改制进程中的下岗工人,脉络清晰、叙事流畅。在国家记忆、城市发展、市民生活等多重背景中描述这个阶层的流散、重聚、自我在社会上位置的寻找,展现原生态的女工生活,敏锐地把握了时代脉搏,冷静地呈现了特定年代特定阶层的生存境遇,深刻揭露了时代和生活的本质。
陈卫炉:《女红》并非是一个以故事情节见长的小说。与传统工业题材小说基于生产矛盾、思想冲突、情节结构不同,《女红》的叙述空间不再局限于工厂车间,它进一步延伸到家庭、社区、街道,甚至境外。作者精心截取了诸多生活的横截面,摆脱了工业题材创作困于“车间一隅”的局限性。在小说中,工厂不再是城市的“飞地”,工人也不再是机器的附庸,取而代之的是两者内在藕断丝连的关系,宏大的城市气象因此得以表达。海草和马跃谈恋爱的襄阳公园、黄浦江边的原棉仓库,厂校教师薛晖进行社会调查的永福新里、定海桥复兴岛,小炉匠摆弄修车摊的杨树浦路,还有“两万户”工人新村等,给我们一种混沌繁杂的城市的整体感。读《女红》时,我也有疑虑和感叹,这么多生龙活虎的青壮年工人,面对巨大的社会断裂和人生的种种不如意,怎么会有如此平和的心境?似乎没有愤懑、痛苦和悲伤,只有繁复而顽强的日子,行云流水密密匝匝,是否将生活和历史的皱褶熨得太平、太光滑了?
李伟长:卫炉的问题很有道理,当文学面对社会重大题材的时候,它怎么反映这个世界。伤痛肯定是需要书写的,但是每个作家有他选择的自由,写伤痛并非评价的标准。你的问题非常到位——时代怎么去表现和保存这种记忆。这种伤痛会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它会被取代,但是这种记忆是肯定存在的,因为如果这种记忆不存在,也就没有《女红》这部小说。只不过程先生用另外一种方式把这种痛放在里面,放在砸锭里面,放在工人走出工厂之后的生活里面,包括放在秦海花身上,看上去是没有结局,这是一种唐·吉诃德式的拯救。
王童:陈卫炉谈到《女红》似乎回避了1990年代大批工人下岗的历史残酷性。在我看来,对于同一段历史,不同的作家会有不同的描述,作家们叙写历史的视角各异。譬如,柳建伟的《英雄时代》既揭示下岗生活的艰辛,也展现工人再就业的顽强。而程小莹则以温情的、平视的视角摹写纺织工人的下岗生活。其视角是温情的,作家并不正面揭露下岗带来的苦痛;其视角是平视的,作家并不作启蒙性的言说,而是平等地讲述纺织工人的故事。程小莹最想表现的,其实是秦海花、小炉匠等纺织工人身上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他们的精神不会磨灭,支撑他们走出“阴霾”,推动他们积极、坚强地活下去,这正是工人精神的价值所在,也是整部小说努力传递的内容。
二、细节中展现温情记忆
杨剑龙:小说写出了企业转型后纺织工人们的重谋生路:厂长秦海花创办了“布房间”集团,包括服装厂、养老院、健身娱乐中心等经济实体,吸收了一大批下岗职工;电工高天宝成为承揽电路工程的包工头;秦海草从日本归来后开设了酒吧;拉大提琴的检修工马跃组建了自己的小乐队;出生音乐世家的清洁工“大背头”开了修琴铺;机修工“小炉匠”上街摆修自行车摊头;宝宝阿姨开办了洗头店;杨彩娣等五人组办了“杨彩娣净菜小组”;厂广播台播音员石榴去了区有线电视台任主持……这些纺织厂的工人们在重谋生路的过程中,书写着各自不同的人生故事,突显走出人生困境的坚强与执著。
李伟长:文学有个很重要的功能是保存记忆。我写过一篇小文章《保存记忆》,作家保存哪些记忆是有选择的,比如现在重新谈到90年代工厂、纺织女工、工业文学,当然绕不过这部小说,因为作家选择了一种很细碎的方式保存这段历史的记忆。他作品里的细节非常细密,是湿漉漉的有润泽的细节。
王童:《女红》开篇部分别开生面、引人入胜。首先,小说开篇对生活场景的叙写达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精雕细琢的生活细节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活生动的生活场景给读者带来巨大的吸引力。其次,尽管开篇篇幅不长,但蕴含的内容却非常丰富。它一方面在生活流式的叙写中自然而然地介绍了人物身份,另一方面还交代了整部小说的时代背景和故事缘起。开篇叙事细密而不拖沓,内容丰富而不杂乱,设计精妙而不露骨,充分体现出作家的写实功力和精心构思。
程小莹:那个氛围和情景的写作是一气呵成的,然后不断地从里面拿掉一些东西,补充一些细节。本来是以对话为主的,后来加了一个细节——吊钩和馊饭。上海人吃泡饭就是这样,上海市民生活大致和泡饭有关。
荀利波:我注意到作品中充满温情的细节,父女之间、母女之间、姐妹之间、工友之间,特别是工人对工厂的不舍,太多这样温情的画面。不过,也有一些地方令我有些疑惑,高天宝每天晚上都要给老婆秦海花洗脚,这在我的家乡云南是不可能的事情,不知道安排这样的情节有何用意?
程小莹:这与高天宝的家庭角色有关。高天宝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他是招女婿,秦海花在外面做事业,他对秦海花形成了偶像式的崇拜,他是上海男人,他是会给老婆洗脚的。高天宝不只是一个上海小男人,他是有技术活的,他跟过一个名师——秦发奋,他在家庭的地位就决定了他可以为女人做一切。高天宝和秦海花之间的关系很微妙,是一种低潮,没有高潮,最后我给他设计一个意淫式的生活。他的太太秦海花当了厂长,他总是仰视她,他的角色决定了他就是这样的人。
我比较喜欢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叙事。回顾三十多年的小说创作,我从来不会做宏大叙事,但是我特别擅长细节叙事。我将散文化随笔式的细节叙述用在小说创作中,理所当然要回避宏大叙事。《女红》就是要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里面去呈现市民生活的细节,所以我选择了一个普通的纺织工人家庭,通过秦海花、秦海草牵出一些人来。我始终认为普通人的生活都是很平常的,大多数日常的生活都是零零碎碎的,如同将干馒头捏碎时掉下来的渣。我小说里有一个细节,秦海花去咖啡馆吃奶油蛋糕,她用手指把蛋糕掉下来的屑屑粒粒一一舔净,我喜欢把这些细节放进小说里,《女红》这部小说完全是靠八十多个细节在支撑。但又不只这些,有时会突然有灵感,如一粒芝麻从嘴里掉落很香,我就会立即写下来,考虑一下放在小说哪里比较合适,这种写作方式贯穿了我三十多年的小说创作。
三、底层叙事中重现历史
李伟长:这部小说是工厂小说,它的区域是泛化的,可以在上海,也可以不在上海。一个作家有他的态度,比如选择怎样的历史来写,选择怎样去构建这个历史。刚才杨老师提到的“砸锭”情节,可能在很多小说里面会作为非常重要的内容来写,而程先生只是很轻描淡写地把这么一个情节交待过去,从这一个选择就可以确定整部小说的基调,它选择的工厂历史是一种个人化的,是集体意识下个人生活的回忆或保存的记忆,这是该小说最独特的。
杨剑龙:许多作家写工厂、工人,大多是以局外人的身份来写,甚至是站在高处来写底层,有一种启蒙者的视角。读《女红》,能感受到作家是身在车间中间、工人之间,他可能就是小说中的李明阳、薛晖。他跟底层是平等的,他并未在启蒙别人。中国20 世纪文学的叙写基本是启蒙叙事,“五四”新文学是要启蒙民众,因此把文言文改变为白话文,文学创作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而《女红》让你感觉到作家的平等书写,它真正是一种底层书写。
陈卫炉:由于20 世纪90年代以来时代语境的变迁,人们开始关注公共舞台后的私人空间,努力揭示被“大写的历史”或遮蔽、或过滤、或忽视、或排斥的“小写的历史”的某些真实侧面,《女红》也表现出这种倾向。面对波澜壮阔的国企改革改制的历史,作家并没有展开短兵相接的正面强攻,而主要采用一种徐缓迂回的战术从容观照历史的暗角。小说有意避开对历史事件、企业重生、生产流程的叙述,而把笔墨集中在工人男女的爱情故事上,用逼真的生活细节映衬出时代变迁。工人个体独特的生命旅程和种种刻骨铭心的挣扎、努力,在作品中得以凸显,藉此可以见证和揭示曾经一度被主流叙事遮蔽的历史真实。
荀利波:这部小说讲故事的方式特别,我们如果不读完整部作品,就难以真正把握作品中的人物和理解作品的思想。小说着眼的是普通人的琐碎生活,如砸锭前秦发奋的喋喋不休,男女纺织工人相互间的揩油,上海民兵的高炮实弹训练,从硬纸片到塑料片的食堂饭菜票,霍山路的小地摊和擦皮鞋的技巧,乍浦路、外白渡桥、四川路桥骑自行车的感觉,765 荷兰头皮鞋,五角场附近透出粉色灯光的发廊,等等,都明显带有了个人回忆性的叙述。恰恰因为其个人性表述和底层叙事,让历史少了政治话语的冰冷,而多了些人的温情。
金怡:《女红》所描写的是上海下岗纺织工人面对新形势的困惑迷茫、失意与得意,但他们始终对纺织厂眷恋不舍,在历史转型期为市场经济的确立燃烧自己,历经艰难地破茧重生。这是可歌可泣的群体,又是很少被重视的群体。《女红》的面世对我们了解那一群平凡鲜活而可敬的纺织工人、了解新时期纺织业的发展历程有着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
赵敏舟:《女红》这部小说讲述的上海纺织业,其实可以扩展到全国纺织业,90年代初全国纺织业都发生了相同的变革。小说中纺织工人在下岗以后走了两条道路:一条是由秦海花、小炉匠等为代表的始终坚持着对工厂的热爱、并付诸实践之路;另一条是秦海草、马跃等为代表的脱离工厂之后、追随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之路,这两条道路虽然不一样,但却是那个时代背景下社会底层最真实的写照。
四、富有生活真味的语言
杨剑龙:文学作品往往写情写色,关键在怎么写。沈从文的小说常常写情色,小说《柏子》写水手跟妓女的交往,写得富有诗意。《女红》把纺织厂的生活写得也很有诗意,不仅是生活的诗意、感情的诗意,还有语言的诗意。程先生有时候恰到好处地运用了一些含蓄的象征的东西,很耐咀嚼。比如,说“在工厂里,男人像一只螺栓,旋入一只螺孔里;女人像一只螺母,旋在一只螺栓上。当然,那只螺栓或螺母,旋在那儿,即使生锈,也仍然是生动的。”他没有直接去写男女之间怎么样,而是用比喻、用象征。这样的语言在小说中有很多,读后就能感受到那种生活的诗意,用一种诗意的语言把底层生活的诗意写出来。程先生用含蓄的语言将生活的气息写得富有诗味,生活的情韵和诗意就蕴含于语言之中。小说里有很多上海话,读起来觉得很惬意,比如说“馊气味道”,北方人肯定说“馊了”,不会说“馊气”。小说创作的语言特别重要,人物性格要从语言里体现出来。语言最能表现出作家的才干,尤其是写底层生活。而最难的是写人物的对话,对话要切合人物的身份,要切合语境。这部作品的语言,好像是随手写下来的,但实际是经过深入推敲的,他写底层生活写得那么有诗意,离不开作家的精心营构。
丁莉华:《女红》精致的细节描写,处处散溢着生活的味道。小说写小炉匠砸锭后的揩车,“小炉匠揩得仔细,连罗拉里卷进的棉絮都一点一点地用指甲剥下来”,经历过工厂转型期的人,是多么的不忍和感伤,那种依依不舍之情,读来令人落泪。还有纺纱女工在纺纱时的情景,“她们的身心,缠绕在机器上。她们用眼睛注视,耳朵聆听,手指扯动着面纱或线,接头。纱卡和涤卡,是最多的产品;灯芯绒也很好”,散文化的笔调让工作时的情景富有柔美如水的画面感,将工人生活描述得毫无枯燥感,给人以美的享受。作家描写生活,巨细靡遗,一点一滴,极其精致地展现,似乎在雕琢一件工艺品,小心翼翼,温柔相待。
荀利波:《女红》的语言中洋溢着工人对工厂特殊情感的怀念,例如作品中写到小炉匠从“1973年开始,三班倒,二十多年”,早已停产砸锭前,他自己来了个交接班,像个仪式,“空推着两把大扫帚,在车间里走来走去,像梦游”,简单的几句话做铺垫,细致刻画了他对工厂的深厚情感。
陈卫炉:《女红》的语言是很有特点的:一是人物对话一般较多运用上海方言,但在描写、抒情的场合主要还是惯常的句式。二是大量短句的使用,使句式变化多样,避免了行文节奏上的呆板与单调,使小说语言变得简洁、准确,看似平淡无奇,却又韵味十足,形成了轻盈干净、自然流畅的语言风格。这实际上是一种散文化小说的叙述追求,与生活流的情节设置高度契合。
李伟长:语言体现的是一种思维习惯,它具有一种显性特征,比如“做生活”、“辰光”,这些词汇背后是用方言思考的习惯表现。2013年的《繁花》,2014年的《女红》,都有用方言写作的倾向。程先生在创作《女红》时,他常常就用上海话在思考,当然运用方言时,应该有创造性的改造,尽量完整地表达出方言的意思。《女红》很多对白实际上有上海话的特征,在叙述的背后也是用上海话进行思维的习惯体现。
程小莹:语言是最特别、最奇妙的,它是人的不同思维的体现。我在语言运用上十分在意。小说中用心最多的是开篇的第一句话:“她们的身心,缠绕在机器上。她们用眼睛注视,耳朵聆听,手指扯动着面纱或线,接头。”这段语言定下了小说的基调,此后便按照该基调进入叙述。我经常会用上海话思维,大多出现在对话中,在叙述中我尽可能用普通话思维。如果用上海话表达更准确,我会注意它的搭配,如“嫌贬”就特别准确地表达了上海话的发音和意思。
五、立体化的人物塑造
杨剑龙:小说中与语言同样重要的是人物。从文学理论来说有圆形人物和扁平人物,这部小说刻画了很多的圆形人物,其性格是立体的。比如说海花、海草,是性格迥异的两姊妹。秦海花,她在父亲的压力下跟父亲的徒弟结婚,她内在的那种心理的波澜、生活的磨折、倔强的个性得到生动的体现。而秦海草是活泼又充满野性的,碰到事情时她比男人还要男人。小说中很多人物并不是主角,但都被刻画得活灵活现,如小炉匠、北风等。小说虽然写的是企业的转型,但写出了人物在不同命运中的自强不息、挣扎奋斗。小说要讲述有意思的故事,80年代提倡散文化小说,我是不太赞同的。小说中的人物须是圆形人物,不能是扁平人物。小说开篇写老劳模吴彩球,虽然笔墨不多,但那种风风火火、爱厂如家、含辛茹苦的老工人形象却是立体化的。
荀利波:整部小说的人物关系简洁,增强了人物的艺术真实感。程先生力避人物关系的复杂化,整部小说有名有姓的人物约二十余人,以秦海花、秦海草的故事为主线,牵引出与她们有交集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服务于展现那个时代纺织工人们的特殊经历,人物关系结构的简洁化,避免了对主题的干扰。
严静:《女红》塑造出了一个个性格各异工人出身的男人、女人。程先生和王安忆笔下的女性形象是不同的,男性视角比较鲜明,城市的描写是女性化的,细腻而有温度;乐器是女性化的,有马跃对大提琴的拥抱、对手风琴的抚摸……女性形象的描写呈现出男作家眼中独有的美感,如马跃在择偶时对海草美中不足的“完美”的肯定,对北风的高挑身材的描写等,高天宝和马跃俩连襟对秦氏姐妹身材外貌的讨论更是惟男作家所为。
杨婷婷:这部小说写了很多女性,这些女性形象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以秦海花、北风为代表,另一类以秦海草、宝宝阿姨为代表。秦海花是一个深受传统观念影响的女性,她始终是隐忍的,她的隐忍可以说是出于对父亲的孝、对职工的责任,她的身上有一种牺牲精神,内心里有一股传统的力量在规约着她。北风身上有一股情欲的力量在蠢蠢欲动,但她始终选择了压抑自己,最后她把自己与现实生活隔绝开来。海草和宝宝阿姨都是敢于追求的女性,宝宝阿姨的不正经并不遭人嫌,她的身上反而透出一种看似傻傻的却又很单纯的可爱;海草的性子是泼辣的,有点野,海草的语言就很好地体现了她的性格。
李伟长:马跃这个人物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有一种非常自由的性格,他在工厂和离开工厂,精神上的东西实际上没有变化,马跃这个人物建立的精神的空间给小说带来很多温润的东西。秦海花这个人物,有的读者可能不喜欢,因为她可能有点正,甚至说没有其他人物那么温润。这个角色是作家自己很喜欢的,作家选择了书写个人记忆,这个角色融汇了作家的工厂情结。秦海花要适应社会转型和新的经济时代,她的知识、技能、观念等肯定会被淘汰,但是作者给她留了点希望。下岗女工也有后来发展得很好的,但那不是工厂的延续,它不是原来的那种机制、人情、伦理的延续。
程小莹:我作为一个男性对于女性是有态度的,在小说创作中追求人物的独特性和随机性。在创作过程中,有些人物不用设置就会突然冒出来,如石榴和宝宝阿姨,这些人物我几乎没有构思,她们在我心目中早已成型,她们会怎么说、怎么做,包括对马跃情感上的温情,这与生活有关,因为我长期泡在女工堆里,早已司空见惯。但是当用文字叙述时,是可以制造出美感的,有时是神来之笔,有时早已烂熟于心,如大背头,他会修琴、教琴,和马跃讲许多道理。马跃是我心目中比较理想化的人物,他本身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有自己的精神空间,他是可以自己和自己玩的人,可以在他身上寄托很多理想化的东西。
小说人物方面我花心思最多的是秦海花。我也承认在细节的分寸度和情感的饱满度上她可能不及妹妹秦海草,她很容易被写成符号式的人物,但是我又特别想把这样的人物写好,保持对人物基本的态度——温和、理解和宽容。考虑到小说篇幅有限,人物不能太繁杂,也就18 万字和两条线索。小说就是把一盘子人弄得活起来,说点有意思的事情,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觉得这就是写我生活中的记忆。
六、《女红》的叙事价值
李伟长:小说可能不是尽善尽美,在结构上实际是有点问题。从开篇的架构到最后的结束,程先生虽然用了很多技巧性的东西来缝补这个结构,但是实际上在小说中间还是有些断痕。和秦海草甚至北风相比,秦海花这个角色其实有点平,北风这个角色虽然没有多少篇幅,但是很多细节会立马让你记住。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但是一些有生命力的细节却是无法虚构的。这种细节可能是听来的、看来的,或自己生活中感受来的,秦海花的细节远远没有海草、北风、宝宝阿姨那么丰满、有光泽。这是一部有上海特征的小说,这部小说肯定会被记录进文学史。
杨剑龙:当下小说创作中有一种现象——奖项创作,他的创作开初就准备奔文学奖而去的,比如茅盾文学奖,那么他写的小说一定要厚重,可能小说二三十万字就够了,却一定要写成五六十万字。还有一类小说创作是奔市场而去的,为迎合市场要掺进各种各样的调料,比如性爱、比如情色、比如警匪。但这部《女红》,读完以后就知道就是写作家心中生活的回忆,就奔他心中郁结的丰富人物而去,奔他心中积淀的情感而去,奔他心中留存的生活而去,他就是想把他们写出来,我觉得这种写作是最真实的写作,但现在我们这样的写作太少了。
现实是残酷的、回忆是温馨的,我们的记忆被岁月过滤了,就像一张发黄的老照片,痛苦被滤去了,留下的只是温馨,这部小说呈现的温情书写可能也因这种过滤。如果我们把《女红》放到中国小说发展的轨迹中来看,体现出显著的叙事价值。
一是从30年代茅盾的《子夜》用宏大叙事写工厂,到穆时英《南北极》在左翼文学影响下写有点反叛精神的工人,再到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写社会主义改造,再到俞天白的“上海三部曲”,中国工业题材的写作整体上是一种宏大叙事,而《女红》却是从小叙事的角度来呈现纺织工业转型历史的,作者把大历史放进小叙事之中,是一种个人化叙事,打破了以前的大叙事的构思,这是这部作品的一个特点。
二是从底层的生存状态角度书写,打破了以往的启蒙叙事。中国文学从“五四”开始基本上是一种启蒙叙事,居高临下启蒙民众,《女红》的作者本身就站在底层,从底层写底层,他没有想去启蒙什么,用底层生存状态的叙事来打破传统的启蒙叙事范式。
三是我觉得这部作品从原生态的角度推进了80年代新写实小说的写实叙事。80年代新写实小说的特征是原生态,当时有人评价说是零度写作,我是不赞同的,作家不可能零度写作,他的情感、观点都会融入创作中。
四是这部小说以沪语化的写作促进了方言进入小说创作。怎样让方言进入写作?晚清时候有些小说用江浙方言写作,从某种角度推进了语言的传播,我们现在的东北话、陕北话都进入了小品、相声、电影等,与这些话语跟北方话语比较贴近有关。上海话跟北方话语有点隔阂,作家在创作时总会斟酌什么时候该用上海话,给北方人读,能读懂吗?作家用上海方言时也是费尽心机的。
虽然这部作品并非十全十美,但从以上四个方面来讲,这部作品显示了它的价值。
(讨论稿整理:杨剑龙、荀利波、丁莉华、杨婷婷、严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