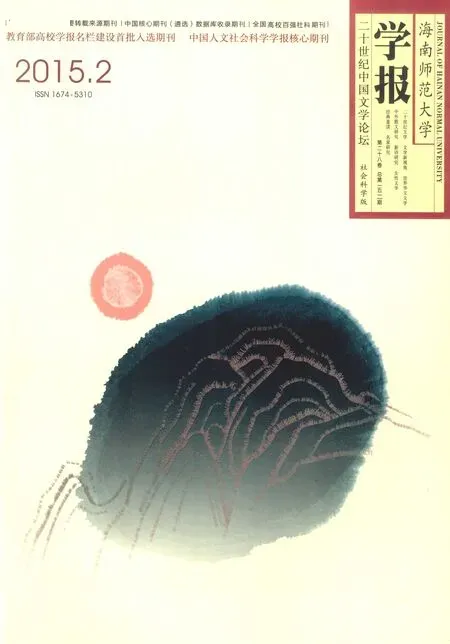“历史的态度”与“艺术的态度”:胡适、王国维文学批评方法之异同
2015-03-28牟利锋
收稿日期:2014-10-23
作者简介:牟利锋(1974-),男,陕西宝鸡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
大谈科学方法的重要,几乎成为胡适一生谈学衡文的标准和信念:“一种科学的精神全在他的方法。方法是活的,是普遍的。我们学一种科学,若单学得一些书本里的知识,不能拿到怎么求得这些知识的方法,是没有用的,是死的。若懂得方法,就把这些书本里的知识都忘记了,也还不要紧,我们不但求得出这些知识来,我们还可以创造发明,添上许多新知识。” [1]350由于提倡方法的自觉,后来学者甚至毫不迟疑地将胡适与他的弟子划归“方法学派”。但是,胡适所谓的“方法”具体如何界定,却莫衷一是。一方面因为胡适在不同的语境下所提倡的“方法论”,内涵显然不一致,徒然增加了接受者的困难;另一方面对胡适的“科学方法”真有心领神会者,也许出于立场的不同,又往往曲为之说,于是乎胡适的“方法”便在众说纷纭的热闹场面之下如坠云里雾里,难见庐山真面目了。胡适的“科学方法”到底何指?作为对现代中国学术影响之巨的方法论,它与王国维等人的研究观念和思路又有何不同?我们不妨从两人互文性的文学批评入手作一比较。
一、胡适的“科学方法”
1921年7月,杜威在中国讲学两年多后启程回国。胡适在论定恩师的影响时,特别指出他“给了我们一个哲学方法”,即“实验主义”。“实验主义”的方法主要包括两步:第一是“历史的方法”;第二是“实验的方法”。胡适乐观地相信,如果这种“历史的观念”与“实验的态度”能成为“思想界的风尚与习惯”,那么杜威哲学的影响力“恐怕我们最大胆地想象力也还推测不完呢” [2]279。这里已经系统地提出了“历史的观念”与“实验的态度”的说法。后来《读书杂志》从1923年开始刊载顾颉刚、钱玄同、刘掞藜、胡堇人讨论古史的文章,胡适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读后感大谈方法的重要,并且自称这要算是他《文存》里“最精彩的方法论”。胡适特别强调:“这里讨论了两个基本方法:一是用历史演变的眼光来追求传说的演变,一个是用严格的考据方法来评判史料。” [2]516可以看出,胡适所提倡的“科学方法”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其一从思维术的角度来说,“科学方法”指的是一种历史的态度或者观念;其二从具体的操作方法角度来说,“科学方法”指的是一套有章可循的方法体系。胡适也正是在从以上两个层面的意义上,分不同的场合使用“科学方法”这一概念。这也许就是他的“科学方法”不断被人误解的主要原因。
许冠三对胡适的“科学方法”有如下一段颇为精当的概括:“综观胡适一生所宣讲的‘科学方法’,实在可分思想学问历史研究两类七门,其含义的广狭和造诣的精粗彼此相去甚远。前者通常又称杜威思想五步术,或工具主义、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在突出它的科学性格时,又名之为实验主义的学问方法,要素有二:一是原于物理学、化学研究的‘科学实验室的态度’;二是古生物学、地质学研究,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历史的态度’,有时亦不恰当地称为‘历史的眼光’或‘进化的观点’。至于历史研究方法,他根柢最深的是以校勘训诂为本的文献材料整理术;他在各种考据文章中经常涉及的,是以内外考证为主的史料审定术;可说得上是他发明的,则是‘历史演进的方法’,(井田辨)和诸小说考证皆用到这一迷人的方法。” [3]所谓“杜威思想五步术”虽然名之曰“术”,其实不论是实验室的态度还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指的都是一套方法的五个具体步骤;而“历史研究方法”,虽然称之为“方法”其实则是一种思维术。所以在具体的分析中,胡适“科学方法”所包含的双重意义或者内涵,在命名上多有混淆,不过两类概念实质上的区别,依然泾渭分明。
二、何谓“历史的态度”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胡适的“科学方法”包含两个层面,其中作为具体操作方法的一面最为大家所熟知,也似乎成了胡适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看家本领”。不过真正称得上是胡适独创的也最富革命性的概念莫过于他所提出的“历史的态度”(或观念)。“历史的态度”首先体现为一种考察问题的视角:胡适认为这“就是要研究事务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样子” [1]212。在阐述詹姆斯“真理论”时,胡适也指出“这种真理论的注意点在于真理如何发生,如何得来,如何成为公认的真理” [1]222。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历史的态度”其实就是一种“发生学”的考察。其次“历史的态度”也指以历史演进的观点来观察史实。胡适对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大加赞赏,简洁明了地称其为“剥皮主义”,并在此基础上抽象出一套考察古史的方式:(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4]82顾颉刚后来也承认自己“层累的造成古史说”受胡适“历史的态度”影响最大,而他所理解的科学方法也就在于“寻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的关系,不把它看成突然出现的” [5]。这种“历史的态度”作为一种方法其实重在历史事件“过程”的梳理。胡适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自己关于历史“多因论”甚至“偶然论”的观点,而反对“单因论”或“决定论”的提法。在他看来,要想了解一件历史事实的真相,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客观地分析其前因后果,而不要急于得出一个抽象的结论。当然更不能先入为主,按照流行的“主义”或者“规律”来任意剪裁史实。真正的规律就在史实之中,在个案之中,无烦深求。后来余英时有一句名言“历史无成法,但历史有成例”,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早在留美之初,胡适在日记里提到“今日吾国之急需三术”,其中之一便是“历史的眼光”, [6]但是真正促使胡适将“历史演进法”作为一种方法论来考虑的还是后来接触到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的生物演化学说,给我们一个大教训,就是教我们明了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所以是一种很复杂现象,决没有一个简单目的可以一步跳到,更不会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变。” [2]508由此出发,胡适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与实验主义是两种完全不“相容”的态度,中间只因为隔着一层“达尔文主义”。而达尔文进化的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出现了一种“历史的态度”。 [1]212前面我们说过,胡适的“科学方法”作为“思维术”要远比“方法体系”精彩,那么再推一步,具体到作为“思维术”的“历史的态度”上面,则“过程论”比“发生学”更具胡适特色,也更具魅力。而胡适对这一方法的应用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
早在《井田辨》一文里,胡适就已经开始用“历史演进法”来处理这一争议颇大的课题。此后在倡导“整理国故”的过程中,胡适便系统地提出自己的“方法论”:“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因为前人研究古书,很少有历史进化的眼光的,故从来不讲究一种学术的渊源,一种思想的前因后果,所以第二步是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因为前人读古书,除少数学者以外,大都是以讹传讹的谬说,——如太极图,爻辰,先天图,卦气,……之类,——故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因为前人对古代的学术思想,有种种武断的成见,有种种可笑的迷信,如骂杨朱、墨翟为禽兽,却尊孔丘为德配天地,道冠古今!故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 [1]557这种“历史的态度”几乎成为一种癖好,促使胡适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研究对象总有从中找出一个有条理的线索的冲动。研究“禅宗史”引以为豪的是他提出的“纲领”,“似乎能成一个有线索的故事了”; [7]263而《〈四十二章经〉考》中最终解决“浮屠”与“佛”的关系问题靠的也正是“历史演变的观点”。
不过,在我看来,胡氏“历史演进法”最为精彩的展示当推他的文学史研究。胡适向以半部书专家著称,《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中国文学史》均有头无尾便是明证。不过这也大半和胡适的自我期许有关。胡适欣赏的是“但开风气不为师”,至于如何善始善终以竞全功并非他的用力所在,但这不意味着此后胡适停止了相关问题的思考。只要我们稍加留意,便可以从其随后的著作中整理出另外半部书各自的线索。唐以后的“白话文学史”胡适自然选择以“小说”为核心,不过相对于上半部的条分缕析,小说的梳理显然有点大刀阔斧的味道。而胡适在此最大的创新就在于以“历史演进法”提出了中国白话小说历史发展的“四期说”:历史演义为第一期,如《三国演义》;“真成了文学的一大门类了,便能使文人学士起敬重之心了,这是小说的第二期”,如《水浒传》《西游记》之类;有著者姓名的小说为第三期,如《水浒后传》《儒林外史》《红楼梦》《镜花缘》;清末“吴趼人、李伯元、刘鹗一班文人出来,专做社会小说”,这是小说的第四期。 [8]而从体裁上看,胡适认为先是演义体、然后经过历史小说、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的小说《水浒传》,最后到了自然主义的杰作《金瓶梅》,中国的白话小说才完全成立。另外,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胡适还提出两个极具包容性和解释力的概念,即“母题”和“箭垛式”人物,这也与其历史演进法密切相关。胡适认为传说的生长就如同滚雪球一样,最初只有以简单故事为中心的“母题”,“后来经过众口的传说,经过平话家的敷演,经过戏曲家的剪裁结构,经过小说家的修饰,这个故事便一天一天的改变面目,内容更丰富了,情节更精细圆满了,曲折更多了,人物更有生气了。” [7]382《三侠五义》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楚辞》研究中,胡适又语出惊人,认为屈原不过是个“箭垛式”人物,与黄帝周公、希腊的荷马同类,并非实有其人,因为“后人感恩图报,或是为便利起见,往往把许多发明都记到一两个有名的人物的功德簿上去” [4]74。
三、胡适、王国维文学批评观的异同
1935年在给任访秋的信中,胡适谈及自家《词选》与王国维《人间词话》的不同,有这样一个评价:“静庵先生的见解与我的不很相同。我的看法是历史的,他的看法是艺术的,我们分时期的不同在此。” [9]《人间词话》被认为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文学批评”,也是“开发性灵”的“一把金钥匙”, [10]但胡适却坦言在王国维“死前竟未见过此书”。不过让我们感兴趣的,还是胡适提出的两人对词的不同看法,即“历史的”和“艺术的”,并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自家观点的充分自信。胡适与王国维对词的不同看法主要体现在分期上。胡适将晚唐到元初的词分为三个段落,即(1)歌者的词(晚唐到北宋初年),(2)诗人的词(北宋到南宋末年),(3)词匠的词(宋末元初),而划分的标准即“历史的态度”,具体地讲就是所谓的“双线文学观”:“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久而久之,文人学士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采用这种新体裁来做他们的文艺作品。……但文人把这种新体裁学到手之后,劣等的文人便来模仿;模仿的结果,往往学得了形式上的技术,而丢掉了创作的精神……文学的生命又须另向民间去寻新方向发展了。” [7]550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也有着明确的文学演进的历史观:“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 [11]由四言而五言、而七言、而律绝、而词,王国维的文学演进观明显以“文体”为中心,而这种“文体代变”的观念背后,其实还是他的“境界说”。“因为‘真切之感受’与‘真切之表达’既是欲求‘有境界’的重要条件,而一种文体‘通行既久’成为习套之后,则它便只成为后来人模仿之习套而不再适宜于创造了。” [12]因此在词的分期上,王国维并未标新立异,沿袭北宋南宋的断代法,只是在论述时明显流露出尊北宋而抑南宋的倾向。胡王二人之所以在词的分期上出现上面的差别,其实与他们各自的文学观念密不可分。胡适重在描述词的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即如何发生、如何发展,而王国维的目的则仍在借分期阐发自己的“境界说”,态度上一重“历史”,一重“艺术”,胡适的这个评价是大体不错的。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胡王两人不但对词的研究有着共同的兴趣,并且都对《红楼梦》发表了精彩的看法,各自开创了一个新的传统。在我看来,用“历史的态度”与“艺术的态度”概括两人在《红楼梦》研究上的特色也是不无恰当的。《红楼梦评论》最初发表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的《教育杂志》,比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都要早十多年。《红楼梦评论》一文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借用叔本华的哲学及美学观点,特别是悲剧哲学概念来解读《红楼梦》。按照叔本华的观点,悲剧大致有三种:其中“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大贤于前二者远甚。” [13]王国维认为《红楼梦》即为这种彻头彻尾的悲剧中的悲剧。虽然《红楼梦评论》被誉为一部真正的开山之作,它的精神与眼光,方法与态度为后来的《红楼梦》研究开无数法门,但如果退后一步,拉开距离,我们便会发现《红楼梦评论》似乎仅仅限于文本分析,并由此表现出一种拘泥于文本,太过相信文本的倾向。一个最为明显的缺失就是对《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来龙去脉未做任何辨析便用做评论的依据。更有甚者,王国维直认“宝玉”之“玉”即为“生活之欲”,以“欲”解“玉”,这种牵强附会已经有几分“索隐派”的味道。
可以看出,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相比较,不论是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还是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都局限于文本本身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两者都属于“大批评”的范畴;而胡适的特点则在于跳出文本,考证作者与版本。一重文本,一重作者与版本背后,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也即前面已经谈到的“艺术的态度”与“历史的态度”。从“艺术的态度”出发则注重文本本身意义的挖掘,从“历史的态度”出发则偏重于探讨文本的来龙去脉与上下四方的关系。两者相比较,艺术的批评往往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也容易引起轰动效应,而历史的考证则显得相对平实一些。艺术的批评因为多从文本出发阐释意义,所以很大程度上受社会思潮与风尚的牵制,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批评”;历史的考证,材料是关键,因此随着新材料的出现,早先的结论也会被不断修正。不过,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得出的基本结论——“自传说”毕竟提供了后来《红楼梦》研究的基础。所以即便是对胡适的考证不甚满意的余英时,在他提出的红学“新典范”中,也无可讳言地“偏袒‘自传说’而远于‘索隐派’”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