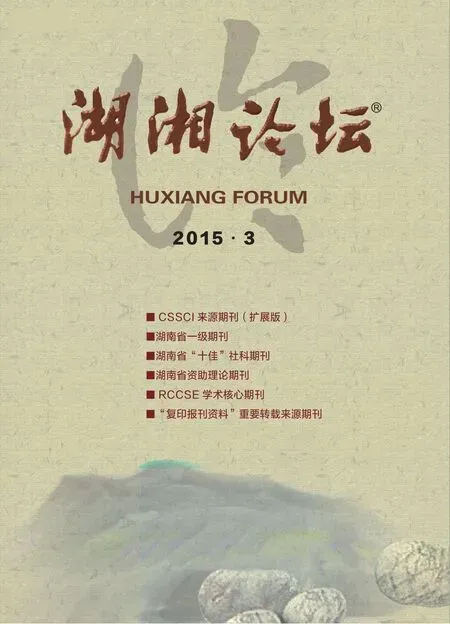从胡塞尔的先验自我到自我的超越性——萨特建构现象学本体论的初步尝试
2015-03-28陈攀文
陈攀文
(吉林大学,吉林 长春 130012)
通过对纯粹意识内部结构的描述,胡塞尔建构出了独特的现象学本体论。对于胡塞尔的现象学,萨特起初对之颇为赞赏。他认为,现象学的魅力在于它对纯粹意识之内部结构作出的独创描述。但是,萨特并非完全认同胡塞尔的现象学观点。萨特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本体论难逃阿喀琉斯的脚踵之灾。这一祸根即胡塞尔意识结构中的先验自我。在《自我的超越性》中,萨特改造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本体论,对意识的内部结构作出了考察和梳理,进而重构了自我的超越性新图式,确立了现象学本体论全新的出发点。
一、胡塞尔先验自我的困境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将“实体”归入“十二范畴”中的“关系”范畴。而范畴在康德哲学中仅只是纯粹思维的外显形式,因而从表面上看康德的“我思”存在笛卡尔思维主体的印迹。但康德并未像笛卡尔那样赋予“我思”以形而上学实体之内涵,而只是把它看作向所有可能性经验对象提供统一性的一个纯粹统觉和终极解释。康德断言,“由于产生出‘我思’表象,而这表象必然能够伴随所有其他的表象、并且在一切意识中都是同一个表象,所以绝不能被任何其他表象所伴随。”[1]P89然而,正是“必然伴随”这一结论,成为了现代哲学发展的一个潜在障碍。我们可以看到,新康德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布罗沙尔式的理智主义都掉入了这一陷阱。胡塞尔早期自以为豪的现象学本体论也在这里深陷泥潭。
对于康德“必然伴随”的论断,胡塞尔在《观念Ⅰ》中做出了不同的解释。“纯粹自我在一特殊意义上完完全全地生存于每一实显的我思中,但是一切背景体验也属于它,它同样也属于这些背景体验;它们全体都属于为自我所有的一个体验流,必定能转变为实显的我思过程或以内在方式被纳入其中。”[2]P174-175在胡塞尔看来,超越论层面的纯粹自我是经现象学还原作用于经验自我后而得出的。一方面,纯粹自我是现象学先验还原之后的剩余项,显现出一种独特的超越性;同时,鉴于不同的体验流,又存在着本质上不同的纯粹自我。这就是说,胡塞尔把“自我”纳入到了纯粹意识的内在结构之中,并加之实体化意蕴。如果说,胡塞尔在这个阶段只是含沙射影地倾向于认为,自我必然伴随着所有的意识现象,自我、我思与我思对象是三位一体的统一整体。那么,在《笛卡尔沉思》中胡塞尔进一步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宣扬这种论调。他指出,先验自我与其各种体验密不可分,是各种经验之轴。但这一处于中心轴的先验自我并不是同一性之空虚的一极,各种习性必须奠基于“先验自我”这个载体。这就是说,先验自我历经意识行为之后就获得了崭新的持久性质。因此,历经意欲决定和价值判断的过滤,先验自我就被建构为一个固定的位格化的自我。也就是说,在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的构想下,自我不仅拥有康德哲学意义上的能够为自身意识提供同一性的纯粹形式,还是一个各具经验内容的莱布尼茨单子式的具体个体自我。
但是,萨特认为,胡塞尔对康德这一哲学观点的解读过于浅显。胡塞尔没有理解到康德哲学中先验意识和经验意识的可分离性。正如海德格尔在《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中所指出的,依据康德的见解,“我意识到了一切行为与我的自我的联系,也就是说,我把自己在其杂多性中的一切表象意识为我的统一,该统一在我的自我性自身中有其根据。”[3]P167而且,先验自我综合着所有表象,具备了统觉的原初性特征。自我作为统觉的原初性的综合,是所有存在之物的存在论根据。所以,“自我”也就拥有了区别于被表象对象的先验性。从本质上看,“自我”在康德先验哲学中具有先验的人格性特征。“自我”始终是主体、自我-主体。康德正是觉察到了存在“无人称的我思”的意识才宣称“必然能够伴随”的论调。而萨特却认为,按照康德的构思理路,“必然能够伴随”问题在先验意识中并不存在,而只有进入经验意识领域才会发生。其中的缘由就在于,先验意识对康德而言“只是一种经验意识存在的必要条件的总体。这样,实现先验的我,使之成为与我们的诸多‘意识’中的每一个都密不可分的同伴,就是以事实而不是以权力来进行判断,就是立于与康德完全不同的观点。”[4]P4-5依据于此,萨特态度鲜明的指出,胡塞尔将先验自我统摄进纯粹意识之内部结构的举动不仅缺乏说服力,而且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
胡塞尔将先验自我统摄进纯粹意识之内部结构的举动导致的理论缺陷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把“先验自我”统摄进意识的内部结构破坏了现象学的明证性。现象学分析的首要特征就在于它所坚持的直观明见性。在胡塞尔那里,意识具有指向性的意向性特征,是不能再有任何内容的绝对虚无。萨特把胡塞尔的“明见性”称为“透明的”、“清澈的”。于是,萨特把意识界定为一种非实体性的绝对,一种自我规定的全部清澈的透明的东西。而非透明的实体只能在意识之外存在。然而,一旦将先验自我统摄进意识的内部结构之中,意识就客体化为厚重而有份量的东西,由虚无变成实有。萨特由此宣称:“先验的‘我’,就是意识的死亡。”[4]P8其二,“先验自我”存在笛卡尔哲学式错误遗迹。萨特洞察到了笛卡尔哲学出现困境的祸根就在于他首先将“我”和“我思”界定在同一层级,进而又将二者撮合起来并视为一切哲学思考之基础和出发点。在萨特看来,胡塞尔在意识结构内部构建“我—思—对象”结构体系的举动重犯了笛卡尔哲学之错误。意识的含义就在于其超越自身而指向外部世界。但意识在胡塞尔那里并没有超出“我思”领域,其指向之物只不过是“我思”范围内的“物”。然而,我思范围内之物仅只是胡塞尔借助“反省的我思”构筑出的先验客体,根本不是对外部现实世界的意向。由此,萨特指出,虽然胡塞尔通过分析批判笛卡尔的“我思”建构出了“先验自我”理论,并试图借助现象学还原方法去过滤笛卡尔哲学中的实体主义和经验主义成分的哲思理路是可取的。但是由于胡塞尔在“我”与“思”之间的界限上态度暧昧,必然导致他现象学哲学思想发展的倒退。其三,“先验自我”必然陷入唯我论困境。萨特认为,胡塞尔现象学还原方法的本意是试图将哲学之基点最终回溯至纯粹意识层面,那么在意识的背后再外设“先验自我”就是一种画蛇添足行为。因为一旦将先验自我统摄进意识的内部结构,就无法确保“自我”以意识之对象的身份外显于意识面前,“先验自我”只能作为意识活动背后的推力,结果必然致使现象学无法对“自我”作出本真的描述。这样,现象学还原仅止步于“先验自我”这一“终极因”层面,俨然成为了一个外在于世界的创造主体。在萨特看来,胡塞尔在《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以及《笛卡尔沉思》中所做的驳斥并未触及唯我主义。“当‘我’(Je)始终是意识的一种结构时,那意识与其‘我’(Je)一起和所有其他存在者的对立就总是可能的。最终,是‘我’(Moi)创造了世界。”[4]P45可见,“自我”只能设定没有任何预先存在的客体,一切都是“自我”创造的结果。
二、萨特对自我的超越性图式的重构
在这样的境遇中,现象学的发展是否意味着放弃建构超越论的自我论之路?放弃这一建构径路又是否意味着要回返康德之路?但是回到康德又未能如胡塞尔那样对自我作出具体的人格说明,而只能达至对主体的纯形式层面理解。基于这样的情势,萨特对意识的内部结构作出了反思。萨特对胡塞尔超越论现象学的层层批判,目的在于为把先验自我从胡塞尔意识结构体系中清除的做法寻找合法性,进而重构一个自我的超越性新图式。
萨特在对胡塞尔的批判中指出,把先验自我统摄到纯粹意识的内部结构中的举动破坏了现象学的本意。在萨特看来,实体主义色彩浓厚的“我思”只是次阶的意识。在此之前还存在更高阶的意识状态,即“反思前的我思”。在此基础上,萨特建构了一个以“反思前的我思”为起点的超越论自我图式。首先,存有一反思前行为,在这一行为内部已经有对于意向的对象的意识存在,但还没有“自我”的意识。接着,未被反思的意识便成为反思意识之对象,但意象的对象在这时仍然还存在;伴随着这个过程,出现了另外一类对象,那就是“心理自我”(Je/I)。它既不属于反思前就存在的意识,也不是未被反思的客体对象,而是处于超越性位置的存在。这一超越论自我必须借助现象学还原方法才得以呈现。当然,萨特毫不含糊地抵触第三种形式的“我”即先验意识的存在。因为在萨特看来,横贯在反思的“我”与被反思的“我”之间的先验意识会阻碍二者的交流,从而割裂作为整体的“我”。
按照胡塞尔的观点,“先验自我”是纯粹意识内部的一种本质属性,纯粹意识一旦缺失了先验自我就会丧失应有的活力。萨特则赋予了“自我”以全新的超越性意蕴。萨特依据自我的不同功能,将其区分为“心理自我”(Je/I)和“心理-身体自我”(Moi/me)两个方面。心理自我和心理-身体自我是同一自我(self)在不同层次的呈现。从总体上看,萨特的自我是行动、性质与状态三者的统一。“行动”是一种主动性意识,当其与对象相结合时会变得暧昧不清,所以这种主动性又必须在反思活动中才能呈现。“状态”则是呈现于反思的意识之中而成为直观之具体意识的超越性统一对象。当然,自我要直接成为状态与行动之超越的统一,还需要“性质”这个中介。“性质”是能够即刻当下化,从而对状态与行动生发影响的超越性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自我的这种统一显然已经越出了自身,变成了超越性综合的一个“极”。在非反思领域,意向对象作为这样的“极”以第一梯级活动的样态汇聚于意识之中。但在反思领域,显现的自我作为如此之“极”处于反思样式的第二梯级活动中。所以,在萨特看来,自我和诸种心理状态之间呈现的并非外在性关系,却是一种同谋。这种同谋表现为,自我是一个不能与意识相等同的超验的存在,而是像与任何其他客体一样,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件。
自我虽然对于其所聚集的状态来说是一种超越的存在,但并非空洞的抽象“极”,而是一个统合了各种状态与行动的无限整体。这种“自我”在反思中与世界一道出现。自我一方面可以是单纯行动的“我”(Je/I);另一方面,自我也可以是整合了状态与性质的“我”(Moi/me),二者既可以在反思活动中合为一体显现,也可以作为被反思意识之意向对象间接出现。因此,萨特借鉴海德格尔“世界”这一概念去阐释“自我”与各状态的相互依存性。“世界本身不是一种世内存在者。但世界对世内存在者起决定性的规定作用,从而唯当‘有’世界,世内存在者才能来照面,才能显现为就它的存在得到揭示的存在者。”[5]P85这就是说,区别于世界的隐蔽性特征,自我总是能够在状态的境域中显现。每一种状态或行动只有脱离了自我的抽象化才能够存在。当然,“自我”之直观提供的东西不可避免地遭到先前直观的诘难,而且绽露出先前的样子。但自我的这一可疑的超越性质并非指存有一个超出我的意识之外的真实“自我”(Moi/me),只是指被意向的自我自身带有可疑性质。被意向的“自我”(Moi/me)是我的状态与行动的自发超越的统一。因此,自我并不是一种假定。我在此并非要去为我的各种状态找寻统一的意义。当我把我的各种状态归入“自我”(Moi/me)之中时,我并没有为其增加任何新的东西。实际上,自我与性质和状态之间呈现的是一种“诗意创造的关系”[4]P29
那么,这样一种创造关系又如何得以实现的呢?萨特首先指出,每一个新状态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通过性质与自我在根源上互相结合。显然,这种创造关系是一种在虚无境况中展开的创造。因此,状态并非曾经在“我”(Moi/me)之中存在。反思的统一活动将每个新的状态与作为具体整体的“我”(Moi/me)相结合。很明显,行动和我(Je/I)之间的关系也同出一辙。对于性质来说,虽然“我”(Moi/me)的性质由它们规定,但自我仍并非以“我”(Moi/me)这种状态而存在。恰恰相反,自我能够保持自身之性质是透过连续真实的创造而实现的。但是,这个自我并非性质之外的创造性源泉。自我的这种潜能历经层层剥离之后,已经丧失了所有性质。在萨特看来,“‘自我’是其诸多状态的创造者,并且‘自我’通过一种保守的自发性支持其各种性质。”[4]P30自我的创造是自发的诗意性创造。这种自发性以综合的方式与他物相关联而又避开自身。如此一来,由自我所创造的东西总是能够超越自身。而意识正是这种创造性的灵感之源,其在创造的过程中位居首列,状态借助于意识而被建立起来,自我又借助状态而得到创建。意识保留了自身之自发性特征,并将其切入自我之中,为自我的创造力准备了一个绝对且必要的合法性支撑。尽管意识历经自我逃避后,其自发性遭到削弱,但仍未遭致自我的侵蚀,意识仍然留守住了创造性功能。在这样一种创造性中,“自我”的非理性特征就显现了出来。意识的自因作用在这里得到了凸显,“自我”正是凭着意识的这种功能而在世界中与众不同。
三、超越论自我的效应
萨特通过对胡塞尔“先验自我”的层层批判,回溯到了胡塞尔对纯粹意识的最初界定之中,重构了自我的超越性新图式。这对理解现象学本体论由胡塞尔向萨特的嬗变提供了一条清晰的理路。萨特基于自我的超越性新图式的致思理路,不仅为其现象学本体论划定了一个逻辑起点,而且,消褪了胡塞尔现象学本体论饱含的唯我论与先验论色彩,并使之介入生活、诉诸行动。
一方面,萨特将意向性确立为纯粹意识的核心内涵,并把其与非反省意识置于同一层面进行思考,为其现象学本体论划定了一个逻辑起点。萨特认为,纯粹意识作为一种非反省性活动,只能透过意向性加以规定。因此,胡塞尔完全没有必要对意识的结构作过多的描述。“现象学并不需要求助于这个进行统一和个体化的‘我’。的确,意识是被意向性所规定。通过意向性,意识自我超越,并且在自我逃避中统一自己。”[4]P39按照萨特的看法,意识并非万物之载体,而是一个虚空。由此可以看出,萨特对意向性问题的解读与胡塞尔的理解出现了异议。依胡塞尔所见,作为纯粹意识内部结构的意向性,其归属必然是先验自我;然而在萨特看来,意识中不容任何其他内容的存在,意向性即纯粹意识本身。胡塞尔在意向性原则上没有彻底坚持他最初的立场。原因在于胡塞尔的意向性仍然局限于“先验自我”这一领域中。换句话说,作为意识活动主体的“先验自我”构造出了意识活动之对象。这样,意识活动不仅构造出了作为事物之意义的观念,而且也构造出了现实之物。萨特指责胡塞尔把意向性视作所谓的意识的构造功能,并认为是贝克莱主义的翻版。胡塞尔“把‘作为对象的意识’看作一个非实在,一个‘作为活动的意识’的相关物,而且它的存在就是被感知,从这时起他就完全背弃了他自己的原则。”[6]P20
当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分歧,归根结底就是二人在对“自我”问题的理解上各持己见。正如萨特所言:“被任何自我论结构所纯化的先验领域都掩藏着自己的最初的纯净。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乌有,因为所有的物理、心理—物理和心理对象、所有的真理、价值都外在于这个乌有,因为我的‘我’(Moi/me)自身已经不再是‘乌有’的一部分。但是,这个乌有就是一切,因为他是对所有这些对象的意识。”[4]P39萨特试图回返胡塞尔“意向性”之原初意义对意识和对象世界的关系做出解释,突出意识的纯粹性和绝对存在性。在萨特看来,作为对象的世界是一种超现象性的存在,其不能还原作现象,不需要依赖意识就能够独立存在。换句话说,意识和存在仅仅是在意向性中才统一为现象,意识既产生不出存在,也不能把存在归结作意识。意向性和纯粹意识在萨特那里是可以等量代换的同一意义的两种不同表述方法。也只有这样,意识才能够作为超越对象以及纯粹向外的主观活动和绝对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萨特宣称:“先验的意识是无人格的自发性。意识命定要每时每刻实存,人们不能在意识的实存之前设想任何东西。这样,我们的意识生活的每一时刻都向我们揭示从虚无开始的创造。这不是一种重新整理,而是新的实存。”[4]P42很明显,这种解释与“自为”——萨特的现象学本体论之核心概念——已经相当接近了。
另一方面,消褪了胡塞尔现象学本体论饱含的唯我论与先验论色彩,并使之介入生活世界,诉诸行动。萨特认为,现象学的一个伟大贡献是把人重新引入现实之中,恢复了对人的现实磨难与痛苦的关怀,但又由于它的唯我论和先验论的先天不足,注定了这一哲学关怀未能贯彻到底。萨特在这里是含沙射影地指出,胡塞尔将一切都统摄进意识的做法提供了对人之存在作出研究的可能性条件,但他在先验自我面前固步自封,结果又出现了对现实问题避而不谈的尴尬局面。萨特明确指出:“在‘我’(Je)总保持为绝对意识的一种结果时,人们还可指责现象学是一种‘理论—庇护所’、并且在世界之外抽取人的一块地盘、由此转移了对真正问题的关注。”[4]P45然而,假若从纯粹意识结构中剥离出先验自我,再依据意向性原则仅仅把它看作纯粹主动的向外行动,意识也就能够更加充分地触及生活世界,人的自发自为特性也能够得到愈加充分的外显。这就是说,意识作为指向某物之意识,不仅为意识与世界统一提供了保障,而且又将世界置于意识的中心,避免了理论哲学传统的空谈怪癖。
自我被排除出意识领域之后,意识中不再存有作为主体的我,而是存有非位置性意识。这样就为意识的自发性和完整性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这个透明无人称的意识成功避开了唯我论倾向。在纯反思层面上,意识避开了心理—身体自我(Moi),而透过创造外在于自身之物去支持并控制心理自我(Je)。心理自我和心理—身体自我的区分,否认了笼统地把自我视为先于意识的存在,强调了心理自我作为行动主体的优先性,进而凸显出行动的重要性,从而把其置于状态与性质的前面。作为对象的心理—身体自我与世界一道呈现,则展现了人之未定的自主性。心理自我作为状态和性质,心理-身体自我则是意识之对象。心理-身体自我形成于意识的不断塑造与综合过程中,而并非传统决定论宣称受生理和欲望决定的心理起点。萨特最后断言:“这种绝对的意识,当它被‘我’(Je)纯化时,就不再具有主体的任何性质,它也不是诸多表象的集合:它只不过是实存的原初条件和绝对源泉。而这种意识在‘我’(Moi)面对世界显得岌岌可危,足以使‘我’(Moi)(间接地并通过状态的中介)从世界那里获取其全部内容。”[4]P46
[1][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3][德]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M].丁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4][法]萨特.我的超越性[M].杜小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5][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
[6][法]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