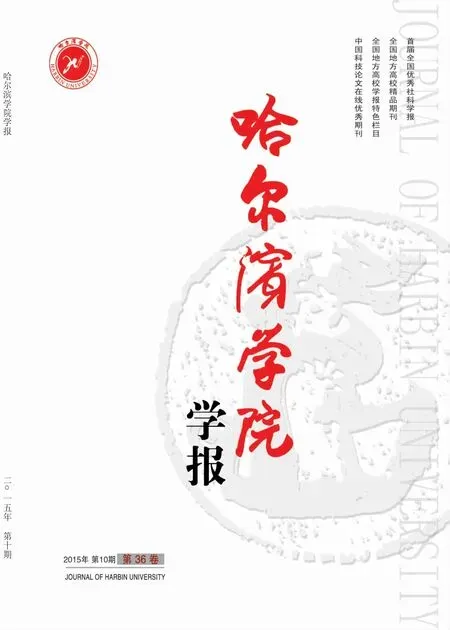近三十年金上京研究综述——金上京考古发现与文物研究综述
2015-03-28王禹浪寇博文
王禹浪,寇博文
(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辽宁大连 116622)
金上京会宁府先后历太祖、太宗、熙宗、海陵王四帝,在此期间,女真人摧枯拉朽般地瓦解了比自身强大数倍的百年辽帝国,形成了与南宋划江而治的“南北朝”局面,为金朝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基础。
金上京坐落于黑龙江省阿城区城南2公里的阿什河西畔,东靠张广才岭,北抵松花江,南望拉林河,西连沃野千里的松嫩平原,区域内水源丰沛,气候适宜,土地肥沃。种种优越的条件,使得上京会宁府迅速发展成为当时黑龙江地区乃至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屹立于广袤的金源大地之上,迸发出耀眼的光芒。随着金帝国的兴衰荣辱,金上京也历经了重重坎坷,最终沉寂于阿什河畔。
一、金上京城考古发现与研究
历经八百年风雨剥蚀和战争破坏,金上京那壮丽辉煌的皇宫殿宇早已湮灭于历史滚滚洪流之中,除了历史的记忆外,留下来的只剩下躺在阿什河畔的古城遗址。而今无数学者前仆后继,努力研究先人遗留的古城,追溯大金帝国当日雄浑壮丽的景象,以求解开尘封在古城之上千年的面纱。
金上京遗址及其周边墓葬、城址的考古工作是研究金上京的基础,迄今为止,考古工作仍在继续,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机构发表了数篇考古报告,这些考古报告成为研究金上京重要的资料。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黑龙江阿城巨源金代齐国王墓发掘简报》[1]和《“金源故地”发现金齐国王墓》[2]两篇考古简报,介绍了1988年黑龙江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阿城市巨源乡城子村发掘的齐国王墓,墓中出土了大量的丝织品,以及“太尉仪同三司事齐国王”木牌一块。它保存完好,出土文物丰富珍贵,墓主人身份显赫,为我国金代考古所罕见,是我国考古工作中的又一重大发现。阎景全的《黑龙江省阿城市双城村金墓群出土文物整理报告》[3]介绍了1980年阿城区金上京东1.5公里处发现的一处墓群的文物整理情况。王春雷、杨力的《金上京遗址西侧发现的金代墓葬群》[4]介绍了1998年在金上京遗址以西发现的一座古墓及发掘过程,为研究金代前期女真族在上京地区的生活习俗、丧葬制度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这些考古报告均为上京地区墓葬研究提供了详细的第一手资料。
为配合绥满公路扩建,黑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阿城至尚志沿线进行考古调查,在亚沟刘秀屯发现一处大型建筑基址。遗址的发现引起了各界的高度重视。《中国文物报》于2012年12月27日刊登李陈奇的《黑龙江亚沟刘秀屯发现宋金时宫殿基址》[5]一文,详细介绍刘秀屯建筑基址的发掘情况。从建筑基址特点、地理位置、周围重要遗迹以及结合有关古文献进行综合考察发现,这应是一处金代皇家宫殿建筑,建筑和使用年代均在金朝前期。关于其功能,有学者认为是当时皇帝百官祭祀太阳之“朝日”殿。刘秀屯金代皇家建筑基址是我国传统礼制建筑的罕见实例,它的发现与发掘,为研究宋金时期政治体制、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建筑风格等,提供了翔实而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在中国建筑史上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国家文物局派出专家组两次抵达现场考察论证,认为:“该基址是迄今考古发掘所见的宋金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宫殿建筑基址,无论对黑龙江考古,还是全国宋金时期考古,都是极为重要的发现”。赵永军与刘阳的《金上京考古取得新成果——发掘揭露南城南墙西门址》[6]介绍了2014年6-10月,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金上京南城南墙西门址考古发掘的情况。此次考古发掘面积1 100余平方米,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本次考古发掘是第一次对金代都城门址进行的科学发掘,了解了金代都城门址的基本形制结构。南城南墙西门址由城门和瓮城两部分组成,门址为单门道,两侧有地袱石与排叉柱等构造。该门址的基本形制特征具有显著的唐宋时期门址的特点,其门道两侧对称竖立大圆木柱支撑顶部过梁结构的做法,墩台及相接城墙内外两侧砌筑包砖的现象,与克东蒲峪路城址的南门址结构相一致,体现了金代城门建筑的新规制。门址门道及瓮城内有多层路面的使用情况,瓮城墙经过两次补筑修复,这些均反映了上京城址的修筑过程和使用情况。瓮城内东北角发现有带火炕的房屋,具有特殊的居住使用功能。瓮城墙内侧筑有砖砌的一类用于排水的特别设施,为了解金代城墙结构特征提供了新材料”。
除此之外,全面介绍考古发现进展与情况的考古综述类文章,也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孙秀仁在《黑龙江地区辽金考古与历史研究的主要收获》[7]一文中系统地梳理了众多金上京地区的遗址与文物,如阿城五道岭地区古代冶铁遗址、上京会宁府故城、金代铜钱和银锭、金代铜镜、金银器与瓷器、金代墓葬,以及简要总结了金代官印的汇集与整理情况,使人们对金代上京地区出土文物种类与数量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李冬楠的《金上京研究综述》[8]回顾了金上京的研究历程,并细数了有关金上京的研究成果,对城周长测量、城门、翁门数量以及城市整体布局等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赵永军与李陈奇的《黑龙江金代考古述论》[9]把黑龙江地区金代考古的历程分为两个时期,其中新中国成立后又分为两个阶段。之后对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现状作一宏观的回顾与总结。概括性地总结了上京会宁府等七座城址、墓葬、聚落址、建筑址、界壕、矿冶遗迹、碑刻,以及铜镜、铜印、金银器、玉器、瓷器等出土文物。作者认为黑龙江地区的金代考古虽起步早,但进展缓慢,缺乏宏观的整体设计和系统性的课题式的工作安排。一些重要的成果没有及时公布,阻滞了一些重要课题的深化研究。在步入新的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作者也提出了加强基础田野考古资料的整理研究、加强区域合作和学术交流等思考与建议。
城市布局是一座城市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有关金上京整体规划布局问题,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金上京形制受辽上京的影响。王禹浪教授认为,“金上京城修建时的整体布局,已经脱离了汉唐以来皇城的宫殿区位于城区偏北,且坐落在两翼对称的中轴线上的传统筑法。并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城池的整体布局,有着浑然不同的风格。金上京城南北二城的布局,以及中间的隔断式的城垣结构,自西向东流淌的河流方位,都呈现出辽上京城的风格特征,透视出金上京城的修建可能深受辽上京城的影响。”[10]韩锋认为,南北二城外郭形制在太宗时期已定型,因而上京城的规划设计是受辽上京临潢府影响的。[11]第二种观点认为是受北宋都城汴京影响,李士良《金源故都——上京会宁府》和孙秀仁的《金代上京城》认为金上京是仿照北宋汴京建成,布局与汴京基本相同。李建勋认为金上京南皇城北汉城的布局是因袭中原王朝前朝后市的规划。[12]第三种观点认为金上京的布局同时受辽上京和宋汴京的影响,景爱认为,金上京形成的工商业区、官署区、宫殿区,模仿了北宋汴京城,但南北城布局,则取法于辽上京,是辽朝南、北分治的两重政治体制的延续。[13]郭长海认为,上京城的规划设计者是久居于辽的汉人卢彦伦,他熟悉辽朝的京都建制,尤其了解辽上京临潢府及辽帝“捺钵”行宫,他被委任知会宁府新城事,规划和设计金上京会宁府,在接受辽上京临潢府模式影响的同时,也受到中原地区城市、特别是北宋都城规划和设计思想的影响,是模仿宋、辽京城形制而筑的。[14]
有关金上京城址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主要有秦佩珩的《金都上京故城遗址沿革考略》[15]对上京城所处的位置、规模形制、宫殿面积、以及出土文物所在进行详细介绍,描绘了当时上京城的经济、政治条件以及优越的交通优势,并绘制金代上京城郊规划中的宫殿寺观一览表,对宫殿名称以及兴建时间做了系统的梳理与统计。许子荣的《金上京会宁府遗址》[16]一文,首先回顾了女真部落发展壮大的历史,上京城发展的历史,而后又对金上京形制、出土文物均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景爱的《关于金上京城的周长》[17]分别介绍了鸟居龙藏在《满蒙的探查》中所载的金上京周长、俄国考古学家托尔马乔夫所测、1936年阿城师范测绘,以及1963年阿城县博物馆进行的实测,为便于比较,而列表展示。作者认为1963年阿城县博物馆所测数据虽被一些书刊引用,但测量结果在统计上出现了错误。景爱《金上京的行政建置与历史沿革》[18]一文叙述了金上京从黄帝寨到会宁州与会宁府,到金上京定号,再到金上京荒废的百年沧桑。郭长海的《金上京都城建筑考》介绍了金上京城廊、宏伟华丽的皇城宫殿、繁荣的街市,作者又对比宋辽时期,总结出金上京向柔和绚丽的方向转变的皇城内建筑格局及风格。赵永军的《金上京城址发现与研究》[19]从梳理文献史料出发,将金上京城的历史分为初建、扩建、毁弃、重建、废弃五个阶段。对金上京城址发现与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总结,指出对金上京城址加强田野考古工作、深入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王旭东的《中国境内金代上京路古城分布研究》[20]一文系统整理了金代上京路内古城,统计上京路各个行政区金代古城563座,并总结金代上京路古城数量多,地域分布不均衡的特点。作者认为,分布不均是由自然环境、辽代已有建城、金代行政建置、经济、交通及军事等多因素影响而造成的。王禹浪与王宏北的《女真族所建立的金上京会宁府》[10]深入探讨了金上京的地理位置、皇宫布局、“白城”称谓、建制沿革以及金上京城的修建过程及其主要建筑等重要问题。伊葆力在实地考察了金上京故址周边的金代遗迹后,发表《金上京周边部分建筑址及陵墓址概述》[21]对祭天坛址、社稷坛址、皇武殿址、宝胜寺故址、护国林与嘉荫候庙址、老营寺院址、松峰山道教遗址、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陵址、胡凯山和陵遗址、桦皮陵墓址、石人沟陵墓址、吉兴陵墓址、上擂木陵墓址、响水陵墓址、西山陵墓址、长胜陵墓址、保安陵墓址等十余处遗址作了详细的调查记录,并进行了初步考证。段光达的《金上京遗址》[22]介绍了金朝各个时期对上京城的营建,用文学笔法叙述了上京城的兴衰始末。
二、金上京地区出土文物研究
金代上京地区出土大量的铜镜、钱币、金银器、官印、铁器、青铜器、碑刻等丰富文物,充分反映了金代上京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以及金代上京地区的社会生活,也反映出女真民族先进的文化与过人的智慧。
(一)铜镜
金上京铜镜出土较多,即在金上京历史博物馆就集中收藏了金上京出土的数百面铜镜。铜镜的装饰题材更是玲珑满目,有龙、凤、蟠璃等虚构的动物,也有花鸟、鱼虫、山水、人物等现实景物,这些栩栩如生的刻画题材则为女真人生活在艺术造型上的映射,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与此同时,金上京出土铜镜多带有汉字铭文和刻记,是研究金代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宝贵材料。20世纪70年代阿城文物管理所编著的《阿城县出土铜镜》[23]将所出土的铜镜汇编成册,由此激发了广大学者对金代上京地区出土铜镜的兴趣。随后,金代铜镜研究如同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景爱的《金上京出土铜镜研究》[24]对金上京出土的铜镜做了大致介绍,如多带有汉字铭文的仿汉内向连弧百乳镜、带而字昭明镜、锯齿纹花边鸟兽镜等、仿唐禽兽葡萄镜、北宋花草镜和缠枝花鸟镜、以及众多金代童子缠枝镜、双鱼镜、双龙镜、双凤镜、双兽连珠镜、人物故事镜、有柄仙人镜、有柄阳燧镜等,铜镜纹饰反映了时代气息与民族特色。作者简要说明了铜镜的使用方法与铜镜制造工序、金代铜镜管理制度,并对铜镜的历史作用与艺术价值做了高度的评价。阎景全的《金上京出土的铜镜》[25]描绘了1964年出土的大双鱼纹镜、1969年出土的刻有“上京巡警院”字样的童子缠枝纹镜,以及1977年出土的刻有“上京会宁”“上京巡警院”等检验刻记的带柄蛟龙仙鹤纹镜。王禹浪的《海马葡萄镜》[26]一文刊布与考证了双城县出土的两面铸造风格一致的铜镜,镜背分内外两区:内区由海马葡萄纹组成,宋《博古图录》称它为海马葡萄镜;外区铸有一圈汉字铭文,为“青盖作镜自有纪,辟去不羊宜古市,长保二亲利孙子,为吏高官寿命久”,共计28个字。内外两区之间用高线圈相隔,铜镜边缘均有刻款和神记。从铜镜加刻的边款、钾记,并结合《金史·地理志》,作者断定这两面铜镜为金代仿制品。王禹浪随后又相继发表了《飞鹊镜》[27]《金代双鱼镜》[28]《“大吉官”及“永安三年”镜辩误》[29]等数篇高水平的金代铜镜论文,奠定了作者在金代铜镜研究领域的地位。王禹浪、李陈奇较早的对金代铜镜作了综合研究,分别对金代铜镜的类型、铭文以及所绘图案反映的艺术特征和社会生活等内涵进行了探讨。[30]随后,王禹浪、那国安又编著了《金上京百面铜镜图录》,[31]为铜镜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张占东的《浅谈上京会宁府出土的金代铜镜》[32]论述了铜镜产生的条件,并以双鲤鱼镜、童子玩莲镜、迷戏镜三种铜镜纹饰为例,深入分析了铜镜背后所折射出的汉文化对女真文化潜移默化的现象。作者认为,双鲤鱼图案造型是女真人借用鱼的生殖繁盛的特性,表达了“多子多福”的美好意愿,又借用鲤鱼跳龙门表达了祈求升官登仕的愿望。“迷戏镜”作为特殊镜类,在历代社会中都是极为罕见的,它反映了金代宫庭生活的一个侧面。田华的《金代铜镜的刻款及相关问题》[33]以及后续发表的《再论金代铜镜刻款及相关问题》[34]对金代铜镜的刻款进行了分析,并就刻款反映的相关问题提出一些看法。21世纪初王宇撰文《金代铜镜研究述评》[35]对近百年来金代铜镜的研究状况概述为三个阶段,并提出了有待进一步解决的若干问题。彭芊芊的《金上京会宁府出土铜镜考证》[36]与《金上京会宁府出土铜镜浅谈》[37]对龙纹镜、双鱼纹镜、海东青鸾兽镜、花卉纹镜、童子攀枝镜、人物故事镜这六种纹饰做了解释说明。张杰、李秀莲的《金源铜镜的宗教文化意蕴初探》[38]从宗教文化角度分析金上京地区铜镜数量之多、质量参差、纹饰与形制的变化与宗教文化的关系,作者认为出土与传世铜镜数量之多,主要是女真人的原始宗教信仰使然:金上京历史博物馆中许多不满10公分的铜镜,推测为萨满神衣上的装饰物。在女真人的头脑中,一直保留着镜光吉祥的遗痕,人们都渴望跳萨满舞的妇人把镜光投在自己的身上,镜光象征吉祥是被群体公认的,镜光也能代表天意是女真人对太阳和月亮崇拜的结果。作者进一步推断,在女真人的宗教信仰中,铜镜具有超万物的神力是光明和正义的象征。金源铜镜形制的变化表现在带耳铜镜的大量出现。而带耳铜镜作者认为是萨满求子仪式中裆下常常挂着象征生育的铜人,宗教上的特殊用途推动了日常生活中带耳铜镜的出现。作者还推测,双鱼大铜镜同样具有宗教意义。杨昔慷的《海兽葡萄镜的初步研究》、徐涛的《金代仿古铜镜》与朱长余的《金东北三路出土铜镜研究》均以金代铜镜为题撰写毕业论文,梳理了金代铜镜的研究成果。
(二)铜器、金银器
魏国忠的《黑龙江阿城县半拉城子出土的铜火铳》[39]介绍了1970年出土于阿什河畔半拉城子的一批铜器,有铜火铳、三足小铜锅、铜瓶咀、铃档、铜镜和五株钱各一件,铜质军马佩饰物三件。其中铜火铳一件,保存最为完好。从这批同时出土的器物来看,几乎都与军事攻战有关,有些器物的形制和纹饰又具有金元时代的风格。作者由此推断,阿城火铳也有可能系金元时代所遗留。但从其形制比较原始,制作较为粗糙来推断,其铸造年代似应在至顺铜火铳和至正铜火铳之前。作者在文中进一步指出,过去文物考古工作者对金代上京地区出土的文物多笼统地认为是金代的作品,从这次出土的铜火铳等器物看来,其中不少应是元代遗物,这就促使我们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对于具体文物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弄清其本来面目。
阎景全的《金上京故城内发现窖藏银器》[40]刊布了1978年秋,在金上京城北城南偏东处出土的一批银器。这些银器的出土反映了金上京工商业的繁荣与发展。随后又于《北方文物》1992年第3期发表《黑龙江省阿城市出土青铜短剑》,[41]刊布了1991年出土的青铜短剑,据专家鉴定,该剑为西汉初年夫余之文物。
1956年金上京遗址西垣南段墙角下出土了一枚铜坐龙,经多方考证,该文物应为御辇上的装饰物,铜坐龙的出土也为研究金代舆服制度、铸造工艺以及金代上京地区的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枚铸造精细、构思巧妙、形象生动,又蕴含文化内涵的青铜龙,遂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许子荣的《金上京出土铜坐龙》[42]详细介绍了铜坐龙的造型,并推测它应是天眷三年(1140)金熙宗初备法驾卤薄,至大定二十五年(1185)金世宗远巡上京结束之前这段时间内留下的作品。陈雷的《黑龙江出土金代铜坐龙的雕塑艺术特色》[43]和《试论金代铜坐龙的雕塑造型及饰纹特色》[44]简要介绍了铜坐龙的出土及其功能、历史文化背景,并对金代铜坐龙的雕塑造型和祥云饰纹特色及其历史文化意义作探讨。姚玉成的《金代铜龙鉴识》[45]对一般学者认为铜坐龙属于金代皇帝车舆上的饰物提出质疑,作者列出学者常引《金史·舆服志》来证明铜坐龙为金代皇帝御辇上饰物的两处记载,指出两处无一明确说明这个“坐龙”为铜质,也未指明其为立体铸龙,作者根据文物出土地点,并结合所出土的其他金代房屋装饰物,推测铜坐龙应为金代皇室建筑房脊上的装饰物。但作者也指出,目前这只是一种推测,在没有更多资料来证明的情况下,得出结论还为时过早。孙丽萍的《黑龙江省博物馆藏金代铜坐龙》[46]简要介绍了金上京出土铜坐龙的情况,以及简要分析铜坐龙的艺术造型。杨海鹏的《从建筑构件角度谈金代铜坐龙的功用》[47]从建筑构件的角度入手,结合了《营造法式》中具体建筑构件的解读及式样图例,分析了金代铜坐龙、石坐龙的形制特点,探讨了金代铜坐龙的具体功用,是利用《营造法式》解读出土文物的一次探索性尝试。王久宇的《阿城出土金代铜坐龙的历史渊源》[48]深入讨论了金代仪制与上京地区汉化的过程,认为铜坐龙饰物充分体现了金代舆服、车辇制度与宋代制度的渊源,铜坐龙为金人沿袭宋代仪制,体现了中原汉文化的审美观点和价值取向。尽管如此,铜坐龙为金人所用,仍然是金源文化的象征。人像类铜挂饰在金上京地区出土较多,形象一般为儿童形象,反映金初女真人祈求多子多孙的愿望。
阴淑梅在《黑龙江省阿城市金上京城址出土的武士像铜挂饰》[49]刊布了一件1998年阿城市白城三队出土的武士像铜挂饰,此挂饰上的武士像的服饰与《金史舆服制》记载不吻合,所着幞头、所着明光铠均有宋的风格。作者认为,武士坐姿与亚沟石刻男坐像的姿态极为类似,是典型的金代风格,故可断定为金代遗物。武士形象的挂饰,较为罕见,表现出的刚毅之态,应为女真人尚武精神的一种体现。作者于《黑龙江省阿城市金上京出土的青铜童子佩饰》[50]一文中介绍了20世纪70年代收集于金上京的6件小铜人,6件铜仁姿态多样,造型生动,代表着金代上京地区雕塑、铸铜业工艺水平。同时期,宋金两地均有童子纹式样的文物,因而作者认为这也是中原传统文化在金上京的影响所致。
з·B·沙弗库诺夫根据渤海人官员等级划分的第六和第七等级的官员所佩戴的鱼形垂饰、女真文官佩戴鱼形垂饰、唐代使臣表明身份的铜鱼以及契丹鱼形兵符,推论金上京以及东北地区各地出土的铜鱼是皇帝权力的象征。[51]
郭长海的《金上京发现开国庆典所献礼器——人面犁头》[52]介绍了20世纪末出土于金上京地区的铁铸犁头,犁面铸造出尤如人面的双眼和嘴巴,故称“人面犁头”。据考证,此“人面犁头”当是大金开国时阿离合懑、宗翰向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所献礼器“耕具九”之首,是金上京发现孤品礼器,进一步印证金朝以农为本的基本国策。
金代官印是金代上京地区出土较多的又一珍贵文物,其印面文字、刻款、书法字体、形制、纽式均是金代民族融合发展的象征,为研究金代的官制、兵制、印制以及金代上京地区地方史,提供了大量的宝贵实物。林秀贞的《黑龙江出土的金代官印》[53]分析“窝谋海”与“窝母艾”当为同一女真语的汉字异写,由此可知,窝谋海村应是窝母艾谋克所辖的一个重要的村寨,其与谋克同名,或为谋克驻地。此印文前冠名“恤品河”三字,因而便推翻了先前学者对史籍中“窝谋海村”的历史地理考证。此外,林秀贞在该文中还详细介绍了金代官印制度的建立过程以及猛安谋克印及制度的演变、武官和军事机构官印及其制度,总结了金代官印在中国古代印制的地位。才大泉的《金上京博物馆馆藏的金代官印》[54]简要介绍了金上京博物馆内馆藏的上京路总押荒字号印、上京路勾当公事裳字号印、都弹压所之印,这几方印均为贞祐年间铸造。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上京故址周边地区不断出土金代的窖藏铜钱,初步统计已达数万斤以上。窖藏铜钱数量惊人,虽对此进行研究的学者寥寥无几,但研究成果丰硕。王禹浪的《浅谈金代窖藏铜钱及货币制度》[55]总结了上京地区出土窖藏铜钱种类及窖藏特点,并结合金代铜钱短缺情况以及禁铜政策等政治学、经济学知识,深入地分析金代窖藏铜钱的原因,为金代窖藏铜钱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石刻
亚沟石刻位于阿城区亚沟南麓崖壁上,是驰名中外的金代女真人形象的珍贵艺术遗存。有关亚沟石刻的年代,多数学者认为是金代早期石雕艺术遗存,如宋德金的《金代的社会生活》、王可宾的《女真国俗》、赵虹光的《黑龙江区域考古学》、朱瑞熙等编著的《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图像的内涵也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石刻图像是金太祖及其皇后的形像,此地即是胡凯山合陵;有人认为,石刻图像与金代陵墓有关;有人认为,石刻图像是护墓的,等等。前苏联学者B.H.热尔那阔夫的《黑龙江省阿城县亚沟车站采石地区发现石刻画像》[56]一文最早对该画像做文字记录,由于该地周围曾出土大量金代文物,因而作者推断石刻画像为金代遗物。在距画像5公里的地方,有金代王公墓葬,也因此推论石刻画像是用来护卫墓葬的。张连峰在《亚沟石刻图像》[57]一文中认为,亚沟图像应为女真王公崖墓的标志,墓主即为墓主夫妻形象。迄今民间尚传说崖下曾有岩洞,并有石桌、石香炉之类的祭器,仍亦可参证。可能是金太祖时,有人为追思其某先考先妣业绩,仿辽代习俗、葬制在陵地雕刻的纪念性作品。李秀莲的《亚沟摩崖石刻族属考释》[58]一文却认为亚沟石刻不属于女真人,而属于蒙古人。作者从石刻图像中的男性“八”字形面容特征,头戴卷沿圆帽,身穿圆领长袍,刻像的袍服是由右向左撩起,说明是右衽,还有披肩,右手握剑柄的形象,以及介于蹲坐和盘坐之间的坐姿,均反映出图像所刻应为蒙古人。作者又根据《阿城县志》等文献记载此地为元代治所和该地曾有元代“镇宁州诸军奥鲁之印”出土两则证据,加以辅证。
景爱的《金代石刻概述》[59]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金代石刻文字的发现、著录、学术价值和研究现状。列举了《日下旧闻考》《光绪顺天府志》《畿辅通志》《山左金石志》《金文最》等十余种辑录金代石刻的历史文献及方志,并指出金代石刻对女真文字研究、补全猛安谋克名称、补《金史》记事之缺漏、金代佛教的流传状况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乌拉熙春与金适的《金上京“文字之道,夙夜匪懈”女真大字石碑考释》[60]对1994年于哈尔滨市道外区巨源镇城子村出土的刻有11个字的女真大字石碑进行解读,按照女真大字的字面直译则是“文字之道,夜朝不懈”。又因《诗经·大雅·烝民》与《诗经·大雅·韩奕》两篇中皆有“夙夜匪解”,因此典雅些的译文就是“文字之道,夙夜匪解”。文章又进一步讨论了大字石碑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意义。
2000年,阿城区出土了一尊石尊,王禹浪与王宏北撰文对该石尊进行探讨,认为石尊当为渤海靺鞨人的遗物,经女真人之手,作为金朝开国典祀,建元“收国”的重器。作者又进一步指出石尊上四象、四灵、四神图案不仅说明了中原文化对金源文化的深刻影响,而且表达了金源文化在全面接受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靺鞨、渤海、契丹等多民族文化加以创新与嬗变。[61]这件代表着女真人高超技艺的金源文化的瑰宝和圣物,正是金源文化的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具体体现。
(四)玉器及其他文物
刘俊勇撰文[62]罗列了黑龙江阿城巨源金代齐国王完颜晏夫妇墓等七处金代玉器出土地点,针对出土玉器进行分类,分“春水”玉、“秋山”玉、佩玉、肖生玉及其他玉器四类,深刻总结了金代玉器的造型和艺术特点,并根据“春水”玉所反映的海东青题材,概括女真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曲石撰文[63]综述了宋辽金考古发掘、传世玉器概述,并根据玉器的类型与用途进行分类,作者共分装饰用品、容器、文房用具、艺术品、仿古器物和杂器六大类分别论述,并总结宋辽金玉器特点。吴敬撰文[64]探讨金代玉器研究方法,并提出研究广度——泛论、专论相辅相成、研究深度——深论、简论相互侧重、研究角度——功能、工艺相得益彰三个研究方法。
张连峰[65]考证了1976年上京城内出土的一面铜牌,该牌呈圆形,直径7厘米,厚0.2厘米,牌面中央錾刻“上京鞋火千户”汉字,背面饰行龙、云朵、火珠纹等。作者断定此物应为上京官衙颁制的腰牌,是金朝时隶属于上京路管辖、位于乌苏里江流域锡霍特山一带的鞋火千户官通行于上京路凭信。近期,伊葆力提出不同观点,并于《“上京鞋火千户铜牌”质疑》[66]加以阐述。伊葆力列举文献记载,见于宋人记述中的这些金国牌符,质地、形状与所谓上京鞋火千户铜牌相异,并从“铜牌”的形制、纹饰及刻款押记等特征来看,推断此器应为金代中期的小型龙纹铜镜,“上京鞋火千户”是铜镜检验的刻记。
孙新章撰文[67-68]介绍了金上京遗址周边发现的大量宋、金时期的围棋棋子,材质种类多达几十种,如玛瑙、青铜、螺钿、绿松石、木质、水晶、玄武岩、汉白玉、瓷片、琉璃等。在金上京遗址上发现这些围棋棋子数量众多,围棋棋子的种类在其他遗址上是不多见的,这也让我们对金代上京地区的高度繁荣的文化有了更新的认识,上至达官显贵的玛瑙、宝石围棋子,下至平民百姓的土陶烧制围棋棋子、瓷片打磨围棋棋子、石子制作围棋棋子,其中还有佛教道教所用棋盘及围棋子,均证明了金上京的围棋文化的快速发展及普及。
三、从金上京考古发现与文物中体现的金上京文化特征
金上京及其周边地区遗迹遗物分布广泛,出土文物之多令人叹为观止。如此众多的遗址与文物不仅昭示了昔日大金帝国的繁荣景象,体现了金上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也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首先,出土碑刻上的女真字与汉字,体现了女真文字、语言的特征。女真字是在汉字基础上添减笔画所创,诞生之初便印刻了中原文化深深的烙印。碑刻上所刻的两种文字,亦能反映金代汉字与女真字两种语言文字的广泛使用;其次,宗教遗址与文物的发现,体现了女真人丰富的精神生活,萨满教、佛教、道教等宗教在金上京地区广泛传播,是女真文化同中原文化交融共存的写照;第三,出土于金上京地区的多方官印,真实反映了金代多种典章制度,如官制、印制等。小小的官印折射了整个大金帝国充分吸收与继承唐宋典章制度的历史文化背景;第四,人物镜、故事镜、双鱼镜等形形色色栩栩如生的铜镜,不仅反映了金代手工业发展水平与金代铜镜管理制度,也反映了深受汉文化潜移默化的女真人的精神世界;第五,天鹅佩饰、武士佩饰、童子佩饰、海东青佩饰,流露出女真民族高尚的情操与不畏艰险、以小博大、勇于拼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高超的手工造诣背后是汉族、靺鞨、渤海、女真、契丹等多民族文化的创新与嬗变;第六,从金上京城的遗址特征来看,无论是城墙、马面、城市布局,以及建筑风格,都充分吸收与融入了中原文化、契丹文化等多民族文化特点。这种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特征,缔造了容纳百川、极具生命力的女真文化,大金帝国虽早已被时间淹没,但女真人所创造的璀璨文化却深深地印刻在金上京地区遗址与遗物中。
[1]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阿城巨源金代齐国王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9,(10).
[2]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源故地”发现金齐国王墓[J].北方文物,1989,(1).
[3]阎景全.黑龙江省阿城市双城村金墓群出土文物整理报告[J].北方文物,1990,(2).
[4]王春雷,杨力.金上京遗址西侧发现的金代墓葬群[A].金史研究论丛[C].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5.
[5]李陈奇.黑龙江亚沟刘秀屯发现宋金时宫殿基址[N].中国文物报,2012-12-27.
[6]赵永军,刘阳.金上京考古取得新成果一一发掘揭露南城南墙西门址[N].中国文物报,2015-01-30.
[7]孙秀仁.黑龙江地区辽金考古与历史研究的主要收获[J].黑龙江民族丛刊,1983,(1).
[8]李冬楠.金上京研究综述[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9,(5).
[9]赵永军,李陈奇.黑龙江金代考古述论[J].北方文物,2011,(3).
[10]王禹浪,王宏北.女真族所建立的金上京会宁府[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2).
[11]韩锋.金上京城市建设[J].黑龙江史志,2010,(15).
[12]李建勋.金上京史话两题[J].黑龙江农垦师专学报,2000,(4).
[13]景爱.金中都与金上京比较研究[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2).
[14]郭长海.金上京都城建筑考[J].哈尔滨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1).
[15]秦佩珩.金都上京故城遗址沿革考略[J].史学月刊,1980,(2).
[16]许子荣.金上京会宁府遗址[J].黑龙江民族丛刊,1982,(1).
[17]景爱.关于金上京城的周长[J].学习与探索,1985,(3).
[18]景爱.金上京的行政建置与历史沿革[J].求是学刊,1986,(5).
[19]赵永军.金上京城址发现与研究[J].北方文物,2001,(1).
[20]王旭东.中国境内金代上京路古城分布研究[D].吉林大学,2005.
[21]伊葆力.金上京周边部分建筑址及陵墓址概述[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3).
[22]段光达.金上京遗址[J].文史知识,2007,(2).
[23]阿城文物管理所.阿城县出土铜镜[M].1974.
[24]景爱.金上京出土铜镜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1980,(2).
[25]阎景全.金上京出土的铜镜[J].学习与探索,1980,(2).
[26]王禹浪.海马葡萄镜[J].求是学刊,1981,(4).
[27]王禹浪.飞鹊镜[J].黑龙江民族丛刊,1982,(2).
[28]王禹浪.金代双鱼镜[J].求实学刊,1982,(6).
[29]王禹浪.“大吉官”及“永安三年”镜辩误[J].四川文物,1986,(2).
[30]王禹浪,李陈奇.金代铜镜初步研究[C].辽金史论集:第3辑[C].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31]王禹浪,那国安.金上京百面铜镜图录[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4.
[32]张占东.浅谈上京会宁府出土的金代铜镜[J].北方文物,1995,(1).
[33]田华.金代铜镜的刻款及相关问题[J].北方文物,1995,(3).
[34]田华.再论金代铜镜刻款及相关问题[J].求是学刊,1996,(6).
[35]王宇.金代铜镜研究述评[J].中原文物,2000,(3).
[36]彭芊芊.金上京会宁府出土铜镜考证[J].黑龙江档案,2009,(2).
[37]彭芊芊.金上京会宁府出土铜镜浅谈[J].黑龙江史志,2013,(11).
[38]张杰,李秀莲.金源铜镜的宗教文化意蕴初探[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2).
[39]魏国忠.黑龙江阿城县半拉城子出土的铜火铳[J].文物,1973,(11).
[40]阎景全.金上京故城内发现窖藏银器[J].黑龙江民族丛刊,1981,(1).
[41]阎景全.黑龙江省阿城市出土青铜短剑[J].北方文物,1992,(3).
[42]许子荣.金上京出土铜坐龙[J].文物,1982,(6).
[43]陈雷.黑龙江出土金代铜坐龙的雕塑艺术特色[J].北方文物,2002,(4).
[44]陈雷.试论金代铜坐龙的雕塑造型及饰纹特色[J].中华文化论坛,2003,(1).
[45]姚玉成.金代铜龙鉴识[N].中国文物报,2008-06-11.
[46]孙丽萍.黑龙江省博物馆藏金代铜坐龙[J].收藏家,2008,(9).
[47]杨海鹏.从建筑构件角度谈金代铜坐龙的功用[J].东北史地,2013,(4).
[48]王久宇.阿城出土金代铜坐龙的历史渊源[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4,(3).
[49]阴淑梅.黑龙江省阿城市金上京城址出土的武士像铜挂饰[J].北方文物,2006,(3).
[50]阴淑梅.黑龙江省阿城市金上京出土的青铜童子佩饰[J].博物馆研究,2007,(4).
[51]з·B·沙弗库诺.孙危.金上京城址出土的铜鱼和铜鹿角的用途[J].东方考古,2001,(00).
[52]郭长海.金上京发现开国庆典所献礼器——人面犁头[J].北方文物,2006,(4).
[53]林秀贞.黑龙江出土的金代官印[J].学习与探究,1980,(1).
[54]才大泉.金上京博物馆馆藏的金代官印[J].黑龙江史志,2006,(11).
[55]王禹浪.浅谈金代窖藏铜钱及货币制度[J].求实学刊,1984,(6).
[56]B.H.热尔那阔夫.黑龙江省阿城县亚沟车站采石地区发现石刻画像[J].文物参考资料,1956,(6).
[57]张连峰.亚沟石刻图像[J].学习与探索,1981,(3).
[58]李秀莲.亚沟摩崖石刻族属考释[J].北方文物,2010,(4).
[59]景爱.金代石刻概述[J].北方文物,2009,(4).
[60]乌拉熙春,金适.金上京“文字之道,夙夜匪懈”女真大字石碑考释[J].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7).
[61]王禹浪,王宏北.金代“建元收国”石尊考略[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6).
[62]刘俊勇.金代玉器研究[J].北方文物,1996,(3).
[63]曲石.两宋辽金玉器[J].中原文物,2001,(6).
[64]吴敬.金代玉器发现与研究述评[A].宋史研究论丛[C].2013.
[65]张连峰.金“上京鞋火千户”铜牌[J].黑龙江民族丛刊,1982,(1).
[66]伊葆力.“上京鞋火千户铜牌”质疑[J].北方文物,2003,(1).
[67]孙新章.金上京遗址出土“云子”雏考[A].金上京文史论丛:第4辑[C].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68]孙新章.金上京遗址出土围棋棋子简报[A].2014年第二届海峡两岸体育运动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