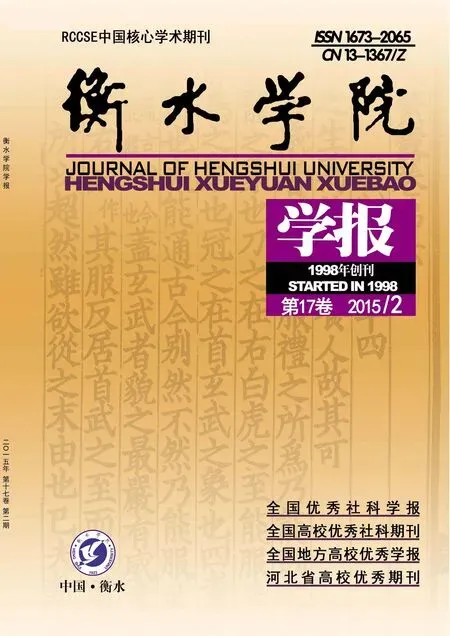钱耕森“大道和生学” 和文化的一朵奇葩——自成一家,自我超越
2015-03-27程潮
程 潮
钱耕森“大道和生学” 和文化的一朵奇葩——自成一家,自我超越
程 潮
(广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广东 广州510006)
从自我成长历程中领悟到钱耕森导师的理念形成于“和的哲学”的时期,“和生学”是“和的哲学”的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斗争哲学”,钱师的“大道和生学”自身经历了“和生学”“大道和生学”和“大道和同学”三个发展阶段,不仅强调异的价值也强调同的价值,更具有辩证性,也具有全面性,不啻和文化的一朵奇葩。
钱耕森;“和生学”;“大道和生学”;“大道和同学”
一个成功的学者,在其学术的道路上都有一个“由博返约”的过程,其“返约”的成功标志是能够自成一家。钱耕森老师早年学术出入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这也是当年很多哲学学者所走的路。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钱师开始集中研究中国哲学,并带了十多届中国哲学专业的硕士生(遗憾的是,直到他退休时,安徽大学作为地方大学仍无权设博士点)。我于1988年下半年成为钱师的弟子。1990年我硕士毕业后,分配到安庆师范学院教书。我自从1994年到广东工作后,与钱师的学术交往也没有以前在本省那么便利,特别是我调入社会学系后,对中国哲学的关注越来越少了。而且我过去总以为在学术上能自成一家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学者都是以或多或少地发表一些文章作为自己的学术宿命,因而也没有想到钱师会成为这少数“自成一家者”中的一员。而且我是在文革之前出生的,从小就接受“阶级斗争”“批斗”“革命”等词汇的熏陶;高中和大学本科阶段接受哲学教育时,仍不免受“斗争哲学”的影响,认为“阶级斗争”“革命”属于矛盾的斗争性,因而是绝对的、永恒的、正面的;“调和”“和谐”属于矛盾的同一性,因而是相对的、暂时的、忌讳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史时,必然会遇到“同”与“异”、“和”与“仇”的关系问题。据《国内哲学动态》1982年刊文介绍,先前的教科书和论著基本主张张载的“仇必和而解”命题是“矛盾调和”的形而上学,是“害怕矛盾”“害怕斗争”的地主阶级思想,而肖景阳和刘扬贵在各自的来稿中重新评价了这一命题,认为“这是建立在元气本体论朴素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辩证法命题”[1]。不过,这种评判只是停留在一个哲学命题上,还没有上升到一个哲学理论或哲学体系上。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是告别传统的“斗争哲学”而开创“和的哲学”的时期,其中代表性的有:冯友兰先生的“仇必和而解”的哲学、张岱年先生的“兼和哲学”、张立文先生的“和合学”和钱耕森先生的“和生学”。各种形态的“和的哲学”的出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内求稳定与繁荣、外求和平与发展的现实需要。
冯友兰先生首次将“仇必和而解”上升到“辩证法”的层次来评判。他指出:客观的辩证法只有一个,即“矛盾的统一”;人们对于客观辩证法的认识至少有两种,即以“统一”为主的“仇必和而解”和以“矛盾”为主的“仇必仇到底”[2]。接着,他发文将“仇必和而解”和“仇必仇到底”作为区分中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标志,并认为“仇必和而解”才是“客观的辩证法”。他从全球视野来审视以“仇必和而解”为特色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意义,指出“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3]。不过,冯先生“仇必和而解”的哲学思想问世后不久,就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许全兴指出冯先生以“仇必和而解”(“和的哲学”)和“仇必仇到底”(“斗争哲学”)来区分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说法不科学,强调“斗”与“和”的辩证统一[4-5]。刘奔认为“仇必仇到底”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误解[6]。
张岱年先生早在1948写成的《天人简论》中就提出了“兼和”概念[7]。张先生退休后,高足刘鄂培先生在其主编《张岱年文集》的过程中拜读了张先生的几乎全部论著,后又在主编《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一书中感悟到“兼和”是张先生思想体系中“一以贯之”的思想,于是他于1999年6月10日来到张先生寓所,汇报自己对“兼和”的理解,指出“‘兼和’是岱年师文化观——‘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哲学基石,是岱年师治学和待人接物之道,是岱年师哲学中的精髓”。张先生愉快地接受了刘先生对其哲学核心思想的评判[8]。张先生的“兼和哲学”问世后,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方克立先生称他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兼和’哲学的首倡者和身体力行者”[9]。
张立文先生于1990年在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95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了“和合学”的思想,并于1996年出版《和合学概论》一书,系统构筑了他的“和合学”理论体系。张先生从文化哲学的视野来构建和合学,认为“和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合学”是现代文化方式的选择。他称其“和合学”包含“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则,是21世纪人类的最大原理和最高价值[10-12]。张先生“和合学”的问世,也得到了学术界的积极肯定。
钱师“大道和生学”的创建,经历了一个产生、完善和成熟的发展过程。据钱师自己陈述:1994年10月5-8日在北京召开的“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和为贵”新论——儒家与现代化》一文,明确提出了“和生学”;2013年12月28日在安徽大学召开的“庆祝黄山文化书院成立25周年暨钱先生从事教学与科研55周年”座谈会上发表了《“大道和生学”运思轨迹略述》一文,将自己潜心研究有年的“大道和生学”和将要推出的“大道和同学”在会上一并推出,而且钱师的“大道和生学”成了本届年会研讨的主题。这意味着钱师的“大道和生学”经历了“和生学”“大道和生学”和“大道和同学”三个发展阶段[13]。
钱师的“和生学”产生于冯友兰先生的“仇必和而解”哲学之后、张岱年先生的“兼和哲学”的自觉形态之前。而钱师是冯先生和张先生的高足,师生往来密切,他的“和生学”自然受到二老思想的影响。钱师的“和生学”产生于张立文先生的“和合学”之后,从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可能受到“和合学”的影响,而且张先生“和合学”的创立,也增强了钱师创建自己的“和生学”体系的信心。但张先生提出“和合学”五大原则(包括“和生”原则)的时间是在钱师提出“和生学”后的第二年,而在中国哲学意义上使用“和生”概念也是自钱师始。因此,张先生提出的“和生”原则,也有可能受钱师“和生学”的启发。与同时代创建的其他“和的哲学”派别一样,钱师的“和生学”也以史伯的“和实生物”“以他平他”之说为源头。但钱师却认为史伯的“和实生物”说高于孔子的“和为贵”说的价值,因为前者出现的时间更早,内容更为深刻,价值更大。他高度评价了史伯“和生学”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国内价值和国际价值,认为它把中华民族所固有的“生”(“大化流行”“生生不息”“日新又日新”“与时俱进”)与“和”(“和谐”)的两种优秀的传统精神创造性地有机结合起来,对孔子的“和而不同”说和老子的“道生万物”说产生了重要影响。钱师特别自豪地指出,他发现史伯的“和生学”,是他阅读古文献时看到的,自家“体贴”出来的;他又以史伯的“和生学”为基础,进而探索成自己的“和生学”。在我看来,钱师的“和生学”更突出的贡献在于他将“和”与“生”联系在一起。当然,他所说的“生”的意义,让人有“生存”“生长”“生产”(“生物”)、“产生”(生财)、“生机”“生意”等无限遐想。
“大道和生学”是钱师“和生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在此阶段,他强调老子的“道生万物”虽然受史伯“和生学”的影响,却又对史伯的“和生学”作出了巨大的超越与发展。老子的新贡献在于把“道”引进来了;把“阴阳二气”引进来了;把“冲气”引进来了;把“和”与“气”结合起来了,形成了“和气”;把
经验的“以他平他谓之和”上升到理性的“冲气以为和”,把具体的现实的“和生万物”说提到了抽象的哲理的“道生万物”说的高度。实际上,钱师通过对老子思想的解读,是要为他的“和生学”找到形而上的本体论依据和从形而上的本体派生形而下的宇宙万物的具体途经。而他正是将史伯的“和生”说与老子的“道生”说打通,从而构筑起他自己的“大道和生学”的新体系。
“大道和同学”是钱师“和生学”的最新构想。在钱师看来,史伯看出了“同”的“不继”的消极的一面,未能看出“同”有“生物”的积极的一面,不懂得“和”“异”之中有“同”,“同”之中有“和”“异”的辩证关系。而钱师认为,多元的“他”只有经过“求同存异”,才能达到“平”“平衡”,才能达到“和”“和谐”,才能“生物”。因此,他从古代哲人的言论和古代的成语、词语中发掘带有正能量的“同”,以揭示“同”与“和”“异”的内在联系以及“同”的积极价值。他又对儒家“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进行重新解读,指出“和”与“同”在“大同社会”里大大超越了史伯提出的“和同之辨”,在全新的高度上互动互补,有机地统一起来,持续不断地共生出万事万物。他希望自己晚年能在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和”文化、“同”文化和“生”文化方面,在将三者打通构建成“大道和同学”方面,以及让“大道和同学”在彰示儒道互补更大的价值方面,做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因此,在“大道和生学”中加入“同”的积极元素,是钱师对当代“和的哲学”的又一特别贡献。
近代梁启超先生“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来追求学术上的自我超越。吾师论道,虽不像梁先生那样的反复无常,但也经历了一个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发展过程。从“和生学”的创立,到“大道和生学”的形成,到“大道和同学”的构想,正是吾师不断自我超越的生动体现。弟子希望吾师保重好身体,再假以时日,将一个更为系统的“大道和同学”理论体系奉献给社会。
[1] 肖景阳,刘扬贵.张载“仇必和而解”命题新评[J].国内哲学动态,1982(2):34-35.
[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5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35.
[3] 冯友兰.中国哲学的底蕴精神[J].中国文化,1991(2):6-11.
[4] 许全兴.“斗争哲学”与“和的哲学”[J].南京社会科学,1995(1):48-53.
[5] 许全兴.“和的哲学”辨析[J].哲学研究,1995(9):37-42.
[6] 刘奔.“仇必仇到底”究竟是谁家之哲学?[J].哲学研究,1998(11):37-39.
[7] 刘鄂培.张岱年文集:第3卷[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213.
[8] 刘鄂培.张岱年的“兼和”论——为纪念恩师张岱年诞辰100周年而作[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9(5):90-95.
[9] 方克立.张岱年先生的“兼和”思想[N].北京日报,2009-6-15(19).
[10] 张立文.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合学源流的考察[J].中国哲学史,1996(Z1):43-57.
[11] 张立文,包霄林.和合学:新世纪的文化抉择——关于一种文化战略选择的访谈[J].开放时代,1997(1):67-72.
[12] 张立文.中国文化的和合精神与21世纪[J].学术月刊,1995(9):67-72.
[13] 钱耕森.“大道和生学”运思轨迹略述[J].衡水学院学报,2014(2):53-56.
Qian Gengsen’s “Theory of Harmony Originating from Tao”: A Rarity in Harmony Culture——Being Unique, Being Self-transcendent
CHENG Chao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in Facult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China)
The concept of Qian Geng-sen came into being in the period of the “the philosophy of harmony”, as is realized in my self growth process. The “theory of harmony” is a kind of “the philosophy of harmon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struggle”. The “theory of harmony originating from Tao” itself experienced the three stages of “theory of harmony, the “theory of harmony originating from Tao” and the “ theory of harmony and similarity originating from Tao” in its development, which not only emphasizes the value of difference but that of similarity, and which is more dialectical and more comprehensive.
Qian Gengsen; the “theory of harmony”; the “theory of harmony originating from Tao”; the “theory of harmony and similarity originating from Tao”
10.3969/j.issn.1673-2065.2015.02.011
B21
A
1673-2065(2015)02-0053-03
2015-01-31
程 潮(1963-),男,安徽枞阳人,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哲学博士。
(责任编校:耿春红 英文校对:杨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