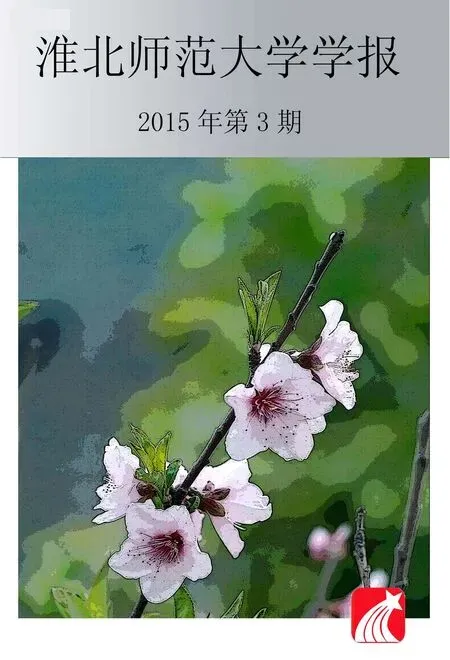曹魏时期的文化典籍整理
2015-03-27魏宏灿
魏 萌,魏宏灿
(阜阳师范学院 a.政法学院;b.学报编辑部,安徽 阜阳 236032)
曹操统一北方后,在加强政权、政治、经济建设的同时,也注重思想文化的整合与重建。曹丕父子传承曹操之遗风,好文学,重视文化建设。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倡导多元化的文化思潮。作为叱咤风云的一代英雄,曹操有意识地综合各类学术文化的合理因素与创造精神,使其互相调节,臻于完善,调和一致,各得其所;立身济世以儒家的道德规范其行为;调节身心吸收道家的艺术精神;治国安邦,采用综核名实、赏罚必信的法术,并有意识地以此思潮引导时代的思想文化观念,向着尚法术好刑名整合。二是鼓励文士们“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1]97倡导建安文士张扬其才艺、个性,展示具有个性精神的文化行为;三是加强文化典籍的整理,通过对文化典籍的结集与编纂,强化文化积累与文化建构。鉴于学术界对前两点论述得较深入,故不赘述。本文仅就曹魏时期的文化典籍整理略作论析。
一
我国整理文化典籍的历史悠久,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开始。《易》《书》《诗》《春秋》都是经过整理的古文献。据《左传》等可知,当时周王室和多国的图书都已经分类收藏。又据《国语》《鲁语》记载,周宣王时宋国大夫正考父曾用周朝太师《商颂》底本校订宋国保存的商代祭祀乐歌,确定以《那》为篇首。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亦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凡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2]这是说《诗经》是由孔子删定编集起来的。“孔子删诗”虽有人不信,但《诗经》经过孔子整理则是学术界一致的看法。此后,西汉刘向曾校阅群书,撰成我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别录》,对文化典籍的整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孔子、刘向整理文化典籍都是个人行为,而作为一种政府行为,曹魏以前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典籍整理之作。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由政府主持的文化典籍的整理则始于曹魏。
文化的整合与重建,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事情,尤其是在经历了汉末大乱之后,社会无序,文化失范,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文化行为游移不定,因而这个时期的文化整合与重建显得更为迫切,也更为艰难。曹魏政权和有社会责任感的文人,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针对社会的需求,面对发生过裂变后的文化,有所为有所不为,展开了积极的探索,加强思想行为规范和文化整合。
曹魏自武帝曹操始,就十分重视文化建设。他先后颁布了《修学令》《求贤令》《整齐风俗令》《举士令》《求逸才令》等一系列和文化构建有关系的政令,使经历了长期战乱的北方广大地区的文化建设迅速得到恢复,并逐步走向正规,为以后的文化构建和文化典籍的整理作了充分的前期舆论准备。《三国志·袁涣传》记载:
魏国初建,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涣言于太祖曰:“今天下大难已除,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以为可大收篇籍,明先圣之教,以易民视听,使海内斐然向风,则远人不服可以文德来之。”太祖善其言。[3]335
曹操接受并采纳了袁涣的建议,文治武功并用。曹操为了从制度上得到保障,更好地开展文化典籍整理工作,还在中央设置秘书令,掌管尚书奏事,兼管图书秘籍。正因为曹操重视文化建设,当他得知老朋友蔡邕之女蔡琰的下落时,便用金璧把她从南匈奴赎回,让她从事古籍整理工作,《后汉书·董祀妻传》所记载的文姬归汉后与曹操的一段对话颇能说明这个问题:
操因问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否?”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载四百余篇耳。”操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妾闻男女有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撰。”[4]2801
由此可知,曹操对文化建构的高度重视。曹操本人文学造诣很深,深知这些珍贵的文化典籍的重要性,所以才不惜重金把一个弱女子从蛮荒之地赎回。
曹丕比乃父曹操更为重视文学和文化在政权建设中的作用。他明确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5]313其又云:“余观贾谊《过秦论》,发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制义,洽以三代之风,润以各人之化。斯可谓作者矣。”[5]314他颁布了《取士不限年诏》《追崇孔子诏》《禁淫祀诏》等,以期加强文化建设。与此同时他还经常“开馆延群士,量酒于斯堂。辩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6]382和邺下文人一起诗酒唱和,切磋诗艺,这对文化的发展与建设起着有益的推动作用。
曹丕代汉自立前,他喜好文学,以著述为务,下笔成章,认为人“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5]283在“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思想指导下,著诗赋百余篇和煌煌巨著《典论》(今仅存《论文》《论方术》)。
曹丕执政后,为了巩固新兴政权,在把注意力放在整顿吏治的同时,也重视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于黄初元年(220)将秘书令改为秘书监,下设校书郎等职,专门从事书籍校刊,订正讹误;命人搜集古代经典文献,藏于秘书内外三阁,并遣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郑默尽职尽责,对官藏典籍进行了认真的整理,“考核旧文,删除浮秽”,用朱紫二笔删定旧文,深得时人称赞。《隋书·牛弘传》引《请开献书之路表》曰:“魏文代汉,更集经典,皆藏在秘书、内外三阁,谴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美其朱紫有别。”[7]182为了宜皇王之省览,曹丕聚集当时著名的文士,编撰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规模浩大的大型类书《皇览》。《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云:“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篇,号曰《皇览》。”[3]88
魏明帝在位时,承其父、祖之遗风,重视文化建设工作,设置崇文馆,召集文士,不仅鼓励他们度诗制曲,而且也倡导整理文化典籍。《三国志·明帝纪》载:“(青龙四年)夏四月,置崇文馆,征善度文者以充之。”[5]608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也称赞这件事:
至明帝纂戎,制诗度曲,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观,何、刘群才,迭相照耀。[8]366
崇文馆的主要成员何晏、刘劭、王肃等人,除了度诗制曲外,还从事古籍整理。
二
曹魏时期,由于统治者的重视,文士和文学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创作的数量和品种增多,客观上也催促了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这个时期的文化典籍整理,成绩显著,较为重要的有三项:一是编纂文化经典,二是注释文化典籍,三是撰著《皇览》,现分论之。
(一)注释典籍
曹操注兵书并作序。其“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3]90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3]54对经传、兵法、诸子、书法、围棋、药理、建筑等都颇为精熟。他对《孙子兵法》十三篇作了整理和注释,并为其作序。其云:
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孙子者齐人也,名武,为吴王阖闾作兵法一十三篇,试之妇人,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后百岁余有孙膑,是武之后也。审计重举,明画深图,不可相诬。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9]7
《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孙盛《异同杂语》也云:
(太祖)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于世 。[3]3
(二)搜集经典
曹丕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认为人“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5]283他经常和文士在一起吟诗作赋,开创了五言腾踊的新局面。此时文学的发展获得了一个相当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文士和文学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文士在积极进取,追求建功立业的同时,“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1]235,创作了许多反映时代生活、表现时代精神、展示时代风貌的作品,使建安时期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的繁荣期。创作数量的剧增,品种的繁富,这些客观条件的具备,也催促着将各类作品编纂成集的产生,而且这种形势变得越来越紧迫了。这时,“自东京以降,讫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10]417在当时的南方即出现了个人结集的事例,《三国志·薛综传》云:
凡所著诗赋雅论数万言,名曰《私载》,又定《五宗图述》、《二京解》,皆传于世。[3]1254
《私载》显然已经结集成书,但仍未以“集”命之,且是薛综自为之。而在北方的曹魏,出现了抄采编集(自编或他编)建安诸子作品为一集的盛举:曹丕于建安二十三年(218)亲自编定陈琳、徐干、刘桢、应玚、繁钦等人文集,并为之作序,著有《繁钦集序》《陈琳集序》《建安诸序》等,为建安诸子诗文的保存和流传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又与吴质书》云: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耶!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5]258
信中“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显然是结集为总集。此信写于建安二十三年(218),由此可知曹丕将诸子诗文编纂为“一集”最迟在此时也。
孔融被曹操处死后,曹丕因深好孔融文章“体气高妙,有过人者”[5]313,曹丕冒着很大的风险以金帛募取孔融文章,“所著诗、颂、碑文、议论、六言、策文、表、檄、教令、书记凡二十五篇”[10]2279,想必也是将其作品撰为一集。南朝诗人谢灵运在《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中透露的这个信息,他各以曹丕、王粲、陈琳、刘桢、应玚、阮瑀、曹植的口吻作诗,由此看来曹丕当年确曾把当时建安诸子邺下聚会的诗歌编为一集,其名曰“邺中集”。黄节先生《谢康乐诗注》引《初学记》所辑《魏文帝集》语:“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玚等同作”,此即邺中侍诗也[11]682。
可见,由曹植、王粲等人所构成的邺中七子,正是《邺中集》的作者群,其作品所以能“都为一集”,乃系魏文帝曹丕于“徐陈应刘一时俱逝”之后,因追往伤今而为者。其集中之作,虽已不可确考,但由于建安诸子朝夕同游共宴,所为之诗文自然形成具有团体特色的时代文风。
曹丕曾将自己的文章汇编成集。他在《与王朗书》中云:
人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雕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百馀篇,集诸儒于肃成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5]283
这里的“论撰”,即含有汇编或编纂之意。曹植也曾将自己的文章汇编成集。其《前录自序》云:“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虽触类而作,然芜秽者众,故删定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13]434这里明白地告诉我们《前录》所收录的的是曹植亲手删定的七十八篇赋,既然说是“前录”,则必有“后录”,可以推测编集的原则是根据文体以类相从。魏明帝在曹植死后于景初年间曾下诏追录曹植遗作结集,《三国志·曹植传》记载了这件事:“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3]576这显然是由后人把曹植生前的作品编撰为集。
应璩曾编撰有《书林》。《隋书·经籍志》云:“应璩《书林》八卷,夏赤松撰。”姚振宗《三国艺文志考证》《隋书·经籍志考证》认为应璩编集,而夏赤松重编。像这种由后人乃至本人收集作品汇聚成帙的编撰现象,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据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征引,当时已出现了不少的文集,如孔融集(见《荀攸传》)、王朗集(见《王朗传》)等,这说明至迟在裴松之以前“都为一集”已有之。
(三)编辑《皇览》
在曹魏时期的文化典籍整理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由众多著名文士编撰的《皇览》。《三国志·文帝纪》云:“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3]883参加编撰《皇览》工作的有缪袭、桓范、王象、刘劭、韦诞等人,历经数载。《三国志·杨俊传》注引《魏略》云:“魏有天下,拜(王)象散骑侍郎,迁为常侍,封列侯。受诏撰《皇览》,使象领秘书监。象从延康元年始撰集,数岁成,藏於秘府,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象既性器和厚,又文采温雅,用是京师归美,称为儒宗。”[3]664
《三国志·曹爽传》注引《魏略》云:
桓范字元则,世为冠族。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为羽林左监。以有文学,与王象等典集《皇览》。[3]290
《三国志·刘劭传》云:
黄初中,为尚书郎、散骑侍郎。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3]618
《御览》引《三国典略》云:
齐主如晋阳尚书右什射珽等上言:“昔魏文帝命韦诞诸人撰著《皇览》,包括群言,区分义别。”[7]183
《史记·五帝本纪》唐司马员索隐曰:
《皇览》,书名也。记先代冢墓之处,宜皇王之省览,故曰《皇览》。是魏人王象、缪袭等所撰也。[7]182
由上述可知,《皇览》始撰于延康元年(220),历经多年的光阴,经多人之手才大功告成。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撰编成规模如此的巨著,实属不易。
此书包括群言,区分义别,为我国古代类书之始,此书的编撰是为了让帝王在日理万机之余能够迅捷简便地了解前代之事,所谓“记先代冢墓之处,宣皇王之省览也”。[7]182
三
曹丕《典论·论文》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将文学视为“三不朽”中“立言”的主要形式,与“经国”並论。因此,建安文士在致力于文学创作的同时,也很注重文献诠释与研究。他们通过对文献的诠释阐述前代思想文化,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因此,曹魏时期文献诠释较之汉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文献诠释已扩展到《诗经》《楚辞》之外的范围更为广泛的文学作品中,哲学经典注释成就尤为突出。
曹魏时代的学术风气受到正在发展的士阶层个体自觉意识的影响,反映到文献诠释中,一反汉代经学支离芜蔓、穿凿附会之诟病,体现出摈落事相、着重大义、发挥己见的精神。在汉代,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不大受人注意的老庄成为玄学思想的依据,一时注家蜂起,原为儒家经典的《周易》《诗经》等,由于包含了大量与道学相通的古代宇宙论和辩证法思想,也成为曹魏文人注释的重点。这类著作盛行于玄学大畅时,作者多为当时的谈玄清议之人,较为著名的有王朗、王肃、王弼、何晏等人。王朗为《春秋》《孝经》《周官》作注,王肃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传》《孔子家语》作注,王弼诠释古代经典,主要有《易经注》《老子经》;何曼阐释经籍主要有《论语集解》等。他们试图贯通儒、道,用道家哲学思想诠释儒学,将儒学纳入玄学的思想体系。因而,除校练名理、著论崇玄之外,诠释儒道经典成为他们表达其思想的有力手段,通过文献诠释构筑自己的玄学思想体系,不仅维护了道学的权威性,提升了老庄的地位,而且也张扬了当时新兴的玄学,使其成为当时文化发展的主导。这种诠释形式,鲜明地揭示出当时人们对玄学这种文化传统的选择,这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此后的文学研究与诠释。
魏曹时期,社会思潮和学术文化思潮都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曹丕将文学看作是“经过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又认为“篇籍”与“立德”同样可以扬名,这开启了整个社会崇文之风,文学成为一项神圣的事业,所以当时作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文学创作、经典诠释和文化事业建设中,许多文士通过各种立言形式,如文学创作、经典诠释等,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与政治理念。这种立言形式,不仅促进了当时的文学发展,推动了文化典籍的整理与诠释,同时文化典籍的诠释对文学的写作又起着指导的作用,这极大地影响着当时学术的发展。学术诠释成为一项具有自己的独立研究对象,将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理论批评视为文学创作的一部分,这个时期的文学研究者同时又是杰出的作家、诗人,甚至是当时文坛领军人物,这有利于将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紧密结合,文学研究不再集中于经典或少数文体,而是包括了前代和当代的各种体裁形类、各种风格的作品,以及不同类型的作家文士力图尽可能全面认识和评价各种文学现象。在整理总结文化典籍和文学创作时,关注当时文学创作的实际,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及整理以理论著称,提出一系列的重要理论问题,产生了诸如《典论》等著作,其中的《论文》就是通过编集建安诸子文章、总结当时文学家的文学创作得失而形成的文学理论著作。对其,张作耀先生作了精辟地评述:
曹丕在编纂七子文集的过程中详细阅读并研究了七子的文词书赋,并加以对比,从而作出了恰当的评价,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学理论。因此可以这样说,七子之文得曹丕之力而流传不失;曹丕因七子之文形成其文学理论。[14]470
这时,文学创作、文化典籍整理互相影响,互相推动,文学的发展促进了文化典籍的编纂整理,文化典籍的整理编纂又推动了文学的发展与自觉。共同构成曹魏文化的辉煌。
[1]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三曹资料汇编[G].北京:中华书局,1980.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魏宏灿.曹丕集校注[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
[6]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7]张可礼.三曹年谱[M].济南:齐鲁书社,1983.
[8]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M].南宁:漓江出版社,1982.
[9]孙子.孙子兵法[M].孙晓玲,编译.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
[10]张溥.汉魏六朝百家传题辞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1]章学诚.文史通义[M].罗炳良,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12]黄节.汉魏六朝诗六种[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13]赵幼文.曹植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4]张作耀.曹操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